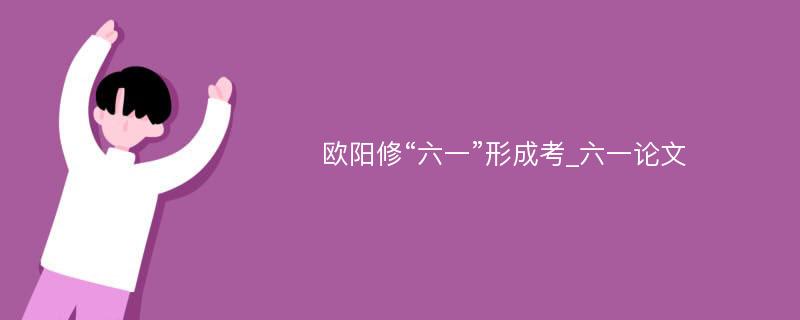
歐陽修“六一”形成考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歐陽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英宗(趙曙,1032-1067)治平三年(1066),歐陽修(1007-1072)首次以“六一居士”之名,自署于其著述之末,時年六十;《集古録跋尾·隋汎愛寺碑》: “李伯藥”字(按:四部叢刊本作李百藥),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倦。治平丙午(三年),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① 歐陽修在碑文跋詞末,連書兩個別號,除了表示對此碑的珍視,似乎亦暗示了這兩個別號在他的生命中的重要意義。② 神宗(趙頊,1048-1085)熙寧三年(1070)九月七日,歐陽修作《六一居士傳》,正式以“六一居士”爲名,作爲他致仕歸隱的表徵: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③ 從四十歲以醉翁——酒與翁自名,到此時的“六一”——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與一老翁,在看似“與此五物偕返于田廬”、“老于此五物之間”歸老于田的自娛外,實展示了歐陽修的文化性格與通脫的人生觀。 二、“六一”定名的過程 (一)“我”爲主體 仁宗(趙禎,1010-1063)天聖九年(1031),歐陽修于錢惟演(977-1034)幕下任西京留守推官,由于錢在文學上的地位與開放寬容的氣度,一時名士皆雲集于其幕下。④歐陽修亦得以廣交文友如謝絳(994-1039)(時任西京通判)、梅堯臣(1002-1060)(時任河南縣主簿)、尹源(996-1045,天聖八年進士)⑤、尹洙(1001-1047)(時以山南東道掌書記知河南府)、富弼(1004-1082)(河陽簽書判官)、楊愈(字子聰,時任戶曹參軍)、王復(字幾道)等一批年輕文士。日爲古文歌詩,游宴吟咏,極一時之樂。如《七交七首》分別吟咏伊洛時期的六位知己,表現朋友間的相知相契;其中《七交七首·自叙》除了是詩酒文會的實録,亦是歐陽修生活情趣的自我表露: 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⑥ “飲德”二句,說明了良朋益友的薰陶,猶如飲醇美之酒,佩芳馨之蘭蕙;“平時”二句則忠實地記録了在吏事閑暇之餘,飲酒賦詩好友歡會的場景。 明道元年(1032),西京幕府諸君子仿白居易(772-846)晚年居洛時“香山九老會”之興⑦,而有“八老”之稱。“八老”分別爲尹洙辯老、楊愈俊老、王顧慧老、王復循老、張汝士晦老、張先默老、梅堯臣懿老、歐陽修逸老。歐陽修非常重視八老的品題,曾先後致書梅堯臣,以爲“八老之名,誠一時之美事”⑧,並依據儒家經典對“七老”之名分別加以解釋。但對于衆人所封“逸老”之名,歐陽修則是“苦求”力辯,自請更名爲“達老”。《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三: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⑨ 而據《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知經其“力請更名”後,已得“達老”之名。而此亦是歐陽修一生中所使用的第一個別號。不論是《七交七首·自叙》或是《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以及同時期所作《戲書拜呈學士三丈(謝絳)》中“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⑩、或“一枰閑且伴衰翁”(11)均可以清楚地看出“醉酒”與“翁”緊緊相隨的密切結合。而這數首詩,似乎亦預示了“醉翁”這一別號淵源之所自。 (二)“酒”、“我” 慶曆五年(1045)八月,因諫官錢明逸、開封知府楊日嚴等構陷,興“張甥案”,歐陽修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以知制誥出知滁州(今安徽滁縣)。(12) 謫貶滁州的歐陽修,收束起遇事即極力抗辯的稜嶒風骨,將生命的重心逍遙“閑放”于山水之間。對歐陽修而言,自年少時期醉酒放歌的爛漫情懷,至貶謫夷陵時携酒訪勝(13),酒始終是詩人生活的重心。不同于早年以詩酒吟放之青春漫浪,年方四十的歐陽修,此時以“醉翁”自名,《醉翁亭記》: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14) “翁”字表達了在經歷景祐以來一連串政治變化後,心理的了悟與自解;(15)而酒亦成爲他放意林泉,達致山水之樂的重要媒介: 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溪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唤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16) 好酒能銷光景,酒不僅是歐陽修對宦途憂戚的一種超越,亦是山花遣情的良伴: 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17) 相較于地僻處遠的夷陵,愁烟苦霧少芳菲(18)、二月山城猶未見花的惡劣環境(19),滁州時期的歐陽修由衷地接受了窮山絶水下拙樸的春色,誠摯地發出對山桃溪杏,古妝野態美的喜愛。《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 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時節開春風。 看花游女不知醜,古妝野態争花紅。 人生行樂在勉强,有酒莫負琉璃鍾。 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20) 詩人以達觀有情的心境,不拘形迹的方式,體驗著以山水爲樂的謫宦生活。其視醜、拙如一,無私的人生觀,亦正爲“有酒人生何不樂”的重要原動力。(21) (三)“山水”、“酒”、“我” 如果說夷陵的山水是唤起歐陽修膠固的心靈,使之與自然冥契的一個萌發,那麽滁州時期的歐陽修則是點染了山水,使山水增添了人文的色彩,凸顯于後世讀者的心目中。 景祐三年(1036)歐陽修爲范仲淹言事忤宰相(呂夷簡,979-1044)事而申辯,並切責高若訥(997-1055)身爲言事之官,不能爲范辯其非辜,反從而詆之,懦軟屈曲之行徑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22),因此坐貶爲夷陵縣令。(23)夷陵(今湖北宜昌縣)屬峽州(24),位于楚之西境,地僻而貧,民俗儉陋,自古以來便有“蠻荆”之稱。以交通而言,若取水道至汴京,有五千五百九十里,陸行則需經二十八驛,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居者往往不得代”,甚或有“歲滿,自罷去”的狀况。(25)遠謫惡地,歐陽修不僅不以爲窮僻,反而視夷陵“江山美秀,邑居繕完,無不可愛”。非僅有罪者可以忘憂,亦深信“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26)夷陵的山水點染了歐陽修,重新唤起他對山水的熱情,所作《夷陵縣至喜堂記》不僅是歐陽修山水諸作的起點,亦記録了他的參與,和參與之後的喜悅。 滁州時期的歐陽修對山水的熱愛,更是有增無減。除了爲智僊所建之“醉翁亭”命名之外,更爲了能“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而構築“豐樂亭”,《與韓忠獻王稚圭(琦)》四十五通其四: 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于泉側。(27) 《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十九亦同: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28) 歐陽修將自己對外在世界的觀照與內在情緒的排遣,做出了理性的融釋,並將個人欣賞山水的樂趣擴大爲“與郡人同樂”,同時將山水之樂與禽鳥之樂、太守之樂相互糅合,從而變得更爲理智、寬容。山水與歐合而爲一,山水儼然已成爲歐陽修生命的一部份了。 (四)“書”、“山水”、“酒”、“我” 謫處于窮山荒僻中的歐陽修,藉自放于山顛水涯,以表達他歸真返璞的精神追求,同時亦藉生活中尋常的依伴以建構他的心靈世界。《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十八: 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静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29) 山城寂寞,復以滁令職閑事少,書成爲詩人謫處幽居的唯二良伴;書中淡泊至味的豐富內藴,亦是詩人忘憂遣懷的最佳良方。《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 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嘆。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 惟尋舊讀書,簡編多朽斷。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間。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煉。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30) 詩作于嘉祐六年(1061)冬,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在浮沉宦海後,回顧其平生讀書的歷程:少年讀書是希求功名,知其苦而不知其樂;官職升遷後,隨俗學庶務,則無暇讀書;中年在經歷了紛華如浮雲的短暫易散後,才領會書中淡泊的真趣。不惟是至寶,同時亦能經得起時間如百煉般的考驗。全詩詳盡的叙述了歐陽修自少至老,一生喜讀書的癖好,其暮年所作對一生的總括“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31)正足以說明除了酒之外,“書”所帶給歐陽修有形與無形的富足,于其生命中的重要性。 (五)“琴”、“書”、“山水”、“酒”、“我” 滁州郡事之餘,歐陽修除了“勤讀書”以豐富他的精神天地外,“琴”亦是詩人安貧寫志的良友之一,《游瑯琊山》: 行歌招野叟,其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磐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琴寫幽泉。(32) 詩中刻畫了太守與林叟山游之樂,醒聆幽泉,醉臥磐石。而“幽泉之響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每把酒欣然忘歸”(33),携琴寫泉語,不獨是職事之餘山居之樂,同時亦標誌著智者志在高山流水的幽雅情懷。又如《幽谷晚飲》: 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峥嶸。 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 安得白玉琴,寫以朱絲繩。(34) 顯示歐陽修不獨知音律,其對名琴的玩好,亦有著深深的向往。 歐陽修嘗自言對琴曲的喜愛,始于年少時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35)出仕爲宦後,因著各個階段不同的機緣,歐陽修有了自己的琴,並開始收集,《書琴阮記後》: 同年孫植,雅善琴阮,云于京師常賣人處買得之以遺余,蓋景祐三年(1036)也。迨今三十餘年,而植物故亦二十年矣。(36) 孫植所贈琴,應爲歐陽修所有之第一張琴。其後官愈高而琴亦愈多,價更貴重: 余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幾,蓋常琴也。後做舍人,又得琴一張,乃張越琴也。後做學士,又得琴一張,則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陵时,青山緑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萧然自釋。及做舍人、學士,日奔走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盈前,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適,無弦可也。(37) 歐陽修任夷陵令在景祐三年十月至四年十二月,劉幾(1008-?)贈琴當在此段時間中。(38)如此,或爲歐陽修生平第二張琴。至于張越琴,則得于慶曆八年閏正月爲起居舍人後;據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載“聚星堂燕集事”在皇祐二年正月,其中有“劉原父(攽)得張越琴”(39),知歐陽修得張越琴在慶曆八年至皇祐元年間(1048-1049)。而雷琴,應即爲《六一詩話》所記雷會所斲之琴: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于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绝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傳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40) 蘇軾以返京途中所獲蠻布弓衣相贈,事在嘉祐五年(1060)(41),以綉有梅詩之蠻布弓衣爲琴囊,足見歐陽修對雷琴之珍寶。張越琴、雷琴並樓則琴,遂有“三琴”之名。歐陽修《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 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42) 關于樓則琴(石暉)之來源,歐陽修《試筆·琴枕說》云:“吾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臠,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43)歐陽修爲手指所苦在嘉祐二年(1057)(44),故自嘉祐二年上數二十年,得樓則琴約在寶元元年(1038)左右之際,或即劉幾所贈之常琴。石暉琴以“照之無光,惟目昏者爲便”(45),宜于老人夜視,又可導氣之鬱滯,故得以常伴左右。歐陽修並言“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可知其對琴的價值觀不在于物價的貴重,“若有以自適,無弦可也”。自適在心不在物,琴既是釋俗累之物,則所重在趣,撫琴的關鍵不在琴而在于人,只要心領神會,即使是無弦之琴也能釋放心靈。 “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46)意在蕭然自釋的人生觀,豐富了滁州生活的內容,《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二十:“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47)顯見琴亦成爲歐陽修于書、酒、山水之外,生命的有機元素之一。 (六)“棋”、“琴”、“書”、“山水”、“酒”、“我” 作爲文人自營一方天地的閑適之趣,“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棋可對弈,亦可獨弈,對弈是人我間意念的交流,而獨弈更常是沉思静慮、澡雪精神的良方之一。歐陽修視棋爲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始于貶謫夷陵期間,《新開棋軒呈(丁)元珍、(朱)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間與世遠,鳥語知境静。 春光靄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籟心,于此一枰競。(48) 詩作于景祐四年(1037)初春;所謂“新開棋軒”指的是歐陽修于夷陵縣府內新闢一間小屋專供弈棋之所,詩人特別賦詩邀丁寶臣(字元珍,時任峽州軍事判官1010-1067)、朱處仁(字表臣,時任峽州軍事推官)在春光鳥語中對弈。丁、朱二人與歐陽修于職事之暇,常相過從,詩酒漫游。(49)山寒未去,春光微興,本即是一片境静,夷陵“山城寂寞少嘉客”(50),更凸顯身處静境中的孤寂。歐陽修將自己的塵心俗念濾化于棋局中,亦在無語的棋局世界裡,寄托自己與世無競的思考所得。“新開棋軒”是職暇與二三好友娛情遣興、自足自樂的小小世界,亦是詩人視“棋”可以澄心静慮,感悟萬念的明顯表徵。《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時掃濃陰北窗下,一枰閑且伴衰翁。(51) 詩人特地親手栽植楠樹二棵于邑居之旁,想像著日後在北窗下濃密的楠蔭中,與好友對弈的閑趣。住處四圍不取芳菲而獨擇嘉木,只爲嘉樹緑蔭可助弈棋之樂,亦無怪歐陽修名所居之廳室爲“至喜”也。 (七)“《集古録》一千卷”、“棋”、“琴”、“書”、“山水”、“酒”、“我” 從歐陽修與梅聖俞的書簡中“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可以看出“六一”之物在滁州時期已初具雛型。嘉祐七年(1062)歐陽修所編《集古録》一千卷成帙;自動念集古到編成千卷,其間歷時十八年。《集古録目·序》: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 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于多聞。(52) 又《與蔡君謨(襄)求書〈集古録序〉書》: 曏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五年1045),逮嘉祐壬寅(七年1062),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 竊復自念,好嗜與俗异馳,乃得區區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53) 不論是性嗜古的趨動,或是基于“可與史傳正其闕謬”求真的學術理念,十八年的集古歷程,都可以說明歐陽修“顓一”的性格特質。亦因爲長達十八年的時間,無論是“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均無一日或忘,收拾世人之所弃的舉動,與其仕宦生涯緊密結合,實爲其生命歷程中一段重要的烙記。 歐陽修嘗自言對金石銘文的關注,由來已久,《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並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54) 又據歐陽發(1040-1089)〈先公事迹〉所記,歐陽修四歲即孤,家貧無資,故母鄭氏(981-1052)“以荻畫地,教以書字”(55),直至十歲左右,才得虞世南碑帖以學書。(56)集古之念的萌發,更確切一點的說,也許早在天聖四年時即已種下,《後漢樊常侍碑》: 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録》。 一方面源于幼時家貧物資匱乏的補償心理(57),一方面有感于幼時所習碑帖不過二十餘年,即已殘缺,遂興收拾世人所弃之念。歐陽修將所有的碑刻拓本進行裱製,裝訂成册,並爲這些銘文撰寫跋尾,或補史實之闕(58),或正史載之謬(59),或以鑑賞家的角度贊賞法書之美(60),或寄寓對人事代謝、往來古今的興嘆(61),成爲一種帶有多角度性——史學、藝術、文學的思索,和多樣性表達方式——嚴肅、鑑賞、感懷的學術記録。其對集古的重視,開啓了金石學研究的領域;(62)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復艱于執筆,《集古録》一千卷,正可作爲來年歸老銷日的最佳賞玩。(63) 三、“山水”未得預于“六一”之故 從景祐元年(1034)“予號達老”,以“自我”爲主體,到慶曆六年(1046)別號“醉翁”,歐陽修在“我”之外,增添了第一個外物——酒。“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與酒同時,“山水”亦成爲歐陽修閑適自娛的第二個憑藉。而山居歲月,讀書飲射,以琴做枕,(64)更是蕭然自釋所憑之物三與四也。故“六一”之名雖遲至熙寧三年方提出,實則酒、棋、山水、琴、書等物,早在謫貶滁州以前,便逐漸進入歐公的生活中,成爲生命的一部份。 對照于“六一”中的“五物”,滁州時期所賴以自適的“山水”,是唯一未得列入的項目;從明道元年(1032)所記“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65)全心全意領受大自然的脉息,到晚年自言“須知我是愛山者”(66),歐陽修的詩歌中,幾乎無一不說山水。山水既于其生命情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却不敵他物未得預于“六一”中,其間原因除前述《集古録》爲歐公畢生志趣之所向外,復可據歐公對山水的態度略得一二。《西湖念語》: 美景良辰,固多于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于閑人。并游或結于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暂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咏。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于無人。乃知偶來常勝于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于己有,其得已多。(67) 對傳統的文士墨客而言,山水本即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山水不僅是游息的場所,亦是精神安頓、心靈歸屬,回歸自我的完全天地。性喜山水幽趣的歐陽修,于其仕宦生涯中,約有二十四年的時間與雲山泉石爲伴。(68)不同于前人的是,歐陽修並不如[晋]謝靈運(385-433)般必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艱辛的尋訪(69),亦不像宗炳(375-443)將山水圖繪于俯仰屈伸的私我空間中,臥游即足。更不像白居易(772-846)(履道園)(70)、司馬光(1019-1086)(獨樂園)(71)、許元(989-1057)(南園、東園)等(72),將大自然具體而微的構築在人工營造的小小園林之內;以園林借代山水,既得閑静自適之樂,又不必舟車勞苦,又可展示個人生活美學的品味。 歐陽修並不將山水納爲私我所有,在詩人的眼中,山水雖爲我而設,但亦爲衆人所設。自然界所有的一山一水,都是開放的、静默地、無私地展示著它的佳美,雖“富貴者亦不可能盡得其全”,但對貧賤之士而言,卻“可以自足而高世”。(73)在興來獨往的所得中,歐陽修領略到大自然所給予個體精神世界的清滌與滋潤,其焕發于山水美賞所得到的提昇與貞定,撑持著他以曠達的態度,化解著生命中的每一個憂患。所得既多,故是否爲我所擁有已不再重要,既得之于無私之天地,亦當還于天地中,與衆人共享。 值得玩味的是,與《六一居士傳》寫作的同時,歐陽修并作《續思潁詩序》一文,表露他對潁州山水的眷念與歸老于潁的决心: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颍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遂漁钓,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强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须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颍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時年五十有二。 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時,而獲償于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74) 從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樂潁州山水之勝,慨然有終焉之志,到熙寧三年(1070)仍念茲在茲,歐陽修拳拳于潁者,實非一日。二文既同時于一天作成,似乎亦暗示了“己一老翁”一方面得以悠游于山水中,一方面又有著五物的玩好,精神與物質兼得的歸田之樂。 四、結語:與“五”爲“六”,居士隱矣 琴、棋、書、酒,本即是生活中尋常之物,亦是傳統文人在閑居之時具有普遍性的遣情之物,故自歐公提出六一具體內容後,其中除“《集古録》一千卷”爲常人能力所不及外,其餘四者實與傳統無异,並無特殊之處。透過對歐公作品的爬梳,吾人卻得以見出“琴、棋、書、酒”四者,于歐陽修的生命歷程中,不僅由來已久,同時更具有階段性的意義。至于“六一”之名靈感所自,就學界現行研究而觀,大抵采“得自于南楚馬希範(899-947)‘九龍殿’——八龍加一”之說;(75)實則在生活情趣,乃至于玩好的喜愛上,歐公所受白居易的影響,可能較諸馬希範更爲明顯。白居易《池上篇·并序》: 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廪。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 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摺腰菱、青板舫以歸…… 弘農楊貞一(歸厚)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也。(76) 從臺池、書、琴、酒的費心建置到天竺石一、華亭鶴二、青石三的艱辛羅致,白居易將所好玩物,全部建構于精心擘畫的一方小園中,他展示了小園從無到有,經營的不易,亦向世人宣示了對所有之物的擁有主權。開成三年(838)白居易正式提出“醉吟先生”一名: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千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77) 白居易以六十七歲“不才之身”,耽玩于酒、琴、詩三者之中得爲“四”,其“爲主”的自得與“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78)的自足意識表露無遺。 歐陽修一生得益于山水的啓發至多,不論是謫處夷陵或是貶居滁州,詩人在寂寞千山中,體察出山泉花鳥的生機與活力,以樂觀的態度,處逆若順。復將對外在世界的觀照與山民共樂,其寬闊無私的行誼,較諸晚年的白居易自足于私人天地的生活型態,更見通達。對于自己尚須“待”五“物”方能成就歸老之樂,歐陽修有著清楚的自我認知: 內樂猶有待于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异”,宜爲有道者所笑也。(79) 事實上,詩人所要銘刻的不只有五物之名,他更標誌了五物于其一生中的不可分割性“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他回歸了一個更加符合自己個性、趣味的天地;走出官場,離開紛擾。安静地在萬卷書香裡回到一個讀書人最純粹的快樂,在千卷金石遺文中體驗出入古今的智慧與愉悅,在悠揚的琴音裡感受平和寧静,在棋局的對弈中化解世事不過如棋的興嘆。展示了“?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80)五物合一,返回本我的决心。如此看來,歐陽修生活的情調和對玩好的珍視,雖源自于白居易甚多,實則卻執行的比白居易更爲徹底,亦更見勝于白的理智與通脫。 ①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冊五,卷一三八,頁2185。 又,孟饗者,帝王宗廟祭禮。因于每年的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舉行,故稱。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序》:“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饗。”吴自牧《夢粱録·七月》:“七月孟秋,例于上旬內車駕詣景靈宫,行孟饗之禮。”治平三年七月,英宗薦饗太廟,時歐陽修攝太尉行事。 南譙,爲滁州之舊名;據樂史(930-1007)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六》:“隋開皇九年,廢新昌郡,改南譙州爲滁州,因水爲名。”(北京:中華書局,2007),册六,卷一二八,頁2524。 ②在《集古録跋尾》中,同樣署明“治平丙午(三年)作”之碑文跋,尚有《唐明禪師碑》“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顯係與《隋汎愛寺碑》寫作時間相近,但歐陽修自署並未稱“六一居士”。其後治平四、五年各有作《黄庭經三》、《後漢碑陰題名》,亦未自稱“六一居士”。 ③見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冊中,卷四十四,頁1130。熙寧三年(1070)作。 ④歐陽修《送徐生之澠池》:“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五,頁145。至和元年(1054)作。是年徐無黨赴澠池任職。 ⑤尹源生卒年乃據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推得;歐文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1一,頁829。 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一,頁1259。天聖九年(1031)作。 ⑦白居易《九老圖詩》并序:“會昌五年(845)三月,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貞)、張(渾)等六賢于束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按爲李元爽、僧如滿),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名,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詩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外集·詩文補遺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六,卷上,頁3861。 ⑧歐陽修《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二;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九,頁2444。 ⑨同上。又梅聖俞來簡今不存。 ⑩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一,頁1270。明道元年、二年間(1032、1033)作。 (11)《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6。景祐四年(1037)作。 (12)據《通鑑長編》卷一五七:“(慶曆五年)八月甲戌(二十一日),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修爲知制誥,知滁州。”;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冊三一六,頁545。 其南行路徑爲自河北取道水路,至汴河南下赴滁。初入汴河作《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雁》,十月二十二日至郡,有《滁州謝上表》。謝表見《歐陽修全集》,冊四,卷九○,頁1321。 (13)歐陽修《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問鄰翁”;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9。表臣,朱處仁字。 (14)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九,頁1020。 (15)四十歲即稱“翁”,于歐陽修而言,當然不完全是指體貌的老邁,而是借酒澆愁的自我書寫,其《贈沈遵》即自道“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贈沈博士(遵)歌》亦云“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都表明了“時尚彊力”的責况。二詩分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頁162、181。 又,沈遵,束陽人,通音樂,官太常博士,曾任太和縣令。嘉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據王安石《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行前與歐陽修、梅聖俞在京師邂逅相遇,梅有《送建州通判沈太博》。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八:“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僊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遣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絶,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一,頁423。 (16)《贈沈遵》;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上,卷六,頁162。嘉祐元年(1056)作。 (17)《謝判官(縝)幽谷種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36。慶曆七年(1047)春作。 又,謝縝,字通微,爲謝絳從兄弟、梅聖俞內弟。梅本年有作《方在許吕幕,內弟滁州謝判官有書邀予詩送,近聞歐陽永叔移守此郡,爲我寄聲也》。幽谷,據歐陽修《與韓忠獻王稚圭》第四簡:“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于泉側……”幽谷即水泉出處。文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中,卷三九,頁1017。 (18)《千葉紅梨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一,頁13。作于景祐四年(1037)春。 (19)《贈答元珍》;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一,頁317。作于景祐四年(1037)春。 (20)《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88。 (21)《新霜二首》其一;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86。慶曆六年(1046)作。 (22)歐陽修《與高司諫書》;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七,頁1785。 (23)據胡柯譜:“景祐三年,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忤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二十一日),降爲峽州夷陵縣令。十月至夷陵。”;譜見《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一》《歐陽修年譜》,冊六,頁2599。 又,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傳見宋祁《景文集》卷六○《高觀文墓誌銘》。 (24)王存《元豐九域志·荆湖北路》:“峽州,夷陵郡,軍事。治縣四:夷陵、宜都、長陽、遠安。”(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六,頁271。 (25)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九,頁995。景祐三年(1036)作。 (26)出處頁數同上。 (27)見《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四,頁2344。 (28)同上,頁2453。 (29)《歐陽修全集》,卷一四九,頁2453。 (30)《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九,頁245。嘉祐六年(1061)作。 (31)歐陽修《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琦)二首》其一;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七,頁1514。熙寧五年(1072)作。 (3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三,頁68。慶曆六年(1046)作。 (33)見蘇軾《黄州》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他集互見古今體詩四十七首》,冊八,卷四十九,頁2703。 (34)《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三,頁1352。慶曆六年(1046)作。 (35)歐陽修《三琴記》;《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三,頁1698。嘉祐七年(1062)三月四日作。 又,《小流水曲》即《流水曲》,古琴曲名。琴音多樣,有急緩高低,亦有高山流水,聖人既能寓志,忠臣亦可抒怨,故所嗜琴曲的不同,實代表了個人心理的傾向。歐陽修喜《小流水曲》或可反映其一生嗜愛山水的心理。 (36)見《歐陽修全集·補佚卷二》,冊六,卷一五五,頁2575。熙寧二年(1069)二月作。 按:孫植生平履歷不詳,據歐公所言,知同爲天聖八年進士及第之年友。且據歐公自署跋文成于熙寧二年,上數二十年,知孫植應卒于皇祐二年(1050)。 (37)同上。 (38)按:劉幾(1008—1088),字伯壽,號玉華庵主,洛陽人;温叟孫,深曉音律。爲司馬光“洛中耆英會”十三人之一,(事在元豐五年1082)時年七十五。神宗時以祕書監致仕,隱居嵩山玉華峰下。哲宗元祐三年卒,年八十一。 (39)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一四七九,頁17。 (40)見歐陽修《六一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156。 (41)參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37。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嘉祐五年”條下則未載此事。 (4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十三,頁1698。嘉祐七年(1062)作。 (43)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册五,卷一三○,頁1976。 (44)歐陽修《與梅聖俞》四十六通其三十八:“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于筆研而欲息之邪?”又《答張學士》四通其一亦同:“某以嘗患兩手中指孿搐,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分見《歐陽修全集》,冊六,頁2461、2493。嘉祐二年(1057)作。 (45)《琴枕說》;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頁1976。 (46)歐陽修《贈無爲軍李道士(景仙)二首》其一;《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四,頁97。慶曆七年(1047)作。 (47)見《歐陽修全集》,冊六,卷一四九,頁2454。慶曆七年作。 (48)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冊下,卷二,頁1304。景祐四年(1037)作。 (49)歐陽修《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有“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之句(景祐三年冬作),後歐陽修任光化軍乾德縣令有《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詩,深情地回憶夷陵山水風物與二人的懷念。二詩分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册上,卷十一,頁315、323。 (50)歐陽修《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出處同上,頁314。 (51)出處同上,頁316。景祐四年作。 (52)《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一,頁1060。 (53)同上,册下,卷十九,頁1847。 (54)《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二,頁2187。嘉祐八年(1063)九月二十九日作。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繫學書事在十歲時。 (55)歐陽發(1040—1089)《先公事迹》;見《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627。 (56)歐陽修學書之齡參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頁21。 (57)關于“嗜好”的心理,王國維先生《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以爲一方面是消遣時間,一方面是排遣情緒;責則嗜好的產生,有時是基于“缺乏”的補償心理。黄啟方先生《漫談嗜好》即指出“至于像歐陽修的好集碑帖銘文,則或是一種淵源有自的補償要求……歐陽修的啟蒙教育,是由他的母親用蘆荻的莖桿在沙地上教他學寫字開始的。別人家的小孩都可以有筆有紙,唯獨歐陽修没有,幼年時期的這種極爲深刻的印象,必然給了他極大的影響。所以一旦他功成名就,希望在業餘也有一個寄托精神的東西時,‘字’就首先浮現出來……不管是古文奇字,或篆隸八分,凡是寫的或刻的字,就都成了他收集的對象”;詳參方和《漫談嗜好》;《古今文選注》冊八,臺北:國語日報社,1977年6月,新第三九九期,總頁2370。 (58)如《後漢而岳華山廟碑》;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五,頁2111。 (59)如《唐田弘正家廟碑》;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一,頁2270。 (60)如《唐颜魯公二十二字帖》;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一,頁2261。 (61)如《唐華岳題名》;見《歐陽修全集》《集古録跋尾》,册五,卷一三九,頁2216。 (62)朱熹《題歐公金石録序真迹》:“集録金石,于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見《晦庵先生朱文公全集》卷八二。 (63)《雜法帖六》之六:“老年病日,不能讀書,又艱于執筆,惟此與《集古録》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潁銷日之樂也。”;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三,頁2316。 (64)歐陽修《彈琴效賈島體》:“橫琴置床頭,當午曝背眠”;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四,頁100。慶曆七年(1047)作。 (65)《游龍門分題十五首·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一,頁5。 (66)《留題南樓二絕》其一:“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上,卷十四,頁465。熙寧二年(1069)作。 (67)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三三,頁2056。 (68)按:倘以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返京述職爲界,則自天聖九年(1031)爲西京留守推官至此共二十四年。 (69)沈約(441-513)《宋書·謝靈運傳》;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附録一》(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523-524。 (70)長慶四年(824)秋,白居易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買洛陽履道里楊憑故宅,是爲履道園。參謝思煒點校《白居易詩集校注附録》《白居易年譜簡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冊六,頁16。 (71)熙寧六年(1073)時司馬光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闢以爲園,以“獨樂”名之,並有《獨樂園記》。參見顧棟高撰《司馬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71。 (72)參歐陽修《海陵許氏南園記》、《真州束園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頁1026~1030。分作于慶曆八年(1048)、皇祐三年(1051)。 又,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歐陽修有《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三十三,頁870。嘉祐二年(1057)作。 (73)歐陽修《浮槎山水記》;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頁1031。嘉祐三年(1058)作。 (74)《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冊中,卷四十四,頁1124。 (75)如《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六一居士傳》,册中,卷四十四,頁1132。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録》亦同。 (76)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六,卷六十九,頁3705~3706。太和三年(829)作。 (77)白居易《醉吟先生傳》;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冊六,卷七十,頁3782。 (78)《池上篇·并序》 (79)《雜法帖六》之六;見《歐陽修全集》,冊五,卷一四三,頁2316。 又,韓愈《與大顛師書》:“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缚。苟非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异。”與歐之引文略有出入。韓文見《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冊七,卷三二,頁3116。元和十四年(819)作。 (80)蘇軾《書〈六一居士傳〉後》;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冊五,卷六十六,頁2048。标签:六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