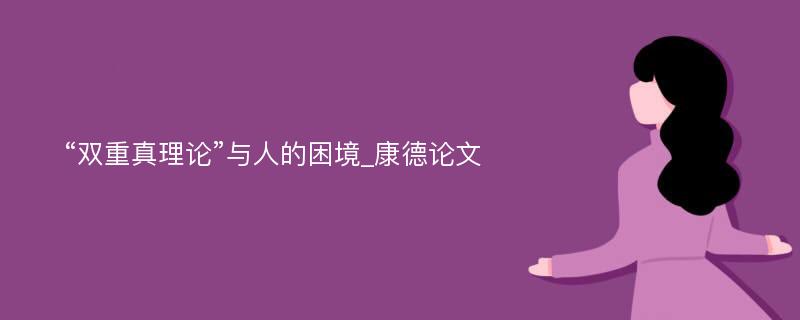
“两重真理说”与人类两难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境论文,真理论文,两重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和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之间历来存在着矛盾。近代以来科学战胜了宗教,但二者矛盾并没有解决,相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冲击下,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信仰、道德却陷入困境,当代社会发展已处在科学与信仰、科学与道德尖锐对立的两难境地。出于对这种两难处境的感悟,笔者以为西方哲学史上提出的“两重真理说”是很有意义的,重新分析和阐释这个学说,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性质、矛盾处境以及未来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两重真理说”是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路西德最早提出的,其后西格尔、邓斯·司各脱、奥卡姆和弗兰西斯·培根等也都有同样主张。这一学说对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两重真理说”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是说同一真理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表述,既可以采用哲学或科学的理性形式,也可以采用神学的信仰的形式来表现;其二是说有两种不同来源的真理同时存在,从经验和实验中得来的是科学的真理,从信仰或“启示”中得来的是神学的真理,二者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这后一种含义在伊本·路西德本人思想中还不十分明确,而为欧洲的后继者所大力发挥。上述两方面含义并不矛盾,只有承认真理有两重表现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出有两种真理并存。从一般意义上看,“两重真理说”也就是承认真理有两重性,真理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科学和宗教都分别地相对地占有真理,但分开来说都不能绝对地占有真理。
现行的一些西方哲学史教材和论著以及《辞海·哲学》册在对“两重真理说”的解释中都认为,它的提出是为了使哲学和科学不受宗教的约束,因此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作用;而利用此说认为宗教和科学同样都是真理,就是为宗教信仰辩护,就是反科学的观点。(注:见《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 页“双重真理”条目;参见《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该书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0—201页;又见《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127页。)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这一学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理论意义。我们应将这一学说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它的提出虽有特殊历史背景,但也有一般理论意义。正是它的一般理论意义和内涵,在今天具有重要启发作用,是我们应该着重加以认识和阐释的。
2
“两重真理说”的深刻意义就是提出了真理的两重性问题,就是启示人们要在科学同宗教的辩证关系中去寻找和确立真理。“两重真理说”的启示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是否代表着真理因而能否绝对地占有真理?宗教和以宗教为象征的精神信仰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是否也具有根本意义?如果真理发展具有矛盾两重性,那么宗教信仰是否也代表着真理发展的一个方面,代表着人类进步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向?质言之,如果真理具有两重性,那么科学是否能代替信仰?在科学之外或在科学之后是否确实应该保持信仰的领域?
我们知道,科学和宗教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科学的功能是认知,是依靠经验来认识、解释自然,属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而宗教和道德的功能则是依靠精神上的信仰和教化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属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或者说,科学的本质是现实,其机理是不可穷尽的自然原理,其目的是解决认识的“合规律性”问题;而宗教或道德的本质却是理想,其机理是超越必然的自由原理,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合目的性”或“合理性”问题。把科学和宗教、科学和道德分开,划清知识与信仰的界限,并实际上承认作为“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研究对象的超经验的精神本体、信仰和道德高于“形而下”领域的具体的工艺、科学,这正是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最重要的传统思想之一,也是近代西方自康德以来在学术思想上所阐发的最重要的思想认识。现代社会的理论与人生误区,也正在于颠倒了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东西的关系,把工具理性当作价值理性,或把价值理性降到工具理性来看待,而否认了信仰与道德作为价值理性本身存在的意义。今天,人们把现实中的物质享受、感官享乐、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有限的存在都当作了人生理想和价值本身来追求,而科学技术的成果又在其可能的限度内助长着这种追求,这就加重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依靠理性的批判逐步战胜了宗教,并逐渐成为推动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但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负面效应也使社会日益陷入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困境与危机。当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的影响下,人类社会已陷入下述“双重危机”:
首先,全球生态危机。这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外部环境危机。大气污染、能源短缺、水质恶化、土壤沙漠化、生物物种涉濒临灭绝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之核爆炸、核泄漏的威胁,流行性病毒扩散的威胁,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种环境危机,这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是人类在科学几百年的胜利进军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反自然”立场的结果。
其次,道德——信仰危机。这是在人与人自身的社会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在的、内心的危机。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物质产品日益丰富之时,人类在道德、信仰上却日益退化,内心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在道德上日益丧失自我约束的机制和客观有效的善恶标准,于是,各种不道德、反道德、反信仰的思想与行为泛滥。例如,文学、艺术、影视、体育、教育、司法等领域一向被视为“高雅”、“神圣”的领域,而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领域都无不被金钱所污染,连“奥林匹克精神”也不能幸免,以至在今日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净土”。同时,各种职业道德、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不断下滑,诸如性解放、同性恋、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暴力犯罪、拐卖人口、黑手党等等问题层出不穷。整个人类似乎已过于“物化”,也过于“老化”,过于经济与实用,乃至普遍缺乏道德、缺乏信仰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说,这是人性与人心的危机,是人类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采取“反信仰”立场的结果。
科学和道德、科学和信仰作为两个有区别的领域,当然不会完全同步发展,但要保持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水平,就必须同时使人类的道德水准也保持在一个很高水平上,否则二者的矛盾必然尖锐化而引发各方面的冲突。当代社会的现实是,科学的急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提高,相反却出现了道德与信仰的滑坡。在当代科学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德伦理问题,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冲击、动摇了人类生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道德观念和信仰。如果人类的道德、信仰都被摧毁了,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人在没有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就会为所欲为,其结果必然是道德滑坡、社会风气腐败和蜕变。
还应看到,上述两重危机的产生还有着更深刻的根源。长期以来,人们在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执著地追求个人物质享受的自私、贪婪的特性,这种特性在近代几百年工业社会中进一步膨胀起来,实际上,这就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这种以追求物质享受为要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对自然的关系上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其立场必然是“反自然”的;而在对他人的关系上必然是个人中心主义,其立场也必然是反信仰、反道德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这首先是人类在道义上的一个误区。(注: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笔者不敢苟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议论,因为人类早已在这个“中心”之中了。问题还在于,人类也难以“走出”这个中心。这是一个悖论: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工具合理性”即“形式的合理性”,但不具有“价值合理性”即“实质的合理性”。所以,只能说,这是人类在道义上的一个误区。人类应该走出这个误区。)随着近代科学战胜宗教,人类成为自己的“中心”、“主宰”,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人类不再敬畏和信仰上帝、自然,而是产生出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崇拜,实际上就是形成自我崇拜,人自己就是上帝,就是信仰的对象。“上帝死了”,人自己就成为上帝,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类就以为自己能控制一切,有权统治一切。而当人把自己当作信仰的对象时,就等于没有信仰,人类也就失去了信仰的准则和道德的标准,也就必然陷入“信仰危机”,陷入生态环境危机。因此,仅靠科学本身的发展是解决不了上述两重危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科学并不能解决道德、信仰问题。
3
“两重真理说”在实质上提出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引申来说,也提出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所陷入的危机,从“两重真理说”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在科学技术与宗教、道德的矛盾关系上陷入尖锐对立的两难境地。如何认识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如何在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保持人类应有的道德与信仰,这一近代自康德以来许多大思想家所提出和思考过的问题,又重新成为当代学者所不能不加以深思的问题。
康德道德哲学或学术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两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也是“两重真理说”,而且是经过了严密的论证。在康德那里,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分属于两个领域,科学属于“思辨理性”,道德属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这就把科学和信仰、知识和道德区别开来,并突出了人的价值以及理想、信仰、意志等精神因素的地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规定了理性认识的“限度”,认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不能认识“灵魂”、“世界”、“上帝”这三个“物自体”的“本质”。康德强调,“物自体”的“本质”虽然是人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但却是信仰所承认、所可以达到的。康德通过“批判”,不但意欲排除理性的误用,而且要给信仰留下地盘,通过“信仰”保留一个不同于现象世界的符合本质、理想的“彼岸世界”。康德明确说过:“我曾不得不抛弃认识,以便让信仰有个地盘;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即形而上学里那种不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就盲目前进的偏见,乃是一切不信仰的真正源泉,不信仰是违反道德的,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独断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8页。)这就是说, 康德限制或否定“知识”就是为了保留“信仰”,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信仰、道德高于理性,高于知识或科学,或者说,信仰是在科学之后应该保留的领域。现行的哲学史教材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都批评康德,认为他贬低科学知识,限制理性,抬高信仰,在理性之后为宗教留下地盘。今天看来,康德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他看到科学也有“限度”、“极限”,科学解决不了道德、信仰问题,科学和信仰是两个领域,在科学之外或在科学之后还应保留信仰的领域。能否在科学之后恢复或重建信仰,即能否在科学有了极大发展之后保留人类精神信仰的特性,维持道德的权威,这是康德提出的问题的本质,这也正是当代社会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康德之前,作为康德的一个思想来源,法国启蒙学者卢梭已经提出并辩证分析过科学同道德及信仰的关系问题。在卢梭看来,道德、信仰是社会进步中一个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而科学、艺术的兴起对道德、信仰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他在1749年写作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这篇著名论文中写道:“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美德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而逝去”,“在为了发财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时候,美德会变成什么东西呢”?(注:卢梭:《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引自《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146—147、148页。)卢梭认为,科学、 艺术的诞生是由于人的“过恶”,对社会起了“腐化”作用,这一批评似乎过激,但当他指出像“高尚、正直、人道、节制”、“祖国”、“上帝”等一类思想已不再有人谛听、这是“一切后果中最危险的后果”(注:卢梭:《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引自《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9页。)时,他的批评不是非常中肯又切中时弊吗?
康德和卢梭作为“18世纪的预言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两位重要的启蒙学者,都用矛盾观点分析历史发展中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们提出的思想是深刻的,也是富有远见的。如果说在近代有什么人是反科学思潮的先驱,那么,卢梭和康德就是这样的人。
4
随着科学与信仰矛盾的加深,二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成为当代文化研究所阐述的主题。这个问题的影响已是如此广泛和深刻,以致当代哲学与学术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都与其相联:
首先,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把科学主义同反科学思潮区别开来。而反科学思潮的本质就是维护道德信仰。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把技术至上的乐观主义同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这些未来学上的思潮区别开来,而悲观主义又与人类的宗教情结密切相关。
笔者以为,离开了科学与宗教、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般所说“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对立就没有更大的意义。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都是随着文艺复兴一起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理性也就是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已经被归结为科学理性。真正同科学具有实质性矛盾关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形式乃是宗教和道德,只有抓住科学同宗教、科学同道德的矛盾,简言之,抓住科学同信仰的矛盾,才能抓住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要矛盾。
其次,当代西方的一些著名哲学家的重要思想都同科学与宗教或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有关,像罗素、韦伯、杜威、德日进、海德格尔、弗洛姆、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都就此提出过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当然,哲学家们思考、解答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都不相同。罗素提出“对立论”,霍顿提出“相关论”,蒂利希则提出“分离说”。(注:参见张志刚:《基督教与科学关系的三种解释》,《世界宗教文化(京)》1996年第5期。)德裔美国宗教哲学家蒂利希(Tillich)认为以往的冲突在于没有把宗教真理与科学真理分离开来,二者并不属于同一意域,“科学并无权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意域的”。(注:蒂利希:《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Faith,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8),第81—82页。)这种“分离说”同“两重真理说”以及同康德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一目了然的。杜威则力图用统一的方法即他的“科技伦理”思想(注:参见胡东原:《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探索——论杜威科技伦理思想》,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6年第3期。 )去解决这个问题。
韦伯(Weber)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继续沿着康德的思路进展,提出二者具有“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区别,亦即具有“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的区别,这就赋予“两重真理说”以更深刻的含义。韦伯认为,科学专注功能而排斥价值理想,宗教重信仰、理想而“牺牲理智”,而对于人这个既有情感、又需要理智的存在物来说,科学和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理性化过程使人难以在获取科学价值的同时又服从宗教价值,这就是现代人在行动上必然面对的二难抉择。这就是说,由于合理性本身的二元性,导致了人们在对实在的认识上要在现象和本体之间实行二分法,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现代社会陷于两难处境的根源。(注:参见苏国勋:《韦伯》,载于《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即泰依亚·德·夏尔丹)也以科学和宗教双重学者的身份告诉现代人类,“科学和宗教是同一求知行为的相联的两部分”,二者对人类前途的论证是一致的,而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和指导思想。无论科学多么发展,社会多么进步,人类依然离不开宗教的指导,否认宗教,只会使人类走上歧途。(注:参见傅乐安:《德日进》,载于《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宗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认为科学只能提供手段、方法,不能提供目标,因而必须用宗教的道德功能去弥补科学功能之不足。
再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涉及到这一问题。例如,法兰克富学派对科学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认为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已使人沦为物欲、机器的奴仆,成为无感情、无灵魂的工具,即马尔库塞所说“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只有物欲而没有精神,只有科学技术而没有道德、信仰的人。当前,在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的思想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成为群众性批判,例如“绿色运动”就很广泛,各个阶层、各种党派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方面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态度,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在“变绿”。
这就是说,由于科学的负面效应日见增长,已使当代社会陷入科学与信仰矛盾、冲突的两难境地,因而科学与信仰、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遂成为当代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而围绕这一问题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论争,也就在一个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提起了“两重真理说”,或者说,这是“两重真理说”的理论价值在当代人类两难处境中的再现。
5
按照“两重真理说”的一般含义,它是指科学的或哲学的真理与宗教的真理并存,因此,在科学昌盛的今天如何认识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在此仅提出下述对宗教的认识:
(1)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承担并表征着人类生活中信仰的、道德的一面,西方宗教也就是西方的道德,东方产生佛教、伊斯兰教以后也形成了东方的宗教伦理。可以说,原始正教(而不是现时世界上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末世邪教”)都是教人心向善,都是为了把人的道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这是宗教在本质上的一个功能;
(2)宗教以其超常的形式提出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问题。 宗教对于现实人生有限性的超越,对于人生理想境界(曰“彼岸世界”)的不懈寻求, 构成了宗教对人生意义特有的“终极关切”(ultimateConcern);
(3)信仰、敬畏宇宙自然, 通过一定的修炼方法以“返本归真”、重归自然,则构成了宗教的更深层次的本质。也正因此,在人类文明的进展中,宗教的批判与超越现实的功能以及倡导人生道德与信仰的功能,都显示了人类进化的一个可能的方向,这是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等其他“世俗的”意识形态所不能比拟的。
科学技术愈是发展,宗教所具有的上述本质与功能就愈是显示出来。在历史上,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宗教的结果,而在当代社会,宗教的发展就表现成为“反科学”的一个方面,就与“反科学”思潮相一致了。对科学技术至上的怀疑与否定,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宗教情结,构成了“两重真理说”的现代诠释,同时,这种怀疑与否定已日益成为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主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具有两重性,这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显示出来的辩证矛盾,宗教这一古老的意识形态确实代表了人类文化或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倾向和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进化中的一条路径。在西欧中世纪时代,提出“两重真理说”,确实起到了在宗教统治下为科学开拓地盘的作用,而在现代条件下提出“两重真理说”,其显明意图已是在科学技术达到鼎盛之时保留以宗教为表征的信仰与道德的价值。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明确“两重真理”,也就是要明确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真理”之外尚有信仰与道德的“真理”,尚有宗教存在与发展的历史理由。
6
试问:如何解决“两重真理”的当代矛盾呢?当代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这种两难处境呢?
答:就其现实而言,处在两难处境下的人类只能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向宗教文化的回归。所谓“最大限度”,是指由科技发展的负效应所形成的物极必反的反弹所决定的范围,亦即是由历史辩证法的张力所决定的范围;所谓“宗教文化”,也并非是指恢复原始宗教的文化,而是指具有宗教情结的、以精神需求和信仰为表征的文化,即有信仰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毁灭科学技术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发展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但也决不会再把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当作信仰本身,——它所崇拜的唯一对象就是作为一切物质与生命之源的宇宙。
综观人类的历史,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两重真理”,在社会进化中确实具有矛盾的循环往复、辩证进展的性质。在古代的原始文化中,原始科学与宗教一度是统一的;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后期,当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之时却戛然而止、走向衰落并最终让位于基督教文化;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经历了千年统治之后,又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取代。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正在达到现时的“极限”,从而又呈现出要被宗教信仰、精神、道德所取代的趋势。科学与宗教的这种矛盾进展,表现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些大的“圆圈”(注:人类文化的“圆圈”式的辩证发展的思想也属于黑格尔。他洞察到了人类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本性,正是理性和非理性、概念规定和神秘体验、可言说和不可言说、有限和无限等等的对立统一,这将无止境地从一个圆圈迈向一个更大的圆圈,从一个层次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参见杨祖陶:《黑格尔宗教哲学研究的补白之作》,载于《哲学动态》1997年第3 期。),这是人类文化的两重性进展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对当代社会而言,如何全面把握文明进程的这种两重矛盾与转化性质,确切地说,如何在科学发展之后重建人类的道德、信仰,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从精神信仰走向科学技术是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从已经物化的科学技术复归于精神信仰,势必成为未来新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
标签:康德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宗教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