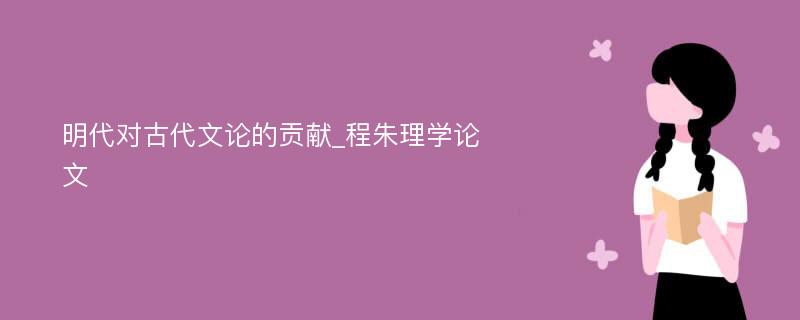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明代论文,古代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6-0052-08
一、“诗文评”在明代正式得名
明代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之一,首先表现在“诗文评”在此时得到它正式的称呼。
在别的文章中我曾说过,“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成立于魏晋南北朝,但当时并没有“诗文评”的名称。它的名称正式出现在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是从目录学、图书分类学的角度被提出的。《国史经籍志》是明代万历年间官修“国史”的一部分,全书未成,只留下焦竑所撰的这一部分“志”,仍以“国史”名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七史部四十三对此书的评语是:
《国史经籍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余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略评介了该书内容,而颇有微词;但今天看来,仅焦竑提出“诗文评”名称,即是一大功绩。焦竑借鉴以往类书,特别是主要以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①为模式而撰写《国史经籍志》,纠正以往的许多谬误,又加以变化,并有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他将书籍重新编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如果加上制书类则为五类),四十八小类(如果加上制书类四小类则为五十二小类),三百二十四个属目。焦竑的贡献在于把以往的“文评”、“诗评”合在一起,第一次提出“诗文评”的名称。这虽是目录学上的名称,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程度——即它作为一个学科从魏晋南北朝成立以来,经隋唐、宋金元,到明代,已经完全成熟,它需要这样一个名字作为自己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很恰切。
关于“诗文评”的学科建立、发展,它与西方文论相对照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诗学文论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的深层内涵和民族根性……我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论“诗文评”中》已经作了论述,兹不赘。这里只想补充一下有关焦竑其人以及当时思想界的一些情况——这与“诗文评”表面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从内里看,从深层看,暗通脉络,密切关联。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又号龙洞山农。南京人,祖籍日照。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皇长子侍读。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著述颇丰,撰著有《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国史经籍志》六卷、《焦氏笔乘正集》六卷、《焦氏笔乘续集》八卷、《笔乘别集》六卷、《支谈》三卷等等;评点类作品有《春秋左传钞》十四卷、《九子全书评林正书》十四卷、《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东坡志林》五卷、《荀子品汇解评》二卷、《墨子品汇解评》一卷、《绝句衍义》四卷、《庄子品汇解评》卷、《苏老泉文集》十三卷等等;还编纂有《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四书直解指南》二十七卷、《词林历官表》三卷、《杨升庵集》一百卷等等。
在明代后期,焦竑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相当先进的思想家和学问家,王(阳明)门后学的重要成员之一。现代有的学者称其为“王学会通派”的一员健将,说他“是一位治学范围极广、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和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会通思潮对于晚明思想学术各个方面的影响。同时,他生前交往广泛,影响巨大,号称东南儒宗”②。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几番贬抑,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清代学术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清代考据学的先导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通雅》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
关于焦竑的思想倾向和特点,我只要说出他的师承,他的朋友,他的学生,读者即会一目了然:
他的老师是泰州学派(左派王学)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和罗汝芳,他们都是左派王学的大将,在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对于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焦竑予以承接与发展。大家知道,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宋代新儒学是一种适应帝国专制社会的创新思想,当时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在宋代它却并未取得官方地位,倒是到了蒙元时代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明前期承袭元代思想体制,继续尊崇程朱理学,其所定下的立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是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内容、以八股制义为形式。明成祖朱棣颁行的官定教科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即以程朱注疏为标准,而科举也几乎成为选拔文官的唯一途径。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做学问就要记诵程传朱注,而其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渐僵化,成为羁绊人们思想的绳索。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明代中期王学兴起,对程朱理学是一个重大冲击;明代晚期的王门后学承续之。泰州学派是中国帝国专制社会后期的一个启蒙学派,他们努力打破程朱“理学”的死板教条。在经学领域,他们反对把程朱传注定为一尊,提倡古注疏,掀起博学考证风气,成为后来清代考据学风的一种范导——这就是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同时他们反对把圣人看成不可企及,以解除对人们思想的束缚。焦竑《支谈》(上)说:“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焦竑有一位忘年交李贽(号卓吾,1527-1602)。一提李贽,人们即会想到这位异端思想家的种种思想和作为,想到他的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想到他对当时思想界的冲击和震撼。而焦竑恰恰同李贽成为亲密朋友。与焦竑同年同馆的朱国祯(1558-1632)在其所著《涌幢小品》中曾说:“焦弱侯推重卓吾,无所不至。谈及,余每不应。弱侯一日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③当时有多少人反对李贽、批判李贽,包括朱国祯在内,对李贽甚为厌恶。但是,焦竑则称其为“圣门第二席”。从前面所引焦竑“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的话,亦可见出焦竑与李贽气味相投、思想相近。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焦竑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生,即明末的进士,也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是与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中国进士,他也是到天主教堂接受洗礼从而改信西教的中国进士。关于焦竑与徐光启的关系,还有一段奇特的故事。万历二十五年丁酉顺天乡试,焦竑任副主考,他从落卷中选出了徐光启的考卷,拔置第一,从而使他起死回生!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记述此事曰:“万历丁酉试顺天,卷落孙山外。是年大司成漪园焦公典试,放榜前二日,犹有不得第一人为恨,从落卷中获先文定公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1]若不是焦竑独具慧眼,一位天才可能就此埋没。徐光启对恩师终生念念不忘,在其《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中说:“吾师澹园先生,以道德经术表标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2](附编二)
焦竑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生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万历二十年壬辰,焦竑任会试同考官,当年经他选拔而进士及第者15人,其中就有袁宏道④。此后袁宏道常常求教于焦竑。同时,焦竑还把袁氏三兄弟介绍给李贽,受到李贽思想(特别是“童心说”)影响颇多,“性灵”说的提出,与此密切相关。而焦竑自己也谈“性灵”。他在《雅娱阁诗集序》中说:“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2](卷十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就特别引出焦竑《澹园集》中的一段话:“夫词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书》不借采于《易》,《诗》非假途于《春秋》也。至于马、班、韩、柳乃不能无本祖;顾如花在蜜,蘖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脱弃陈骸,自标灵采……斯不谓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独词之知,乃曰以古之词属今之事,此为古文云尔。韩子不云乎?‘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古以为贼,今以为程……谬种流传,浸以成习,至有作者当其前,反而视而不顾,斯可怪矣!”[2](卷十二《与友人论文书》)在引了这段话之后,郭先生说:“此文攻击七子之摹拟剽窃,颇与公安之论相同。”[3]此足可见焦竑对公安派的影响。
焦竑还与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学者利玛窦有一段友谊。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来到南京,结识了焦竑与他的好友李贽。《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一书记述了这段经历:
这时在南京有一位状元,即是在考进士时,三百位进士中考第一名的。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他因失官返乡,极受地方人士尊重。他对中国的三个宗教极有研究,这时极力宣传三教归一之学说。当时有中国另一位名人李卓吾,在焦竑幺家中做客。他做过大官,曾任姚州或姚安知州,却弃了官职和家庭,削发为僧。因为他博学能文,又年已古稀,声望极高,有许多弟子信了他创立的宗派。这两位大文人对利神父非常敬重。特别是李贽,本来非常高傲,大官拜访他时,他不接见,也不拜访高官大员;而他竟先自动造访利神父,使神父的朋友们都感到意外。利神父按照中国习惯回拜时,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在场,大家谈论的是宗教问题。李贽不愿与利神父争论,也不反驳他的主张,反而说天主教是真的。李卓吾在湖广有许多弟子。他得到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之后,便抄了几份,分送给湖广的弟子们。因了这位大文人对《交友论》的推重,神父们的名声便也在湖广一带传开了。[4]
从这段记述,我们看到焦竑和李贽是多么开明。此时他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焦竑在《管东溟墓志》中曾说:“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2](续集卷十四)即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又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收摄各种学说。
综上所述,由焦兹这样一位学者提出“诗文评”的名称,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歪打正着”(不是专谈诗学文论,而是从目录学角度提及),但是实际上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乃“正中历史下怀”也!这其间,颇有值得往远处和深处思索的空间。
二、明代诗文评全貌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也层出不穷,使此时“诗文评”成为又一个辉煌时期。例如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宏观地说,一方面,这辉煌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明朝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之中,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而明代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思想、学术和审美文化等)也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明代“诗文评”的辉煌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仅诗话之作(包括有“诗话”之名和无“诗话”之名而实为诗话)就有170多部,而词话、曲话、小说评点都超过前代;它们在继承自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郭绍虞先生说它“空疏不学”,大概指个别作品而非全部,因为,明代的许多“诗文评”著作,如高棵《唐诗品彙》、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前后七子的一些作品如《四溟诗话》、《艺苑卮言》,还有李贽、叶昼等人的小说评点,徐渭、臧懋循、吕天成、王骥德等人的曲论,还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与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的争论……其实并不“空疏”,也非“不学”。
如果用简略的话概括明代“诗文评”全貌,或许可以这样描述:
明初宋濂(景濂,1310-1381)、方孝孺(逊志,1357-1402)等人所提出的是带有复古色彩的正统的适应皇权政教的文论⑤,紧接着他们的就是御用的台阁文学思潮,表现出来的是靡弱文风。
之后,高棅(廷礼,1350-1423)承袭严羽,提倡“悟入”,阐发的是宗法盛唐的诗论;而他划分唐诗为“初”“盛”“中”“晚”的思想,颇有影响,其主要观点表现在其《唐诗品彙》中,该书“自序”云:“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⑥
明中期,天顺、成化年间以宰臣李东阳(西涯,1447-1516)为领袖的茶陵派祖述沧浪之说的文学思想,是七子思想的先导;其《怀麓堂诗话》有一段名言:“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而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献吉,1472-1530)、何景明(仲默,1483-1521)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于鳞,1514-1570年)、王世贞(元美,1526-1590)、谢臻(茂秦,1495-1575)为代表的后七子,掀起两次复古思潮——他们以复古为途径以改革文风,同时他们的复古实质上也是对已经僵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对抗(官方规定只能读程朱理学,他们却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两次复古思潮之间又有西涯门徒杨慎(升庵,1488-1559)兼容并包的文论思想,以唐顺之(应德、荆川,1507-1560)、王慎中(遵岩,1509-1559)、茅坤(鹿门,1512-1601)、归有光(震川,1506-1571)为代表的唐宋派文论。
明后期,万历年间在王门后学(尤其是李贽等人)影响之下兴起了肆意张扬情欲的文学思潮,如徐渭(文长,1521-1593)、汤显祖(义仍,1550-1616)等的主情和尚意趣,以袁宏道(中郎,1568-1610)为代表的公安三袁的性灵派之张扬性灵、反对摹拟,钟惺(伯敬,1574-1624)、谭元春(友夏,1586-1637)的竟陵派也倡性灵但着眼点多从欣赏角度出发。此外,还有李贽、叶昼(文通,生卒年未详)等人的小说评点,开清代小说评点风气之先;王世贞(弇州,1526-1590)《艺苑卮言》、徐渭(文长)《南词叙录》、臧懋循(晋叔,1550-1620)《元曲选序》、吕天成(勤之、郁蓝生,1580-1618)《曲品》、王骥德(伯良,1540-1623)《曲律》……上承元、下启清,是元与清之间戏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以往的戏曲艺术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以上所述文论家、诗论家、曲论家,他们的思想趋向和文论观点各有不同,在历史上的功过不一;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皆有可论。譬如,我们可以重点说一说前后七子。他们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但不管是功是过,他们无疑是明代“诗文评”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的文论思想不但与派别之外的文论思想不同,而且派别内部也有争论(前七子李梦阳与何景明之间,后七子谢臻与李攀龙、王世贞之间,就有不少笔墨官司),每个人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发展(李梦阳晚年对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和一味摹拟的主张就有所反省,而王世贞对早年之《艺苑卮言》也有悔意)。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明显感到严羽的影响(明清许多论家身上都有严羽的影子),足见传统力量之强。他们的诗学文论思想相当复杂和丰富,不可简单予以肯定或否定。一方面他们以“复古”为径而行革新靡弱文风和对抗程朱理学之实,却又的确堕入摹拟古人的泥潭——这是他们无法辩解的弊病;另一方面他们又的确提出了许多精彩思想,如李梦阳说:“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士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号,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5](《诗集自序》)谢臻《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带有总结性的多方面的诗论文论曲论思想,都有精彩之处,值得研究。
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此后王门后学(特别是李贽)的狂飙思潮,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其推动之下,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派等提出了带有巨大冲击力的诗学文论思想,更值得特别关注。
三、阳明心学和王门后学的巨大作用
中国“诗文评”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对诗学文论有巨大的显著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诗学文论思想有时就是某种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种新的思想的兴起,必然对诗学文论的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萌芽时期的“诗文评”思想,即十分活跃。
两汉时期,董学兴盛,与此相应产生了一批文论作品;但是随着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等理论将儒家思想模态化,随后一二百年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故汉代后期诗学文论并无大的创造性进展。
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大变动,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加之佛教思想传人,思想领域产生新潮,于是影响到诗学文论,造成大繁荣的局面,“诗文评”学科正式成立。
宋代理学(新儒学)的兴起,也对宋代“诗文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表面看起来不那么直接)。
理学在宋代绝大部分时间并未成为主流,且常常受到压制。当它作为非主流思潮的时候,反而富有活力。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一方面,它对于民众生活理念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秩序、伦理秩序的建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理学这样超越于国家合法性之上、拥有某种真理话语权力,常常被一些普通士人作为对抗国家皇权控制的思想手段,因此理学在一定时期还具有某种批判能力,而且理学通过士绅进行了“文明”的大普及。南宋末期程朱理学得到官方认可;元代至明初,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元代至明代前期,是一个思想平庸的时代,原因即在于因袭成思,没有什么开拓。在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学者们由于有切肤的历史记忆和实际的策略需求,所以学问中常常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此时的许多学者只是把思想当做背诵的文本,又把文本当做真正的思想。“本来,像理学那样具有批评和诊断意义的思想,是具有超越性和独立性的,它是从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中自内发出的,但是,当后来的模仿者被这些思想所吸引,把这些充满睿智而且有所针对的话当做真理进行复制的时候,它就已经蜕变成仪式或文本。”本来具有批评力和诊断力的思想,一旦成为流行的时尚,成为背诵和记忆的文本,就僵化了。读的书就这么几本,说的话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这几本书、这几句话虽然是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和真理,但它们仿佛是悬置在半空的高调,难以指导社会生活,于是便成为抽象的教条[6]。明代初期正是如此。皇家把程朱理学定为全民必须遵循的思想和科举考试的准则。人们的思想被限制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里,不准越雷池一步。永乐年间,皇家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理学被定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于是,程朱理学也就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羁绊和枷锁。
到了明代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城市商贾以及一些贵族,因为富庶了,开始产生新的生活趋向,城市和乡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不同的文化趋向,被传统观念不齿的冶游、侈靡、聚敛等风气,在以商业与消费为中心的城市中滋生蔓延开来……而已经变成教条的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知识无法解释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种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这种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这就造成了思想危机。这时出现的结果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策略发生背离,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恰恰正是因为这种平庸和圆熟,迫使这些学者反身寻找另类可以刺激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那个时代,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在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除了逐渐从主流文明和上层人士中淡出的佛学之外,就是南宋时代曾经与朱学对垒的陆学。于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开始从陆学吸取滋养,渐渐突显“心”的意义,从曹端(月川,1376-1434)、薛瑄(敬轩,1389-1464)、吴与弼(康斋,1391-1469)、胡居仁(敬斋,1434-1484)到陈献章(白沙,1428-1500),这种心、理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被慢慢加深扩大,终于引来了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大变化,而到明中期的王阳明(守仁,1472-1528),正式形成了心学。阳明心学兴起,特别是王门后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其实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并没有某些学者所说的那么大的对立,王阳明只是从理学出发而对理学进行修正。这修正,主要表现在突出“心”的作用。他认为追求真理(“道”、“理”、“良知”)的方法和途径,根本不在“外”,而在“内”,即内心的修养历程;人要获得“良知”,不假外求。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心”“理”一也,“心”外无“理”。不能像朱熹那样把“心”与“理”分开。因此,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是从外部世界去找道德提升和心灵澄明的途径,而是发掘内在心灵自有的灵明。于是王阳明对儒家经典作了重新诠释,特别是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意思进行新的说明,将之变成一系列内在心灵的省思和调整活动,这样,“知”与“行”也即统而一之了⑦。
这就是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主要修正。
在程朱理学已经僵化为教条而不准有异说的当时,在它已经失去批判能力、建设能力和解说新事物能力的时候,阳明心学的出现,发出不同的声音,在沉闷的天空里升起一颗新的思想气球,为众多士子学人打开另一片思维天地。这对长时间禁锢在程朱理学之下的诗学文论领域,当然是一种解放。而对诗学文论的这种解放作用,在王门后学——泰州学派或称左派王学那里就更突出、更直接地表现出来。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何心隐(1517-1579)、罗汝芳(1515-1588),特别是李贽(1527-1602)等,对儒家传统观念,对历史传统和社会秩序进行攻击,打破俗人和圣人、日常生活和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的界限,肯定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正当性,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提倡童心(赤子之心)。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7](《意心说》)李贽在《杂说》中还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7](《杂说》)
李贽的这番言论,无异于向程朱理学投了一枚炸弹,他甚至说六经、《语》、《孟》“其大半非圣人之言”,“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说它们“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那些程朱理学的卫道者听了李贽这些话,还不气个半死?怪不得他们不遗余力对李贽口诛笔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对于当时的广大学人,这些言论则是一种启蒙,是一盏解放思想的明灯。
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历来为论家所瞩目,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较早的是徐渭。他生性狂放、纵情,不愿受传统礼法之束缚,性情怪癖,据说有人去访问他,若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在创作上他个性鲜明,风格豪迈而放逸。他特别提倡独创,反对摹拟,认为写诗如果一味摹拟,摹拟得再好、再像,至多是鸟学人言,有何价值可言?此番言论、此种主张,被后来的袁宏道引为同道,他们虽生不同时,却气味相投。袁宏道非常敬仰徐渭,曾写《徐文长传》,对徐渭有一段精彩描述:“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8]由袁宏道的评述,我们亦可见徐渭思想、创作于一斑。
大约在徐渭之后数十年,有临川汤显祖出,是位更激进的主情派,并把这股潮流更推进一步。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动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日传者。亦世所不许也。予常以此定文求之变,无解者。”[9 ](三十一卷)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又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9](三十四卷《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显祖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9](卷四十五《寄达观》)。在汤显祖眼里,情是至上的,他在《牡丹亭记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的诗文和戏曲作品,贯彻了他的这些主张。
与汤显祖差不多同时,出现了公安三袁(老大袁宗道、老二袁宏道、老三袁中道),其最主要的代表是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袁宏道。公安派张扬个性、张扬情欲、张扬独创、反对摹拟,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摆出一副与世俗观点誓不两立的姿态,对抗传统观念。在《与张幼于》一文中,袁宏道说:“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10](卷二十二《与张幼于》)他提出的“性灵说”,可以说把主情派的思潮推到极致。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说:“(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10](卷一《叙小修诗》)所谓“性灵”,就是情性、情感,“性灵说”要诗文突出地表现情感,把情感放在首要位置。其实,提倡“性灵”并不自三袁始,前已说过,袁宏道的老师焦竑就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写诗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主张诗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他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9](卷三十二《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但是,他们都没有袁宏道说得这般激烈和透彻。
此外竟陵派也谈性灵。公安、竟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也有差别。有学者已经指出,公安、竟陵两派,虽然都是标举性灵,但他们所指陈的对象及用法是不同的。请看公安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和竟陵钟惺《诗归·序》所说的“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以及谭元春《诗归·序》“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等等的说法,比较之下即可明白: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用性灵来说明文学创作时,要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才不会迟滞呆板;竟陵派钟、谭等人,则用之于鉴赏古人的诗作,认为看前人作品,贵在能从纸上字里行间,看出古人的真性情,而产生共鸣。同样谈“性灵”,公安派谈的是创作论的范围,竟陵派谈的是鉴赏论的范围[11]。
不管怎么说,晚明的这股革命思潮应该得到重视。
有人可能会说,重视情感是中国“诗文评”史上许多论家的共同主张,何止明后期的这些人?不错,认为诗必须表现情感的思想,的确古已有之,《毛诗序》不是说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在明朝,高唱“复古”、主张摹拟的前后七子也认为诗歌必须有情。徐祯卿(1479-1511)《谈艺录》中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发。既动于中,必形于声。”又说:“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诗文评”史上类似论述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明后期的这些主情派却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秉承王门后学的思想倾向,向内心情感无尽开发,极力张扬情欲而达于极致。如果说历史上其他论家谈情,常常把情放在理的约束之下,那么晚明的这些主情派,则是把“情”放在“理”之上,以“情”格“理”。在他们这里,情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矛头直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当时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有某些偏激的地方,但他们在明代帝国思想专制历史上的革命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①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运用的分类理论,较之西汉刘歆《七略》与四部的模式而有所突破。他将《艺文志》分为12大类,仍将经类排在第一位,而把礼、乐、小学分出,各立一类,与经类并列;仍保存诸子类,而将天文、五行、艺术、医方及类书分出,各成一类,与诸子并列;他于诸子类设杂家、小说两家;于文类,设文史、诗评二种;于杂史、传记二家之下复分若干种。
②所谓“王学会通派”是指王门后学中追求超脱生死的精神境界、会通入世出世、宣扬无善无恶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治学讲究“求真”(打破一切人为限制、平等对待各种思想资源,唯真理是求),“自主”(要求打破权威对真理的垄断,否认即成规范的天然合法性,自作主张)。参见刘海滨《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卷前“内容提要”。
③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六“黄叔度二诬辨”条。
④焦竑《澹园集》卷二十七《心夔乐公墓表》说:“壬辰,与礼闱校士之役,所荐拔十有五人。”而袁宏道亦称焦竑为“座主”(《袁宏道集》卷二有《白门逢焦师座主》二首)。
⑤宋濂说:“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中国有一种观点,“大文”等同于“政教”,即文的政教化;这与当代西方美学对比起来很有意思: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则将政教审美化。
⑥见高棅《唐诗品彙》卷首。高棅,又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长乐(今属福建)人。《唐诗品彙》正集90卷,选唐代诗人620人,诗作5700余首;拾遗10卷,增补61人,诗作900余首,完成于洪武癸西年(1393)。常见的本子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陆允中、张恂等人的校订本。
⑦我吸收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有关阳明心学(以及后面有关左派王学即泰州学派)的一些观点,因为所引内容,有许多并非原话,同时也加进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故未加引号,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