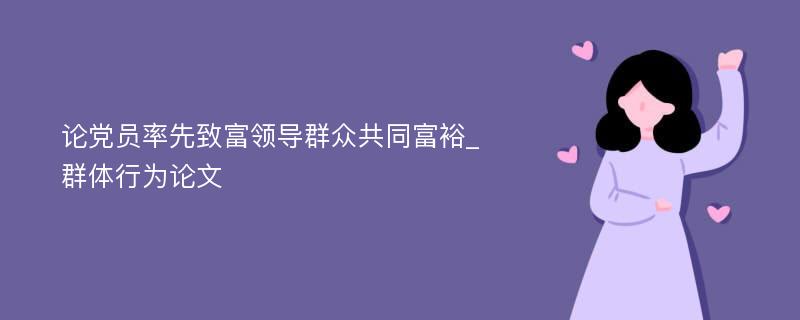
论党员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员论文,群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立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重大方针政策,并积极倡导共产党员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敢于率先“带头致富”。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构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鲜明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责任和使命,发挥出新的历史作用。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走向中,如果重点还只是停留在或笼统地或一味地继续鼓励党员“带头致富”,显然已经很不适宜,甚至远远不够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工作中要时刻想到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群众,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富裕起来”(见江泽民1995年1月23 日《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如何正确处理好党员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问题,已经是摆在全党面前一个重大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党员“带头致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有积极意义,但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应该明确新的侧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动因的。可以认为,大体上基于这样几个考虑:
一是因为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开始实现战略性转移,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与此同时,提出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民政策。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党的政策变化还心存疑虑,更多地处于一种观望和等待的状态,许多人的头脑里仍然残存着“富”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僵化思想。在这样一种强大社会意识和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党的富民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因此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以促动党的富民政策的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党员“带头致富”重要的不在于党员本身如何致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员敢于富、可以富这样一种事实,向人们昭示着党在特定时期的一种政策取向,表明党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并以此推动和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与转变,去挣脱“左”的思想禁锢和羁绊,是一种无形的精神驱动力。
二是重新塑造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这种定位并不断地发挥出其先进性和战斗性,使党树立起了崇高的光辉形象。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大为下降,“无钱办事,无人办事和无力办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在农村,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因为集体经济的匮乏而无从发挥,一些党员因为自身的贫穷而发挥不了带头作用,甚至被人瞧不起。在这种形势下,党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勇气和气魄,大胆鼓励共产党员“带头致富”,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党员能够勤劳守法致富的活生生事实,证明我们党及其党员有致富的本领,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胆识和气魄。如果说,让一部分党员可以“带头致富”只是表明党的政策出现一种新的走向的话,那么,再通过一部分党员能够靠勤劳守法而“带头致富”的现实,则给党和党员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群众对党的信心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是着眼于发挥共产党员的样板“示范效应”。理论上确定了党员可以“带头致富”,事实上一部分党员能够“带头致富”,这就构成了确定这一政策的两个层面上的意义。此外,我们党提出党员“带头致富”还有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人想富、盼富,但不知如何致富,在这种状况下,有必要用一些党员“带头致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让更多的人看他们是怎样致富的,从中学习致富的经验和方法,避免或少走弯路。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而在这“一部分人”当中,党员的“示范力量”是较大的,有样板意义和典型价值,可以发挥其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
二、鼓励党员“带头致富”具有双重性, 它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它只能是阶段性和局限性的
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着的。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一直提倡的党员“带头致富”政策,逐步暴露出了诸多始料不及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负效应之一:孵化出了一个党内“富裕群体”。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党当初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尤其是政策上的需要(如推动党的富民政策落实等),提出了党员“带头致富”,而对于党员究竟可以“致富”到什么样的程度、规模和目标等,不够明确;对于“带头致富”起来以后应该怎么办,也显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对于党员如何“带头致富”,“致富”的手段、途径等,缺乏严格的规范、限制和要求。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党的鼓励党员“带头致富”政策的鼓动下,党内一个“富裕群体”开始涌现。
对党员“富裕户”或者说党内“富裕群体”,要从数量、规模上作出准确统计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这样认为,构成党内这个“富裕群体”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党员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我们姑且称之为“显性富裕户”;另一部分是党内一部分无法合理合法解释其资产来源而又确确实实“致富”了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富裕户”。党内“显性富裕户”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这里,我们仅以江苏省盐城市的一个调查数据为例,该市自1989年以来至1995年底,已有私营企业主党员122名,与1992年相比,增加了10倍,近年来, 每年以117%的速度递增。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它的绝对数有多少, 而在于它的增长速度之快、比例之高的确值得重视。这种现象在全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可谓不普遍。这一判断是不成问题的。另外,据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是私营企业。等于说,加上这一部分“富裕群体”,党内的“显性富裕户”是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而党内“隐性富裕户”的膨胀是更为严重的一个现实。有学者作过这样的分析统计,全国目前已有100万人(还有一说为300万人)拥有100 万元以上的财产。然而,国家工商局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1994年底,注册资产愈百万的私营企业接近2万户, 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主中的百万富翁在全国百万富翁中仅占2%。退一步说,即使占到20%,那么, 还剩下80%即80万人的百万富翁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财产来源是可以找到公开、半公开的来源的,如文艺、体育“明星”、模特、名作家、名编导等,这部分从业人员大概有1000万人,但能够跻身百万富翁行列的充其量不超过3%,即使高位统计也不过30万人。那么, 还有50万人,即百万富翁的一半,则属于无法合理合法解释其财产来源的人。(以上资料分析,参见《中国的隐形经济1996》一书,黄苇町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党内的“隐性富裕户”。在作以上分析考查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党内的“富裕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已经初步形成。
负效应之二:出现了与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相互矛盾的现象。党内“富裕群体”的出现,使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一部分党员群众常常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迷茫之中。现实中有这样一些突出的表现:
一方面,我们党在政策上不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因为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性质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是完全背离的,是与党的先进性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党在政策上鼓励党员“带头致富”,并因此而在党内不断涌现私营企业主党员,私营企业主党员队伍继续壮大。
一方面,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党内一部分“带头致富”的党员,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党员,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性质,由于要去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增强个人财富的积累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资本的人格代表”(马克思语),作为现实的“经济人”(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地具有自私性动机,以寻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作为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或理所当然地要去更多地“为人民币服务”。
一方面,党的目标是为了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一部分党员“带头致富”的结果使一部分党员与党员、一部分党员与群众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特别是一部分党员在“带头致富”过程中,伴随着原始资本积累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雇佣剥削行为,这与党的目标又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一方面,党针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在政策上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进入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另一方面,作为党员的私营企业主,按照党章规定又应当享受作为党员应当享受的那部分权利和义务等等。党之所以陷入这种尴尬被动的局面,同我们党一味地倡导党员“带头致富”,而很少考虑其后果有关,也与一部分党员没能正确处理好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关系有关。
负效应之三:促使党内矛盾和腐败问题更趋复杂与尖锐。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在党的鼓励党员“带头致富”政策的号召下,致富中的绝大多数党员是靠勤劳守法而致富的(这主要集中在前面所说的党内“显性富裕户”这一群体中),但也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靠某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手段(自然更是不合乎党章——这一党内根本法规要求)而“致富”的。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富人中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很少”。这个数据是发人深省,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党员致富问题,不无参考意义。特别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党内的“隐性富裕”群体的存在,它不仅是对“带头致富”的一种根本歪曲,更主要的是这一群体是党内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病发区”。由此而引发的党内种种矛盾和腐败现象,表现得更加复杂尖锐。
一是加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新时期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更多地表现为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一些党员迅速地“带头致富”,使原本就有所失衡的利益杠杆强度倾斜。一方面贫富差距问题日显突出,高、低收入阶层在党内外都开始出现反差;另一方面有的党员只顾自己“致富”,寻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而不顾其他党员和群众的贫富问题,一些群众看到有些党员只顾自己“带头”致富,而不是“带领”他们共同致富,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对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任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发展为埋怨和指责。原本就在一定程度上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出现新的不安定因素。
二是致使有些党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变异,导致许多党员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一些党员在“带头致富”过程中,求富心切,发财迫切,于是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地出现拜金意识强了,政治意识淡了;利己意识强了,助人意识淡了;个人意识强了,组织观念淡了;自我意识强了,群众观念淡了;享乐意识强了,艰苦意识淡了;竞争索取意识强了,奉献牺牲意识淡了;“经济人”意识强了,党员意识淡了等等。党内急功近利、趋利求富,甚至问钱不问政治,见利忘义之风日盛,有的干脆把自己“降低为一般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去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甚至向党讨价还价,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滋生蔓延开来。
三是出现了“权力寻租”、“权力致富”的腐败现象。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注意和思考这样一种事实,有的党员在企业当头,为了个人尽快“致富”,弄得“庙穷方丈富”,有的党员在一个地方负责,群众没富起来,自己却腰缠万贯“先富”了起来。河南省的一份调查材料分析认为,现在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因企业经营者和领导班子问题而明显导致企业亏损的,占1/3以上。而这里面又有五种情况:(1)经营者素质差,无所作为;(2)经营者独断专行,决策失误;(3)企业领导人有短期行为,个人先狠捞一把,自己富了, 企业穷了,以致垮了;(4)领导班子内部争权夺利,内耗过大;(5)经营者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图个人享乐,挥霍浪费企业资财。这个材料所分析的事实是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问题的。
我们再以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检查机关查处大案要案的重点是盯住这样几类案件上看:(1)国有企业严重亏损, 但“庙穷方丈富”的企业领导;(2)国有企业改组、改造过程中, 借机侵吞国有资产;(3)国有企业领导采用非法手段转移国有资产;(4)国有企业领导以企业名义从事中介活动并将所得据为己有等,由此反映出以上问题的严重、严峻性。
“富了方丈穷了庙”、“个人先捞上一把”,这样的事例和心态不可谓少。据某市的调查资料显示,该市“带头致富”的一部分党员中,厂长经理出身的要占35%左右。他们中有的为了个人“致富”,不惜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有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曲线致富”,损公肥私等等。长江动力集团的原总经理于志安、蚌埠卷烟厂的原厂长李邦福、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佑卿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教训。这些人的“致富”是建立在大量的公有资产流失基础上,是建立在“权力致富”和“设租、寻租”基础上的。造成这种腐败现象,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提倡党员“带头致富”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长期以来一直不加规范地鼓励党员“带头致富”,诱导乃至强化了他们的权力致富意识,正是一味地不加规范地鼓励党员“带头致富”而给一部分党员干部提供了“合法”的强大的“寻租”刺激和“寻租”冲动,这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党员认为,要“致富”就得靠手中最大的资本——权力去创造自身“财富”,去实现增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88年前后的“官倒”现象,以及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都是权力致富的反映和折射。于是,“权力揽买卖”、利用权力去“设租”、“寻租”等腐败现象也就不断出现,乃至屡禁不止。
三、 当前要把鼓励党员“带头致富”重点转向到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上来。共产党员要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正确处理好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关系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重点转移到倡导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上来。
其一,要求党员“带领群众致富”,是响应党在现阶段政策重点调整、转移的需要。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富民政策,不但使一部分人确实得以先富起来,而且使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还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整个社会心理实现了从怕“富”到想“富”、求“富”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新的战略部署。党已经更多地用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已经开始启动中西部发展战略,从政策上和投入等方面,加大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度;已经开始通过调整分配方式等缩小贫富差距等等。我以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走向,在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其重点和重心已经明显移位到了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正在进入新的实施阶段,我们党在当初旨在引导和推动人的思想观念解放而提出的党员“带头致富”政策,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应该也必须随着党的富民政策重点的转移而转移,以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性。
其二,要求党员“带领群众致富”,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这种宗旨要求在战争年代的集中体现就是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便集中体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上。换句话说,前者主要体现在翻身求解放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当家致富上。党员要自觉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就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党员不能只顾个人致富,而不关心群众疾苦,忘了群众的利益,那样不但会脱离群众,而且与党的宗旨是相背离的,同时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如果说,过去提出的党员“带头致富”或多或少难免有个人利益驱动因素的话,那么,要求党员“带领群众致富”,则是一种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精神的具体体现。
其三,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是对党内正在迅速发展的“富裕群体”的有效规范和必要控制。多年来,随着党员“带头致富”队伍的不断壮大,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富裕群体,必须及时地进行规范。而对于党内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存在的“隐性富裕”群体,更应该进行及时的限制和必要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也是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党由鼓励党员“带头致富”转移到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实质上就是党开始进行规范、限制而在政策上的一种导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四,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不妨可以作这样一些方案选择。方案之一:作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党员,鼓励他们适时地将部分或全部私有财产用适当方式转变为集体财产,以壮大集体经济,或为群众共同致富垫付启动资金。山东的王廷江,当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尚且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何况是共产党员?有的党员则可以着重把自身致富的本领、经验、手段乃至市场传授、转让给群众,使群众致富有门,致富有路。方案之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少提或不再提鼓励党员“带头致富”,而是重点提鼓励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但考虑到一些具体的特殊地区的实际情况,目前在一些农村,尤其是那些老、少、边、穷等经济落后地区,仍然继续沿用党员“带头致富”的提法,但对致富的规模、途径、手段进行必要的规范,对致富以后的思想与行为取向提出明确的要求。而就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党员来讲,在一方面对“带头致富”的党员进行规范的同时,及时地把重点逐步转移到要求党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上来,使广大党员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方案之三:对于一味只顾自己致富,并不能自觉甚至根本不想也不愿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党员,在教育帮助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劝其退党,以保持和体现党的先进性。
新的历史阶段下,正确处理好党员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逐步把重点转移到鼓励党员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来,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