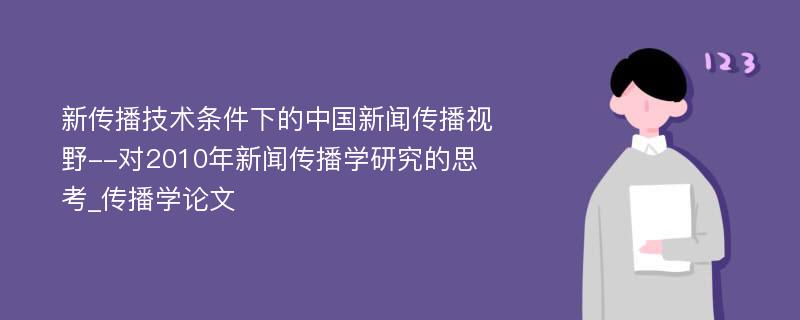
新传播技术条件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视野——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新闻论文,条件下论文,视野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动力,现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传播科技的发展。学者们正在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得以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话题和方法的整合
新传播科技给新闻传播实务的教学和研究也带来了整合的要求。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内陆地区,新传播科技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网络传播的普及,以及以互联网为平台的web2.0的发展趋势,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适应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不知不觉中,研究话题和方法的整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学科内容分化过程中稳定下来的一些话题,其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在新闻传播学界,常挂在嘴边的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然而信息时代的生活改变了这种先验的设想。没有纯粹的西方和东方,全球化造成了思想的流动和融合。西方新闻理念中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中国式的思维,例如能够在那里发现类似中国典型报道和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而传播学中的不少理论(例如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在中国的论述中其实早已变味,被赋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
不仅传播学的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传播学的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也开始渗透到研究新闻现象中了,主要表现在对各种传媒行为商业化的批判上。在新闻学的话语中,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成分无形中越来越多了,原本只有少数学者知道的欧洲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现在变得颇为大众化,例如本雅明、马尔库塞、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罗兰·巴特、斯图亚特·霍尔等等。
一位研究者的发问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
“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
第二,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最重要的是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客观世界日益拥有了主动表达能力,更多的客观事物将加入到人类的信息交流体系之中,整个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将形成全新的信息交流系统。”①
学科和学术立场的融合
传播学研究本身,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已经较难清晰地分清某项研究属于哪个学派,因为不同的方法正在融合。划分学派只是认识这个学科的途径,不同学派的融合反映了学科的成熟和包容。
正是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压迫下,新闻传播学的很多问题已经不能在原来划分的范围内得到回答,打破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界限,甚至打破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新的思考方式。例如在多种新媒体渠道下关于“受众”认识已经需要调整,信息传播的迅速、广泛和其草根性质,再造了受众的权力(不完全是政治意义的权力,指具有无形的社会性质的力量),形成了受众与媒介的新型关系,受众拥有了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的某种权力,乃至形成社会主导意见的权力。
中国学界近些年比较集中地研究为传媒学起源奠定理论基础的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学术立场的融合表现。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论著,相当多很难说清楚属于哪种学派的研究。同一篇论文或著作中,研究的论据常常来自不同的学派。即使较为对立的学派,在方法论上却很接近。这种情形,国内的研究与国际是“接轨”的。欧洲不少批判学派背景的学者,实际研究中亦采用地道的量化分析方法,而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中,亦出现较多的人文——历史——哲学色彩的论证。
虚拟真实对现实真实的挑战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在虚拟世界驻足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世界驻足的时间就越少;在网络等虚拟世界中越是想让大脑和眼睛获取“无限”信息,人的身体就越是被禁锢在极为有限的现实空间中,甚至就在一把椅子上。真实中的不真实与不真实中的真实,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在一般的观念中,真实意味着可触、可测、可检验,反之便是不真实。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通,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②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③ 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未来的传播学领域将聚合起更多的学科背景,面对人类与大千世界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借助多元学科知识、使用多元科学工具与方法,深入探讨信息传播和系统控制的特点与规律,建造起更具说服力和适应度的理论体系。”④
人文思路对新技术及环境的质疑
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1.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3.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⑤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对科学方法的冷静反思
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
最近几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连续举办暑期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班,大部分主要高校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先后参加,已经使得实证研究的量化和质化的分析方法得到普及。
现在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新闻学研究的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例如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构建逻辑》⑥,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⑦,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MMN实验),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采用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这个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的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⑧
有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或叫“重温”)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
注释:
① 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2期。
② 闵慧泉:《真实与虚拟:新媒介环境下的追问》,《现代传播》2010年2期。
③ 马忠君:《虚拟化生存的基础》,《现代传播》2010年3期。
④ 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2期。
⑤ 孙玮:《媒体融合与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国际新闻界》2010年12期。
⑥ 中国受众媒介“接触—使用”状态定量研究课题组:《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构建逻辑》,《国际新闻界》2010年9期。
⑦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关于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的脑认知机制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11期。
⑧ 胡翼青:《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