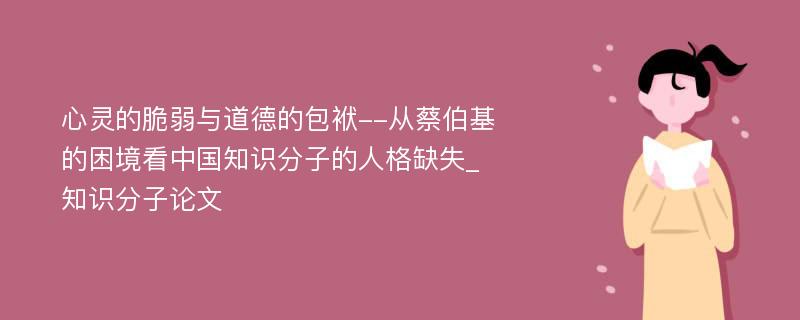
心性的脆弱与道义的重荷——从蔡伯喈的两难抉择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荷论文,心性论文,道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缺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琵琶记》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主题便有各不相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宣扬了封建社会的伦理孝道,有的认为它吐露了一家两代的苦难忧怨,有的认为它揭示了元朝人民的悲惨境遇,有的认为它批判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僵滞……客观地说,上述观点,都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或深或浅地触及到了《琵琶记》的内蕴,都有一定道理,都能在特定前提下给人以感发和启示,不过又都不免偏狭。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经不起诘难,即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够详密谨严,一部作品产生后六百多年,对其主题竟无法得出一致公认的结论,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人们对《琵琶记》的主题为什么会聚议纷芸莫衷一是呢?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它内蕴广博复杂,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作品主人公蔡伯喈形象的多意性、性格的多重性和行为的矛盾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若要正确把握《琵琶记》的主题,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应正确把握蔡伯喈这个典型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性格特征。
不过,由于蔡伯谐是《琵琶记》中各种矛盾纠绕的焦点,再加上他本身言行的非常态显示,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把这个人物说清楚,很难像对待一般人物那样去探究他灵魂的底蕴和思想演化的轨迹。但难于把握不等于无法把握,研究任何课题只要努力总会找到突破口。那么完整把握蔡伯喈形象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是怎样理解并评价蔡伯喈的矛盾心态。如果我们对蔡伯喈的矛盾心态有了正确体认,自然也就能对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做出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并进而对《琵琶记》的主题做出深刻全面的剖析揭示了。
蔡伯喈矛盾心态的第一个感性显现是仕与孝的两难。
一直占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孔孟思想,因其内涵驳杂,人们不易对它进行简约的质的规定,但是将“孝”视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想人们一般能接受。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当政者出于教化、麻醉人民的需要,他们把“孝”加以引伸和泛化,给它外加上种种符合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内容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而不敢也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不敬。这样,原本属于伦理范畴的一种人类社会固有的普普通通的精神慰安和亲情互补,随着人性的减弱、理性的增强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侵染,便堕落成了一个带有浓重政治律令色彩的神圣不可亵渎的法则,堕落成了一片具有极大伸缩性并时时笼罩在人民心头的拂之不去,抹之不掉的精神阴影。它高高在上,有权对人类的一切道德行为做貌似公正的裁判:凡忤逆“孝”的原则的行为,都将会受到“孝”所造成的舆论圈的围攻;而当舆论不足以制衡,作为“孝”的化身的统治者便会直接出面加以惩戒。人们为了免致忧毁,便自觉地拿“孝”来衡量并规束自己的一切言行,以尽可能的符合“孝”的要求。惶惶唯恐不及,棲棲只怕得咎,便成了孝道者的一种普遍心态。“孝”的内涵的无限广延,表面上看抬高了“孝”的权威,实则造成了它的荒谬,即实现了统治阶级想用“孝”的合理内核以掩饰他们一切无理行为的迷梦的荒谬。
“孝”的貌似有“礼”而实则无“礼”,看似公正而实则乖谬,是造成封建社会人的行为怪异和心理失常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是造成《琵琶记》的男主人公蔡伯喈仕与“孝”相冲突、并最终导致他陷入仕与“孝”抉择两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人类乌鸟反哺的天性和本能,也由于受人类优秀文化的感化和熏陶,蔡伯喈一开始是把“孝”,把奉养年迈的双亲当作他今后人生途程上的第一要务而时时萦挂心怀。对于其它的事情,甚至对于封建社会里被视为士子正途的必经“金门槛”——科举,他都弃置一边。从《琵琶记》的描写我们得知,饱受了囊萤映雪、十载寒窗之苦的蔡伯喈,是一位才学超卓的知识分子。他自己曾说:“蔡邕沉酣六籍,贯串百家,自礼乐名物以至诗赋辞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乐术数,靡不极其精。”〔1〕他把步蟾宫折桂,视如平地拾草芥; 登玉堂金马,看做举步游春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不是蔡伯喈觍颜骄矜,他确是一个“济时英,经世手”。正由于他是名重当时,州郡才连下辟贤书征召。面对唾手可得的功名,蔡伯喈是什么态度呢?他是“心恋亲闱,难舍亲闱”。他想到年迈的高堂似风烛夕日,躬身服待尚且朝不保夕,一旦自己这个蔡门唯一的壮丁离去,岂不是眼睁睁把父母推向绝路?所以,他辞召不仕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心甘情愿,内心也有过矛盾斗争,但最终毕竟还是以念亲报孝的道义驱除了仕宦扬名的诱惑,下定决心,打算力行孝道,“只要尽甘脂”:“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是今日。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却落后了戏彩斑衣”。应该说,蔡伯喈的这种认识和选择应予肯定,因为它是保障人类得以正常生息繁衍的优秀传统的落实,是人性闪光点的外显,也适合“孝”的合理正确内核的要求。有儿若此,父母本应感到满足,感到骄傲和自豪。遗憾的是,蔡公并不这么看。他受被封建阶级篡改过的忠孝观的毒化,满脑子可叹可怜的愚腐识见。他教训蔡伯喈,说他只注意了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进汤食、疗疾患、送终老等“孝”的“微末常事”,忽视了“孝”的至大至重者。蔡公所谓的至孝大孝是什么呢?是立身事君。他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如果以家贫亲老为借口辞试绝禄,不是孝,而是不孝。蔡伯喈反问:我去应试,考中便罢,如不得官,既不能事君,又不能事父,这岂不是两耽误了?蔡公执迷不悟,顽固地认为:事亲事小,做官扬名事大。“你若衣锦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都是喜。”蔡伯喈在他糊涂老爹给他布下的饱含统治阶级意识的“孝”的怪圈里,一筹莫展:不仕,亲命怎敢违?出仕,父母依靠谁?出仕的行为又破坏了亲训必遵的礼制规定,损害了父母在上的威严,无疑也是不孝。进不是,退不是,难煞了蔡伯喈。
蔡伯喈落于这种两难抉择的窘境,我们当然可以归咎于蔡公的糊涂僵滞。但如果仅罪蔡公,对他也是莫大怨枉。实际上,蔡公更是受害者。他不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应是被统治阶段泛化了的孝道观。一旦“孝”的内涵无限广延,连“仕”也置于它的框架内,“仕”与“孝”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冲突的解决,无论选择哪条路,最终的受害者都将是实施“仕”与“孝”的个体,胜利者,得益者则总是规范“仕”与“孝”观念的统治阶级。蔡伯喈出仕后父母双亡,自己也饱嚐自悔自责的痛苦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蔡伯喈矛盾心态的第二个感性显现是仕与本位的迷失。
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耻于谈钱言利,清高自许。孔子曾谆谆酵诲过他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校斗量升,见利忘义,是庸碌卑俗的商人,以及专心敛财扩地为要务的土豪爱干的事情,“君子”对这样的事不愿为不忍为也不能为。“君子”干的都是些“小人”不感兴趣,却关于人性修养之大节、伦常秩序之规范和社会运作之机理的形而上的事情。知识分子是“君子”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中坚。他们为了承担起历史交给他们的济世拯民、治国安邦的大任,便必须有意识地培植抗拒声色口腹之美的坚强心理,自觉阻抑乃至消除因本能而时时骚动不已的物欲。他们知道,只有安于贫贱,甘于淡泊,才能磨砺精神高扬人格,才能使自己在任何危苦处境下,都不会忘记作为人类的良心、社会的精英所具有的神圣使命。由于我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总觉着社会历史的神圣使命在不断召唤着他们,他们才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现世的享乐,来换取更多的人能更理想地生活,并想以此推动整个在社会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他们陶醉于自己假想出的这种美妙的理想光环,对凡俗的营求追逐视而不见,或是虽见而不动心,不艳羡。
这是一种多么可感可叹且令人无法非议只能敬仰的人生。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抱着这样的人生信念来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塑造自己的人格,使他们能在外宇宙的纷扰中保持内宇宙的平衡,使他们在财货的窘迫和精神的富足下强化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如此说来,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节操,从不把自己的得失萦怀,从不为名位而讫讫奔走了吗?我们当然还不能下这样的断语。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尽管我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颇为矜夸,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欺人又欺己的盲目自信。他们的言行,和他们对自己的期许也包括社会对他们的高估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里,由于皇权的无上尊崇性和官宦阶层的特殊性,使得士——知识分子一从母体剥离,便注定了他们理想的幻灭结局。当他们觉得自己的修为已具备了介入并影响社会的资格而步入仕途,残酷的现实便一下子把他们从天上拉回地面。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加入很欢迎。知识分子的加入,可以带来新鲜血液从而保持本阶级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清高狷介、卓尔不群又颇为厌恶。因为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高洁人格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统治阶级灵魂的丑陋卑污。统治阶级感到不安。故此统治阶级一方面欢迎知识分子投入自己的怀抱,一方面又给他们立下了苛刻的“进门”规矩:必须转型原有人格,抛弃原守观念。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交换。面对这种交换,知识分子中的坚定者会拂袖而去,老死田园;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会乘机献媚,平步青云;而知识分子中的动摇者则可能先是抗拒既而妥协最终同化。老死田园者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节操尊严,投机、动摇者则或情愿或被迫交出了自己的灵魂而蜕变为官僚统治者。可见,“仕”是知识分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口,一道门槛。对于这道关口,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而一旦他们轻率地跨入这道门槛,及至觉悟想抽身退步,又谈何容易。经“仕”的大网收罗一遍,纯粹的“士”——做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游离开其它阶层之外的知识分子——便剩不下几个了。当然,也就谈不上在历史舞台上,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发挥他们本身所特有的巨大作用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也是中国人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从高则诚赋予蔡伯喈的性格特征来看,从蔡伯喈在《琵琶记》中所显示的言行来看,蔡伯喈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动摇者。
蔡家不是门阀大族,无祖荫可庇;也不是富商豪神,无资财可依。但是,家道衰微,物质享受的低下,并没有使蔡伯喈难堪不平。他没有太大的奢望,要求不高。父母双全,安寿康宁。妻子贤淑,两情欢洽。一家人父慈母爱,夫唱妇随,融融和乐,事事遂顺。蔡伯喈感到很满足。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安安稳稳、闲适从容地度过,并没有什么不好。光宗耀祖、青云驰骤的念头,只是从他脑海中一闪即逝。因为他不愿意抛弃年在桑榆的高堂,贤淑俊稚的骄妻和纯朴恬淡的田园。蔡伯喈“坐对排闼送青青山好,看将绿护田畴绿水浟”,他感慨“清淡安闲,乐事如今谁更有?”“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候?”“人生青春难再,惟有快活是良谋。”蔡伯喈的这种人生态度,从消极一方面来说,是把个人的安乐看得太重;从积极一方面来说,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纯正品性不受上层统治者熏染,却也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蔡伯喈自我设计的这种人生方案,在环境舆论的影响、统治阶级的胁迫和家庭亲人的期待三者所形成的一股强大合力的重重碾压下,最终没能得到落实。
封建社会,不管知识分子怎样自我设计、自我看待,人们评价他们价值高低的标准往往是功名利禄的大小。取得的功名利禄越显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越辉煌。反之,如果褐衣不脱,田园常驻,那么即使品格皎日月,气节贞青,也难为世俗爱重。这种追功逐名的环境包围着每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的家长自然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威压。已得高位令名者,要求子女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求固家业;清寒卑贱者,则希望子女能乘龙飞升改换门楣,当士子们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和父母沉重梦想的载体,他们想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仕”的牢笼的束缚,又谈何容易!因此,蔡伯喈能顶住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屡辞征书,可是,父亲的热切企盼和邻里的善意义举却粉碎了他的斗志。蔡公苦苦哀求:“萱室椿庭老矣,指望你换了门楣。”“你若衣锦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并向蔡伯喈描绘中官后的美景:“你休道无人供养,你做得官呵,三牲五鼎供朝食,须胜似啜菽并饮水”。邻居张大公也谆谆劝告:“你为甚在十年寒窗下无人问?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你若衣锦归故里,谁知你读万卷书?”又慷慨允诺:“秀才但放心前去,不拣有甚欠缺,或是大员外老安人有些疾病,老汉自当应承。”亲情邻意叠加,淹没了蔡伯喈不愿赴试的千万条理由。无可奈何,蔡伯喈只好“马行十步九回头”地踏上了应试之路。
蔡伯喈凭借自己超凡的才华,“折得蟾宫第一枝”,中了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转眼之间身价百倍。但是,地位的变化并没有相应地给蔡伯喈带来成功的喜悦,他内心并不轻松。他凭直觉敏锐地体察到自己跻身官僚阶层后,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无条件地服从皇权的安排。对于一个本有独立人格、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不甘心可又必须接受的痛苦的安排。蔡伯喈抑郁、愁烦、愤怒,他拼命保护着自己心灵深处那一角可怜的“圣地”——独立和尊严,想不让官僚阶级的浊流浸渍,以使自己在今后人生疲惫时有个休息的场所。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皇僚势力面前,蔡伯喈显得太单弱了。他挣扎到最后,还是未能避免被支配、同化的悲剧:他不想攀高趋贵,宰相偏偏看中了他,软硬兼施让他做了女婿;他想辞官归里孝敬双亲,又被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而冷冷拒绝。蔡伯喈绝望了。他只好把知识分子的那点孤高、纯真、自由打叠起来,横下一条心,顺着所有官僚阶层的人所惯走的道路蹒跚着滑落下去。
蔡伯喈矛盾心态的第三个感性显现是仕与情贞的对立。
中国是雄性的国度。封建社会的男子,无论是在生产实践领域,还是在两性情感生活当中,都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要求男子承担起社会主角应干的一切,男子也乐于承担社会分配他们的重任。造成这种史实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男子的生理特征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们做驱动历史航船前进的舵手,另外,则导源于孔孟儒学对两性社会角色的畸态规定。孔孟儒学出于“唯小人与女子唯难养”的偏见,抓住男子的一点点优势无限夸大,并创造机会让他们的优势充分施展,随后再从理论上将他们的优势抽绎概括形成普遍范式,从而把男子抬高到令女子瞠目结舌、自惭形秽的程度。两性角色的反向分裂和固置,虽说在社会生产领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在情感领域却显得无比乖谬和反常。因为真正情感交流的前提是平等。任何人想在情感领域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领域树立权威,最终的结果都会是得不偿失。所以,伴随着中国男子家庭地位的尊显,伴随着他们支配欲和统治欲的无节制满足,情感交流特别是爱情交流,就由双向回环演化为单向恩赐。恋爱婚姻,就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婚姻而抽去了梦牵魂绕、灵肉混一的恋爱。恋爱的结晶家庭,也就完全以和社会组织同构同质面貌出现失去了它原有的爱的温馨和情的浪漫,成了一个个冷冰冰的人生道路上的驿站。男子是这一个个驿站的主人,他们当然可以任意栖止,任意施为,可是,他们既已失去了情感交流的平等对象,那么他们的人生苦恼和情感变化,便不愿也没法向别人倾吐而只能自己默默咀嚼了。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婚姻不光给女性造成痛苦,男子的身心也备受戕害。
封建礼制的污土窒息掉人们的真情而堆起的千千万万座爱情的坟墓,在情感的旷野里是那样密集和醒目。多数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却刺激了少数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他们度人推己,悚然心惊。他们一面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礼教以见容于社会,另一方面又在世俗容忍的范围内有意识地进行试探和抗争。正由于有了他们的努力追求,中国历史上才有了几个虽然稀少却绚烂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有的美满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的凄惨如陆游和唐婉,但无论成功与失败,都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和感召。
对爱情的荒漠感到厌憎的高则诚,应该是在接受了这种鼓舞和感召的前提下,才塑造出了蔡伯喈这个在爱情生活中虽有真情却又不敢大胆表现,虽然不满传统教的束缚却又无力反抗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
蔡伯喈的婚姻,走的也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老路。是封建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把他和赵五娘两个原本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女硬捏合到了一起,这是蔡伯喈的不幸,不幸之中又有大幸,蔡伯喈竟得到命运的青睐,在百不遇一的微小机率中碰上了一个知音,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令他满意的人生伴侣。蔡伯喈额手称庆。他准备和“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蘋蘩之托”的新婚妻子一起,在服侍父母终老后,过一辈子男耕女织艰难而又甜蜜的农家生活。
被逼出仕,惊破了蔡、赵的鸳鸯梦。行前,蔡伯喈和赵五娘泪汪汪,互相叮咛。蔡伯喈托嘱赵五娘:服侍年迈的双亲,“饥时劝他加餐饭,寒时频与衣穿”;赵五娘则劝戒蔡伯喈:“儒衣才换青,快着归鞭,早办回程。十里红楼,休重娶娉婷”。蔡伯喈对于自己的出仕,只是看作完成父亲宿愿的孝行,而没有意识到他一旦步入仕途,会对他的婚姻产生什么不利影响。赵五娘意识到了,她从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被压制、遭抛弃的不幸,敏锐地意识到了丈夫一旦考中,地位的变化会给他们的爱情蒙上浓重的阴影。赵五娘忧心忡忡,她对自己婚姻的前途充满了疑惧。
果然,蔡伯喈中状元后的遭遇印证了赵五娘的担心。
蔡伯喈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欣喜的笑纹还未在他脸上开满,祸事便接踵而至。他被牛丞相看中,要招他为婿。对于一般的世俗弟子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幸运。而对于忠厚笃诚、情真意挚的蔡伯喈而言,却是意想不到的麻烦。蔡伯喈赶忙申说自己家有妻室,无意再娶,再婚不告父母,也于礼不合。蔡伯喈的推三阻四,“不识抬举”,触犯了牛丞相的权威。他为了压服蔡伯喈,抬出了皇上,请皇上下丹凤诏,命蔡伯喈完婚。蔡伯喈在上殿陈情不听,辞官辞婚不准的情况下,只好违心地再婚牛府。
蔡伯喈的妥协说明了他的软弱。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对于他的这种情感上的不贞我们也不能过份苛责。既然整个社会都把女子视为体现男子价值和能力的附属物,那么这种附属物相应的就可多可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男子占有的女子越多,他的地位可能就越尊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就越高大,所以,我们对蔡伯喈的已婚再娶,应该同情而不是鄙薄。
我们同情蔡伯喈,当然并不意味着肯定他的负心变节。我们同情他,是同情他在婚姻中的不由自主、受人摆布的地位,是同情他旧情难忘新人难抛的尴尬处境。
无庸置疑,整个男性群体在封建社会里占居绝对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为了取得并巩固这种地位,却不得不付出在感情生活中自主地位丧失的沉重代价。具体说来,就是男子对女子的支配以及整个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对单个男子支配的双重制衡现象的存在。也就是说,家庭中的男子要受父母主要是父亲择媳意志和标准的操纵;在社会中尤其是步入仕途的男子,要受所属阶级文化规范和上层人物权益维护及再分配需要的影响。拿蔡伯喈来说,在家他要受蔡公的管教。蔡公要他和赵五娘结合。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蔡公要他和赵五娘分离,他又只能眼泪长流地和赵五娘辞别。在官场他要受职权比他高的人物特别是皇帝的摆布。牛丞相看中了他,他就必须娶牛丞相的女儿。一旦蔡伯喈稍有推拒,牛丞相便抬出战无不胜的皇上迫使他就范。可见,蔡伯喈对自己感情的命运无力也无权把握。在家庭中他无力无权,是由于他自愿尊奉传统的人伦孝道观念;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场中无力无权,则是由于他屈从于封建等级制特别是皇权的强力威压。如果说由于蔡伯喈对孝道的尊奉还偶获情感的谐适,那么他对强权的屈从就只能导致他情感的分裂,导致他旧情难忘而新人难抛的痛苦处境了。
造成蔡伯喈在新情与旧情的纷扰争夺中郁闷、恐慌、痛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主要导源于他的试与仕。
蔡伯喈应试中了状元,他才具备了得到牛丞相青睐的资格,他才有可能以“天禄石渠贵客”的身份与“瑶台阆苑神仙”结合。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往往把婚姻当做巩固地位、扩大势力的惯用手段,因而他们要求联姻的对象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家世显赫,有祖荫可庇,有权势资财可依;二是本人志高才雄,有功名可待。二者全备虽理想却难求,退而求其次,目光浅狭者多挑剔家世,目光“远大”者则偏重个人的资质潜力。牛丞相算是统治阶层中的“目光远大”者,他对张尚书、李枢密的求婚一概回绝,特别提出:“除非做得天下状元,方可嫁他;若是别人,不许问亲。”他知道,状元是天子的门生,是未来相位的候补人。招赘了状元,也就是为女儿同时也是为自己、自己的家族的将来找了一座靠山。这样一来,便决定了蔡伯喈只要考中状元,就免不了菟丝再挽的悲剧。
蔡伯喈入仕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和尊严。他一入仕,就等于他自己的后半生卖给了皇帝。皇帝要臣下死,臣下都不敢不死,皇帝为了本阶级的团结和利益,让蔡伯喈牺牲一点儿女私情,更是小事一桩,蔡伯喈怎么能拒绝呢?所以,当蔡伯喈不甘受“闲藤野蔓”的纠缠而上书皇帝请求公道时,皇帝的一句话,便打碎了蔡伯喈的幻想和意志,他只能忍受着良心的谴责和道义的煎熬,把自己的贞情埋葬。
蔡伯喈曾多次哀叹:“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其实,读书求知并没有错。错在“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观。是仕,使赵五娘形只影单泪水涟涟;是仕,使蔡伯喈迷失本心并丧失独立人格。仕,是染缸,是鸦片,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旦经受不住它的诱惑而投入它的怀抱,不管你情愿不情愿,最终往往会堕落成一个“须眉浊物”、“国贼禄蠹”。蔡伯喈的人生规迹私心灵蜕变历程,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注:本文所引《琵琶记》原文,皆据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