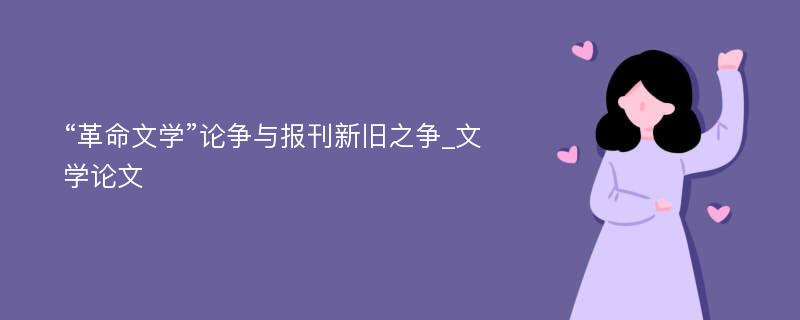
“革命文学”论战与报刊的新旧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之争论文,新旧论文,报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 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②,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③。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新”与“旧”的对峙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④。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⑤。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⑦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⑧。《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⑨,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⑩ 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通过考察卷入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的数十种报刊,我们发现,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大多是1928年前后方才创刊的新兴刊物,比如影响最大的《文化批判》(1928年1月)、《创造月刊》(1926年3月)、《太阳月刊》(1928年1月)、《流沙》(1928年3月)、《泰东月刊》(1927年9月)等等;而《语丝》(1924年11月)、《北新》(1926年8月)、《文学周报》(1921年5月)、《小说月报》(1921年1月改版)等革命文学家主要对手报刊的创刊时间则要早得多。1928年这个历史刻度对刊物的特殊意味,倒正好应了鲁迅那个说法:“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11)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文学论战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是报刊的“新旧之争”,它固然是不同文学理念和政治态度的反映,但同时多少也表现为报刊出版在新陈代谢时不可避免的争执与振荡。
革命文学家这种对“新”的追求和对“旧”的厌弃,甚至被用来鉴定作家的进步抑或落后。冯乃超在向鲁迅首先发难时,直呼鲁迅为“老生”(12)。如此人身攻击激起了鲁迅的极大愤怒,斥之为把“论战”变成了“年龄战”(13)。蒋光慈也曾明确说过:“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是已经是衰颓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的逼着!……”(14) 在这里,“新”“旧”之辨不再是某种事实的描述,而已扭转为一个价值评判的问题:“新作家”因其“新”而获得了对时代的发言权,“旧作家”因其“旧”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喜新厌旧”的态度既显示了革命文学家们在线性时间观支配下的一种现代性冲动,也暴露了他们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
王独清指出:“我们目前的世界已经分裂成了两个整个的团体:一个是在尽情地榨取,一个是在血淋淋地苦斗。这两个团体底激战将要愈进愈猛,而绝没有一点可以融合的余地。”(15) 于是,成仿吾会声色俱厉地要求作家和读者选择:“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16) 郑伯奇也断言:“今后无论那种刊物,无论那个作家,都有思想的背景的,不是正动,必是反动。”(17) 在此背景下,对那些卷入“报刊之战”的刊物来说,尽管每期登载的文章立论各异,但是反对还是赞成“革命文学”的问题上则大都态度鲜明。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报刊,很难找到那种能够提供相对宽容的空间,让论战双方在上面同时出现,展开平等而理性的辩难。它们总是可以被大致归入某个集团或者某个阵营,自顾自地“论”而且“战”,与哈贝马斯所谓依靠报刊的“普遍开放的原则”(18) 建构一个理性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西方经验相去甚远。
除“旧”布“新”
当然,事情也有它更复杂的一面。对一个刊物来说,它的姿态往往又会随着刊物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摇摆和调整,从而使得它与其他刊物的关系以及在整个文坛格局中的位置常常游移不定。比如《创造月刊》,它创刊时(1926年3 月)的初衷只是想为创造社保留一个以发表创作为主的纯文艺刊物,因为当时创造社已经有一个以发表批评和论文为主的《洪水》半月刊。其实,这种“文”(作品)—“论”(评论)搭配的刊物组织模式,是在延续前期创造社《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创造日》相互分工合作的关系模式。不过,在1928年1 月续出第一卷第八期以后,《创造月刊》开始在醒目位置越来越多地刊登提倡革命文学的论文,比如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等等。在事实上,它此时已经与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一道成为“革命文学”阵营最主要的阵地之一。但或许是仍不满于刊物保留的因袭形象,《创造月刊》利用第二卷出版的机会,宣布刊物要来一次“革命”:
第一卷的《创造月刊》,是中国文坛上唯一的纯文艺杂志,曾得了万千读者的热爱。现在是第二卷在开始了!它将重新开始它的步武,将积极地从商品化的,奴隶化的现代艺术,求她真正的解放,更将建设解放的艺术,建设人类解放的艺术,建设Proletarian艺术,同时还要积极地肃清一切庸俗的批评家的见解,克服一切反动的著作家的言论。因此,以后的《创造月刊》是不再以纯文艺的杂志自缚,它将以战斗的艺术求他的出路。(19)
从“纯文艺的杂志”到“战斗的艺术”,《创造月刊》这样原本就已革命的文学刊物尚且需要自我改造,力图变得更加革命,那么随着革命文学运动渐成潮流和时尚,那些当初对立于革命文学的刊物也不得不改换门庭,刷新改版。一度成为“革命文学”阵营最强劲对手的《语丝》,在鲁迅卸任主编,尤其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直接接手编务之后《即第五卷第二十七期以后),对待革命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刊物在醒目位置上登载了介绍各国左翼文学状况的论文:《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第五卷第三十四期)、《英美的左倾文学》(第五卷第三十九期)、《苏俄普罗文学发达史》(第五卷第四十四期)、《戏剧之唯物史观的解释》(第五卷第四十七期)、《革命十年间苏俄的诗的轮廓》(第五卷第四十八期)。这些论文大多是译文,涵盖了左翼文学比较发达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日本、英美和苏俄),也涉及了不同的文学类型(戏剧和诗歌),显然是在有意识有计划地介绍和提倡。创刊时声称不愿“被色彩与旗帜来束缚”,“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20) 的《金屋月刊》,此时也开始翻译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一万二千万》。邵洵美等人为了追逐时髦、招徕读者而这样放弃自己的立场,立即引来革命文学家不无得意的嘲笑:“……素以唯美派自居的《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21) 在这股席卷全文坛的“转向”潮流里, 《大众文艺》的变化尤其引人注意。
《大众文艺》月刊1928年9月20日创刊,由郁达夫、夏莱蒂主编,现代书局发行。此时的郁达夫早已和创造社决裂,按照冯乃超的说法——“时代忙快地流换,地球不绝地迴转,他们没落的没落,革命的革命去了”(22)——他是“没落”的代表人物。郁达夫在创刊号上这样解释“大众文艺”的含义:“‘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23) 在这里,郁达夫既没有讲清楚何谓“大众”,也没有讲清楚何谓“大众文艺”,但他从反面把“大众”与“阶级”区别和对立起来,认为“大众”的文艺就不应该是某一“阶级”的文艺,它的对象应该是一般的读者。显然,在以提倡文学的阶级意识为指归的革命文学热潮中,为刊物确立一种非阶级姿态本身也是另一种阶级立场的表达。郁达夫还表示:“‘大众文艺’也没有多大的野心,不过想供给一般读者以一点近似文艺的东西而已。”(24) 在此理解下,《大众文艺》倒也果真办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以翻译为主的纯文学杂志:鲁迅、夏莱蒂的译文,郁达夫、叶鼎洛的小说……大概也正是因为“没有多大的野心”和面向所谓的“一般读者”,刊物出了半年就难以为继了,不得不停顿下来。
1929年11月1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出版,主编改为陶晶孙(署名“大众文艺社编辑”)。续出的《大众文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之前常见的鲁迅、郁达夫、叶鼎洛等作者不见了,代之以陶晶孙、段可情、邱韵铎、龚冰庐等一批创造社的成员;翻译的小说少了,出现了一个叫做“大众文艺小品”的栏目,专登一些浅显的小品,还多了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木人戏”(木偶戏)的作品。陶晶孙在编后记里表示新《大众文艺》将“刷新内容”,但如何刷新却有点含糊其辞,只是对“大众”的概念稍微做了一点澄清:“大众是个无组织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大众,因为没有统计,不能说出确数,总之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25) 通过把“大众”与“农工阶级”联系起来,陶晶孙事实上是在修正郁达夫对“大众”概念的非阶级甚至反阶级的理解,从而重新定位《大众文艺》的基本姿态。如果说“因为大众文艺有历史的关系,和书局的关系”,陶晶孙“采了一个渐进的方针,没有能够把他顿时改变”(26),那么,在二卷三期上展开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笔谈,则让革命作家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纠正郁达夫的“错误”,或者说是纠正郁达夫时期的《大众文艺》的“错误”。郭沫若指责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是“和无产文艺对抗而产生的”,“它的所谓‘大众’是要把无产阶级除外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而真正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所以,“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27) 王独清说:“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底大众,——新兴阶级底大众。”(28) 虽然对何谓“大众文艺”以及如何建设“大众文艺”各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用一种阶级的眼光去打量“大众”则是讨论者们基本的共识。在此背景下,第二时期的《大众文艺》一改郁达夫时期“没有多大的野心”的平淡,而以巩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线”为己任,做好“利用一切表现方法的启蒙工作”、“提倡完善的普洛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刊物的对象也不再是“一般读者”,而是识字的“智识小资产阶级”,并凭借开办大众文艺小品、漫画、少年大众、通信等栏目,“在短时间内要进一步向半识字里面去,再进一步才向农工大众前进”(29)。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大众文艺》就由一个奄奄一息的远离革命的平常刊物,翻新为名重一时的现代书局“四大左翼杂志”之一,直到1930年5、6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在追新求变的风气里,“左转”已成各刊物顺应潮流、赢得读者的普遍做法。于是,在“革命文学”论争已近尾声的时候,钱杏邨终于可以豪情满怀地宣布这场新旧文学观念之战——同时也是新旧报刊之战——的胜果:
经过了一年的苦斗,以及种种客观的条件的成熟,而获得了存在权的普罗文艺,在这一年,虽然因着环境的高压,在形式上没有积极的发展,但那它的力量已经伸展到了各方面——甚至有产者文坛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我们只要展开有产者文艺的刊物,总会看见关于普罗文艺论文以及创作的翻译与介绍,有时也要刊登中国的普罗文艺的作品;姑无论其动机为助长杂志的销路,抑是具有其他的原因,但他们绝对的不能否定普罗文艺,已是极其明显的事。
就是极其保守以及反动的书铺,在这一年,也不免热衷于普罗文艺的销行,而发行关于普罗文艺的书籍了。(30)
余论:报刊生产与文学现代性
上述从报刊对峙和转化的角度来描述“革命文学”论战的过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原本就已聚讼纷纭的革命文学运动增加一种新的叙述话语,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理解完全可能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敞开空间。在当下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热烈讨论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把对“现代文学何以‘现代’”的思考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从语言、叙事模式、文类规范、思想主题、内在精神等各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相比于传统文学的诸种特殊性。不过,这些考察大多是从文学“内部”展开的,而一系列现代文学赖以存在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条件则被忽视了。事实上,正如戴安娜·克兰所说,“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31)。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已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场所”,“这种社会活动场所的特征影响进入这个文化空间的内容的性质,影响到内容的性质如何相应地受到它在这个语境之中表现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它的反应。”(32) 埃斯卡皮则以一种更加历史化的方式指出,正是西方18世纪现代出版业的迅速崛起和繁荣,才导致传统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从此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作品”成了一种待售的商品;“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也不只是学习或者消遣,而更应被看作是在消费文学商品。“总而言之,必须看到文学不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33) 也就是说,文学活动诸要素的关系被重新整合,居于枢纽地位的不再是作家也不是作品,而是出版,正是它才使已延续数千年的文学活动呈现出“现代”的特殊面貌——“文学现代性”由此发生。在这意义上,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与报刊出版的密切关系——“革命文学”论战同时也是一场“报刊之战”——尽管多少得益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但仍可以反映出现代文学在生产方式上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普遍状况。因此,前述把“革命文学”论战置于报刊生产的新陈代谢轨迹中加以描述,非但不是“降格”革命文学运动事关重大的文学史意义,恰恰相反,它通过厘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流通痕迹,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继续思考“革命文学”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深刻联系。
注释:
①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什么是文学史?》,见郭宏安等编:《国际理论空间》(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③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④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见饶鸿競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3页。
⑤ 关于《文化批判》创刊的细节及其与“革命文学”论战中文人集团的关系,可以参考拙文《“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报刊阵营与文人集团——以〈文化批判〉的诞生为例》,[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⑥ 郭沫若:《“眼中钉”》,《拓荒者》第四、五期,1930年5月10日。
⑦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年2月1日。
⑧ 《〈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28年1月1日。
⑨ 成仿吾:《祝词》,《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⑩ 《编辑初记》,《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11)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12) 冯乃超的原话是:“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13) 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10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 华希里(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太阳月刊》四月号,1928年4月1日。
(15) 独清:《新的开场》,《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16)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年2月1日。
(17) 何大白(郑伯奇):《文坛的五月——文艺时评》,《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
(18)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9) 《一个伟大的从新的开场!!!》,《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7月1日。
(20) 金屋月刊编者:《色彩与旗帜》,《金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1月1日。
(21) 邱韵铎:《“一万二千万”个错误》,《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号,1929年11月。
(22)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一期,1928年1月15日。
(23) 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第一期,1928年9月20日。
(24) 达夫:《编辑余谈》,《大众文艺》第一期,1928年9月20日。
(25) 陶晶孙:《从编辑谈到投稿》,《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1929年11月1日。
(26) 《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上册),1930年3月1日。
(27) 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上册),1930年3月1日。
(28) 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上册),1930年3月1日。
(29) 陶晶孙:《卷头琐语》,《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上册),1930年3月1日。
(30) 刚果伦(钱杏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1929年12月15日。
(31)(32)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第21—22页。
(33)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标签:文学论文; 大众文艺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批判论文; 郁达夫论文; 读书论文; 创造社论文; 鲁迅论文; 成仿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