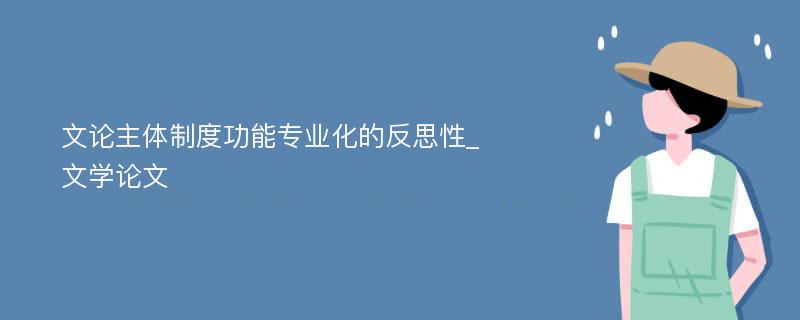
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学科论文,体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897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实现教育现代化或教育的现代化,不仅是百年来中国教育家的一个主要梦想,也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王治河 樊美筠76)。我国百年来教育的现代化,经过前辈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沿着西方和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建制,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根本上并没突破西化和苏化模式。钱穆先生对此痛心疾首:“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76)。陈平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76)。
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西化和苏化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是功能的专门化。功能专门化是一个现代性话题,它是西方现代性分化的产物。哈贝马斯借用韦伯的观点指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142)。由于现代性的分化,这三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又沿着分化的规律和路径越分越细。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指出,当代知识的特征是功能的专门化。他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分化,“科学有一个特征。它同几乎所有有组织的人类活动一样,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内经历着日益增长的割裂、分化和专门化(一分再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细)。自然哲学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后来分成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十九世纪的思辨哲学产生了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分析哲学等等。在今天的任何一个领域,新问题都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专门化:化学曾经被分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最近在一种报表上又细分为碳水化合物化学、留类化合物化学、核化学、石油化学和固体化学”(142)。在这种功能专门化的体制下,大学严格按一级学科专业分院系,各个院系又严格按二级学科划分教研室,即使从事一个专业的老师,还要划分更加细化的专业方向。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定位于“教育的现代化”,学科建制和知识生产都是以功能专门化为原则。仅就文学学科而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该学科三足鼎立的二级学科。这三个学科可逐一细分为各自独立的学科方向,如文学理论作为二级学科,可分为文学概论、美学;美学又可划分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如此类推,文学理论的知识领域日益部门化、差异化和专门化。
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学科建制的功能专门化?
一、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祛魅
文学理论学科体制是现代性分化的产物。分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分化是现代社会告别传统社会、结束宗教一统天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性进程的动力源,是建构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所谓“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主要指在中世纪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知识从来都是宗教的奴婢和工具。知识只有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时,才成为通向真理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自主性是确保知识真理的标准,而知识的自主性则是现代性分化的产物。所以,韦伯认为分化是建构通向永恒真理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文学理论学科作为现代性分化的产物,理应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内容和方法的学科,成为阐释文学艺术真理的知识体系,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服从政治的十七年,文学理论学科的自主性完全被政治消解,成为文学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合法化叙事的知识体系。可以说,十七年的文学理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学科的代言者。新时期以来,我国有良知的学者,历经数十年,排除万难,“以学术为业”(韦伯127),重新确立了以审美意识形态为独特本质的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为文学艺术的专业化发展、为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从事文艺学、美学和文学评论的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韦伯所言:“只有严格的专门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132)。可见,这正是学科建制自主性的价值所在。确立审美性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所在,这是文学理论学科建制走向专业化、自主性的标志,也是其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诉求,当然更是其功能专门化祛魅的彰显,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否定文学理论学科的自主性和功能专业化,我们反对的是过度的自主性和片面的功能专业化。
二、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功能专门化具有祛魅和返魅的双重性,这种同一自反现象,被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4)。何谓“自反性现代化”?乌尔里希·贝克借孟德斯鸠的“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来加以阐释。他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5)。通俗地讲,西方现代化带来了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业文明、科层化、民主化等等丰硕成果,将人类历史跃迁到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殊不知,工业化虽带来了富裕丰盛的物质文明,却又在扼杀和破坏人的生存家园;城市化虽大大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却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和贫穷的蔓延;工业文明虽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肉体消耗,却导致了人的异化;科层化虽提高了社会的理性化和有序化,却导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民主化虽倡导自由平等,却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如此这般的二律背反充斥整个社会,使现代性面临困境与危机。持历史进步观念的学者认为这些矛盾是暂时的、外在的。果真如此吗?齐格蒙·鲍曼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奥斯维辛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时,最初也曾错误地认为“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前言1)。鲍曼将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的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仅归罪于希特勒的人性劣根性。但随着鲍曼对奥斯维辛历史事件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大量的材料都证明大屠杀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21)。鲍曼借费恩戈尔德的话,佐证了自己的上述结论。费恩戈尔德说: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转引自鲍曼11)
可见,奥斯维辛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其现代化的胜利成果生产出来的怪胎。奥斯维辛历史事件的产生,恰恰是自反性现代化的铁证。
同属现代性话语的功能专门化,其自反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透彻而尖锐地予以分析:由于功能专门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社会结构组织日益科层化、专业日益自主化、人才日益专门化、叙述语言日益私人化;与此相对立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边缘化、游牧化,亚文化迅速崛起,由此社会矛盾纵横涌立。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社会与文化、科学与人文、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悖立乃至不可通约,彼此间产生巨大鸿沟。对此,贝尔不得不惊呼:作为具有内聚力和统一性的文化已无法去表现“如此独特而繁乱,或者不可思议”的“经验”(143)。西方的现代性的分化,原本是对大一统的宗教的祛魅,却未曾预料到祛魅的结果乃是返魅,现代性陷入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表征、经济结构与文化表征、文化自身的种种断裂的牢笼。文学理论建制的功能专门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其自反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至今我国文学理论的建制仍行驶在功能专门化的历史轨道上,对功能专门化的诉求远远重于对自反性的反思,才使文学理论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出现了某种困境和危机。要从根本性上探究当前我国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必须从建制的角度进行反思,即对文学理论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进行反思。
三、文学理论功能专门化自反性的返魅
文学理论的自反性主要体现了文学理论的返魅,这种自反性的返魅不是返回到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窠臼中不能自拔,而是呈现一种新的形式,即由其自反性带来的从自主、自足到自恋的返魅;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碎片化的返魅;形而上学体系构筑的体制化、玄学化、教条化的返魅。
首先,从过度自主性到自足、自恋的返魅。从现代性的进程看,分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自反性规律告诉我们,分化在祛魅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地返魅,表现为各个知识领域的过度的自主性、封闭的自足性和唯我独尊的自恋性。哈贝马斯认为,从宗教分化出来的科学、道德和艺术三大知识领域各自形成独立、独特的逻辑结构、对象和方法。从内在结构看,科学、道德和艺术分别对应着“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哈贝马斯143);从研究的对象看,科学对应的是“真理”、道德对应的是“规范性的正义”、艺术对应的是“本真性和美”(142);从针对的问题域看,科学把握“知识”,道德把握“公正性和道德”,艺术则把握“趣味问题”(142)。三大领域只有取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并被民族国家的体制确认,即体制化后,才能构筑学科的自主性。可见,各个学科的“自主价值标准的确立”既是现代性分化的结果,亦是权力体制化的产物。但当学科被体制化后,它的运行路径只能朝着自足、自恋的方向一走到底,否则学科将因丧失了功能专门化而式微,乃至消解。哈贝马斯专门梳理了现代艺术功能专门化的路径、得失和命运。他指出,“在现代艺术史上,人们会发现在艺术的界定和实践方面越来越趋向于自主性的发展。美的范畴和美的对象领域最初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在18世纪的历程中,文学、美术和音乐被体制化为独立于宗教和宫廷生活的活动。最后,大约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概念,它激励艺术家依照为艺术而艺术的独特意识来创制作品”(143)。也就是说,艺术自主性的过度发展,导致了“艺术一样的艺术化生存”(哈贝马斯144)。
“艺术一样的艺术化生存”,因其过度张扬艺术的审美化生存,艺术家为追求纯审美理想隔断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科学、艺术与艺术之间的互文性,将自己封闭于艺术的象牙塔,玩弄技巧、热衷艺术实验以至于自我陶醉于所谓的艺术的标新立异,即自恋之中。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其初期和中期,因其始终以“敌对的姿态”、否定一切的精神和对“秩序”、理性主义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而取得了文化霸权。虽然现代主义文化在文学、诗歌、音乐和美术方面,没有造就多少艺术巨作,但是“现代主义无疑有功于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创作高峰”(贝尔32)。到了20世纪,即在资本主义晚期,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被公众拥趸、被博物馆收藏、被请进大学殿堂、被民族国家认同,总之被体制化后,艺术沦为替国家歌功颂德的工具,丧失了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潮流的威迫下,为在商业市场上求得生存的最大空间,不得不一味地标新立异,一味地离经叛道,走上艺术自治的不归之路。艺术的这条不归之路使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代价之一是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特别在扩大艺术的自治、反对道德约束方面,甚至影响到文化标准的本身”(贝尔32)。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过度地强调艺术的自治、自律,突破传统,颠覆道德,造成了文化标准的更易和丧失,失却了文化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艺术变为自由买卖物件”(贝尔33)。吊诡的是,现代主义文化艺术高举艺术自律、艺术自治的大旗,恪守艺术的边界,追求先锋实验,未曾预料到现代艺术最终却与商品为伍。这大约就是自反性现代化规律在文学艺术功能专门化方面的效应的呈现。更为纰缪的是,现代主义艺术过度的自主性、封闭的自足性和唯我独尊的自恋性,导致“专家文化与公众文化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鸿沟”(哈贝马斯143),艺术追求“与生活和谐的乌托邦已失效了,出现了一种艺术与生活的对抗关系”(哈贝马斯144)。这大约就是自反性现代化规律在文学艺术功能专门化方面呈现出的负面效应,不过,这负面效应却导致了百年的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式微与消解。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对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反思,应该是一副清醒剂。
在文学理论史上,因过度自主性、自足性导致某一思潮流派存留时间短暂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俄国的形式主义。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在颠覆文学研究沦为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工具,在确立文学自身“独立的立足点,使其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独特的学科”(杰弗逊 罗比等21)的宗旨下,提出了文学性和陌生化的美学原则。文学性和陌生化原则的提出颠覆了“艺术是一种认知方式”的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文论向传统文论的开创性突围,成为20世纪文学艺术的新标志。但是由于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性和陌生化仅仅限定在文学的形式尤其是诗学语言的形式特性上,使文学独立于作家、读者和社会,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足的、封闭的系统而丧失了生命力。詹姆逊曾喻之为“语言的牢笼”。安托万·孔帕尼翁在评价文学性时指出:“‘诗学’的功能,仿佛文学(诗学文本)为了强调信息的自为性便废黜了其他五个功能的作用,并将与它们相联系的其他五个要素(发信者、收信者、指涉、代码、接触)剔除出局[……]诗歌,就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35)。俄国形式主义仅仅存活了30来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苏维埃极左政治路线的挤压与迫害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如果单从学术角度论之,我们以为,过度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是其短命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时代语境迫使它采取矫枉过正的极端方法,这是情理之中的,应该公允地评价俄国形式主义,给予它应有的学术地位。
但是,与20世纪初的时代语境不同,20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研究、跨学科一体化研究已席卷了所有学术领域,成为当代显学,更何况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媒体文化、休闲文化、商品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喧嚣裹挟之下,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早已突破了康德式的无功利的美学观,审美趣味发生断裂,纯文学艺术失去主流地位而被边缘化,快餐文化、时尚文化甚至反文化反艺术蜂拥沓来,诸如此类,多样而怪异、复杂而多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伯曼 书名),一切新的东西都瞬息万变。丹尼尔·贝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情绪描述为:“完全彻底”的“价值的颠倒”、“诗人最隐秘的经验”取代“对童年痛苦的强调”、“自我的热衷”、“荒诞感”蔓延、“幻觉当然在吸毒和致幻经验中得到了推崇”、“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智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熔艺术与政治于一炉”(170)。丹尼尔·贝尔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痛心疾首,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当代文化的客观现实,不得不冷静、清醒地对待、思考,认识到“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在美学与内容方面都是如此——已经基本完结”(196)。丹尼尔·贝尔已经看到审美救赎只是个幻象,他开出的拯救当代人类的药方寄希望于后宗教的建立。在这里,评判丹尼尔·贝尔解救人类命运药方正确与否,不是本文题中之意,我想表达的是单靠传统的审美观念、回归经典、坚守精英文化,既不能解决当代文化问题,亦不可能挽回纯文学艺术的中心地位,更谈不上提升当代人的价值尺度,因为那只是“审美幻象”,无益于现实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的建制应该突破“审美”本体论,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灵活多样的方法、更加稳健的跨学科步伐来进行建构。我们不要怕带上“泛学科”、“泛文化”帽子,走自己的路,只要有利于解答现实问题,文艺理论的学科建制就有生命力。
其实,对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我们承认审美性是其重要的本质,但不是唯一本质,更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本质。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学者从审美现实的巨大断裂中,已经洞见到文学艺术本质的开放性。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罗兰·巴特认为“一言蔽之,文学,即教授所授之物”(转引自 孔帕尼翁22),此即“文学就是文学”(22)。伊格尔顿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11)。约翰·M.埃利斯说:“‘文学’一词的作用很像‘杂草’一词:杂草不是一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工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愿在他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转引自 伊格尔顿11)。热奈特认为“文学性具有多样性,所以必须用多种理论来进行解释”(转引自 孔帕尼翁37)。孔帕尼翁则强调“文学没有实质,是一个复杂、异质、变化的现实现象”(37)。上述学者并不是要否定文学艺术的本质,而是要建构一个开放的、科学的、能回应现实的文学本质。在这个真理尺度上,承认理论的幽灵是存在的,但理论不是提供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理论是相对的”,“理论是批评、是论战、是战斗”(孔帕尼翁14;6),唯其如此,文学理论才有生命力。
其次,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碎片化。碎片化模式是指“现代教育学科过度条块分割现象以及分离身心和隔绝知识与生活的倾向”(王治河 樊美筠84)。学科分类的专业化将知识分割成一块块老死不相往来的知识碎片,人为地将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知识与生活实践对立起来。怀特海认为,“学科碎片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把同专业的人安排住在一起,认为这样有助于学习和研究,这样该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和化学专业的学生就很少接触了,更不用说接触人文专业的学生了”;“过分的专业化特别是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对立的坚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悲剧,对社会的未来将造成严重伤害”(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84;85)。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碎片化表现为:大理论与小理论的对立;理论与生活、与文学艺术现实的对立;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私人化语言与公共话语的对立。功能专门化的文学理论只注重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风格论和批评论,而且限定在宏观领域的叙事上,对于文学艺术当前所出现的民间叙事、民俗叙事、身体叙事、网络叙事、身份叙事、福利叙事、民主叙事以及表达芸芸众生政治体验、政治诉求、政治身份建构、民主渴求等等微观的政治叙事,因其越出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围,难以登上高贵的文学理论殿堂而空缺。功能专门化的文学理论过度强调自主性,凡与文学审美性不相兼容的生活知识、大众知识、科学知识都遭到排斥,一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就只能是单一的、碎片的、孤立的、精英的、私人化的。吊诡的是,明明是用以总结文学经验、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理论,作家并不买账,还讽喻为“理论是灰色的”。如果说十七年的文学理论是灰色的,还言之有理,但恢复了文学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仍然被说成是灰色的,就值得我们深思。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表明,我们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是内在关联同时发生的,每一问题都不可能单独得到解决”(王治河 樊美筠85)。解决这些问题,如艾滋病、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房地产,不是单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治理好,而是要动用多种学科知识,靠系统工程的综合治理,才能有效解决。法国一位总理说过:“毁灭男人事业的方式有三种:沉湎女色是最快乐的一种,迷恋赌博是最迅速的一种,而迷信专家则是最确定的一种”(转引自 王治河 樊美筠85)。要改变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碎片化、精英化、专家化,我们认为不妨首先关注小理论,将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小理论,或曰微观政治诉求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在对21世纪批评作述评时,围绕身份、对话、空间和地点、批评的声音、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五个关键词,既密切关注当代学术热点,又进行跨学科研究,认为小理论研究是21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其次对文学理论开展多重阐释,在西方,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比如迈克尔·莱恩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男/女同性恋研究、历史主义、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方向解读同一文学文本,展开多重、多维的立体式文学研究。这种多重阐释建立在学科间性的立场上。罗兰·巴特认为应当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而创造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的新对象,则是交叉学科性研究的关键。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才能突破纯文艺学的疆界,实现跨学科的整合。在课程设置上,以文学理论和美学为轴心,向多学科延伸,既有文艺学的专业方向,又能通达上至大文化,下至不同的知识门类,实现从文明史、文化史、科学史的大视野,融科学与人文、基础理论与前沿最新知识、理论与现实为一体的知识结构。
再次,形而上学的体系构筑。从五四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界热衷编写、修订文学理论教材,将教材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架之中,授予其合法化性、通用性和工具性。大学的文学理论的体制化使理论简化为教案。孔帕尼翁指出:“理论不应被简化为一门技巧,一门教案,当它成为规则技巧的汇编、带着色彩斑斓的封面被摆在拉丁区书店的橱窗中时,它就已经在出卖自己的灵魂”(7)。他认为此类教材的功能降低到只能“让教师省心,为学生分忧”,原因就在于“那些教材所谈的不过是理论中的细枝末节。它们不是让理论失却本性就是将其引入歧途”(8)。与文学理论体制化相伴而生的是理论的教条化,即理论先行、先入为见;概念立法、观念僵化;经典重复、常识永恒;原理加例证、演绎归纳。这种教条化的文学理论在大学课堂上已失去风光,目前文学理论在大学殿堂虽然还被众多学子研习,但其缘由并非是钟爱,而是体制规定文学理论为本科、考研必修课使然,文学理论实质上已被边缘化。文学理论边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形而上的教条化。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和文化实践,应该随着文学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由于理论严重脱离文学实践和文化实践,文学理论不仅不能科学地回答文学实践、文化实践涌现出来的新问题,而且还成为桎梏文学的堕力。理论应该是战斗的、是批判的、是富于活力的。一种新的理论的产生往往是对固有观念的反思、批判、甚至颠覆的成果,而不是一味追求本质化、概念化、精致化、体系化、神秘化成为一种玄学。科学的理论不仅会被作家艺术家所拥护,而且也应当为大众所接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很多著名的理论家为文学理论的通俗化、实用性和战斗性而不断探索,如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和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所以,孔帕尼翁认为:“文学理论绝非宗教。再说,文学理论未必只有一种‘理论意义’,我完全有理由说,它很可能在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生有反骨的”(7)。
总之,文学理论体制的功能专门化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既具有祛魅的历史进步性,又具有返魅的自反性,即过度自主性到自足、自恋的返魅;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形而上学的体系构筑。功能专门化使文学理论丧失了理论的实践品格、历史品格、创新品格而陷入困境。理论的幽灵无处不在,文学理论的复兴,单靠传统的审美观念、回归经典、坚守精英文化,既不能解决当代文化问题,亦不可能挽回纯文学艺术的中心地位。我们应该在恪守文学理论审美性、自主性的前提下,坚守理论的相对性、开放性、实践性,从而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灵活多样的方法、更加稳健的跨学科步伐来进行建构。
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性论文; 自反性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体制化论文; 文艺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