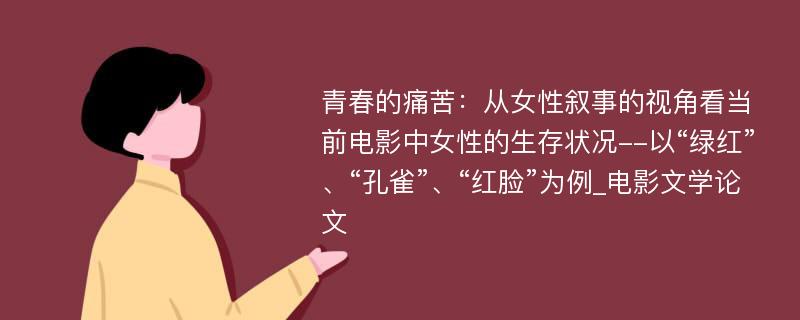
青春的伤痛:从女性叙事视角看当下电影中女性生存境况——以《青红》、《孔雀》、《红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境况论文,为例论文,孔雀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梅尔文·L.德弗勒曾说:“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生信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成分影响他们。”①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是以电影技术为手段,以画面和音响为媒介,在银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门艺术。”②任何电影的题材都来源于生活,而在当下电影中大多数女性形象都被男权文化赋予种种意义和价值,女性的自我之声被抹杀、被压抑。女性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愿望普遍被男权意识为主导的形态所代替和淹没,女性的生存境况没有得到重视。在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的今天,当下电影的叙事视角和电影中所形成的关于女性的影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正如福柯所感慨的那样“这个世纪最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事件和幻象”③。电影《青红》、《孔雀》、《红颜》主要给我们讲述了女性个人青春成长的梦想和伤痕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女性生命面对强大的父权喑哑失语,看到了女性理想的破灭,看到了女性生命的轮回与无奈。本文将以这三部电影为例,在女性叙事的基础上,探讨当下电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青红》——父权制下女性无言的疼痛
《青红》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2005年的作品,主要讲述了青红这个核心角色所承受的命运的悲剧和在父权制下所承受的无言的疼痛。上世纪60年代,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无数个家庭跟随着自己的工厂从上海、北京、沈阳等大城市来到西部贫瘠的山区。他们在这里开荒建厂,支援三线建设。时至今日,大部分的人依然留在山区,那里成了他们新的故乡。电影《青红》以这个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贵阳的故事。青红的一家响应政策号召,举家迁至贵阳,和上海的许多家庭一样,这些家庭为三线建设作出了贡献,却被遗忘在山区。变革中的中国给国人带来新的希望,而在这里,对于那些被政策遗忘的家庭而言,回到故乡成了他们的心愿。遭受了边缘化命运的父辈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生活,希望能回到父辈们迁出的故土。于是父亲严格要求女儿青红“在家好好复习,别没事老往外跑,考上大学,风风光光的回上海”。而孩子涉世未深,不能体会和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返沪的梦想对于她来说意义不大。青红和当地的青年小根恋爱,父亲坚决反对,以至于每天放学都跟着她,“像跟踪犯人一样”。故事的情节就在父亲和青红的矛盾中展开,确切地说,是在父亲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展开。在父亲的强权压制下,青红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当无奈的青红告诉小根“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家不久就要回上海了”。小根一时冲动之下强奸了青红,悲剧在继续进行。在这里,男女都是陌生的、无法进行交流的客体。即使相爱的人也无法共同承担苦难,只能是悲剧的牺牲品。青春尚在,青红却早已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与外界失去交流。而小根则以强奸犯的罪名被枪毙。可以说,这部电影从女性的叙事视角体现了女性的残酷青春。正如王小帅所说:“《青红》以青春为由头,却有多重的意义:对自己生命和权利的认证;对勇气的认证;对专制的否定,父亲被专制压住,又去压制孩子,为的又是一种自由,一种非专制。”④女性主义学者罗婷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将西蒙·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概括为三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批判父权制文化中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传统观念。在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女性总是被动的客体,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⑤。《青红》再现的是残酷青春中女性难以言说的疼痛。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价值是通过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女性按自我要求实现的。这就使女性出现了分裂——外部世界对个体女性的要求和规范与女性内在要求之间的张力使女性形成了分裂、分离意识。女性在这种意识下产生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社会规范的自我,这个自我只要母性和妻性得以被认可,就会得到满足和实现;而另一个自我却是女性本真的自我,是自由的女性个体。在影片中,女性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冲突的。对父亲来说,青红的社会价值就是努力考上大学,风风光光的回上海;对青红来说,其自我价值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不是被父亲束缚着。在这两种价值的冲突中,青红选择了社会价值,听从父亲的安排,而这一切却是以牺牲青红的自由选择权利为基础的。在电影中,小根和青红约会的地点被放置在一个有着长长的白色栅栏的气象站旁边,这白色栅栏在电影中出现了多次,每次都是小根在栅栏外徘徊,青红和小根近在咫尺却总不能走到一起,因为中间有白色栅栏。在这里白色栅栏的象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那是一堵妨碍自由和爱情的藩篱。克莱拉尔认为:女性是为拯救男人而生的,女人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在家庭中,女人附属于男人。⑥如果说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囚徒,被时代束缚,作虚妄的挣扎,而青红又何尝不是呢?在这里,最温暖的父女之爱被父辈的梦想所掩盖;最动人的爱情被粗暴地虐杀,就像那夜色下撒落在山丘上的两只红色高跟鞋;在这里,人仅有的一次生命被践踏,被摧残……
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代人在漂流人生中与命运相抗争的主题,将父辈的梦想与子女的青春叠加在一起。它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张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脸庞,其个性也仅仅局限于隐忍。怀特·海曾经给青春下定义:青春就是尚未遇到悲伤的生命。而当以青红为代表的少男少女的青春梦想和父辈们改变命运的人生梦想相冲突时,有人就此结束了青春与梦想,亦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只是青红隐忍、惶恐的面容;我们看到的只是青春在时光的暮色中渐渐模糊。⑦
通过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在强大的父权制面前,青红没有说话的权利;这种压抑的父权也体现在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青红的母亲身上。她的青春早已湮灭在这山村里了。在强大的夫权面前她没有说话的权利。家庭的权利牢牢地掌握在父亲的手上,母亲在家中则明显的处于失语状态。母亲偶尔为女儿辩解,替女儿争取些许自由的空间,也会遭到父亲严厉的批评,得不到父亲的接受。母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会“赢”来父亲粗暴的顶撞和狮子似的怒吼。
“在时代的印记中,在个人的生活记忆里,伴随着青春的觉醒,向着未知的他处突围,却带来死灰般的残酷。”王小帅的青春物语,以痛彻的锐利刺穿时代的隔膜,赢得戛纳无限的光荣。支边青年回上海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电影《青红》就是这样讲述着归家情结和对旧体制的逃离,以及这两者纠结在一起的“死亡”爱情故事。青红青春的疼痛和母亲无言的疼痛让我们反思: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女性的生命是不能承受之重,是生命中难以言说的痛。
二、《孔雀》——现实社会中女性理想的破灭
女性主义学者罗婷认为西蒙·波伏娃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个体的女性价值理论。女人作为和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一性别,与男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具有相同的能力和潜质,可以发展和超越自我。女性的价值同男性的价值一样,是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它是通过每一女性个体现实、具体的行动来衡量。⑧《孔雀》就是这样的一部女性叙事的电影,它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方某小城的一个普通家庭三兄妹被遗忘、被遮蔽的青春成长故事,让我们沉重地体会到了青春女性的理想破灭的疼痛。
影片中的姐姐是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她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只希望自己是一只耀眼的孔雀。她想当伞兵,喜欢那种置身于空中的感觉,像风一样的自由。当姐姐在空旷的广场挣脱笼罩在身上的降落伞时,她看见了一张英俊的脸,姐姐呆呆地看了许久,也许是因为这张英俊的脸的出现,使得姐姐的这个梦变得更加美丽;也或许,是因为姐姐痴迷了这个梦,从而喜欢上梦中出现的那张英俊的脸。姐姐付出了行动。姐姐陪英俊的男人打乒乓球,她想通过“贿赂”的方法获得当伞兵的机会,但姐姐并不擅长这些“生活”的勾当,当她看到另一个想当伞兵的人将一块西瓜娴熟地递进那个英俊男人的嘴里时,姐姐将自己买来的烟酒推进河里,呆呆地看着它们漂向远方。姐姐失败了的当伞兵梦想就像被针刺破一般,只留下“嘭”的破裂声。尽管姐姐当伞兵的梦想被刺破,但她依旧想要飞翔。她用天蓝色的布缝制了一个降落伞,将伞绳捆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用力一蹬,自行车就飞起来了,她兴奋地叫着,摇着车铃,甚至双手撒把来彻底的放松身心,这是真正意义上心灵梦想的飞翔。但这种飞翔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自行车倒地的坚硬的声响,姐姐看到妈妈倒在地上把降落伞揉成一团,姐姐不想再多看一眼这残酷的世界,她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了。遗失的降落伞被一个叫果子的男人捡走,为了拿回降落伞,姐姐只身到小树林找他,并在这个男人面前退下来裤子。姐姐是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感觉,她甚至认为这和身体无关,可以任由残酷的生活来摧残它。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的栖居,诗意即情感,即人与人之间的爱”。“诗意的栖居”就是要有一个情感的“空间”提供给自己的灵魂栖居。这个情感的空间是一切人绝对需要的,连居无定所的流浪人都需要。⑨在家里,姐姐缺少父母的关爱,父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哥哥,从不正眼看姐姐。当妈妈为姐姐找了份幼儿园的工作谈到这工作是如何的来之不易的时候,姐姐说:“不好找,那就再等等看”时,妈妈的话充满了冷嘲热讽:“还等啥,你以为好工作都等着你!你以为你是神仙!啥都看不上眼!这工作已经很不错了,总比你去刷瓶子强!”父亲的反应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她想待业到什么时候啊?”仿佛在家里,姐姐就是个白吃饭的。姐姐有个美丽的伞兵梦,当姐姐去广场看跳伞回家晚了时,妈妈看也不看她一眼,冷冰冰地说:“你还知道回来啊?”当姐姐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妈妈居然把拿在手里的松花蛋摔在地上……家庭的氛围总是那样的压抑和令人窒息。为了寻回家中缺失的爱,姐姐弄伤了自己的胳膊为的是能换取所谓干爸的同情。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共同的慰藉和乐园。虽然这乐园外面有冰冷的眼光和恶毒的流言。不久,“生活”的残酷再一次显露出来,老人摸了电门,姐姐在洗瓶厂里被老人的儿女痛打,并在一群漠然而视的女人面前骂她“狐狸精”。姐姐没有哭泣也没有悲伤。她仿佛自知,这也只不过是另一个破碎的梦。
后来,姐姐结婚了。姐姐被那个她不爱的男人用自行车接走了,姐姐像逃离牢笼一样离开了家。为了反抗平庸的生活或是为了逃避平庸的生活,姐姐并没有珍视她的青春,她在肆意的挥霍年华,不要亲情也不要爱情。可是后来姐姐离婚了,带着行李趔趄的撞开了家门,和一个少数民族的男子生儿育女,回到了姐姐一直在反抗和逃避的平庸生活。
姐姐,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总希望自己的生命像降落伞一样飞起来。可满是行人的狭窄街道预示着姐姐永远无法自由翱翔,那是她永远无法超越的现实环境。总有一股这样或那样的力量把想飞的翅膀折断。她倔强地反抗着甚至是逃避着沉闷、庸常的日常生活。可这种生活就像一道无边无际的网,任她左冲右突,头破血流却最终找不到方向。处于大时代的人总和蝼蚁一样被生活的轮子逼迫着不停的往前走,却看不到方向。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姐姐的种种逃避根本解救不了她,看不清人生的她注定是个悲剧。⑩
在社会男权之网下,姐姐的追求也只是困顿前的挣扎,结果早已预料为徒劳。一种强大的社会规约力量,遏制本性自由的伸展,无情地将命运锁定在既定的窠臼中。一个生命在孤寂、晦暗的世界里无望的挣扎与孤独,尽管她年轻生命本能的跃动和残余不尽的激情还在激烈地涌动。不安分的姐姐的青春成长梦想的破灭透露出当时女性成长面临的困境。虽然妇女获得了解放,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觉醒,自觉寻求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困难依然重重。影片中印迹和梦想的破灭,几乎没有温暖可言,这种“伤痛”的影像带给观众最大的感觉便是无奈。
三、《红颜》——他者的位置,女性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红颜”在中国其实是个很沧桑的名词,在中国,“红颜”一词被赋予了太多的意味:是罪恶的起源,又是不幸的象征。在中国有句古话是“红颜薄命”,如果仅仅将故事的悲剧归结于“红颜”都似乎太过简单。电影《红颜》告诉我们:他者的地位,给女性的生命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影片《红颜》讲述了16岁、26岁、36岁三个不同阶段的女人的故事。这三个女人可以说是尝尽了世间的悲凉酸楚。它是一部描写陷入精神困境的中国女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一曲女性命运的挽歌,同样也是一部让女人和男人都绝望的电影。
影片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个仍旧保守的年代,未成年少女未婚先孕是个可以摧毁一生的悲剧。16岁的小云和男友王峰偷吃了禁果,有了身孕,被学校勒令退学之后,男友留给小云一句话:“我走了,这是个是非之地,越早离开越好”之后,男孩远走他乡继续他的人生;而小云则被留下来孤独地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小云在世俗的眼光中慢慢长大,当然,跟随她长大的还有她的肚皮。16岁的少年是懵懂的,哪里知道早尝禁果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两个孩子双双被开除,成人的社会成了孩子的噩梦,他们毫无怜悯地唾弃这对没有还手之力的年轻的生命。小云不得不为一时的冲动承担全部的压力,尽管是正常的恋爱却被贴上不可饶恕的标签。在这个男权规则的社会里,她的生存欲望一再受到挫折。小云由16岁的女孩逐渐变成女人,从她怀孕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做一个普通女人的平凡的生活。世俗的眼光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她的眼睛,刺向她那颗无助的心,她的命运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不时被风雨袭击的小船。男友选择了离开,小云则在这个丑陋的世界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成了大家“看”的对象。
西蒙·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或者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要做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11)在影片《红颜》中,小云直接被纳入以男性为主体的评价体系的另一端,成为可选择的、可占有的并且可让渡的客体。在剧团老板那里,小云是个等待被选择的砝码,在歌厅老板那里,小云是一个可以被转让的物件。26岁的小云成了一名川剧演员,和剧团的老板刘万金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在这里剧团老板刘万金是小云的情人,既然是情人就应该担负起情人的责任,但是,当小云在为某台的促销活动表演时,刘万金的老婆一家人突然当众叫开了嗓子,对这个闯入的“第三者”大肆辱骂,当众直呼其“贱人”、“骚货”和“淫妇”,当两三个人的愤怒逐渐延伸到在场的所有看热闹的人们时,她们那心中隐藏的阴暗面刹那间“嘣”出来,人们冲上台,撕扯着小云的衣服,抓揉着小云的长发,踢踩着小云的身体,面对突如其来的羞辱,小云没有发怒,没有反抗,任凭人们对其羞辱。此刻,刘万金在哪里?本应由两人共同承担的责任,却又留给了小云一人承担。后来虽然刘万金和老婆离了婚和小云结了婚,但依然不能给小云庇护和慰藉,在婚礼上小云被老板戏弄、侮辱之后,刘万金又是什么态度?谁相信一个付出了真爱的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女人被其他的男人进行人身侮辱吗?他在小云身上获取的同样只不过是肉欲的快感,而小云只不过是供其玩乐的工具。对于小云来说,十年前的耻辱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从她的身上褪去;十年后,她依然是镇上人口中的“破鞋”,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需求。尽管最后那一脸早熟又顽劣的小勇给小云的生活带来了些许“亮色”,让小云那颗饱受痛楚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得到些许温暖。当小勇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全心的爱慕,燃起了小云被爱的渴望,赋予她悲剧命运中一抹温情的亮色的时候,命运却和她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小勇是十年前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明白了事实真相后,小云选择了离开,这个离开在她十年之前她被抛弃的那一刻就酝酿着,离开后,小云的路在哪里?离开,是小云无奈的选择。在小云的生活中,除了小男孩小勇外,男性在这里是缺失的。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男性只根据自己的利益原则来建构自己,因而常常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紧箍咒,对女性生命形成压抑。(12)无论是小云的男友王峰还是剧团老板的刘万金,抑或是那个钱老板,他们的自私,陋习甚至丑陋反衬出一个美丽女性生命的蹉跎多难。
另外一个苦命的女人是王正月,即王峰的姐姐,她同样是处在一种他者的位置。小云的儿子小勇被王正月以职务之便收养下来,这个天真的女人原以为可以和丈夫一起分享这个意外的“宝贝”,却不想因此换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王正月带着小勇去部队看望丈夫时,当士官的丈夫怀疑小勇是她和别人的私生子,拒绝听她的解释,在这里男性的缺失使这个女人早早就抛弃了青春。将自己丢入琐碎的生活中。为了弟弟的孩子——小勇,她放弃了自己的婚姻,独自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这个坚强的女子承担了别人的“孽种”、忍受了爱人的抛弃,经历了这么多的苦痛后,这个女人面对弟弟死亡的消息早已波澜不惊了。
第三个女人是小云的母亲,她是个人民教师,丈夫英年早逝。为了小云也一直没有再婚,与女儿相依为命。知道小云的“丑事”后,她又伤心又气急,却不忍心给女儿堕胎,而是让女儿生下孩子送人。十年后,她渐渐感觉到女儿与她疏离了,一种孤独感紧紧擒住了她的心。女儿每次回来和她说的话都很少,只是把钱放在桌上,吃完饭就走,她和女儿之间缺少沟通。她虽不再企望爱情,却渴望正常的亲情,所以当发现小云孩子的去处后,疯狂地希望小云将孩子要回来,可以消除她寂寞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红颜是十年前小云的父亲去世后就化成了灰尘的——黯淡、孤绝而且无助。当小云最后选择是“把这事烂在肚子里”,并且离开这个小镇的时候,她不再压抑自己,她放声大哭,这哭声惊心动魄,撕心裂肺。她悲怆的呜咽让所有人痛心不已。因为她不但失去了隔代亲情慰藉的机会,还失去了哪怕一星期只见一面的女儿。
《红颜》中三个女性都是坚韧而美丽的,从16岁到26岁到36岁,这中间不知流过多少岁月,掩盖了多少眼泪,伴随着岁月的风吹雨打,人世的沧桑变化。女性所独有的那种美丽的色彩最终都被生活漂白,黯淡无光。
四、结语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感叹“无论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和文明之中都充满了女性的表象和关于女性的话语,但女性的真心话语却成了一个永远的在场的缺席者”。在这三部电影中,一色的青蓝淡黄,永远看不见阳光的渗透和阴冷潮湿,这一切告诉我们的是女性的青春乃至一生的伤痛。在电影中,女性是社会的异己者、孤独者、反抗者。三部电影的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近乎相似的关注角度和倾诉情怀,对已经与正在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缅怀,对失落理想的追忆,对无奈现实的感喟,对悲情人生的零度观照,在主题和情感上勾勒出了一条绵延的线索。其中尤其以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和同情为主。他们的电影叙述设定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投射出中国妇女的艰难境遇。
在媒介传播中,女性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如实地反映妇女和其他处于亚文化状态或边缘文化状态的人群的生活;第二,将这类人群当作一种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仅仅是当作一种消极被动的力量来反映。(13)我们应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力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分析方法透视当代妇女问题,旨在警醒世人,号召政策投入,对社会和女性敲响双面钟;从女性本身而言,要认识到女性的自强、自立已经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已经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女性要关心自己的生命质量,关注周围男男女女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把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身份看作自我认知的重要前提。
西蒙·波伏娃指出: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其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不过,要达到这种真正的平等关系,首先要基于男女之间的平等、尊重、互助以及试图超越彼此性别局限的勇气和决心。(14)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没有女人,世界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男人,世界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但是,女性和男性相比,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说,确实是弱势群体,但女性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生存地位。社会心理的形成必是社会的成因铸就的。女性的信赖心理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弱点,而是后天社会教育的规范,社会环境的制约,社会生活的强迫,男性社会压力下的结果。作为同等权利的人,确实应该提倡男女平等,但女性是弱势群体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帮助女性而不是歧视、压迫、鄙视她们。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的理想处境是在社会制度、男性观念的全面解放的前提下,超越不利处境,全面实现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15)而妇女解放的目标和理想结果是在男女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完全平等并和谐共处,共同创造两性组成的美好未来。所以,生活在当代,男女两性在社会上需要合作,在精神上需要沟通和交流,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理解,男女双方的自我认识才会有所提高,男女两性才能和谐相处。而女性也要自己重视自己的尊严,真正提高女性在社会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女性主义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女性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以及女性的主体意识。一种健全的女性意识应该包括对女性自身的自我剖析和反省。
注释:
①②③转引自:徐志祥:《影视艺术评说》,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页、第7页、第1页。
④李道全:《青春,已暮霭沉沉:析王小帅新作〈青红〉》,《电影文学》2005年第9期。
⑤(11)(14)(1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第89页、第3页、第106页、第210页。
⑥⑧罗婷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4页、第215页。
⑦朱洁:《〈青红〉:穿越时空隧道的青春祭奠》,《电影艺术》2005年第12期。
⑨傅光明:《女性的心灵地图》,新世纪出版社。
⑩何海巍:《“生存美学”的阐释与误读——评电影〈孔雀〉中的姐姐形象》,《电影文学》2005年第6期。
(12)沈洁:《〈红颜〉——一场女性命运的另类书写》,《电影文学》2005年第12期。
(13)卜卫:《媒介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