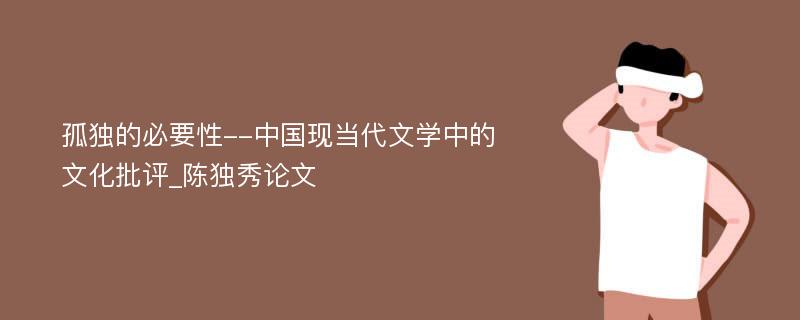
孤独之必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当代论文,孤独论文,文化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严格说,文化批判只是一个现代现象。在西方,是启蒙运动之后,即“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体制性主流之后,知识界对现代文化的反思运动。但是,把文化批判看成从西方引入的思想方式,或是把文化批判等同于“西式”自由主义,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在中国,文化批判经常与启蒙二位一体,不能与西方的情况相比附。
体制是文化批判的他者,也是文化批判的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对体制的批评都是文化批判。文化批判自身看来有以下三个标准:
首先,文化批判不是批判体制本身的运作,而是批评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不是指斥督励前规范:朱熹批评皇帝模范汉高祖唐太宗“假仁借义行其私”。批评虽尖利,实为“前规范批评”。与司马光批孟子“君轻民贵”论是“以德抗爵”听来正好相反,实质上一样是顺应理论。文化批判是对规范的超越,即所谓“元批评”(metacriticism)。
文化批判也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病,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思辩。也就是说,批判不是象牙塔中的玄思,它是社会性的,却又是非实践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是批判者个人的事(例如陈独秀实践“离开书房就进牢房”的誓言),但此种实践已不是文化批判的一部分。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批判应当把自我作为反思的他者之一。文化规范的力量在其“自然化”,它独断,却好像并不强加于人。例如阿Q,“我们虽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可以说,没有清醒自我批判,认为文化规范波及天下我独能免,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批判。
达到这三标准,很难。因此我们说文化批判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气候,能达到这三者的批判者个人,也很难找。因此,文化批判在政纲尚无完人可作先师。
宋明理学虽然富于形而上思辨,程朱道学“去人欲存天理”,做的是前规范训示。孔子的省身,“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的“反诸求己”。引向陆王心学的良知本体论,都是前规范的自我督励。道家主张“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老子),似有自我批判意识,但以“不谴是非”为原则,逃脱了规范的反思。佛教在中国士大夫化成即心成佛,或民俗化成积德求报,失去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力度。佛教在传入中国前后,在自识上不断加难度:原始佛教说六识,在五感官识上有“意识”,取得表境转化;大乘唯识宗讲八识:第七持业识,向内思量自我而加执取,取得思量转化;第八心识(阿赖耶识),为我,法生起根据,取得异熟转化。北朝“地论”学派,已加入第九天垢识,成佛之道必须超越主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永远只是待实现的理想境界。但初唐后中国佛教的主流不再是唯识宗,而是“事随理园”的华严宗,及与其相近的中国式的“顿门”禅宗,走向即心见佛,见性成佛,自审力就差多了。唯识宗直到晚清才重新受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重视,岂是偶然。
李卓吾常被认为是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个烈士,怕不能算是文化批判的第一个圣人:且不谈面对的是中枢蠹烂的文化局面,“生性不受管束”(《豫约》)的意气用事,“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与周友山书》)的过分自信。相比之下,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焦循等人,他们的文化思考更为清晰。
王船山“理欲明而心更审之”(《四书训义》卷十四)指明了理学道德论的根本错误。而且他明白理学的最大恶果是原教旨主义式的礼教下延,把规范全民化。‘性心自发’之误在于认为“野人贤于君子”(《读四书大全》卷七)。
可惜船山之论一直无人看懂。孔子不惮其烦地区分“君子”与“小人”。而理学反其旨,把君子之德强加于全社会,拆除了儒教维持意识形态功能的最大保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身并不荒唐,其荒唐在于把礼教强加于本享有一定礼教豁免权的小民。明清以后,越到下层烈女越多。“礼教吃人”,士人为礼教牺牲是题中应有之义,维持名教是他们的责任。吃到老百姓,才是可怕的事。
五四以来激烈批判名教者,给西方式民主观念弄糊涂了,没有弄懂中国社会的道德分层机制。结果与晚明一样,知识层从礼教解放了出来,村镇老百姓却恪守规范,以致社会角色倒置。
2、
说文化批判在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立足,并不是说中国缺乏批判思想,单靠批判思想,并不形成文化批判。今天读先秦诸子,几乎个个都有批评,却说不上是文化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学理上无稽,说孔子有托古改制的批评思想,却并不错。托古固然是保守,文化批判原就不以激进为唯一可取的倾向:在文化主流唯激进是骛时,文化批判很可能是保守的。
文化批判的建立,首先须以主流文化体制为对象,为条件。当主流体制尚未确立,文化批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当主流体制摇摇欲坠,文化批判会难以抵挡中枢真空的强大吸力,变成在野思潮,争夺主流思想地位,从准体制进取正体制。所谓体制,应读成复数,它不一定单指官式体制。
沈从文在1942年的《文学运动的改造》中再次把“在朝”与“在野”并提,可谓目光如炬,大陆批评家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提出“庙堂文学”与“在野文学”都是“社会本体文学”。而在当今中国,以强大的大众传媒为渠道的俗文化,也正在成为新的体制。
先秦时,文化失范,“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墨家“兼爱”,儒家‘兼陈万物’,都是进取天下的架式。此时道家指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号召“绝学”,退出竞争,却可能具有接近文化批判的色彩。
所以文化批判最宜为一种盛世之学:正是巩固的文化体制,才最需要文化批判。衰世时,文化批判反而应该自敛,不去参与墙倒众人推,更准确地说,不仅批判将倒之墙,更应批判众人之推,因为后者正在成为一种新体制。
1922年周作人钱玄同等五教授与陈独秀的争论,是足以说明现代中国文化批判诸特征的一个重要事件:陈独秀等人领导的“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反基督教宣言,号召“铲除恶魔,务期净尽”。周作人等指出:“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已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
陈独秀的回答是:“先生们早已犯过这毛病,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经反对国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女守节等等”(陈独秀《信仰自由的讨论》《晨报》1922年4月5日)。
周作人和陈独秀的这场争论,的确预示了五四运动的分化,紧跟着就有“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之争”。如果我代周作人回复陈独秀,就说此一时彼一时。五四开始时并没有“在野体制”,到1922年,在野体制(周作人称为“多数的力量”)已经形成。
此场争论,治现代文化史者一直没有注意,周作人本人也不愿多提,在《知堂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带过。最早是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在《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一文中详加讨论(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后来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对此事论述甚详。钱理群认为,由于周作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他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关系比鲁迅更为密切。而此时周作人(以及钱玄同等北大五四激进派教授)不得不作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抉择:至少是理论上宣布了他将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划清界线的意向”。
中国的盛世之学是两汉谶纬,宋明理学,乾嘉朴学之类的顺应理论,少的是批判的声音;中国的衰世之学却常有批判锋芒,以致落下“晋亡于清谈”,“梁亡于佞佛”,“明亡于王学”之类的口实。此类说法固然是夸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开明书店,1948)就认为梁亡于佛老,这相当普遍的说法站不住脚,梁代政纲废驰另有原因。但批判(尚非真正的文化批判,这点上文已经谈到)在衰世越发兴盛,难辞其咎。
3、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也是中国文化批判者认识自身的历史。诚然,中国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批评运动,从康梁谭嗣同严复,到邹容章太炎;从胡适陈独秀,到付斯年罗家伦,到朱光潜储安平殷海光;从大陆五十年代的‘右派分子’,到八十年代“文化热”,到九十年代的几次辩论;从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到当代台湾学院界的文化批评:文化批判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些运动有多少符合上面说的文化批判标准呢?分开说,几乎没有:合起来说,在四个方面都渐渐接近标准:从摧枯拉朽的过分偏激,到面对相对坚实体制时的坚毅沉着;从拒绝“费厄泼赖”的目的至上,到理解文化批判保持边缘位置的重要;从以引入新规范为进步,到超越规范的理论思索;从情绪式地介入政治,到耐心而宽容的学理讨论;从难以摆脱的救国救世使命感,到意识自我批判在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进步不能算小。
试回想,中国现代哪怕著名的唯美诗人,都免不了以救世自许。录一段徐志摩的话:“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气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欧游漫录·给新月》)徐志摩在这里不是拿政治比喻他的诗人雄心,他同一文中引的范例是从诗人进入社会主义政治的莫理斯,是剧作家萧柏纳,是参与英国工党建立的费边社。我不是说徐志摩有政治野心,我是说大部分五四作家,无论左右,对政治与文化的分野不甚了解。
一个世纪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不过是从崇祯到康熙,不过是从李贽开讲于麻城芝佛院到王夫之开讲于衡阳石船山。毕竟今人比古人学习得快,我写此文,正是康有为1896年开讲于广州万木草堂之后一百年,我们的经验教训,比从李贽到王夫之的一个世纪多无数倍。
但是,我们应当感到惭愧,中国至今没有可以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批评学派,巴黎后结构主义学派一比的学术,虽然中国文化的转型,正在关键时刻,召唤着有自信力也有自省力的中国文化学派出现。
4、
而下才说到本文想说的题目。起头长了一些,要说的问题复杂,我自己得理清思路。
本文要说的是,中国有文化批判传统深长,其主干却不是哲学或伦理学,而是文学:不是论辩式思索,而是隐式思索;不是论文体例,而是小说和美文;不仅文化立场是非主流的,语言方式也是非主流的。当我们在前几章发现中国文化批判的思想家难够标准时,中国有不少文学家登上文化批判的堂奥。戴震与曹雪芹几乎同龄,就成就而言,两人都是一代顶峰级的人物,作为文化批判,《孟子字义疏证》远逊于《红楼梦》;陈独秀与鲁迅,胡适与周作人,也几乎同代,拿他们的最佳作品相比,深刻程度几乎不类。
当然,这样的类比有点不公平:论辩直露,文学隐曲;论辩清晰,文学模糊。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种差异如何影响文化批判。
首先,批评的超越性,在文学中比较容易取得。艺术意境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大观园或边城之汰尽人间污浊,作为对文化规范的谴责,清清净净存在于世俗规范的污泥之外。文学家有点乌托帮思想,作品更深刻;论辩家迷上乌托邦,很可能立即脱离文化批判,进入主流政治运动,把乌托帮变成社会实践。周氏兄弟都曾热衷于日本白桦派的“新村主义”,1920年时周作人几乎是社会主义的权威,连毛泽东都拜访过周作人,请教社会主义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文化批判。
文学的反思必然是非实践的,因为其基本表述方式是隐喻或象征,二者均以实质的缺席为前提。真缘此,就占了思辨的上风:文化规范必须以其全方位与现实清晰地对应立起体制。而文学艺术的模糊反而引向意义的深度。中国文化批判的名著《阿Q正传》,鲁迅生前评论已经汗牛充栋,但直到逝世前不久,鲁迅还是说没有等到知音。[(1)]《红楼梦》有不少实解(“反满书”,“索隐影射书”,“阶级斗争史”,“理治之书”等),从王国维开始,出现各种虚解,实解比虚解明显浅得多,虽然任何解都不能说毫无道理。
阿多尔诺指出:“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不真实,而是它自命与现实相符这点是不真实的”。他又说:“没有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也没有真正的哲学,在其本质意义上,能作为自在之物耗尽自身”。他的意思是,艺术,哲学,其意义都是非即时的,待实现(待阐释)的,而意识形态除了力求证明它的当即实践性外,没有别的立足之地。[(2)]
虚构作品主人公的毁灭,是文学家比论辩家方式更令人信服的自我批判。王国维首先发现《红楼梦》虽然与《桃花扇》一样被称为悲剧,原因却大不一样。社会变迁为《桃花扇》悲剧之因,《红楼梦》悲剧之因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普通之道德使然”,因此“大背吾国人之精神”。[(3)]连贾宝玉这样的梦想者,也发现水一般干净的少女一出嫁,“就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乐园只是精神分裂的一个征象,王国维看到,文化规范使主人公身遭最惨痛的悲剧,悲剧的牺牲者不明白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自己依靠悲剧的规则生活。所以王国维说《红楼梦》的悲剧是出于主人公(挑战社会规范)的自由意志。
由此想到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据称的怪题“《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究竟是不是狂人?”[(4)]狂人愈狂,其狂语就是愈加犀利的文化批判。那么鲁迅是否想把每个中国人都启蒙到狂人一样?同样,也可以问曹雪芹是否希望满世界全是贾宝玉没有一个甄宝玉?显然不是,连小说中都不可能:狂人已经发现早已参与吃人,“有了四千年吃人历史”;如果此篇太短,那么接下来的《药》《长明灯》诸篇则把“觉悟者”的孤独,生前死后都得不到大众理解说到了最惨处。而且,鲁迅并没有一味指责大众(那就成了前规范批判)。他自己一生中遇到许多革命者,几乎从来没能深交。曹雪芹与鲁迅都明白,他们的批判是非实践的,他们的知与行可以分裂,只能分裂。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5)]《阿Q正传》的真义在于鲁迅明白他自己就是未庄上的假洋鬼子,赵太爷,阿Q三者合一。
所以论辩式批判者很难做到的自我批判这一条,在艺术式批判中却可以作得很深刻:没有完人,没有完美,一切乌托邦都会坠毁,一切纯净都已经被污染。狂言为真,狂人却随时可能被真实世界没收过去,“赴某地候补矣”。
这种危险并非虚构。
说八十年代重复了五四的缺点,论辩批判再次不如文学批判,如此简单打发,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一轮文化批判与文学运动尚未走完:有关人物都时有新作,思想和作品都在发展。批判者的自我认识也与先前大不一样。任何结论都会失之过早——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应当会合起来讨论。
我只想借一个题目讨论当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问题,这个题目就是寻根。
寻根不是超越性批判。寻根者认为非主流文化——楚黔河谷,藏蒙边地,或荒山野村——有这个主流文化正缺乏的价值样式,或生命力量,不管他们找到的价值是真是假,也必然是一种规范移植,应当和西化的价值移植同例。
但是,与西化不同的是,向僻乡异族化外之境寻找现成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与陆王心学之以天地洪荒为人心赤子相似,免不了被笑为“与吃菜事魔者等矣”(焦循《孟子正义》),所以寻根本身有内在悖论。寻根作者,没有几个心里真有一套理论,证明山野蛮民能拯救中国文化。这整个潮流是个文化批判姿态。
文化批判正是必须停留于姿态:它本来就不能用来拯救文化,这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与寻根相比,西化很容易搞真了,声称批判能与实践对应,真能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结果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与拉丁美洲作家以寻根文学奠定民族文化价值不同,中国文化的根子不需要远寻。
所以,寻根文学由于它特有的理论不足,反而可以成为有效的文化批判。而如果作者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话,这种文学能成为强有力的文化批判。自觉的寻根,是在作价值的否定性开发。作品开出的处方虽有实际的美学效应,却只有幻觉中的文化“生命力”。
韩少功尽管是中国第一个寻根宣言的作者,他的作品却从来也不是真正的寻根努力。名篇《爸爸爸》把孤悬于山野的村民部族写得比庙堂主流文化更为不堪,朽败愚昧无一不备,却没有其堂皇庄严;部族生死存亡前扑后继的战争本是堂而皇之的民族史诗之源,却除了血腥只有可笑;连战败集体自杀都毫无可歌可泣之处,只剩猥琐和没落。那个连喝毒药都死不了的白痴丙崽,却成为一个国民文化自我反省寓言:“我们是否也是丙崽?”,与“我们是否也是阿Q?”一样,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突然照镜子看到的丑陋。
马原虽然在斐然有成的几年之后,八十年代末突然搁笔,象韩波(Arthur Rimbaud)一样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他为数不多的创作却注定落在当代文化不断回顾的视线之中。马原笔下的西藏远远不是田园诗式的香格里拉,或是(如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中的)宗教神秘之土,而是一个内地来的汉人面临不可解之谜的迷惘。短篇《拉萨河女神》和长篇《冈底斯的诱惑》以“随机性”实验开一代风气之先,这随机却是不可理解的惶惑,是文体的自我瓦解。《折纸鹞的三种方式》勾勒的拉萨与其说是迷宫,不如说是理性的陷阱。名著《虚构》把异族女性袒露的性诱惑,放到藏地一个麻疯病隔离区的女病人们身上,“我”作为一个汉族青年男子误入其中。在这里,“原始生命力”成为令人震骇的肉体残缺,却又并非没有性吸引。
异族女性之魅惑,本是寻根小说乐此不疲的“根”之象征。寻根文学的基本美学公式,就是汉族男性面对异族女性坦荡诱惑的无奈。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洪峰《勃尔金支牧歌》,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则一直以文化中心来的男性“我”,惊艳于大河上下面貌不断变幻的女性(“她者”)内在的矛盾使异价值的乌托邦风化,令人信服地自我颠覆了寻根的神话学。[(6)]
乌托邦的自我颠覆其实在寻根的前驱者沈从文那里已经出现。相对于五四的价值外求,沈从文的作品实在是一种反动,但是沈从文却是比其他五四人物,包括扶植他的新月派诸人,更加自觉的文化批判者。他的文化批判最令人深思之作却在他脍炙人口的湘西“乡下人”小说之中:“柏子”,“萧萧”,“贵生”,“夫妇”等篇什中,村野小民的生活方式自由不羁,任性而纯洁,几乎可以做陆王心学的注释。然而仔细读来,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文明压力下,道德纯朴人性敦厚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沅水的船员,辰州的妓院,乡下的童养媳,抓奸取乐的村民,都不再生活于乌托帮之中。正如论者凌宇所发现的,“乡下人”已经是“陌生人”加“蒙昧人”。[(7)]套用前面的话:沈从文并不希望中国人都象柏子那样幸福地“不觉悟”。
5
要推论出中国式文化批判的特点,上面的简短讨论当然是不够的。下面提出的一些看法听来会有点牵强,虽然并非言出无据。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文化批判的理据不一定是什么圆满的真理。而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偏执,庄子说的“一曲之士”。偏执之所以能起文化批判作用,是因为文化批判并不是追求真理,并不是为主流文化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以它的特殊表现方式,提醒主流文化体制:应当旁骛,应当分心,三步之外必有芳草,而一心一意朝什么目标挺进,不但会失去转型的机会,而且直路总是通向历史的陷阱。
有很多论者已经敏悟到这一点,却不明白这究竟是好事还是不足。论者指出“韩少功想肯定什么?这远不如他的否定对象明确”。有论者认为鲁迅在二十年代末“找到了肯定性力量”,而周作人“始终坚持五四以来对于整体历史和国民性的否定态度,这一方面出于他的文化批判的持久和深刻,一方面也由于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的差别,而导向民族虚无主义。(赵京华《寻找精神家园》)他的结论是周作人不及鲁迅,我倒觉得此位研究者对周作人“文化批判的持久的深刻”原因找得很对。
文学的构筑总是比较模糊,但是文化批判本来就是一种目标不清晰的抗争。理论过于清晰,体系化,整体化,就会导向排他的“真理性”,即自命与现实对应,同时声称其他已成体制或未成体制的体系,都是谬论。文化批判的失败往往不是外界压迫,而是此类自我膨胀的毁灭冲动——我在四年前一篇文章中称之为“学院溢出”,即批判理论从学院溢向街头,从边缘溢向中心,成为体制化竞争圈中的一个角色。
以文学为形式的文化批判,比较起来,不太容易滑向学院溢出。这可能是因为文学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是批判的。艺术的必然运动是拒绝程式,拒绝以重复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话语,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因此,或许可以说,真正的优秀艺术品,或多或少,总包含着文化批判的成份。[(8)]
贾宝玉代曹雪芹说:“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八股)上竟没头脑”;鲁迅感叹中国知识分子不敢睁眼面对现实,但是在文学中例外:“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在他们的作品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他自己不再用小说,而用政论发表“不满”时,他从中国历史上最犀利的文化批判者,变成杂文——文人议政——的开创者。
拒绝体系,或者说,拒绝参加体系化运动,必然使坚持真正的文化批判的艺术家,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在五四人物“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之时,成了“荷戟独徘徊”的“游勇”。
周作人在二十年代末发现,“苦雨斋夜话的人只有钱玄同与俞平伯二君,……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同年他写道:“现代的社会运动(指五四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永日集·爆竹》)。次年四月,周作人到北大上课,遇法学院学生强行接收校址,竟被非法拘留两个多小时。周作人曾被北洋官方拘押过几次,这次他感叹,昔日老英雄的鬼魂复活在今日小英雄的身上。看来周作人对五四后期的“学院溢出”感受很深。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五十年代初彻底众叛亲离,自杀未成,只好躲入博物馆三十年。当代作家当然有些不同。但是韩少功是八十年代成名作家中最不招摇的人之一,独自在海南岛大商海中办《天涯》杂志;马原八十年代末从西藏回东北后,突然扔开笔,从文学界销声匿迹,做各种各样古怪营生去了。
孤独,并不是因为具有文化批判思想的是少数。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艺术家,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文化批判色彩。为行文方便,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讨论。有学者清点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家,很惊奇地发现:“坚持知识分子‘超然性’,同时不忘积极的文化介入,比较好地坚持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9)]因此,他们的孤独,是自我意志的孤独,并不是缺乏同道,只是君子同而不党,拒绝离开边缘的诱惑。
在文化的主流体制巩固时,做一个批判者,而且是够得上本文所说的三个条件的批判者,难乎哉。林毓生赞扬殷海光,说在五四高潮时期,做一个五四人物,太容易。“在外界客观环境剧变以后,殷先生能在种种横逆之中,以一人之力,使五四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十年,那就要坚定的精神力量了”。林毓生指的是五六十年代,那时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使他处境非常孤独。我在此并不想评价殷海光在文化批判上的成绩,也无法说清他的自由主义是否妨碍了文化批判,此非我力所能及。但是,我想说的是,象殷海光那样“不识时务”,正是文化批判者的本色。
五六十年代大陆的殷海光们,情况惨的多。被迫检讨之余,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消失。原因是大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根本不允许保留任何文化边缘,哪怕很狭窄的一条边缘。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大陆出现了被称作“文化热”的文化批判运动。其功其过,需要另一篇文章讨论。奇怪的是,在九十年代的全面商业化大潮中,在文化人被社会看成“又穷又傻”时,许多八十年代曾经激昂一时的文化人,也以“后现代式的多元化”为遁词,宣布文化批判已经过时,对正在迅速成为体制的俗文化赞美有加。以“后殖民主义”为战旗回向体制,回向狭隘民族主义。[(10)]
自然,没有必要敦请这些“圣之时者”坚持文化批判,毕竟一个文化的大部分的参入才形成所谓体制。我想到的只是林毓生对殷海光的评价:如果体制既立,那么现在正是需要批判者的时候: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
孤独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文化批判者应当知道,我们自己选择了孤独,孤独也选择了我们。
注释:
(1)“《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6年10月19日致沈西苓。文学作为文化批判,难处也就在这里:它的意义要靠批评来实现。可以有纯文学,但不可能有纯批评。克里斯多娃认为:“诠释行为本身有一种内在的政治含义,不管它诠释出什么意义…给文本以政治含义恐怕是认识论的最后结果”。(Julia Kristeva,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lis,ed.W.J.T.Mitchell,<
(2)Theodor W.Adorno,<
(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765页。王国维解释说《红楼梦》中其实无“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就宝黛之恋而言,贾母“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袭人闻黛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之语,“惧祸之及”;而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于最爱之祖母”。
(4)见阎焕东《狂人日记与〈狂人日记〉新论》中所引陆耀东,张恩和,陈涌等人的看法。《理想研究论文集》北京市理想研究筹委会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92——3页。
(5)《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一卷,262页。鲁迅自己忍耐不住点出应当如何理解《阿Q正传》,1933年,在《再谈保留》一文中,用第三人称说了这件事:“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是否自己也包含在里面”。(《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五卷,145页)他这段话却无人注意。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在绍兴参加革命政府工作,认为“很有希望”,所以恐怕也挂过“柿油党的银桃子”牌子。
(6)马原这个中国最有哲学悟性的作家,从文坛消失,是大陆文坛的一大损失。拙文《ma yuan the chinese fabricator》,发表于《world literaturetoday》spring issue 1995,pp.312-6。此文中文稿竟然无处发表,刊物编者们都认为马原是个放弃了文学生涯的过客,不值得再提。我想把几本样刊寄给马原,竟然没有一个文坛朋友,包括他的沈阳同乡,能提供地址。但是我相信,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象马原一样深刻地揭示了汉文化与非汉族文化复杂的互动关系,马原自己可能没有完全自觉到这一点。要把这些层次说清楚,需要赛以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显示的洞察力。
(7)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6。他的分析是“乡下人”,从道德上看,是“自然人”;从理性看,是“蒙昧人”;从现代世界的现实来看,是“陌生人”。
(8)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解释过为什么艺术必然反体制。他在评论现代戏剧的先驱者阿而多(artonin artaud)时说:“阿而多想做的,是擦抹普遍意义上的重复……重复有许多名字:上帝,存在,辩证法”。而否定重复,“即是在时间上决然地,不回头地耗净此刻,从而必然地结束可怖的演绎,结束难以避免的本体论,结束辩证法。”(writing and difference,chicago,1987,p.245)
(9)赵京华,《寻找精神家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23页)。他举出的名字有朱光潜,陈寅恪,金岳霖,宗白华,梁宗岱,梁实秋等,还不算稍激进的鲁迅等人,或稍保守的胡适,周作人等人,(他把后两种人另作分类)。的确有独立精神的文化批判者占了本世纪上半期(那是个暴风雨般的战争和革命年代)文人的绝大多数。
(10)关于中国大陆文化界近年的新保守主义,请参阅拙文《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期,以及《文化批判与现代主义理论》《二十一世纪》1995年5期)。参加这次辩论的有徐贲,张颐武,郑敏,许纪霖,吴弦,万之,张隆溪等人,以及《二十一世纪》刊登的十多封来信。此类辩论当然不可能谁说服谁,但是有助于学界仔细思考一些问题。
标签:陈独秀论文; 鲁迅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国学论文; 殷海光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