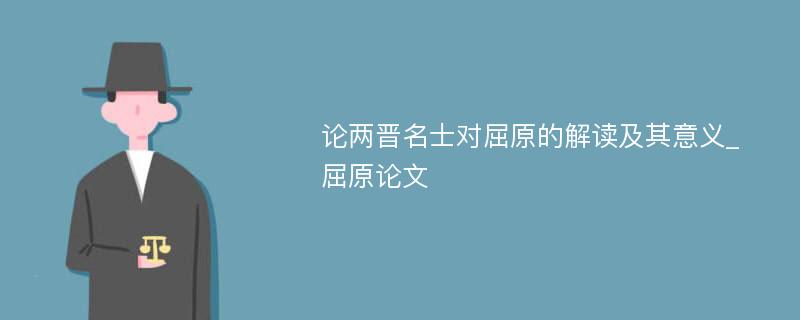
论两晋名士对屈原的解读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两晋论文,名士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原,就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而言,尤其是对于传统的士文化而言,其品格的重要性远过于他对文学的贡献。秦汉封建帝国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游士之风。两汉四百年间独尊儒学,奠定了封建士文化的基本品格。屈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离骚》被冠以“经”之名;作传者称颂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王逸据五经之义注释屈原,谓其“忠贞之质”、“清洁之性”,“百世莫匹”。自汉以后,“忠贞”一直是士人价值观的核心,屈原正是作为忠贞的楷模而不断受到尊崇。
魏晋时期,儒学衰微,士风变化。魏晋时期的屈原评价有相沿承袭两汉的一面,如对屈原沉江的惋惜。但是,魏晋士人所关注的中心显然不再是其忠贞的道德品质了。他们所看重的,是屈原的才华横溢,是屈原的恣情奔放。由此,《离骚》成为当时名士的“必读”。魏晋名士行为狂放。“狂”谓自恃其才而傲然独立,“放”谓自恃其情而恣肆无惮。这与忠贞所要求的敦厚平和、忍辱负重的品行相距甚远。尽管魏晋以后的儒家学者对名士们的放荡不羁有过很多批评,可魏晋士风仍然颇受士人的欣羡,名士精神成为古代士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魏晋名士对屈原的认同浸染着时代的气息,屈原的形象也促进了当时士风的深化。分析魏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探讨其间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有益于屈原研究史的展开,也有裨于深入认识屈原形象在传统的士文化中的作用。本文的探讨范围限于两晋。
一
两晋士人对屈原的评价,就目前史料的梳理,见于两类材料之中:一是直接的言论,一是模拟屈原的作品。在这些论及屈原的文字中,士人所推重的主要是屈原的才华。
西晋高士皇甫谧作《释劝论》晓喻敦促其应聘入仕的亲戚,以为“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而不入”,如自然界之有阴阳,有寒署,两存之,两美之,于是方见圣皇仁德,并非唯仕为贵;若乃衰末之世,“贵诈贱诚”,士之仕否则关系国家存亡,义无可辞。他列举道,“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晋书》)卷51,皇甫谧不以屈原为越俗的高士,而将他与苏秦、廉颇、公叔痤、范蠡等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是那个年代里举足轻重的才能之士。苏秦等人,或以口辩著称,或以谋略显名,或为文臣,或为武将,均以其才干功业而史册有载,只有屈原的功绩缺乏记载。但皇甫谧仍是高度评价他的才干,说楚国之所以倾亡就是因为屈原的被疏放!
两晋朝廷任官,以中正执九品铨选,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严重阻遏了士人的进仕之途。西晋刘毅上疏批评当时选官重门第而轻才干,引史为证曰:“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平、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晋书》卷45)人主用才则收功,不用才则损政,这是常见之论;但刘毅以屈原为例告诫朝廷,说才士被弃于人主却流芳于史册,则颇有深意。首先,与皇甫谧一样,刘毅是以才士而目屈原。其次,士即使不为君主所用,却仍然“显名于竹帛”,可见士有不依赖于君主而存在的价值。而屈原就是这种独立自存的士人的代表。
皇甫谧和刘毅表达了一种有别于汉人的屈原认识。在汉代,关于屈原的才能没有多的议论,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其才干不曾多花笔墨。但是,司马迁不理解屈原为什么非得以沉江来解决不被信用的问题,提出过“以彼才游诸侯,何国不容”的疑问。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正是游士风行天下之时。当时士人以才识立身,他们游说诸侯,得意则一日而登卿相,失意则“视去国如脱屣”,转而他之。才识的个体属性赋予他们一种自由的身分,自尊的品格,一种对自身价值无所不适的信心,进而可以轻蔑官位,傲视王侯。司马迁的疑问正是从战国之士以才立身的特性而提出的。在屈原自沉的问题上,贾谊、司马迁、扬雄等的议论不仅是同情屈原的不幸,更包括了他们个人遭际的悲伤。当扬雄为屈原指出“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的选择时,他所强调的已不是士自身具有的才,而是士之才得以发挥的机会。换句话说,即只有得到君主的赏识,士才能实现其才华的价值。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使“择君而仕”成为了历史,自此君与士之间的契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汉人的“不遇”之叹是士失去其自由身份而成为大一统政权的依附品之后的悲伤。贾谊、司马迁、扬雄都是抱着怀才“不遇”的个人心情来理解屈原的,对于他们,机遇比才华本身更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汉代士人对于空前强盛的大一统政权抱有深深的依附之情和维护之心。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道德的泛化,又强化着汉代士人的这种心理感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极少言及“才”与“遇”的问题,而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屈原的忠君之心。《离骚序》谓屈原“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九章题解》云“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反复渲染屈原“履忠被谗”而“不忘其君”、“不改其志”,把情感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屈原作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一点,即“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的“人臣之义”。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等汉代士人,无论最令他们感动的是屈原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还是他那怨愤深切而不弃其君的坚贞,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均在屈原对于君国的忠诚无私。至于屈原那“内美”、“修能”之才,在他们眼中本不是问题,也不成为关心的重点。鲁迅所讥刺的“不得帮忙的不平”应是据此汉代的屈原而发。因此,当皇甫谧将屈原与苏秦、张仪诸人等列,当刘毅把屈原视作不受“遇”与“不遇”的限制而独立自存的士人时,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系心楚王”的道德光环,而简单地把他看作是具有自由精神的战国之士。
二
晋人简单地视屈原为战国才士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汉末以后士人思潮的新变。
汉代以察举选官,东汉时最重道德科目的察举。道德是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而维护着群体生活的利益。缺乏必要的考核,以道德举士常常是取于社会舆论的裁判,而忽略士人的真实才干。禄利诱惑之下,东汉后期的士人矫情作态,驰鹜声名,虚伪助长,浮华大兴。当时民谣讽刺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见《抱朴子·审举》引)建安三国,群雄角逐。曹操公然诏告天下,要无视士之道德品行而“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猛纠汉代用人失实之弊,以应治乱用人之急。在这种情势下,士的个人才能被充分肯定,被大肆宣扬。建安时代的“求贤”有着现实的意义,而且重在“军国之才”,要求具体而实用。由于这时对“才”的标举是针对汉代以道德举士的弊端而发,伴随着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个人才华与儒学道德的反动,才华的表现范围从政治而及于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当时孔融、祢衡、郑泉等人纵情任性的违礼行为,因被视作才士之癖而受到宽容,更为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对才华的张扬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对儒学道德的鄙弃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当玄学兴盛时,鼓吹“自然”的老庄哲学使士人进一步挣脱儒学论理道德的约束,崇尚才华、表现才华就是崇尚和表现士人自己,风潮之盛,以至于走到了荒诞的地步。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自主自重的战国之士在这一时期因而受到特别尊重。两晋士人强调屈原的才华,甚至用他来警告君主,以显示士人的特殊价值,使屈原形象的道德意义大为削弱。他们略去汉人所着力渲染的忍尤含垢的眷君情怀,而突出了屈原恃才傲物、高自尊贵的才士性格。东晋时,伏滔与习凿齿争辩秦楚人物之优劣,各自列出一长串历史人物作论据。习凿齿为楚人辩护,有“鲁仲连不及老莱夫妻,田光之于屈原”的反驳(见《世说新语·言语》注。)虽然类比不尽妥贴,但习凿齿是把屈原归在了战国时代田光一类禀性高傲而行为激烈的士人之中的。这是两晋士人对屈原的普遍认识。
在汉末人物品题风气中出现的“才”与“性”的讨论,魏晋以后成为玄学清谈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士以才而著名,才因人而不同,对才的重视必然导向对人的个性的探讨。魏晋的文章中,“才能”、“才用”、“才气”、“才理”、“才情”一类词语随处可见,又常用“天才”、“俊才”、“清才”、“高才”、“奇才”等来概括人物,可见当时的人物品评,同尚才华又颇有分辨。才性论者以性为人的自然禀受,才为性的外在表现;人受气不同,性分各殊,才能有偏。尽管持论者在才与性的关系上看法不一,但承认才性的个人性质,“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则是当时的普遍认识。这样,才性论就从本体论的高度肯定了士人的个体存在,破除了道德一律的清戒,为士人的独立个性张目。而且,玄学以“自然”为宗,尽才是为尽性,尽性本于自然,这也从理论上为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与才性的探讨相关的是关于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更从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上将魏晋士人的个性解放推向高潮。屈原的高自标举、怨愤深激、狂狷急切的情感表现,在汉代受到班固的批评,在魏晋却得到名士们的尊重和认同。《晋书·隐逸传》记载,夏统曾斥责劝其入仕的亲戚说:“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夏统不仅自视甚高,而且,他针对时世而设计的三种方案,都建立在自我的选择之上,大有战国之士唯我独尊的气概。他把屈原作为三种方案之一,表达了他对屈原的行为的敬重。在这里,屈原的“同汙共泥”是与长沮、桀溺的“避世”相对而言,夏统强调的是屈原处于浊世而放任心性的愤疾之行。三种方案之中,他取的正是屈原的方式,而不是长沮、桀溺在行为上的逃遁和感情上的漠然。上巳节的洛水边,王公贵族衣冠鲜丽,车乘如云,夏统于小船上翻晒草药,旁若无人;及至引吭而歌《小海唱》,清激慷慨,起风涌浪,裹挟雷电,惊动王公,使之惊呼:“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名士的狂放与屈原的形象叠合到一起了。
在这种士人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的浪潮之中,两晋士人对屈原的才士评价,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他们重新看待屈原的“露才扬己”和“贬絜狂狷”之行,以之为其人个性的充分表现,这就否定了班固站在维护君权的立场上对屈原的批评。尊重屈原的个性,同情屈原的遭遇,晋人对于屈原作品中复杂而悲苦的感情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三
对屈原作品的模仿,汉代已形成热潮。两晋时期,拟作不少,如傅玄《拟天问》《拟招魂》、挚虞《愍骚》、陆云《九愍》《九悲》《九思》等。汉人推重屈原,首先在其忠诚之志,高洁之行。在王褒等人的拟作中,抒写的中心是“失志不平”。如经常以大量的比喻描写黑白颠倒的世俗,反复征用古事来批判忠奸误置的政治,以充分表现屈原对君国的忠诚,对谗邪的愤恨和不改其志的高节。王逸注释屈原作品,处处申明“慕其清高”,“珍重其志”;为拟作解理,称东方朔《七谏》为表现屈原的“殷情之意,忠厚之节”,刘向《九叹》是“追念屈原忠信之节”等等。汉人对屈原作品重在其维护君权的政治意义和道德价值,往往用“志”来概括他的思想感情。晋人拟作则鲜明地提出重在其情。汉晋时代所谓“志”与“情”,有涵意相通处,但是,各有所重。汉人讲“诗言志”,“志”的范围相当狭窄,唯在儒学所提倡的政治伦理道德,即使是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也要服务于政治教化。而魏晋时提出的“诗缘情”说,与“诗言志”相对而言,强调的是“情”的个人性质。王戎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见《世说新语·伤逝》),就是人所习知的魏晋名士反对礼教约束、张扬个人情性的宣告。两晋拟骚之作重在屈原之情,这不仅反映了时代思潮给予文学创作的影响,也见出晋人的解读屈原自有一种不同于汉人的角度。
陆云是西晋文学的代表之一,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他有拟骚之作,还有关于屈原及其拟作的一些议论,可以代表西晋文人的一般认识。陆云在给陆机的信中谈到:“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此种文,此为宗矣。”(引自《全晋文》卷102,以下同)在另一处,他称道屈原文章说:“此是情文。”陆云把楚辞视作别一种以情为宗的文章,读屈原自当依情而入。“清绝滔滔”谓其文辞雅丽而曼衍。其《九愍序》云:“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玩”即体味。“以其情而玩其辞”是说要从情感的体验中来认识屈原文辞的特色。他说自己之所以作《九愍》,是因为“见作九者,多不祖宗(屈)原意,而自作一家说”。既然以情为宗的拟骚,方得屈原本心,陆云又自许识得屈原之情,那么,《九愍》之说是重在表现陆云对屈原的情感认识了。自汉以来对屈原的评论没有象陆云这样公然而笼统地称言其情的。王逸《章句》中每言“愍其志焉”,“悲其志也”,“毕其志也”,反复申说以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志”。与陆云同时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称屈原赋为“古诗之赋”,因其“以情义为主”(见《全晋文》卷77),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可见汉人的影响。而陆云读屈原,首标其情,拟屈赋,心会其情。这里的“情”既包括汉人所推尊的“志”,更包含着新思潮下士人理解屈原作为“这一个”所特有的情。
《九愍》完全依循《九章》的篇次而作。与汉代拟作不同的是,在《九愍》中,那些香花恶草的是非比喻,那些忠臣奸佞的历史罗列,都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仅作为楚辞的一种特征而保留;那些慷慨激昂的忠贞志节的抒发,如“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七谏》),“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哀时命》),没有了;陆云所着力渲染的是屈原面临选择的困惑与无可选择的绝望。如:“将结軏而世狭,原援楫而川广。虽我服之方壮,思振策其安往?”“岂大川之难济,悲利涉之莫由”,诉说着世事坎坷,似有路又无路;“俟沧浪之濯缨,悲余寿之几何”,“餐秋菊以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悲伤理想之渺茫,似有望却无望;更痛心的是,“欲假翼而天飞,怨曾飙之我经;思戢鳞以遁沼,悲沉网之在渊”,“忠与邪其莫可,岂余命之所穷?”面对众多选择,却没有一种可以选择,如此人生,多么令人震惊,令人惧怕!《九愍》中大量抒写对时光流逝的忧心,对生命短促的悲伤,在屈原伤时自励的情感中融入魏晋士人惶然无奈的情绪,把那种对命运的困惑,对人生的绝望表达得更迫急,更悲哀。
在屈原的作品中,“九死不悔”的坚定与执著是贯穿始终的情感的主旋律,而困惑与绝望只是时时泛起的一种基音。但正是由于这种基音的回响,才强化了“九死不诲”的力度,丰富和深化了坚定执著的内涵。《离骚》讲述屈原游天却不得其门而入,求女而频频受挫,既得灵氛之吉占,又要巫咸以证之,每曰:“心犹豫而孤疑”,“聊浮游以逍遥”,表达了作者屡遭失败而仍须选择的困苦和疑虑。《惜诵》云:“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思美人》称:“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舆而狐疑”,描述了作者无从选择又必须选择的绝望。困惑与绝望构成了执着于理想追求的屈原在情感中的巨大冲突,使他的自沉的意义超越了寻常的生死解脱,而在于探询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屈原形象的悲剧性是在困惑与绝望的情感中的展现和升华。这一点恰恰没有受到生活在强盛政治之下的汉代士人的注意。魏晋是一个观念体系正处于崩溃与重建中的时代,士人自觉意识的苏醒,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个性精神的高扬,都强劲地撼动了汉代以来以儒学伦理道德为准的价值观。但是,新的观念虽然在士人中流行而波及社会,却并未得到执政者的认可和支持,并不能取代维系数百年的观念传统。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之中,士人的心态矛盾而痛苦。他们对生活、对生命倍加珍惜,也倍加哀伤。浓厚的伤感使魏晋士人对于心灵的苦难十分敏感,他们为屈原作品中对生命、时光的忧伤所感动,深深同情屈原面对各种矛盾冲突而感受到的困惑与绝望。《九愍》中有一些越出《九章》的内容,如揉合《卜居》《渔父》中的情节加以抒写,陆云自道:“亦无他异,附情而言。”《卜居》中郑詹尹之释策,是因为屈原并非不知路者,他是知路而无从选择,是“疑”在自我,而非其他,故《九愍》曰:“谅不疑其何卜?”只是屈原之“疑”,非龟策所能决。对于士人,自我疑虑,自我困顿,最是痛苦。感受到屈原的“疑”,方能理解他那深入灵魂的自我考询。陆云揣摩、体验屈原之情以写《九愍》,渗入了他的主观认识,弱化了屈原忠君的道德情感,突出了屈原的困惑与绝望。屈原形象的悲剧性在魏晋士人的情感体会中获得了发掘。
四
魏晋时期士人对自觉意识的高涨和个性自由的张扬,是在以社会整体为重的儒学伦理道德对个体生命的长期压抑下发生的,带着很浓的矫枉过正的意味。当时社会,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已经衰微,儒学思想却仍有着深刻的影响。魏晋士人信奉老庄“自然”之学,向往逍遥自由之境,但还不能放弃传统的士人功业思想,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往往处于冲突之中。个人自由与社会存在不能圆融,意味到自由的意义而使士人清醒地面对冲突,因此更加痛苦。汉人生活在空前强盛的大一统政权之下,信念坚定,充满希望。他们也有不幸,也有痛苦。这不幸和痛苦主要来自于外界,或明君不明,或谗谄蔽贤,而他们自己的功业价值观并不因此而动摇。即使悲伤于“士不遇”之时,他们犹有期待:或有“遇”而立功的幸运,或藉著述而后世传名。对他们来说,屈原的忠贞执著是榜样,是激励。司马迁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从对屈原的同情中找到了安慰;当扬雄为仕途坎坷而痛苦时,他也从对屈原自杀的惋惜中找到了一点平衡。因此,他们都没有理解屈原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他本人,来自于他的内心。两晋士人既肯定屈原的忠贞与高洁,更通过情感的体验而触摸到忠贞与高洁之下跳动的那颗痛苦的心。他们不仅强调了屈原的情,而且描述了他情感上的冲突,感受到他痛苦中那撼人心魄的一部分,在对屈原作品的阐释上比汉人深入了一大步。以“骚”代指楚辞文化,以“骚人”代称诗人,显然是由于《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抒写其悲苦绝望之情感人至深。这两个名称都出现在魏晋以后,与当时人对屈原之情的重视和理解不无关系。
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与老庄玄学的盛行是分不开的。屈原是个积极入世者,庄周则鼓吹消极出世,两人的生活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屈原那种高自尊贵的气度,卓尔不群的品格,毫不掩饰的爱憎以及激烈的行事方式,表现了战国之士所具有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就其人格与个性的表现而言,这种自由精神与庄子所宣传的“逍遥游”的理想并无隔绝。玄学的兴起本来就带有在功名社会与个体自由之间寻找某种契合的意图。庄子要取消行动,以齐物我、一死生、泯是非、忘利害来达到个体的自由,魏晋士人做不到(实际上,任一社会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两晋士人无人不作隐居山林之想,却人人都在仕进之途上奔忙或奔忙过。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由对立而最终走向合一反映了西晋以后儒道调合的发展趋向。魏晋名士向往庄子的自由之境,又不能忘怀功名的社会价值。他们所生活的世族社会也不允许任何妨害政治秩序的个人行为。个体与社会的龃龉使名士们的政治性格与其文化性格相分裂,他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主要表现为从个人的行为方式上对礼教作反抗。儒学政治伦理的价值体系,即使在名士们也是承认和维护的。班固称屈原是“贬絜狂狷景行之士”,既赞美他的忠贞志节,又批评他“露才扬己”,“竞于群小”,“愁思神苦,强非其人”,认为其行事方式不合于儒学谦谦君子、执守中庸的教训。当两晋士人以崇尚个性的眼光看待屈原的怨愤激切与狷介直行,他们就从任情率性这一点上捕捉到了屈原与庄子的精神相通之处,而引狂放的屈原为名士们的同调。王恭声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两晋士人尚情,动情,好悲哀之音,这是《离骚》得名士青睐的一个原因。依王恭之言,“无事”则身暇,饮酒则使人“形神相亲”,在一种身心两忘的境地中去体会一段痛苦哀婉又愤怨迸发的感情,那种悲伤绝望,那份淋漓痛快,才是真正的名士感觉。王恭的不拘俗迹,时誉为“神仙中人”。他自恃才高,有强烈的济世之想,曾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晋书》卷84)两晋名士的追求个性自由,走的不是庄子指示的否定一切的道路,而是风神的滋养,情性的自适。屈原有忠贞的政治品格,又有任情率性的行为,名士们依其所需而有所取。两晋士人将屈原的品德与行事分开,以狂放为其个性而同时予以肯定,至于这两方面在屈原身上是否融洽,却没有多作理会。谢万作《八贤论》以出处论优劣,虽然推重屈原“皎皎鲜洁”的品德,但因其出仕而居之于劣;孙绰遂作《难谢万〈八贤论〉》,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见《世说新语·文学》),则以其心性任放不为劣。无论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他们对屈原狂放一面的肯定,不仅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融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那部分文化性格。只要看看后世对屈原狂放的批评不曾中断,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因此不以屈原入史,就足以见出两晋人的屈原解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龚自珍《最录李白集》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其实,最早从个性自由的精神层面沟通庄周、屈原者,还当推魏晋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