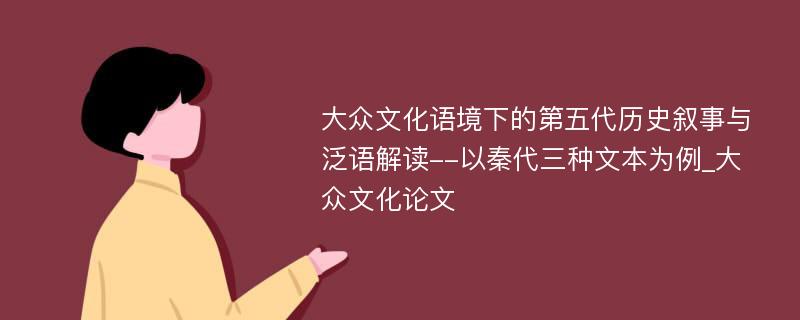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第五代”历史叙事及泛文本解读——以三部“刺秦”文本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语境论文,大众论文,个案论文,第五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陈凯歌《荆柯刺秦王》:精英反思视角下的感性诉求和理性黄昏
在五代群体中,陈凯歌是最具反思意识的。80年代的他几乎是以沉思者的姿态把传统 中国纳入其电影的思考中心。《黄土地》中的顾青,作为乡土社会的闯入者,更喻指着 现代文明的声音。在他的影响下,“走出黄土地”,过一种别样的生活,对于年轻一代 构成了充满诱惑的召唤,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书写也成就了对现代追求的乐观主义表 达。
走出80年代的《黄土地》、《孩子王》,90年代的陈凯歌依旧走在反思的路上。这一 倾向在他的两部充满“超载能指”的文本《边走边唱》和《荆柯刺秦王》中清晰可见。 但细加辨析,我们发现,陈凯歌的反思视角实则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如果说,《黄土地 》时期的陈凯歌更多地是对人生活于其间的压抑性文化环境的反思,由此,翠巧的投奔 八路军成了一种个体抗争环境的具正值意义的理性追求,那么,到90年代的《荆柯刺秦 王》,导演更多地是对个体为之召唤并为之束缚的理性化追求的深深质疑。在《荆柯刺 秦王》里,我们已无法获得关于理想的乐观主义表述,我们获得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 :满怀理想的秦王为统一六国,不惜血腥杀戮,六亲不认。但“待到山花烂漫时”,赵 国被击败了,燕国的刺客荆柯被消灭了,幸福却成了无法兑现的支票,留下的是一个众 叛亲离的历史人质。换言之,秦王得到了江山社稷,却失去了生活的所有,他被名和利 抽象为一个空洞的符号。
陈凯歌曾云:“将来当人们没有衣食之忧时,总是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是怎么回事。 ”“荆柯的形象也是提出这些和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相关的问题”。(注:《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99页。)换言之,在此 期导演心中,理想意味着对人性的感性回归。片中另一具参照意义的人物是嫪毐。应该说,其在片中是以阴柔谄媚的形象出现的,但影片在内底的表述里却给予了微妙的肯定。有两处可证:一是长信侯率谋反门客直闯秦宫,后遭樊于期为首的秦军反击,在“四面楚歌”中,他坚决不降,一阵乱箭,门客倒地,他连呼投降,正当观者产生不屑时,一句充满人味的台词“不杀我的门客,我就降”,恰和秦军的言而无信构成对照;而在秦王处置嫪毐及其私生子,他与秦王的对质段落中,更以他对秦王的道德谴责,他与母后的激情话别给予了肯定处理,并借其口对母后道出“不过是你想做我的女人,我想做你的男人,夫妻一样过日子,偏你是母后,就难了“这样的伤情话语,撇开历史史实,至少在影片中最终是以情感化的长信侯压倒了政治化的长信侯,在形象的翻转中是对本真生活的诉求。
事实上,这种对理智化生存的质疑在陈凯歌的另一寓言体作品《边走边唱》中早已呈 现。那个坚信“千弦断,琴匣开,买药来,看世界,天下白”的信念,并为之压抑了现 世感性生活的盲人琴师神神无疑成了终极理想的囚徒,而其徒弟石头则以一种现世生活 的享用姿态拆解并颠覆着他的理想。而这也几乎成了90年代陈凯歌理性反思的惯性动作 。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梁》预示了感性文化潮的到来,10年之后,陈凯歌则以精英化 的理性沉思对曾经追求的理性本身提出质疑。这是否可视为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大众 文化感性潮对知识精英的洗礼?但陈凯歌在两小时的文本中以多线的故事结构,融入庞 杂的思考内容,以此企图表达对一种感性生活的回归,这本身是否带有悖论式的意味?
二 周晓文《秦颂》:大众消费语境中的欲望召唤和替代满足
对于作品,创作者和接受者永远存在着阐释的裂缝。80年代末,周晓文的《最后的疯 狂》和《疯狂的代价》被评论视为娱乐片的突破,不以为然的是导演自己,他更愿意视 这两部电影为带有娱乐性的艺术片。而至1996年《秦颂》出炉时,周晓文的阐释同样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声称拍《秦颂》是自己“一直对表现历史环境中的特殊个性有兴趣,同时希望借历史的氛围展示中国文化的精髓”,(注:李尔葳:《与周晓文谈<秦 颂>》,《90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但另一方面 ,他又称《秦颂》应该“跟所有的正史野史的记载完全没有关系”,(注:《<秦颂>剧 本讨论纪要》,《当代电影》1995年第6期。)多少有在精英和大众之间两厢讨好的意思 。
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商业历史文本,《秦颂》恰恰无法逃脱大众文化语境中历史书写 的基本策略。一方面,既然历史被哲学界宣判为一堆“碎片”,既然大众宣判了历史叙 事的理性黄昏,那么,给历史一个“软着陆”,让观众在爱恨情仇的演绎中触摸历史的 表象,无疑更契合观众的消费诉求。从表层看,影片采用了与《荆柯刺秦王》相类的“ 一女二男”的叙事模式,即历史被置换成情感故事。但如果说《荆柯刺秦王》中的赵姬 在秦王和荆柯间的感情位移尚被巧妙地包裹在“正义”的旗帜下,在《秦颂》中,任性 的栎阳公主和高渐离之间的感情便颇使人生疑。我们难忘高渐离在咸阳郊外初见栎阳时 的满口脏话和鄙夷神情,但面对秦王和高渐离的僵局,栎阳主动谋求以“女性气”征服 ,却频频奏效。高渐离绝食几天,滴水不进,但当栎阳以童谣弹奏对以策略,唤起的却 是其赤裸的情欲,并在欲望的释放中完成让瘫了的栎阳重新站起的超现实叙述,这一“ 感情”段落背后因缺乏人性的基本支撑而陷入对观众欲望的生硬挑逗。其后,高渐离在 秦国宗庙中与出嫁在即的栎阳公主狂热放纵的段落,除却完成一次欲望化搬演,并无多 少爱情的所指,在此基础上栎阳的为爱自绝也多少成了刻意煽情的策略。可以说,《秦 颂》正是借所谓的人性化定位展示出位的男女情欲,并以此完成历史消费的即时性快感 。
另一方面,出于对大众的民主平等诉求的想象式满足,英雄的凡俗化成为历史叙事的 又一策略选择。同样在《秦颂》里,秦王赢政被改写为一个政治胜利而身心疲惫的精神 失败者。影片中出现的秦王“孤独的背影”无疑满足了世俗大众对作为凡俗之躯的英雄 的文化想象,而在观者对失败英雄的影像认同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压力的缓解和稀释。英 雄走下神坛,还其肉身需求,这本无大碍。但任何一种对历史的反拨都需在一个“度” 中展开。作为一个多有定说的历史人物秦王,影片为显其凡俗,刻意展示其在征服高渐 离心灵时的无助,尤其面对高渐离的一味放纵(如对秦王的任意谩骂,对栎阳公主的大 胆强奸),一忍再忍,甚至不惜为其辩护,这种对人性化策略的过度运用带给观者的实 则是一种不解和“出神”。
作为一部明确运用商业化叙事策略的历史电影,《秦颂》显然有潜在的观众意识,但 至少就票房言,这一策略并未得到有效回应。或者导演从根本上低估了新一代由盗版
VCD和DVD培养起来的接受了众多的欧美和港台优秀商业片的观众群体,刻意的情欲化渲 染如不能和叙事情境,和基本人性有效缝合,已不能唤起观众的真实兴奋。
三 张艺谋《英雄》: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致化大众文化的微妙合谋
和周晓文相反,张艺谋的电影传播恰恰面临着另一错位,从《红高粱》始,人们更习 惯于将其电影置于精英文化的视域中解读。而从今天看,其电影的真正意义恰在于它们 和大众文化潮的互文式关系。当年,在大众文化呼之欲出时,张艺谋及时转向历史话语 的置换,以张扬的男女故事取代抗日的民众故事,以《红高粱》将第五代的理性方向搅 动了一下。而90年代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继续展示着情欲书写和历史反思 的惯有路数,倔强的女性成了文化反叛的有效符码,释放着大众模糊的冲动。
时至2002年,张艺谋携《英雄》再造电影神话。全明星的商业包装,成功的营销策略 ,似乎给沉寂的大陆电影注入了一帖强心剂。然在影片中,张艺谋又一次越过观众对历 史和武侠片的惯性想象而作了微妙的个人改写。没有了《红高粱》的粗砺和狂放,有的 只是无以复加的精致和唯美。没有了英雄对政治的悲壮反叛,有的只是英雄对主流的认 同和理解。在国家一统的历史肯定中,代表反抗的刺秦动作渐渐收缩为不刺甚至被刺。 在世界和平的最高原则下,刺秦褪去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表述,而成了个人淹没在大 历史中的主旋律表达。正在这一点上,《英雄》完成了对以稳定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 的示好。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商业大片,暗合政治只是一箭双雕,而醉翁之意仍在于大众, 确切地说更在于消费型的都市大众。这一群体随着社会的文化转型,并经由传媒的全力 打造,如今已浮出水面,并正在获得大众文化的话语权。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更关注 的是对当下的享用和延续。因此,如果说80年代的《红高粱》以粗放的感性形态释放了 大众的狂欢诉求,那么,到了2002年这样一个大众文化主流化的时代,一个大众渴望远 离暴力和获得世俗享受的时代,张艺谋及时转向,弃“土匪式的草莽英雄”,而推出以 “和”为最高原则的儒雅化英雄,其恰恰投合了当代大众的深层文化心理:当大众蜕变 为由都市中产小资构成的主导力量,当品位格调成为都市大众的关键词,大众文化也正 面临着由粗鄙向雅致的蜕变。而《英雄》创造并投射的正是日益中产化的大众消费意识 形态和生活方式想象。
鉴于对时尚的应和,张艺谋再次回到造型美学上,只是这一次造型已不再背负深度寓 意,而更可以看作是纯粹的视听盛宴:无名与长空的对抗呈现的是清虚的意念之战;如 月与飞雪的追击呈现的是红衣女子的飘逸;无名与残剑的对决成了点到为止的武艺写意 ;残剑与赢政、无名与赢政的两场本应惊心动魄的宫中对抗则被置换为极具视听效果的 绿色帷幔和剑刺之声。而残剑和飞雪的大漠之战因纠缠了太多的家国之恨和男女之情, 而最显凄美和感伤。至于杀机四伏的史传历史早已退至叙事背景。按照杰姆逊的观点: 在现代主义阶段,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而在后现代主义阶段,视觉形象主要转 向“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的空间模式,(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 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那么,《英雄》的意义正在于它以一种空间的 历史叙事取代了时间的历史,并成功地借此在主导文化允诺的范围内,尽可能释放了当 下的大众意识形态。当然,张艺谋在精确地捕捉到时代无意识的同时也难免不被诟病为 革命精神的丧失。但作为一部以商业为目的的主流大片,人们尽可以换一种评价标准。
四 结语:存在即合理?大众文化的乌托邦?
一部“刺秦史”,按早期五代的逻辑,极可能演绎为一段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思型叙事 ,在消费主义盛行,价值理性膨胀为个体的感性放纵的当下时代,却走向“历史故事” 的消费,即如反思,也是对理性的反思。精英、大众甚或主导意识形态以一种暖昧的方 式汇聚,从而建构了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新意识形态神话。
面对这些文化信号,一味地持批判姿态无疑更显苍白。存在即合理。确实,我们很容 易在感性化、消费化的当代文化潮中看到中国大众在长期的政治乌托邦和理性乌托邦的 压抑之下对自身需求的反拨。但另一方面,第五代的历史书写呈现向大众文化的集体倾 斜,事实上也包含着被大潮裹胁的失语之态。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应是众声喧哗 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霸权都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文化乌托邦。因此,电影市场如何在 集体趋从后树立起真正的分层观念,成了电影人理应反思的对象。毕竟,电影的商业化 并不等同于大众文化的一元化。只有建立起各种文化形态,各种意识形态各得其所的电 影文化版图,当代大陆电影才有可能摆脱来自理论和商业的双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