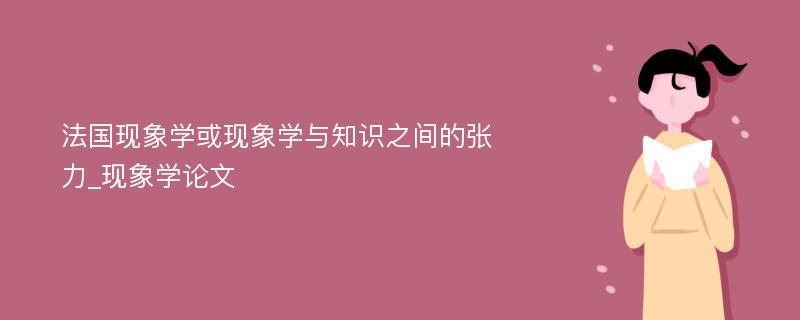
法国现象学或实存与知识的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法国论文,知识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9-0122-09
通过创造性地吸收和转换笛卡尔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精神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哲学资源,通过批判和改造世纪初的德国现象学,20世纪法国哲学得以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尽显其璀璨夺目。美国学者施奈德在《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1950)中表示:“胡塞尔的影响彻底变革了大陆哲学,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主导地位,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寻求适应它,并用现象学方法表达自己。”①就20世纪法国哲学而言,我们不妨把这段话修订为:现象学的影响彻底变革了20世纪的法国哲学,这是因为现象学逐步获得了主导地位,而任何法国哲学实际上都适应了它,并且或直接或间接地用现象学方法表达自己。在我们看来,法国现象学是多元而复杂的,现象学家们之间的内部分歧绝不亚于他们与其他哲学家之间的外部对立。这一分歧根源于德国现象学中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姿态对于胡塞尔的知识论立场的巨大冲击。尽管也存在着延续胡塞尔式的逻辑研究和认知导向的某些努力,法国哲学解决这一德国式分歧的主导性倾向是把胡塞尔哲学海德格尔化,与此同时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国式创造性误读。这些努力始终体现出主体哲学与概念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意味着实存论与知识论之间的强烈张力,推动了法国现象学从意识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de la conscience)到身体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du corps)再到物质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Matérielle)的演变,表明了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
一、主体哲学与概念哲学之区分
20世纪法国哲学流派纷呈:实存论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existentialiste)和解释学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herméneutique)曾经独领风骚,结构-后结构主义也一度称雄,而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则始终有其生命力。研究实存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学必须注意到实存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联盟关系;探讨结构-后结构主义则需要关注受法国式科学哲学影响的结构分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如何拒斥黑格尔主义。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出现了把这些流派分别归入“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之中的尝试。依据福柯的看法,就是要在实存论传统与知识论传统之间进行区分。在1984年即将去世之前,福柯为著名学术刊物《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的“康吉莱姆专集”撰写了《生活:经验和科学》一文。这是他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次年得以发表出来。在这篇评价其老师的文章中,他表示,“不用否认过去这些年以及战后以来已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非弗洛伊德主义者,某一学科的专家们与哲学家们,大学教师与非大学老师,理论家与政治家对立起来的各种划分,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贯穿所有这些对立的分界线。这就是把一种关于经验、意义、主体的哲学和关于知识、合理性、概念的哲学分开的分界线。一方面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家系,另一方面是另一个家系,即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和康吉莱姆的家系。这一分界无疑可以追溯得更远,我们可以透过19世纪去寻找其踪迹:柏格森和彭加勒,拉舍利埃和库图拉,比朗和孔德。”②
美国著名的法国哲学研究专家古庭在其专著《20世纪法国哲学》③中接受这一区分,但他只是在“结构主义的入侵”一章中用一节的篇幅探讨了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哲学家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和塞尔斯的思想及其对结构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国内法国哲学研究专家莫伟民教授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概念哲学一词,他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④中把20世纪的18位主要法国哲学家归入到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两大阵营中,认为其中个别哲学家进行了综合两者的努力。我们倾向于使用“主体哲学”(或实存哲学、实存论)和“概念哲学”(或认知哲学、知识论)这样的表述。这是因为,就20世纪法国哲学而言,不管主体哲学(或实存哲学)还是概念哲学(或认知哲学)都面对着如何看待意识哲学及其解体的问题。其实,关键不在于两种哲学类别的差异,而在于清理它们与现象学的关系,在于探讨它们是如何批判和超越传统的主体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的。主体哲学基本上可以归属于现象学之列,主要表现为实存论现象学(身体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学,列维纳斯等人的译介工作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概念哲学也并非真正脱离了现象学,尽管它认可的不是实存论现象学,而是某种知识论的现象学。概念哲学家、数学哲学家卡瓦耶斯在引进胡塞尔的知识论和逻辑研究方面贡献突出;而曾经跟随胡塞尔、柏格森以及布伦茨威格学习,但喜欢海德格尔哲学达到如痴如醉地步的所谓概念哲学家、科学史家科瓦雷甚至非常有功于实存论现象学。列维纳斯正是通过科瓦雷把柏格森与胡塞尔联系起来,并以海德格尔为中介实现了对现象学的实存论解读。同时要注意到的是,科瓦雷与华尔、科耶夫、伊波利特等人共同为引入黑格尔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现象学的最初引进包含了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的共同努力。福柯下面的论述非常具有启示意义:“无论如何,这一分界线已经在20世纪被构成了,正是透过它现象学在法国被接受了。于1929年宣读的,随后被修订、翻译和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很早就已经成为两种可能的阅读的关键:一种阅读在主体哲学的引导下寻求使胡塞尔彻底化,并且急不可耐地与《存在与时间》的那些问题相遇:这乃是萨特1935年关于‘自我的超越性’的文章;另一种阅读追溯胡塞尔思想的那些基础问题,形式主义和直观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乃是1938年卡瓦耶斯关于‘公理方法’和‘集合理论的构成’的两部论著。不管随后有什么样的再度分叉、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接近,这两种思想形式直到这一段时间已经在法国构成了两条巨大的、相当彻底异质的纬线。”⑤从福柯的上述说法可以看出,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都与胡塞尔现象学有着解不开的关系,只不过它们对它采取了不同的姿态。换言之,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法国并不只是按照一种方式被接受。一方面,某些哲学家对现象学进行了实存论的阐述,并因此导致了主体中心论;另一方面,另一些哲学家则关注胡塞尔哲学中的知识问题,使主体退居到了非中心的地位。在3H时代,由于实存论现象学的巨大影响力,知识服从于实存,理性让位于非理性,概念依据于经验,所以主体中心论的声音就显得非常的宏大,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彰显,相关于主体问题的概念获得频繁使用。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体离心化的声音逐步通过结构主义以强大的音频散发出来,主体的被动性以及与去主体相关联的话题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探讨,导致身体现象学向物质现象学的过渡。
列维纳斯、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对现象学创立者胡塞尔采取了某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在他们眼里,“胡塞尔与其说是现象学运动的中心人物,不如说是它的一位已经过时的奠基者”⑥。他们强调的是海德格尔的重要性,“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已经被一种完全有别于胡塞尔的现象经验的现象经验独特化了”⑦。他们把胡塞尔有关逻辑基础的研究抛到一边,紧紧抓住他关于先验主观性问题的论述,同时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实存论改造。这一切都源于列维纳斯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胡塞尔认识论进行的海德格尔式解读。他并不关注逻辑的本质,而是关注胡塞尔对意识行为的强调,认为胡塞尔哲学的实质是关心纯粹意识的实存,而海德格尔关心的则是处境化的意识的实存。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就寻求把胡塞尔表述为已经洞见到关于存在的存在论而言,我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工作受到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⑧。无论如何,法国实存论现象学家要么不重视胡塞尔,要么对他进行了某种误读,并让胡塞尔哲学明显带有了海德格尔色彩。胡塞尔延续并强化了自希腊哲学以来的理论化倾向;通过借助于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列维纳斯以及他影响下的实存论现象学家显然作出了摆脱这种纯粹理论姿态的努力。列维纳斯表示,“在海德格尔赞同现象学方法论的同时,他认为胡塞尔的模式太依赖于意识的首要性以及一个使如其所是的世界具有意义的反思性的我思。…海德格尔不赞同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因为他认为我们实存的首要样式不是理论的,而是作为理论的先决条件的在世存在”⑨。这其实意味着身体现象学对意识现象学的冲击。
卡瓦耶斯的概念哲学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旨在对现象学作知识论的展开。依据巴拉什的说法:这位数学哲学家在致另一位数学哲学家洛特曼的信中表示,他探讨科学理论的本质和命运,既根据胡塞尔,又与之相对立地尝试来定义它。巴什拉注意到了卡瓦耶斯的工作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联性,突出了这些工作在引介和澄清胡塞尔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表示,自《论逻辑以及科学理论》第一版出版以来,“卡瓦耶斯的思考或许引起了更多的对于现象学的思考以及胡塞尔作品的法语翻译。因此,对胡塞尔作品的认识使卡瓦耶斯的思考的语境更加获得了注意。反过来说,这一思考将以无法比拟的方式揭示胡塞尔哲学的诸问题”⑩。事实上,卡瓦耶斯在这本著作中大量地引用了胡塞尔的《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方面,他注意到“形式存在论与命题存在论的关系问题开启了《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11),另一方面,他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看出,“胡塞尔把数学切割成两部分:与一般存在论相混合的一个形式的部分,整合到物理学中的一个应用的部分”(12)。在他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与观点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分析先验主体性的构造行为与意向”,而“逻辑的实质没有被考问”,“它显然不能够考问逻辑的实质,因为任何意识都不会见证其内容通过一种行为而得以产生,因为现象学的分析从来都只会在行为的世界中活动”(13)。他本人所要进行的工作恰恰就是考问逻辑的实质,既不关注先验主观性问题(意识现象学),也没有像实存论现象学那样对之进行身体现象学改造。在说明分析哲学为什么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中获得了流行,而在法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时,有学者认为首要的原因就在于,逻辑在法国始终是一门受到忽视的小学科,普遍唯理语法学派、笛卡尔、精神主义者以及新康德主义者布伦茨威格都不重视它,而像卡瓦耶斯这样关注逻辑的数学家死得又太早,没有能够改变学科的命运(14)。卡瓦耶斯无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影响。无论如何,概念哲学和主体哲学都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的,它们的关系也因此完全可以在现象学内部获得处理。
二、个体实存与客观知识的张力
胡塞尔现象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场巨大的革命,然而,他本人却始终坚持哲学的传统精神。列维纳斯就此评论说:“逆时间后退,胡塞尔的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发挥的影响看都同样具有革命性的作品,就其着手探讨的那些主题和它借以探讨它们的方式而言,却显示出忠诚于欧洲文明的那些本质性的教导。”(15)他忠诚的就是所谓的普遍科学理想或普遍数理科学理想。胡塞尔显然为自己规定了一种知识主义和逻辑主义的目标,并因此否定所谓的自然主义。他表示,“所有形式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从通俗的唯物主义到新的感觉主义,它们的特征都在于,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16)胡塞尔把矛头直接指向在他所处时代影响广泛的孔德式实证主义;法国实存论现象学家当然批判实证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追求严格的科学哲学理想,更不要求为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相反,他们对科学和知识保持某种批判的态度。梅洛-庞蒂要求我们“非科学地”看待事物,对科学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他甚至认为“回到事情本身首先就是否定科学”(17)。亨利走得还要远,他直陈科学造成了新的野蛮,科学迷信导致“全部其他价值的瓦解”,“以至于质疑我们的实存本身”(18)。这些批判性的思考要求克服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并因此突出了人的实存的优先地位。早在引进德国现象学之前,马塞尔已经把法国哲学引向了对于个体实存的关注。他在论文《实存与客观性》(1914)中突出个体实存与客观知识之间的张力,认为“承认实存的首要性是适当的”(19)。而进一步深化该主题的《形而上学日记》明确要求“赋予实存以形而上学优先性”,并且表示,“实存和客观性的区分在我看来显示了一种怎么都不可能被夸大的重要性”(20)。他在回顾中也表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向我呈现的乃是我所谓的实存的不容怀疑的特征,乃是对将实存还原为不管什么样的其他东西、对它进行质疑的不可能性这一意识”(21)。
在整个3H时代,实存明显优先于知识,知识只具有派生的、次要的地位。当列维纳斯等人对胡塞尔的知识主义目标进行实存论修正的时候,卡瓦耶斯则试图继续深化这一目标。然而,在较少关心逻辑问题,不太容易接受分析哲学的法国,实存主义的尝试显然占据了优势地位,而知识主义或逻辑主义不可能迎合法国人的口味,也因此没有办法在法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不过,卡瓦耶斯等人的努力终究会显示出其力量。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等人在索邦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哲学传统,通过自己的学生福柯等人,他们的思想在结构主义时代甚至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古庭表示:“尽管有其全部的原创性,结构主义在法国并不是反对主体的中心性的第一个主要的运动。正如福柯在评论他在其中接受教育的哲学界时指出的那样,早在结构主义问世之前,在法国哲学中就存在着‘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与关于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哲学’之间的基本区分。在福柯的学生时代,经验哲学当然是实存论现象学(但福柯在各种版本的精神主义中、在柏格森那里找到了它更早的例证),‘概念哲学’历史地与可以回溯到孔德的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一传统主要由巴什拉和作为索邦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的他的后继者康吉莱姆为代表。虽然在法国之外,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工作不太为人所知(国外的人们把法国哲学简单地等同于实存论现象学),但他们对法国几代哲学学生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他们的‘概念哲学’仍然是实存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替代物。”(22)我们应当注意一下古庭用词的微妙差别:他大体上把“主体哲学”或“经验哲学”等同于“实存论现象学”,而“概念哲学”可以替代“实存哲学”而非“实存论现象学”。也就是说,概念哲学或许可以替代实存主义,但并不因此替代现象学。说得更直白一点,用概念现象学替代实存论现象学自有其道理,但概念哲学本身就与现象学相关,不存在替代它的问题,最多只能够突出它的某些方面。其实,无论是概念哲学还是主体哲学都关注知识,也都关注实存,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对我们前面提到的福柯式区分进行了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价值的描述。他写道:“福柯认为1930年以后的法国哲学被分成了两种潮流,一种是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来自萨特和梅洛-庞蒂,一种是关于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哲学,来自卡瓦耶斯、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主体问题在第一个潮流中始终是核心。不管理论家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还是语言学框架内工作,提出真理(或知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的笛卡尔式的我思,始终都是出发点。在此关于主体(或者其缺失)的思考导致关于知识的结论。巴什拉颠倒了哲学的先后秩序;通过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它的各种形构或变形,他们导致的是关于主体的结论。”(23)这其实表明,20世纪法国哲学始终面临的是实存与知识之间的张力,不同的哲学家从两端之一出发,但最终还得面对同一个问题。当然,实存论现象学在实存和知识问题上的姿态显然是首要的方案,其他哲学流派只不过是对它的批判性补充。法国实存论现象学批判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体,法国科学哲学大体上也赞成这样的立场。在这方面,巴什拉无疑具有作为重要参照的价值,他“不仅攻击实证主义,而且攻击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他“同样拒绝实存主义和现象学”,这就造成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像德里达一样,他置疑关于同一、实存的哲学,拷问关于主体的传统笛卡尔式的假定,但他并不寻求用差异,而是用一种非柏格森式的关于变易(一种非连续的而不是连续的变易)的哲学,用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主体,用一种与封闭、确定的理性相反的开放、创造的理性来取而代之”(24)。这里所说的动态的主体和创造的理性都与法国现象学的许多主张相符合,从根本上说否定了先验主体的支配性地位,也因此改变了纯粹知识的理想。
福柯本人的情形显然比较复杂,尽管他反复声称自己否定现象学方法,但他确实与现象学有着无法摆脱的关联。一般认为福柯接受概念哲学的影响,并深化了概念哲学,也因此更多地与新康德主义、甚至实证主义传统相关。就算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概念哲学与现象学的剪不断的关联。其实,福柯主要属于主体哲学,其目标不是知识和科学,而是实存和主体。更确切地说,通过反思现代性哲学话语,福柯注意到的是实存与知识、主体与概念之间的张力。具体地说,福柯关心的是经验、知识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涉及的是主体如何诞生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德贡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现代性话语反思中的“黑格尔主义的福柯”形象。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清理批判主义传统,也可以说他的现代性反思是从康德出发的,但他并不是笼统地涉及这一问题。德贡布表示:“福柯也区分出了来自康德的导致哲学分化的两种‘批判传统’。第一种是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它希望哲学反思科学的条件。另一传统——福柯说他本人归属于这一传统——乃是反思我们的历史的传统,它在这一问题中获得承认:什么是我们的现实?根据他的看法,这一传统由于黑格尔、尼采、韦伯或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名字而获得阐明。”(25)一般认为3M时代是反黑格尔主义的时代,福柯本人完全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的时代,要么依据逻辑学要么依据认识论,要么根据尼采要么根据马克思,都试图摆脱黑格尔”(26)。但福柯并没有因此否定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这其实表明,福柯始终迷恋于主体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他写道:“要真正摆脱黑格尔,必须以准确评价值得摆脱的东西为前提,必须以知道黑格尔在什么地方或许暗中与我们密切相关为前提,必须以知道在允许我们反对黑格尔的东西中仍然属于黑格尔主义的东西为前提,并且估计到我们借以反对他的东西或许仍然是他对抗我们的一种诡计,他在终点处静静地等待着我们。”(27)福柯显然没有摆脱其师梅洛-庞蒂的阴影,而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现象学心理学家宾斯万格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其实,实存论现象学内部的立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更多的混乱。严格说来,现象学之外的立场不过是内部分歧的某种扩大,甚至会出现内部差别大于外部差异的情形。原因在于,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弟子、再传弟子众多,但他们并不完全忠诚于他的思想,况且他本人也始终处在不停探索的途中。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何谓现象学?在胡塞尔最初那些著作出版半个世纪之后,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28)按照他的解读,现象学一方面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科学,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关于实存、从人为性出发的科学;一方面是一种悬置自然态度的先验哲学,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已经在此,必须现象学地考虑与世界的素朴联系;一方面具有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的雄心,另一方面又是对实际体验到的空间、时间和世界的说明;一方面它主张不考虑人的心理、社会、历史因素而描述我们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种“发生现象学”,甚至是一种“构造现象学”。有些人认为通过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进行区分,就可以消除上述矛盾;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整个《存在与时间》都源自于胡塞尔的指令,从总体上看只不过是对胡塞尔在其晚年看作是现象学第一主题的‘自然的世界观念’或‘生活世界’的解释,由此矛盾再度在胡塞尔本人的哲学中出现”。(29)当利科说“宽泛意义上的现象学乃是胡塞尔作品及源自胡塞尔的诸异端的总和”(30)时,他显然承认了现象学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重重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最终都意味着实存与知识之间的张力。
三、从身体现象学到物质现象学
尽管把意向性视为超越性,由此突破了胡塞尔对意向性的内向性和构造性解释,但由于强调自为和虚无,萨特哲学至少在存在论层面上依然接近了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然而,一旦涉及人的在世存在或“人的实在”,他明显不再关注纯粹意识,而是突出了身体及其实存的意义。事实上,法国现象学一开始就主要不是与胡塞尔的具有明确理论化倾向的纯粹意识现象学联系在一起,而是体现为以海德格尔和舍勒为基础,通过创造性地误读胡塞尔而获得实现的实存论现象学或身体现象学。这种瓦解意识哲学的倾向首先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1945)中,随后在利科的《意志哲学》(1950-1960)、列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1961)和亨利的《身体的哲学与现象学》(1965)中获得了集中体现。这种身体现象学围绕“本己身体”展开,不管是语言(文化)、身体还是世界,都突破了内在意识或观念化的秩序,体现了物性(自身维度)和灵性(观念维度)之间的张力。但是,在身体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物性的维度越来越获得强调,而灵性的维度渐趋消失,逐步产生了所谓的“物质现象学”,亨利的《物质现象学》(1990)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名称,但隶属于概念哲学传统的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的相关作品才是其典型体现,身体、语言(文化)、世界在这种物质现象学视野中变成了完全物质性的力量。20世纪法国哲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而现象学在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31)。依据新的资料及对旧材料的新解释,我们可以对这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进行某种新的描述。
第一阶段是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分别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新唯心主义、新批判主义)和生命哲学相互竞争、各领风骚的时代。虽然彼此对立,但它们都深受精神主义传统的影响,由此为德国现象学的引入和进行法国式转换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列维纳斯对胡塞尔哲学的海德格尔式实存论读解影响了法国现象学的主流方向,而马塞尔在现象学方面的独立思考也为20世纪法国哲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海德格尔的具有身体哲学指向的现象学成为了法国哲学的首要选项,而马塞尔哲学已经体现为身体现象学,其《是与有》(1935)不仅是这一阶段的身体现象学的集中体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随后阶段的现象学走向。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以“我是我的身体”突破了笛卡尔的“我有一个身体”。他这样写道:“当我肯定某种东西存在的时候,我总是把这种东西视为是与我的身体相联系的,是能够被置于与它相联系的,不管这有多么的间接。只是必须明白,我之所以赋予我的身体这种优先性,就在于它以完全非客观的方式被给予我这一事实,就在于它是我的身体这一事实。”(32)当然,在他关于“有”的现象学描述中,“有”与“是”并不是完全对立,它始终围绕着人的实存而展开。依据梅洛-庞蒂对马塞尔的读解,其最基本的论点就是:“在某种方式上,我是我的身体。”(33)其实,梅洛-庞蒂认为马塞尔的老师柏格森已经走在身体哲学的途中。
第二阶段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实存论现象学占据主导地位的3H时代。这一阶段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三位德国大师的重大影响,该时期的哲学研究“是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研究”(34),或者说主导趋势乃是“让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联姻”(35)。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哲学家都把身体及其实存视为首要的主题,而身体既不是在认识活动中被构造的对象,也不是自在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体现为心身统一的“第三维度”。梅洛-庞蒂写道:“在身体从客观世界退隐并在纯粹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一种第三类存在的同时,主体丧失了它的纯粹性和透明。”(36)利科针对胡塞尔的先验主义及其对立的经验主义表示,“人们相反地将会看到,一切都让我们远离那著名的、晦涩的先验还原——在我们看来,对本己身体的领会已经使这种还原失败了”(37)。关于意愿和非意愿的研究要求克服笛卡尔式的纯粹我思,并因此把代表了身心之统一的本己身体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思的全面经验包纳了我欲求,我能够,我体验,并且以某种一般的方式,包纳了作为身体的实存……有一种关于本己身体及其与意愿着的自我之关系的现象学本相学”(38)。与此同时,语言(文化)和世界都意味着物性和灵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关系。萨特强调自为即绝对自由,但对于梅洛-庞蒂和利科来说,只存在着处境中的自由,即“肉身化的自由”,所谓“人的自由之伟大和卑微已经汇入到了一种依赖的独立中”(39)。这一阶段显然是身体现象学的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都深受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三位怀疑大师的影响。语言问题是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主题,结构主义因为关注语言问题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配偶”(40)。然而,后结构主义重新回到了现象学,回到了对于主体问题的关注,比如德里达被明确地归入到现象学家之列,福柯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学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利科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法国现象学的解释学转向;列维纳斯实现了现象学的伦理学转向;亨利也发表了他最主要的现象学专著《显示的本质》(1961)和《身体的哲学和现象学》(1965)。当然,利科、列维纳斯和亨利的重大影响要在后面一个时期才能体现出来。语言问题在这一时期具有首要的地位,尽管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表象功能,但语言的自身维度或物质性获得了极度强化,也因此导向了某种文化唯物主义。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哲学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身体的地位获得了更明显的体现。如果说利科、列维纳斯、亨利依然强调身体是一种心身统一体的话,福柯和德里达则已经把身体视为严格物质性的存在,强调的是原始的身体经验。由于语言(文本、话语)的物质性以及身体的物质性获得了极高强度,某种所谓的物质现象学由此诞生了。事实上,列维纳斯和享利都关注自身物质性与物质本身的物质性的关系,虽然前者注意到的是一种外在性关系,而后者强调的是内在性关系。
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与现象学的复兴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在这个时期,多元化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现象学明显地占据着优势地位,这意味着现象学在后现代氛围中浴火重生。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在3M时代出版的那些重要著作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利科还通过对叙事理论的研究拓展了自己的解释学的现象学;亨利和马里翁则综合了3H时代对主体性的强调和3M时代对主体性的瓦解,主要突出了被动主体与绝对显示之间的关系,这其实否定了“回到事物本身”对于意识的依赖,强调了绝对给予的意义。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等与概念哲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更加强化了身体、世界、语言(文化)各自的物质性,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的能量交换关系。德勒兹否定唯心主义欲望观,根据一种“唯物主义”原则把无意识看作是身体机器的运转:“无意识到处在动,有时不停地,有时不连续地。无意识喘息,无意识发热,无意识吃东西。无意识拉屎,无意识接吻……到处都是机器(绝非隐喻意义上的)在运作:机器的机器,连同它们的搭配和衔接。”(41)概念哲学家一方面强调主体的消失,另一方面则把物质性的身体抬高到了首要的地位。物性完全取代了灵性,意识要么不存在,要么只不过是物质的产物,从而回到了庸俗唯物主义的论点。如果说主体哲学否定纯粹意识主体的话,概念哲学干脆就否定了意识主体。很显然,在瓦解意识主体方面,概念哲学比主体哲学要激进或极端得多。当亨利把自己的生命现象学同时名之为“物质现象学”时,他其实代表了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和其他现象学家在内的共同倾向。
20世纪法国哲学的四个阶段的进展并不以“飞跃”的方式出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学运动贯穿了全部四个阶段,虽然它在各个阶段的地位和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通常所说的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争,应该严格地说成实存论现象学与知识论现象学之争,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当结构主义者声称他否定现象学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否定了现象学的实存论倾向,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于现象学的认识论和解释学倾向的,事实上,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作出了综合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的不懈的努力。当我们说结构主义只不过延续了现象学的另一个传统,也就是由卡瓦耶斯开创的对于胡塞尔纯粹逻辑领域的研究的时候,这种努力与理想语言分析有一致之处;而解释学则与日常语言分析有共同的地方。如此说来,正像分析哲学中会出现从理想语言分析向日常语言分析的过渡一样,现象学从理想的逻辑研究向日常的实存解释的过渡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梅洛-庞蒂关于语言现象学的研究在这一过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构主义者只不过更加突出地强调了他以及利科对于语言和文化的物质性的思考。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后结构主义在突破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向实存论现象学的回归。由于后结构主义者几乎都有其结构主义的经历,也因此可以被视为放弃了自己的反现象学或超现象学的立场。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复兴时期的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一样走向了对语言、身体、世界的物性化理解,也因此共同走向了物质现象学。
20世纪法国哲学经历了复杂多变却丰富多彩的发展历程,伴随法国现象学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的强势复兴,现象学尤其体现了作为一个延续整个世纪并跨入到新世纪中的哲学流派的强大活力。亨利在1990年表示,“随着最近几十年的各种巴黎时尚,尤其是因为最表面因此代表了其最延伸形式的结构主义的崩溃,随着打算替代哲学但从来都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外在视点的人文科学重新回归它们自己的位置,现象学越来越呈现为我们时代的主要思想运动”,他甚至认为,“现象学之于20世纪,就如同德国唯心论之于19世纪,经验论之于18世纪,笛卡尔主义之于17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或邓斯·司各脱之于经院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于古代哲学”(42)。如此说来,探讨20世纪法国哲学,其实就是在追寻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
注释:
①转引自H.Spiegelberg, The Movement of Phenomenolog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Martinus Nijhoff / The Hague,1965, p.xxi.
②M.Foucault,Dits Et ?魪crits IV(1980-1988),?魪ditions Garlimard,1994,p.764.
③G.Gutting,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④参见莫伟民、姜宇辉、王礼平《二十世纪法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M.Foucault,Dits Et ?魪crits Ⅳ(1980-1988),p.764.(福柯所说的时间有误,萨特的论文应该是发表于1936年,而卡瓦耶斯的著作则出版于1937年——引者注)
⑥H.Spiegelberg,The Movement of Phenomenology: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p.404.
⑦J.Beaufret,De L' Existentialisme A Heidegger,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rin,1986,p.134.
⑧E.Lévinas,Ethique et Infini,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et Radio-France,1982,p.36.
⑨[美]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1927-1961》,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⑩G.Bachelard,《Preface》,in J.Cavaillès,Sur La Logic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PUF,1960,p.vii.
(11)J.Cavaillès,Sur La Logic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PUF,1960,p.44.
(12)J.Cavaillès,Sur La Logic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PUF,1960,p.66.
(13)J.Cavaillès,Sur La Logic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PUF,1960,p.75.
(14)P.Engel,"Continental insularity:contemporary French analytical philosophy",in P.Griffiths(ed.),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
(15)Levinas,En Découvrant 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Libraire Philosophique J.Vrin,2001,p.11.
(16)[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页。
(17)M.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魪ditions Garlimard,1945,p.ii.
(18)M.Henry,La Barbarie,?魪ditions Bernard Grasset,1987,p.8.
(19)G.Marcel,Journal Metaphysique,Librairie Gallimard,1927,p.321.
(20)G.Marcel,Journal Metaphysique,p.xi.
(21)P.Ric?覺ur et G.Marcel,Entretiens Paul Ricoeur-Gabriel Marcel,Aubier-Montaigne,1968,p.20.
(22)G.Gutting,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227-228.
(23)M.Tiles,"Epistemological history:the legacy of Bachelard and Canguilhem",in P.Griffiths(ed.),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p.143.
(24)M.Tiles,"Epistemological history:the legacy of Bachelard and Canguilhem",in P.Griffiths(ed.),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p.143.
(25)V.Descombes,Philosophie Par Gros Temps,Les ?魪ditions De Minuit,1989,p.15.
(26)Foucault,L' Ordre Du Discours,?魪ditions Garlimard,1971,p.74.
(27)Foucault,L' Ordre Du Discours,pp.74-75.
(28)M.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p.i-ii.
(29)M.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i.
(30)P.Ric?覺ur,A L' ?魪co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Libraire Philosophique J.Vrin,1986,p.9.
(31)杨大春:《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
(32)G.Marcel,?魭tre et avoir,Paris:Aubier Editions Montaigne,1935,p.9
(33)M.Merleau-Ponty,Parcours 1935-1951,?魭ditions Verdier,1997,p.37.
(34)M.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 1951-1961,?魭ditions Verdier,2000,p.294.
(35)M.Foucault,Dits Et?魭crits Ⅳ(1980-1988),p.434.
(36)M.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403.
(37)P.Ricoeur,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1.Le Volontaire et L' Involontaire,Editions Points,2009,p.20.
(38)P.Ricoeur,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1.Le Volontaire et L'Involontaire,p.27.
(39)P.Ricoeur,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1.Le Volontaire et L'Involontaire,p.603.
(40)M.Foucault,Dits Et ?魪crits Ⅳ(1980-1988),p.434.
(41)Deleuze & Guattari,Anti-Oedipe,PUF 1980(Nouvelle ?魪dition),p.7.
(42)M.Henry,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PUF 1990,p.5.
标签:现象学论文; 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福柯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