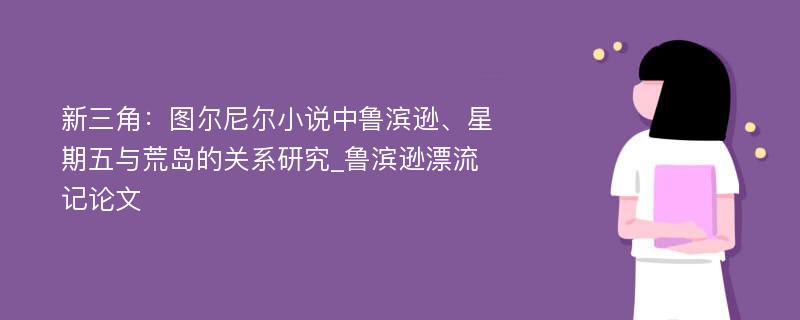
全新的“三角”——鲁滨逊、礼拜五与荒岛在图尼埃小说中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滨逊论文,荒岛论文,关系论文,礼拜五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5-0059-11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早已成为文学上的经典,几个世纪以来,这部杰作仿佛生命力极强的种子,随风播撒之处“生长”出大量的仿作。单只在法国,称得上是它的“后代”的,就有凡尔纳的《神秘岛》、吉罗杜的《苏珊与太平洋》、圣-琼·佩斯的《鲁滨逊画像》等等。不过,这几部作品虽然直接受到了笛福原作的启发,但对于人物和情节的处理都很自由。比如在凡尔纳笔下,海难后的生还者增加到五人,其中更有一位体现了应用科学与技术胜利的工程师;吉罗杜的作品里,淳朴率真的法国少女苏珊替代了严谨克己的英国清教徒鲁滨逊。相反,文学史上最近的一次改写——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以下简称《礼拜五》),则比较保守地遵循了笛福的原作,只是在全书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幅里,图尼埃的文本才彻底脱离了模仿的对象。
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有着哲学、人种学教育背景的图尼埃①显然不想也不会对前人亦步亦趋。图尼埃曾经说过:“鲁滨逊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是构成西方人灵魂的一个基本要素。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他都活生生地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神话必然是我们拥有的最为生动、最富现实性的神话之一。”他因此想从鲁滨逊的故事中“选取某些角度作为小说的铸模,把当代的人类状况在里面浇铸成形,把生活在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人们的情绪与追求书写下来”。(Tournier,1977:221)图尼埃的创作意图告诉我们,笛福的原著只是他借来安插故事的框架,他势必要从新的时代精神出发,突破原作的一些局限,给作品注入新的哲理。实际上,其他仿作因为在人物和内容方面已经与《鲁滨逊漂流记》有了太大的距离,反而损害了与后者的可比性,《礼拜五》却从与笛福原作相仿的情境出发,通过引向截然相反的结局,让我们看到了对原作更大的颠覆和超越。
以岛上发生的爆炸为界,《礼拜五》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基本沿用《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情节,后一部分则完全是图尼埃自己的发挥。当然,即便在前一部分,《礼拜五》与笛福的原作在叙述方式、内容侧重上也有很多的不同。比如原作使用的是第一人称,中间夹杂着鲁滨逊的日记(当然也是第一人称),新作采用的则是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错的叙述方式——小说的主体部分使用第三人称,鲁滨逊的“航海日志”使用第一人称。这样,与人物保持距离的叙述者记录下鲁滨逊的言行,“航海日志”则直接呈现了主人公的思考与内心活动。此外,在情节的安排上,图尼埃也对原作进行了增删、移位、替换等的方式改写。他把原著中与岛上经历无关、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上岛之前和离岛之后的部分,全部删去,还删掉了鲁滨逊在岛上生活的一些片段,如地震、饲养鹦鹉、小岛附近的一次沉船事件等等。相反,他增加了与鲁滨逊的孤独、性欲、精神历练密切相关的许多插曲,比如沉溺于泥塘、逃遁进山洞、与植物和大地交媾等等。一些情节他虽然予以保留,甚至相当忠实于原著,却调换了它们的先后顺序,比如笛福的鲁滨逊只是在给自己搭建好住所、找到记时的方法、开始写日记以后才开始“呆望海面,希望有一只船出现”,又过了很久才打造出独木舟;在图尼埃的笔下,鲁滨逊同样死里逃生,第一个反应却不是从沉船上抢救必需的物资,而是眺望大海,“恨不得救星马上就从海上到来”。(Tournier,1972:21)②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荒岛,夜以继日地造出小船“越狱号”。此外,图尼埃的鲁滨逊在修建住所之前,在下定决心要改造荒岛的同时,就决定要记述“航海日志”,对他来讲,比起重建外部世界的秩序,理清内心世界的头绪更为重要。相反,在笛福的作品里,鲁滨逊的“写作”只是外部既定秩序的反映:“在这个(软弱的)阶段过去以后,在把家用物品和住处安排妥当……把一切都弄整齐之后,我便开始记起日记。”(笛福:63)
图尼埃还经常置换笛福提供的材料,比如关于火药的部分:笛福的鲁滨逊在雷雨天受到警醒,意识到把火药桶集中存放的危险,随后把火药分成小包放到不同的地方,避免了爆炸的可能;图尼埃的鲁滨逊却没有这种防范意识,以致最后火药引发了爆炸,将山洞夷为平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让人看到了图尼埃在“仿照”的幌子下对原著的巧妙改写。以下我们将以图尼埃小说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为视角,分析他们各自呈现的新特点,以及三者之间不同于笛福原作的关系。
一、岛屿
在笛福笔下,小岛是鲁滨逊要努力驯服、使之为自己服务的对象。正是通过与以荒岛为代表的恶劣生存条件的较量,鲁滨逊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小岛尽管可以升华为大自然的象征,但主要是作为地理上的一个所在,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提供处所。与此不同,在图尼埃的作品里,“荒岛与鲁滨逊、与礼拜五一样,都是小说的主人公”。(Deleuze:257)当鲁滨逊将小岛的形状比作“一个双膝跪地、没有头颅的女人身体”时,他发现了后者隐秘的女性气质。联想到从前认识的某个奔放的意大利女郎,他将小岛命名为斯贝朗莎,从而把这种女性特质彰显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小岛具有的遮蔽与亲密的特点使之相继充当了母亲与配偶的角色。
起初,受到万物有灵论的影响,鲁滨逊还只是把斯贝朗莎看作“阿根廷草原上的一头未被完全驯化的母牛,尽管已经用烙铁打上了印记”。接着,主人与牲畜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比附和认同:“鲁滨逊只有在和斯贝朗莎全面重合之际,才会无限丰富充实。”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以致“今后将有一个飞翔的‘我’,一会儿落在肉身上,一会儿落在岛屿上,从而让我轮流成为这个或那个”。等到鲁滨逊让计量时间的漏壶停止,暂时把自己的总督—将军—统治者的混合身份搁置一边,他已经感觉到“斯贝朗莎不再是一块有待治理的领土,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具有不容争辩的女人的天性”,他自问岛上的山洞是否是斯贝朗莎的嘴巴、眼睛或“某个身体上的天然开口”。在小岛顶部的山洞里,他发现一处凹陷,正好能让自己蜷缩着身子、以胚胎的姿势钻进去:“……试了好几次,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体位——蜷起身子,膝盖挨住下巴,交叉两脚,两手放上脚面——正正好好地嵌了进去,以致他忘记了四肢所受的局限。”鲁滨逊于是又倒退到胚胎在子宫里的孕育阶段,感到“在这样的深度,斯贝朗莎的女性气质上又叠加了母性的所有特点”,因此接下来的联翩浮想中,他对母亲的回忆占据了上风。母亲对他来说是真与善的支柱,是坚实而好客的大地,是包容他的恐惧与痛苦的场所。鲁滨逊在斯贝朗莎的肚腹中感受到了永恒的快乐:“这里完美地结合了黑暗温暖的子宫的宁静与坟墓的宁静,完美地结合了此世与彼世。”这个母亲般的庇护所使他的生命有了牢固的根基,使他得以回归那份“失去的、让人惋惜不已的本真”。鲁滨逊从斯贝朗莎那里重新获得的,不仅有内心的平静,还有生命的动力:旱季来临,乳头状的地突上溢出最后一股清泉,恰如母亲的乳汁,让鲁滨逊不胜感激,宛如新生的婴儿一般哇哇大哭。
然而小岛与鲁滨逊的母子关系还是很快就结束了:一次鲁滨逊在山洞里打盹,朦胧中险些遗精,意识到自己与小岛母亲的关系隐含着乱伦的危险,自此只敢把行动局限在地表(山洞以外),于是,小岛充当伴侣的时期开始了。
的确有那么一个阶段,鲁滨逊将小岛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强烈地感觉到身下的小岛是一个躯体:“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自己正睡在小岛身上,就像睡在某个人身上,感到小岛的身躯就压在他的身下。”(Tournier,1972:126)描写地貌的词汇与描写女人生理部位的词汇混合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性的暧昧:“玫瑰山谷”被比作“女人略为肥厚、却很有承载力的背部”;低处的草地“有着起伏的肉体,在下方收紧,形成一片狭小、坚实、弧状的平地,被一道横谷从正中分开,谷里覆满乱蓬蓬的浅色绒毛”;由于发音临近的关系,“山谷”(combe)一词让鲁滨逊联想到了“腰腹”(lombes)。鲁滨逊于是“用尽全力去拥抱这庞大的土地的身躯”,他的“性器就像犁一样插到地里,怀着对一切造物的无限怜爱,一泄如注”。当然,简单的性欲满足无法让鲁滨逊甘心,囿于清教的伦理观,他要确认这种“夫妻关系”,使之合法化。于是他从《圣经》里找到一曲雅歌献给斯贝朗莎,斯贝朗莎也用《圣经》里的诗句殷勤地与他唱和,小岛被赋予了言说的能力,“《圣经》用最古老的祝婚歌帮助她表达着爱情,书里经常把大地比喻为女人,或者把妻子比喻成花园……”作为妻子的小岛甚至很快就生育出他们的女儿:在鲁滨逊的精液流淌处长出一种叫做曼德拉草的植物,“根茎嫩白而有肉感,奇异地分成两叉,明白地显露出一个少女的体形”。鲁滨逊于是明白:“原来他与斯贝朗莎的爱情并不是不育的。”(Tournier,1972:138)
鲁滨逊与小岛的夫妻关系不久也以失败告终,因为他恼怒地发现,曼德拉草并非自己在岛上的独特标记,别的男人也有同样的播种能力(礼拜五仿效他做了同样的事,生产出同样的后代)。他于是再也不去玫瑰山谷了,因为小岛在那里表现得像个荡妇,随便跟什么人都可以上床。
综合来看,笛福小说里的荒岛,是没有生命的处所,是作为主体对立面的、被索取与被改造的客体。而在图尼埃的作品中,小岛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改造,相反,它被拟人化,具有了性别,是礼拜五现身之前小说的主角之一,是鲁滨逊以外的“他者”,甚至是兼具思考与言说能力的“主体”。小岛的“思想”经常以启示的方式间接地表达出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爆炸发生以后,岛上的山洞被碎石封住,洞口的一堆乱石隆起成山头——洞穴变成了山冈,凹陷转化为凸起,小岛改换了性别,或者说,展示了它潜在的双性同体。获得警示的鲁滨逊从此弃绝了将小岛女性化的道路,而是希望像它、像礼拜五一样也成为双性同体的“完人”。
二、礼拜五
在《鲁滨逊漂流记》里,礼拜五是一个黑种土人,有着吃人等野蛮的恶习,鲁滨逊用火枪和基督教文化这两种武器对他进行驯服和教化,使他甘心成为自己的奴仆。被驯顺的礼拜五虽然也显露出忠实、诚恳、可爱的一面,但他与鲁滨逊之间显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实际上,作为“白人”与“文明人”的对立面,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彰显后者的尊贵和优越。
图尼埃的小说直接以礼拜五命名,突出了与笛福原作的不同。显然,与“文明人”鲁滨逊相对应的“原始人”礼拜五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礼拜五的出场在两部小说中对比鲜明。笛福的鲁滨逊是刻意地解救了礼拜五:因为缺少帮手,他早就精心算计,要搭救一个土人,让他对自己感激不尽,心甘情愿地沦为奴隶:“我要想找到一个仆人,现在正是时候……这明明是上天号召我搭救这个可怜虫的命哩。”(笛福:188)图尼埃的鲁滨逊之所以搭救礼拜五,却并非出于机心和自愿,他是因为看到三个土人向自己埋伏的地点跑来,担心被发现才决定开枪,而且他想瞄准的,是前面被追赶的那个,不巧射击的时候被狗撞了一下,打死了在后面追赶的土人,阴差阳错地救下了礼拜五。礼拜五因此托的是幸运或者说是上天的福,他和鲁滨逊的关系开始于一场误会,后者并不值得他感激。当我们看到小说中“黑人的前额抵到地上,两手摸索着把白人的脚放到头上,表示归顺”这段描写时,联想到笛福原作中相应的一幕,不难领会出图尼埃戏仿的意味。图尼埃塑造的礼拜五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自然神 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神话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动物与人还没有真正分开的时代,两者能够不加区别地互相替代。神话时代是(动物与人)可以交流的时代,一种生物可以兼具两种属性。”(Bouloumié:70)凭借与动植物的特殊关系,礼拜五就是这样的“神话人物”,他与动物十分亲密。依照印第安人用“活的被子”御寒的习惯,他和泰恩(海难后幸存的狗)相遇的第一晚就抱着它睡觉,让鲁滨逊颇感惊奇的是,那顽劣的动物竟然温顺地接受了。他把威严漂亮的公羊安道尔,这“岛上所有山羊的国王”看作自己游戏的伙伴,不惜送上性命也要与它玩耍纠缠。所以鲁滨逊总结说:“他与动物的关系更具兽性而不是人性……动物把他当作了自己的一员。”礼拜五与植物的关系也是不分彼此。他喜欢住在树林里,在“藤编的吊床上一躺就是几天”;他用植物装扮自己:“头顶花冠,赤裸的全身绘满了常春藤的绿叶,枝桠沿着他的大腿爬升,环绕住他的躯干”;或是相反,给仙人掌披上衣裳,使之成为千奇百怪的“植物模特”。而植物的天性也都顺从于他:那些“被连根拔起、颠倒过来又插到地里,枝桠在下、树根朝天”的灌木竟然在根须上长出了绿芽。
礼拜五的美是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反映:“他的赤裸好像也有遮掩……他走着,以无上的炫耀移动着身躯。”他结合了充沛的体力与高度的灵巧:用手走路,攀爬大树,搭弓射箭……优雅与力量的协调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超自然的完美形象。礼拜五没有“进化”,他也不需要进化,他的独立是绝对与神圣的。兼具兽性、人性与神性的礼拜五,最好地诠释了图尼埃作品中“神话人物”的性格。可以说,隐藏在礼拜五身后的,是代表自然的神灵迪奥尼索斯:“改造成‘植物—人’的他狂笑得发颤,围绕着鲁滨逊跳起疯狂的舞蹈。”绿野植被的神,恣意妄为的神,欢乐洋溢的神,这不正是乔装的酒神迪奥尼索斯吗?
图尼埃与尼采一样,有意忽略了酒神可以带来的癫狂与死亡,强调了酒神的自由奔放、热爱生活。在自传《圣灵风》里,图尼埃曾明白地表达了他对尼采的崇拜。(Tournier,1977:200)尼采对他的影响在《礼拜五》中不乏证明:鲁滨逊直接采纳了“超人”这一说法,(Tournier,1972:116),叙述者也把鲁滨逊比作查拉图斯特拉。(Tournier,1972:237)尼采自况为“哲学家迪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对他来说,迪奥尼索斯代表“对生活的积极肯定”和“对生命的承诺”。(Nietzsche,Crépuscule des idoles:100—02)他用这些品质揭露基督教“对生活的痛恨”、“把一切价值都颠倒,使之与生命对立”。(Nietzsche,L'Antéchrists:194)在图尼埃的笔下,礼拜五—迪奥尼索斯正是要为所有这些被颠倒的价值恢复名誉,为原始而未被驯化的、神圣而未被基督教化的一切平反昭雪。
颠覆者 像笛福的鲁滨逊一样,图尼埃的鲁滨逊一收留礼拜五,马上就在仅有两人的微型社会里确立了统治关系,他对礼拜五的奴役与压迫甚至比笛福的原作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教给礼拜五“劳动的美德”,甚至荒唐到让他“去给主路上铺置的卵石和石块儿打上光蜡”,尽管“一阵小雨就会把蜡冲得无影无踪”。“文明起源于对外的征服和对内的压迫。……文明的一方总是带有原罪:征服与政治压迫。”(Diamond:3)鲁滨逊的行为让我们验证了西方文明本质上罪恶和血腥的一面。
表面上看,礼拜五驯良无比,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然而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动摇了小岛的体制,因为很明显,他对主人灌输的那些“定义、原则、信条和教规”并不理解,所以他忍不住要大笑,“把总督及其治理海岛的煞有介事的一套搞得窘态百出、原形毕露”。鲁滨逊在他的眼里看到了装腔作势的自己,不能不正视自己的疯癫。礼拜五在一个仅靠盲目信念的力量维系着的体制中,撒下了怀疑的种子。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他最后把鲁滨逊储存的食品以及从沉船上运来的财物全都毁了的时候,鲁滨逊的反应并不很强烈,倒像是他早就预料到,甚至早就期待着这场无妄之灾似的。
正像打破禁忌、反抗压制的迪奥尼索斯,礼拜五首先颠覆了鲁滨逊对于身体的审美。在他的鼓励下,鲁滨逊终于离开阳伞,大胆地暴露在日光底下,把自己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他的身体放射出热力,他觉得自己的心灵也从中汲取到从未有过的信心。”
礼拜五摧毁了清教主义设置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分界。书中那棵倒栽而汁液回流的柳树,象征着礼拜五让鲁滨逊业已确立的经济与道德秩序经受的颠覆。他汲干了稻田,“水稻的收成告吹,他连想也没有想到”。把牲畜集中起来喂养,目的是供给食物而不是为了训练它们、使之成为狩猎游戏中的玩伴,这在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不懂得哪些是要大力捕杀的有害物种,不但饲养老鼠做自己的宠物,还满怀爱心地照顾一只被遗弃的秃鹫,看到他嚼碎蛆虫嘴对嘴地喂给那只丑怪的动物,鲁滨逊恶心难忍,却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自己的反感、恶心、对于高雅的苛求……是文明的最高保证,还是一种无用的、需要丢开以开始新生的压舱物。礼拜五的首要职责是摧毁“西方人”在岛上完成的“功业”,后者各方面都是他鲜明的对照:长发没有髭须的少年与光头蓄着胡子的成人相对,正像黑人与白人、“冲动、慷慨、爱笑的土著人”与“有条不紊、吝啬、忧郁的英国人”相对。于是他有意无意地引发了山洞的爆炸,使所有文明的留存化为乌有。爆炸发生以后,掌控局面的,就是礼拜五了,于是我们看到:奴隶变成了主人,儿子成为了兄弟,“黑鬼”开始教授给白人新生活的原则。作为重视原始文明之丰富性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图尼埃正是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了那些“反文明的人”:“是的,我是想将此书献给移民法国的许许多多沉默无言的外籍劳工,献给所有这些匆匆来自第三世界的礼拜五们……我们的社会就构筑在他们身上。”(Tournier:1977:236)
启蒙者 在笛福的笔下,礼拜五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创造能力的,他的那些零碎的小玩意儿,都是笛福自己从英格兰本土上批发过来的。笛福感兴趣的,仅仅是心灵手巧的主人公鲁滨逊,他既审慎又聪敏,完全能在没有社会支援的前提下自给自足。图尼埃的礼拜五则不仅仅是一个破坏者,更是一个创造者。这个野人轻易地解决了鲁滨逊的所有难题:利用贪吃的蚁群搬移生活垃圾,把卵石缚上绳子做成“无声的武器”。他还用鳖壳制成盾牌,发明了风筝与风力竖琴。礼拜五的创造性尤其体现在他的“启蒙”作用上,他开启了通往“新人”——剔除了现代文明的熏染、恢复质朴无邪的人——的道路。
礼拜五教会了鲁滨逊天真地笑,让他挣脱清教徒的苦修与克己,释放出自己的本真天性。起初,狂笑的他在鲁滨逊看来像是“被魔鬼附体”、“十分可怕”,这种笑法“惹得主人发火第一次动手打了他”。但是很快,这笑声就似花儿的绽放,表述着生的快乐,成为“揭露并对抗愚蠢与凶恶”的理想武器。
鲁滨逊从礼拜五那里学会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较之高深的智慧,一个人的身体蕴涵着更多的真理”。(Nietzsche,1971:46)在礼拜五的影响下,鲁滨逊与自己的肉体获得了统一:“于是他发现,一个被接受、被喜爱、被模糊地欲求的身体……不仅是嵌入外部世界的更好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忠诚与强大的伙伴。”他还发现身体能够帮助一个人与自然本原完美地融合,当阳光穿透他的身躯,给他注入生命的活力时,他经历了与宇宙的交合,这种交合被比拟为男女的性爱:
对我来说,只要沐浴在太阳神的光芒里,……肉欲的快感就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销魂……和乌拉诺斯的做爱给我注入了一股鲜活的能量,让我蓄满了一天一夜所需的精力。如果非要把这种与太阳的交合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那么把我看作阴性、定义为天的妻子比较合适。(Tournier,1972:229)
鲁滨逊开始对大自然采取迥异的态度:亲切、信任、融入,不再以清教徒的眼光怀疑未经改造的自然会趋向堕落与罪恶,他对太阳的崇拜就传达出这种与自然融合的意向。一种全新的时间管理方式也随之出现:现时与当下的欢乐替代了对过去的咀嚼回味,或对未来的设想构建。远离一个“破败、肮脏与荒芜的世界”、“陶醉于青春与活力”的礼拜五“决不脱离这个永恒的现在”,“这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永恒的现在”。
礼拜五还让鲁滨逊发现了游戏的乐趣与意义。通过游戏,他为自己、也为鲁滨逊的愤怒找到了发泄的途径(捣毁竹编的木偶、鞭打沙土制成的模型),在他的启示下,两人互换衣服和角色,重新演绎他们之间的许多生活片段,疗治了彼此的心理创伤:“鲁滨逊终于明白,这种游戏对礼拜五很有好处,可以把他从关于奴隶生活的记忆中解脱出来。鲁滨逊自己也从中受益,因为对于身为总督与将军的过去,他总是心存一丝悔意。”
最后,礼拜五让鲁滨逊重新认识到无目的行动的价值。当他不知疲惫地搭弓射箭,却既不瞄准猎物也没有任何目标时,他只想“让它们(箭镞)起飞,在空中飞得尽可能地远、尽可能地久”;看到箭头开始下落,“他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样”。这种挣脱地心引力、实现超越的梦想终于在他发明风筝的时候实现了,看着“活在白云之间的风筝”,他也“一边大笑一边模仿着它的舞蹈”。
礼拜五从不发号施令,他只做暗示,让鲁滨逊仿效。俩人成为双生兄弟的意义正在于此。正像他们交换衣服与名字一样,他们的灵魂也混合相融、合二为一了。礼拜五因此是通往更高秩序的中介,是鲁滨逊发现的“另一处岛屿”,即“不再是可以带来赢利的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而这“另一个礼拜五”,更使“一个全新的鲁滨逊在旧有的躯壳里挣扎,并预先接受了让治理有序的岛屿毁灭的命运”,从此,“他跟随着一个不负责任的启蒙者,走上一条未知的路”。(Tournier,1972:189)
三、鲁滨逊
在斯坦利·戴蒙德发表于1974年的人类学杰作《寻找原始人》中,作者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要到原始人那里去寻找没有异化的人类生存,指出摆在文明人面前的任务是向原始人学习。图尼埃用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先于戴蒙德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礼拜五》发表于1971年)。在他的笔下,鲁滨逊身上的“文明的痕迹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环境中消失殆尽,裸露出人的存在和生命的真谛,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块白板上经过尝试、探索逐步建立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礼拜五既是新人的助产士,又是他们的向导”。(Tournier,1977:229)那么,鲁滨逊是如何在礼拜五的帮助下,摆脱可怕的孤独,一步步参透人生的真谛,完成向“新人”的转变的呢?
孤独的英雄 首先,鲁滨逊是作为孤独的人物来表现的。他被抛到一个荒岛上,成了人类的孤儿,无时无刻不在与失望、与发狂和自杀的诱惑进行斗争。今天的人们能够在他身上找到共鸣,因为“不断增长的孤独是当代人最险恶的伤口”。(Tournier,1977:221)精神失常、吸毒与自杀在城市居民里的肆虐,表明了孤独对于那些最为脆弱的人群所意味的灾难。
孤独可以预先否定一个人的所有努力,让他的所作所为都显得是一种徒劳,因为“他的每个动作,他的每项工作都是对别人发出的召唤,却总是得不到回应”。于是经过长时间的辛苦劳动完成一项工程以后,孤独的人都会感到空虚、衰竭,轻易地沦为怀疑与失望的利爪下的猎物:“耕作是徒劳的,畜养是荒谬的,储存是有悖常理的……防御工事、《宪章》、《刑法》又有什么意义?要养活谁,要保护谁呢?”(Tournier,1972:124)
然而鲁滨逊“不只是孤独的牺牲品,他还是战胜孤独的英雄”。(Tournier,1977:225)他最终驯服了它,甚至把它提升为生活的艺术,在当代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威信——我们都有过远离尘嚣、遁入世外桃源(小岛)的梦想。对于许多人来说,度假的魅力与金黄的沙滩、婆娑的棕榈、滔滔的海浪密不可分,鲁滨逊则拥有这一切,他满足了现代人对闲适生活的种种想象:修修补补、侍弄花草、饲养一些宠物……试图在鲁滨逊身上找到认同的现代人于是获得了安慰:像所有伟大的神话一样,鲁滨逊的神话有助于“捍卫个人在社会中的某种难以适应”。面对一个“令人窒息的机构”,(Tournier,1981:31)它能够帮助我们坚守可贵的自由。的确,图尼埃笔下的鲁滨逊,在经历了二十八年的孤独生活、外援终于来临的时候,却拒绝离开孤岛、重返文明社会,正可以与浮士德、唐璜等人引为同路,他们都是打破秩序的叛逆,以各自的方式向社会说了“不”:鲁滨逊的自甘孤独、堂吉诃德的荒唐幻想、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唐璜不可抑制的欲望……他们之所以成为“神话人物”,就在于他们“既是与我们一模一样的兄弟,又是与奥林匹斯山众神平起平坐的超人的偶像”。(Tournier,1977:226)
当然,鲁滨逊成长为英雄之前,是一个18世纪的英国清教徒。
英国清教徒 在《礼拜五》的开头,鲁滨逊的肖像借由船长的眼睛绘制出来:短发、红褐色的胡子,衣着朴素,“眼神清澈,有种说不出的坚定与自制”。船长用三个词概括了鲁滨逊:“虔诚、节俭、克己。”(Tournier,1972:8)
首先,关于虔诚。笛福的鲁滨逊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为我所用”,他多次提到自己流落到荒岛之前的“罪恶生活”,“在危难中间不知道畏惧上帝,遇救的时候也不知道感谢上帝”,“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个上帝,有个造物……”(笛福:81)只是落难到荒岛以后,为了抵制孤独、维持理智,他才想起了上帝、想起了《圣经》。他所信奉的加尔文主义主张每个教徒通过忏悔和自省直接与上帝交流,并要在日常事物中找出精神启迪。这样,个人就成为独立的信仰单位,为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久而久之,个人向上帝负责变成了个人向自己负责,而祈祷就变成一种思考形式或精神寄托。这种自省和祈祷不但贯穿了鲁滨逊的全部岛上生活,而且成为他自我检讨和寻求鼓励的主要方式。马克思因此敏锐地指出:“我们不必对鲁滨逊的宗教信仰认真,因为他只是从中获取乐趣,他把那些祈祷看作他的一种创作活动。”(Marx:88)
相反,图尼埃的鲁滨逊在上岛之前是一个虔诚的贵格派教徒,在岛上经历的心智的锻炼却使他逐渐放下《圣经》,背离了基督教义,返回到一种对自然本原的信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刚刚上岛的时候,图尼埃的鲁滨逊比他的原型更有把一切秩序化的严肃和激情。他甚至给小岛制定了《宪章》,配备了《刑法》。他在宪章中参照的权威正是贵格派的创立者福克斯。此后,岛上的生活便按照宗教的习俗确定了节奏:周五实行斋戒,周日停止工作,“上午十时,在教堂齐集、默诵圣书经文”。
其次,关于节俭与勤劳。图尼埃的鲁滨逊也有功利的一面,因为他的另一位精神导师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于1706年的这个波士顿清教徒是印刷商与记者,尤以避雷针的发明而闻名。在他写于1748年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我们看到他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总之,美德品行都是出于利益的需要。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即尽可能多地挣钱与积蓄,深刻地影响了鲁滨逊。“所有的消费都是毁灭,都是恶。”鲁滨逊禁止自己吃掉第一次收获的粮食时这样想道。他把烂熟于心的富兰克林《年鉴》中的箴言写到岩壁上,如“时间不可浪费,这是生命得以形成的经纬”、“贫穷叫人道德沦丧”、“举债是首恶”等等。
图尼埃的鲁滨逊因此不容许自己虚掷时光,他拼命工作,不断增加粮食的贮藏,完全不像笛福笔下的那个根据需要而调整种植规模的“前辈”:“我可以生产整船的谷物,可是我用不着它,因此我只种的够吃就行了。”(笛福:119)他对工作的这种痴狂根植于加尔文主义。新教伦理强调通过工作与生产获取救赎,认为工作具有一种宗教的意义,是使人免于堕落的途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
很自然,几乎各个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都充满这样的观念:为了信仰而劳动,就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报酬很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在这方面新教的禁欲主义并没有加进任何新东西。但是它不仅最有力地深化了这一思想,而且还创造出了唯一对它的效果有决定性的力量,即一种心理上的认可: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结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韦伯:140)
我们看到,图尼埃无意像笛福那样讴歌鲁滨逊的勤奋与坚毅,通过他对岛上环境的改造而颂扬劳动、颂扬人对自然的斗争,进而形象地反映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气概。在图尼埃的笔下,鲁滨逊的辛苦劳作主要是受到新教“劳动天职观”的影响,是获得灵魂救赎与上帝恩宠的手段。
第三,关于克己(纯洁)③。
图尼埃借船长之口,启发了我们对鲁滨逊的“克己”应该抱有的戒心:“你要提防克己,这是灵魂的腐蚀剂。”鲁滨逊的清教(禁欲)主义最极端地表达了“反人性的矫正”,上面嫁接着“充当了社会伦理的仇视肉体的偏执”。(Tournier,1977:223)图尼埃在自传《圣灵风》中否定了这种反自然的态度,指出它正是鲁滨逊屡次受挫的原由,例如他在制作面包的时候,面团的松软让他联想到淫荡的肉体,于是他退却了:为了保持纯洁,维持“人性的高度”,他用自订的刑法惩戒自己。他要把“道德的秩序”强加给被他看作混乱的自然,他要把一切秩序化。对秩序的推崇发展成癫狂:他先自视为总督,既而当上国王,最后把自己等同于造物主。
他的种族主义情绪的来源之一,也正是这种让他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自然的危险的“纯洁”观。他在日记中写到:“这家伙(指礼拜五)的血远非纯净,他身上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个杂种!黑鬼与印第安人的杂种!”在他看来,这种混血黑人是“最低等的人类”。况且,礼拜五看上去只有十五岁,还未成年,这更增添了鲁滨逊的轻蔑,因为对他来说,“一个野蛮人(尤其是一个野蛮的孩子)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新生的人 图尼埃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分为三个时期,除了后两个阶段(“未有礼拜五之前”和“与礼拜五共处”的阶段)与笛福的原作重合之外,他还加进另一个阶段——烂泥塘阶段,它位于最前面,使整个故事的脉络更为合理。因为按照逻辑,鲁滨逊先是希望有人会发现自己(于是竖立一些标记,吸引过往船只的注意),接着动手打造了一条小船;等到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以后,他经历了一个绝望、颓唐的时期——躲避到了烂泥塘里。泥塘是混沌的象征,意味着鲁滨逊回到了造物之初,他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类似于大地上诞生的第一人,也要经历人类进化的各个时期。情绪最沮丧的时期过去以后,他振作起来,重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开始在岛上开垦建设,使荒凉的小岛俨然成了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这是小岛被秩序化的时期。最后,随着礼拜五的到来,“崇拜土地的鲁滨逊”转变为“崇拜太阳的鲁滨逊”。正像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鲁滨逊转变的三个阶段,是与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表述的三个认知阶段——感觉与情绪、科学与技术、在直觉中感知真理——相对应的。(Tournier,1977:235)
鲁滨逊的再生也可以看作一个“炼金”的过程,在经历了“四行”④的洗礼以后,在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崩溃做过殊死的搏斗以后,他才最终达到了可以直面死亡、领悟宇宙真谛的境界。
首先是水。海难虽未使鲁滨逊丧命,却把他抛掷到荒岛,情绪绝望中他沉溺于泥塘,让流质的淤泥围裹自己,让沼泽里蒸腾的浊气麻醉自己。幻象破灭后,他开始接受并进而改造所处的现实,由此迈入第二阶段,即“土质时期”。他辛勤劳作,重拾人类社会的一切技艺,把岛上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然而精神的孤寂还是使他躲进洞穴深处,好似又回到母腹寻求庇护。意识到这种方式隐含的乱伦危险后,他惊惶失措,幸而礼拜五适时出现,充当了使他摆脱“泥土之根”的启蒙者。“化蝶的蛹”寓意鲁滨逊努力挣脱地面飞向天空,“在泥土与空气之间,他就像落在石头上的蝴蝶,挣扎着要完成从土向风的转变”。这是因为人的灵魂有着顽固的“向地性”,总想在大地上找到死亡的宁静,而“飞翔能够战胜那些乱坟冈迷人的召唤”。鲁滨逊的身上继续发生着变化,他开始“每天一早总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等待日出”,他棕红的头发象征着火焰,“像是指向天空的熊熊烈火”,他自己则“好像浸在太阳火焰中的一把利刃”。经过火中的涅槃,他获得了永恒的太阳之子的尊严:“迸发的第一缕阳光落到我红褐色的头发上,好像父亲监护与祝福的手。”这“太阳骑士”般的授勋仪式表明了鲁滨逊的新生。炼金的过程在小说的最末完美地结束了:“黄褐色的阳光给他罩上一层永不变质的甲胄,为他铸造了一副完美的金属面罩,他的眼睛像两颗金刚石,在上面熠熠闪光。”鲁滨逊达到了双性同体所代表的神的境界:“如果一定要用人类的语言表达这种与太阳的交配,那么把我定义为雌性,就像天的配偶大概是合适的……事实上,就礼拜五和我已达到的最高层次而言,性别的差异已被超越了。”(Tournier,1972:230)鲁滨逊最终体现的“新人”具有传说中的双性同体的完美、神一般的完美。
对性别差异的超越强调了鲁滨逊对人类状况极限的突破。他获得了双性同体的力量,时间停滞并可以倒流,他“年轻了一代”,由礼拜五的父亲转变为兄弟,还得到了永生:“他决不脱离这个永恒的现在,在那完美至极的尖端上保持着平衡的现在……”当他幻想着把身体“改造成一只巨大的手,五个手指分别是头、手与腿”时,他找回了柏拉图笔下球形阴阳人(双性同体)的体力。他在最后几篇“航海日志”中进行的思考,表明他已经达到了斯宾诺沙在《伦理学》中提到的最高层次的智识,即“纯艺术或宗教的精神活动”。
今天看来,笛福作品中的鲁滨逊与荒岛、鲁滨逊与礼拜五的关系反映了作家因为囿于时代和阶级地位而不无局限的价值观、世界观:颂扬人对自然的斗争、将殖民主义合法化,等等。作为对原作的一次重要改写,图尼埃的《礼拜五》突破了这些局限,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公正对待落后民族等20世纪先进的理念融入其中,实现了对原作的超越。
在礼拜五这个启蒙者的指引下,鲁滨逊摆脱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负累,不再以种族主义者的眼光自封为主人、教父、开化的英国人,而是把礼拜五看作自己的双生兄弟;他也根除了殖民主义者的恶习,不再以征服、统治的面目出现,而是像礼拜五那样真正地融入自然,使荒岛对他的敌意乃至威胁荡然无存。最后,和谐的新式“三角关系”使鲁滨逊拒绝返回人类社会,心甘情愿地在岛上“享受”孤独。
图尼埃在谈及《礼拜五》时曾经说过:“我的这部小说真正的主题……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和融合……丹尼尔·笛福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鲁滨逊才有文明可言,在这一点上他对礼拜五是不屑一顾的。”(Tournier,1977:229)至于让鲁滨逊向礼拜五学习,这在笛福的时代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20世纪的上半叶,图尼埃的法国同胞、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仍从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出发,把原始人看成是没有能力区分主客体、没有逻辑或前逻辑的神秘思维者。(Lévy-Bruhl:7)而在一系列标志着转向的人类学的主要著作,如前面提到的戴蒙德所著《寻找原始人》,问世之前,图尼埃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创作意图:借原始文化为镜,以原始人为尊贵和理想,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这的确显得难能可贵。
注释:
①1942至1946年,图尼埃在巴黎索邦大学主修哲学,师从加斯东·巴什拉,并加入一个青年哲学社团,其成员有日后成为法国哲学界翘楚的德勒兹、福柯、夏特莱等人。1948至1949年,图尼埃到人类博物馆旁听人种学课程,后来在自己的散文集《吸血蝠的飞翔》中,回忆了列维-斯特劳斯对自己写作生涯的重要影响。
②《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一书引文皆出同一版本,见参考文献。为避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
③原文使用的是“pur”一词,该词做形容词用,意思为“纯洁的、纯正的”;做名词时则指人,意思是“笃信者”,具体地说,指那些“对一切抱有正统观念、为了原则不惜任何代价的人”。
④西方古代哲学家认为土、水、风、火是组成宇宙一切物体的四个本原,称为“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