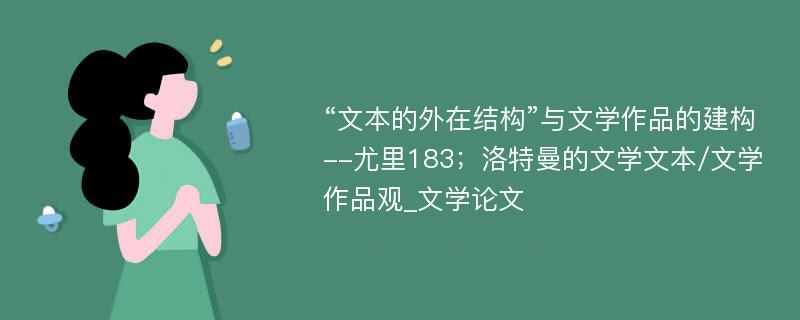
“文本外结构”与文学作品的建构——尤里#183;洛特曼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尤里论文,文学作品论文,文本论文,洛特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作品与文学文本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不再认为作品等于文本,我们自然会追问:作品大于文本?作品小于文本?
我们比较熟悉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本观与作品观,也比较熟悉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与作品理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巴尔特、伊瑟尔的同时代人——前苏联学者尤里·洛特曼在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上也是很有开拓而卓有建树的。
以研究“艺术文本的结构”饮誉世界的前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曾明确提出:“应当断然拒绝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文本和艺术作品是同一个东西。文本乃是艺术作品的元素之一,诚然,这是极其重要的元素,没有它,艺术作品的存在乃是不可能的。但是,艺术效果整体上乃是在文本同复杂的一套生活观念和思想美学观念的对比中产生的。”①通俗些说,洛特曼主张作品大于文本。文本是作品的基石。那么,在洛特曼看来,文本又是什么呢?从20世纪60年代发表《结构诗学讲义》到1993年去世,文本问题一直是洛特曼理论探索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诚然,洛特曼的文本观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洛特曼早期的文本观侧重于意义的生成机制,艺术文本被视为“以特别方式而被构造的机制,这种机制具有涵纳绝对高度浓缩的信息的能力”②,据此,洛特曼强调文本完整的符号性,或强调文本在某种文化语境中其功能的整体性;洛特曼后期的文本观则侧重于这种机制的多语言多层面多向度的文化功能,“文本不再被理解为有着稳定特征的某种静止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③。
质言之,文本是一个结构乃是洛特曼始终不渝地加以恪守的一个理念。在洛特曼看来,文本指的是“获得语言表达的结构关系的总和”④,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表达性,即文本表现出来的现实方面:文本是由一定的符号铭录刻写下来的,而与非文本结构相对立;其二、界限性,即文本的相对完整性:文本具有区别于非文本的特征;其三,结构性,即文本各要素的相关性:文本是处于不同层次的符号子系统组合而成的结构整体⑤。
正是从作为结构的文本这一基点出发,洛特曼执着地考察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分析艺术文本内各层级结构的意义生成机制,阐释艺术文本外各序列结构的意义建构功能。
“文本结构”不难理解,“文本外结构”则需要作一番阐释。
艺术文本的结构是开放性的,“它与种种不同的关系系统发生联系:作家、流派的风格系统、民族、时代、社会、文化的关系系统。在这种复杂的关系系统中,艺术文本的每个细节和整篇文本都同时纳入不同的关系系统中,获得一个以上的意义”。单义的科学文本以及其它按多语义原则构造的文本(例如教会的和秘密团体的文本),“在不同的结构—语义层次上为表现不同的内容服务,对程度不同的读者揭示不同的真理,当对读者揭示了一个新的语义层,旧的语义层就不再蕴涵真理”⑥,艺术文本则不然。文本与文本外的关联是作品的多重涵义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是艺术作品的意义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洛特曼甚至提出与文本内结构对应的“文本外结构说”⑦。早在1964年的《结构诗学讲义》中,洛特曼就单辟一章专门讨论“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他指出:“文本外结构作为一定层次的结构要素构成艺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⑧在1970年的《艺术文本的结构》中,我们可以读到:
……艺术文本必须被列入更为复杂的文本外构造中,同时与之构成成对的对立……文本外结构可以改变自身某些要素的概率,这取决于它们是否被列入“说者的结构”——作者的结构或者“听者的结构”——读者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在艺术中该问题复杂性所引致的全部结果。⑨
这些表述比较晦涩。荷兰学者杜沃·佛克马对之作过解说:文学文本至少是两个互相重叠的系统的产物,语言系统是其中的基础。因此洛特曼得出结论说,文学以及一般艺术是“派生模拟系统”。文学系统是超语言的。语言信息的接受者必须懂得语言代码,以便解释信息。据此,文学文本的读者除了懂得文本赖以写成的语言之外,还必须懂得文学代码。如果接受者不懂得发送者所使用的文学代码,他一般不能理解文本,甚至认为那根本不是文学。由此,洛特曼断言:“如果没有对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关系补充归类,艺术文本的定义就不完全。”⑩
质言之,文学文本的内部规则与该文本所属的“文化代码”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具有“自律性”的文本结构,与具有“他律性”的文本外结构,在互动共生中建构文学作品。
通俗地说,“文学作品以文本形态奉献给读者,而现实生活、文学传统、历史文化背景、观念等等则属于非文本(文本外)体系。非文本(文本外)体系包括赋予文本以含义的、历史形成的艺术代码的总和”,“非文本(文本外)体系作为一定层次的结构进入艺术作品之中。因而,从艺术作品是文本与非文本(文本外)统一体的角度认识艺术,便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文本外结构所提供的背景材料对于批评家则更为重要。”(11)
米哈伊尔·洛特曼在阐释其父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时,也强调文本与文本外结构的关联:“文本结构又像有机体的结构。文本是有生命的,生命在自己的环境中是存在的,文本也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文本离开了文化,就停止了生命,它还可以存在但要停止发展。文本是同文化一起发展的……文本本身就要求有一个环境保障它的生存,这就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可定义为文本组成的系统,是不同文本构成的。我们自身也是一些文本,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可称是文本。”(12)强调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关联与互动是艺术文本固有的机制,是文学作品固有的机制,这是以尤里·洛特曼为领袖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学派的结构主义文论的一大创见,或者说,是前苏联结构主义文论的一大特色。
洛特曼以这一理论实现了同西方学界与本土学界的双重对话:“这种结构观既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的封闭的艺术结构观,他们人为地割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热衷于凌驾一切之上的抽象结构,也不同于苏联文艺学中忽视艺术本身特点的那种传统模式。”(13)20世纪60年代在塔尔图大学启程的这种对话,可以说是双锋双刃的,既是针对苏联本土仍居主流的社会学文论范式的一种“突围”,也是针对正如日中天的西欧结构主义文论范式的一种超越。
谙熟尤里·洛特曼著作的意大利符号学家翁伯特·埃科早就指出,“尤里·洛特曼在探讨文本理论这一问题时,超越了结构主义的教条,展示出更为复杂同时也更加清晰的视界。在突破结构主义者将代码与讯息两项对立的偏执之后,洛特曼将对文本的研究与对语法的考察区分开来。”(14)而佛克马在20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尤里·洛特曼的研究方法好在运用同一符号学的方法,既分析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又分析文本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外部关系。如果这一方法使我们能够填平文学的接受研究以及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同新批评的自主解释以及内在解释之间的鸿沟,并且把这些高度歧义的方法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那么洛特曼的书将在文学研究中的确带来一场哥白尼革命。”(15)佛克马的这一番话带有几许期待口吻。这位荷兰学者作出如此断语时,正值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文本理论探索正在展开之中。应该说,佛克马对洛特曼文学理论探索的这一取向的把握是准确的。今天,洛特曼理论已成遗产。我们可以认为,洛特曼运用“文本与外文本”的范畴,以艺术文本为中心来考量艺术文本在其中生成又在其中发挥功能的文本语境,就文学研究而言,“既跳出了内部研究窠臼,又避免了外部研究的缺憾,成功地将艺术的内部机制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为填平文艺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鸿沟,迈出了坚实一步”(16)。
从审美活动的学理上来看,艺术文本的结构化与功能化过程,文学作品的建构过程,确实就是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的互动共生过程。
文本与文本外关联,不仅是文学文本得以功能化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学文本的非艺术功能得以产生的基本缘由。洛特曼指出:“正是基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将审美模式与伦理的、哲学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诸多模式联系起来的努力,才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人类文化史上,将特殊的艺术信息重新编码为非艺术模式系统的行为也就不断发生,尽管这样必然会失去许多只有艺术本身才包含着的信息,甚至遭到抗议(常常是辩解)。”(17)不难看出,这里已经涉及艺术文本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功能的复杂机制,或者说,艺术文本在被接受过程中被建构成艺术作品的复杂机制。
艺术文本是联结发送者和接受者的纽带,“经常存在着两种语言、两套代码:作者的与读者的。接受者不仅要借助他自己所掌握语言去译解信息,还要确定发送者将文本编码的‘语言’。由于作者的语言和读者的语言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等级结构,这就使得文本的信息量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系数。面对同一艺术文本,随着读者语言的不同,或对作者语言的不同把握,从中所获取的信息量以及信息给人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围绕着艺术文本的信息这个中心,读者与作者会形成四种关系:作者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读者功利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作者和读者都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作者和读者都实用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读者审美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作者功利性地对待艺术文本信息。”(18)
在这四种情形中,第一与第四都在表明同一艺术文本信息在作者与读者那里引起了立场上的不同,或者说,由于作者的编码语言与读者的解码语言之不同,同一艺术文本的功能在作者与读者那里发生了错位。洛特曼也正是从作者的编码语言与读者的解码语言的互动关系出发,立足于艺术文本结构的分析,进入艺术文本类型的考察,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理论,即建立在“同一美学”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与建立在“对立美学”基础上的文学作品。
我国另一位洛特曼符号学文论专家、北京大学孙静云教授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9):
第一类作品是吸取同一美学精华构建的作品。这类作品的艺术现象与结构是程式化的,读者的作用在于验证全部结构是否与自己的经验相符。民间口头创作、中世纪艺术和古典主义作品等均属此类。评价这类作品主要看其是否遵循一定的艺术原则(如修辞规范、构成隐喻的法则、叙述方式以及读者所熟悉的各种情节组合模式等)而创作。违反读者经验中的艺术原则者,则被认为不够水平。这类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同读者所熟悉的模式化“规则”体系完全能一致。这种传统的模式化规则在对艺术作品的认识上(更广泛地说,在传送信息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类文艺作品是以对应(立)美学原则为基础构建的。这类作品的代码是读者经验中不曾有过的。艺术现象在作者笔下不是简化而是复杂化。这种复杂化不是表面上的“装饰化”,也不是“细节化”,而是作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替读者所熟悉的模拟生活的方式……如果把这第二类作品比作数学游戏的话,那么,它不是“没有规则的”游戏,而是在游戏过程中制订规则的游戏……对应(立)美学文学现象的特点是,对刻板结构的破坏在读者意识中已成为下意识的习惯,同时,这种已被破坏的刻板结构在艺术文本中没有任何表现。
应该看到,对艺术文本类型的这一区分本身,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首先是同当时前苏联主流文论模式的对话。洛特曼指出:“将各种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划分为同一美学和对立美学两大类,其概括的深度与广度要超过用‘艺术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对各种艺术现象所做的区分。”(20)也应该看到,对艺术文本类型的这一区分也是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潜对话:“由于引进了‘同一美学’这一概念,洛特曼实际上颠倒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立场。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可以是跟规范一致,而不必是偏离规范。‘同一美学’只能在需要(或‘据说需要’)向心力和聚焦作用的某种文化而不是在具有离心力和个性化倾向的现代艺术中占支配地位。”(21)
还应看到,洛特曼的文学文本理论更是同西欧结构主义文论的对话,是同索绪尔、雅各布森的对话。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洛特曼,在其“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问题”的演讲中(22),梳理了其父尤里·洛特曼的文本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语境。按照米哈伊尔·洛特曼的理解,如何获得文本的本质上,“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理解与其他学派有原则的差别,其原因在于对交际的性质认识不一样”。索绪尔宣称语言体系决定言语的应用,塔尔图学派则强调言语影响和改造语言,语言要在交际中发展。另外,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的述行性,在此意义上,“文本就是交往行为,就是交往关系”。如上所述,“文本实现交往、选择听者、改变符码,再进一步说,文本会改变作者”。文学史上常有文本摆脱作者控制的情形出现。
由此可见,与此前学派的看法不同,塔尔图学派认为文本占据中心地位,文本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譬如,法国符号学派的中心议题是话语及其生成的考察,“占据中心地位的不是文本(text),而是话语(discourse)。巴尔特、福柯提出话语理论,也认为话语并不服从语言体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介乎词与物之间的空间,在词、物、思想三者之中的空间,这里能产生思想、观念等等。但若比较文本与话语,文本有开头与结尾,话语却没有,文本有作者,话语却是不带人称的。于是,巴尔特与福柯说,作者死了。那什么还活着呢?福柯说只剩下了没有人称的空间——话语”。塔尔图学派则认为文本是事件,就是自觉的负责的行为,评价文本要看它的后果。话语却像是交际的生理活动,不带有信息性质。因此,塔尔图学派认为,研究文本需要考虑它提供了什么新信息、新思想,对文化、对语言有何贡献。
塔尔图学派不仅将文本置于中心地位,而且特别重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本与文本之间是有联系的,即文本间性。“文本间相互发生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文本与文本直接发生联系,一种是在阐释过程中出现文本间联系。一个文本可以成为另一个文本的潜台词、潜在含义。离开这个潜台词的文本,我们无法理解原来那个文本。潜台词文本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形式是引证其他文本。巴赫金说过,任何话语无不是引文,此说可以讨论,不过‘他人话语’的确很重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就运用了许多潜在的引语。科学语言如此,文学文本尤其如此。如果潜台词是整个语境,但没有明确指出引自何处,情形就十分复杂了。上面说过,整个文化可以视为文本组成的系统,现在又可说文化是文本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文本与文本互相包容,影响后面的文本,形成不断的运动”(23)。
可见,洛特曼的文本理论是在与本土学界与国外学界之多向度的对话中形成的。
正是在这种多向度对话中,洛特曼的文本理论在结构主义时代超越了结构主义,在继承雅各布森诗学理论的过程中发展了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从而成为后索绪尔时代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一种符号学文论。
也正是在这种多向度对话中,洛特曼实现了其文本研究的拓展——由诗歌文本—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化文本的拓展,实现了其研究视域的拓展——由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的拓展,实现了其文本理论的拓展——由早期的意义型、单语性文本观向后期的功能型、多语性文本观的拓展,实现了其文本运用领域的拓展——由文学文本—艺术文本—历史文本—乃至包括仪式文本、行为文本在内的文化文本。
洛特曼认为,“作为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艺术作品,乃是无限的世界的模型”,“每一个单个的文本既是在模拟某一部分客体,同时又是在模拟包罗万象的宇宙客体。”(24)艺术文本这一能量无限的模拟机制,引导着洛特曼把一切都视为文本。洛特曼这种不断拓展文本研究疆域的追求,这种将一切文本化的追求,不能不令人想起那个宣称“文本之外无他物”,鼓吹“解构论”的德里达。
那么,前苏联学者尤里·洛特曼的文本理论与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的文本理论之间有契合相通吗?有差异分野吗?
对洛特曼符号学文论颇有专攻并已撰有专著的我国青年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澄认为:“洛特曼的文本理论彻底打破了意义的终结性和一次性。在这一点上,它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在精神上是契合的。”(25)康澄也看出,尽管洛特曼与德里达都否认了文本具有终极意义,但两人的文本理论又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为:“首先,与德里达忽略文本的内在结构与深层结构不同,洛特曼不仅肯定了文本拥有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而且他认为正是这种复杂的内在结构保证了文本具有与人脑相类似的功能;其次,洛特曼对于原文本极为尊重。他否定文本带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但认为文本如同‘黑匣子’,是意义的发生器。一切变化都源于文本,它是传递、保存和产生意义的智能中枢。”
洛特曼否定文本的固定意义,是因为他认为:“意义产生于异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解读文本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是翻译活动。将用‘他人的’语言写成的文本翻译成用‘自己的’语言写的文本,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各类型的文本本质上存在着不可翻译性,才产生了新的文化意义。‘交际过程是翻译行为,是变化的行为。文本不仅使语言、信息发出者发生变化,而且在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确立联系,使信息接受者也发生变化。进而,文本本身也发生变化,且不再等于它自身了’。不可翻译的翻译使文本的变化具有不可预见的性质。”
正因为“洛特曼认为文本意义的产生基础是翻译,而德里达则提出阅读文本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动’”,所以“洛特曼在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原则的同时,其研究方法出现了许多解构主义特征,但又从根本上有别于后者。洛特曼的文本理论既反对意义的终极性、确定性,又积极探索意义的产生机制;既是动态、多样的,又是求实、科学的”(26)。
诚然,对苏联学者尤里·洛特曼的文本理论与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的文本理论之间的差异,还可以往深处开掘。是不是还可以追问:德里达与洛特曼在文本理论上还有哪些“相通之处”?这两人异曲同工的“大文本理念”,或者“泛文本化”思想,何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那同一个年代里不约而同地应运而生?这是不是与它们同属于后索绪尔时代的产物,他们同生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但又勇于超越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的精神追求颇有关联呢?
若将洛特曼的文本理论视为一个文本,那么,这一文本理论之被传播被解读被接受被运用的过程,它的跨文化的旅行过程,就是一个生动有趣的“理论旅行”的文本。检阅洛特曼文本理论的跨文化之旅,梳理理论旅行的这一文本的建构过程,也是不无意义的。
洛特曼以其结构符号学的文本理论,早就赢得国际学界普遍关注。可以说,这是前苏联文论界最早(甚至早于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位进入超越国别超越民族疆界之跨文化“理论旅行”之征途、最早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的重要理论。《结构诗学讲义》1964年在塔尔图大学以《符号系统论丛》第一辑问世,美国布朗大学于1968年就重印了这部书;1970年在莫斯科问世的《艺术文本的结构》,1972年在慕尼黑便有了德译本。佛克马当年写《20世纪文学理论》时就参考了洛特曼著作的德译本。1971年,第一部俄德双语版“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论著文选”——《苏联结构主义文学学文本》(Textedes sowjetischen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n Styukturalismus)在慕尼黑面世。中国学者1988年介绍尤里·洛特曼文论时推出的一个专辑《外国文学报道》,竟是从德国人编的这个《苏联结构主义文学学文本》(中译为《苏联结构主义文艺学文集》)文选中选译了尤里·洛特曼的3篇论文。德国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编出两部“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符号学著述的书目(1974,1977),而这是苏联本土学者当时都不敢梦想的;1986年,在亚堔还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符号学文选(1962-1973)》。在德国,有一位学者多年密切跟踪尤里·洛特曼的理论探索。他就是卡尔·艾梅马歇尔,德国鲁尔大学教授斯拉夫学学者,后来出任以尤里·洛特曼冠名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化研究所”所长。卡尔·艾梅马歇尔的长篇文章《苏联文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发展、特点和问题》(1971)对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理论作了即时的评述。这位德国学者撰有《尤里·洛特曼学术活动的方法论层面(五十—六十年代)》(1972)、《尤里·洛特曼:整合性文化学的符号学变体》(1974)这样颇见深度的专论。
几乎与佛克马将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写进其《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77)同时,在英国,安·舒克曼写出一部《文学与符号学——尤里·洛特曼的著作之研究》(27)。1984年,在美国,Jonaid-Sharif Lutfurahman写出《文本·符号·结构——尤里·洛特曼的诗学》。2003年,韩国学者金苏匡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尤里·洛特曼的创作演变的主要方面》(28)。洛特曼的文学理论建树早已进入当代文论大家的视野,雅各布森当年曾鼎力支持尤里·洛特曼创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埃科曾为尤里·洛特曼著作的英译本作序(29);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1983,1996)(30)中以“塔尔图学派的主要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的研究工作”为例证,来阐述符号学分析在文学研究进程中的历史贡献。洛特曼的力作《艺术文本的结构》、《诗歌文本分析》早已被译成德、法、英、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韩国等多种文字。洛特曼之文学作品建构于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互动共生的“内外互生”理论,与埃科之“开放的艺术作品”理论,与伊瑟尔之“具有召唤结构的文学文本”、“具有艺术极与审美极的文学作品”理论,与巴尔特之“由作品走向文本”、“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理论,与克里斯蒂瓦的“现象文本”与“基因文本”、“具有生产性的文本”理论一样,共同参与了当代国外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理论的革新,当代“文学”概念的更新与当代文学研究视界的刷新。
注释:
①尤里·洛特曼:《诗歌文本分析》,列宁格勒:教育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
②尤里·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0年,第360页。
③尤里·洛特曼:《符号圈》,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④尤里·洛特曼:《诗歌文本分析》,第43页。
⑤尤里·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第67-69页。
⑥施用勤:《文艺结构符号的探索者》,《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1期。
⑦原文是внетектовые структуры。学界此前译为:非文本结构,外文本结构,超文本结构,笔者以为均欠妥帖。
⑧尤里·洛特曼:《结构诗学讲义》,普罗维德斯:布朗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64页。
⑨尤里·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0年,第65-67页;此处采用彭甄博士提供的未刊译稿,个别地方据俄文原著作了改动;彭甄译自俄文的《艺术文本的结构》,已列入中译《洛特曼文集》。
⑩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48-49页。
(11)孙静云:《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思想》,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12)米哈伊尔·洛特曼:《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13)施用勤:《文艺结构符号的探索者》,《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1期。
(14)翁伯特·埃科:《为尤里·洛特曼的〈思维的宇宙〉所作的序文》,尤里·洛特曼:《思维的宇宙》,莫斯科:俄罗斯语言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410-411页。
(15)佛马克、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第50页。
(16)王坤:《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思想》,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17)Juri Lotma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7,p.68.
(18)参见王坤:《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思想》,《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第271页。
(19)孙静云:《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第262-263页。
(20)Juri Lotman,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p.292.
(21)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第53页。
(22)2005年5月30日-6月1日,塔尔图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洛特曼应邀来北京出席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全国洛特曼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问题”主题报告,阐述了著名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这篇演讲稿的中译文发表时被易名为《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
(23)参见米哈伊尔·洛特曼:《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第11-13页。
(24)尤里·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第204、205页。
(25)康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文本》,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第123页。
(26)参见康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文本》,王立业主编:《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第124页。
(27)Ann Shukman,Literature and Semiotics-A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Yu.M.Lotman,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7.
(28)Kим Cy Kвa:《尤里·洛特曼创作演变的基本层面》,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03年。
(29)Yori M.Lotman,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Introduction by Umberto Eco,London & New York:Tauris Publishers,1990,p.306.
(30)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