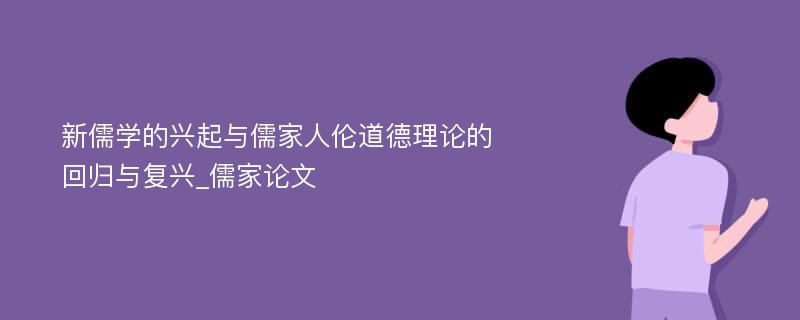
理学的兴起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与振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伦论文,理学论文,学说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儒学自汉代以后由单纯的官方意识形态文化转向意识形态文化和理念形态文化双重起效的新阶段。自此以后,儒学不仅保持了它独尊的意识形态地位(实质上是保持了封建政治思想统治地位),而且也恢复和再现了它的理念形态文化的魅力。如果说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或者说是新儒学,突出而集中的表现即在于实现上述二者的结合。正是这二者的结合和双重起效,儒学最终在古代社会得以稳定和延续近千年,再没有出现以往历史上的反复,由此佛、道永远被排除出思想上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儒学的统治直至封建社会的灭亡。
一
追溯历史,儒学在先秦时期原本是一种理念形态的文化,概言之,孔子所创立的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人学即关于如何作人的学说,是探求以人文之理为中心而兼顾自然之理的理论体系。儒家为了使人和人类能够摆脱其直接性和本能性,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立,把个体的人提升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存在,对人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人及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的问题,而且给人在世界上以一个正确定位,凸显了社会发展的“人的目标”,建立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不仅如此,儒学还构建了一个理想人生、理想人格和反省人类完满性缺失的思想体系。另外,儒家还设计和规划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提出了独到的以德治国和“天人合一”的政治和自然的理念。总之,儒家极重视对人的培养,充满了对人类命运关注的人文精神,提供能够满足人和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知识需要和思想的指导,质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要学会作人和作一个具有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似乎离不开儒学设计和指引的人生轨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儒学在创始阶段就显示了它骄人的魅力,在百家并起时代就成为显学。这不是官方和当政者的提倡,恰恰相反,显学的地位是在被官方和当政者的排斥和反对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说明,观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具有独到的学术品性。先秦时期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由于重视人生和人的发展的人文精神,不利于秦王朝极权专制统治,故为秦王朝所不容。由此秦王朝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焚书坑儒”,以暴力为批判武器的焚书与坑儒并施,企图把儒学消灭殆尽。然而“烟销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焚书的烟灰尚未冷却,而反秦的义旗烽起,举义旗者并不是读书人,而是进行农耕劳作的农民,因此,焚儒书和坑儒生并未能挽救秦王朝的灭亡的命运。中国古代历史反复证明,人为的设限和暴力的强制并不能消灭学术,真正有用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无法消灭的。事情的发展正好是这样的。随着秦的灭亡和汉的立国,曾被扼杀的儒学重又勃兴,走上它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时期。
儒学在汉代之勃兴乃是因于历史发展之必然,概言之,主要因于以下三点:(1)秦的历史已证明,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的单纯的暴力统治,不但不能使国永固,而且相反地却加速帝国的灭亡;(2)治国安民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需要一种能取代法家思想的新意识形态,作为先秦颇有魅力而为显学的儒学自然被成为首选;(3)先秦时期的儒学虽是一种关于如何作人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学术,是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但它为汉代缔造和建构成熟的封建意识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思想资源,提供理论上的准备和知识的依托。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原因,使刘汉统治者不能不选择儒学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封建意识形态。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舍此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由于汉代统治者选择儒学乃是为了建构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这就决定了汉代的儒学不可能是先秦的儒学的简单复活和再现,换言之,汉代统治者所需要的决不是属于一般子学即是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而必然是与政治紧密结合而被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儒学。因此,汉初境治者需要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改变其原来与政治相脱离的状态。经过西汉七十余年的酝酿与改造,最后由董仲舒总其成,实现了儒学的政治化,这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作出了理论上的集中概括。
儒学的政治化在理论上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即是儒家思想被法家思想所融铸,或者说以法家思想改造儒学。众所周知,把社会最初确定为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关系是儒家,孔子与齐景公的一次对话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作君的要有作君的样子,作父的要有作父的样子,同样,臣和于亦然。以后到孟子,在孔子的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妇有别”一伦,并把“三伦”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由孔子至孟子,都把“三伦”关系作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所阐述的是彼此之间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的关系。但到了法家韩非时其情形就不一样了,他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顾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者篇》)。把“三伦”确定为封建宗法等级关系的政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对孟子的“三伦”排列次序作了调整,君臣关系提到“三伦”之首,而父子一伦已退居第二,“三伦”实际上已演变为“三纲”。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全盘沿袭了韩非的思想,在理论上正式把“三伦”提升为“三纲”,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是“三纲”之说之由来。董仲舒虽然打着的是儒学的旗帜,实际上所表露的则是法家思想的内容,儒学已政治化。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用阴阳的理论把“三纲”神圣化,把“三纲”论证为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是阳尊阴卑的等级关系,并把等级关系说成是“天之制也”即天的规定。“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君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人间的一切尊卑贵贱都因“阳而序位”,都出于“天”的规定,君和父当阳,所以居尊为贵,臣和子失阳而当阴,所以为贱。一言以蔽之,臣和子应该附庸于君和父,作君父的奴隶。这就是所谓儒家阳尊阴卑之说。由此,儒学揉合阴阳学说,把儒学神圣化了。东汉之际谶纬之学的流行和泛滥,则进一步地把儒学神化了,已演变为类似于神学的儒学。先秦理念形态的儒学经过董仲舒等汉儒的改造,已变为国宪,变为神圣的政治权威原理,成为了国家的法典。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当谏书,几乎无所不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建议,儒学由此成了官方的独尊的意识形态即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随着儒学的政治化,儒学失去了学术上的包容性的品性,学风为之一变,儒生成了政治的附庸,章句之学和传注之学甚为流行,注经和传注代替了学术的自由讨论,学者们只能诵儒经和厮守儒经教条,而不能有丝毫之拟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儒学走到如此神圣的地位,这是当时学者们始料不及的。
儒学成为官方独尊的意识形态,使曾被秦扼杀的儒学变成了汉代的统治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学的命运,儒学与政治的结合,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尽管几千年封建社会历经风浪,屡经推移变化,但儒学作为治国的法典和政治原理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检视历史,从东汉至宋八百余年,虽中经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儒学表面上似乎淡出了政治舞台,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历代统治者总是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把儒学作为治国的政治权威原理,总是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以儒学进行政治运作,以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规划和设计政治,即是在玄学和佛学统治的时期亦是如此。玄学和佛学虽然盛行一时,但它始终未能象儒学那样,成为国家的政治原理和法典,换言之,治国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儒学,历史流传的“儒能治国,佛能治心,道能治身”就十分恰切地说明了上述情形。与其说这表明儒、道、佛在中国思想上的互补性,毋宁说是支配国家政治和思想统治的仍然是儒学。这不仅为宋以前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也为宋以后的历史甚至直至封建社会灭亡历史所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说汉代勃兴的儒学,是被改造了的儒学,并不是先秦的原典儒学,质言之,是与政治紧密相结合而成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或者说已成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的儒学。
二
儒学的政治化,虽改变了它的历史命运,由被压抑而推到了意识形态独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政治的制约作用也使儒学本身带来了发展的危机。在封建专制社会,一旦学术与政治结合,学术势必成为政治的工具,势必成为政治原理,对它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就不可置疑,就不可能象学术一样自由讨论。历史证明,汉代兴起的儒学正是这样的。在封建政治的制约和作用下,政治的魔力蚕食着儒学的学术灵魂,极大的挤压了它的学术空间,由此儒学失去了它学术的品性,失去了它作为知识体系的理念形态儒学的魅力,从而走上了僵化和衰落。根本不能应对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思想理论上不断发出的挑战。具体言之,对以下历史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它无法面对:为什么儒学在魏晋时期受到玄学的排挤而不能自振呢?为什么受佛学的冲击而不能应对佛、道的挑战呢?为什么从唐代始儒生转向尊佛而儒学不能自救呢?如此等等,儒学都无法面对,显得毫无生机和活力。
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要使儒学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克服儒学发展中的危机,囊关键的是重新对儒学注入生机与活力,很显然这不是简单恢复汉代已确立的并已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所能做到的,换言之,要对儒学进行再造与更新,既要继续发挥“儒能治国”的权威效应,尤其要恢复和重光早期儒学“治心”和“治身”的学术效应,振兴其理念形态儒学的魅力,使官方意识形态儒学与理念形态的儒学双重起效,实现“治国”和“治心”的结合,并于前者即“儒能治国”自古已然,无而再认定,然而后者则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儒学本质上是人伦思想为核心的人学,因此,重建理念形态的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以人学为主旨的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和重建,或者说是使以人伦为本位的儒学归位。自不待言,这种似汉代儒学一样的变革,同样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重建儒家人伦道德学说,因为关系儒学发晨本身的重大变革,因此,无论从现实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理论创新的要求,都有必要对以往即对汉以后流传千载的儒学传统重新审视和评判。在这点上,唐代韩愈与李翱因于儒学复兴而开展的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对理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好和他们的思想相合拍,他们之间不仅思路一致,而且从韩李的思想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启示和理论成果。最主要的是韩愈、李翱在下述二个问题上深深地吸引了理学家。其一,韩愈振聋发聩的提出,流传千载的汉唐儒学不是真正的孔孟儒学,“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韩愈全集·文集卷四·送王秀才书》)这就是说,传孔予之圣道惟孟轲一人而已,汉儒自不在其列,因此要发明圣道和接续道统,必须回到先秦儒学原典,从孔孟著作中直取本义;其二、与上述相联系的,因为汉唐儒学不是真正的孔孟儒学,因此,儒学传授谱系也必须重新确立,韩愈独自发明了一个似佛教法统的儒学传授谱系,这就是他一再向学坛和儒者所宣示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全集·文集卷一·原道》)韩愈提出的这个儒学传授谱系是否可靠,是否真的反映了儒学演进过程和承续关系,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否定孟轲之后失去儒学承续传统,乃是为了否定汉、唐的儒学传统,为重新建构新儒学体系和发明所谓圣道提供理论和历史的根据。韩愈本人正是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说:“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并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列入儒学传授的谱系了,即所谓“已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之道也”。(《韩愈全集·文集卷二·重人答张籍子书》)以上韩愈对时逾千载被奉为神圣的独尊的儒学传统的评判,甚为理学家所折服,对韩愈推崇备至,甚至把韩愈与圣人孟子相比肩与并论。尚在理学酝酿时的理学先驱石介便说:“孔子后,道屡空,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认为韩愈是继孟子之后倡明圣道的唯一之人。为此,石介不甚感慨地说:“为贤人而卓”而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尊韩》)。欧阳修也说:“韩氏之文文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所而有之。”(《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三·纪旧本韩文后》)对李翱在复兴儒学的贡献,欧阳修表示了极高的敬意。“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又不得翱时,与翱上下之论也”。类似以上对韩李推尊在宋代多有之,兹不复论。但他们都自认是韩愈道统的继承人。不仅如此,理学家发动的疑经惑古的新风,实际上也源于唐代。唐代中叶出于儒学复兴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打破治学必须专守注疏的著述,舍传求经的新学风随之骤起,其突出表现对《春秋》、《诗》、《礼》、《易》、《论语》予以重新阐发,其中啖助《春秋集传篡例》、陆淳《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辩疑》影响最大。他们一致指出《春秋》三传之失,“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旨,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也。”(啖助:《春秋集传篡例卷一·春秋宗旨议》)唐代儒者开启的疑经惑古之风,正好为理学家破弃热衷于章句训诂的汉儒家法求之而难得的。宋儒在唐代儒者疑经的基础上把打破专守义疏的新的学风推到了高潮。理学家对汉唐儒学批评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批评汉唐儒学囿于传注,应该废弃。儒者“争为注释,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门而入。”(孙复:《孙明复小集卷二·寄范天章书二》)主张将这些不得“尽于圣人之绪”的传注从太学中剔除,不得颁行天下;(2)对汉唐奉行的儒学经典本身提出质疑,对被《史记》所认定而流传达千载的儒经,如《系辞》、《说卦》、《文言》等,欧阳修抱有怀疑,斥之为非圣人所作。另外,对于《毛诗序》、《礼记》、《中庸》及《尚书》的某些经文的论述和说法,也提出了疑问;(3)基于以上认识,理学家几乎都主张对儒家经义重新探寻和阐发,以重建儒学理论系统。理学家在审视汉唐经注和传注的基础上,酝酿和开始了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其开创者首推孙复。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独出新义,被欧阳修推尊“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七孙明复墓志铭》)给予很高的评价。刘敞《七经小传》发义新奇,为学者所关注,吴曾《能改斋漫录》指出:“始异诸儒之说”,认为此说使人耳目一新。对北宋学风上的上述变化,南宋学者陆游曾作出总结和肯定。他指出“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诗》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理学家已从破弃传注,进而已怀疑到儒经本身,再由存疑经学发展为重新阐发儒经本义,一层深入一层,层层演进,揭开了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架势,展开了儒学发展史前所未有的理论工程,迎来了儒学发展的新时代。
三
理学家建构儒学体系虽只笼统地谈到要以《孟子》为本,要直接阐发《孟子》的本义,但实际上已把儒学的“内用”即“治心”和“治身”放在理论建构的首位。在他们看来,儒学作为治国之道,自古已然。儒学既是国家诏令、法典等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法典、诏令本身,二者往往相重合和等同,儒学的“外用”即外在的政治功能作用达到复以无加的程度。惟有它的内在心性和修身的效应几乎被遗忘,而佛、道却在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诚如佛教高僧契嵩说:“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不可也。”(《镡津文集卷八·寂子》)契嵩在此指出儒学重有为,治国非儒莫属,而治心则为佛之理论所优,非佛不可。契嵩的评论,把治国和治心分离开来,这是不正确的。真正要治好国,也要“治心”并用,仅有前者,是不能治好国的,东汉以后儒学的衰微以及被佛、道挤压甚至居其上,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不能使“治心”起效。虽然如此,但契嵩指出儒能治国而不能治心,确实说明汉唐儒学弊病的所在,道明了儒学衰落的真正原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理学家认为重建儒学不能走汉代只重视儒学外用的政治功能作用的老路,而着重的要重建内用的治心和治身的思想理论,治心是将儒家学说内化为人的心灵意识,很显然这不舶靠外在的政治强加,换言之,必须恢复和重光儒家的学术品性。也只有如此,才能应对佛、道的挑战,应对宋代现实的伦理危机。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理学家把心性之学作为振兴儒学的理论突破口,把对心性之学的阐发作为建构新儒学的核心。理学家对此作了很多的论述。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二程集》)程颐认为只有正其心,做到心诚无妄,方可至圣,因此,“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圣。”(《二程集》)又说:“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二程集》)程颐把心、性、诚融为一体,认为这是人之成圣的内在根据,程颐把儒学的内用提到空前的高度,“学也者,使之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集》)很显然程颐是把心性之学放在理学建构的首位。周敦颐同样对心性之学的阐发和论证作为他学说的中心,“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二程集》)抽象的哲理推论,旨在阐明道德性命之说。心性之学牵涉对性的本质的把握和认识,牵涉到性与情的关系,因此,心性之学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广泛的理论问题。惟其如此,所以理学家放宽了心性研究的视眼,对性与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苏轼就是其中之一的学者。苏轼指出:“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谓之情耳。”(《毗陵易传》卷一)他对性情之学作了深入研究,无怪乎秦观对此评价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简》)把心性之学奉为为学之要,不独理学家如此,其他的思想家几乎无不如此,这成了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命题和思潮。史家兼思想家司马光曾这样说道:“大人之道正其心而已矣,治之养之,以至于精义入神。”(《温公易说》卷三)“心”乃“道”之所系,若治之养之,自可使精义入神,因此,“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司马温公文集卷六十四·中和说》)虽然为学范围很广,但为学之要在治心。司马光说“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司马温公文集卷六十四·中和说》)司马光最明确不过把治心作为治学的根本,突出了心性问题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无疑这是宋代学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儒学主旨的重大变化。似乎把握了心性之学的这个中心,对儒学便可循而达之,开门辟道,把学者引入学术的殿堂。新学学派始创者王安石言:“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王文公文章卷三十四·虔州学纪》)王安石把道德与人心融为一体,明确提出道德出于人心,这就说明宋儒重视和把心性之学列为头等的理论课题,很显然旨在说明心性是人伦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明心即是明乎道德,归根到底明心是为了阐发人伦道德精神。治心即是以道德治人。
理学家把心性之学置于建构新儒学的理论突破口,诚如上述,既有其理论的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首先,由于治心即是道德治人,求心即是阐发人伦道德精神,因此,倡明心性之学乃可满足挽救宋代社会严重伦理危机的需要。唐末五代十国,既是一个军阀混战和政治极其动乱的社会,也是一个道德伦理无序而引发了普遍的道德危机的社会,构成封建社会基本人际关系重要方面的君臣父子关系严重失序。欧阳修指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乘(乖),而家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记》)众所周知,失去了道德及其规范约束的君臣父子关系,这不是一般的失序的问题,而必将带来社会的极大混乱,使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和谐关系遭到彻底破坏,其直接的危害便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文章扫地而尽于足矣。”(《资治通鉴·后周记》)五代社会,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相互厮杀,僭越篡夺,比比皆是,杀戳欺凌,无处不有,君臣之间毫无道德可言。家庭父子关系亦然。屡被史家所唾弃的曾任五朝八姓的宰相的冯道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冯道身为宰相,寡廉鲜耻,善于钻营,投机应变,毫无气节。司马光指出他对上(君)“如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诈,曾无愧作。”无忠可言。冯道看水行舟,弃气节于脑后。“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由。”(《资治通鉴·后周记》)司马光认为象冯道这样的道德堕落者,当时虽很突出,但决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整个社会便是道德沉沦的社会。他感叹地说:“五季以来,风衰义丧,士惟知苟荣贪位。四维既灭,人纪沦亡。宋初颓风犹是也。”(《古今史论大观·后篇》卷十四)社会伦理危机,是国家衰败的重要标志,是乱象丛生之源,坏人心,乱纲纪,危害至深。欲取江山先取人心,治国必须治心,因此,宋代社会要从根本上摆脱五代十国的政治纷争,使国家和社会呈现清明,统治者自己必须把“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由内圣开出外王,推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仅靠武力的平定和诏令、法典的强制,这显然无法达到上述目的的。武力的征服只能触及肉身尚且不说,即是诏令、法典一类政治性的举措也无法达到治心的目的。法典、诏令在专制社会只能对人的行为起一种禁止的作用,只能使人在准和不准之间作出选择,并在这二者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使人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和不自觉的状态。然而道德对人的调节和教化则与此大不相同。第一,法律达不到的地方甚至人心的最深蔽处,道德都能起作用,广及国家、社会、家庭,广及人的外在行为,广及个人的思想和心灵世界,其作用几乎无所不及。第二,道德伦理对人的调节,不仅对人的行为起禁止的作用,被动地选择准和不准的问题,而是从自省的基础上自觉地向人们行为发出指令,在应该不应该而不是准许不准许问题上作出自己的选择。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象慑于政治权威的惶恐的被动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主动地而自悦的状态。总之,历史表明,一个社会的安定和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需要有双重的保障,即既需要一种有形的赏罚支配人的肉体,更需要以无形的赏罚支配人的精神生活,对于前者在赵宋立国就被看重和力图之,对于后者即道德基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无法担当此使命。因此,旨在治心的道德的重担自然历史地落到了理学的重建上,孔子关于道德比法更重要的思想及孟子的“心”与道德同体与一源的思想为理学家提供了学术上的依托,提供了思想的凭借和资源。总之,宋儒以心性之学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建构,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另外,理学家推明心性之学,以心性为儒学之本,这也是回应佛、道挑战的理论上的需要。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中,统治者只迷信于权力和权力性的影响,迷信于权力的震慑,轻视非权力性即道德的教化和示范性影响,因此往往不能治国与治心并用。虽然儒学在本质上是人学,提出了系列旨在“治心”的道德和规范体系,但由于受政治的制约,儒家思想成为法理,其中道德也变成了政治工具。迷信权力的崇拜,把内圣与事功对立,因此,他们认为治国根本不需要修身,根本不需要治心,所需要的是权力和权谋,否定内圣可以开出外王。统治者事实上的治国与治心分离,所造成的结果,是高度的专制的震慑和权力的膨胀,而儒学由此失去了它在思想上的影响力和解析力。诚如前述,儒学的外用即政治的功能作用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它的内用即“治心”的功能则被边缘化和不被重视。与此恰恰相反,而佛、道的影响力却大增,甚至它们在一段时期填补了治心的空白。佛教虽治国无能,与封建宗法关系为主旨的政治体制不相容,但在民众中的教化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它给冲突无状社会中的饱受痛苦的民众预约了进入幸欤无比的天国的廉价门票,给民众以精神上的慰藉。以慈悲为本和以普度众生为怀,给民众一种关爱精神和急于解脱冷酷生活的人们一种温情。佛教的这些宣示,无疑对民众有一种心向的诱惑力,好象只有佛门才是清净圣地,可以超脱自己的苦难。道教虽从道家所脱出,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宗教神学,在皇权至上和皇权支配教权的中国社会,它不可能在治国方面有大的作为。但道教在治身方面有它独到之处。它注重养身,关怀病体苦楚,关注人的长寿与健康,讲究肉体保养,所有这些,都给蒙受统治者欺凌和肉体病害痛苦双重折磨的民众,带来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尤其对无力医治病痛的弱势民众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另外,佛、道在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宣示,使之更具有教化的魔力。如对儒教的影响力,理学家不得不承认说:“佛似大智慧,独见情性之本”。史学家兼思想家欧阳修曾深沉地思考了一个问题,佛教既然“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怪说》),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社情,那么为何在民众中有如此大的魔力呢?以致民“皆相率而归焉”。(《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这是什么原因呢?欧阳修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佛教有使人受其诱惑的理论系统。欧阳修把此理论概括为:“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因此,他认为对待佛教不能采取韩愈的简单地毁佛的强制的办法,这种办法是无法战胜佛教的。真正要免遭佛教的冲击,挽救儒学的危机,最关键的是从理论上回应佛或道的挑战。为此,欧阳修提出新的斥佛的对策,这就是“莫若修其本以胜之。”那么什么是胜佛之本呢?“礼义者,胜佛之本也。”(《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众所周知,礼义乃是人伦道德学说的基本内容,因此,要真正战胜佛教的挑战,争取群众对儒学的信仰,只能依靠儒家的道德学说。“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也。”(《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论》)那么如何重修或者说阐礼义呢?理学家认为只能从儒家典籍中探寻,只能以早期的先秦孔孟儒学为学术依托。他们批判了学术界存在的以为性命之学只能从佛学中求的倾向。理学家李觏指出:“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李觏集卷二·邵武军置田处》)李觏认为性命之学并非佛家独具,儒家学说早有之,只不过被人淡忘了。“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李觏集卷二·邵武军置田处》)李觏把佛的性命之说归之取于儒学,这可能有失实之处,但他认为儒家学说确有丰富而系统的性命之说却是正确的。对孔孟的典籍诠释中便可充分的发现和证明这点。事实上,理学家正是从先秦儒家典籍的阐发中,重修和建构其儒家心性理论和人伦道德学说体系的。理学家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发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囿于传统,大胆地打破了儒家经典只有《六经》的限定,而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认定。《六经》本为《庄子·天运篇》提出,后为汉儒所认同,故有儒家《六经》之说(《乐经》已失,实际上只有《五经》),所谓“经”原本是“经常”之意,后演变为永远不变的真理。理学家对庄子关于孔子与老子对话中所提出:“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篇》》并不置疑,同样奉《六经》为儒家经典。但与传统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为学之本并不能仅限于《六经》,而应该根据理论建构的需要,对经典重新认定。因此,理学家首次把《五经》之外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为为学之本,看作是与《五经》同样重要,甚至其重要性还超过了《五经》,特别是《大学》、《中庸》原只是《礼记》中的二个篇目,变成了重要的儒学典籍,这是儒学发展中不寻常的变化。到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总结了北宋理学家的成果,作《四书集注》,正式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书,由此《四书》正式得名,《四书》由此升格为经典,与《五经》并列,这就是后来联称《四书》《五经》的由来。
理学家抬高《四书》并以此作为其学术上的依托,同样这也与唐代韩愈、李觏等儒者对《四书》的推崇与升格有关,换言之,接受了唐代思想家的影响。唐代由于复兴儒学和建立新的儒学道统的需要,不少的思想家对《四书》表示了关注,企图把《四书》提升到象经书一样的地位。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杨绾曾上本朝廷,要求将《孟子》、《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新唐书·选举志》)柳宗元则进一步把《孟子》、《论语》尊为“经言”。(《柳宗元集卷二十五·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到唐懿宗时,皮日休则径称“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并说“其文继乎六艺”,“真圣人之微旨也。”(《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把《孟子》视之圣人的经典。对于《大学》《中庸》唐代儒者也颇为关注,也在阐发中屡出新义。总之,以上学者,实际上已将《四书》升格到与经书并列地位。唐代儒者所开启的从《四书》中探索儒学新义和建立新道统的尝试,给宋代理学家既以思想上的启迪,也为他们建构理学体系指出了发展方向。理学家把《四书》作为自己的学术的依托,实际上是对唐代韩愈等思想的直接继承。
另外,《四书》确为理学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资的思想资源。《论语》被理学家推崇,就在于它建构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为儒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毫无疑义,这也是理学家重建儒学所赖以依靠的理论基础。《论语》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为什么人需要互相关爱,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关爱情怀?人的仁爱精神的内驱力是什么、人如何发掘和调动这种内驱力呢?理想、人格和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另外,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以及寻找与此相协调的何种自然环境呢?如此等等,儒家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宋代儒学发展中急待的思想养料。理学家如果真要把儒学恢复为人学,要建立重于“内用”的理念形态的儒学,必须把《论语》作为理论依托。《中庸》提出性、天道、人心、道心、中、一、诚等概念系统,也是理学家阐发的心性理论直接援用的概念。《大学》提出治国必须治心,当政者不能只迷信权力和权力性的影响,也应该关注非权力性的影响,并自觉的加强当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政治上起表率作用,等等,这些论述恰是理学家要使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转向于理念形态儒学相结合所需要阐发的理论。
《孟子》一书所含蕴的儒家思想理论,几乎是为以后历代儒者和愚想家所肯定和推崇。《孟子》的仁政学说,批判了暴政和霸道,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现了人本主义,虽然在实际中无法达到,但它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为挣扎在水火中的受苦受难的民众提供了希望和安慰,也为他们提供了批判暴政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发扬了孔子的仁学,可与佛学的心性论相抗衡。关于存心养性学说,既说明道德缘起于心,“四心”与“四德”(仁、义、礼、智)同本同源,也说明了儒学重“内用”的心性之学。以上所有这些,都是理学家在与现实中与佛、道论战中所时刻碰到的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也是儒学被意识形态化后所被忽视和边缘化问题。孟子的论述,对理学家提供了思想凭借和理论上的支撑和依据。总之,《四书》可为理学家建构以心性为中心而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框架和概念系统,提供了欲求而难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源。事实上理学家在建构新儒学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四书》的影子,完全可以这样说,理学家对新儒学体系的重构便是在阐发《四书》思想本义的基础上展开的,或者说《四书》是他们的为学之本。理学家与《四书》的思想联系随处可见。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就是其中的开创者。明代思想家薛瑄曾指出周敦颐的“《通书》一诚字括尽”。(《宋元学案》卷十一)黄宗羲在评述周敦颐的著述时也说:“周子之书,以诚为本。”(《宋元学案》卷十二)细释周氏之书,事实确是如此。周敦颐把“诚”作为他理学体系的最基本的范畴,是本于《中庸》。首先,周敦颐把“诚”作为宇宙的本体,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通书·诚上第一》)认为“诚”化生了万物和宇宙,很显然这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如出一辙。其次,周敦颐也同《中庸》一样赋予了“诚”以道德属性。“无妄,则诚也”,(《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二十三》)“诚无为”,这就是说“诚”具有“无妄”即诚实无欺的道德属性。“诚”不仅是宇宙自然的本体,而且是人伦道德的本原。“诚,五行之本,万行之源也。”既然“诚”是“五常之本”和“万行之源”,(《通书·诚上第二》)自不待言,人伦道德缘起于“诚”了。由此可以看出,“诚”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道与人道的共同本质,是这二者即“天人合一”的结合点。正因为如此,所以“诚”也就是最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无怪乎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第一》),又说:“圣,诚而已矣”。“诚”既是道德境界,又是道德修养本身。综上所述,周敦颐建立的“诚”为基础的理学体系,直接渊源于《中庸》。
张载立学以《四书》为本,同样明显和突出。他对《四书》的推崇可谓达到了顶峰。他说:“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一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沪”。在张载看来《论语》、《孟子》是圣人所作,乃是经言,集学术之精华,既渊又博,学者们只须对此细加体悟,仔细韵味,不必旁求。“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张载集》)虽然张载肯定了唐代以来学术界疑经惑古之风,但他以为《中庸》、《大学》出于圣门,代表孔孟真传,不可置疑。《四书》是为学之要,学圣之需。
张载本人对此身体力行,他的理学思想同样以《四书》为理论起点,是对《四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代表作《正蒙》便是如此。张载为了进一步阐发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天人合一”观,致力于从《论语》觅寻理论依据。《论语·公冶长》记载说:“子贡曰:‘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此记载,张载作了另一种诠释,他认为子贡之说不合孔子本意。他指出说:“耳不可闻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子贡以为不闻,是耳之闻,未可以以为闻也’”。(《张载集》)并还说:“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张载集》)张载认为夫子性与天道而子贡所未闻,只说明子贡自己耳朵未听到,耳未闻不能说孔子没有传授过“性与天道”的问题,事实上张载的论证是正确的。《论语》曾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者尊奉也,即孔子尊奉天命与人伦道德的结合,因此,子贡说孔子未言性与天道问题是不确实的。《论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多有论及。张载否定子贡,就在于要从《论语》发掘出长期被忽视的儒家的性与天道的问题,并从中找出论证依据。类似于从《论语》开发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南宋思想家张栻亦如此,他同样也批评上述子贡的言论,同样也从《论语》中开发出性与天道的理论。
检视张载的著作,《四书》的重要范畴多被他沿用。对天、道、性、心、诚诸范畴,张载的阐发几乎不遗余力。“某观《中庸》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张载集》)张载把这些范畴与《易》中某些范畴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太虚即天,太虚气化曰道,道与虚相结合为性,性与知觉相融便是心,心是这四者结合的最高点。由此提出“大其心”、“尽其心”的直觉体验的省悟之道。张载对《中庸》如此,对《论语》《大学》《孟子》亦如此,用功甚力。他著名的人性二元说,就是对孔子“性相近”和《孟子》的性善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的总结与综合。总之,张载理学思想存在着与《四书》不可分离的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二程与《四书》的紧密联系,自宋之后的学者们几乎都首肯,从不置疑。二程曾作过样的表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二程集》)具体言之,要把《大学》尊为“孔氏遗书”,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不仅如此,对《四书》不能只从字面上考究,要以书之精义切已,内化为心灵意识,领悟人生哲理。“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已,不可只作一场话说”。(《四书集注·读论语孟子法》)他们认为《四书》是学者“入德之门”。理学家程颐、程颢把《四书》抬高到如此重要地位,同上述理学家一样,他们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儒家经典的精义。“《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集》)二程以为《四书》总括了儒学的精神,治《四书》由《六经》就可不治而明,这虽然有夸大之嫌,但就儒家人伦学说和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心性之学,在《四书》中比较系统而集中则是事实。因此,二程把《四书》置于为学的首位,确与他们凸显儒学的伦理本位有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二程理学思想的诸多范畴是本于《四书》的。他们思想体系中的“理”、“性”、“格物”、“穷理”、“诚”等范畴及其对此义理的阐发,都可找到与《四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的关系。二程主张的“知止于至善,为人于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二程集》)这既表明人伦之学是二程理学思想的主旨,也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把《四书》置于为学首位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因于建构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需要。
纵观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倡明儒学人伦之学,显示与重光儒学治心与内用的魅力,把封建专制法理的儒学改造为可与内化心灵的儒学结合,是宋代整个理学家的总目标。北宋和南宋理学家都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此总目标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形成斑澜多姿的理学派别。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创始人和领军人物胡宏和张栻对《四书》作了系统阐发,建构一个别于二程理论的性本论的体系。在此时期心学家陆象山,另开思路,对《四书》本义探索和阐发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既不同于二程理本论又别于湖湘学派的性本论的心本论,为明代阳明心学开了先河。朱熹作《四书集注》,系统地总结了理学家对《四书》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学术史上正式确立了《四书》学,《四书》由此成为经典,理学思想体系进入到已臻于成熟的形态,进入到儒学发展的顶峰。
综上所述,理学家以《四书》为依托,从《四书》开发与阐明的儒家心性论和人伦道德学说,既是理学与汉唐儒学的区别点,也是宋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总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宋代的理学并不是汉唐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即封建政治思想统治简单的照搬,而是实现了人学为本旨的而表现为以理念形态的儒学的复归,质言之,实现了以人伦为本位的儒学的归位。以此言之,理学的兴起也可谓是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重建和振兴。在封建专制下,政治与学术不能分,以政为学,学术最终解不脱政治的制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理学家把儒学推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的新阶段,不能否定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儒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