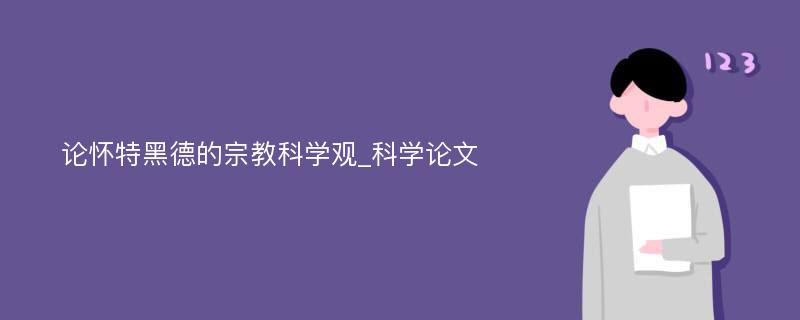
论怀特海有关宗教与科学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宗教论文,观点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讲宗教与科学,怀特海(注: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数学原理》(与其学生罗素合著)、《过程与实在》等。)有一段著名论述:“如果考虑到宗教对人类有什么意义,科学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除各种感官的冲动以外,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一种是宗教的直觉,另一种是精确观察和逻辑的推理。”[1]基督教传统和近代自然科学作为两种强大的作用力量,在西方文明史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印记。但在人类进入耶稣新千年的时候,科学发展一方面因其辉煌成就而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因其引发的全球问题而日益使人类精神困惑。于是,重估宗教与科学及其关系的意义就空前突出。怀特海在70多年前写就的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对宗教与科学及其关系专门作了论述,其中的思想观点至今仍颇有启迪。
1 “宗教对人类有什么意义”?
对宗教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把握。不同于科学,宗教对人类有什么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howthe world is),而是世界尽然存在(that the world is)。“怎样存在”是科学研究的问题,它揭示世界上的具体事物怎样彼此关联,怎样相互转化。“尽然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身不是指一种种现象、一个个事实,而是讲所有的现象、事实的整合,即世界或宇宙的整体。把世界当做整体,设问世界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便是宗教的问题,它超出了科学的理性限度,涉及到从无生有的形而上学。
世界的存在整体、宇宙的无中生有这些问题之所以是形而上的,因为它们都超越了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外,实际中似乎与人在世界中生存这事实相悖,但从精神上看,则是一种有意义的致思。它使人能够脱离具体的现实,获得不同于常规思考的一般原理。怀特海注意到了“超越”(detachment)这一形而上的本质,并到旧约圣经的内省部分去寻求其真谛。他在《约伯记》中发现了“超越”的愿意:对待自己孤独性的宗教人格特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玄思冥想的佛陀等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都被描绘成孤独的个人,这种孤独使他们超越了当下的环境,产生了普遍的宗教意识。因此,在怀特海看来:“宗教是个人针对自身的孤独性而进行的活动。……宗教即孤独性。……集体的狂热、信仰复兴、宗教团体、教会、仪式、圣书、行为典章等都是宗教的外表,是变化的形式。……然而宗教的目的超越了这一切。”[2]怀特海的宗教立场把孤独的“个人”问题作为中心,将人性从种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内趋人的精神世界,赋予世界以意义。把世界看作最终是由主体而非纯粹的客体构成,无疑是从科学到宗教的一种变化。可见,怀特海对宗教的这种理解不仅超越了具体事物上升到存在整体,而且由外部的物理世界返回至内在的主体精神,实现了对科学的意义整合。
至于宗教对科学的意蕴,可从怀特海有关宗教比较的论述中阐发出来。怀特海把佛教和基督教分别比拟为“孕育宗教的形而上学”和“探究形而上学的宗教”。他指出:“对佛陀来说教义是首要的,关于他本身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教义说教的辅助手段。与此相反,山上的训诲、隐喻之言、以及关于基督的事迹等,福音书所展示的是令人敬畏的事实,教义表达得是否明确不是问题的关键,第一位的是宗教事实。”[3]怀特海认为,在佛教中,比佛陀本身事迹更重要的是教义内容,这种强调教义的特征是形而上学的,而基督教则是立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宗教,形而上学的说教是后来的神学家附加的。这区别一方面使人联想到佛教与诺斯替教(Gnosticism)的相似性,它们都呈现出理智的色彩,强调精神的普遍性和对物质时空的超越。从西方文化的传统来看,这种理智主义从古希腊的“证明科学”(apodeiktike episteme)发展到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僵化理性而趋于极端化。但它同时是构成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要素。另一方面,基督教诉诸具体历史事实的思维导向正是现代思想之根源。现代思想乃是从理性思维到历史思维的一种转变。怀特海考察了宗教改革和科学运动作为近代历史性变革的两个方面之后,提出:“如果我们把这次历史性革命看成是一次提倡理性的革命那就完全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次十足的反理性运动。这是回到玄思神秘事物上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4]他以《特里腾宗教会议史》(Historyof the Council of Trent)为依据证明了当时教会对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套经院神学的拒斥。因为教会认为经院神学在遇到困难时总是运用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告诫神职人员应避免像经院神学家那样的华而不实的问题和乖僻的争论。作为现代思想特征的历史思维包括了经验的研究方法。它寻求的不是事物和现象的普遍原因,而是满足于特殊领域中的有限理解。怀特海认为,从普遍理性到关注事物的特征和根源这种转变乃是一种思想进步。舍此,科学就不可能步入其伟大的时代。他把形成现代思想的17世纪誉为天才的时代,并指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历史思维的形成及其影响,是构成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二要素。因为近代自然科学不只是一种理性演绎,更是一种经验证实。所以,它又是一种“实验科学”(scientia experimentalis)。
虽然可以从怀特海的宗教比较中揭示出构成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大要素:理性思维的“证明科学”和历史思维的“实验科学”。但是,这两大要素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它们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现代思想的新面貌和构成现代世界的新奇观。诚如怀特海说的:“所谓现代思想的新面貌,就是对于一般原则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注重实际的人致力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世界历史的每一时代,也富于哲学头脑的人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创造普遍原则。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向就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5]所以,尽管现代思想拒斥了中世纪的理智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理性的追求。怀特海相信,只有将理性与经验并重,把普遍原则与详细事实相结合,才能构筑现代文明世界。
2 “科学的实质是什么”?
科学是普遍理性与经验事实的结合。在科学中,经验事实作为证据必须纳入相关的理论框架才具有意义。对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经验证据,任何经验证据都渗透着理论,它们因理论背景的不同而不同。相类似的情形是,在宗教中信徒们认为世界、生命和人类的存在这一切事实,都必须与神的存在联系起来才变得可以理解。从宇宙万物的和谐到大肠杆菌的精致,所有这些事实只有在对上帝设计的信仰中才觉得能够理喻。不论是科学抑或宗教,关键在于它们整合经验事实的方式即理论体系或信仰依据。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抑或宗教的信仰依据终究又可归纳为两种形而上学的约定:科学对经验事实的自然主义解释和宗教对经验事实的超自然主义解释。两种解释差异的实质在于事实与价值相分与否。
近代以来,牛顿物理学及其机械论宇宙观预设了世界是充满质料的空间,“这种质料本身并没有知觉、价值或目的。它所表现的一切就是它所表现的一切,它根据外界关系加给它的固定规则来行动,这种规则并不是从它本身其所以能存在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6]怀特海认为这种预设是“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把科学发展某一阶段出现的抽象观念误认为是对具体世界真实描述。在怀特海看来,科学对世界以纯粹事实为基础的机械论描述其实是一种观念的抽象,根本不是世界的真实面貌,因此需要加以批判。对此,他发展出了一种植根于审美价值经验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体系:实在根据关系得以规定,一切关系则被规定为价值关系,即从人的审美反应一直到物理粒子的吸引与排斥,这一切存在物普遍具有的肯定与否定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消除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严格区分,支持了一个充满价值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价值与事实并无分别,价值恰恰是事实的一部分,即事物自身结构的一部分[7]。“在发展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过程中,怀特海把感觉价值的审美经验作为首要的经验事实。一切关系和性质等,都被规定为所与价值和感觉价值的原始审美关系的事例或抽象。”[8]“在怀特海看来,价值和评价贯穿事物的始终,而所谓近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不过是那基本评价事实的有限抽象,虽然这种抽象从实用角度来看是有用的。因此,怀特海哲学是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在哲学和科学中居支配地位的机械宇宙观的一个新颖且更为精致的替代品。”[9]
怀特海对“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的批判,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的机械宇宙论,而且还深入至哲学上的康德和休谟的观点,康德认为,作为经验价值第一源泉的,既不是经验对象,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认知主体本身。对比之下,作为怀特海形而上学起点的审美价值经验则是关系性的和价值性的范畴。一方面,它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另一方面,它不是纯粹的认知关系,而是实在的价值关系。此外,康德把审美经验的源泉放在了主体性条件之中,而怀特海则将其放在了支配自然的、客观的事物序列的客观条件之中。因此,如果说康德的分析是从主体性进展到一个明显构造起来的经验的话,那么怀特海则把这一分析翻转了过来,“并且说明了从客体性进展到主体性的过程。”[10]在怀特海看来,康德的分析是一种理想的而非现实的抽象,若将这种抽象视作根源,便是远离常识的误置。至于休谟,他把因果关系当作事件间恒常的和接近的关系,并认为是由人通过某种获得性思想习惯而把这些相似性的事件联结起来的。怀特海宣称,休谟的观点又是“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的一个明显例证。因为它错把我们的理论抽象当作具体的现实。这里的理论抽象便是几何的、数量的或空间知觉的世界,由于呈现于其中的材料生动而清晰,休谟和他前后的很多人一样,把它视为具有“表象直接性”的感觉世界,并认定它是源始性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复杂知觉模式,它源自一个更具有源始性的“因果效验”的知觉模式。相对于“表象直接性”,呈现于“因果效验”中的材料却内在而模糊,以至于休谟等人误把它认作派生性的东西。然而,怀特海认为,对于人的经验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是这种尽管内在的、模糊的却充满价值的、具有现实性的“因果效验”,而不是那种虽然生动的、清晰的但无价值的、抽象性的“表象直接性”[11]。
从牛顿物理学到康德、休谟哲学,其中的共同特征是价值的不在场,他们无论作出科学预设还是进行哲学分析,最终都诉诸一个纯粹事实构成的世界。这是一种既高度复杂而又十分抽象的观点。近代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演绎出来的。但是,这种后来抽象出来的科学事实对于源始具体产生的宗教价值的发展却有促进作用。怀特海认为,源始形成的宗教作为人性对思想体系的全部反应,“这种反应的性质是复杂的,其中包括着人性低处所发出的感情因素。科学和哲学的不带感情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就可以帮助宗教的发展。”[12]
3 “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
对宗教与科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既有一般的类型学分析,又有具体的历史学考察。类型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伊恩·巴伯(Ian Barbour)的四种类型说:冲突(conflict)、自主(independence)、对话(dialogue)和整合(integration)[13]。不同意这种类型学的思路,科学史家布鲁克(John.H.Brooke)认为:“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表明,科学和宗教之间在过去存在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支持一些一般性的论题。结果,真正的教训正是在于这种复杂性。”[14]怀特海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研究,基本上是遵循历史学的途径。他的名著《科学与近代世界》尝试研究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西欧文化诸形态受科学发展影响的范围,旨在对近代以来的支配西欧科学、文化和宗教的宇宙观进行哲学的批判。
此论著中关于“宗教与科学”这一章的论述,引人注意的并非是他对这两者之间关系所做的理论分析,而是他对这两者之间关系作出的积极理解和持有的宽容态度。首先,他以宏观的视野去观察人性的演变,所谓“用一个较大的比例尺画下它的历史图案”,发现两个显著的事实:“第一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第二是宗教与科学两者都在不断地发展着。”[15]尽管接受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这一历史事实,但是怀特海却从发展的眼光对它作出了积极的理解,这一点与罗素等对立论者的观点明显不同。怀特海以科学史上相互对立的理论为例,说明:“只是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这些真理显得彼此不调和而已。”[16]他相信:“冲突仅是一种征兆,它说明了还有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有那里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微的科学将互相调和起来。”[17]其次,怀特海仍然以科学史为背景,论证了“对不同意见必须作最大限度的容忍的充分理由”:“在实际知识的发展中矛盾则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18]在怀特海看来,科学史上的一些教训如此,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发展未尝不是如此。他以基督教的箴言总结了这种宽容的态度:“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matthew,13:30)”。
怀特海对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历史事实作出了积极的理解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他并不到此为止。他进而认为:“在一个明智的时代中,决不会有一种积极的观点抛弃调和真理的愿望。安于分歧就是破坏公正精神和高尚的道德。”[19]在怀特海的观念中,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本性中的两种永久因素,我们可以不理会它们之间的冲突,那便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对此,怀特海的论述具有双重含义:一则是“宗教和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一方面拥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拥有的则是神性的美的玄思。”[20]可见,这是对科学与宗教的一种明智的区别。不过,他并不像蒂利希等分离论者那样由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走向两者之间的相互隔离。他同时指出两者之间关系的另则意义:“一方面看见的东西另一方面没有看见,而另一方面看见的东西这一方面又没有看见。”[21]这里,他说的是科学与宗教的一种互补关系。正如光的微粒性和波动性这两种互补的属性最后被整合到光的波粒二象性中那样,科学与宗教这两种对人性互补的真理终将被整合在一个更宽广的真理和实现于更美好的前景之中。这是怀特海的愿望,将这一愿望诉诸一种理论就是他建构的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的形而上学。
怀特海还专门考察了科学对宗教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科学的进步对原始宗教产生了一种解构作用。原始宗教指人性对外部世界引起恐惧的对象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人们遇到恐惧的情况时,只要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这种本能的反应便会化解。现代文明中的心理学多半可以解释原始宗教的旧辞汇。在这样的科学语境里,若把上帝描述为一位在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后面的容易引发其暴怒的全能君主,就会激起现代人各种各样的批判。这可以说是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人凭借不断明晰的理性逐渐澄清了人性内固有的复杂反应,开始把宗教世俗化。恰如怀特海说的:“现代宗教思想中掺入了一种非宗教动机,这就是为现代社会谋求一个舒适的组织愿望。宗教被描述成为安排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宗教成立的理由是它有裁定正确行为的作用。正确行为的目的又很快地退化而成为光只为了使社会关系愉快。”[22]现代思想把宗教归纳为行为准则的裁定者,怀特海认为这是宗教观念的一种退化。宗教史上,圣·保罗曾经指斥法律,清教徒的神职人员则把正义说成一堆破铜烂铁,因为他们都认为坚持行为准则就意味着宗教热忱的减退。科学对宗教的历史影响即使原始宗教“祛巫除魅”(韦伯语)而成为理性化的现代宗教,又通过世俗化的过程从根本上冲击真正的宗教观念。为避免来自科学方面的解构,唤起人们应有的宗教热忱,拯救真正的宗教精神,怀特海阐明了他理解的宗教观念:“宗教是人性寻求上帝的反应。”当然,这里的“上帝”不是人格神,而是“某种东西的异象”[23]。这种东西是“终极的善”和“终极的理想”,它使一切事物具有意义。怀特海指出:“一种宗教的思想方式或仪式,如果促使人们领会到高于一切的异象,它便是强大的。对上帝的崇拜不是安全的法则,这是一种精神的进取,是追求不可达到的目标的行动。高尚的进取心被窒息就是宗教灭亡的来临。”[24]把人性中高尚的进取心理解为宗教精神的本质,怀特海的这种宗教观念显然不会与科学精神相抵牾,反而会培育科学精神在其中的成长。
综上所述,怀特海的宗教与科学之论对哲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产生的意义显而易见。哲学上,他作为整合科学与宗教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观念不只批判了近代科学的机械宇宙论,指出纯粹事实的观念不过是一种理性抽象,从这种抽象出发的世界观则是一种误置性的谬误,而且还引发了后现代的观念。“尽管怀特海从未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语词,但他谈论现代的方式却有着一种明确的后现代语调。特别是在他的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中,他反驳了现代并描述了其显著的特征。”[25]然而,这不是解构性的后现代观念,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观念。因为怀特海正确地评价了现代世界的成就,也清楚地认识到其局限性,并指出要超越它。正是这样,他的后继者在追溯“后现代科学”的思想历程时,把他誉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在科学方面,怀特海把科学与宗教理解为人性的公正精神和高尚道德,这为科学家进行研究和创造活动提供了远大的精神支持,同时也解释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能够持有宗教信仰而追求科学真理的无可否认的事实。科学与宗教的这种一致非常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感情”。爱因斯坦说:“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的工作中取得成就。”[26]“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27]
收稿日期:2002-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