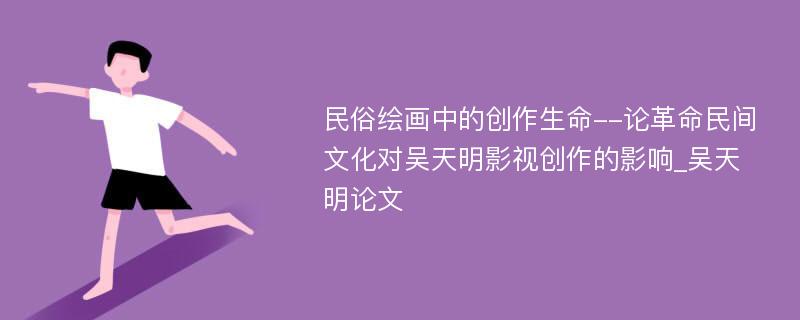
风俗画里写人生——论革命的民间文化对吴天明影视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俗画论文,民间文化论文,人生论文,影视论文,吴天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中国电影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电影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它基本是成长于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电影题材也以表现都市市民生活为主。1949年以后,新成立的各电影制片厂虽然也都设立在城市中,然而电影题材却多转为乡镇生活了。北大学者戴锦华论述了相关现象:“1949年以后的文化拒绝此前的都市文化,将其指认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或殖民地文化,是一些名副其实的‘恶之花’……一种特殊的联系,即革命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联系。它同时是革命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改写。”(注: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第60—61页,知识出版社。)
吴天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导演。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倡和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革命的民间文化一往情深。这位游击队长之子出生在充满着血与火的革命圣地上,那又是一片历史悠久、民间文化极为发达的皇天厚土。吴天明对此抱有极深的文化骄傲:“黄河和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故乡感到自豪。我要深深地植根在这块土地上,去吮吸那丰富的营养。”(注:罗雪莹著《热血汉子——我认识的吴天明》,《电影艺术》1986年第2期第25页。)吴天明自幼就浸润在民间文化的海洋中, 在校演出队和农村业余剧团里,他广泛涉猎了秦腔、快板、相声、民歌等经过革命文化改造了的各类民间艺术样式,艺术的天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形成了革命和民间文化的牢固的情结。这一文化模式塑造了他巨大与渺小的双重艺术人格。他指认自己是大地之子,从大地汲取了强大的创造力:“一见到农村的沟沟梁梁、窑洞土坡,就觉得特别亲切,创作的灵感随时都能迸发出来。”(注:罗雪莹著《热血汉子——我认识的吴天明》,《电影艺术》1986年第2期第24页。)同时他也让自己“隶属”于这片土地。于是对土地的忠诚难免带上了“愚忠”的意味,只有对土地的崇拜之情而缺乏清醒的批判意识。这种观念和情感在带给他创作动力的同时,也制约着他创作的深度和高度。
民歌与土地情结
《人生》起始,镜头缓缓展现出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和S形河谷, 悠远的《黄河船夫曲》随之在天地之间荡起。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声画形象使民歌和那雄浑的地貌一起,成了西部电影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没有航标的河流》(以下简称《河流》)中作为盘老五、吴爱花恋爱戏背景音乐的湘曲,《老井》中旺泉、巧英在山上嘶吼的《小亲圪蛋》,瞎女艺人唱的荤曲儿……都显示情爱、性爱是民歌永恒不变的主题。
巧珍就是唱着情歌走到观众面前来的。《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是她的主题歌。这首歌在她人生的重要关口一次次出现,成为其命运转折的段落标志:她最初羞涩地唱着这首歌走向她暗恋多年的“哥哥”;热恋时,加林最爱听的也是这首深情的歌;送别加林的桥头又是这首歌响起,先前欢乐的调子变得悲凉了,“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的尾句一再重复,表达了巧珍对加林不舍的感情,也传达出她内心隐隐的担忧,更是对她悲剧命运的一个暗示。影片结尾是加林在回乡的小路上越走越小的身影,这首歌最后一次响起,好像一声声沉痛的叹息:为巧珍的痴情,为加林的不争,为命运的难测……它带给全片浓重的悲剧意味和回味不尽的余韵。
在片中有另一位活在民歌中的姑娘与巧珍映照,这就是德顺爷讲述的他年轻时的恋人灵转。在德顺爷年轻时,她唱着《走西口》迎接他来,唱着这首歌送他走。德顺爷对她的回忆都是和民歌连在一起的。在“月夜进城”一场戏中,吴天明巧妙地用声音蒙太奇将这支歌由德顺爷的声音转化为灵转的声音,写实转化为写意。穿过长长的岁月,德顺爷对活在歌声中的灵转的思念之情绵绵不绝。灵转以她遥远的音乐形象呼应了巧珍的现实形象。
巧珍、灵转们被普遍认为是典型的缺乏现代气息的传统型女性,但她们的魅力又不可抗拒。于是在对巧珍这一艺术形象的评价问题上,出现了人们一边批判她的观念的落后性、一边被她的魅力所吸引的毁誉参半的矛盾现象。我们发现:似乎巧珍身上并没有多少儒家士大夫的正统思想,见不到多少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反,她对腐朽的封建婚姻观念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叛逆性:她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以贫富贵贱做选择对象的标准,而倾慕有文化、心气高的加林。她对爱情的追求相当大胆:在高加林落魄之时走近他,主动表达出炽热的恋情,温热了他那饱受挫折的心。的确,巧珍的精神传统更接近民歌。这是一个陕北民歌中那种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兰花花式的女子,她因爱而燃烧,她可以为恋人牺牲自己的一切。失恋后她虽未像民歌、民间故事中的古代女子如刘兰芝、祝英台等那样以身殉情,但在那老式的婚礼上,我们分明感受到她哀莫大于心死的深切伤痛。
吴天明用代代相传的民歌赋予了巧珍这一形象一种原型特质,给她增添了浪漫的光彩,使其从现实的生活里升华了出来,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爱的化身。于是这个形象就具有了一种古典美。用古典的原则来衡量,巧珍身上的种种缺陷也显得可爱了:她没有文化,却十分纯朴;她在加林耳边唱的情歌远比城市姑娘黄亚萍的“大雁诗”要实在,要美;她缺乏独立性,但其牺牲精神却是如此感人;她不够坚强,却爱得惊天动地……
深究起来,不仅仅创作者本人对这一艺术形象有情感倾斜,中国大众集体意识中都有对这类传统型女性的热爱情结(他们在百花奖评选中接连选中吴天明影片中传统型女性扮演者:《人生》中扮演巧珍的吴玉芳和《老井》中扮演喜凤的吕丽萍,而对扮演现代型女性的演员弃之不顾的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这一情结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共同培育的结果。就连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都说自己可以说是个“刘巧珍党”,经过了“一场感情和理智摔跤”,才“从开始把全部同情放在巧珍这个人物身上,到最后更侧重于高加林。”(注:钟惦棐著《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见《电影观念讨论文选》第391页,39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是互动关系,吴天明的创作无法超越这样深厚的社会集体心理。纵观吴天明的创作,他作品中这一类唱着古老民歌的付出、牺牲型的传统女子和德顺爷一类智慧、慈祥的长者正是吴天明心底深处地之母、地之父的形象。他们是吴天明情感的对象和人生的导师。作为地之子,吴天明不自觉地将情感向他们倾斜,向他们投以仰视的目光,这正是这一代知识者面对土地——农民时下意识采取的共同姿态,是革命文化赋予工农大众以知识者的改造者、教育者的身份的必然结果。生在圣地的革命家庭、经历过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吴天明对这类形象的钟情,除了天然的血缘情感,也不排除被改造了的文艺家对改造者的膜拜。明显地,对巧珍的同情的另一面正是对高加林的批判。影片上部肯定了加林走出故土、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当杂志上的飞机在高加林的幻觉中冲天而起的时候,当高加林发出:“联合国都想去”的壮语的时候,这个当代青年显得多么豪迈!吴天明此时此地对高加林的赞赏是坚定而鲜明的。而到了下部他却在抛弃巧珍的问题上谴责了自己的主人公。吴天明的价值观于是产生了分裂:当代意识遭遇了传统观念的遏制,最终让高加林壮志难酬并且心亏气短。回乡山路上,在巧珍深情的歌声中,高加林小小的身影是那么落魄、那么灰溜溜的。其实,最终离不开土地、舍不下“地之母”的不是高加林而是创作者本人。吴天明心中的土地并非等同于农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的土地,而是他供奉的精神圣土。这是与土地——人民——革命有着扯不断联系的那一代中国知识者、文学艺术家们共有的心灵家园。
戏曲与革命文化
戏曲是民间文化的精华,它与革命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河流》里吴天明用两次唱戏的情节表现了不同的时代气氛。第一次是土改时盘老五的恋人吴爱花和老区长合演《夫妻识字》,欢声笑语,表达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反映了干部群众亲密无间的鱼水深情。第二次则是十年动乱期间的样板戏图景。与上一次唱戏其乐融融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风声鹤唳的肃杀之气。手持大棒的造反派挨家挨户驱赶人们去看已经演了多遍的《龙江颂》。演出后靠造反起家的区革委会主任李家栋“借样板戏的东风”,在暴雨之夜搞劳民伤财的“挑灯夜战修水渠”,农民们怨声载道,干部关系紧张到极点。在这里,戏曲完全没有了民间的气息,而变成了强权政治工具。吴天明在片中表现的恰是戏曲在中国现代史上两次被革命文化改造的情景。早在1938年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一次看了旧剧之后就指示道:“群众是喜欢这些传统形式的,但内容应该更新。”(注:钟敬之编《延安十年戏剧图集》第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 982年版。)很快, “革命的内容和民间文化形态的结合构成主流文化”,(注: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第62页,知识出版社。)而以《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为代表的延安街头铺天盖地的秧歌剧是《讲话》之后这一文艺潮流的源头。随着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发出“旧剧革命”的号召,这场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注:毛泽东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毛泽东文艺论著选读》第138页, 吉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1977年。)。这封信于1950年和1967年两次发表,推动了建国以后的戏剧革命和文革中的样板戏运动。复旦大学学者陈思和注意到了延安秧歌剧运动与文革中样板戏运动的联系:“周扬借群众之口,说旧秧歌只是‘溜勾子’秧歌,‘耍骚情地主’,而新秧歌是‘斗争秧歌’。‘新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这生动的描述让人想起60年代的现代京剧样板戏,谁说这里没有某种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呢?”(注:陈思和著《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见《鸡鸣风雨》第36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吴天明在当时的创作中对革命样板戏固然采取了控诉的态度,却对革命秧歌剧无保留地赞赏,反映了吴天明本人跟革命的民间文化的血缘联系和天然感情。小说原作中简短的一句:“她晚上演戏扭秧歌,像只蝴蝶”被他演绎成一大段载歌载舞、激情充沛的戏,那其实正是吴天明童年生活情景的生动再现:那时他“参加了自乐班,演出从解放区传下来的革命秦腔戏:《血泪仇》、《穷人恨》、《大家喜欢》(也叫《改造二流子》),连演三个娃。”(注:笔者1998年12月采访吴天明录音。)从此他演着这些革命戏曲长大,在那种浓烈的革命氛围中构筑着自己单纯而美好的情感世界。那种干群同乐的乐观图景,恰切体现了他的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
今天,革命文化对戏曲这类民间文化不再采取强行改写的态度,而是在深层结构上与其达到了和谐统一。吴天明90年代创作的《变脸》中的戏曲基本恢复了古老的传统面目。川剧《观音得道》是一出歌颂孝道的正统戏,观音为救父舍身坠崖,感动了佛祖,让她得道升天成了佛。电影主人公小狗娃为救师傅,模仿戏中观音的做法,舍身从戏楼上坠下,感动了红戏子“活观音”和川军陈师长,救出了变脸王。作为封建中国这个“家天下”的国教,儒教以孝为本,忠、义等思想都从孝发展而来。狗娃曾因性别欺骗置变脸王于“无后”的大“不孝”境地,最终却完成了孝、义、情的完美统一。片中观音、狗娃和戏子梁素兰的孝行义举与传统目连戏中的目连行孝救母、《秦香莲》中的韩琦舍身取义等诸多戏曲情节如出一辙。
《变脸》是吴天明电影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片跟他的上一部电影《老井》的创作时期相距了8年。其间创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整个中国也经历了大的社会转型期。如果说在《人生》、《老井》那个寻根时期,吴天明主要致力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矛盾的反思;《变脸》之后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倾心认同。他将人的善和真情与传统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变脸》赞美孝义,《非常爱情》描写经年不变的忠贞爱情,《黑脸》则是对包公式的当代清官的一曲悲壮的赞歌。在人情味日益淡泊的当代社会里,这些煽情的影片,带着浓厚的怀旧情绪,借着古典戏曲的流韵,传达出创作者对传统道德的呼唤和对革命理解的执著。
民间戏曲所歌颂的传统道德与吴天明的革命理解在他的影视作品中达到了和谐统一。作为一个老革命之子和有过多年党龄的文艺工作者,吴天明深知父辈从事的农民革命的理想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河流》里好干部徐鸣鹤作为“父母官”“与民同乐”(片中老农语)、同台演戏的欢乐情景,深切表达了吴天明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但正如吴天明的作品中揭示的,无论是十年动乱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假共产党”(盘老五、姜锋语),败坏党风,断送革命成果,令吴天明痛心不已。在电视连续剧《黑脸》中,他塑造了理想化的反腐斗士姜锋的形象,战胜了腐败分子,捍卫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主人公姜锋铁面无私、疾恶如仇、为民作主的鲜明性格,活脱脱是千百年戏曲舞台上万民传颂的包公形象的现代翻版。姜锋说:“纪检干部是包公的脸,猎人的眼,海瑞的脾气,狮子的胆。”将革命的纪检干部所应具备的素质与古代著名清官的个性明确联系起来。姜锋的那句名言:“当官不为民作主就该死,还卖什么红薯啊?”也是对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台词的发展。《黑脸》中众多百姓上“官府”告状、向救星磕头求助、拦路喊冤、递万民折……他们采取的告官方式与古代清官戏中的弱民们无二。清官的强悍与法的无力、人民的软弱是相对应的。清官为民除害、“为民作主”(姜锋语)的壮举,显示着人民还没有依据法律,自己作主的事实;清官作“父母官”、“与民同乐”(《河流》中老农语)、爱民如子的德政,是以人民甘为“子民”的奴化心理作基础的。人民指望集权力与道德于一身的清官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仍是人治社会的封建思想遗风。泛道德化的背景正是法制薄弱的现实。幻想着政治的“君子之治”,不过是创作者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望。古今清官意识与现代民主思想,与马克思的“公仆”观,与《国际歌》的“没有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的境界还相去甚远。
戏曲对吴天明的另一影响是大团圆模式。归国后的作品《变脸》、《非常爱情》、《黑脸》都安排了大团圆结局。这种主人公历经磨难、最终却功德圆满、好人终得好报的大团圆形式,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意识形态的提倡和为传统艺术熏陶出来的大众审美定势,共同保证了大团圆的主流地位。从《讲话》对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问题的一锤定音,到解放后所谓“本质论”对文学艺术界多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主旋律的高扬,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一以贯之。革命文化和民间文化在这一点上有着高度的契合。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恢复五四时代悲剧传统的是80年代从伤痕、反思到寻根时期的一系列文艺思潮。吴天明的创作是从那时起步的,他那时的电影创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的:《亲缘》《河流》《人生》《老井》中有情人均未成眷属,主人公的命运都以死亡、失败、离散、失意告终。真实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使他敢于直面生活,体现了那个时代清醒的反省意识。今天吴天明的创作走向大团圆的结局,既是社会商业化潮流的推动,又是创作主体向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的主动回归。鲁迅先生在论述《莺莺传》这部作品的结局从起初的莺莺被弃到后来变为团圆的情形时指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都知道,但不愿说出来,以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述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到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注:鲁迅著《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吴天明对大团圆结局的设置也包含着这种无奈,他似乎已没有勇气去揭生活的疮疤,而更愿意在脉脉温情中抚慰自己饱经磨难的心灵。而这种选择迎合了主旋律的要求和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
民俗与家族本位观
民俗是民间文化的活的标本,有学者曾论及乡土小说与风俗描写的关系:“几乎每一部新时期的乡土小说都浸润着风俗画的浓墨重彩,有人把它说成是乡土‘文化小说’,则是因为它们总是通过风俗人情的描写来透视出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注:丁帆著《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第19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同样, 西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突出的地域特色形成80年代影坛最有影响、最具文化意味的流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色的“风俗画描写”及其这种描写中透视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西部电影的另一大创作群体第五代导演们不同,吴天明从不造“伪民俗”,而是力求真实地、以生活的本来面貌展现民俗,不带很强的主观意念。然而,无论主观性的表现还是客观性的再现,“民俗在反映人生的文艺作品中,都不是镶嵌于人生的简单饰物,而是沉淀于人物内在心理结构、又显现于人物外在行为方式的永恒伴侣。”(注: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第8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婚丧嫁娶从来是民俗集中演出的舞台。吴天明的农村三部曲里都拍了婚礼的场面。在《河流》里,爱花苦苦等待盘老五时,一支娶亲的队伍从她身后走过。吴天明在一个镜头里安排了三个空间:窥视的盘老五、等待的爱花、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婚仪背景的设置使一个无言的镜头包容了大量的信息:它令人联想到二人定情时的情景,衬托了主人公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凄楚心情。悲喜的反差给影片造成了张力。在《老井》的街道上,进行着一场粗俗、原始的婚礼仪式:一群人将新娘、新郎硬抬到桌子上叠压在一起。巧英厌恶地看着,一转头发现俗气的照相摊上,旺泉和喜凤正在媒婆的张罗下拍结婚照。旺泉穿着喜凤置办的规规矩矩的新郎装,与山上那个潇洒、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判若两人。旺泉的窘境和背景中野蛮的婚礼场面同时出现,令人自然联想到旺泉这场婚姻的悲剧性质。
被推到前景上大肆渲染的是《人生》中巧珍的婚礼。 这场戏长达8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在鼓乐欢腾的场面里,加林送的纱巾成了巧珍头上的婚纱,因而巧珍的主观镜头毫不造作地变成了惨烈的红色:高加林的家院、留下他们相恋时无数遗迹的坡坡梁梁……红衣的巧珍本人则像祭坛上的牺牲。她默默地向浪漫青春告别,祭奠自己刻骨铭心、此生不再的爱情,婚礼反成“葬礼”。透明的红巾上那一滴晶莹的泪,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老井》拍了两次丧葬场面。第一次是为被炸死在井下的旺泉爹举行的葬礼。棺材夸张的血红色,令人想到老井人血的打井史。在这口棺材面前,万水爷再次给旺泉施压:“你和喜凤的事,你爹他答应人家了。”旺泉耷拉下眼皮:死者的遗愿、家庭的重负,最终迫使他放弃了个人的爱和幸福,他认命了。红棺材幻化出的那轮挣扎而出的初日,在颤抖的管乐声中,正像旺泉那颗滴血的心。第二次葬礼是为被压死在井下的“亮公子”举行的。棺中旺才的脸被纱布缠满。旺才妈把独子的爱物一样样放在他身边:《爱情诗选》、有美人头的电影画报,让人想起旺才生前的所作所为,平日那些可笑荒唐的行为在这里一下子显出了合理性,体现着作为人所应有的正当的欲望和追求,这个“连女人味儿都没尝过”的年轻人的牺牲令人格外痛惜。
除了表现大场面的民俗,吴天明还注意挖掘日常风俗生活中的意蕴。如旺泉倒尿盆的情节。“在北方山区,上门女婿倒尿盆是一种风俗习惯,它表明了传统观念中上门女婿地位的低下。”(注:罗雪莹《老井边的对话——吴天明谈〈老井〉的创作体会》,《吴天明作品集》第242页,华岳出版社,1989年版。)吴天明通过三次倒尿盆的细节,生动刻画了旺泉心理发展的几个历程:第一次是在旺泉抵挡了几日,最终与喜凤作了名副其实的夫妻之后,极其尴尬地端起尿盆。表现旺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开始了只有义务、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第二次的背景则是旺泉在与巧英共同勘探井位的过程中重燃爱情之火,于是借拒绝倒尿盆之由,试图摆脱这个屈辱的婚姻;但喜凤怀孕的事实,又一次扑灭了他反抗的念头,他只得再次端起尿盆;第三次是在旺泉经历了井下与巧英的生死之爱之后,回到了段家,生活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他已没有勇气割舍一切,很自然地继续端起尿盆。三次倒尿盆显示了旺泉从无奈到反抗再到顺从的“俗”化过程,他一步步地走向与传统的融合,越来越深地扎根于太行山中,以至无法拔身。在旺泉性格中,时代精神与民俗传统交织冲突,使得这一形象达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性”有机结合的境界。
吴天明电影中大量的民俗描写都传达着一个主题——个人价值的牺牲。所有的婚礼都拍成了悲剧性的,或是主人公无奈的选择,或是衬托人物的悲剧境遇。丧礼上死者已逝,而他们的遗愿正在迫使生者为群体的利益继续做出牺牲。日常的风俗也表现了当代青年如何一步步放弃对个人理想和幸福的追求,渐渐融入千百年稳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世俗以它那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裹缚着吴天明影片中的男男女女,迫使他们放弃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来维持家族——社会的延续和稳定。这是吴天明的电影人物摆脱不去的宿命,是以血缘家族为根基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本质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革命文化的主流意识。
可以说,是否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一条分界线。李泽厚指出:“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个人本位主义’与‘家庭本位主义’的差异和冲突,恐怕还是其中的要点之一。前者认个体为社会的基础,强调个人权力、公平竞争、契约关系、私有财产、公和私的区分等等;后者认群体为社会基础,强调伦常关系、个人义务、等级秩序、家国一致、公私一体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的‘革命传统’倒与固有的这种传统大有一脉相承处,仍然是集体、义务、合作……高于个体、权力、竞争……因之两者的差异和冲突在今天便日趋尖锐。”(注:李泽厚著《再说“西体中用”》,见《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作为一个深受革命的民间文化熏陶的艺术家, 身处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这种尖锐的冲突必然深刻地影响着吴天明的创作的心理,也必然鲜明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当他真实地描写传统观念和现代社会潮流的冲突,揭示人物在这一冲突中的挣扎与痛苦时,他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有一种悲壮的艺术感染力;然而当他站在传统的卫道立场,以旧有的价值观来裁判人物和事物时,其创作观念和作品意蕴就流于陈旧和肤浅。
农村青年高加林落难回乡,在高原上自虐般地挥镢挖地,把双手磨得稀烂;德顺爷抓起一把黄土按到他的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于是,高加林的血就和黄土融到了一起。《人生》中的这个镜头颇具象征意味:吴天明就是这样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黄土地紧紧连在一起的电影艺术家。黄土地博大而温暖,源源不绝地为他提供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它又是落后而愚昧的,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的精神世界。吴天明创作的复杂性在他这代艺术家中是具有典型性的。革命——土地——人民是他们终身不变的情结,“革命的民间文化”融会着他们强烈的生命体验,给他们的创作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