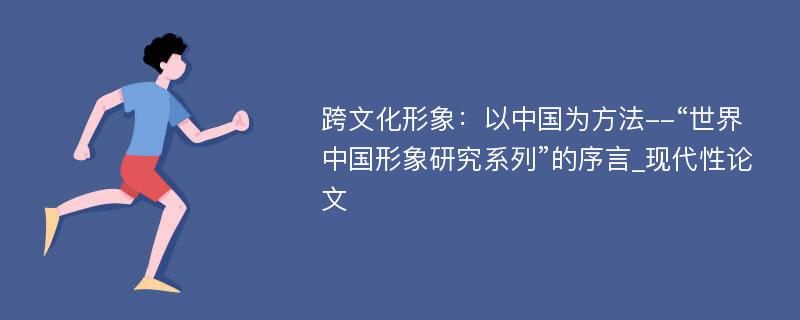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象论文,丛书论文,跨文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第一组课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第二组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丛书具有草创意义;第三组课题则有待开启,那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
第一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1)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2)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3)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机制。
第一组问题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本套丛书也有所推进。笔者曾经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在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西方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决定着1250-1450、1450-1650、1650-1750年三个时段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对中国的表述策略。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构筑起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意义,同时设定停滞、专制、野蛮的中华帝国的“他者”形象。只有在中华帝国甚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停滞背景上,才能确认现代西方、现代西方的进步与现代西方在世界历史中优越中心的意义;只有在中华帝国代表的整个东方专制主义黑暗大地上,才能为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只有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野蛮性”的映衬下,才能充分展示、全面肯定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将有关中国的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现代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的幻象空间,并从启蒙知识向帝国权力领域分配。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西方问题”也有“中国问题”。“西方问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跨文化实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为西方现代性经验提供了自我确证的想象资源。西方现代性形成于跨文化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性自我,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中国问题”是西方现代性想象构筑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的传释与自我东方化想象①,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进而影响现代中国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方向与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学领域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识形态或社会无意识意义上形成“互为主观性”与“互相他者化”的关系?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已经延伸到我们的三组课题的第二组与第三组。
第二组课题更进一步,研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形象,它涉及三方面的问题:(1)世界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自身的特色与传统;(2)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的关系网络;(3)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实践中的权力结构。三方面的问题逐步深化细化,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色与传统本身,只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跨文化的中国形象流动的结构性联系,某种中国形象的“世界体系”。第二方面问题在于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关系网络中的多向性关系,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有其自身的视野、关怀与传统,同时又由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受其他相关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复述”或“反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如日本的“东洋”观念下的中国形象,在上世纪前半叶对亚洲某些国家的中国形象有支配性影响。当然,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掌握着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其影响的范围与程度,决定于该国的文化国力。地区性大国可能影响该地区的中国形象,全球性大国则可能影响全球的中国形象。第三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叙事中的主宰力量,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不仅可能彼此影响,而且,可能受到某种跨文化霸权力量的宰制,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中国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受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支配,反思“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的过程与方式,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本套丛书关注的正是这第二组课题。近年来,学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视野内越来越多地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但是,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不仅应该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应该重视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否则,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维面与多元意义语境,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布莱·特纳在《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一书中指出,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关键在于,超越西方视野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东方主义到全球主义,或用多元化的全球主义取代东方主义/西方主义,这样不仅破除东西方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偏见束缚,也要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偏见②。
带着这种全球主义视野与期望进入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思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表征与流动,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的特征与表现方式。他们如何、在什么知识领域或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形象?他们与中国构成一种什么样的想象的文化关系?如何在中国形象中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彼此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共同性或导向性?这种共同性或导向性是否潜藏着现代性赋予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现代世界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不同地区文化,这些地区/文化圈中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多有自身的视野与传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特征。不仅大的文化区域内的中国形象彼此不同,比如说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与阿拉伯的中国形象不同,其关注点、基本特征、评价尺度都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文化传统内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也由于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战略而不同甚至相反,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同处东南亚地区,同为回教国家,同样有大批的中国移民,同样处在建国时代,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形象就完全不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彼此不同,但在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又相互关联,甚至隐含着某种跨文化的话语霸权。比如说,发起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正在世界不同文化区或国家传播,它一方面表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某种同一化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不同文化区或国家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其特有的现代性焦虑与期望。
开展世界不同文化区或民族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才具有了真正的全球化意识。而真正的全球化意识不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批判精神或问题意识。我们一方面注意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差异结构,另一方面也关注它们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表现出的越来越强烈的同一化倾向。这种同一化的内在结构究竟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有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规训的痕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日本或印度、阿拉伯或东南亚、拉美或非洲,都难以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或东方的西方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中国形象都成为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研究世界的中国形象的实质性的问题,就难以回避世界的中国形象如何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问题。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正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纵,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
第二组课题的意义在于,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必然面对所谓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建构的跨文化流动的形象网络。从这一研究假设出发,前景似乎是开阔的,但研究深入的境地,却越来越窘迫。因为现代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经常表现出一种同一性文化霸权趋势,这种文化霸权便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尽管我们在研究中不断发现不同国家地区中国形象自身的传统或一致性,但当这些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历史后,它们的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浸染或“形塑”。现代性精神结构赋予西方一种知识与价值制高点的优势,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自我想象与中国形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渗透着“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因素。于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将逐步聚焦到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问题。而表现这种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的文化方式,便是非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问题。
所谓“自我东方化”,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③。西方人规划的世界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同时向非西方世界推进,加入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在被迫接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后,也在文化上相继主动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东方化”过程。当然,本人认为,这个“自我东方化”的过程,还包括三方面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1)非西方国家或地区认同东西方二元对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认同为此世界观念秩序奠基的进步/停滞、自由/专制、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与西方现代进步、自由、文明的优越性,认同现代西方文化霸权下自身低劣的他者地位;(2)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在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中开始自我批判与文化改造的历程,努力地“去东方化”,出现两种极端倾向:彻底否定自身传统彻底西方化,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发挥所谓“东方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中都同时包含着认同因素与反抗因素;(3)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去东方化”,不仅构筑了一种“东方”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还同时构成“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过程中还包含着“东方”内部的“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东方”国家中究竟谁更“东方”,谁比较“西方”,也是“东方”国家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根据④。
所谓“自我西方化”,是“西方主义”概念的延伸。伊恩·伯鲁马和阿维赛·玛格里特在《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一书中,将东方的自我东方化以及对西方的回击或报复性想象称为“西方主义”⑤。西方主义是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一套虚构与言说“西方”的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敌我意识,其否定性的西方形象往往表现出四种典型的象征意义:(1)现代腐败贪婪漂泊不定的城市生活;(2)败坏传统世界纯正道德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商人;(3)只强调科学理性、否定人类美好的信仰;(4)狂妄的不信神的人终将毁灭世界与善良的人。西方主义论者强调西方主义的“怨恨情绪”与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但笔者认为,西方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积极进取与温和理性的内容。非西方国家或民族对西方的美化与西方化的自我想象,也属于西方主义的一部分。正如有两种东方主义⑥一样,也有两种西方主义。而且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是相互关联相互交换的,存在着所谓的是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关联区域”。西方主义不仅从东方主义中浪漫的东方情调中汲取自我肯定的资源,也从东方主义中西方自我肯定的思想资源中确立自己的现代化方向。它涉及现代世界最有建设性的跨文化实践,最完整地表达这种跨文化实践境界的术语应该是“东方—西方主义”。
第二组课题的意义来自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解构中西二元对立的立场上,对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深入的反思。域外的中国形象是一面多棱镜,但遗憾的是,这个多棱镜总是折射着“西方之光”。带着第二组问题进入第三组问题,那便触及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
第三组问题与前两组问题密切相关,但更有意义也更有研究潜力。它直接关注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重大问题: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西方的中国形象支配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西方现代性想象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思想转换成现代中国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域与问题框架。繁荣与进步、自由与民主、启蒙与文明等等,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与方法,都变成西方的,这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关注的自我东方化问题。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必然延伸到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自我形象的回馈性影响问题上,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世界现代化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危险与诱惑⑦。从停滞衰退、东方专制、野蛮半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到剧烈变革、动荡危险的现代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在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但是,变化的是中国形象的特征,不变的是构筑中国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具有历史连续性活力的话语构成原则。在这种文化霸权中,现代中国看得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却看不到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身份。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不论“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而这种霸权真正令人生畏的是,你无法不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思想中国,除非你放弃思想。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是否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如何从思想中拯救中国的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还不仅是柯文先生所说的“从中国发现历史”的观念的选择,更直接地是对西方的中国思想的解构,分析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的中国话语的生产分配并发挥文化霸权作用的方式与意义。
世界的中国形象课题假设现代中国自我认同的多重维面与多重意义。我们在与“西方”构成的强暴性的、自恋式的想象的认同关系中,才能找到现代中国的自我。不幸的是,我们面对“西方”在强暴性的、自恋式的想象的认同关系中建构现代中国自我的困境,同样出现在我们面对全球化世界其他镜像他者的处境中。表面上看,全球化时代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从中中国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那么,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则是个多棱镜。在多棱镜中认同现代中国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建构是发现现代中国自我的意义的丰富性,解构的功能则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认识到镜像认同的虚幻性与异化。但实质上的问题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纵,多元化的世界的中国形象,往往最初来源于西方并最终归结为西方。
二
本丛书关注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的第二组课题——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全球化中国形象网络形成的过程与方式。
研究世界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文化区。国家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但人们对文化区的理解则有所不同。现代世界的文化地图可以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八大文化区相互关联、相互之间又有中介过渡带,同时又各自具有共享的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纽带。八大文化区分别是:(1)具有所谓资本主义经济、代议制民主政治、基督教信仰加启蒙哲学三大文化特征的西方,包括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2)地跨欧亚大陆、具有欧亚主义传统与东正教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历史的俄罗斯;(3)历史上属于东亚汉字—儒家文化圈、现代成功“西方现代化”的日本与韩国;(4)印度文化影响的、信仰多元、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的南亚地区;(5)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传统的、地处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6)叠加着华夏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地理整一性多于文化整一性的东南亚;(7)格兰德河以南、讲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信奉天主教的拉丁美洲;(8)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文化区未必是地理上连接体,移民或殖民造成的人口流散也可能构成跨地域的文化区,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语言与信仰、观念与习俗、制度与传统上届于西方,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都属于伊斯兰教文化的边缘区。当然,任何文化地图都存在着模糊性,同时,在该项研究的起始阶段,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文化区的国家民族的中国形象做更细部的研究,只能选出不同文化区代表性的国家做典型,兼顾评述该文化区中国形象的一般特征。
世界八大文化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与中国有着不同的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历史。我们以九个专题分别讨论“世界的中国形象”。这九个专题是:西欧的中国形象、美国的中国形象、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印度的中国形象、日本的中国形象、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阿拉伯的中国形象、非洲的中国形象、拉丁美洲的中国形象。设立这九个专题的考虑在于,或者是某一大文化区的中国形象传统具有丰富的差异性,有必要区分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地区或国家,如同属于西方的中国形象,我们划分出西欧的中国形象、美国的中国形象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或者某一个文化区中某一个国家的中国想象具有典型意义,意义丰富而传统深厚,可以代表该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如日本的中国形象之于东亚、印度的中国形象之于南亚;或者某一个文化区的中国形象具有整体性特征,又难以找到一个具有想象内容的丰富与深刻性的代表性的国家,如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阿拉伯的中国形象、非洲的中国形象、拉丁美洲的中国形象。
研究世界的中国形象还是首先面对西方。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这一时代命题的起点。西方是一个文化概念,指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基督教地区。西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界域,广义的西方可能包括整个欧美,狭义的西方则仅限于西欧与北美。我们在西方的概念下分别讨论西欧、美国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主要考虑有三个方面:(1)西欧是整个西方的原发地,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其中国形象已形成自身的意义系统,拥有丰富的认知与想象资源;(2)美国尽管只有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形象的历史,但20世纪以来却影响逐渐加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话语权;(3)俄罗斯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决定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在意义、问题与方法上都不同西欧北美。
西欧的中国形象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从虚无缥缈的“丝人国”传说开始,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大中华帝国”,中国形象从神话进入历史。以启蒙运动为界,西欧的中国形象分为两个阶段;此前西欧的中国形象出现了三种话语类型,“契丹传奇”式的中国、“大中华帝国”式的中国、“孔教乌托邦”式的中国,有不同的意义,也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与发展趋势,那就是在不同层面上,从物质到制度到观念,不断美化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现代性社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此后出现的三种话语类型带有明显的否定意义,中华帝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中华帝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华帝国是文明秩序的“他者”——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的启蒙“宏大叙事”中,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西欧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学科的深度观念史研究,而且是对西方现代观念史的研究。它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
不同文明区域或国家的中国形象,有不同的问题,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主体文化本身。李勇教授认为,西欧的中国形象是西欧以想象为具体方式的表意实践活动,形象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就是对不同类型的形象进行文化文本解读,揭示表意实践过程的基本状况和形成机制,探寻潜隐的原因。要完成这样的解读工作至少需要三个环节:首先是研究立场的确立,即文化研究中常用的“表征分析”的立场。那些塑造中国形象的西欧文本即在掩盖着他们的意图(可能是无意识心理)也同时昭示(揭示)着那些意图的存在,就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真相就在那里”,就看我们有没有眼力,有没有看透它的视角或立场;其次,西欧的中国形象作为供解读的对象是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形成的,每一种中国形象都与其他类型的中国形象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要解读这些中国形象就必须清理出这些中国形象类型的代表性形态。形象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亲缘关系,它们都是把文本放在历史语境之中解读。因此,西欧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建立起完整的历史叙述之后,就可以清理出在西欧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形象类型,以及它们在历史上呈现出来的代表性形态是什么;最后,研究西欧的中国形象,确立分析的立场和清理中国形象的历史形态都要落实到对形象形成机制的解释上,说明一种中国形象是如何从一个个具体文本转换为集体想象形象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符号运转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首先对形象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一个具体的形象分解成具像、侧像、全像、类像和型像这几个层次/要素,从文本到形象的转换首先就是这些形象要素之间的从最直观的具像到隐蔽的型像之间的纵向转换。当然,这种纵向转换又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完成的,各种现实因素又会介入进来,构成从文本到语境的横向转换。这两个方向的转换是分析形象形成机制的基本框架。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8],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其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其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又如何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不同于西方汉学研究,也不同于比较文学,在研究对象、前提、观念与方法上,均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学界研究西方汉学者,也频繁使用“中国形象”。实际上这种有意无意地混淆概念,在研究中是有危险的。西方汉学的意义在于假设它是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如果使用中国形象研究取代汉学,那就假设汉学的意识形态化,其知识包含着虚构与想象,协调着权力,因此也无法假设其真理性。笔者曾写过《汉学或“汉学主义”》⑨一文,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质疑汉学学科的合法性并尝试进行解构性批判,希望学界警惕学科无意识中的“汉学主义”与“学术殖民”的危险,基本用意也正在于此。西方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知识问题,而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以及渗透知识与想象的权力运作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一般社会观念意义上研究中国形象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文本,从一般社会科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专业的汉学研究、诸如新闻报道、游记、传教报告、日志等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有关中国的外交等官方文件,一直到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诸如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在研究对象上已经超出汉学或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围。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与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满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只意识到研究什么,没有反思为什么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来就不是汉学、也不仅是比较文学的问题,而更多与跨文化研究相关,揭示形象隐含的文化政治意义。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没有问题的学科,而跨文化研究形象学,是没有学科的问题。比较文学形象学仍然是文学研究,而跨文化研究形象学则首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思想性挑战及其开放性活力,也正体现在这种跨学科性与非学科性上。
西方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主导着中国形象的话语权,14-15世纪是意大利,16-17世纪是西班牙与葡萄牙,18世纪是法国,19世纪是英国与德国,20世纪则是美国。20世纪美国的中国形象不仅影响西方,甚至也影响整个世界。这也是美国文化霸权或软实力的表现。美国不同于西欧,有自身精神的期望与焦虑。美国是20世纪的“中央帝国”,对中国这个衰落的“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英国在19世纪自觉到“拯救”印度,美国在20世纪自觉到“拯救”中国。他们起初坚信中国将被改造成一个顺从并感激美国的经济上开放、文化上基督教化、政治上民主的美国式的“藩属国”。20世纪前半叶的“恩抚”,后半叶的“遏制”,表现出美国特有的“中国情结”的两个极端。美国的中国形象是耐人捉摸的,经常是爱恨交加:一方面是“恩抚主义”,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另一方面是“遏制主义”,把中国当作一个背叛的、邪恶的、危险的、不可思议的国家,内心充满不确实的恐惧与仇视,从“黄祸论”开始,一直到“中国威胁论”。20世纪美国的中国形象反复无常,具有某种精神分裂的特征。
异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强大时,塑造者往往将其纳入视野的中心,多采用仰视视角,以仰慕的态度把对方放在重要位置,用理想化的形式来描述对方,同时赋予其强大、先进、发达、进步、文明等特征。相反,当被塑造者比塑造者贫弱时,塑造者倾向于将其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俯视视角,以轻视甚至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对方,趋向于用低劣、愚昧、落后、贫穷等词汇来描述其特征。美国曾和欧洲一样,有过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历史,但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将自己作为中心,以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丑化中国,使中国形象带上明显的漫画特征。姜智芹教授探讨美国的中国形象的著作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梳理、分析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期美国之中国形象的流变,阐释美国是如何对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进行想象和认识的,以及在这种想象和认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探讨中国在美国现代性自我构建中的意义。第二大部分分为三个专题,以个案的方式,分别论述“美国文学”“好莱坞电影”“传教士儿女们”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和塑造。第一部分是面上的讨论,第二部分是点上的分析。研究美国有关中国形象,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美国价值观的认知,也促进了我们对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在国民性批判和现代性文化自觉方面。
俄罗斯是另一个西方,如果说美国是西方中的西方,俄罗斯则是西方中的东方。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传说可以上溯到12世纪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中提到的国家“希诺瓦”和“契丹”,但清晰的中国形象要到17世纪俄罗斯的使节出使清朝和18世纪西欧的“中国风”东渐俄罗斯。此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出现了三种套话:“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兄弟之邦”。“哲人之邦”的形象类型出现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启蒙思想中美化、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进入俄罗斯。现代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多受西方的影响。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同样在俄罗斯思想界获得反响。俄罗斯文化界,不管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是一致:中国形象从道德高尚、制度开明的“哲人之邦”转向停滞腐败、专制无能、野蛮堕落的东方帝国。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素来与俄罗斯帝国特有的文化政治传统相关,是俄罗斯文化身份确认与地缘政治想象的产物。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贯穿俄罗斯历史的扩张主义思想与激情。“衰朽之邦”是现代俄罗斯扩张主义思潮的产物,分享着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想象;而苏联时期的“兄弟之邦”形象,则是“红色帝国”苏联的全球战略格局的想象性实现,甚至继承了“第三罗马”与“斯拉夫帝国”的文化传统。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敌意,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但在这种不能轻易否定其真诚的“兄弟”想象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那种“我是兄,你是弟”的文化政治霸权的无意识。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自身的历史与问题。首先,俄罗斯思想是在面对强大的西方他者进行自我确证时想象并引述中国形象的,于是,中国形象出现在俄罗斯思想中,任何时候都是与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相对立的他者形象,没有独立的他者意义。一个特殊的文本现象就是俄罗斯思想总是在与西方形象对比时讨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家的言论中,中国形象不断出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论题下。中国形象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而取决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其次,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不仅是俄罗斯的西方形象的派生物,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派生物。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思想资源完全来自西方。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是俄罗斯思想总在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忽略俄罗斯本土的中国信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折射,是中国映现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的他者形象。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构成俄罗斯文化自我确认的东西方两极,但这两极远不平衡。再次,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形象并不丰满深厚,俄罗斯思想通过中国形象构建俄罗斯自我的想法也不认真。中国形象包容在西方形象之中,不论是意义还是价值,也都无法与西方形象抗争。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思想中,实际上不可能构成与西方相抗衡的对等的两极;俄罗斯思想试图在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之间谋取自我确认的平衡,实际上也不可能,俄罗斯身份依旧会划入巨大的西方。此外,俄罗斯思想试图利用中国形象超越西方的东方主义,但又陷入俄罗斯式的东方主义。西方式的东方主义是排斥性东方主义,东方是一个不断蔓延令人无法捉摸也无法控制的他者;俄罗斯式的东方主义是包容性的东方主义,东方是一个不断被收复被涵化的他者,因为俄罗斯本身深广的东方性使东方可能被包容到自身。俄罗斯式东方主义包含着更危险的文化霸权,它从根本上趋向于取消中国形象的意义。最后,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总体上看浅显暧昧,这是由俄罗斯文化自我本身的暧昧性决定的。从西方看俄罗斯,俄罗斯是东方;从东方看俄罗斯,俄罗斯又是西方,这种分裂的二元性使俄罗斯文化的自我想象左右为难,既沮丧又傲慢。没有明确的自我便没有明确的他者。
三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以某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性身份的自我认同。现代中国首先在西方的镜像面前确认自我,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现代中国不断从这个虚幻的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自我构建的过程同时成为自我异化的过程,认同与其说是确认,不如说是误认;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一种主宰叙事,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他们的中国形象生产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自我东方化”或“自我西方化”叙事的一部分。
印度与中国领土相邻,文明相关,历史上已有两千多年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但直到现代之前,印度一直没有清晰的中国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中国成为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美好的中国形象在印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后是战争,印度的中国形象急剧转化。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敌意与社会冷漠。印度与中国从“和平共处”到“敌对共处”,三十年间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总体特征是政治敌意与社会冷漠。印度的中国形象全面复制西方冷战思维下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好战的暴政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敌人。这种充满敌意的中国形象多少显得轻率武断,它在政治上表现强烈,但社会影响微弱。印度一般社会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依旧模糊不确定。这个时代印度的中国形象有三大特点:一是充分政治化,中国形象是印度国家政治战略刻画的,充满敌意,但又缺乏现实性;二是充分西方化,印度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复制西方冷战时代的中国形象,其中缺乏印度的主见与立场;三是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仅流行于政治领域中,在民主制度下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影响既不广泛也不深入,印度社会或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中印崛起”的大时代里,人们很难找到确定明晰的中国形象。印度媒体塑造的“中国”让人将信将疑、喜忧参半,“中国崛起”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虚构;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成就,它为东方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另类现代性的证明;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威胁,打破了既定的世界现代政治秩序与知识秩序。中国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印度现代性自我认同。
研究印度的中国形象,有四个明显的问题值得反思:第一个问题是,印度与中国有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丝绸西去,佛陀东来,但印度的中国形象,除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之外,基本上是个空白。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如何理解这种冷漠,跨文化形象生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什么是那个时代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想象关联?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印度突然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热情,而且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诗人如此,政治家更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或政治冲动,使中国在印度想象中突然变得重要而美好起来?长久的冷漠与一度的热情究竟缘何而生?中国形象在印度现代文化自觉中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在过去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的中国形象先是逐渐被美化,充满政治浪漫热情,后是突然转化,丑化的中国形象表现着新生的仇恨与久远的冷漠。值得注意的不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中的敌意,而是它的“随意”。意识形态的中国形象与一般社会想象的中国形象断裂。1962年的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否还有比战争更深远更内在的文化原因?第四个问题是,冷战结束,中印崛起,在敌意即去未去、善意将来不来的时候,冷漠依旧。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一切都为什么?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已经失去了思考对方的意愿与能力?难道只有西方在思考世界,而我们只思考西方并模仿西方思考?
研究的自觉,不仅要描述是什么,还要分析与解释为什么。这是理论的“理论性”所在。跨文化形象学假设在三层意义上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一是该国或该地区历史上不同时代关于中国的认知与想象,它关注的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知识的局限与积累问题;二是该国或该地区关于中国的知识或想象与现实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关系,它关注的是该国或该地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又如何影响其现实关系方面的问题;三是该国或该地区文化自我确证中的中国形象的意义,它关注该国或该地区文化如何使用中国形象作为他者完成自我认同或自我确证,中国形象与其自我想象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第一层意义是知识论的,关注认知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问题;第二层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关注国家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第三层意义是话语理论的,关注文化身份确证中自我与他者的知识与权力关系问题。
学术思考回应时代重大问题,不论就历史、未来还是现实而言,研究俄罗斯、印度、日本的中国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多少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发展的命运。现代日本的中国形象,是日本现代性自我认同中“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双重叙事的一部分。日本曾有“唐风一边倒”的时代,现代中国形象的转变是极具戏剧性的。首先是所谓“脱亚入欧”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东亚古国支那、朝鲜与日本,前二者“不思改进之道”,守旧堕落、愚昧野蛮,日本“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⑩。日本的现代化就意味着摆脱中国与朝鲜之类“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与西方现代国家共进退。在“脱亚入欧”论背景下,日本构筑的中国形象显示出种种半开化文明的停滞衰败、专制残酷、愚昧野蛮的特征。福泽谕吉彻底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学与仁政,儒学守旧迷信,是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仁政与暴政都是东方专制政治形式,建立在奴役与愚昧基础上,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野蛮的暴政”,后者是“野蛮的太平”(11)。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福泽谕吉欢呼这是一场文明征服野蛮、光明战胜黑暗的战争,所谓“文野明暗之战”。福泽谕吉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中国文明,到津田左右吉那一代冷酷轻蔑的文化批判主义,则进一步从历史与思想根源上否定中国,认为道家不过是逻辑混乱、思想浅薄且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儒家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思想幼稚而虚伪,为中国社会积时历久的身心奴役提供了信念基础。“脱亚入欧”论直接导致“大东亚共荣”的战争意识形态。战后竹内好先生在检讨日本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所谓“近代的超克”观念时,详细分析了现代日本表述这场战争的宏大叙事来自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是所谓“世界史的必然”(12)。
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西方的文化霸权不可否认也难以摆脱。现代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有关中国的严肃认真的思考,都与这个民族面对西方文化进行自我想象与自我塑造的“文化自觉”相关。日本现代的中国形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战前基本上是否定的、批判的、蔑视的,在低劣的中国形象中,日本现代文化获得自我确认与自我满足,当然,这种文明优越感或自信心并不来自日本本身,而是来自于现代西方。二战结局是日本战败,中国革命成功,日本从中反省到日本现代文化脱亚入欧的困境与中国革命开创的亚洲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前景。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一度发生转变,日本知识界开始反思日本的中国形象,典型的代表是竹内好,开始将革命后的中国当作东方“超克”西方现代文明的可选择的模式(13)。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在批判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14)。中反思竹内好代表战后日本的中国观,竹内好等人依旧在东洋与西洋二元对立的结构上讨论问题,那个东方的东方主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亚洲国家是否可能以自身为尺度想象他者确认自我?是否还真正存在着所谓东方价值或亚洲价值?难道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将不同国家的文化关系最终归结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西方发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总是一方面将西方当作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强势他者,另一方面在非西方国家中建构所谓弱势他者。战后日本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很快就过去了,中国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建设历程却充满动荡与混乱,相反,失败的日本却迅速复兴,经济的飞速发展恢复了国家自信也恢复了日本近代以来被轻蔑否定的中国形象,传统的“脱亚入欧”论也复活了。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个多世纪以后,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他的《别了!亚洲》。在该书“前言”中他明确表示“日本已经不再是亚洲的一部分了。日本已经成为‘高耸在梦之岛之中的霞关大厦’。周围的亚洲各国是‘梦之岛’(东京的垃圾场),而日本则是耸立于中央的超现代化大厦”(15)。
我们提出“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论题,其意义在于探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多元国际文化环境以及现代中国自我认同的多重维面与多重意义。“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拥有整体性思考视野,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1)世界不同文化区不同国家中国形象的特征与意义;(2)它们彼此之间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与权力方式;(3)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与现代中国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与形象网络已经形成,具有快速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机制。在这一跨文化流动与分配的中国形象网络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常构成生产之源,决定或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这些国家或地区首先在确认他们自身与西方的关系,然后再从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立场选择中国形象。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拥有的话语霸权值得关注,这不仅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问题,也是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现代俄罗斯、印度、日本想象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形象总是出现在其“自我东方化”或“自我西方化”的文化想象中。在西方发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总是一方面将西方当作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强势他者,另一方面在非西方国家中建构所谓弱势他者。中国形象的意义往往并不取决于中国,而决定于西方,决定于这些国家面对西方进行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方式。中国与西方往往成为他们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双重他者,出现在他们的世界知识与价值的两极。
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它不仅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多少决定着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全球话语权上。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日本乃至东南亚、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叙事的一部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俄罗斯、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更不必说那些思想文化传统不够丰厚坚实的小国。东南亚是个复杂的文化区域,十个国家分布在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地处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交汇处,近代以来又受西方文化冲击。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表现出特有的多样性,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政治背景,中国形象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几乎难以在一个论题下讨论。而且,宋明以来大量中国移民移居东南亚,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不仅是庞大的大陆国家中国的形象,也是身边邻里华人的形象,国家、种族、阶级、信仰等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任何整体性研究都难以进行。
前现代的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零乱而模糊。不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地区没有清晰的中国印象,而是这些印象缺乏史料证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历史因缘深厚,中国形象甚至可以追溯到这些国家先民的神话传说中,缅甸《琉璃宫史》、马来亚的《马来纪年》都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泰国、菲律宾等国也可以发现类似记载。越南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多,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形象也更丰富更现实化、历史化。但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才具体明晰起来。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20世纪前叶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中国是亚洲觉醒、民族革命、国家解放的象征。这种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当地华人,他们对现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亚细亚主义的介绍,影响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事业。最典型的是印尼,苏加诺曾经坦言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灵感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孙中山是“最伟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自1918年,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已深入我心”。苏加诺在泛亚洲主义基础上想象中国,其思想背景与倾向令人想起当时印度泰戈尔、尼赫鲁那代人。中国与印尼是分享着“亚洲共同性”的“东方兄弟”。正如苏加诺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中所表述:“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为亚洲人民共同的遭遇必然会产生共同的行动;共同的命运必定产生共同的情感;在抵抗大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埃及、印度、中国、印尼人民面对同样的敌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泛亚洲主义原则的原因。”(16)
现代东南亚的中国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转变,曾经作为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兄弟的中国成为冷战中共产主义威胁的代表。东南亚国家一度在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中认同中国美化中国,印尼独立后曾经将中国当作国家建设的典范,苏加诺1956年的中国之行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民族主义想象的“亚洲共同性”,被冷战意识形态拆解,19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形象纷纷“恶化”,中国成为共产主义恶魔。印尼在苏哈托时代甚至与中国断交,冷战几乎促成整个东南亚与中国的反目,马来西亚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政治传统,选择冷战的反共阵营,东姑政府主导的中国形象,是贫困、独裁、缺乏宗教自由、以共产主义强权方式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邪恶可怕的形象。这种形象有马来西亚本身的背景。马来西亚是新加坡以外华人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东南亚国家,而且还有马共在丛林长期坚持反政府的游击战争,选择与中国敌对是马来西亚的政治需要。东南亚的中国形象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可能既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又是身边的华人的故乡。如何才能将中国与当地华人区分开来,这是个微妙而危险的话题。民族主义思潮从思想本质上认可作为亚洲兄弟的中国,但不能认可华人移民居留在东南亚国家;新国家政治从国家安全与权利竞争上可能排斥中国,但却在国家认同上接受当地华人,东姑的说法很典型:“华人必须把这个国家视为他们的家,而不是暂居地,或者更糟糕的是仍把它当作另一个中国,因为已经有这么多个中国。主要的是有8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是1600万人的中华民国(台湾),然后是500万人的香港,以及大约200万华人的新加坡。因此忘掉中国,记住把马来亚作为已经给予我们生活中所有美好东西的地方。如果所有的华人都这样想,我本人绝不相信有任何理由去担心我国的未来。”(17)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形象直接关系到其国族认同与建国理想,其中国想象一直处在某种紧张与焦虑状态。中国形象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意义。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是个充分“中国化”的地区,现实中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约舒亚·库兰奇克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改变世界》(18)强调,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大有取代美国之势。虽然不无危言耸听的嫌疑,但也确实注意到某种倾向。东南亚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点,中国是否能够重建西太平洋核心国家地位,决定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中国与东南亚,而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目前东南亚出现的隐约的“中国威胁论”,真正的源头是来自美国的警惕或忧虑。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不可回避地缘政治战略背景,跨文化的中国形象问题在后殖民与后冷战时代提出,对“中国崛起”有着严峻的“大国战略”意义。
四
“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及其知识与权力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恰恰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起点。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进入现代世界观念秩序的起点上,其中国想象都经过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或重塑。即使该国家地区具有自身的中国形象传统,也难以拒绝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规训”,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不过是掺杂着本土想象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不是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模式,就是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前提。为模式者简单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前提者可能“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但期望与焦虑都针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起,中国形象成为该国家地区“自我东方化”或“自我西方化”想象的参照。
今天,西方媒体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的信息源;而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与旅行家的讲述,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的信息源。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的支配权,来自代表强势文明的地域与国家。中世纪是阿拉伯,现代是西方。中世纪阿拉伯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人自大的笑话:据说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长着两只眼睛,其他民族不是独眼龙,就是瞎子。这个笑话在布哈拉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写的《中国志》中出现过,马可·波罗时代就传到欧洲,至少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1404年在撒玛尔罕帖木耳的王宫里、意大利使节巴巴罗1436年在波斯,都听到过这个传说,并先后带回欧洲复述(19)。这是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贸易、迁徙、传教,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与南中国海走廊的“香料之路”或“瓷器之路”,建立起伊斯兰文化核心区与古代中国的文化关联。先知穆罕默德说过:“追求知识,哪怕远到中国。”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经典《道里邦国志》《黄金草原》《全史》《云游者的娱乐》,包括《一千零一夜》,都曾记述过中国,而最有代表性的文本还是公元9世纪阿拉伯商人口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和14世纪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赞美中国的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比较印度与中国,认为还是“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20)。伊本·白图泰讲述了他的中国见闻,赞叹:“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21)古代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美好的,他们不仅赞美中国的财富,还仰慕中国的制度,其中或许有夸大之辞,但不无诚意。而真正的有意义的是,古代阿拉伯世界在中国不是发现关于另一个国家的真实,而是寄寓关于自身现世生活的理想。
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在漫长的中世纪曾经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的传播源,而进入现代以来,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反倒是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而且具有明显的“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特征。在阿拉伯国家的东方主义自我想象中,中国是一个比阿拉伯更东方的东方,这让后殖民时代的阿拉伯国家多少感到某种优越感。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中规划了三个“东方”:第一个“东方”是伊斯兰东方,从奥斯曼的欧洲土地开始,包括埃及直到中亚,中心在波斯与阿拉伯,那是“典型的东方”;第二个东方主要是印度与中国,可能还包括整个东亚、南亚地区;第三个东方在地理与文化上都具有模糊性。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岛屿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似乎都属于第三个东方。第三个东方可能在地理上不属于东方,但文化上却分享着“东方性”。在西方想象中的文化地图上,东方的界域在于特定的文化同质性,那就是所谓的“野蛮的东方性”,如神秘、放荡、残暴、堕落、专制、腐败、古旧、停滞、混乱、邪恶等特征。在西方规划的世界观念秩序中,阿拉伯地区可能是跟西方最近的东方,他们都是地中海文明的孩子;也可能是跟西方最远的东方,穆斯林与基督徒传统的世仇一直延续到今天。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在受东方主义影响的同时,也受“西方主义”的影响(22)。在他们的“西方主义”想象中,崛起的中国可能沾染了西方化的堕落特征:浅薄傲慢、道德败坏、只图物质享乐,缺乏精神信仰……当然,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圣战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形象值得警惕,但整体上阿拉伯地区关于当代中国的印象仍是美好的,这方面李荣建教授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拉伯的中国形象研究是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信众,处于政治权益或信仰取向,他们的中国形象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在文化同一性基础上使用“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划定研究领域与对象,都是轻率而危险的。
阿拉伯的中国形象是个重要的个案,而目前的研究只是开始,因为理论不是描述现象,而是分析问题。在这方面,拉丁美洲、非洲的中国形象研究,也只在起步阶段。19世纪的华工、20世纪的革命曾使拉丁美洲与中国命运相关,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昭示了另类现代性的可能,对拉美世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的经济交往进一步扩大,中国成为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同时,“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恐怖论”也开始在拉美流传。中国在拉美的影响或许触及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但远未动摇美国的权威。而在此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真正的“威胁”是美国,美国在全世界一百三十个国家驻军或建有军事基地,但为什么没有“美国威胁论”?中国的全球发展谨小慎微,却惹起美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如何自身强大又不表现成对他人的威胁呢?关键还在国家力量强大的合法性,这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意义所在。西方扩张五百年,从基督教到启蒙哲学,不断为其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直到今天,西方的“普世价值”依旧是其力量的合法性依据。现代性世界秩序语境中,国家力量必须获得“正义”支持,那是“启蒙合法性”所在;而缺乏普世价值的“正义”支持,国家力量的生长势必在人们的想象中成为国家秩序的“威胁”。世界是有“道理”的,给人以产品的国家,如果不能给人以正义,将成为威胁。不管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敌意还是友谊,我们都应该清楚这一切的由来,问题出在哪里。
从郑和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历史近千年。人们可以想象当年郑和船队停靠在东非海岸时的场景,遗憾只是没有历史记载。中国史籍中描述的感恩戴德的场景固然是难免的,或许对这些强大的外来者也有猜忌、恐惧与不安?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过一部拉士鲁朝时代的阿拉伯语手稿,其中记载着郑和船队访问阿丹港的情况,有趣的是,在当地人眼里,郑和船队的中国人似乎有些自大无知,“在人们的言传当中,有一条是确实可信的,那支那王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支那)王的仆人’。的确,在他们(支那人)中间大概也有对诸国的情况和王侯们的事情愚昧无知的人……”(23)东非海岸当年目睹大明使团到来是否可能有同样的感想?早年的记忆虚无缥缈,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劳工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非洲的中国形象开始具体化,其中有对中国人的勤劳与苦难的赞许和同情,也有沾染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偏见的鄙视与轻贱。但中国形象的意义并不明确,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我意识未觉醒,他者形象也不可能明确。意义明确的中国形象出现在20世纪后半叶非洲的反殖与民族解放运动中,新中国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革命时代中国对非洲的无私援助在非洲留下良好的印象,建设时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走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中非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增多,非洲的中国形象在更具体化的同时也更复杂,中国作为一个友好的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可能是正面的,中国人在非洲从事经济活动,如果有骄横欺诈的行为出现甚至流露出的种族主义偏见,中国人的形象则可能是负面的。另外,非洲大部分国家曾经是西方殖民地,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同样影响着非洲,“中国威胁论”“中国非人权”“新殖民主义”等论调正污染着非洲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在非洲的前景或许不容乐观。
如何面对一个恶意生长的世界?问题在哪里?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基本上属于观念史范畴,如果进入实践领域,它则关系到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与战略问题。中国当下最大的“战略威胁”与“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相关。学术研究难以回避现实问题。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决定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研究对象是“思想”或“想象”,研究的问题却是当下国际文化与地缘政治战略的,如何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跨文化形象学是个全新的领域,论题正待开辟,方法也在探索中,本套丛书只是一种尝试。即使有些研究难免差强人意,也是有价值的,草创之作可能成为一种激励,促使更多的人进入这一领域,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入思考。我们已在这里留下“领域”与“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与我们的朋友,一同深入第二组课题的研究,同时,更加谨慎认真地进入第三组课题。
注释:
①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存在一个翻译、中介的过程,比如作为所谓“意见领袖”的中国本土知识精英,在“翻译”西方的中国形象时,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动的选择和意义创制的作用。周云龙同学阅读本文后提出此见解,对笔者颇有启发。
②参见Orientalism,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by Bryan S.Turn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③德里克在批判赛义德的《东方学》时指出,赛义德只注意到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的创造,忽略了东方主义也是东方人自我构建的产物,“需要亚洲人的合作才有实行的可能”,德里克提出“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概念。“……这一概念的用法应被推及亚洲人对亚洲社会的看法,用以解释自我东方化这个可望成为东方学史一个固有内容的倾向。我们常将欧美对亚洲社会的影响看作是‘西方’观点及制度对亚洲的影响。就东方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已是‘西方’观点的一部分这一点来说,‘西方’的影响亦包括了欧洲对东方的态度对亚洲社会的影响。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与‘西方’观点的影响是不可分而论之的。认识到这一可能性之后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对所谓亚洲‘传统’提出质疑,因为如果我们细察之,这些亚洲‘传统’也许不过是些‘臆造的传统’,是欧亚人接触时的产物而非前提,并且它们也许更多是生自东方学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而非亚洲人自己对自己的审视。”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281-282页,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参见拙文:《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载《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
⑤参见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lts Enemies,by Ian Bumma & Avishai Margalit,Penguin Press HC,2004.
⑥笔者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另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参见拙文:《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⑦周云龙同学阅读本文后提出进一步的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自我形象的回馈性影响,也可能是一种主动的挪用。运用话语理论思考该问题,必将忽略非话语层面的可能性,比如邪恶的与浪漫的中国形象,是否完全来自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本土的主体经验是否已被完全掏空?或许不尽然。如何从学理上回答这一问题,“西方主义”作为一种主动挪用西方的话语来完成自身的转换,可能已经凸显出某种不彻底的主体意识。
⑧阿尔杜塞研究意识形态的意义时使用“想象”(Imaginary)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他说意识形态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霍尔(S.Hall)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现”,他认为“表现”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edited by Stuart Hall,London:The Open University,1997,Chapter I,"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on".
⑨参见拙文:《汉学或“汉学主义”》,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
⑩《脱亚论》引文根据林思云先生据日本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时事新报》刊原文翻译出的中文译本,网上亦有“流水成溪”先生所译的文言版。
(11)参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324页,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13)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尤其是收入该文集的《何谓近代——以日本和中国为例》。汉语文本的相关研究著作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沟口雄三的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汉译本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译名通俗化,却扭曲了原书名的意思。
(15)[日]长谷川庆太郎:《别了!亚洲》第3-4页,鲍刚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16)参见刘宏:《建构中国隐喻:苏加诺的中国观及其对印尼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影响》,载周宁编:《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第325-34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参见鲁虎:《官方建构、华人族群和对华政策:马来西亚政治领袖东姑的中国观》,载周宁编:《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第370-38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参见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by Joshua Kurlantzick,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库兰奇克强调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发展大有取代美国之势。
(19)《克拉维约东使记》道:“契丹人都是技艺精巧的工匠。但自以为是,他们自夸世界上只有他们才长两只眼睛,法兰克人只有一只眼,摩尔人都是些无目瞎子,因此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见Narrative of the Embaa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A.D.1403-1406,Trans.By C.R.Makham,London,p133.由杨兆钧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的《克拉维约东使记》省略了这段文字。又见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y Sir Henry Yule,London,p178:巴巴罗赞赏波斯国王送给他的中国丝绸精美,波斯国王哈桑对巴巴罗说:“先生,当然如此,您知道波斯有一句谚语:中国人有两只眼睛,法兰克人只有一只。”伊斯兰世界通称欧洲人为法兰克人。1500年前后出使中国的布哈拉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写的《中国志》也说:“……在中国人和可汗的心目中,他们天下第一,中国就是全世界。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帝国之外,世界上不再存在任何文明国度了。”[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159页,耿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
(20)参见[古代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4-25页,穆根来、汶江、黄倬文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39-540页,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与西方的东方主义相对,东方也有“西方主义”。西方主义是一套虚构与言说“西方”的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敌我意识。西方主义虚构了各种所谓“西方”的形象特征,诸如贪婪无度、纵欲堕落、拜金主义、冒险流浪、背信弃义、冷漠强权……西方主义分享着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其历史构成的诸种思想中,从宗教信仰到社会政治观念,有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斯拉夫主义、泛亚细亚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与当下普遍流行的反美主义。西方主义将各种扭曲的、失败的文化怨恨发泄到一个虚构的西方上,丑化、“胡化”“兽化”或妖魔化西方。“西方主义”不仅是一个现代性概念,还是历史中久已出现的文化地理的他者化产物。西方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波斯与希腊罗马的战争时代、中世纪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冲突时代、甚至中国汉朝的汉匈冲突时代。在这种思想或想象传统中,西方始终是被排斥被丑化的。西方扩张时代开始,印度、中国、日本先后都出现了有关西方的他者化套话。随着西方冲击与压力的加强,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抵抗的情绪也越发激烈,这种抵制情绪经常发泄到现代化器物与制度与文化上,今日伊斯兰激进主义是其极端化表现。西方主义的立场是所谓东方的,但方法与武器却经常是西方的。在西方主义的思想资源中,有东方传统社会的,也有西方现代性内部包含的否定性因素。今日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负面印象,就继承了各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西方思想渊源。首先是19世纪德国以赫尔德为首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浪漫主义反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世界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物质主义,以浪漫的美学的东方想象否定西方社会现代性。与西方负面形象的前两种象征意义相关;其次是俄国19世纪以斯拉夫主义为首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与俄国斯拉夫主义相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再次是20世纪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现代化的道路是战胜西方而不是依附西方;又次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最后是今日伊斯兰激进组织。以怨恨情绪为核心的西方主义,具有浓厚的宗教狂热与民族主义情绪。就伊斯兰圣战组织而言,他们不仅反对西方,也反对西方化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甚至反对伊斯兰世界本身的世俗社会或世俗国家,如叙利亚、埃及。有关“西方主义”的论述,可参见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by Ian Buruma & Avishai Margalit,Penguin Press HC,200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主义”尽管以一种“反西方”的方式“表态”,但其思维模式或内在思想框架依旧是西方现代性的。即使搁置美化西方的“西方主义”不论,表现为“民族主义”的“西方主义”在反西方的外表下,可能是更深刻地表现为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一致。因此,单纯强调“西方主义”的“反西方”性,往往遮蔽了“西方主义”内在的西方性。
(23)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第44-60页,“郑和分宗访问也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标签:现代性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跨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他者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