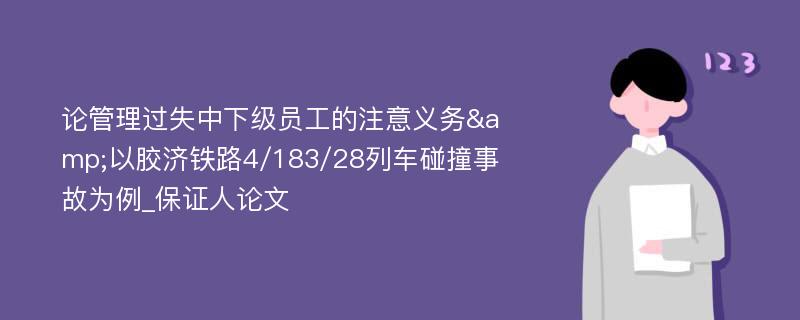
论管理过失中下级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以4#183;28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为例的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过失论文,下级论文,从业人员论文,列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以企业等组织体的形态从事附带危险的业务时,组织体的管理者应当确立安全管理体制(以下简称安全体制),以防止业务中的危险源造成法益侵害,如煤矿企业的管理者应当在采煤区设置合理的通风系统,配置瓦斯检测设备,并派遣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对瓦斯浓度进行不间断的检测,以防止瓦斯中毒、爆炸事故,管理者因怠于确立安全体制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被追究管理过失责任,①不仅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得到认可,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逐步得到落实。③ 但是,在因管理过失而引发的事故中,下级从业人员(包括现场作业人员)能够协助消除安全体制的缺陷而没有消除,这些主体是否违反了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一律认定不存在注意义务的违反,则形同于鼓励下级从业人员放纵由管理者开启的因果侵害过程,不利于对法益的周密保护。相反,如果轻易地认定下级注意义务的违反,则容易使其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造成过失惩罚的苛酷。在因管理过失而引发的事故中,应当让何种范围的下级从业人员承担何种性质的义务,以避免或者减轻法益侵害,应当成为业务过失犯罪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该义务属于下级对上级的义务,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义务,在方向上正好相反,因而违反该类义务的过失也被认为是“反向的监督过失”,④而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传统的监督过失展开了较多的探讨,但是对这种所谓的“反向监督过失”尚未展开深入的讨论,笔者将以“4·28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案”为例,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4·28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基本案情及审判⑤ 2008年4月28日凌晨4时48分,北京—青岛T195次列车以131公里的时速行经山东胶济铁路王村段时,部分车厢突然脱轨,侵入并行的另一条铁轨,和正常运行的对开5034次列车相撞,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地段为限速80公里/小时的施工路段,而肇事车辆行经该地段的时速高达131公里。但列车超速的具体背景为:为确保行车安全,济南铁路局在2008年4月23日印发文件,要求事发地段限速80公里,并定于4月28日0时开始执行;但其在4月26日发布的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事发路段的限速,使得事发列车所属的北京机务段未能将限速数据输入列车的“黑匣子”(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⑥4月28日午夜1时路过事发地段的2245次列车,发现现场临时限速标志(80公里/小时)与“黑匣子”的数据不符,并向该局进行报告后,该局立即补发了4444号调度令,将事发路段的时速限制在80公里,但是事发地段的车站值班员漏发了该调度命令。T195次列车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司机既没有收到限速的指令,也没有发现铁路部门在事发路段设置的限速标志,使得列车超速运行,引发脱轨及碰撞事故。⑦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于2009年12月3日对该案做出的一审判决认为,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属多个环节违规造成,原北京机务段机车司机李某、原王村站助理值班员崔某、原王村站值班员张某、原济南铁路局调度所列车调度员蒲某及郑某、原济南铁路局副局长郭某,身为铁路职工,违反铁路规章制度,导致发生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后果特别严重,均构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并判处李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判处崔某、张某有期徒刑4年、3年6个月;判处蒲某、郑某、郭某有期徒刑3年(除郑某外,均为缓刑)。⑧ 因济南铁路局在调度命令管理上的缺陷,使列车司机在限速路段超速行车,造成列车脱轨、碰撞事故,以此认定负有相应职责的郭某等人存在管理过失,在学理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司机李某由于没有发现事发路段的限速标志,未能觉察调度命令存在的错误,因而未能向管理部门报告以避免事故发生,其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并应当以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论处?这就需要讨论李某作为一个现场(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问题。 关于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当前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一种方案是不讨论其不协助管理者确立安全体制的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直接认定其注意义务的存否及内容;另外一种方案是将下级不协助管理者确立安全体制的行为界定为不作为,并在不真正不作为犯框架中先讨论其是否具有保证人地位,再认定其注意义务的存否及内容。对此,笔者将在比较这两类解决方案优劣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合理的问题解决框架,并在该框架下探讨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并顺带分析本案中李某注意义务的有无及内容。 三、不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不讨论下级从业人员的相应行为属于作为还是不作为,而是立足于过失犯的要件,认定其在管理过失中注意义务的有无及内容。这是日本实务界中通行的见解,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最高法院对大洋百货大楼火灾、千日百货火灾等案的判决看出端倪。 (一)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判决之见解 在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董事兼人事部长C、防火管理者E等被告人,就百货大楼在防火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如没有制订消防计划,没有实施消防训练等,没有向董事长提出或报告,在大楼内起火后,由于从业人员没有进行火灾通报、避难引导,致使未能及时逃跑的多名店员、顾客葬身火海。⑨两名被告人是否负有向上级进言的义务,是其刑事责任认定的关键。日本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进言义务的有无,不仅取决于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的有无,还受制于被告人在防火管理业务中的地位、权限。鉴于两名被告人均能认识到防火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及该缺陷可能会引发伤亡事故,且通过向上级进言以消除该缺陷,也能避免结果发生,对结果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的认定并不困难;相反,关于二被告人是否在防火管理业务中具有相应的地位和权限,才是决定进言义务有无的关键,也是争议的焦点。日本最高法院最终以相关主体并未实际从事防火管理业务(C)或者不具有该业务的实质权限(E)为由,否定了向管理者的进言义务,具体理由是:首先,就董事兼人事部长C而言,作为股份公司的董事已经在董事会中选任董事长,并赋予后者执行防火管理业务的权限,如果不存在董事长无法履职的特殊事由,就不能认定其对董事长的监督义务;⑩而且C未被任命为防火管理人,其任职的人事部门所辖业务也不包含防火管理,应当认定其并没有实际从事防火管理业务,故而,应当否定C向A进言的义务。(11)其次,就防火管理人E而言,E尽管被任命为防火管理者,但是从案件的事实关系上看,其并没有被赋予实质的防火管理权限,也应当认定其负有向A进言以完善防火管理体制的义务。(12) (二)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判决之见解 在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中,千日百货大楼管理部科长兼防火管理人的被告人N,在保安人手不足,无法在百货大楼打烊后关闭足够数量的防火隔离门时,没有向上级进言以增加保安数量或商请入驻商户的协助,导致在因大楼内的工程施工发生火灾时,未能延缓火势的蔓延,造成夜间营业楼层的重大伤亡事故,(13)N作为下级从业人员是否负有向上级进言以消除安全体制缺陷的义务,这也是该案争议的焦点所在。 日本最高法院认为,N进言义务的有无,不仅取决于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也取决于其在防火管理业务中的地位及权限。由于N是大楼的管理部科长兼防火管理人,不仅实际从事防火管理业务,也被赋予了采取一定防火管理措置(如制订消防计划、进行消防训练等)的实质权限,因此,其在防火管理业务中的地位、权限毋庸怀疑;相反,向上级进言以避免火灾中伤亡事故的发生或扩大,是否存在着现实可能性,即结果回避可能性的有无,是值得商讨的。最高法院最终认为,通过向上司进言、寻求商户的协助,以确立完善的防火管理体制,即关闭正在施工楼层的防火隔离门,并在施工现场派驻保安,具有现实可能性,进而肯定了N对上级的进言义务。(14)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案判决中肯定的进言义务,具有补充性,即被告人负有的首要义务是自行采取必要措置以防范火灾发生,仅在自行采取措置较为困难或成效不显著时,才负有向上级进言的义务。(15) 因而,关于下级向上级的进言义务,日本最高法院在上述两个判决中的结论虽说不同,判决思路却一脉相承,都是在不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前提下,对下级的注意义务进行认定:不仅要考察结果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的有无,而且为了防止注意义务的扩张,还要考察其是否实际从事了相关业务并具有相应的实质权限。对此,笔者认为,在认定其注意义务时,考察结果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的有无,在过失犯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考察其是否实际从事了相关的业务活动、是否具有采取危险防范措置的实质权限,很难找到刑法信条学的根据,因为是否实际从事业务活动或具有采取相关措置的权限,不过是反映了企业内部的业务分工,为何这种内部分工会影响到刑法上注意义务的有无?该要件的引入会不会导致过失犯构成要件体系的混乱?这些都是该解决方案无法化解的质疑。 四、建立在作为与不作为区分基础上的解决方案 建立在作为与不作为区分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将下级未能协助上级确立安全体制并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的,视为(不真正)不作为犯,并对过失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和注意义务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只有下级处于保证人地位,才能成为相关作为义务的主体,而其保证人地位的有无是进一步讨论其注意义务的前提。德国的理论界、实务界基本上都秉持这种见解,而日本理论界中相当多的学者也采取该种见解。 (一)德国实务及理论上之见解 对于下级从业人员未协助上级消除安全体制的缺陷并导致法益侵害发生的,德国实务界把讨论的重心首先放在了该下级是否处于监管业务中危险源的保证人地位,并且倾向于通过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否定下级通过进言等方式协助上级确立安全体制的义务,例如,德国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凝血剂研究所,因输血用药品的制造、管理体制存在着缺陷,导致病原菌混入该药品,并使服用该药品的病人死亡的案件中,处于研究所所长助理地位的女医师,未向所长提出改善凝血剂制造、管理体制的建议,关于该不作为能否以过失犯来处罚,成为诉讼中争议的焦点,德国联邦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从大学所属州的相关法令,能够认定该研究所所长对所内事务负有总括性的职责,被告人只有在所长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在代替所长履行职责的场合,才能就相关事务承担责任,被告人不是该药品的制造责任者,也没有接管制造的业务,且不能认定其实施了危险的先行行为,因此,否定了该女医师的保证人地位,进而作出了无罪的判断。(16) 而德国刑法理论界在讨论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时,也是将下级的保证人地位作为讨论的前提,并倾向于否定其保证人地位以及向上级进言的义务。(17)对此,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企业等组织体中,鉴于上级对整个组织体乃至下属行为的掌控,理论上将其视为造成组织体事故的原因的掌控者,并将防止组织体事故的保证人地位无保留的分配给了上级,(18)在其中并没有下级从业人员的存身之地。对此,有学者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其将因未协助上级确立安全体制而可能被追究责任的下级从业人员,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处于组织体外部就组织体的安全运营向管理者提供专业建议的行为人,第二种是处于组织体内就组织体的安全对策向管理者提供信息的员工,并进而认为,为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提供根据的是不作为者的保证人地位,而且该地位是由能够直接采取措置以避免事故的法律、事实权限所奠定,仅仅有报告或建议的权限,不足以奠定不作为犯的保证人地位;故而,在第一种主体的场合,在企业的安保业务被法律要求应当雇佣安保专家的场合,由于这些安保专家有义务从专业角度对企业主提供建议、检查安保态势,并在安保对策上存在缺陷时,应向企业主报告,但即使因安保专家未报告的缺陷而发生劳动灾害时,尚未有安保专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对此的一个有力的说明就是,实施安保对策的权限,本来就保留在企业主手中,而处于顾问地位的保安专家,欠缺保证人地位。(19)同样,在企业内部工作的被期待报告安保缺陷的员工,即使发现企业的安全体制存在着缺陷,也只能利用专业性意见说服他人,而没有命令他人消除该缺陷的处分权或命令权,仅仅是指出缺陷的权限,而非消除缺陷的决定权,不足以奠定其保证人的地位。依据该见解,无论是对组织体外部的处于顾问地位的人员,还是对组织体内部的下级从业人员,都不能以其怠于向管理者提供确立安全体制的建议为由,追究其过失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20) (二)日本理论界之见解 日本理论界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前述所谓进言义务的案件展开,基本上也是先将下级未向上级进言的行为界定为不作为,而后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下讨论其进言义务的有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岛田聪一郎、齐藤彰子等人的见解。 岛田聪一郎认为,下级参与到业务中危险源的管理时,才能考虑其保证人地位,认定其有向上级进言或者敦促其采取结果回避措置的义务。其以防火管理体制的确立为例将进言义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负有作为义务(或处于保证人地位)的防火管理者,既可以依照自身的权限采取措置,也可以向上级进言并由后者采取措置的,向上级进言只是履行结果回避义务的一个选项,既不向上级进言,也不亲自采取相应措置的,应当认定其违反了注意义务。第二,防火管理者等接受了危险源管理的主体,在自己无法采取结果回避措置,只有通过向上级进言才能避免结果的,应当认定下级进言义务的存在,如在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二审判决中,管理科科长被认定的进言义务,即属这种类型。(21)第三,没有实质参与防火管理业务的场合,由于下级没有接管对危险源的管理,因欠缺保证人地位,不负有进言的义务。(22) 齐藤彰子也认为,下级的保证人地位是进言义务存在的前提,而保证人地位根源于法益保护的依赖性。依其见解,由于下级通常没有采取结果回避措置的实质权限,只能向有决定权限的上级进言,并通过后者才能避免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法益保护通常依赖于有决定权的上级,因此,应在原则上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及其进言义务;(23)但是下列两个场合是例外的:一是避免结果发生不需要特别专业知识的场合。上级如果在保留决定权的前提下,将认识、评价危险以及判断危险防范措置等任务委任给下级,下级由此获得了上级的信赖,排除了上级自行或者委任他人承担该任务的可能,相关法益的保护不得不依赖于该下级,应当肯定其保证人地位及向上级进言的义务。(24)二是在避免结果发生要求特别专业知识的场合。有决定权的上级,在采取何种结果回避措置的问题上,更为依赖拥有专业知识的下级,应当认定该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及向上级的进言义务;但是和第一种场合不同,由于其在知识上的优势,其还负有督促上级采取必要措置的义务,即在上级已经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有所认识,但没有采取必要措置时,该部下应当督促上级付诸行动。(25) 从上述理论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都是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内讨论管理过失中下级的注意义务,德日之间的见解差异还是相当明显。其中,德国的相关见解将安全体制的确立义务无保留的分配给组织体的管理者,通过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否认下级有协助确立安全体制的义务。在笔者看来,该类见解尽管在防止下级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方面,是值得赞赏的,但彻底的否认下级可能基于业务分工而获得对业务中危险源的监管以及由此而获得的保证人地位,不符合现代社会中企业等组织体的分工日渐发达的趋势,也不利于安全体制的确立和组织体事故的防范,理由在于:第一,组织体原初设定的安全体制即使是有效的,也可能在运转过程中发生故障,需要下级协助才能排除。如工厂的废弃物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有害物质未经处理便进行排放的,(26)负责监视该设备运转的下级作业人员,如果不向不在现场的有管理权的上级报告,上级不可能对该设备进行修复,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无疑是放纵有缺陷的作业系统继续运转,并坐视企业灾害的发生。第二,组织体当初设定的安全体制,在运转过程中可能因遭遇新的危险而出现漏洞,需要下级的协助才能完善,如前述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中,大楼在夜间值班时原本配备了五名保安,但是由于大楼内部正在进行工程施工,导致现有的保安数量不足以防范火灾的发生或扩大,(27)如果下级从业人员不向上级提出增加保安数量的要求,上级很难认识到安全体制的漏洞及完善举措,否认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同样不利于对事故的防范。 与此相对,日本刑法学者在原则上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及进言义务,而在下级对安全体制的确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时,例外的承认其保证人地位,课予其相应的注意义务,既避免了其承担过重的注意义务,又在必要时要求其积极参与安全体制的构建,防止灾害事故的发生,与德国的相关见解相较,更为柔性,更加务实,但是下级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是仅止于进言义务,还是进一步延伸到督促义务?在进言的内容中是仅包含对危险的判断,还是同时包含了回避结果的措置?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和澄清。 五、本文的相关立场 (一)分析框架的厘定 1.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行为形态 在管理过失中下级从业人员的行为有可能成为刑法评价对象的,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刑法理论上被反复讨论的行为类型,即在危险发生前未协助上级确立安全体制,致使事故发生的,如前述的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中,防火管理人在火灾发生前没有向上级提出增加保安人数的请求,因人手不足未能充分关闭防火隔离门,致使起火时无法延缓、控制火势,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28)另外一种则是较少得到讨论的行为类型,即在由管理过失所引发的危险出现后,未采取有效的紧急应对措置,导致法益侵害扩大的,如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的销售科长,发现楼梯起火后,尽管即刻前往现场查看,并指挥属下进行灭火,但是未能采取立即关上防火门的措置,使得火苗迅速窜入三楼店内,致使火灾事故加重的。(29)上述两类行为,不仅在存在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由上级所开启的因果侵害流程,未加以阻止或者未投入能量的耗费;而且在规范的层面上,评价的重点也应当放在没有采取积极措置以避免结果这一消极性举止上,因此,无论是立足存在论,还是立足规范论的判断标准,(30)其行为均属于不作为。此外,从该不作为可能违反的刑法规范看,都是过失犯条款,而过失犯的犯罪构成被公认为属于开放性犯罪构成,其实行行为没有、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规定,既可以作为形式完成,也可以不作为形式来完成,而在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这些过失犯罪时,依据当前通说上区分真正(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真正(纯正)不作为犯的标准,(31)应当认定为不真正不作为犯。因此,对下级在管理过失中注意义务的讨论,也应当在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下进行。 2.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中保证人地位与注意义务的关系 在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下讨论下级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应当注意区分保证人地位和注意义务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过失不作为犯中,不作为表现为没有阻止滑向法益侵害的因果流程,能被视为不作为的主体有很多,必须首先确定这些不作为者中的哪些主体能够被课予结果回避义务,而这种作为义务主体的特定,在学说上是作为保证人地位的问题加以讨论的,这是不作为犯特有的问题;至于应当从各种各样的结果回避措置中选取哪些结果回避措置作为行为人的义务,这涉及结果回避义务的内容,是过失犯特有的问题。因此,结果回避义务主体的特定,和结果回避义务内容的特定,应当加以区别。只有在认定了保证人地位的人当中,才能对注意义务进行考察,即通过考虑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等要件,做出认定。(32) 从这个角度而言,德国实务界、理论界以及日本理论界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在逻辑上最为清晰、合理;而日本实务界,在没有讨论保证人地位的前提下,贸然论及下级的注意义务,即使以是否实际从事相关业务、是否拥有相应权限等要件限定注意义务的扩张,仍然存在着重大的逻辑缺陷。 3.下级从业人员的保证人地位之根据 下级从业人员的保证人地位的根据,即下级从业人员是为何能获得保证人地位。就保证人地位的根据而言,在理论上占主流地位的学说,已经由形式的法义务理论,(33)演变为由阿明·考夫曼提出并被许内曼所彻底发展的功能性理论,(34)由此,保证人地位的取得有两种根据:一种是基于和法益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如父母和婴幼儿,所获得的保护无助法益之照料性保证人地位;另外一种是基于和有可能侵害法益的危险源之间的特殊关系,如主人和其饲养的有可能伤害他人的宠物,所获得的对危险源进行监管之监护性保证人地位。(35)如果依照该保证人根据的两分说,下级从业人员获得保证人地位的根据,是基于对业务活动中危险源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危险发生前对危险源的控制。在以企业等组织体的形态从事危险的业务活动时,正确认识、评价业务中的危险,并采取防范危险措置的权限,原则上由管理者享有,管理者基于对业务中危险源的控制而获得监护性的保证人地位,(36)下级从业员的保证人地位通常无从谈起,但由于现实中业务分工的发展,常常会出现管理者将判断是否存在危险以及应当采取何种危险防范措置的权力,分配给承担相关业务的下级,造成决定权与判断权相分离的情形,如在举行燃放烟花的群众活动时,在人流过分密集的地方,需要派出警方的机动部队对人群进行限流、管制以防止踩踏事故发生,虽然派出机动部队的权力属于警察局局长、副局长,而是否需要派出机动部队的判断权却属于派驻活动现场的警官。(37)在该种情形下,没有下级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作为上级就无法有效的行使决定权以构筑有效的安全体制,下级虽说处于辅佐的地位,但对于防止结果的发生不可或缺,也认定其获得了对危险源的控制,并肯定其保证人地位。 二是危险发生后对危险源的控制。对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危险,只有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才能防止法益侵害的产生或扩大。在分工较为发达的组织体中,常常将监控现场危险以及紧急应对危险的任务分配给下级从业人员,如在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三楼的销售科长,根据其业务的分工,负有在其所辖的区域内灭火、防止延烧的职责,(38)这类人员,如果在危险来临时不迅速消除危险或者不采取紧急救助的措置,很容易导致法益侵害的发生或扩大,可以说其获得了对现场危险源的控制,应肯定其保证人地位。 (二)管理过失中下级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 依照上述分析框架,在认定管理过失中下级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时,应当在认定保证人地位的基础上,根据过失犯的要件——结果预见可能性、回避可能性,确定注意义务的有无及内容。(39) 1.无保证人地位即无注意义务 下级从业人员是否取得了对业务中的危险源进行监管的保证人地位,依据笔者的见解,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其分担的业务是否包含了监管危险源的内容,二是是否拥有对危险源监管的实质权限。只要欠缺上述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就足以否定下级的保证人地位,并排除了其承担注意义务的可能性。 首先,在下级从业人员所分担的业务不包括对危险源进行监管的内容时,则该下级不是监护性的保证人,不承担阻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例如,在没有安装灭火器的酒店,一旦起火,不能进行紧急灭火,可能会导致人在火灾中丧生,对此,在酒店工作的厨师也存在着预见可能性。但是没有动手安装灭火器,也没有向经理建议安装灭火器的厨师,对因酒店火灾而带来的伤亡结果,不应当承担过失责任,(40)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厨师分担的业务不包括防火管理事项,无法从中引导出其对酒店火灾进行监管的保证人地位,即使具备结果预见可能性、避免可能性,在火灾发生前也不负有向经理进言的义务,同样在火灾发生后也不负有紧急灭火、实施救援的义务。(41) 其次,下级从业人员所分担的业务,尽管包括危险源监管的事项,但在不具有相应的业务权限时,也应当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的欠缺。如在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被告人E尽管被任命为百货大楼的防火管理者,其分担的业务包括了防火计划的制订、防火训练的实施,但没有被赋予构筑防火管理体制的实质权限,(42)因此,应当认定其不是监管大楼内火灾危险的保证人,协助确立安全体制的义务自然无从谈起。 2.存在保证人地位时注意义务的认定 在下级从业人员的保证人地位被肯定时,笔者认为其注意义务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危害源正在现实化为法益侵害结果(简称为危险发生后)时的紧急应对义务,二是危险源现实化为法益侵害结果之前(简称为危险发生前)的进言义务。 (1)危险发生后的紧急应对义务 危险发生后的紧急应对义务,在笔者看来,主要是针对基于业务分工而监管作业现场危险的下级从业人员。所谓紧急应对,既包括对法益侵害的危险进行紧急的控制、消除,也包括对处于该危险中的法益主体实施紧急的救援。如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的三楼销售科长,发现其所管辖的区域内起火,而且火苗有可能延烧到三楼的店内,酿成重大火灾事故,该销售科长有义务立即采取灭火及其他防止火势蔓延的措置,以避免火灾的危害或者降低火灾的危害程度。(43)但是要注意的是,紧急应对义务应当立足于事前的判断,并考虑到紧急状态中人的能力界限,因为险情的出现是突发事件,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和行动,即使从业者受过相应的训练,也难免会惊慌失措,如果立足于事后角度的判断,将会为现场的下级从业人员设定过分苛刻的义务,导致过失惩罚的苛酷化,如在大洋百货大楼火灾案中三楼的销售科长,发现起火后,立即命令其手下用灭火器进行灭火,自己移动包装箱以防止延烧,导致丧失了关闭防火隔离门的最佳时机,致使火苗窜入三楼店内扩大了灾害后果,(44)虽然从事后来看,销售科长确实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举动,但是从其确认起火到火苗窜入三楼店内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其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中已经做了尽可能的努力,如果认定其存在过失,不过是“在一生难得一遇的紧急事态中,对一个外行人在约1分钟内所作的判断和应对,特别提取以秒为计算单位的缺陷,为其打上刑事过失的烙印,是过分残酷的”,(45)因而,应立足于事前的判断,认定该销售科长未违反注意义务。 (2)危险发生前的进言义务 危险发生前的进言义务,在笔者看来,是针对基于业务分工而协助管理者确立安全体制的下级从业人员。在该类人员发现安全体制存在缺陷或者安全体制的缺陷客观上能够预见时,下级才负有向上级进言以确立安全体制的义务,如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案中的防火管理人,在明知大楼三楼正在进行工程施工,为防止火灾发生,有必要将三楼的防火隔离门关闭并在施工现场派驻保安,凭现有的保安数量无法做到时,应当向有权限的上司进言、提议增加保安数量的义务。再如,经常作为期待可能性问题讨论的“马尾绕缰案”,(46)笔者认为,也是一个涉及管理过失中下级从业人员义务的案件,马车店的老板为保障交通安全有义务向雇员提供合格的马匹,其雇员发现马匹有马尾绕缰的癖性并且容易在奔跑途中受惊的,作为业务中危险源的监控者,该雇员有向老板进言的义务,其已经向后者进言却没有被后者接受的,导致该劣马奔跑中受惊并造成行人受伤的,自然应当认定马车店老板存在着管理过失;(47)而雇员已经向老板进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违反注意义务。至于老板做出了明显错误的指示,雇员没有拒绝执行的,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笔者将在下文中予以阐释。 至于进言义务的内容,当前理论上的通说认为,不仅包括安全体制缺陷的存在及危险性,也包括能有效消除该危险的适当措置。(48)笔者认为,通说见解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因为分担了监管危险源业务的下级,只有向上级报告安全体制的缺陷、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并指出完善该安全体制的措置,拥有决定权的上级,才能运用权限完善对危险源的管理,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将其作为进言义务的内容,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在笔者看来,不应当忽略下述例外情形,即在上级具有应对危险的优越性知识、技能时,下级只要向上级报告安全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及具体特征,就可以认定其履行了其注意义务,不应当再要求其提出完善安全体制的具体建议,如在举行烟花大会时,由于人潮汹涌,保安公司已经无法防止踩踏事故,需要由警方接手的,保安公司负责人向警方说明动用警察的必要性,并提供关于现场状况的必要信息,就算是履行了注意义务,至于警方采取何种措置才是最适当的,由于警方具有更优越的判断和处理能力,就应由其临机把握。(19)接下来的问题是,处于保证人地位的下级是否负有督促上级采取适当措置的义务,这涉及进言义务的程度问题,对此,学说上还存在着争论,(50)笔者认为,不应当要求下级承担额外的督促上级作为的义务,理由在于:一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安全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及完善的对策,只要被上级所接受,就足以防止结果的发生;二是如果下级的进言没有被上级接受,要求处于隶属地位的下级,去督促拥有业务决定权、乃至人事权的上级,采取防止结果发生的必要措置,这毫无疑问是过于沉重的义务负担。(51) 在下级向上级进言后,上级仍然发出了错误指示时,下级有无拒绝的义务?如“马尾绕缰”案中的雇员,在向老板报告了马匹的缺陷后,老板仍然下达了将该劣马拴在马车上的指示,车夫有无拒绝执行的义务?笔者认为,在这种场合下,由于能够认识到执行上级错误指示会带来法益侵害的结果,其有拒绝执行的义务,如其不加拒绝并造成法益侵害的,应当肯定过失的不法,只是念及不服从该指示可能招致的恶果,从欠缺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认定其责任的阻却。(52)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对危险源进行监管的下级,在发现安全管理的缺陷后,未向上级进言,但即使进言也很可能没有效果的,如上级对安全体制的缺陷已经明知,却无动于衷,即使下级向其进言,也难有成效的,这时“可以否定结果回避的可能性或者否定因果关系,但是不能否定其进言义务本身”。(53) 六、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中列车司机的注意义务 (一)列车司机的注意义务之认定 “4·28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中,司机李某的注意义务问题,也应当在过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下讨论,因此,应当首先确定列车司机是否对列车运行中的危险源处于监护性保证人地位;其次,在肯定保证人地位的前提下,认定注意义务的有无及内容。 1.司机的保证人地位之认定 在从事铁路运输这一附带危险的业务时,司机是否获得了对列车运行中的危险源进行监管的保证人地位,可以结合业务分工的规定及业务运作的实际来考察。首先,从业务分工的规定来看,根据当时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之规定,司机在行车时不仅要遵守列车运行图规定的运行时刻和各项允许及限制的速度,确保列车安全正点,而且要彻底瞭望,确认信号,严格按信号显示要求行车,在遇有信号显示不明或危及行车和人身安全时,应立即采取减速或停车措施。(54)这些规定表明列车驾驶业务包含了对危险进行监控以及紧急应对的内容。其次,从业务运行的实际来看,由于司机处在作业的第一线,对安全体制的缺陷往往有直接的认知,如其不向管理部门进言,后者很有可能无法采取有效的结果回避措置;而且在列车运营中遭遇紧急事态时,只有司乘人员才最有条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阻止法益侵害的出现或扩大。因此,应当认定列车司机是列车运行中危险源的监护性保证人。 2.司机的注意义务之认定 本案中列车司机所可能涉及的注意义务,根据前述分析框架可划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关于事故发生前的进言义务,即在列车脱轨事故发生前,向铁路管理部门进言限速标志与调度命令的矛盾,并确认调度命令管理存在缺陷的义务。由于结果的避免可能性不存在太大问题,该义务主要取决于结果预见可能性的认定。综合本案的情况,笔者认为,不宜肯定该预见可能性,理由有以下两点:首先,从正面来看,客观上要注意到事发路段的临时限速标志较为困难。因李某驾驶的特快列车(T195次列车时速为131公里)只配备了一名司机,经过事发路段时已经连续驾驶八个多小时,(55)而且抵达事故地点的时间为凌晨四点半,可谓正值司机最为疲惫之际,在当时的具体情形下,对于一般的列车司机而言,要注意到线路两侧一晃而过的限速标志,应该说是较为困难的。(56)既然发现限速标志是困难的,那么发现段限速标志与黑匣子中车速数据的不一致,也是困难的,故而,客观上预见调度命令存在缺陷及因该缺陷而造成的事故,就丧失了现实基础。第二,从反面来看,为保障现代铁路高速、安全运行的需要,应当允许列车司机等现场作业人员信赖管理者会提供安全的运营设施或条件,不用考虑管理者犯下错误的情形,除非存在特殊情形动摇该信赖,(57)否则的话,列车司机不得不亲自检查列车的运行图是否正确、信号设施有无出现问题、车速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等,会妨碍其集中精力从事列车的驾驶,不利于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效率。关于铁路施工段的限速事项也不能例外,列车司机一般无需考虑铁路管理部门在发布、传达调度命令时会犯下错误,除非其已经注意到运营路段的限速标志与黑匣子的数据不一致,动摇了其信赖的基础。由于本案的司机没有看到临时的限速标志,其对管理者适当行为的信赖也没有动摇。(58)因此,从上述正反两面来看,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应被否定,李某不承担在事故发生前向管理者进言的义务。假如李某偶然发现了限速标志与黑匣子中数据的不一致,应当认定其有向管理者进言的义务,而非立即降低车速的义务,如其未履行该进言义务,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构成与上级的管理过失相竞合的过失;如果其履行了进言义务,但是管理部门做出了不降低车速的错误指示,由于司机无法分辨何种速度是安全的,即使其服从了该指示,超速驶过事发路段,也不存在对注意义务的违反。 其次,关于事故发生后的紧急应对义务,即在脱轨事故发生后,救助列车上的乘客以及阻止其他列车进入事故现场,以防止事故后果扩大的义务。对于事故后紧急应对义务的认定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结果回避可能性,除非在事故发生后,司机因精神、身体上的伤害无法采取相应措置,一般应当认定其有义务救助列车乘客、阻止其他列车进入现场,但是从目前披露的案件信息看,没有证据表明李某未采取适当措置避免事故后果的加重,因此,也很难认定其违反了该紧急应对义务。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在事故发生前还是事故发生后,均不宜认定李某违反了注意义务,不应以铁路运营重大安全事故罪论处。 (二)关于本案判决思路的评析 就本案的判决结论而言,李某被判定构成铁路运营重大安全事故罪,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固然有不妥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量刑的结构,作为现场从业人员的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在所有的被告人量刑最重,而处于管理者地位的铁路局副局长郭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在所有的被告人中量刑最轻,从判决的格局来看是下重上轻,而且是越往上就越轻。这种量刑结构反映出这样一种判决思路:对距离法益侵害最近的列车司机从重处罚,而对距离法益侵害较远的管理者从轻处罚。 笔者认为,该判决的思路本末倒置,模糊了刑法评价的重点,造成了刑事责任分配的不公,理由在于: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然在于列车的超速行驶,但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是由铁路管理部门预先发出的调度命令所设定,司机只能依照该命令行车,即使发现线路上的限速标志与“黑匣子”中的数据不符,也只能先向管理部门进行确认,才能确定列车的安全运行速度。在因管理者在调度命令管理上的缺陷,致使列车超速行驶,并引发重大铁路安全事故时,不仅应当认定管理者构成属于直接过失类型的管理过失,也应当将其视为支配了整个因果侵害的流程,并置于刑法评价的重点;相反,列车司机仅仅是未能通过向管理者进言以纠正安全体制中的缺陷,即使构成过失,也不过是和管理过失相竞合的过失,若是不构成过失,则不过是管理者所启动的因果侵害过程的一个环节,并非刑法评价的重点。而本案的判决将现场作业者的行为置于刑法评价的重点,既不当加重了现场作业人员的刑事责任,也不当减轻了管理者的刑事责任,对此,应当给予彻底的清算。 在笔者看来,判决的基本思路产生于传统的过失责任的判断方法,该方法从法益侵害的结果向前追溯,在与该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的行为中,先对离结果最近的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如果该最近的行为确实成立过失,就将其作为直接过失对待,并考察处于监督地位的人是否构成间接过失类型的监督过失;相反,如果距离法益侵害结果最近的一个行为不构成过失,再向前追溯,做相似程序的判断。(59)而在组织体事故中仍然采取上述判断方法的话,一旦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失当并触发了法益侵害,就容易将其行为界定为直接过失,并依次向上论及组织体上层的监督过失,(60)构成直接过失的现场作业人员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的正犯,而构成间接过失(监督过失)的管理者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狭义的共犯,(61)前者所应负的刑事责任一般重于后者应负的刑事责任,最终会形成“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责任越小”的不合理的处罚格局。因此,应当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组织体在业务活动中所生的灾害事故,应当在将其视为一体的前提下讨论业务活动的适当性,着眼于分担了组织体业务的各从业人员在防止危险上所能发挥的实质性作用,认定各个主体的刑事责任;(62)根据该方法,在因管理过失引发的灾害事故中,管理过失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介入了下级或现场从业人员的行为时,也不妨碍认定距离法益侵害较远的管理者构成直接过失,如在森永奶粉案中,(63)就本案的业务分工而言,奶粉工厂的制造科长独立掌握了奶粉添加剂的订货、检测等有关奶粉制造事项的决定权,在其发出了订购工业用磷酸二氢钠的指示,又未建立对工业用食品添加剂的有效检测机制,导致含有砒霜的有毒物质添加到奶粉当中,并引发食物中毒事故时,尽管制造科长与食物中毒事故之间介入了副科长及其他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鉴于制造科长在避免中毒事故的发生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应将制造科长视为整个法益侵害过程的开启者,并将其过失评价为直接过失;(64)相反,制造科副科长在原料采购上不过是执行科长的指示,在避免食物中毒事故方面无法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尽管和食物中毒事故的距离更近,也不能将其行为评价为直接过失,甚至不能将其评价为过失。(65) 故而,对于在企业等组织体中发生的法益侵害,如果该侵害从根本上来源于下级从业人员的不适当举动,应当考察该举动是否构成直接过失,而后在考察上层的管理者是否因监督失当构成监督过失,即采取自下而上的判断方法;相反,如果该法益侵害从根本上源于企业安全体制的缺陷或者管理者的错误指示,应当将管理者评价为直接过失者,(66)而后再考察没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下级是构成过失的竞合,还是仅构成因果经过的一个环节,即采取自上而下的判断方法。 七、结语 综上,对于下级从业人员在管理过失中的注意义务问题,应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框架中讨论:先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的有无,而后再考察其是否承担危险发生前的进言义务以及危险发生后的紧急应对义务。另外,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上,也应当采用自上而下的判断方法,力求避免“下重上轻”的责任分配格局。 注释: ①参见[日]大塚裕史:“企业灾害和过失论”,黎宏译,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②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以下。 ③参见“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2期,第63~64页。 ④[日]松宫孝明:《過失犯の現代的課題》,成文堂2004年版,第220页。 ⑤关于本案的判决全文并未公布,而铁道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简称“国家安监总局”)也没有公布事故的调查报告,但是“国家安监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关于本案披露的信息,也是引用了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4.28铁路事故追踪:胶济线每3个月出1次事故?”,载“国家安监总局”官网: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685/2008/0509/28965/content_2896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20日),以这些媒体的报道作为讨论素材,想必离事实不会太远,而且笔者是想将本案作为一个研究分析的教学案例,媒体勾勒的事实与客观真相之间的出入,也不那么重要。 ⑥列车的黑匣子可以实现列车的自动控速,即如果列车司机使列车的运行速度超过预先设定的速限时,该装置将会导致列车的自动减速或停车。 ⑦“一起不该发生的特大列车相撞事故——‘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原因追踪”,载新华网: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zhuanti/2008-04/30/content_1312551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8日;“S形线路潜伏巨大危险三次机会本可避免惨祸”,载南方周末官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44253,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8日。 ⑧“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案宣判司机等6人获刑”,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p/2009-12-03/19211918434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8日。 ⑨参见[日]出田孝一:“时の判例”,《ヅュリスト》1992年1001号,第105页。 ⑩不能期待董事长履行防火管理业务的特殊事由,根据出田孝一的解释,包括了因董事长死亡、生病丧失履职能力的场合(但排除了董事长业务执行不当的情形),而这种场合,正如岛田聪一郎所言,已经不存在董事对董事长的进言义务的问题,而是董事本身成了安全体制确立义务的主体。参见[日]岛田聪一郎:“管理·監督过失における正犯性、依賴の原則、作為義務”,载[日]山口厚编:《クロ一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112页。 (11)参见前注⑨,[日]出田孝一文,第108页。 (12)同上,第109页。 (13)参见[日]甲斐克则:“ビル火災死傷事故と管理·監督者の刑事過失”,《ヅュリスト》1991年980号,第149页。 (14)参见[日]山中敬一:“デパ—トビル火災と管理監督過失”,《法学教室》1991年129号,第93页。 (15)参见[日]平野潔:“雑踏事故における注意義務”,《人文社会諭叢(社会科学篇)》2011年26号,第140页。 (16)BGH,NJW2000,2757,参见前注⑩,[日]岛田聪一郎文,第112页。 (17)当然,也有个别见解认为下级没有向上级报告蕴藏危险的因果经过环节,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属于积极作为的,对于该损害结果应当承担责任;属于不作为的,因欠缺保证人地位,没有阻止结果发生的责任。参见[德]ゲルハルト·ダネカ—:“フォマルな組織にぉける過失”,須之内克彦译,载クタ—ト·アメルンゲ编:《組織内犯罪と個人の刑事责任》,成文堂2002年版,第270页。 (18)参见[德]许迺曼:“过失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捉襟见肘”,单丽文译,载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26-527页。 (19)参见前注④,[日]松宫孝明书,第217页。 (20)同上,第218页。 (21)参见前注⑩,[日]島田聡一郎文,第110页。 (22)同上,第112页。 (23)参见[日]齊藤彰子:“進言義務と刑事責任”,《金沢法学》2002年第44巻2号,第159页。 (24)同上,第150~162页。 (25)同上,第162~164页。 (26)参见[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丛选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27)参见前注(14),[日]山中敬一文。 (28)参见前注(13),[日]甲斐克则文,第149页。 (29)参见前注⑨,[日]出田孝一文,第108页。 (30)存在论的标准认为,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区别应当取决于一个实行性因果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规范论的标准认为,应从规范的角度观察,看刑法评价的重点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相关见解,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二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31)相关见解,同上,第477页。 (32)参见[日]大塚裕史:“過失犯の共同正犯の成立範囲:明石花火大会步道橋副署長事件を契機として”,《神戶法學雜誌》2012年62卷(1/2),第13页。 (33)这种理论把法律、合同和先行行为判定为保证人地位产生的三大根据,并在1930年前后占据着主流地位,后来又增加了“紧密生活共同体和危险共同体”,参见前注(30),[德]克劳斯·罗克辛书,第536页。 (34)同上,第536~537页。 (35)同上,第536页以下。 (36)当然如果管理者是由多人构成的集体时,就应认定多个管理者的保证人地位。 (37)参见[日]内海朋子:“雜踏警備にぉける注意義務”,《橫浜國際經濟法学》2012年第21卷1号,第78-79页。 (38)参见前注⑨,[日]出田孝一文,第108页。 (39)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是立足于新过失论的见解,即对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构成过失的行为不法,与法益侵害结果这一结果不法,共同构成过失的不法,而客观注意义务是以一般人能力为标准的结果回避义务。 (40)参见[日]前田雅英:“過失犯論の現代的課題——戰後の理諭的展開を踏まえて”,《法学教室》1992年146号,第31页。 (4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因做饭的过程中产生的起火,厨师就会对因该先行行为产生的危险,存在着对其进行监控的保证人地位,只要存在着回避可能性,就负有紧急灭火、实施救援的注意义务。这一点是前田雅英教授所忽略的,应给予批评。 (42)参见前注⑨,[日]出田孝一文,第109页。 (43)同上,第108页。 (44)同上注。 (45)[日]米田泰邦:《管理監督過失处罰》,成文堂2011年版,第161页。 (46)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41页。 (47)当前理论界关于马尾绕缰案的讨论,都没有涉及马车店老板的管理过失问题,是应当反思的,相关讨论,同上,第741页;[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19页。 (48)参见前注(23),[日]齊藤彰子文,第150页以下;前注⑩,[日]島田聡一郎文,第114页;前注(15),[日]平野潔文,第138页以下。 (49)参见前注(37),[日]内海朋子文,第80页。 (50)参见前注⑩,[日]島田聡一郎文,第114页;前注(23),[日]齊藤彰子文,第150页以下。 (51)岛田聪一郎认为,考虑到下级督促上级采取结果回避举措的困难,可以通过否定下级履行义务的可能性,以免除其责任,(参见前注⑩,[日]島田聡一郎文,第114页。)笔者认为,履行了信息提供义务的下级,即使没有督促上司采取行动,本身就不能认定为注意义务的违反,应直接排除其违法性,而不是其责任。 (52)应当注意的是,在德国劳工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今天,雇工不需要担心因不服从雇主不合法的命令而被解雇,可以合理地期待雇工可以拒绝雇主的不法命令(参见前注(46),[德]克劳斯·罗克辛书,第741页)。 (53)前注⑩,[日]島田聡一郎文,第109页。 (54)参见《铁路技术管理规程》(2006年9月27)第270条第(二)项。 (55)该车于前一天的20:13从北京站发车,中间虽停靠天津西、沧州、德州等站,但停车时间较短(在2~6分钟之间),不足以让司机充分的休息。 (56)不能因2245次列车司机发现了限速标志,就认为本案司机也能够非常容易的发现,因为前者是速度较慢的普快列车,而且是在午夜1时经过事发路段,司机在精神上还较为清醒。 (57)在这里涉及过失犯中信赖原则法理的适用,即在交通或其他业务活动中举止适当的人,通常可以相信相对方或分担业务者也会像他一样行为,在因他人行为失当导致法益侵害时,欠缺过失。参见前注(46),[德]克劳斯·罗克辛书,第717~718页。 (58)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立足事后的角度,认为列车司机只要将视线转向窗外就能够很容易发现该限速标志,就肯定其预见的可能性,而是应当站在事前的立场上,考察其从事列车驾驶作业时是否容易发现该标志,否则会导致前文所批评的过失惩罚的苛酷化。 (59)参见[日]板倉宏:“監督過失”,载《刑法の争点(ヅュリスト增刊)》,有斐阁1987年版,第101页。 (60)同上,第101页。 (61)参见前注(40),[日]前田雅英文,第29页。 (62)参见前注(59),[日]板倉宏文,第101页。 (63)相关案情,参见前注①,[日]大塚裕史文,第86~87页。 (64)参见[日]井上佑司:“監督者の刑事過失につぃこ,《法政研究》第48卷第2号,第273页。 (65)同上,第276页。 (66)我国有学者认为以指使、强令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排除了监督过失的存在可能性(参见前注②,陈兴良书,第334页)。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是合理的,因为在指使、强令他人为可能构成过失的行为时,如指使、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时,这时指使人、强令人构成直接过失,而被指使、强令的工人未拒绝上级的违章命令,有可能构成过失的竞合,也有可能只是不能被评价为过失的因果经过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