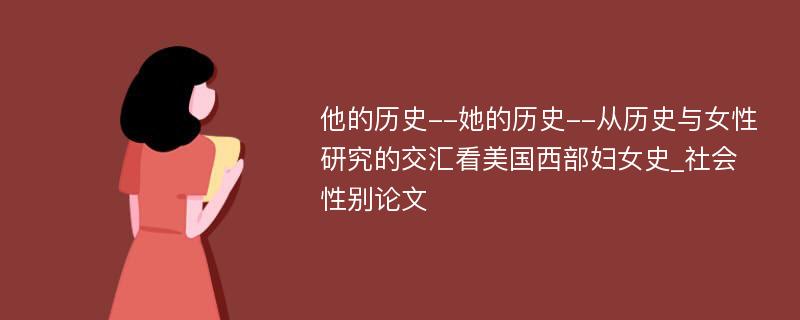
他史——她史——两性史——站在历史与女性研究的交叉点上看美国西部妇女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交叉点论文,上看论文,美国西部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1)02-0058-07
每代人都迫切地需要从对自己时代有意义的观点入手来掌握历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察视角,过去的历史在不同的探索目光下行貌各异。时逢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紧锣密鼓之际,人们本能地关注到了最具代表性的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美国西部史学家们也不断地将他们的研究扩展到特纳及其后继者们未曾涉足的其它各个领域,并不断试图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西部妇女史的研究虽然几乎不曾为国内学者关注,但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后的今天,它已成为西部历史研究和妇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一、传统西部历史:曾经是“他史”的时代
对于美国西部史,我们从不陌生。“19世纪的美国史大半都是在西进的影响下度过的”。[1]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人从东部出发穿越大陆,滚滚西行,用他们的汗水甚至生命去驯服莽荒的边疆,使原先只是位于东部沿海的美国成为今日美国的雏形。这部瑰丽的美国式的史诗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了一代代的历史学家为之孜孜以求。
自从1893年年仅32岁的F.J.特纳以“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以说是对于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2]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之后,便开始了美国史学界美国边疆史学派的年代,这“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3]
众所周知,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几乎是忽略妇女的,西进运动以其艰苦更是被视为一项男性的事业。作为边疆史鼻祖的特纳就是如此,“在他那篇论文中特纳讲了这样一句话:Kit Carson的母亲是Boone。这是他正篇文章中唯一提到女性的地方”[4]他之后的一些边疆史学家如Ray A BilIington,Tomas D Clark,Robert Athean,Robert Riegel等在处理妇女和西部开发的关系时作出的也是类似的模仿。“难道妇女在美国西部历史中真的不重要吗?”T.A.Lason反驳道“人口调查显示……在西部的许多地区都有大量妇女。根据1870年人口调查统计,21岁以上的妇女有172145人……拓荒妇女对社会的发展作出是重要的贡献。”[5]特纳的边疆理论模式极大地贬低了妇女在西进运动中的地位,这一点已受到了许多西部妇女史学家的指责。一位学者在考察妇女在美国边疆历史中的传统地位后,对特纳这种对妇女视而不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6]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认为“特纳的边疆学说缺乏对妇女的任何实质性的分析……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偏见,特纳的注意力集中于男性社会。”[7]
20世纪前半期的大部分历史学者延续着特纳的这一传统——忽视妇女。就算他们的书中包含有一点有关妇女的记叙,充其量也只是些老套的典型形象,在这些书中,“将她们描绘成拓荒着的好妻子或是学校中的女教师,要么干脆就是略带传奇色彩的狂野女子形象,比如是Calam-ity Jane那样的不法之人,再不然就是那些在西部社区中时常出没的妓女和舞女。”[8]或者“一个更老的,从某种程度上更理想化的穿越大陆的形象是把男性和女性都表现成坚强独立的开拓先锋,他们坚定不移地迈着向前的每一步,在此,特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9]
二、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的西部妇女史:从“她史”到全新两性史的探索
每一代历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都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当代人的兴趣注入到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史料的重新取舍与排列还是老故事的新版本,都是社会经验的积累造成兴趣转变的结果。纵观某一历史研究领域,我们不难发现,该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都直接受到时代的影响,并且都映射出当时的人们反观现实的态度和观点。美国西部妇女史的产生以及发展的历程与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各种学术思潮的作用息息相关。
考察它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其产生至70年代为第一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第二阶段,80年代后期至今为第三阶段。
1.萌芽之初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反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忽视女性的这一态度,向世人证实西部历史中有过女性的经验,所做的工作是重拾以及汇集那些被忽视的部分并试图将之填入历史的空白之处,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认为仍是处于男性为中心的范围之中思考。
在20世纪40至50年代,已有少量关于西进运动中妇女的严肃研究问世。但它们绝大多数是根据一些政府档案、报刊文章进行研究的,而且这都是一些由男性编写的材料。比如"Georgia Willis Read的"women and children on the Oregon-California Trail"(1944)[10]就是基于对政府档案的研究之上。
有少数人也开始从一些女性杂志和女性自己写的回忆录等材料出发,Nancy Ross 的 Westward the women(New York 1944)和Helena Hunti-ngton 的 Pioneers in Petticoats(1959)[11]采用了妇女自身的叙述材料,只是其中的调查取样实在有限。她们的分析解释虽比之前的研究更加现实,但仍局限于“拓荒者母亲”的传统形象。
这一时期关于西部妇女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要算历史学家兼小说家 Dee Brown 的 The Gentle Tamers (New York1958)他笔下的西部妇女是将文明和优雅的欧洲文化从东部带来的“驯荒者”,这一观点直接从他的书名中反映出来。
少数民族斗争和新左派运动轰轰烈烈的美国六、七十年代是西部妇女史研究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妇女史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廖若晨星”[12]当妇女们通过社会运动和当时兴起的各种女性主义思潮认识到自己“就是这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13]并发现“按传统方法记载和解释的历史,是以男性价值观为准则的男人活动的历史,妇女则被忽视了。”[14]的时候,她们强烈意识到必须要研究妇女自身的历史,要“集中力量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15]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极大影响着妇女史的发展。它们的反传统和社会批判意识与妇女史研究惺惺相惜。新社会史“为研究以被史学家所忽视的群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还提供了研究群体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计量方法,和来自社会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等跨学科方法,提供了研究诸如家庭关系、人口出生率、性别关系等历史现象的概念化工具”。[16]后现代主义“推倒了现实这堵大墙,使一切社会建构相对比,从而为女性史学树立了榜样。”[17]女性史学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许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率先运用人类学的见解,其中有些人士则是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尖兵”。[18]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以及学术背景之下,随着人们日渐留意对少数群体的研究,西进运动过程中妇女在边疆的地位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特纳的理论也同时被提出各种质疑。David Potter是这方面的先锋之一,他在一篇发表于1962年的论文中讨论了妇女与美国性格的问题,他主张修改特纳的学说以适应妇女历史的研究,他强调边疆对妇女产生的消极影响,认为,对妇女而言,边疆停止推进时她们才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这与当时流行的把边疆视为机遇之门的看法截然相反。[19]
必须看到,妇女史的研究本就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历程,西部妇女史的成长更是一个艰苦而富挑战性的过程,正如一位著名的西部妇女史学家提到的那样,“女性实际上被忽略了,直到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妇女的生活在研究中都被视为是没有价值。而对于边疆妇女而言,这一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每天14-16个小时的辛苦操劳已使她们没有多少闲暇来在日记或报刊上记述她们的思想和行动了。”[20]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成熟,这一研究的地位迟迟的得不到肯定,在1974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在大学中用于教授西部历史的标准教材中仍是“统统忽视女性”的。[21]
2.成长的年代
可以说,美国边疆妇女史的真正成长是在70年代以后,“妇女们坚持要揭示她们的过去这一做法兴起于60至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中”。[22]7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激发了一群女性学者挑战西部妇女史这一研究领域,这些先驱有 Clenda Riley,Sandre Myres,Judith Austin,Joan Jonsen 等人,她们自己也认为“女性主义运动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激起我(对妇女史研究)的兴趣。它使我们这些第一代妇女史学家看到了我们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之间的联系”。[23]在她们的率领下,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妇女历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有Robert L.M-undres"Wives,Wothers,daughters:Women' s life on Road West" (1970);Ruth B.Moynihan"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on the Over-land Trail"(1975);B J Zenor"By covered Wagon to the PromisedLand"(1974);Glenda Riley"Women in the West"(1980)等。[24]在这十年间,一些杂志都曾出版了关于西部妇女史的专刊,它们是Journal of the West,12(Apr.1973);Montana,the Magazine Of WesternHi-story,24(Sum.1974);Heritage Of Kansas 10(spr.1977);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46(spr.1978);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49(may.1980).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向人们揭示妇女的的确确在边疆生活过,向人们证实妇女历史是西部历史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同时也关注妇女与边疆的互动关系。Gray Harry写于1972年Women of California中就简要地论述了在California成为“黄金之州”的这一历史中妇女为之作出的重要贡献。Wortman Marlene Stein & Wheeler Adade Mitchell在1977年出版的the Road They Made:Women in Illinois History中讨论了从印第安时代末期至内战时期Illinois妇女的地位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与更为宏大的历史发展过程相联系进行研究,同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加深人们对Illinois历史的认识。
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很注意向西迁徙过程中或是已经在西部定居的妇女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在史料的收集上也有所突破,尽量使用妇女们自己留下的一些第一手材料。例如在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a series book,three,women during and frontier the civil war 1860-1890一书中Sanders Beverly在该书的第三章中通过对一些当时的书信和日记等材料向人们讲述了当时的妇女在西行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些什么以及她们是如何去适应边疆生活的,其中也涉及了边疆妇女的职业和平等等问题。“这一学术重心也反映了社会史和女性研究对理解西部历史上所做出的努力”。[25]
另一方面,由于理论的欠缺和材料的不足,很多研究者只有利用男性历史学家创造出的一些老套模式来填补这一真空。“边疆历史学家在研究边疆妇女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二者择其一的情况:将之放入一种‘男性的’如强硬的、雄性的、政治的这类措辞中呢,还是将之放入一种‘女性的’如驯良的、从属的、品行端正并坚强的这类措辞中,第三种选择也是更常用的是在作品中增加对其政治权利的叙述。”[26]因此,许多这一时期的研究只是在给西部妇女的旧式神话进行了抛光或是创造一个新的版本。
还有一些学者从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她们认为西部妇女是被剥削和奴役的,事实上那些妇女们完全没有享受到那种属于西部特有的自由和权力,甚至认为西部开发对于妇女的生活产生的是退步的而非进步的影响。她们提出在西进运动过程中,妇女被迫转换了原先的社会角色,虽然西部定居点上的妇女们不断地试图重建她们原先的文化,但她们事实上被雇佣的双手不仅使得她们无法回到原先的社会结构中继续扮演自己所熟知的社会角色,而却阻碍了她们去创造一个新的。[27]一些类似的观点认为西部虽给男子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对于女子却并非如此,因为边疆的工作太不适合女性了。相对温和一点的看法是:虽然边疆为妇女提供了不少机会,但能利用好这些机会的人并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在西部妇女史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两本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它们是John M.Faragher Women and man on the o-verland trail(New Haven 1979)和Juilie Roy Jeffrey Frontier wo-men:the trans-mississippi west,1840-1880(New York 1979)。两位历史学家都试图通过一个稍微另类的途径向世人展示西部妇女的不同历史画卷。
应该指出的是Faragher的书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导,虽然全书聚焦于穿越大陆的移民迁徙过程,但其实他的注意力要集中对在某一时段之间的中西部农场家庭的研究上。Faragher运用了大量人口统计学的技术,并对一系列当时的日记、回忆录、甚至民歌和民间传说进行了精心的分析,以次考察这一时期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以及他们自己对这一地位的认知情况。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出发,Faragher把所有的关系依据阶级、种族、以及性别斗争等来加以界定。通过对西进运动中两性关系的研究,Faragher认为妇女是被剥削的、处于从属地位而且无权的;他将移民的妇女视为一个消极的群体,认为她们并不情愿向西迁移,而只是“因为婚姻的关系不得不服从”。他总结道,西部并未向妇女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未给妇女予更加平等的社会地位,反而“边疆延伸了那种农业社会所历史地施加与两性关系上的影响”。而且西行的妇女,和她们的中西部的姐妹们一样,“被局限于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势力,依靠同她们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来获得社会地位。”[28]
Jeffrey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地域范围之上,并运用了多种传统的方法论,得出了很与众不同的结论,虽然她也未能证明西部开发使妇女获得了何种新的平等,但在她的笔下,边疆妇女们精神饱满,尽可能的利用着这个新的国度提供的一切机会。Jeffrey同时指出,虽然西部妇女仍然保持着较保守的态度并“鲜有人面对边疆做出了抛弃传统的反应”,但她们在边疆生活中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当她们遇到边疆生活的挑战时她们是多么的坚强并且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她们是坚强而非软弱的,是积极而非消极的,她们勇敢地战胜了边疆的艰苦条件”,与此同时“没有人放弃传播文明这一使命”[29]Jeffrey认为,边疆妇女在记录自己对西部开发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评估其价值时是充满欣赏和骄傲的。
Jeffrey的著作及一些她之后的研究所做的是试图在19世纪的旧式神化和后来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笔下千篇一律的边疆妇女形象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30]而且这些研究逐渐开始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西进运动中的妇女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经历,她们对边疆的条件所做出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说关于边疆妇女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她们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事物”[31]在这一观点中我们可以为之后二十年西部妇女史的发展方向找到一丝渊属关系。
第二阶段的研究转而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也试图从女性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一时期的历史,来评价边疆对妇女的意义。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的是女性的那一半历史,即为“她史”的阶段。
3.走向成熟
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之上,第三阶段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多元文化理论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出发,建立在一个更高的出发点以及更宽泛的视野之上,逐步真正地承认了女性也是文明和历史的基本创造者,同时开始探究两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论提出挑战,并且试图重建一部全面的新西部历史,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由强调“她史”转入一个全新理论构架之上两性总体历史的阶段。
(1)80年代:社会性别·多元文化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西部妇女史的研究与其相关学科的发展相辅相成,8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学术界新文化史的升温,人们转而强调文化对边疆妇女的作用,而不再从环境决定论出发。正如著名的西部妇女史学家Glenda Riley指出的那样:既不是草原也不是牧场创造了妇女的生活,相反,他们的传统文化模式才是占主导的因素,比如当时存在一种认为妇女应从事家务劳动和尽为人母之道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些决定了边疆妇女的生活方式。[32]
研究少数民族和两性关系的历史学家们不断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从一个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西部开发的历史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们无论是在职业的选择、政治地位的状况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经历,甚至不同背景下的妇女在处理她们与其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妇女的关系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80年代后期至今,在妇女史研究方面运用得最多的一个分析范畴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理论自从其产生的70年代发展至今,在不断的挑战之中得到了完善和丰富,虽然现在该理论存在各种流派,但其中基本的一点相同:社会性别是与生理性别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另一种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对两性关系的理解。社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的差异是由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的而非生理的差异。
“在美国,女性历史与社会性别研究一直居于新文化史研究的最前线”。[33]的确,它们不仅处于学术的最前沿,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西部妇女史,它们也分别从不同层面施以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可以说,“种族、社会性别和劳动力等范畴可以扩展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的妇女们在跨越文化和种族界线经历的历史叙述。”[34]西部妇女史的研究也在这种不断受到其它不同研究成果和理论的丰富的氛围中逐渐走向成熟。
(2)90年代:差异的女性历史
该研究近期的很多发展几乎与社会性别的研究是同步的。在西部妇女史最近期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差异的概念,并同时强调社会性别和种族、族裔、文化差异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的了解,可以认为西部妇女史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eese Linda Williams 的 Women of Oklahoma.1890-1920(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7)该书考察了在打开印第安领地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白人、黑人以及美洲印第安妇女在Oklahoma边疆的生活,作者的研究主要基于一些日记和书信等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该书的焦点汇聚于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和文化的交叉点,并着重关注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妇女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第三章中讨论了不同种族妇女间的复杂社会关系,在第四章中向读者讲述了19世纪移民对Cherokee族人传播白人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在当地建造学校的过程,黑人先锋妇女在全黑人社区又是如何充当教育、社区发展的领导者,以及妇女在国家和地区政治活动和新闻出版业中获得了怎样的成功等问题。
研究者们逐渐抛弃了这去那种将西部视为一个隔离的地区来研究的方法,转而强调一种文化的延续性。同时逐渐将妇女作为个体而非划为类型来研究,这意味着虽仍然将视妇女为一个群体,但强调的是她们的相异性。Crowe-Carraco Carol Women who made a Diffe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该书是由一系列的传记构成,她们分别是9位19世纪至20世纪之初生活在Kentuky的知名妇女,有从印第安人的虐待下死里逃生的Jemny Wiley(1760-1830),有身为教师和妻子的Lucy Audubon,也有在南方饱受摧残的黑人妇女Malinda Gatewood Bibb(1815-?),有为妇女运动出过力并为妇女权利而工作的Laura Cl-ay(1849-1941)及女记者Alice allison Dunnigan(1906-1983)等人书中讲述了当时这些妇女们不得不克服的各种种族障碍。
那篇由Joan Jensen & Darlis Miller所撰写的著名论文,终于在90年代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回应,在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Nov.92中汇集了三篇就该论文而展开讨论的新作品。其中一位作者在论文中探讨了关于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研究中的概念、方法论和语言以及有关有色人种妇女的史料编撰问题。[35]另一篇论文中,作者从政治事业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当今所指的“西部妇女史”究竟为何物,并论及人种学和民族学对历史学提出的一些挑战问题。[36]第三位研究者努力地寻找一种可以恰当地处理人种、阶级、社会性别这三者关系的理论,并谈到了新文化理论的重要性和美国西部的多民族性的特点。[37]
(3)世纪之交的超越:全新的两性历史
第一代的西部妇女史学家们觉醒于认识到女性在传统西部史的研究中几乎被完全忽视,奋起反抗那种只从男性视角研究男性社会的“他史”,并开始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复活“她史”的努力,这一工作虽然揭开了西部历史的另一维度,但所做的往往局限于对以往历史研究的批判和补充。
在运用社会性别、多元文化、差异等视角进行思考之后,在最新的研究中,女性逐步被承认为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创造者并且可以与男性同样地置于衡量历史重要意义的尺度之下进行研究。妇女的历史不再只是补充。在此基础上,西部妇女史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对象和范围也越来越具体,出现了一些就某一专门职业的妇女而做的专著,Cor-dier Mary Hurobut,Scholwomen of the prairies and Plains:per-sonal narrratives from Iowa,Kansas,and Nebraska,1860s-1920s(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2)该书描绘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Iowa,kansas,Nebraska的大草原上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妇女的生活,通过对96名妇女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学校报告、照片及档案的分析,几乎详尽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并通过这一研究反映出了美国公共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深刻变化,同时向人们讲述了这些妇女是如何从先锋教师变成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这一过程。
Sally Zanjani A minne of her own:women Prospectors in the American west(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7)该书的历史背景是1849以后California的淘金潮,作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第一本关于西部女性采矿者的专著。其研究范围不仅限于加州,而是在通往英属哥伦比亚、阿拉斯加和育空河的整个路程中,“正如该书的名字一样,该书本身也是一个先锋之作,……尤其是该书大概是得益于一个更加清楚界定解释的构架,利用了最新的社会性别史及其理论”虽然该书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其中许多高度原始自然的材料使得该书受到社会性别史和劳动史研究的青睐。”[38]
时至世纪之交,终于有学者明确地提出“是将妇女史演变发展成为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史的时候了”,[39]这一研究终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超越。在西部妇女史研究中,妇女史学家们迈出的是相同的步伐,她们提出:“今天这个更新,就民族学上而言更为宽泛也更多变的西部妇女形象是对以往旧观点的挑战,它建立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在个新的历史基准体系之下对所有妇女群体作出价值评估,并将妇女的历史编入西部历史之中,这一过程将使重写西部历史成为一项必需的事业。”[40]
这一研究对新的西部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西部史的专著,它们“都对西部历史上的民族、妇女、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西部史已步入了新的领域”。[41]
美国西部开发曾使得一群已跨入工业社会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岁月之中,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家庭和妇女是不可不被重视的。历史记述之所以有意义并且看上去有道理,关键是因为其中贯穿了具有解释效用的价值观。都是同一段历史,为何会显得色彩斑斓,就源于这一关键的地方的变化。随着人类文明已跨入网络时代,家庭、女性的地位角色势必将被重估,这一点将影响着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对西部妇女史的研究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应看到,西部妇女史的研究是一个站在西部历史和女性学、女性史研究的交叉点上的一个综合各相关学科的课题,它构建于对传统史学理论以及一些较新发展的相关理论较好的把握及综合运用之上,而且在研究实践中也势必要求其相关学科为其提供理论及材料等方面的支持。这是一项势必遇到重重的挑战的涉及深层文化改造的事业。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美国女历史学家人数的不断增加,对妇女史的研究客观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在1990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从1930-1970年间,在历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女性近占10%,但时至1988年,这一比例升至38%。而且,在过去的20年中,女性历史研究者明显职业化并且她们在历史学界的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42]在女性意识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历史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这在客观上对妇女史的研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中国女性历史的研究方面,在经过80年代的高潮后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希望在西部史研究再次升温的当前,西部妇女也能受到应有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