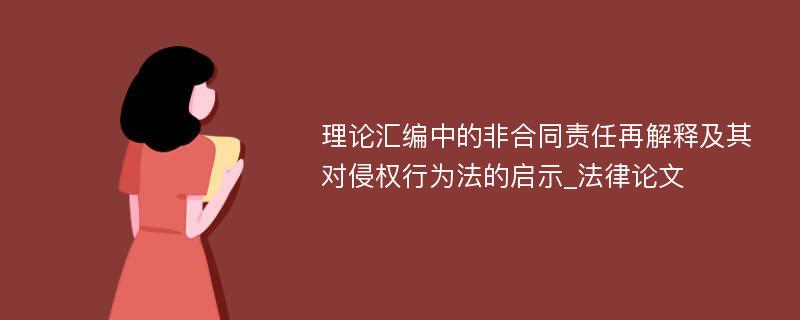
《学说汇纂》合同外责任的重新解读及其对侵权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合同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中国学者正在探讨有关“合同外责任”(responsabilità extracontrattuale)的议题,我希望通过重新解读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提供一些对该议题的讨论有益的思考。关于合同外责任的问题,我已经发表过一些论述,在此,我将补充一些新的评论,并进一步明确阐述我的观点。
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我认为强调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1.合同外民事责任是在优士丁尼诸法典的基础之上得以发展的,它确立了一个给付一笔金钱的债,这笔需要支付的钱款构成了对于因不法行为而产生的损害的“赔偿性罚金”。
2.不过,在此基础上,合同外责任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问题,有时,当涉及人时,因为对人的生命、身体、心理的完整,尊严和自由的侵害,也可确立一个支付固定数额,或根据“善良与公平”原则确定其数量的私人性质的罚金之债。
3.同样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合同外责任有时也确立了避免或排除危险情形的义务,也就是预防损害的义务。
一
关于第一点,即有关因不法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我在以前的论述中,已经提出了一个一般原则以及背离这个一般原则的一些特殊情形。
(一)就整体而言,我们看到,优士丁尼《学说汇纂》通过重新建构《阿奎利亚法》中所规定的事实构成,确立了一个一般性原则:任何故意或过失的、没有正当事由的行为,导致一个他人对其享有权利之物的毁损事件,或者致使一个人死亡或受伤,并且导致财产损害,将产生一个给付一定数目的金钱之债,这笔钱款构成了对所遭受的财产损害的赔偿。①
为此,可以认为这种事实构成由以下七个构成要件所组成:
1.行为;2.故意或过失;3.行为人的能力/可归责性;4.缺乏正当理由;5.因果关系;6.损害事件;7.侵犯与受损物有关的权利。
下面我按顺序来论述这些构成条件:
1.行为。起初,这种行为应当是“杀害”、“焚烧”、“折断”、“损伤”,通过人和物的直接接触来构成,②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一个有特定形式要求的行为”。但后来它也可以用来指没有任何直接的身体接触但“导致”了事件发生的任何行为,③这包括对本来可以阻止某一事件发生的、应当实施的特定行为的不作为。④这个深刻的转变反映在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虽然对此等因果关系的考察与对行为的分析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详见下文)。
2.故意(dolo)或过失(copla)。⑤故意是对事件发生的欲求,也包括只是接受事件的发生,而并不是行为人有意地追求达到的目的(偶然的故意)。对于过失,昆图斯·穆齐(Quinto Mucio)的定义仍然具有完全的现实意义:“没有采取一个勤勉的人本来应该能够采取的措施,或者是采取得太晚。”⑥(这个概念考虑了损害事件的“可预见性”和相应的避免它的必要性;它也可被定义为疏忽、不谨慎、无经验和行为人违反根据情况本应遵守的规范和纪律)。有时,虽然仅使用“colpa”(过错)这个术语,但也包含了故意的意思;它们构成主观方面的要素。应当注意的是,故意是一种现实的意图的态度,而过失则不需要对应于某种真实的意图,而是取决于在实施行为的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与所谓的“善良/勤勉家父”的行为构成的衡量标准之间的对照。这里说的特定情况十分宽泛,如果是那些专业化的活动,要求有相应的能力或者体力等。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疏忽、不谨慎、无经验以及违反规范和纪律总是应受谴责的,但不总是受到实际的责难,也就是说,并不总是受到法律的制裁。一般来说,只有当上述的违反产生一个损害事件时,才会有法律制裁(我之所以将其限定为“一般来说”,因为有时仅仅违反此种勤勉、谨慎和熟练的规范和纪律也会有法律制裁,例如,许多道路交通规则是关于谨慎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即使不产生损害,也将被处以罚金。同样,很多关于劳动场所的安全规则也是如此,等等)。最后,应当注意到“colpa”(过错)有时是以一种更一般的、更加非专业性的方式被使用,不是“过错——疏忽”,而是指任何一般地违反了法律规范并导致实施者的可责难性的行为。⑧
存在故意或过失才需要对导致的损害负责,这构成了一般原则的特征。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要件构成将其遭受的损害分成两组,只有那些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而遭受的损害才能得到赔偿;其他的损害被认为是“意外”,⑨他们自己要承担这些“意外的”损害,他人对这些损害的发生不存在“过错”。这样似乎违背“团结协作”原则,可以主张的是,为了平等对待与损害事件的发生有关的人,受害者也只应当承担那些因他的过错产生的损害。⑩但是,一方面,将一个人或一个物放入产生某一特定事件的因果关系序列的发展中,并不能自动地显现出责任本身,(11)只有当行为不再表现为特定的形式,行为人对事件的产生本身不再是显而易见(参见上述)时,通过法学家的分析才会出现故意和过失的要件。另一方面,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东西由于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遭受的损失负责,这一事实符合合同责任领域中阐明,但是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所有人承担物的灭失的风险”,或者“意外事件由所有人承担”,根据这一原则,只有在那些典型情形中,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背离此原则(参见第(二)点第2部分);这些典型情形可以变得很多、很宽泛,但相对于一般原则(至今它仍是罗马法系的基本特征),它们仍然是作为例外而存在(超越这个一般原则的另一个方式是保险,可以是个人的、自愿的或者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社会安全的公共体系规定的,实际上,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它对与合同外责任有关的社会关系影响深远)。(12)
3.行为人的能力,对一个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因素的行为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必要的前提。对于疯人,将他的行为等同于一个意外事件,排除他的责任,如同掉下一片瓦片或者由动物造成的损害。对于孩子,六岁之前不需要负责任,而从七岁到适婚之间,则认为应当承担责任,这建立在《十二表法》中对同样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偷盗责任的法律规范的类推论证的基础之上。(13)
但是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可以有一些可能的发展。事实上:
(1)类比于动物和瓦片,应该使我们注意到,对于动物,排除了《阿奎利亚法》上的责任,但具有《十二表法》中有关动物引起的损害的责任。(14)关于掉落的瓦片的问题,涉及相邻关系的规定,后者可以通过一个允诺对还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损害提供赔偿的保证,也即潜在损害担保(cautio damni infecti),在此基础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将被要求承担责任,除非存在不可抗力。(15)
(2)另外,关于无能力人,提出其照管的问题。事实上,对危险的疯人和他们的犯罪,在一个罗马皇帝的批复中已经强调了:照管疯人者应当谨慎行使他们的职责,使得被照管人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来说都不是有害的。(16)就这样,通过一个情况非常严重的具体案件,在不可归责的人的非法行为问题上,引入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潜在扩张性的原则。(17)
4.缺乏正当理由,或者行为具有违法性,是本质性的要素。我曾列举过主要的正当理由,这些类型并不是严格的典型化的:正当防卫、(18)自力救济、(19)紧急避险、(20)行使一项权利或者被允许的权能,(21)只要不故意或过失地超过其功能上的限度。(22)
关于这些排除责任的情形,可以简要地强调一下有关“紧急避险”的一个问题。在一方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也即为了保护一部分的装载货物和船只,而将一些货物丢入海中,对此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规定如何在所有的人之间连带地分配损失,对这样的情况,在此我不具体展开分析。(23)在另外一方面,在有关的文献中,讨论的典型案例是,在火灾中,将处于中间位置的房屋毁坏,以避免火势蔓延。对此案的分析存在一个有意思的说法:被毁坏的房屋也属于因火灾的原因而“同样地灭失”,所以不认为是一个损害。(24)不过,这个视角关注了一个人为了避免对另一个人的损害而遭受的损害,由此开启了一种考虑到这样的损害如果不发生的话,当事人的利益如何予以重新平衡的规定。(25)
5.因果关系的分析与《阿奎利亚法》文本中描述的行为紧密相关。它与行为的分离是我们基于法学家对一些特定案例的思考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抽象化和重新整理的结果。
拉贝奥所考察的行为的因果效力是具体的。一个文本提到:“如果有人轻微地击打一个生病的奴隶,而此奴隶死亡,拉贝奥正确地说,此人应根据《阿奎利亚法》负责。因为一个行为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致命的,而对另一个来说却不是。”(26)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具体情况中,此行为对于那个奴隶来说是致命的。在拉贝奥分析的情况中,讨论了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被放入导致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中,而先于它存在的那些因素并不能够导致该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考察的某个行为,同时伴随着,或者之后尾随着其他的要素,因果关系的链条的辨别将变得更加复杂。对此似乎存在不同的理论构建,其不同之处,对分析嗣后的因果关系来说变得很重要。
首先是多个行为人的情形,这些行为人共同制造了一个导致某事件发生的事实(一根坠落的梁压倒了一个人),(27)这时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仅由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导致事件发生,这样的事实并不重要,事实上,考虑每个人单独的行为都不能引发事件,因此也不是法律规定的行为,这样的观点可能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即没有人应当负责任。(28)如果事实是多重的(同一个人多处受伤),应当区分每个人的行为的份量,如果能够知道哪个是具有决定性的,责任可以只由制造这个致命伤害的人承担;如果不能知道谁是这个导致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决定性行为的行为人,和前一个例子一样,由所有的人都承担责任。(29)
接着是这样一种情况,多个都能够引发事件的原因,不是同时发生,而是相继发生。在具体因果关系的基础上,事件应认为由最后一个原因导致,因为只是与这个原因相关联,事件才具体发生了;可能由前面的其他因果因素导致的事件,即使这些因果要素能够单独产生该事件,事实上也并没有发生。因此,造成前面的因果要素的人不必为可能导致的事件负责,只有带来最后的因果要素的人是有责任的。即使没有发生前面的因果要素,不可能会发生后面的因果因素,也是一样的(如果后来的因果要素不是人的行为,而是自然事件,理由也是相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发先前因素的人也并不用负责)。(30)不过,与此解决方案不同的观点认为,责任应由双方承担。论证的理由是,这里应该类比多个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形,即每个人的个别行为都不能导致事件的发生。(31)在这种分析中,似乎与具体的因果关系脱离了。(32)
6.损害事件是由杀害或伤害一个奴隶,或者毁坏或减损一个物所构成。
关于损害事实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已经论述过的方面,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想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对损害事件,应当注意到,在扩张《阿奎利亚法》适用范围的过程中,也考虑到物从物理的角度看仍然是完整的,或者总之没有发生减损,但为了能够使用它,必须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33)
进而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也即没有导致物受到损坏,而是因为使其被抢或被偷,导致物不可获得。这些情形先是以典型的方式进行处理的,后来被归到一个模仿那些可归于《阿奎利亚法》责任的行为的诉讼中。此方面的典型的例子是解开他人奴隶的束缚,使其逃跑。这被放在诈欺之诉中讨论,可能是因为并没有造成对物的实际损害,但行为同样侵犯了所有权人的权利。(34)将这个案例归入到《阿奎利亚法》(35)的领域说明了《阿奎利亚法》发展的一个轨迹。(36)根据这一发展,损害事件不再必须是一个物的实际的毁坏或减损,也可以是另一种损害类型,即导致暂时或永久地失去受法律保护的对物的“用途”,即使物品仍然是完整的,或者为了恢复这种用途需要支出费用(这种理解损害事件的不同方式对应的是一种不同的对损害的评估方式,即不再仅仅关注对物本身及其可能的附属物的评估,也包括这个物作为财产要素的价值,即丢失物所导致的财产价值本身和/或此等物提供的“用途”的丧失)。(37)
7.受损害之物属于他人,直接表现了对权利的侵害(通过对物本身的侵害来体现)的特征。对于这点,阅读原始文献也可以看到进一步发展的线索。
在前面已描述的损害事件及可估价性的扩展的框架内,对那些非所有权人的主体的法律保护也得到了扩展,他们应当是与物有关的“用途”的享有者,并且他们对物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阿奎利亚法》提供的法律保护就不仅仅限于所有权人,也适用于用益权人、(38)使用权人、(39)导水地役权(40)或者质押的权利人。(41)对他们来说,存在一个如果物没有被毁坏或减损,他们原本可以享有的财产利益的评估。从物权的角度看,他们是权利人,但不像所有权人享有那么完整的权利;在质权的情况中,它涉及的利益并不包括使用或收益,而仅仅是表现为担保功能的“用途”。另外,对他物权人利益的保护义务不仅仅存在于由第三人引发损害的情况,也包括由所有权人本身对物品造成的毁损或损坏的情况。(42)
进而,我们看到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当第三人损坏或减损被借物或租赁物时,物的借用人(43)或土地的承租人(44)是否也可以提起一个赔偿金之诉(很明显,如果是所有权人所为,将适用与债的关系相关的诉讼,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议题之内)。借用人和承租人对物不享有物权,只是相对于债务关系的另一个主体来说,他是一个权利的享有者。只限于考虑某个主体暂时地持有一个物,从中获取“用途”,并且这种持有是由差别很大的不同的合同所产生的效果,(45)我们看到在这里就开启了第三人行为对债的关系的损害的赔偿这个重大问题。在罗马法学家中存在广泛争论的是,即使排除了直接诉讼,是否也不曾规定过一个扩用之诉或事实之诉。(46)即使对此存在一些疑问,我认为很有必要指出,就如同后来的评注(Glossa)中所支持的那样,(47)对因动物招致的损害,借用人或承租人也享有诉权,(48)因此这个做法在《学说汇纂》的同一卷已经开启。而对原始文献,需要关注其统一性,我在其他场合已经强调了这个问题。另外,在《学说汇纂》第九卷之外,对第三人破坏债务适用诈欺之诉,从这个诉权的授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此等损害类型日益成熟的关注。(49)(利用诈欺之诉的可能性应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个诉讼在合同外责任的罗马法体系中的作用:事实上,诈欺在现代学说中已被法律行为之意思瑕疵的框架所吸收,通过“诈欺——欺骗”导致实施法律上的行为一方的错误;但也存在其他发生诈欺但不产生合同责任的可能性,对于这些情形允许诈欺之诉,可见诈欺之诉具有很大的弹性。(50)(51)
二
我已强调过,解读《学说汇纂》中论述《阿奎利亚法》的这卷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也包括了不要求存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形,或者甚至负担损害赔偿的主体不需要有一个行为的情形。
第一个情形是我在前面附带提到过的非野生动物招致的损害,并且饲养动物的人或者第三人没有过错;如果饲养动物的人有过错,他本人应当对该事件负责,对此情形适用一般原则。(52)如果使用动物的人或者第三人没有过错,并且事件的原因源于一个反常的行为或动物的劣性,此动物的所有权人应当承担责任。(53)在这种情况中,他不是基于他的过错或者行为承担责任,而仅是基于他是所有权人这一事实。我认为,可以补充一点,如果证明这是一次意外事件,所有权人的责任可以免除(54)。(55)
在第九卷中,另一个有关的情形是:在一条街道上,从一个公寓的上层掉落或抛掷的物对一个路人造成的损害事件。对于这个情形,考虑到经过这些街道的行人“安全”的特别需要,(56)以及多层公寓的建造所带来的危险,住在这座公寓的这个人对于从其中掉下或抛下的物承担责任,不要求存在过失或者故意,甚至也不需要他的一个行为:事实上,他只是基于与他居住的房屋的关系被要求负担责任。(57)对这个情形有许多的讨论,有一些解释者希望提出过错的要件,有的时候房屋的住户没有选择好管理房屋的人也是一种过错,而这个人导致了损害事件的发生。不过,重读《学说汇纂》可以确定,罗马法学家在这种情形中创造了过错的一般原则在上述情形之外的另一个例外。(58)
同样在第九卷中,优士丁尼的法学家们创造了一章有关处于家父权之下的人的责任,此即《学说汇纂》第九卷第四章,规定了无过错的和非基于家父行为的责任。这种责任在现代不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但体现了对合同外责任一个重要方面的思考,也就是对具有扶养和教育职责的人(子女/未成年人,学生,学徒)的行为,对在家庭中合作的人的行为,以及对下属的行为负责的情形。(59)与此相近的是对有关职员的行为负责,这首先是从有关船东、旅店主、旅途中更换马匹的驿站的所有人的问题开始的(《学说汇纂》第四卷第九章)。(60)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情形中,责任的归责的标准不可归结于上面研究的过错的一般原则,必须提出可归责性的专门因素及其基础;这里不能对此继续深入探讨。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其他导致损害赔偿的情形。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强调的是,这些是有限的类型,构成了一般原则的例外。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无过错责任的情形并不建立在同一个归责标准的基础之上,而是各自不同的:从对产生损害的物享有所有权;对产生损害的物的使用;与导致损害的人存在一种权力或教育的关系;与导致损害的人存在一种家庭性质的合作关系;与导致损害的人,在生产性企业中存在劳动合作关系;某些被特别指出来的活动所具有的特殊的危险性;主动开展某些活动,以及/或者经济利益,等等。(61)
三
“合同外责任”并不仅局限于损害赔偿之债的问题,有时,在有关对自由人的损害的情形中,也可以表现给付一个固定的、或根据“善良与公正”所要求的数额的私人性质的罚金之债。
从最初的私犯发展出一种涉及“处罚”的债,而处罚的理念与赔偿的理念是对立的。不过,《阿奎利亚法》规定的对私犯的罚金和其他的不同,它逐渐被转化到损害赔偿的方向上去(关于损害的评估,从物的“价格”或者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62)再到此物所具有的所有利益,(63)再转变为如果没有遭受行为人所导致的毁坏或减损,该物所具有的全部利益的价值)。(64)这个赔偿性的罚金被认为是“混合性的”。
私犯中还包括对人的“侵辱”(iniuria),它包括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对自由人的侵害行为,包括侵害荣誉、自由以及身体的完整。对这种私犯的处罚也是一个金钱之债,以“救济”为目的,并不根据“物所具有的利益”来计算,而是根据“善良与公正”所要求的数额来计算。(65)
这两种私犯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因此当同一个事实同时符合了二者的构成要件,就有可能导致从它们中产生的债和相关诉讼的共同存在的可能性:这里的并存是聚合性的,因为“受保护的利益”(财产的完整/人的尊严)和“要求给付的罚金”(赔偿性罚金/救济性罚金)在两个不同的类型中是不同的。(66)但这个聚合性质的并存被重新考虑了,作为结论,提出了一个赔偿性罚金和侵辱罚金的结合,人们认为,如果依据其中一个诉已经获得支付,当提起另外一个诉的时候,应当进行相应的扣除。更确切地说,如果受到损害的一方已经根据《阿奎利亚法》通过赔偿性罚金的支付获得赔偿,当法官根据“善良与公正”所要求的标准计算对人的不法行为的救济性罚金时,应当扣除受害人先前已经获得的支付,否则的话,前一种罚金将被考虑两次,因为第二个估算是更加宽泛的,已经包括了前者在内。(67)
不论是最初的聚合性质的并存,还是两个方面的结合,都说明了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复杂问题。它说明,对人的完整性的侵害有双重的维度:即损害和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后一个维度不能简单地被损害赔偿所吸收。
在《学说汇纂》第九卷中,(68)关注的主要方面是针对“混合的”情形。在该情形中,关于罚金的理念,一方面被延续下来,另外一方面则有一定的缓和。这个罚金,结合了“损害赔偿”与“侵辱的救济”两个方面的因素,并且即使通过重新组织材料,仍然特别关注着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对此,我们尤其可以看到,《阿奎利亚法》将其适用扩展到对自由人的侵害的时候,强调了只考虑医疗费用和由于暂时和永久的无能力而造成收入损失的层面,这些是依照损害赔偿性质的罚金的计算原则来核算的。(69)这也是在因动物产生的责任的例子中唯一被考虑的层面,而明确规定另一个层面不被考虑,因为“自由人的身体不允许根据它所具有的利益来计算”。(70)进而,这个观点被发展到因从房屋的高处抛落或掉落的物致伤路人的情形中。(71)最后,对于因同一事实致死的情形,规定了一个支付固定数额的罚金的债,这很明显表明了它不具有赔偿的性质。(72)
现代学理对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解释,首先使得任何类型的“罚金”、责备、处罚的规定都属于公法,因此由国家垄断,而对于“私人”只留下损害赔偿的领域。处罚和赔偿的视角,反映在一些法典的术语中,有一些法典仍然保留了处罚的维度,将我们正在讨论的类型叫做“私犯”(delitto),而其他一些法典则完全取消了这样的维度。(73)但是,对于这种删除是否合适,仍然是可以质疑的。现代学理解释简单化的删除,同时割裂了二者之间联系的脉络,而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缺漏,则构建了“精神损害”这一自相矛盾的概念。
对人的侵害既引起损害(医疗费用,收入的减少等),在一些情形中,也包括对人的尊严的侵辱,对后者需要的并不是进行赔偿,根据罗马法,这是需要通过固定的或者根据“善良和公正”的标准所确定的罚金来救济。(74)
四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合同外责任”,根据罗马法的贡献,有时也包括了排除具有潜在危害的情形的义务,即预防损害。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许多潜在的会产生损害的因素和行为,以及我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有害后果。
毫无疑问,盖尤斯和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将私犯放在债的渊源中,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体系化工作,这种成就是不应当被抛弃的。“过错应当被处罚”这一规则的中心地位,是合同外责任的一般原则的基础,它强调了勤勉、谨慎、熟练的标准,也因此就实现了对损害的预防。后来,无过错的损害赔偿之债的情形则矫正了利益衡量上的一些失衡,这些矫正对于一些特别界定的情形是很有用的。
不过,现实情况总是很复杂的,法律制度有着多重的内涵。如果只看到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这条线索,将会带来片面性并失去许多其他可能的贡献。
对《学说汇纂》第九卷的分析展示了有关制度更多的内涵。在《学说汇纂》第九卷第三章中,在从窗户抛落物或掉落物的情形之外,还规定了一个完全是预防损害发生的性质的类型,即可能砸到路人的放置物或悬挂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民众诉讼对这样放置物品的人提起诉讼,而后者将受到一个数额固定的罚金的处罚,该罚金将支付给起诉者。受到处罚的不是放置物品的行为,或者是某个需要明确的主体的行为,而是将物品放在这个危险位置的事实。与其他情形不同的是,没有规定对可能的损害赔偿的担保,而是直接规定一个违反不实施该行为的义务的罚金之债,这具有一个明显、强化了的对损害的预防功能:这里的责任并不指对还未发生的损害的赔偿之债,而是一个对具有潜在危害的行为的处罚。
更进一步的可能的发展是引入一些在这一章中没有被系统规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合同外责任不再局限于债的渊源问题之内。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对公共物、洁净的空气和水的保护中,我们看到“民众禁令”(interdetti popolari)的使用,即根据一个长官的简单分授权和即时裁决,同样是市民的人,也可以针对其他私人实施的禁令,被执行禁令的人应当中止其活动,如果他坚持的话,必须证明他的活动的正确性和无害性。私人将垃圾倒入水道造成水污染,而没有经过有权的官员的批准,此等行为应当被制止;(75)不履行本应由私人完成的垃圾清理并造成空气污染,可介入并弥补之;(76)对水网的改变,可能带来损害的,(77)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包含了大量的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的章节,对此我在另一个论述中已经大致描述了。(78)
也许并不必须将这些内容放在一个统一的法律或者法典的一卷中。不过,如果想要整体地重建合同外责任的体系,我认为,将罗马法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问题的这些方面,也考虑在内,非常重要。预防损害发生的这个层面,是这个议题中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方面。(79)
注释:
①在我看来,1986年的《民法通则》在第106条第2款已规定了这个原则,最新的中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稿)第7条第1款也做了规定。它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草案》中与其他标准的关系,参见第(二)点第2部分的论述。
②D.9,2,7,1:“杀害应当理解为:某人用剑、棍棒或其他武器以及用手(如卡死)、脚、头及其他方式杀死他人者。”另外可参见D.9,2,51pr.;D.9,2,27,6;D.9,2,27.(《民法大全选译 私犯之债阿奎利亚法》,米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D.9,2,7,3;D.9,2,7,6;D.9,2,9pr.;D.9,2,29,5;D.9,2,9,2;Gai.3,219;J.4,3,16.
④D.9,2,8pr.(“即使医生手术良好,但进一步的治疗处理却被懈怠,则他不能被免除责任,而要被视为有过错而负责任”)。所有权人“忽视”对受伤的奴隶的照顾也属于这种类型的行为(D.9,2,52pr.):在这个情形中,他要承担责任,因为一个人应当对由他的过错产生的损害负责。
⑤J.4,3,3:“任何人既因故意,又因过失按这一法律承担责任。”《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版),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意大利语中,colpa既可指过失,也可指过错,本文根据具体语境选择翻译——译者注。
⑥D.9,2,31.
⑦D.9,2,8:“一般认为,如果骡夫由于没有经验而不能驾驭骡子,结果踏死他人奴隶,那么他即因有过错而负责。同样,如果是因其力弱而未能控制住骡子,那么将力弱视为过错并无不公;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从事他明知或必然知道由于他的力弱会给别人带来危险的工作。”D.9,2,27,29。“过错”这个概念总是包含了对实施这个行为的人的谴责。
⑧“过错——疏忽”的标准是对规范的违反,此规范的基础是“可预见性”,也就是为了防止可预见到的消极事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相当于在特定的环境中根据这些规则所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就如同前面说到的,有时候,“colpa”(过错)这个术语在更普遍和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包括了不遵守非基于勤勉、谨慎而设置的规范。这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比如,一个练习标枪的人应该遵守谨慎的规范在特定的标枪练习场内练习,如果击中了一个突然穿过场地的人并不构成过错(除非他为了开一个危险的玩笑将标枪掷向他看见的正在穿过的人);如果他在另外一个不同于此的场地扔掷标枪,则构成过错,因为违反了谨慎的规范(D.9,2,94)。但是如果我们将在场地里练习的人分为士兵和非士兵,并且我们认为后者总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在任何情况下进行类似的训练,应该说,这个禁令不是一个有关谨慎的法律规范;说一个不是士兵的人置禁令于不顾,在场地进行练习,属于“过错”,这构成了一个对“colpa”(过错)这个术语更宽泛的使用,并且导致一种更加宽泛的责任概念(J.4,3,4)。如果“过错——疏忽”是建立在“事件的可预见性”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在一些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个更加严格的关于“预防措施”的标准。
⑨J.4,3,3:“意外事故”;Gai.3,211的末尾:“因此,那些在无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偶然地造成损害的人,不受惩罚。”(《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D.50,17,203,包含了这个原则:“一个人因自己的过错招致损害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损害,也就是不受到赔偿。”(quod quis ex culpa sua damnum sentit,non intellegitur damnum sentire.)
(11)D.9,2,7,2:“如果某人,因为别人推了他一下,引起了一个损害……被推的这个人不用负责任因为并没有不正当地引起损害”;D.9,2,52,2(最后两行,参见注释32);D.9,2,29,4:“如果一条船使迎面驶来的另一条船沉没……;但如果这船是由于不能控制的推动力驱动……”
(12)《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2条规定(《民法通则》第132条已有规定),在行为人和受害者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就是受到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在各方之间分担损失。我认为这是对“团结协作”的需求的高度认同。我认为:(1)适用有关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的情形的如此一般性的规范,会具有技术上的难度,特别是在引发事件的原因很复杂,尤其是同时存在多个原因的情况中;(2)有必要确认如何与该草案第28条有关不可抗力的规定相协调;(3)最关键的是,由于该规定极其一般化,在确认其中所规定的“实际情况”时具有技术上的困难(客观方面,也就是实现损害的方式;或者是主观方面,比如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因此,在阐述该规范的理由上存在着困难,也就是说,它究竟是想对经济上更弱的一方提供某种保护,还是想要将经济损失转移给更有能力以间接的方式,转移给社会整体(比如,一个大型的生产企业将赔偿计算在它的“生产成本”中,然后“转移”到产品的定价中)。
(13)D.9,2,5,2:“由此便产生疑问:如果一个精神病人造成损害,是否也可提起阿奎利亚法诉讼?贝加苏予以否认:因为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又何以存在过错呢?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样,如果一个四足家畜引起损害或者一片房瓦从屋顶落下,阿奎利亚法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即令一个儿童造成损害也视为同样。然而如果是未适婚人引起损害,则拉贝奥认为,由于未适婚人对偷盗负责,所以同样也要依《阿奎利亚法》负责。我认为,如果该适婚人能够实施不法行为,那么这就是正确的。”同样的规则在D.47,2,23中也被提到,并形成了“过错的能力”这个概念。
(14)D.9,1.(参见下述)
(15)D.39,2,43 pr.:“某人允诺为邻人提供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损害的担保。由于风的原因,瓦片从屋顶掉落在邻居的瓦片上并将其砸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因此而给付什么东西。答复是:如果是因为房屋的瑕疵或者不够坚固的话,应当给付;但如果风的强度太大,以至于即使房屋足够坚固仍然能够掀落瓦片,那么不应当给付。”;D.39,2,24,4.
(16)D.1,18,14:“[给调查的官员]……如果你传唤了在那个时候对他进行看管的人并已经调查了他们疏忽的原因,根据你认为是否属于他的过错的可能对看管人中的每一个人做出判决,我们认为你做的是正确的。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使疯子自己不受到损害,而且也为了使别人不受到损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应该有理由归罪于那些在[履行]他们的看管职责中特别疏忽大意的人。”(《学说汇纂第1卷》,罗智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1条规定了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责任,并由无能力者进行适当的补偿。
(17)被引用的这个片断被认为是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条的历史基础。(Di Marzo,Le basi romanistiche del Codice civile,Torino,1950).“在损害是由无判断能力或无意思能力的人(persona incapace di intendere o di di volere)导致时,应由对无能力的人负有监护义务的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他不可能阻止该行为的除外。”
(18)D.9,2,3;D.9,2,4;D.9,2,5pr.;D.9,2,30pr.;D.9,2,45,4;D.9,2,52,1.《意大利民法典》第2044条规定了这个正当理由。《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9条规定了行使正当防卫的主体不应当超过防卫的必要的限度。
(19)D.9,2,39.
(20)D.9,2,29,3; D.9,2,49,1 ; D.43,24,7,4 ;D.47,9,3,7 ; D.19,5,14pr.
(21)D.9,2,5,3; D.19,2,13,4; D.9,2,7,4 ; D.9,2,29pr.; D.9,2,29,7; D.9,2,31
(22)D.9,2,5pr.;D.9,2,6; D.9,2,27,7 (阻止抚养); D.9,2,39; D.18,6,14 ecc.
(23)D.19,5,14 pr.; D.14,2有关共同海损的《罗德法》。
(24)D.43,24,7,4:“还有一种抗辩,杰尔苏怀疑是否可用以对抗原告:为了阻止火势蔓延我拆掉了邻居的房屋,结果我将被提起暴力或欺瞒之诉,或被提起非法损害之诉。法学家加卢怀疑是否应将‘为了阻止火势蔓延而拆掉邻居房屋的抗辩’放入诉讼程式中。法学家塞尔维说,如果拆除是执法官所为,裁判官应将这一抗辩权授予他,但同一抗辩权不得给予私人;但如果是通过暴力或者隐瞒的方式完成的,如果火势不至于蔓延到被拆毁的地方,争议应当按它的价值来评价;如果火势到达了房屋,拆掉建筑物的人应当被免责。塞尔维还说,如果有人被控诉‘非法损害’,也是一样,因为没有招致任何的不法行为,也不存在任何损害,因为建筑物一样会被烧毁。如果某人是在没有火灾的时候完成了这个行为,而后又发现了火宅,不能以此为借口,因为拉贝奥认为,不能依据将来的事件来证实是否引起损害,而是应当根据现今的情况。”
(25)《意大利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了“在法官公平判定的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0条规定了紧急情况下对避免损害的干预的合法性,即使干预是有害的,以及适当地分配损害的可能性。
(26)D.9,2,7,5.
(27)D.9,2,11,4:“如果几个人扔下一根横梁并因此砸死一个奴隶,那么按早期法学家们的看法,他们都依《阿奎利亚法》负责。”D.9,2,51,1-2(参见注释(31)及(28))
(28)D.9,2,51,2的末尾:“……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个规定是荒谬的,那他应该想到,如果没有人要为此负责将更加荒谬……如果数人蓄意偷窃,共同将他人的房梁拖走,而该房梁单个人是拖不动的,于是,所有参与者都要依盗窃诉讼负责,尽管根据缜密的推理,他们中谁也不负责任,因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将此房梁拖走。”
(29)D.9,2,11,2:“但如果数人将一个奴隶打死,那就要查证,是否所有这些人都应负杀害的责任。当其显然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殴打致死时,那么这个人即负杀害的责任。但当致命的打击不明时,那么依尤里安之见,所有的人都要负杀害的责任;而且,如果针对其中一人起诉,其余人不因此免责。”;D.9,2,51,1,参见下面的注释。我认为《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1、12条对此问题的规定很有意思。
(30)D.9,2,15,1:“如果一个受了致命伤的奴隶在随后发生的某物倒塌、船只失事或其他人的打击下过早死去,那么,不能按杀害而要按伤害起诉;不过,当一个受了致命伤的奴隶在被解放或转让后,因此伤而死,则可以杀害起诉。这两种方案之间之所以有如此的区别,是因为,对于后一种情形来说,按照《阿奎利亚法》,你的确已在伤害了他的时候杀害了他,尽管这种后果只是在他死亡时才明显表现出来;而在第一种情况下,某物的倒塌并不能够用来确定他是否被杀。”相同的方式:D.9,2,52pr.:“如果一个奴隶受伤而死,其死亡既不是因为医生的能力不足,也不是因为主人方面的过失,那么,加害人将因不法杀害而被起诉。”(这个片断还表明,如果受伤的奴隶是因为后来的医生的能力不足或者主人的疏忽而死亡的,使他受伤的人没有责任,而由医生或者主人负责)。
(31)D.9,2,51pr.:“一个奴隶受到严重伤害,以致他将肯定死于这一打击,这期间他又被指定为继承人,后来又由于另一个人的打击而死亡。我问:是否对二者均可按《阿奎利亚法》以杀害提起诉讼。尤里安回答:一般说,某个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提供了死因,那么他就杀了人。但依《阿奎利亚法》,将“杀”一词的意义理解为用暴力,并且几乎是用手造成死亡,这是明显取自对“殴打”(caedere)和“打死”(caedes)这两个词的解释。此外,依据《阿奎利亚法》,并不仅仅是那些将某人当场杀死的人要负责任,而且那个因其伤害而肯定使某人死亡的人也要负责。因为,如果某人给一奴隶造成致命伤,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将同一奴隶殴打,以致其比因受第一个伤害而死的时间提前,那么就要判决二者均依《阿奎利亚法》负责。”
(32)我要重申的是,在一般原则的范围内,分析因果关系并不足以确认责任的承担;如上所述,过错也是必须的。并不只是在现在提到的这些例子中,责任人的行为是可受谴责的,但可以增加一个关于一连串因果序列的案例,其中,将具有可谴责性的行为当作是导致责任的行为:D.9,2,52,2:“骡子正拉着两辆装载的板车向城府的山坡上行使,前一辆车的车夫顶住往回倒退的板车,以减轻骡子的负重。在此时,前面的车开始向后滑退,在两车之间的车夫从中间跳出之后,后面的车被前面的车撞上向后退下并碾过一个奴隶的小男孩。该小男孩的主人问,他现在应起诉谁。我回答,法律的解决方法应从原因中寻找,因为如果顶住了前面车的车夫随意地放了手以致其骡子不能驾驶住车而由其自身的重量后倒,那么对骡子的主人则不发生诉讼,而对将车顶住的那些人则可依《阿奎利亚法》起诉。……但是如果骡子受到无论何物的惊吓或车夫由于恐惧被压倒而放开骡车,则对车夫不能起诉,而对骡子的主人起诉。但是如果既不是骡子的问题也不是车夫的问题,而是骡子不能驾驭重量,或者是当骡子正努力驾驭时滑倒或摔倒,以致车子后倒,而车夫由于车子后倒不能控制住车重,那么这时既不能控告骡子的主人,也不能控告车夫。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都不得对后面的骡车主人提起诉讼,因为后面的骡车不是自动地倒后,而是被撞倒了。”
(33)D.9,2,27,14:“如果你在他人的谷地里扔了草或燕麦,污染庄稼。所有权人……可请求事实诉讼。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同于损坏物或者使物变质的损害类型,或者说,对物没有任何损害,只是将其他人的东西混入该物中,将其分离开来成为一个负担。”;D.9,2,27,20;D.9,2,27,17:“如果行为人实际并未把奴隶的价值减少或缩小其用途,则不能提起阿奎利亚法之诉,而只能提起不法行为之诉。因为《阿奎利亚法》诉讼产生于造成了损害的侵害。如果一个奴隶虽然没有减少其价值,但却为治疗和痊愈而花费,我认为这种情况是造成了损害,故可以根据《阿奎利亚法》提起诉讼。”(一般的事实之诉参见:D.19,5,11)
(34)D.4,3,7,7:“拉贝奥也问到:如果你解开了我被缚的奴隶,他因此逃跑,是否须授予诈欺之诉?而昆图斯在对拉贝奥的注释中说:如果你这样做不是出于怜悯,你承担盗窃之诉;如果是出于怜悯,应被授予事实之诉。”
(35)J.4,3,16末尾:“……但如果不是以身体实施损害,伤害也不是对身体造成……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和扩用的阿奎利亚诉权皆不敷使用,已决定,有罪过者应就基于事实之诉承担责任。例如,某人出于怜悯解开了他人奴隶的镣铐,让他逃脱的情况。”
(36)其他要考虑的例子有:D.47,2,50,4,某人放走牧群,但并不是为了让同谋偷盗,而仅仅因为不加以考虑;类似的可见Gai.3,202,片段的末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阿奎利亚法的扩展适用,要求存在物的损坏,或者只要对于所有权人来说物已丢失即可;对于后者,应该考虑J.4,1,11(中间部分)提到的事实之诉,其中对于仍然保持完整的物、但侵犯其受法律保护的使用权的情形也存在损害责任。另外还有D.19,5,23,D.19,5,14pr.
(37)也请参见第三部分。
(38)D.9,2,11,10;D.9,2,12.
(39)D.4,3,7,4.
(40)D.D.9,2,27,32.
(41)D.9,2,30,1.
(42)D.9,2,17.
(43)D.9,2,11,9.
(44)D.9,2,27,14.
(45)人们认为,使用借贷是一种单务的、无偿的合同,而租赁是双务合同,有一系列确认双方责任的分析。
(46)主要的争议与这个例子有关:第三人损害了借用人或租赁人应当返还的物,产生了他们对出借人或出租人的(合同)责任,也就是他们应有的保护(D.19,2,41)。但问题并不限于这个层面;很明显,还包括在他们享有物的阶段对物的用途的消减,这应当在不同的合同中有不同的处理。
(47)Glossa:comodata a D.9,1,2.
(48)D.9,1,2pr.
(49)D.4,3,18,5:“如果他人杀害了你允诺给我的奴隶,多数法学家正确地认为,应当授予关于诈欺的诉权对抗他,因为你已被解除了对我的义务。”;D.4,3,19.
(50)关于一般诈欺抗辩,参见D.4,3;在此不能展开这个议题。
(51)这开启了一个问题的发展,即处于债的关系外的第三人对债权人的损害。在意大利,第三人的合同外责任首先是在有关由于一个不法行为引发债务人的死亡而给关于抚养的债权带来损失的情况中得到发展。一般来说,抚养债务人根据法律,依据亲属关系承担这个抚养职责,因此对他而言只存在义务;债务人的死亡引起债务的消灭;但如果是因为第三人故意的或过错的行为引发的死亡,对债权人的间接损害是明显的。进一步的问题涉及某个承担了不可替代的给付义务的债务人的死亡的情形。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议。
(52)D.9,1,1,4-5;除了饲养动物的人,第三人也可以导致动物造成损害:D.9,1,1,7等;也可参见已经引用的D.9,2,8,1;D.9,2,52,2等片段。
(53)D.9,1,1,4:“因此,如同塞尔维所写到的,在四足动物的野性被激发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发生这一诉权。例如,爱踢的马踢了人的情况;或爱攻击的牛用角攻击了人的情况;或过分野性的母骡致人损害的情况。而如果由于地面不平、或由于赶骡人的过错、或在超过正常驮载的情况下,四足动物翻倒所负载的货物在某人身上,不适用这一诉权,而应依《阿奎利亚法》提起不法损害之诉。”(如果所有权人让其他人使用动物,已经告诉他动物的瑕疵,不负担责任。)
(54)D.9,2,52,2;事实上,这个片段并没有深化在其他片段中已经提到的某人使骡车承载过多的问题,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55)《意大利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了“所有权人和利用人”的责任。《侵权责任法草案》的第78条规定了“饲养”动物者的责任。我想提起注意的是,当饲养者没有被告知动物的恶习的时候,他所承担的责任与动物所有人的责任是有差别的。
(56)D.9,3,1,1-2.
(57)D.9,3,1,3:“即使悬挂物掉落,即使没有人将它抛落”;D.9,3,1,4:“这一诉权被授予用来对抗那些居住在房屋中的人……虽然提起的是不法损害之诉,也不要增加对过错因素的关注。”
(58)这个类型没有包括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也没有包括在1865年和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我认为是一个漏洞;它出现在现今有效的1857年的《智利民法典》第2328条;1871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119、1121条;1917年的《巴西民法典》第1529条,由2002年的新民法典第938条保留。类似的是《侵权责任法草案》第82条。
(59)这个问题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048条,《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1条中得到论述。
(60)这个问题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049条,《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3条中得到论述。
(61)我认为指出这点是很重要的:1986年《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该条第3款提出了,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时候,适用无过错责任;第3款没有具体列举这些情形,仅指出了在该法的其他部分或者其他法律中存在着关于无过错责任的情形的规定,因此这一款的规定在这一问题上,只具有体系建构的功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8条采用了同样的做法(我很遗憾不能仔细分析上述提到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的条文)。关于这个规定,我对于《侵权责任法草案》第2条以更笼统的方式做出的规定有些疑惑。这个条文提出了一个不需要过错作为要件的规范,因此更加一般化。当然,对此应当注意到该草案第17条规定的各种救济措施(在《民法通则》第137条中对这些措施已有规定)。我在开头的第三点已经指出(对此在第四部分还将做一些论述),在罗马法中也规定了预防措施。对于那些旨在于预防或中断有害事实的措施而言,似乎不需要这些事实是由于某人的过错。然而,我认为,这些措施应当在有限类型的基础上,通过典型情形进行规定,而非建立在像第2条那样笼统概述的前提基础之上;另外,排除对物权或对人的侵犯可能并不在民事责任的领域中进行论述。我认为,第2条具有一个有意义且重要的目标,即确定了整个法律的共同前提,以统一的方式描述客体,并指向该法的其他规定。但条文的现在的这种写法可能会引发解释上的不确定性的严重后果。如果它本来只是被赋予了一个体系化建构的简单功能,而解释者却把它当作是一个可适用的规定,因为它提出的前提,也就是“损害”,它本身并不足够,而应当由过错或者一个法律规定的特殊类型的损害进行补充,就像第8条规定的那样。
(62)D.9,2,21pr.-1; D.9,2,29,8;D.9,2,33pr.
(63)D.9,2,23 pr.;D.9,2,51,2;D.9,2,37,1;D.9,2,22:探讨所有与物相关的用途。
(64)D.9,2,21,2;D.9,2,55.也参照上述。
(65)D.47,10.
(66)D.47,10,15,46:“如果某人因为奴隶被鞭打提起不法侵辱之诉,然后又提起不法损害之诉,拉贝奥写道: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一者涉及因过错造成的损害;另一者涉及侵辱。”
(67)D.44,7,34pr.:“某人侵犯性地打击他人的奴隶,根据这个事实既可被提起阿奎利亚法之诉,也可提起侵辱之诉。侵辱取决于意图,损害取决于过错,因此两个诉讼可以同时存在。但有人认为,如果选择了一个,另一个就丧失了。……因此,赞成这样的想法更加合理:他可以提起第一个他想要提出的诉讼,如果在另一个诉讼的基础上可以获得另外的东西,则可以提起另外一个。”
(68)《学说汇纂》第47、48卷发展了“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私犯”这个范畴的断裂,但这个范畴在《法学阶梯》中仍然是统一的(J.4,1-5)。在《学说汇纂》中,第九卷围绕着一个不同于刑事法的中心问题展开,从中发展出合同外民事责任的基础。这个对材料的重新组织整理将对人的保护分成两部分:对人的侵辱这种私犯被放到刑事法之中(D.47,10)。
(69)D.9,2,7pr.
(70)D.9,1,3.
(71)D.9,3,1,5;D.9,3,7(以“公正”为基础的评价并不等同于对人的侵辱的损害赔偿的评价,可能是因为主体要素的不同;类似的制度我们可以在积极的可转让性中看到:D.9,3,5,5)。
(72)D.9,3,1pr.;D.9,3,5,5.
(73)一些民法典在债的部分,规定了产生于“非法行为”的债(如《普鲁士法典》(1794),第一编,第六节;有类似表达的,比如《德国民法典》(1900),第823-853条;《阿根廷民法典》(1871),第1066-1136条),或者产生于“非法行为”的债(比如《意大利民法典》(1942),第2043-2059条),或者产生于“私犯和准私犯”的债(比如《法国民法典》(1804年),第1382-1386条;《智利民法典》(1857),第2314-2334条),在一定的情况中明确专门列出“补偿和赔偿”的内容(《奥地利民法典》(1811),第1293-1341条)。最后,开始使用民事/合同外“责任”的表达(《秘鲁民法典》(1984),第1969-1988条;《巴拉圭民法典》(1987),第1833-1871条;《古巴民法典》(1988),第88-99条;《巴西民法典》(2002),第927-954条)。
(74)我看到几个法律草案专门规定了“对人的尊严的侵辱”。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继续发展的选择,同时技术上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抛弃“精神损害”这个概念,在“损害赔偿”之外完善“救济性罚金”(概念术语上的问题是很细微的,我不懂中文,因此无法给出具体的建议)。我认为,首先,确立这个“救济性罚金”的标准并不应当是“财产性质的”,而应当根据“善良与公正”,或者根据固定的数额。
(75)D.43,23,2.
(76)D.43,23,1,2-14.
(77)D.43,13.
(78)请允许我推荐罗智敏关于这个主题的博士论文。
(79)我想指出,《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由《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7条所重复的有关救济措施的一系列广泛的方法,促使我们重新阅读《学说汇纂》,关注对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的多种应对措施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对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的可能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除了公共行政部门,还包括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由公民提起民众诉讼。
此译文得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薛军副教授的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