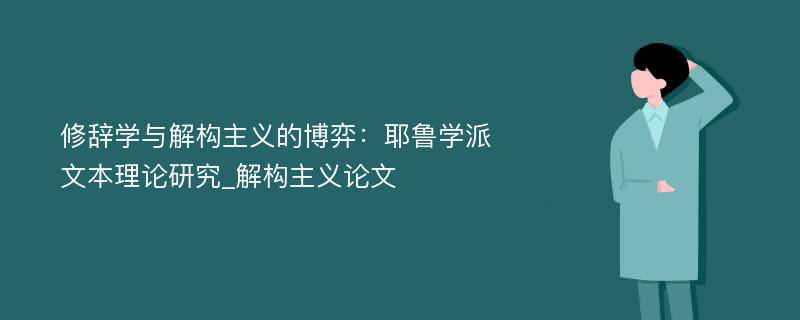
修辞与解构的游戏——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鲁论文,修辞论文,学派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4)-022-05
耶鲁学派对修辞情有独钟,他们的文本理论是建立在修辞学基础上的,所有的文本都被看成是隐喻、换喻、提喻或寓言等转义的汇集地,这就导致了文本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多元性,文本在生成的洪流中不断地凝聚又逸散、稳固又破碎、建构又解构。修辞性最终导致了文本的自我解构,他们由此从内部找到了文学之树常青的秘密,进而将“文学性”定位于“修辞性”。
一、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
在形而上学体系中,修辞一直是一种装饰、附加、补充,作为外来者服务于理性的中心。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批判和规约是建立在一系列区分之上的:语言技巧与道德内容、修辞与辩证、意见与真理。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演说家如果一味地以优美的言辞来迷惑观众,而不进行事实判断,不以真理为指引,便是可笑的,而这种修辞学也根本不是技艺,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欺骗为要务。[1](P400)如此一来,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便设定下来,修辞学在语言形式层面所制造的偏离始终威胁着对本质和真理的认识。修辞学渐渐被赋予了道德败坏者或女性化的形象,它花枝招展,涂脂抹粉,以诱惑和欺骗为业——从西塞罗、昆提利安一直到洛克和康德,修辞的魅力与美女的诱惑力被视为等同的。甚至在尼采那里,女人还被视为权力意志的障碍:“女人需要弱者的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女人会使强者弱化。”[2](P272)女性对权力意志的干扰,正如修辞对真理的偏离一样,成为了一个外在的他者。
耶鲁学派强调文本的修辞性,并不是将修辞作为文本得以增色添彩的工具,而是要确立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从形而上学的历史上说,为修辞正名,就是要为女性正名,为所有那些曾是形而上学体系中边缘化之物正名。卡勒在《论解构》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女性看成是补充和寄生之物,但最终却走向了自我解构,卡勒的论述是极具启发性的。首先,人们很容易在精神分析中看到一种“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男性的器官是参照点,它的存在就是规范,女性是依附在这个正面规范之上的一种离格,一种意外,或一种反面的繁复化。”[3](P148)于是,女性被认为是阉割的,是一个不完全的男人,其性别界定是建立在对她最初之男性压抑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对男女二元对立的解释与其说是对人类无意识的揭示,不如说是为男权社会做辩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和女性的他者地位,正如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恰恰是强制性地将父亲作为性的对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性是被阉割的就是意味着曾经具有男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女性是“原生的”双性人,卡勒指出:“也只有通过设立这类双性,弗洛伊德才能视女性为衍生的,寄生的:先是种低级的男性,后来通过对阴核(男性)的性的抑制,呈现出女性。”[3](P152)所以,女性以其男女两种模式的综合,成了性的总体模式。这同德里达的解构思路是一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原型女人的变体。
肯定被压抑项的原生性,以此消解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是耶鲁学派的基本策略。如同女性的原生性一样,修辞也应当如此。就文学文本而言,既被视为美化又被看成偏离的比喻性语言是其基本构成,追求中心的企图一直存在,同时修辞对抵达中心的阻碍也从未消失,这就表明修辞作为补充之物乃是中心所必需的,中心从来都是以被补充的状态出现的,所以补充即是本质,修辞之替补正是一种原始性替补,即修辞是原生性的。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这种替补的逻辑有清晰的表述:“外在即内在,他者和欠缺作为代替亏损的增益而自我补充,补充某物的东西取代了事物中的欠缺;这种欠缺作为内在的外在,应该早已处于内在之中,等等。”[4](P314)解构主义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固有秩序,使得内在/外在、本质/补充、内容/形式这样的二元对立归于消解,于是,文字不再是声音的附加而具有了原生性,女性也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也具有了原生性,修辞同样不应当是话语中心的补充,也是原生性的。耶鲁学派最为关注的是文本的修辞问题,其原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本语言的修辞原生性。尼采在修辞学课程讲稿中就明确指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转义(tropes),语言就是修辞,它只能传达意见,而不是什么关于事物本身的真理认识。[5](P20)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语言中修辞的原生性,从这个角度讲,真理反倒成了修辞的派生物,是修辞失去了审美色泽之后的“死的”话语形象。德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语言的修辞性:“转义不应当从审美角度理解为一种装饰,也不应当从语义学角度理解为一个从本义命名衍生出来的比喻义。”[6](P105)非修辞的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转义是语言真实的本质。在文本中出现的词语更是如此,语词既然在产生之初即是偏离,文本作为语词的编织物,更是缺乏本源、目标或基础,“每个词本质上都属于一个纵横交错的词词间关系的迷宫,这些关系追溯的并非一个指涉本源,而是某个一开始就已经是比喻转换的东西(根据卢梭或康迪拉克法则,所有词语本源上都是隐喻)。”[7](P144)因而,所有的词源学都是错误的词源学,所有想摆脱修辞去追求文本中心或本义的企图都是虚妄。
第二,文学性即修辞性。毋庸置疑,文学文本是由修辞性的语言编织而成的,尼采曾在早期的文字中充分揭示了文学中修辞的非神秘化,以及更重要的,这种原生性修辞使文学成为“最高的真理”。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在修辞性语言中进行着虚构,但同时又宣布自己是在欺骗,它把表象当做表象,把谎言看成谎言,这与真理对修辞本性的遗忘形成鲜明对照。德曼对文学修辞本性的认识来自于尼采的修辞观,他也是强调文学在欺骗中追求快乐:“当文学用形象组合的自由来诱惑我们的时候,尽管这些组合比费尽苦心的概念建构更加虚无缥缈,但这并没有减少文学的欺骗性,因为文学断言了自己的欺骗性质。”[6](P115)文学的这种断言成了对自身毁灭的“无休无止的反思”,文学也因此无法摆脱修辞的桎梏,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性就是修辞性:“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8](P106)德曼的这一表述正是对上述观点的全面总结:“决定性的”是指文学的修辞本性,而“动摇不定的”则意味着文本在自认为是在欺骗的修辞性语言中成为碎片,丧失了稳定的指涉性意义。
第三,哲学文本的修辞性。在《白色的神话》一文中,德里达已经对哲学/文学的二元对立进行了解构。修辞一直被看成是文学的特征,哲学以求真为目的,被认为是超越了文本的修辞结构,但德里达指出哲学本身也是一门深深根植于修辞的科学,如果将修辞清除出去,哲学文本将空无一物。哲学话语对自己的修辞本性有意地进行掩盖和遗忘,从而使自己与真理相接近,这与文学透明的欺骗性相比,是真正的欺骗,形而上学的网络正是以此方式秘密建构起来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曼指出,“文学结果成了哲学以及它所向往的真理模式的主题”,[6](P115)如此一来,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都成了修辞经营的园地,修辞性也就成了一切文本的真正的“本质”。将修辞性引入哲学,并不是想让文学凌驾于哲学之上,它们都是修辞多元化、生成性的产物,二者相互交织,哲学有着文学性,而文学也有着哲学性,德曼指出:“一切的哲学,就其依赖于比喻的程度而言,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一切的文学,就其内含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哲学的。”[9](P50)哲学一直在对修辞进行驱逐,试图使自己成为“净化了的”语言,但它总是失败,原因就在于修辞本就是哲学的中心,这种驱逐在实施之前就成为不可能的,柏拉图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类似原型的女人,耶鲁学派也找到了原型的文学。强调哲学文本中修辞的原生性,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这门学科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优越性,它与其它文本一样,都是修辞的产物,因而只是话语或符号。
从语言中的修辞原生性到文学中的修辞原生性,再到哲学中的修辞原生性,解构主义将修辞认识论贯穿始终,所有的文本都被看成是隐喻、换喻、提喻或寓言等转义的汇集地,这就导致了文本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多元性,文本在生成的洪流中不断地凝聚又逸散、稳固又破碎、建构又解构,这种虚无主义的文本观正是人们对解构理论所诟病之处,然而肯定这一虚无却又是生命权力意志的体现,直面生成,期待文本中的每一次转义,也就是珍视生命中每一个精彩的瞬间,这是耶鲁学派文本观的重要启示。
二、文本解构的游戏
解构一词的英文是“deconstruction”,其中的“de”表示否定,而“con”又是肯定,二者的并置很好地命名了解构修辞寻求差异的运动。如果从统一性的角度,也就是从deconstruction一词整体含义来看,解构无非就是指要把完好的文本弄成支离破碎的片断或部件,但是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一词语,或者说进入解构修辞内部就会发现,解构与建构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鉴于‘解构批评’是运用修辞的、词源的或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这种批评就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它与它的分析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它非但不把文本再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7](P131)所以任何一种对文本的阐释,都是一次游戏过程,包括解构批评自身,都是在解构-建构的悖论中完成这一游戏。
将解构的过程看成是读者对文本随心所欲的阐释,是对耶鲁学派文本理论严重的误解。对此,德曼、米勒等人经常提醒人们,解构首先是文本自身差异的运动,如米勒所言:“各种各样的意义并不是读者将自己的主观解释任意强加给作品的结果,相反它们受作品文本的制约,在那个意义上它们有确定的范围。”[10](P45)文本自身的意义由于修辞的原生性而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读者在与文本接触的瞬间是有确定性的,这是由读者自身的特点造成的,也正是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遭遇导致了德曼所说的“盲识与洞见”,读者从文本中得到的解释只能是从某个角度的透视,因而是片面的,文本在向读者敞开的同时也必然掩盖了一些东西。文本自身是混杂而多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包含着大量自我解构的因素,所以,德曼指出:“解构不是我们添加到文本中的某种东西,而首先是构成文本的某种东西。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又否定它自身修辞模式的权威性……”[6](P17)将文本视为修辞的产物,那就意味着文本同时具有建构和解构的成分,在日神式的冲动中,修辞为文本赋形,拟构一种秩序;但是在酒神精神的推动下,修辞又同时展示了另一种或多种可能性,使这种秩序瓦解;然后,在语言的废墟上,重建又开始了……这正是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也是尼采“生成的游戏”,以及德里达“意义的自由游戏”,而强调文本的修辞原生性和自我拆解性,正是德曼等人所重视的“解构的游戏”。
首先要强调的是,文本中的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对抗,导致文本的自我解构。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米勒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位批评家的语言中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任何一篇文学文本内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批评文本同诗歌作品并不是对称的关系,以及一首诗同其先前的作品都有歪曲偏离的关系,解构主义解读是一种“寄生性”解读,它与单义性解读一同坐在文本这一食物旁分而食之。单义性解读与解构主义的解读之间是寄主和寄生物的关系,但这并意味着主人与客人的二元对立,它们与文本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二者之间“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单义性解读总是包含着解构主义的解读,而解构主义解读也绝不可能摆脱它试图对抗的形而上学解读。[7](P103)单义性解读是和形而上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相联系的,这种解读将文本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试图接近文本中永恒的真理;而虚无主义则作为解构主义的标签而出现,它是隐居在形而上学内部的一个幽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在自身内部始终包含着自己的寄生物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总是要摆脱虚无主义的纠缠,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没有寄生物,寄主也就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成立恰恰是在妄想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形象建立起来的。所以任何文本中必然都存在着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正如尼采所言,最高价值观念总是在贬低着自身,形而上学在建立理性大厦的时候,总是以厌恶和恐惧的心理同虚无主义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就像磁铁的引力一样在大厦不断加高的同时将虚无主义带在身旁。
不过,米勒指出解构主义并不等于虚无主义,他说:“‘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清理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解构主义’程序,把幽灵和寄主的关系颠倒,玩弄语言游戏的游戏,这样就可能超越虚无主义通过形而上学以及形而上学通过虚无主义而产生的反复增殖。”[7](P109)解构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文本中的寄生性关系揭示出来,即文本中的形而上学及其颠覆性对应物的盘根错节,纠缠不清,这就是认定文本是异质共生的并且是自我拆解性的:任何解读包括解构主义的解读都有可能划定文本的形而上学领域,虚无主义则从旁嘲弄任何固定下来的价值,这正是文本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所致,每一种意义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于是每一个中心都会被其它中心所取代,确定性与虚无性总是相生相伴的。这也表明解构主义并不只是意指单纯的“解构”,而是包括“解构-建构”的双向修辞过程,解构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文本自身的修辞性所致,然后在修辞性的阅读活动中得以彰显。
抛开形而上学问题,文本自我解构的游戏乃是修辞的游戏,米勒形象地称为文本的“迷宫”和“阿里阿德涅的线”。正是由于文本具有自我拆解性的修辞特点,异质性和矛盾性使得文本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任何批评家或读者试图理出一条线索,都是在验证迷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在解开迷局的同时又设下一个迷局。理解文本的传统态度是:想方设法找出通达意义的清晰线索,这种线索可能是作者的意图,也可能是文本(作品)的主题、意象,乃至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利用确定下来的线索将文本(作品)串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且不说文本的修辞状况是如何复杂,以至于经常是斩断纠结的线团而非理出头绪,就说用以解释的语言其准确性难道就勿需置疑吗,不也是具有异质性和矛盾性特点的修辞吗!这样,线索缠绕着线索,修辞覆盖在修辞之上,文本的迷宫非但没有被破解,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米勒在《阿里阿德涅的线:重复与叙述线索》一文中是如此描述线和迷宫的关系的:“在探查迷宫的过程中,线被极其复杂地绕来绕去,最终战胜了迷宫,但同时也造就了另一张复杂的网——这里图案迭置于图案之上,如同那两个类似的故事本身一样。”[7](P138-139)当然,耶鲁学派关心的不是解释学的问题,而是文本自身的修辞问题,米勒在此所探讨的“线与迷宫”,首先强调的是文本中不断重复的叙事线索,每一次都试图寻找起源、发掘意义的真相,即用线去探索迷宫,但每一次都是在制造起源、生成意义。这正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狄俄尼索斯对阿里阿德涅的诉说:我是你的迷宫,这是一种永恒轮回,线性序列不断地深入文本的迷宫,每一次都成为一个循环,一个可以永远返回的圆圈。于是,线不可能是外在于迷宫的,就像线性术语构成了文本自身而非可有可无的寄生物,因此米勒指出:“线和迷宫各自居为对方的本源又成为对方的摹本,或者说是产生对方的摹本,原本就在那儿的一个本源:我是你的迷宫……”[7](P142)线非但不能整理出文本的单一结构,即使它最终穿过了迷宫,但在其起点与终点之间形成了另一个迷宫,要想获知这一线索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这样的过程无异于新的轮回,线索指出线索,迷宫指向迷宫,如此循环不已。文本何以如此?前述“语言的修辞原生性”已经指出,任何词语本质上都是一个纵综复杂的迷宫,它的产生是修辞转义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指涉本源,任何命名和描述都是以隐喻的方式“重新开始”,自身就是本源。
如此,解构的游戏总是在生成中得以完成的,以修辞冲破形而上学的困扰,以修辞破解修辞,成就了文本的短暂性和永恒性——文本无数短暂的修辞形象加入到解构-建构游戏的永恒轮回中,这既是文本之“生成”,也是其“生成之在”。
三、文本中差异的运动:重复与误读
对差异性的重视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大特点,在尼采、巴特、福柯、德鲁兹等人的文章中多有论述,他们对解构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从语言和修辞的角度强调差异问题,还是主要得益于索绪尔的差异理论。耶鲁学派从中领悟到的是文本中能指的漂移和差异的永恒运动,在德里达那里是一种哲学性的表述即延异,而耶鲁学派则致力于探讨文学中差异的运动,下面就以重复与误读为例。
重复是文学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很少被人们重视。米勒认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重复形式:首先是言语成分的重复,包括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及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第二种是文本中事件或场景的重复,最后是一部小说对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10](P2)重复既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即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的各种社会、心理或历史事实以及与作者的精神和生活相关的现实情形,米勒所关注的重复主要指的是文本内部的一种修辞状况,他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所做的分析都是集中于语言细节上,这也是耶鲁学派的一贯立场:重视文本自身,即使社会历史因素必然只有通过文本得以体现。人们往往会把重复与相似性或同一性联系起来,这是受形而上学影响的传统理解,也是米勒所谓的“柏拉图式的重复”,他引用德鲁兹《感觉的逻辑》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重复模式是在预先设定相似或同一的基础上思考差异,而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它将相似、同一看成是本质差异的产物,这就是“尼采式的重复”。柏拉图将现实和艺术看成是理式的摹本,这种重复是对理性的遵从,同时也是偏离和差异,这样差异就成为内在于相似或同一之中的差异。而尼采的重复模式则认定世界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只有存在差异事物才能彼此相像,相似乃是差异之中的幻象。
比如,米勒在《小说与重复》第五章分析的《苔丝》便是一个关于重复的故事。米勒引用了《苔丝》中描写苔丝遭亚雷凌辱的片段来讨论,他认为这个片段描写的事件是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演,它指向历史中一长串类似的事件。苔丝被迫重复她自己和别人的经历,并在那些重复的过程中遭受苦难,“这部小说的正文为它的标题、副标题、卷首引语以及前后相关的四篇序(或注释)重复着”。[10](P2)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重复意指着同一事物或某个意义中心,“柏拉图式的重复”使人们从相似或同一的角度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米勒认为,这是一种假象,每一次新的展示,新的叙述,都是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经过仔细分析以后就会发现相互之间是充满矛盾、不可调和的,因而最根本的问题只能是一再被重复、一再被重新解释,却是无法解决的:“使苔丝的生活陷入那对称的图案而不可自拔、并引导她一步步走向断头台的富于创造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10](P146)这样一种“尼采式的重复”使我们认定每一个事件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中心的根本缺失,这样重复就成为差异的生成运动,因而米勒指出:“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我认为体现了文学特征的那种异质多样性的最明显的形式在于对苔丝遭遇多种多样互不相容的解释的同时并存。”[10](P146)
也许有人要质疑,既然强调差异为何要提重复,只谈独特性不就足矣?其实差异和同一都是相对而言的,耶鲁学派的确是强调生成和差异,但这离不开其寄生物“同一”,就像形而上学也离不开其寄生物虚无主义一样。从另一方面而言,重复的强调也是对本源、目的等形而上学观念的解构,柏拉图式的重复让人们不断回返中心,尼采式的重复强调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不仅意味着中心的缺失,也表明我们只是在进行重新解释的修辞游戏,并没有创造新“事物”。在《权力意志》的第1062条中,尼采在批判了柏拉图式的重复后指出,我们会不断地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2](P38)而在文本之中更是如此,每一次新的描绘或叙述并没有使问题更深入,只会让情形变得更复杂,而非更加接近中心。正如《吉姆爷》中的多重叙述只是在文本的织物中不断添加修辞阐释的丝线,始终围绕着事物,表面上是要接近其实是游离于某个虚拟的中心或起源之外的。这样一种观念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进步”历史观形成鲜明对照,文本中的重复就像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圆环,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也只是在增添这样的圆环,不可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文本。这样,差异才成为真正的差异,而不是从相似或同一中解析出来的差异,差异的运动也不会走向辩证的统一。
修辞性阅读是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的一大特色,这种阅读同样是强调差异的运动。按照德曼、布鲁姆等人的观点,文本根本上是不可读的,每一次阅读因而都是制造“谬误”,也就是在制造差异,任何“正读”都是“误读”,正如德曼所说:“解读就是理解、诘问、熟悉、忘却、抹去,是使其面目全非和重复——也就是说,无休无止的拟人化。”[8](P241)阅读活动和所有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致的,即尼采所说的“移情”和“拟人化”,是“主体”的一种移置,也是“主体”幻象生成的修辞过程,在《阅读的寓言》的一段文字中,德曼再次表述了这一观点:差异的残余构成了一种经验主义意识,其中似乎正在产生“精神、意识、自我。”[6](P242)但在形而上学的桎梏被打碎以后,这种阅读不是走向意义的统一,而是揭示了文本和阅读者的偶然性和有限性,所以这种“拟人化”不是趋同,而是充分显示了差异性的存在,阅读活动正是因差异而成为“二度”或“三度”寓言,也就是阅读的不可能性的寓言。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经典文本的历时性差异运动。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把当代诗人看成是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面对着“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两者处于对立之中:父亲企图压抑和毁灭儿子,儿子则试图用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来贬低父亲,从而开拓自己生存的空间。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1](P6)经典文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那些想出人头地的作家们去继承,而是要同他们相竞争,以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因此学会去超越前人,制造差异或陌生化是优秀作家走向成功的首要条件,布鲁姆写道:“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12](P21)另一处:“对前辈诗歌最初的爱,迅速地被改造为修正的冲突,若无这种修正的冲突,个性化就没有可能。恩培多克勒坚持认为冲突引起了最初的大灾变,分解了各种元素,点燃了意识的普罗米修斯圣火。”[13](P8)那些最伟大的作家总是颠覆一切价值观,标新立异。布鲁姆所强调的文本的陌生化或原创性来自于“影响的焦虑”,文本审美价值的产生在于艺术家之间影响和竞争,他者以权威的形象策动作家呕心沥血、推陈出新,也就是说,陌生化或原创性首先是和他者影响的焦虑和自我内在性的追求紧密相连的,有了这样的竞争意识,艺术上的偏离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没有竞争和差异的制造就没有超越和创新,经典生成之路也就被阻塞了。
正是由于差异的运动,文本的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解构的修辞游戏通过对中心性和统一性的颠覆,使文本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而赋予了文本“存在之真”。
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反复修辞论文; 文化论文; 迷宫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