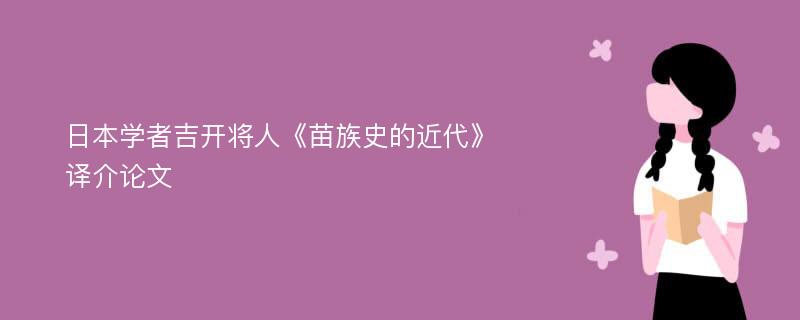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 《苗族史的近代 》译介 *
陈 芳1 ,李炯里2
(1.2.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基于中国、日本、欧美、泰国等多方面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文献,以“苗族先住说”为中心,考察了该学说在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受容、发展、变化的过程,对该过程进行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并就其中的部分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值得参考。
关键词 :苗族;吉开将人;苗族史
日本学者关于苗族的研究开展时间较早而且研究领域广泛,其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大体分为第一阶段1900—1945年,第二阶段1945—1992年,第三阶段1993年至现在。第一时期的研究以鸟居龙藏为首,他从1901年至1926年陆续发表的学术成果中有不少关于苗族的研究,尤其是1907年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堪称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时局和关系,苗族研究大多是放在东亚史学、中国近代史或对中国整体的地理研究中开展的子项目,缺乏田野调查,不能够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当时苗族的各方面状况。第二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将苗族作为唯一研究对象,开展全方位、大范围、长期的调查分析。第三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部分学者通过深入苗族居住地进行长期调查研究取得了更为直观和详实的研究成果[1]。在这些不同时期的研究中,鸟居龙藏、铃木正崇、金丸良子等人作为较早从事苗族研究的学者备受关注,部分研究成果已经被译介,为我国学者的苗族研究提供了参考。近年来,日本青年学者的苗族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吉开将人的研究较为体系化而且具有代表性,虽然目前国内关于其研究成果的介绍仅限于1篇简短的评论,但是评价极高,指出该研究是“现代中国苗族史研究的学术史”[2],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和介绍。
一、吉开将人及其研究
吉开将人出生于日本爱知县,199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93年修完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生课程并于同年到北京大学留学,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中国的留学经历使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2000年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和越南关系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民族问题等。2006年起吉开将人将研究重心放在苗族结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从2008年开始至2011年分为7期陆续在《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上发表了「苗族史的近代」等相关论文。该论文长达25万字,查阅了中日、欧美、泰国等地的珍贵史料,包含书籍、报纸、杂志、书信、手札、记录、档案等,数量达到1000多份,体系完整。从该论文的构成和内容来看,称之为学术专著也未尝不可。由于「苗族史的近代—汉族西来说和多民族史观」和「苗族史的近代(续篇)」联系较为紧密,而「苗族史的近代—(三)——(七)」的关联较强,所以,以下将分为这两大板块进行介绍。
二、「苗族史的近代—汉族西来说和多民族史观」及「苗族史的近代(续篇)」
在开篇「苗族史的近代—汉族西来说和多民族史观」[3]中,吉开先整理了传统汉学在清末以前的观点,即上古“三苗”故地被视为长江流域,而居住在中国西南被称之为“苗”的人群与上古“三苗”有着紧密联系。进而指出这种传统观点在清末受到来自于欧洲的东方学说的影响之后,逐渐发生改变。因为欧洲的东方学者19世纪于西亚和中亚地区陆续发现了与天主教、基督教宣扬的“普遍史”观(认为人类是亚当和诺亚的子孙,或是各地文明的因素并非在本地发明而由西方传播等说法)相关的学术材料(语言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资料),于是欧洲东方学界掀起结合基督教传统“普遍史”诠释中国上古史上一些问题的热潮。在此背景之下,“汉族是外来民族而非中国土著”的“汉族西来说”假设性构想逐渐形成。随后,围绕中国土著民族的问题,欧洲的东方学者将蚩尤或“三苗”的传统历史认知作为关键点进行探讨,于是“汉族由西方迁徙而来之前占据中国内地的先住民族可能是苗族”的“苗族先住说”应运而生。吉开强调来自于欧洲的“汉族西来说”和“苗族先住说”被法国学者拉克伯里将发展成为一组对应的学说,其后给全世界带来深远影响。接下来考察了这两个学说在中国和日本各自吸收、发展、衰落等过程。吉开指出虽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接触到这两个学说,但是没有传播开来。与此相反这两个学说首先于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日本历史学家久米邦武、法学家户水宽人通过拉克伯里的论著接受了这两个学说。东洋史学家白河次郎(1900年)将它们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最后作者重点论述了几位著名日本学者即田能村(1904年)、高楠顺次郎(1898年)、鸟居龙藏(1902年—1903年)对苗族先住说的接受和发展。
在其后的「苗族史的近代(续篇)」[4]中,吉开探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梁启超、陈天华等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白河次郎的中国史论(1901年)的情况,指出梁、陈等人在其后的言论(1902年,1903年)中体现出受到苗族先住说的影响,而在此之前的苗族观根基是传统华夷的思想。不久后创办《新民丛报》(1902年)产生了新的苗族史论,它将旧有的苗族“劣势”观与近代东洋学的苗族先住说合二为一,在社会进化论“优胜劣汰”的论理框架内,对苗族进行了重新定位。其后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实施以清朝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和以章炳麟为代表的排满派围绕是否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构想,出现了对立和共鸣,“苗族先住说”成为党派论争的新焦点。后来随着章炳麟离开《民报》和论争的结束,各个党派对“苗族先住说”的关心急速冷却。此后“苗族先住说”随着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之“五族共和”政治口号的提出,逐渐被淡忘。吉开指出,对于“苗族先住说”的受容,中日之间存在本质不同,对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苗族先住说仅为东洋学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用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作理论根据。
三、「苗族史的近代(三)—(七)」
在「苗族史的近代(三)」[5]中,吉开指出尽管苗族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中的存在感逐渐消退,但“苗族先住说”并没有完全消失。民国初年,“苗族先住说”和“汉族西来说”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对此产生危机感的章炳麟继续批判这两个学说,此时,梁启超的民族史论也发生了变化,他虽然坚持“苗族先住说”说,但对“汉族西来说”的态度变得谨慎。顾颉刚对“汉族西来说”表示怀疑,但仍然保留着“苗族先住说”(1923年)。随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通史类图书的刊行,部分学者开始摒弃“汉族西来说”(吕思勉,1923年;常乃悳,1928年)。吉开认为这一时期汉族史的学说从“西来说”变化到“土著说”是由于当时发展壮大的考古学成果为学者提供了考察民族史的另一种资料。傅斯年(1933年)通过考古指出“汉族是黄河中下游的土著居民,中国文明起源于东方”,他与王国维、徐中舒等人构成了同一系谱的一系列上古史论,并完全否定了“汉族西来说”,构筑了一个多民族史像,但“苗族先住说”的影响依然存在。吉开总结指出苗族史论在民国后失去政治色彩,再受到批判,其后“苗族先住说”在学术界逐渐成为纯粹的历史学说讨论的对象。民国初年,出现了强调苗族存在的“六族”说,从此以向汉族不断“同化”为基调的民族史论遂成主流。
他们好像不是在分手,为什么这么风轻云淡,没有大吵大闹,没有歇斯底里,没有争吵推诿,或者他们都在等对方先说出来,其实心里早已经对这段感情没有了信心。
在「苗族史的近代(六)」[8]中,吉开考察了“苗族先住说”在西南民族中间的流行及受到西南地区知识分子关注的始末以及在此掀起的一场为后来的中国民族论发展确立方向的大讨论。吉开首先关注到,高玉柱(1938年)、喻杰才(1939年)等人组建的多个组织,它们在成立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在当地举行的各种宣传活动,极大刺激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意识。在“抗日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各个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抗战的同时,也积极谋求本民族权益的扩大化,体现出边疆“抗日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在云南和贵州的民族合作引起了当局的警惕。1935年,马毅提醒当局在贵州某地在苗族出身学生的主导下,开展了拒绝汉化,树立苗族意识的“苗族复兴运动”,还积极宣传了“苗族中原先住说”。作者根据排除法,认为马毅提到的贵州某地就是贵州西北部威宁县石门坎地区,而苗族学生是杨汉先等人。然后作者从地理和历史分析了马毅注意到贵州石门坎地区杨汉先等人活动的原因,并从杨汉先(1940,1942年)等人的回忆文字和众多史料中考证到晚清民初在石门坎的传教士们开展近代教育的过程中,苗族接受了“苗族先住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苗族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苗族人以“苗族先住说”为基础,积极致力于将民族文字及民族传统土著化。而在苗族人重新发现本民族传统的过程中,以蚩尤为始祖的苗族中原先住说,被吸收进阐释苗族文字起源的介绍中,作为苗族拥有古老文明的重要证据,与苗文一起,在中国西南广泛传播。由此,石门坎苗族的民族意识随着布道传教的苗文广为传播并造成了较大影响。最后,就马毅(1939年)呼吁警惕“苗族复兴运动”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社会造成的反响,作者从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和学界动向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苗族史的近代(五)」[7]中,吉开主要结合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的时局介绍当时边疆民族知识分子选择“苗族先住说”的背景和其影响。首先,考察了今天湘西地区的苗族在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和“屯田”政策的推行后,随着抗租运动的蜂起,一批受过教育的苗族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改革并走入政界的情况。从湖南的石板塘创作的苗歌中可以看出苗族知识分子们对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故事进行了大胆的重新解读,把与汉族(黄帝)对抗的伟大英雄(蚩尤)视作始祖,并以此作为本民族是中华古老民族之一的重要证据。其后其同乡石宏规在陪同凌、芮考察湘西后,基于“苗族先住说”和“蚩尤先祖说”,回顾了苗族的历史并提出汉苗通婚以消除民族歧视的观点。1936年,以石宏规、石启贵为首的三名“苗族代表”,联名向湖南省政府提出主张积极推进苗族传统的“改良”,对苗族实施优待政策的方案。吉开认为虽然是同一个调查,但是凌纯声等人描绘的完全否定“苗族先住说”的苗族历史像与石宏规等苗族知识分子描绘的苗族历史像截然不同。1934年,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一系列苗族政策。同时国民党也意识到西南苗族的重要性,1935年蒋介石考察了贵阳和昆明,其后,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贵州和云南两省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1937年起,苗族社会中希望参与中央政治的期待和要求显著提高。其后作者分析石启贵等人积极的政治态度的内外两个因素,并注意到石启贵没有采用他者称呼和“苗”,而是提出以“土著民族”的身份获得与蒙、藏同样的国民大会特别代表名额的要求。吉开认为石等人选择“土著民族”作为本民族的自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得苗族不同于以往总是被汉族叙述的对象,而是转向自己娓娓道来。1926年以后,从湖南到云南一带,“土著民族”从一个泛指西南民族的他者称呼变为民族自称。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在川滇的西南民族中间,“西南夷族”(“苗夷”“夷苗”)等称呼取而代之开始流行。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件时期,伴随着边疆民族的自立和抗日浪潮的急剧高涨,“中华民族”一体性言论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民族”和“种族”被区别开来,并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定义。齐思和(1937年)、顾颉刚(1937年)、谭其骧(1938年)以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种双向的“融血”论为基调展开中国民族史论,这有别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非汉族单方面向汉族靠拢的“同化”论。这些议论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末“中华民族”论的盛行和“民族”概念的重新定义。
在「苗族史的近代(四)」[6]中,吉开重点梳理了民族学扎根于中国之后的发展状况,并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边疆及其民族历史像的认识。关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者梳理其过程为:20年代中后期为躲避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先后到达广州,在南方形成新的政治、学术中心。1928年傅和顾在蔡元培的指导下筹建中国第一个国立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确立包括西南边疆民族在内的历史和语言学术研究体制。傅、顾(1928年)筹建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人类学作为研究领域之一,以自广西到云南这一广大区域的“西南民族”为其研究对象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一时期在广州出现的这种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学术热情,其学术史沿着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这一线索展开。随着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傅和顾重拾上古史研究,广州的关于西南边疆民族的学术实践被史禄国和杨成志继承下来并各自发展开来。这一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田野范围,从广东、广西拓展到东北和更加广阔的内陆地区。1930年后对四川、贵州也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活动。1932年邹鲁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西南研究会”。这一时期,中国西北、东北、西南备受关注。关于西南苗族,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历史学领域已经转向土著史观,但在民族学领域,旧式的先住民史观依然影响甚大直至1932年。1935年国立编译馆将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译成汉语,江应樑(1937年)批判鸟居在书中表现出的以汉苗对立为基轴的民族观毫无科学根据。凌纯声和芮逸夫(1940年)彻底否定了“苗族先住说”,认为历史上的“髦”或“髳”,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渐次南下,后来进入贵州,“苗”之称呼由误解产生,一直沿用到今天。凌纯声(1940年)指出黎族是长江流域最古民族集团的后裔,在黎族与此后进入现居地的后发集团——今天的苗族之间,又加入了瑶系诸族、傣系诸族,瑶系诸族和苗族在年代顺序上相互重叠、交错。他否定了过去以“苗族先住说”总括起来的各种华南民族史论。
这是苏轼为“东坡饼”写的一首诗,描写了一位美人用纤纤素手搓出颜色均匀的面,放入油中慢慢煎,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此饼因陋就简的制作过程,以及出锅后金黄的色泽,玲珑剔透的皮相和香甜酥脆的口感。作者巧妙地勾勒出饼的匀称、酥脆、色美、味香的特点。最后一句运用修辞,将饼的形状比喻成美人的钗环,引人遐想,令人回味无穷。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乐趣的高尚品质。
在「苗族史的近代(七)」[9]中,吉开通过史料论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转型期内,苗族社会所处的状态、苗族人民形成的民族意识等。首先作者依据梁聚伍(1946年)的记录指出,在抗战时期虽然有政令发布,但是对西南各民族的歧视现象并未消失。这一时期内,重庆政府在中国西南各地针对非汉民族逐步实行了各种同化政策。四川军人杨森(1936年)、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7年)、贵州省政府下属的“边胞文化研究会”(1939年)对苗族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同化政策。这些同化政策使原本处于民族区域社会最底层的苗族精英们由于石门坎地区的教会教育获得许多机会。另一方面,前近代以来持续独占优势地位的彝族通过参军、留学日本、升入国内大学的手段,努力维持其在区域社会中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旧时处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彝族和苗族之间,实现了新型民族精英们的融合。其后,作者根据江应樑(1948年)的记录考察了受过高等教育的苗族朱焕章等当时在石门坎执教或求学的苗族人抱着怎样的民族意识及怎样解读其本民族历史这一问题,指出作为当事人的石门坎苗族,即使是在时代的变革中,仍一直传承着“蚩尤始祖说”和“苗族先住说”。其后考察了朱焕章、石启贵作为苗族代表、杨砥中作为彝族代表参加国民大会(1946年)的过程和大会后“土著民族”代表争取政治地位的情况,总结出1946年12月《中华民国宪法》正式通过后西南民族实现了与西藏、蒙古比肩而立的愿望。其后,作者指出西南民族参政愿望的实现和其后直接选举的实施,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非汉民族的民族团结,最终酿就了支撑西南民族团结一致的历史意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籍别作出了政治性的定义,并根据将新型人才录用为“民族干部”的原则,积极介入调整“民族”间的利害关系。其中苗族自身所描绘出的本民族历史也沿着“民族识别”的轨迹,踏上解体、重组、再解体的道路。
材料进场验收形成的资料包括:材料进场清单、材料质量文件和材料验收资料。材料到货清单需详细记录了进场材料的规格型号、数量、材质、到货日期、收发货单位、收发货人员等信息;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必须证明材料的可靠性,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包括技术证件、产品合格证和见证取样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材料验收资料包括材料自检记录表以及送检记录表等。
四、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的研究价值
吉开将人的「苗族史的近代」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重点追踪了“苗族先住说”和“汉族西来说”两个学说在近代中国社会受容和改变的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的题目是“苗族史的近代”,而不是“苗族的近代史”,所以它的重心放在了近现代中国苗族史研究的学术史上。该研究考察了两个重要学说在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受容以及发展变化,其视角在我国学术界、日本学术界都实为罕见。
在使用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时,我们对原有内容进行了筛选和整合,但这些工作并不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证部分的数据均来自该调查报告。
通过吉开将人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苗族先住说”和“汉族西来说”这两个学说产生、发展、淡化、改变的详细情况,同时通过吉开详细的文献搜集、整理和阐述能掌握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我国学术界的动向及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研究成果等,还能从中厘清我国民族学发展的清晰脉络。
吉开将人在研究中还关注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通过珍贵文献考察了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崛起、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提出鲜明政治主张、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这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尤为罕见。此外,吉开将人通过横向和纵向的主轴运用大量中、日、西方文献铺陈展开的论述方法也非常值得借鉴,同时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我们的苗族研究提供一定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陈芳.日本学者苗族研究的历史及成果评述[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241-242.
[2] 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读吉开将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N].南方周末,2012-09-06.
[3]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汉族西来说和多民族史观[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24,2008(2):25-55.
[4]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续篇)[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27,2009(2):81-121.
[5]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三)[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29,2009(11):29-84.
[6]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四)[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30,2010(2):1-61.
[7]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五)[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31,2010(7):1-51.
[8]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六)[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32,2010(11):49-138.
[9] 吉开将人.苗族史的近代(七)[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34,2011(7):1-55.
Brief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cholar YOSHIKAI Masato ′s Modern Times of Hmong History
CHEN Fang1,LI Jiong-li2
(1.2.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Guizhou ,China )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plentifu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f China,Japan,Thailand and western countries,Japanese Scholar YOSHIKAI Masato,holding the concept of “Miaozu Xianzhu Shuo (Hmong is the original occupants of ancient China)”,explored and combed the re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igentsia.He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s and research methods on some problems which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Key words : Hmong;YOSHIKAI Masato;Hmong history
*收稿日期 :2018-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陈 芳(1974- ),女,贵州麻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汉翻译,中日文化对比研究;2 .李烔里(1973- ),女,河南沁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汉翻译,日本社会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89(2019)01-0005-05
责任编辑 :陈 潘
责任校对 :陈 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