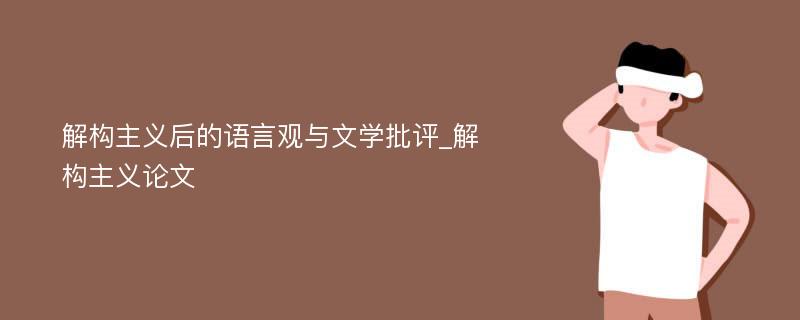
解构主义之后:语言观与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主义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3)06-0041-06
20世纪中叶至今,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哲学观念和精神价值取向发生巨变的时代。法国思想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当代命名为“后现代”,以明示这一时代所发生的“现代性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ity),意指普遍性话语——也就是“元叙述”(注:元叙述(metanarrative):依照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一书,指各种宏大的叙述和理论。宏大叙述和理论的特征是:其一,它们旨在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其二,它们为了否定另一些事实和现象,往往把某些特定的事件和现象放置在一个宏伟的构架中。在利奥塔看来,这些总括性的元叙述,不管是源自宗教、马克思主义,还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精神分析,就其目的或影响而言,均需解构,以展示其强制性和压迫性的面目。参阅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在此时面临的整体衰落和失势,表达“由进步和征服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想”(注:Tilman Kuchler,Post-Modern Gaming:Heidegger,Duchamp,Derrida (Studi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Vol.1),(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4),p.1.在区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一对范畴时,人们往往从广义的角度看待、理解现代性或现代主义。Hans Bynagle在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Philosophic Classics,Vol.V)的导言中这样描述为后现代主义所排斥、挑战并企图超越的“现代性”:“启蒙时代之后现代西方思想及文化所包含的信念、主张和志向。”它在哲学上尤指“现代人头脑中对于理性的信心,例如对客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的志在必得,例如对人类获得进步的十足信心。”)在该时期被抛弃的命运。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当代的特征描述为“人的终结”(the end of man),以概述传统思维方式的解体——在该思维模式中,形而上的主体居哲思系统的中心,占据特权地位。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干脆宣称,20世纪的哲学史是一场核心自逻辑向语言转化,最终到达嬉戏(play)的运动过程。
术语不同,他们确认的却是同样的结论:以存在(Being)为基础、以形而上的一元(the metaphysical One)为主题的时代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元(multiplicity)、差异(difference)、运动(movement)为特征,以自由(freedom)、嬉戏(play)为主题的时代。对此,流行的一句话是,西方形而上学终结了。
在向形而上学宣战的各派语言哲学中,宣告形而上学末日来临,并真正动摇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语言是解构主义者的出发点,然其直抵的终点是一种全新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形式松散,但却在一贯地维持着自身的辩证性和逻辑的严谨;它的策略和立论经精心设计,无不直指形而上学的要害又巧妙地逃开了形而上学的陷阱。这一点,从它经常对人们的认识方式发出的警告便可轻易察觉:形而上学的“终结”并非在时间意义上、在本体层面上给形而上学画上句号;“超越哲学之旅不在于将哲学一页翻过去,而在于不断以某种特定方式阅读哲学。”(注: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lan Bass(Britai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78),p.288.)
作为一种语言立场,解构主义首先是针对语言符号、词语、书写的传统价值定位进行的一场全面质疑。解构主义者将传统语言观所蕴含的“口语/书写”对立范畴端上台面,从其抑制、抵触书写的态度中发现了西方传统对书写生发出的变形问题(deformation)、差异问题(difference)以及多义问题(ambiguity)的忧惧。解构主义者以此为认识基础,开始从“广义书写”这一新的层面探讨语言的本质构成;他们将书写所暗含的意义发生延宕、差异的必然性确立为语言存在的根本基础。书写将语言的形态扩展到无声、无形的领域,其运作原理又将语言的意义引向无限,从而消解了传统的语言“符号”概念和理论,对语言的存在状态及其“本质”给予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
……书写的历史宣告了书写的绝对外在性,但它描述的却是书写原则内在于语言。外部的不健全(这种不健全既来自外部又引致外部的构成,由此同样或相反可以说家乡病,思乡病),作为有生命力的词语的消除原则以及词语与自身死亡的关系,位于该词语的核心内部。换言之,仅仅把卢梭坚信为“外在的”的事物的内在性展示出来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不是展示的问题,它更应该是一个关于构成内在性的外在性的思索:关于构成言语、所指意义、此在物的外在性的思索……(注: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313.)
这种书写,发生在言语之前、之内……(注:Ibid.,p.15.)
即便我们欣然言说着,我们的语言却已经以太多的连读替代重音,失去了其生命和温度。它已经被书写所吞噬。语言中的重读因素已经被辅音侵蚀穿透。(注:Ibid.,p.226.)
解构主义者这里提出的观点是:一、书写系统并非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外在于语言;二、口语或声音在其发源之时就受到了书写的增补作用(supplement)的干扰,口语被赋予的那种想象中的意义的完整性从一开始便被书写所瓦解,因此口语本身便永远充斥着差异和非此在意义的踪迹。
书写所具备的差异运作机制及其产生差异的力量,是语言存在并发生意义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无语言符号存在于书写之前”,因此,解构主义者把此前所有将声音和真理、声音和存在、声音和意义配置在一起的语言思想,以及一切将语言基本单位固定为“能指(透明工具)—所指(逻各斯)”式符号的观念,命名为“逻各斯中心—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认识传统,指出这种以压抑书写为表征、以语言或语音代表的真理为语言之本原、语言之终极目标的语言观传统所压制的就是意义不稳定、不确定的差异传统;(注:德里达在《论书写学》一书中这样说道,“在与语音一字母式书写相关联的语言系统中,产生了将存在的意义确定为此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完全彻底的口语时代,为了某些重要原因总是将一切有关书写本原、书写地位的自由思考用括号括起来,中止它、压制它。”(Of Grammatology,p.43.)主张语言符号既非实体亦不具此在性,而只包含差异的嬉戏;语言被“历史地构造成了一块差异的织物”。(注:Of Grammatology,p.141.)
至此,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层面确立了起来。从这里向深层生发、渗透,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我们知道,“语言转向”把认识论阶段的中心课题“知识问题”转换成“如何通过语言获取知识”的方法论问题后,语言哲学即是把认识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语言哲学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对语言本身有所显现,更在于它是进入思想、进入人类概念体系的一把钥匙,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换言之,语言哲学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语言转向”产生的双重成果和意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解构主义正是通过改变人们对语言的传统认识,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解构主义之前的思想史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方面,人们把显现出的存在(即此在)当作世界的全部,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寻求从整体把握世界;另一方面,在怀有知识欲望的人们眼里,世界是整一的、有序的,具有确定无疑的、恒常的、超验的本原和终极目的;此本原和目的,可供人类运用其先验理性和逻辑去追寻。本原和终极目的作为人们的求知中心,可以说,一直左右着西方哲学史的流程。本质、实体、物质、主体、超验性、意识——试看这些与人类认识基本原理相关的词语,无一不体现了此在世界的恒常性质。然而,解构主义的书写论摧毁了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以此在为存在形态的世界。“书写是最为原初的产生的差异的活动”,书写力量的发现和确认,促使支撑此在世界的确定本原和绝对中心坍塌了——世界不再存在绝对的主体和客体,主体和客体会随着差异的活动相互转换;世界也不存在抽象的真理和谬误,不存在本原性的绝对真理,因为真理和谬误是互相渗透的;同理,善与恶、生与死、感性与理性、自然与文化……种种形而上世界中的绝对二元对立范畴,种种用以描述形而上世界的恒常本质特征的概念和结构,均告消解、失效。这也就是说,书写产生的差异,赋予了解构主义者力量,以重新建构“存在”(being)与“不存在”(nonbeing)、有与无的关系:
在无语音的状态下,书写自身所背叛的是生命。它同时威胁着呼吸、精神以及作为精神与自身关系的历史。它是呼吸、精神和历史的终结和尽头,标志着它们的瘫痪。书写打断话音,通过字母的重复消灭或封冻精神创造……它是在者生成过程中(in the becoming of being)的死亡原则和差异原则。(注:Of Grammatology,p.25.)
书写意味着代表权威的声音的中止,意味着完全显现的内在自我消亡,意味着真理自我显现的历史结束。书写作为“无声”的状态,孕育了“有声”。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认为,“逻各斯中心—语音中心主义”受到书写观念的解构,其重要性和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意义走向多元”这一层次上,它更表现在中心主义的解体和形而上学所依存的二元对立两极的相互反转上。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解构主义者之所以喜欢在口语/书写这一对前人并不曾关心的语言范畴上大做文章,是由于它们是表现西方思想传统变迁的一对核心性隐喻。对于口语和书写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认识,预示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迥异,意味着宇宙、时空、人类历史的存在方式、存在形态、演变模式对于解构主义者和非解构主义者来说,具有天壤之别。信赖口语为语言之源,也就是相信存在为世界的基本特性和万物的根本共性,信仰世界具有稳固不变且具超越性的中心(本原),是一个具备等级性的结构。而相信语言之源在于书写,则是把形成差异的力量、活动和差异本身看作世界之本,把无——如声音的沉默、无意识、无中心、无序等——看作有的前提以及增补成分;这种视角消解了有与无的对立关系,因此,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在时空上无确定始终、在结构和解构的力量同时并进的作用中、在中心的形成和消解中变化、运行的世界。德里达总结说,“这套通过语音物质‘听(理解)自己说话的体系……必然支配了一整个时代的世界史,甚至产生了世界、世界本原的观念。”(注:Ibid.,p.7.)诺里斯也宣称,“人类的声音是对于开诚布公地建立在某种本原和此在的形而上学上的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认可”;(注: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1991),p.2.)此处所指,即就建立在此在基础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言,其根本的思维模式便是反映在符号学中的“声音—符号—书写”语言构成公式;而解构主义者的目标则是企图以“书写—踪迹—差异”这一思维序列取而代之。
解构主义者凭借书写理论既推翻了传统的符号学思想,又消解了形而上学思维体系。解构主义语言观的视域之异于传统语言观,由此可见。
那么,解构主义语言观诞生之后的文学批评世界又是怎样呢?
紧随解构主义语言观的脚步面世的是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和批评读解。这一于“形而上学终结”后乘胜追击而得的批评果实,引发了批评界关于批评“危机”的激烈论争。耶鲁批评家将“书写”、“踪迹”、“增补”等语言运作机制和“意义不定论”等观点引入文学考察、文本阅读,迎来了事先便可预见的批评危机——中心主义批评的危机。危机在解构批评者看来是激动人心、值得庆贺的,但在传统批评家看来,这无疑是批评学科的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要驳斥、反抗乃至“解构”解构主义,以证明解构批评的虚妄不经。
耶鲁学派一方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有J.H.米勒对解构阅读的描述:
解构,作为一种解读模式,通过小心谨慎地进入每一个文本的迷宫而发生作用……解构活动要消灭建筑物之下的地基,是藉着展示文本早已消灭那地基来实现的。解构并非肢解文本的结构,而是展现它早已被自身肢解。(注:J.Hillis Miller,“Stevens'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II”,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Robert Con Davis(Longman,1989),pp.416-427.)
保罗·德·曼也表达了他的误读理论:“文学语言的关键特质实际上是比喻性——这里指更宽泛的修辞意义;但是,修辞不仅远远不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客观基础,而且它恰恰意味着误读的可能永远存在。”(注:Paul de Man,“Literature and Language:A Commentary,”New Literary History,Autumn 1972.)
显然,耶鲁批评家遵循的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的思路,尝试在批评实践中树一面自由、多元主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他们倡导“误读”、阅读的“解放”,宣传文本的“自我解构”;他们试图说明,从解构的途径进入文本,便注定走上了不归路,因为前面只有无数的岔道,各岔道上又伸出无数岔道,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读者在迷途中忘记或抛弃自己进入文本时的动因——寻找某种真意。若有人在此刻发问,那么,阅读究竟是为了什么?批评研究的意义在哪里?他们会答曰:没有答案。他们鼓吹并身体力行解构批评,就是为了使人们悟到,问这些问题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硬要把“意义”一词强加到解构阅读活动中,也许可以说,任何人,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和意识开始阅读,总会发现文本自身充满矛盾,令其“不可读”,或者文本自身是碎裂的,阅读注定是“失败”——这种发现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是值得庆贺的事。米勒明知自己创制的解构修辞学批评有把读者以及自己导向穷途末路的危险,却仍旧欢欣鼓舞,便是因了这种缘由之故(“修辞研究通过摧毁自己的基本原则,借助于自己的理论程序,通向深渊”(注:J.Hillis Miller,“Stevens'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II”.))。
面对解构主义者对批评的改造(不仅把“旧式”批评置于死地,而且任由自己的解构批评将读者引向深渊),另一些批评家自然表示了他们的怀疑和批评。《批评的危机》的作者威廉·E·凯恩指责当下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学理论“越来越对自身和自身的存在缺少批判、缺乏怀疑”;理论工业的产量在剧增,但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枯燥无味且不真实,与批评实践和批评教学中的具体论题毫不相干,与人类需求和利益完全脱节”,理论家们“追逐着最新潮流,操作着最新的方法,却从不过问价值和意义等问题”。他认为解构主义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失去依据,批评学的目标——从文学文本中获取具体知识——在解构主义方法中解体。(注:William E.Cain,The Crisis in Criticis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xi-xvii.)约翰·M·埃里斯在《反对解构主义》一书中对解构主义批评的症结表述了不同观点,但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解构主义的内在本质是反理论的;因为文本性赋予读者、批评家和文本以自由,理论却是把无限的可能拢集在条条框框下的努力。解构主义的反理论性,必然导致解构主义的批评纲领空泛而毫无意义,因为主体/客体、实质/非实质等对立范畴的界限在阅读活动中被取消,使读者的阅读成为漫无目的的游荡。(注:John M.Ellis,Against Deconstru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94.)当然,反对者当中,影响最大的要数M.H.艾布拉姆斯力撼解构主义工程的论文《解构主义天使》。在文章里,艾布拉姆斯指出,德里达企图以书写说、异延论解构逻各斯或语音中心构成的形而上体系,而实际上,他在构筑推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依靠自己和读者头脑中固有的本原、基础、终极等先验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德里达不过是用书写中心代替了语音中心,书写中心的前提同样筑成了形而上学的结果——不可名状的“异延”所蕴含着的自由嬉戏所构成的世界观担任着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艾布拉姆斯从解构主义语言论的“两面性”,引出了米勒作为批评家所担负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作为解构批评家进行着解构的游戏;另一方面,他又走出书写中心,以主体的身份发言。在艾布拉姆斯看来,米勒的批评从构思到传送至读者的心灵,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均几经书写(意义不确定)和声音(意义确定)之间的转换,因此,一方面,解构主义者将书写中心式的解读运用于文本的行动潮流固然无法阻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拒绝让解构法则替代日常理解和语言技巧的人来说,他们仍旧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文本。
不过,艾布拉姆斯通过批判米勒的批评模式而否定解构主义语言观和思维方式,是失之偏颇的。至少,他在分析解构主义语言论时忽略了一点,即德里达提出的语言中不断发生的“擦抹”(erasure)作用包含着抹去和保留双重含义。书写对于本原、中心、终极,解构主义思想对于形而上学,并非在全盘删除的基础上构建自身以取而代之,而是颠覆、批判,又有所保留。甚至在解构“工具”的选择上,德里达也坦言一切取自形而上学的百宝箱,因为他承认没有什么工具是不属于形而上学的,他只能从这一点出发,着手自己的工程。对此,斯皮瓦克在《论书写学》前言里有一段清晰的解释:
我们必须知道,即便在我们有意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仍处于形而上学的“围墙”(cloture)之内。如若把形而上学的这种“终结”(closure)(注:法语的“cloture”和英语的“closure”均有双重含义:围墙、包围圈;终结、结束。)仅仅设想为形而上学在时间上的完结点,我们就会犯历史循环论的错误。使目的和手段相符、制造一个包围圈、使定义和被定义者相符……——这些也是形而上欲望。我们的语言体现了这种欲望。因此,我们正是从语言的内部着眼努力开一个“口子”。(注:Of Grammatology,p.xx.)
因此,艾布拉姆斯对德里达构建书写论的方式做出的批评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书写学说之所以能够成功,恰恰就在于对形而上学的挪用。
然而,同样,我们不能否认,艾布拉姆斯对耶鲁批评的分析和批驳是鞭辟入里的。立足于形而上学内部,运用形而上学的术语展现形而上学体系自我颠覆、已然瓦解的状态,同时演示反形而上学的思想,这是德里达构建解构哲思的方式。他依靠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营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对世界形态和本质的新型设想。正如“逻各斯”作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超验实体因而不可实证一样,这种新观念和新设想毋须实证也不可能实证。德里达在著述中尽量避忌使用肯定或界定式的语句描述解构思想中的关键词与核心主张,而是不厌其烦地以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方式推进自己的立论,其实就是在反复重申解构主义的要义不在于用概念或定义捆扎复杂而抗拒言说的思想,借此圈一片自己的领地;恰恰相反,其要旨在于借用形而上的语言,传达一种反形而上的思想。解构主义的目的和手段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状态,注定了它要被读者接受,便多半得诉诸读者的想象力和领悟力,而不能借助于实证方法。线性的因果推论和实证,与解构主义的“差异”主张格格不入。然而,耶鲁批评家们无一不在“解构”的旗号下做着实证性的工作。解构的宗旨在于使人意识到形而上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对语言活力的压制、对多元常变的世界的简化,同时令人领会语言或文本的丰富性和意义无限性。而耶鲁批评家实际做的却是将解构学说立为超验信条,将其非概念性的“术语”当作概念来论证。艾布拉姆斯点出米勒角色的两面性(解构性和非解构性),可见并非没有道理。
批评的危机既是公认的事实,那么,围绕“危机”一词的争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争端?
实际上,批评的危机是解构主义批评模式引发的、关系到批评的角色及其存亡的危机。对立两派间的论战,传达了人们的关心: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之下,批评要往何处去?
在符号语言观的指导下,我们不仅相信语言的指意单一而确定,而且认定语言会揭示出某种超越语言的真理性中心。“语言理论决定文本理论”。(注:Vincent 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An Advanced Int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81.)中心主义语言观孕育出的批评理论逃脱不了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艾布拉姆斯针对西方批评史建构的概括性框架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是4个独立的范畴;从“作品”指向另3者的箭头表现了批评的向度;“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在批评史上的兴衰沉浮,昭示的是批评中心的一次次建立、一次次更替。符号语言观所信赖的超验所指,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就是批评家所信赖的文学价值核心,如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审美价值体系等。由此,批评便担任着双重任务,一是从理论上反思、认识、理解自身;二是依据价值核心,对具体作品进行描述、阐释和评价。传统的文学批评是一门探索真理的学科(科学);批评家围绕某一真理性的中心构建理论框架,实施文本批评,而文本批评实践又总能论证其批评理论。与此相比,解构主义批评,作为相应于解构主义语言观和世界观的批评主张,无疑打破了上述格局,并将批评的双重事业推向困境。首先,解构主义者解构形而上学,其消解的对立范畴无疑包括文学/非文学、文学/批评、真理/谬误等;文学形式与非文学形式、文学与批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永恒的真理变成了踪迹的运动,批评也就不可能以发现和揭示真理的身份自居。那么,批评将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自柏拉图以来的批评传统是否就此中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否它将应验解构主义批评家的构想——走向那值得欢呼的“深渊”?其二,有固定中心的等级价值体系,不管是社会的、个人的,还是道德的、审美的,都隶属于形而上学系统;如果说在结构主义时代价值评判还只是因为批评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被搁置一边,那么,在后结构主义时代,批评所肩负的评价使命已经正式被自己的理论立场所摒弃,宣告寿终正寝。批评变成阅读,文本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变。传统的文本有标题、有作者、有开头和结局、有整体性及有限的内容,文本的构架之外即为指涉的现实领域;可是,在解构主义者眼中,文本却丧失了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边界,成为一个差异网络——它所包含的是一系列差异的踪迹,这些差异的踪迹又指向其他的差异踪迹。那么,面对无穷无尽、变化不定的踪迹,面对没有界限的文本,面对批评家设立的没有中心、没有标准的解读要求,作为阅读的批评实践将如何操持?批评是否只能走上以米勒为首的解构主义批评家所设计的困顿之途,即艾布拉姆斯所抨击的近似于“精神分裂”式的批评?
将解构主义语言观与解构主义批评相对照,将解构语言观的革命意义和解构批评生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一切争执的起点都在于解构主义者为维系逻辑推论的严整性,而依据“形而上学—符号语言观—前解构式批评”这一模式铸造的“解构主义世界观—书写论—解构批评”这一思维线路上。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对西方思维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它不单单是一门“以确定万物的真实本质为研究目标的哲学性”(注: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24(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p.1.)学科,它早已化身为人们进行认识活动、进行思考的一种固定程式。蒂尔曼·库什勒在《后现代游戏》一书序言中这样总结人们的“形而上欲望”:“把事物纳入种种法则;运用规律分析运动,使之静止;通过解释活动得出意义的构造,以消除意义的含混;最后,把多元化的现象简约为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注:Tilman Kuchler,Post-Modern Gaming:Heidegger,Duchamp,Derrida,p.1.)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统治力量几乎无所不在;人们的意识世界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冲动,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拥有真理和自由的绝对主体,习惯于运用逻辑和理性把芜杂多变、难以言说的世界简化地描述成一个静态的、有序的世界,将万物蕴藏的多样性表述推演为最终的一元。
我们生活在形而上学的国度中,解构主义思想也只能以一种思想“反应”的形态产生于形而上学内部。解构主义挪用形而上学来反对形而上学,挪用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论来反抗理性和逻辑,使我们窥见了形而上思维以外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可能。这一构想以独特的思路途径避免逻辑混乱,它在当代诸种有志于“治疗”形而上学或颠覆形而上学的语言哲思中无疑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创造。然而,如若批评者对批评实践的实证性与解构之思之间不相容的关系不加辨析,在惯性思维的驱使下企图证明文本的“解构性”的话,他注定要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走向一种既不见容于形而上批评传统,又违背解构思想的窘境。“解构主义世界观—书写学—耶鲁解构批评”体现的无疑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艾布拉姆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