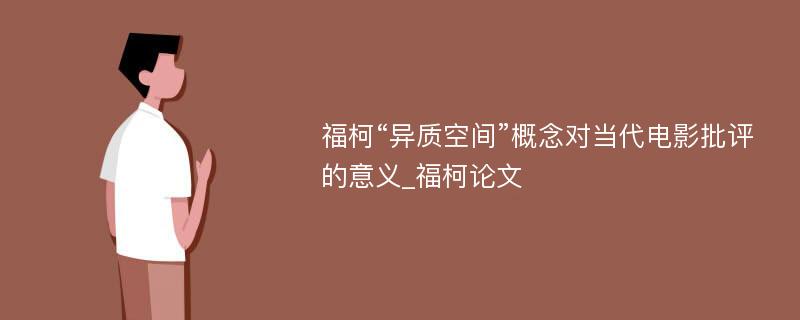
福柯“异质空间”概念对当代电影批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概念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柯在1967年完成的巴黎演讲稿《关于异类空间》(Of Other Spaces)中阐述了“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概念。Heterotopia这一命名源自希腊文,“hetero”意为“其它的”、“不同的”,而“topia”意为“地点”,所以这个词从字面可译作“差异地点”,此外另有“异质空间”和“异托邦”等译法。这一概念本在医学领域应用,意指错位或冗余的器官。在福柯的阐释下,异质空间的概念在(后)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理论魅力。借助异质空间提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研究者可以对社会空间进行“差异地学”的研究,其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是空间中存在的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空间。在“差异性的地点”的字面意义之外,异质空间的涵义还有一层,即“遗忘”与“移置”[1]。由此,在异质空间理论视角的观照下,社会研究者面前所呈现的往往是非主流的、另类的、被遗忘和忽视的空间景观与社会关系,关联到文化与政治,叙事与审美等诸多问题。
福柯提出,异质空间具有六种特征[2]:第一,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异质空间,但异质空间江不存在绝对普遍的形式。第二,每个异质空间都具有其精确而特定的功能和价值,而这种功能和价值将随它所在的文化的变迁而发生这种或那种变化。第三,异质空间可以在同一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地点。第四,异质空间通常和时间的片断性相关。第五,异质空间有时必须经由特定的文化仪式或具备群体的共识才能进入。第六,异质空间对于其它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有两个极端:幻觉性的和补偿性的。在现代性和都市性不断发展延伸的当代中国,这种理论视角的适用语境已然生成。而且,如上的症候也必然在文艺领域得到显现。于是,从“异质空间”及其相关理论入手,对当代电影进行批评,可算作是一种独特的思路。
一、异质空间的界定与辨析
在福柯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形态与前现代空间形态的差别在于空间散落为众多的“基地”(site),它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和异质性,并且不断产生着矛盾和对抗。而异质空间就是建立在“基地”基础上的特殊的空间形态,包含了有别于主流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福柯给异质空间的定义是:“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的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纵然如此,却仍然可以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拟地点的差别,我称之为差异地点。”[3]
福柯曾以镜为喻来进行说明——“我相信在虚构地点与这些截然不同的基地即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以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总之,镜子是一个无地点的地方,所以是一个虚构地点。在此镜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打开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这是一种镜子的虚构地点。但就此镜子确实存在于现实中而言,又是一个差异地点,它运用了某种对我所处位置的抵制。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对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我自己。从这个凝视起,就如它朝我而来,从一个虚像空间的状态,亦即从镜面这彼端,我因之回到自我本身;我再度开始凝视我自己,并且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4]
毫无疑问,空间的认识者无一例外地身处在他习以为常的隐蔽的社会文化秩序中,他们对空间的认识过程酷似在普通的镜像中只看到自身的形貌,却并未察觉需要对形成这形貌的机制和秩序进行反思。不过当认识主体面对一个由异质空间所构成的镜像时,他者的异质性就会映衬出主体所处的秩序的存在,并有可能推动文本对自身身处并习以为常的秩序进行置疑和颠覆。最终,主体在对异质空间的观照中有可能达到对自身及社会环境的重新认识,获得新的知识,并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共存问题上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异质空间的认识论价值是打破某一秩序的宏大叙事,发现众多“微小叙事”的价值。这个理论视角在伦理维度的推论,即是平等、包容和自我反思的精神。对社会是如此,对艺术作品也同样如此。
由于福柯对异质空间的解释带有某种含混性和未完成性,所以各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莫衷一是。格诺奇奥认为“与其说异质空间是具体可见的空间,不如说是不可见,随时在改变的‘匮乏’”[5]。这同样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如果说乌托邦是对现实的完美超越或者与现实相反的恐怖梦魇,那么异质空间总是缺乏真正的同一性的表述,缺乏对彻底颠覆同一性的力量的约束。同时异质空间的视角也引出了有关焦虑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正是来自“匮乏”)。在探讨的最初阶段,他者的存在加强了我对我自我位置的确认,而且他者显露出与我不同的“匮乏”。此时我们需要考虑:他者究竟缺乏什么?不过认识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匮乏”或许是“他者”劣于我的证据,但更可能代表着另一种我所不具有的(文化)形式。它的形式穿越由匮乏所构成的镜面,使“另一个我”与我并存[6]。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异质空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的板块不会也不能被拼入同一个拼图。”[7] 系统的同质性,即如此被异质空间消解了。
但格诺奇奥对异质空间概念在文化研究中被任意使用的状况不为不满:“如果去掉对想象力的限制,那么问题就会变成:究竟还有什么不能被指认为异质空间?由此可见,大多数对这个概念的不加批判的使用,把它作为一种非公平的或抵抗的空间来看待都应当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8] 这种说法的价值,有待社会空间实践和批评实践来共同检验。
苏贾有关异质空间的论述带有总结的性质。他在《第三空间》一书中首先明确了列斐伏尔和福柯之间的观点差异,认为后者忽视中心和中心性的立场有别于前者持有的综合性态度,因此要理解福柯意义上的异质空间必须了解福柯开放的散点式批评姿态。借助对《关于异类空间》一文的解读和评价,苏贾认为福柯有关异质空间的论述的精髓在于开放性和怀疑论。“福柯的异形地志学缺乏完整性、一贯性和逻辑性,这一点未免让人失望。它们似乎局限于专门的微观地理,鼠目寸光,离经叛道,游离于政治之外。但是,它们又是成果丰硕之旅的发祥地,从这里可以走向第三空间,走向差异构成的空间,走向他性的地理历史”。[9]
据凯文·亨廷顿的著作《现代性的荒野:异质空间与社会分类》调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社会研究者都喜欢使用“异质空间”这一概念。他们当中有Teyssot,Connor,Soja,Delaney,Chambers,Lyon,Bennett,Genocchio等人,其中每位学者都有各自的观点和阐述。他得到的结论是:第一,异质空间的概念通常会被学者们不加理论化地应用,包括那些试图界定它的学者;第二,异质空间被应用于后现代性的批评语境多于现代性语境。亨廷顿本人认为:“异质空间与其说是一件事物,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异质空间存在于空间之间,在空间的关系之中”[10]。
如果本文必须对异质空间作一个界定,那么构成这一概念内涵的要点应为“异质性”、“空间”、“权力”和“秩序”。“空间”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当中,都是包容性极强的语词,可以指代现实的地点及相关经验、关系和抽象的秩序及法则。这对概念的描述是十分重要的。福柯的描述以“现实加虚幻”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后)现代性的逻辑,那么阐释“异质空间”也可以参照这点,适时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异质空间既看作“地点”、“现实空间”、“事物”或“事件”,又看作“关系”、“法则”、“秩序”和“过程”。这种看似自我矛盾的说法,其实已经贴近了异质空间作为方法或视角的独特魅力所在。借用伊格尔顿的观点来评价异质空间,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用概念来框定住对象,却又以某种理智的杂技在瞬间使概念化的同一性滑动起来的哲学风格。”[11] 或许只有极具(后)现代性的概念,才需要使用这种诡辩式的命名和阐释。在此基础上,论者只需强调异质空间能够在其内外并置两种或多种相互矛盾的秩序和法则,并且打破其所处的系统的均质性和同一性,就可以有效地回应格诺奇奥的诘问了。
二、由社会批评到文艺批评
异质空间在理论研究和分析方面,因其对空间研究的适用性,无论面对全球空间,国族空间,都市空间,或者家庭空间和身体的空间,都具有独特的阐释价值,提供着独特的视角和思路。
在对国族空间的文化差异性的阐释方面,张隆溪评述“异托邦”的概念说:“这可能是有关不可分类事物的最著名的假想空间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命名和分类并不依照西方所能理解的体系或逻辑。‘异托邦’以其荒谬的分类法动摇了西方通常的逻辑类别。福柯在谈到他读过的‘某本中国百科全书’时说,‘异托邦’体现出另一种思维体系的异域美。对于福柯来说,中国处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不管是地理距离还是文化距离,它都是欧洲和西方的对立面,中国的国土是‘非托邦’,中国的文化是‘失语’,中国是欧洲人不可能‘命名、描述和思考的’。福柯的‘异托邦’就像谢阁兰的‘内在’一样,都是极其宏大,无法用言语命名和描述的空间,都只存在于某个距欧洲自我要多遥远就多遥远的地方。”[12] 国族文化之间的“异”的空间,也纳入了“异质空间”的关注范围。不同的国族认同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中,成为了社会空间中不可通约性的来源之一。
此外,有研究者在评述福柯的思想时认为:“福柯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这一概念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环境的文化冲击中表现的很明显。异质空间指的是不同空间可以和其它空间发生联系,虽然它们看似毫无关系。异质空间的经历使人们考虑他们所处的究竟是哪个世界。”[13] 这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异质空间的阐释价值,这也关系到本文重点讨论的电影中的都市空间中的社会景观问题。其原因是,在我们讨论现代都市的殖民地历史,或在全球化趋势中文化认同的问题作一讨论时,“都市化”与“殖民化”可能具有同构的逻辑。
另有批评者以异质空间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来探讨都市社会事件及媒体效应,如阿方索和埃利奥特合著的论文《关于神圣化的间离:作为异质空间的黛安娜车祸事件》[14] 将黛安娜王妃车祸事件及其社会效应作为异质空间的个案来探讨。又如在景观设计和文化实践方面,台湾社会研究者陈钦河的论文《华山艺文特区活动形塑场所精神关系之探讨》[15]、郑国贤的论文《时空异置下论文化资产展示中的记忆与经验之断层——以兵马俑秦文化特展为例》[16]、陈其澎的论文《透视浴室——沐浴空间与沐浴文化中异质情境的研究》[17]、吴铭兴的论文《台湾异质空间之研究——以台中市逢甲商圈为例》[18]、江柏炜的论文《“洋楼”:闽粤侨乡的社会变迁与空间营造(1840s—1960s)》[19]、黄耿皇的论文《论权力场域的究竟建构:以台湾军司令部到陆军联谊厅转变为例》[20] 等都借助异质空间的概念及其视角来探讨地区文化历史及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意味。现代学术界所进行的此类研究,基本思路大都是重申了福柯在演讲中透露的学术倾向,将现实的空间(都市建筑和景观,乃至浴室等私人空间)视为(社会)权力机制的产物,反过来又通过这种产物透视权力机制对其发生的形塑作用,并引出一纵向历史的类型思考,从而由看得见的“小空间”或“小历史”的立场来窥探看不见的“大空间”或“大历史”。
具体到建筑艺术领域,福柯在对异质空间进行现代阐释的一系列论文及访谈当中,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批评,已然作出了艺术和社会批评相结合的尝试。大陆建筑研究者汪原在论文《福柯及其“异托邦”对建筑学的启示》中,重申了福柯关于异质空间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异质空间除了对空间系统的连贯性和总体性的界限提出质疑和破坏之处,还具有零碎、瞬时、矛盾和转化的力量。作者文中举出了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家Denis del Favero的环境装置个案,以此说明异质空间的功能:“该装置位于悉尼的地铁站上,由访谈、广播、图像、文本和声音作品这些多种形式组成,它通过了一种对地铁空间的大胆的使用,即将地铁空间作为与问题发生关联的场地。这一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考虑到了‘异托邦’,即现代地铁系统的非场所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监视和控制的惩戒模式相联系的权力的增长。在这一层面上,整个装置的最有趣的是录音带所播放的声音反复被地铁警察的叫喊声打断,而这些叫喊声并非出于什么安全原因。由于以媒体、艺术、体验、表征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形式包含了各种知识的展示,这些装置立刻就成为各种知识发生关联、置换和矛盾的场地,因而能将不确定装置入既有的空间秩序中,通过临时影响被人们认同的、定义和限制了的秩序关系,依次产生出动摇这种秩序的根本力量。”[21] 在此类研究中,异质空间的视角不仅能够分析现实的空间之中的秩序和权力机制,而且可以将现实的空间作为权力机制的隐喻,凸显其作为(建筑)艺术品的形式意味[22]。
从社会批评到文艺批评,异质空间作为视角和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检验。如上的批评实践证明,由异质空间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艺术作品中的现代都市空间,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选择。
三、走向电影批评
在电影研究中,异质空间可以与空间社会理论和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方法相结合,将电影的社会意涵研究、叙事研究与电影的本体研究整合起来,形成电影研究的新思路。这方面的论著并不多见,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有陈少红的专著《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23] 中对香港导演陈果的个案分析、台湾学者张小虹和王志弘合著的论文《台北情欲地景——家/公园的影像置移》[24]、杜菲的论文《雕刻时光: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索拉里斯〉中的异质化空间》[25]、刘纪蕙主编的论文集《他者之域:文化身份与再现策略》[26]、大卫·克拉克主编的论文集《电影城市》[27]、陈衍秀的论文《游离岛影初探: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流”转“离”散之“岛”影——以〈噤声三角〉、〈南之岛之男之岛〉、〈0304〉、〈马祖舞影〉、〈基隆屿的青春纪事〉为例》[28] 等等。以上的研究者们本着各自对空间和乌托邦的理解来进行电影研究,均提供了对异质空间概念可能的阐释,并利用这种阐释来进行文本解读,或者推进对电影的本体认识。
其实,福柯提到的异质空间六个特征中,几乎每一特征都可以对电影研究提供启发,引导研究者开启电影研究的新主题和新视角。
异质空间的第一特征认为没有一种文化不产生异质空间。循着这个思路,那么电影研究者面对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也可以说:没有一部电影不呈现异质空间。关键的问题是,某一部电影作品中的空间能否在与其它空间的比照之中发挥特殊的功能,在叙事流程中创造特殊的意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空间中的那些具有颠覆潜能的关系乃至空间场景,才有可能建构并发挥异质空间的功能。在这一原则的关照下,无论电影艺术形式本身,或是电影中的具体场景,都可看作是整合了并非一种文化倾向和文化意味的建筑物。
第二特征论及的墓地的空间形式作为一种异质空间的范例在电影表意中的作用是耐人寻味的,从这个思路出发的主题研究可以关联陈果的《香港制造》(1997),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2001)和徐静蕾的《我和爸爸》(2003)等文本的叙事段落,阐释艺术本文所呈现的社会空间和场景的文化意义。
第三特征可以关联到电影叙事空间与电影中呈现的实现空间之间的关系,比如电影中的“反思性叙事”及其意义。此外。异质空间对于在功能上互相交叠的现实空间的关注也与当代电影导演的实践相关,如贾樟柯在谈论其作品《公共空间》时提及的碎裂和拼接的城市社会空间中,不同的空间与其功能叠加在一起,拥有一种独特的意味,也为电影叙事的表意提供了多种可能;“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的空间和现在的空间往往是叠加的。比如说一辆公共汽车,废弃以后就改造成了一个餐馆;一个汽车站的候车室,卖票的前厅可以打台球,一道布帘的后面又成为舞厅,它变成了三个场所,同时承担了三种功能,就像现代艺术里面同一个画面的叠加,空间叠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29] 在这一原则的观照下,贾樟柯电影叙事中的某些城市场景,可以视为散发着当代社会文化意味的装置物。在电影呈现的现实空间中,表层的物质性和深层的社会文化性,都集中到影像的文本之中。电影文化研究的推进,在物质存在和文化变迁方面,都能够汲取丰富的资源。
第四特征中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代表的异质空间的历史性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方面可供研究的个案有《如烟往事》(鲁晓威,1993)和《爱情灵药》(苏兆彬,2002)中的相关场景。与此相关的更为深刻的电影本体论意味在于,现代电影与图书馆或博物馆一样,都是在(叙事)空间的组织之中“收藏”了已逝时光及文化经验的集合体。蒙太奇、长镜头、闪回(前)、切换、淡入(出)等镜语叙事手段,是电影所独有的为“片断化的”时间和空间的感知经验进行排序和组合的手段,如同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功能一样。
第五特征对黑帮电影、监狱等类型电影的相关场景拥有一定的概括力和适用性。电影中呈现的都市社会中的边缘人群,由此视角可以得到关注:如街头青少年和同性恋者经由自身的都市空间而建构的异质性的社会关系和情欲取向等等。
第六特征在对殖民地的例证进行的阐释中,又与萨义德的理论有共通之处。同样富于启发的是以船为代表的“漂浮的”异质空间,于是《女人·TAXI·女人》(王君正,1991)、《夏日暖洋洋》(宁瀛,2000)、《国道封闭》(何平,1997)和《运转手之恋》(陈以文,2000)中不断发生重组和漂移的汽车内部空间也会在这个阐释的框架下凸显其文化意味。这在类型研究方面可与“公路电影”相对接。同时,在与卡斯特尔所提出的“流动空间”的概念的联系中,都市空间的电影呈现将更加贴合(后)现代性征候中的社会境况。
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被研究者表述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异质空间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有着无数不同而又经常冲突的空间。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导致身份危机(crisis of identity)。”[30] 这种说法给予当代文化研究者的启发是,必须通过研究都市人来完成对都市空间的研究。
在“异”空间的映照下,社会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显出了一幅斑驳芜杂的地图。在电影研究中,异质空间的问题同样是值得思索的,它可以在影片意义的生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成为对电影和都市的关系进行考察的切入点。此种视角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空间或地理状况,可启发电影研究者对电影文本中的空间呈现及社会文化意涵进行研究。
此外,异质空间可以与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的众多现象互相应和,研究者由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从文本内外两方面展开对电影的阐释,有助于揭示特定时代电影中的都市呈现及审美特质。
本文试图借助对电影中都市意象的研究来推进的论题即——异质空间在拓展影片的都市社会文化内涵方面的功能及价值。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还包括:电影中呈现的都市(空间)与电影(空间)的关系;(后)现代性与电影叙事;社会转型与电影主题及审美特质的变动。在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中,“异质空间”不可避免地要溢出福柯的框架,被置于广阔的空间理论的背景下,在中国电影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