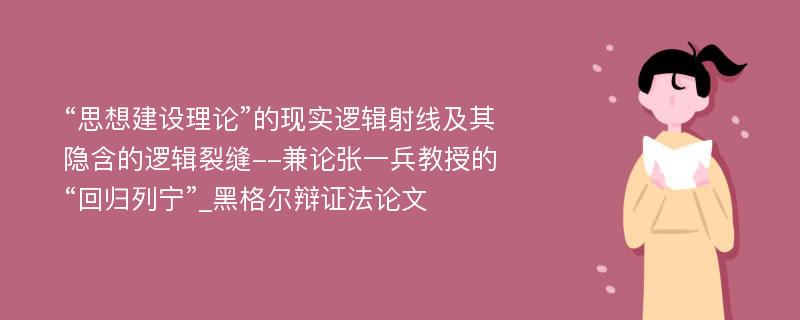
“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及其隐性的逻辑裂隙——兼评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列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裂隙论文,隐性论文,列宁论文,射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2-0064-06
《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新近发表的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专题的研究力作。该书以列宁的哲学研究历程为主要关注点,以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伯尔尼笔记”①为核心文本,首倡并运用“思想构境论”,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历程进行细致地“构境”,从而拟现了列宁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几次重大的“逻辑异轨”。就本书所运用的独特的文本解读方法而言,作者更突出了解读者对于文本对象的主导性地位,这也意味着作者并不避讳思想解读过程中的主观性,而更加重视的是思想史解读过程中所能达及的相对客观性。毫无疑问,这其实是一种高度的学术坦诚和方法论自觉。②然而,这种极力伸张解读者主体性地位的新文本解读方法如何避免掉入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陷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避免使“思想构境论”化身为专家学者们主观主义式自说自话的逻辑保护伞,进而致使对列宁思想之境的重构沦为学术版的“罗生门”,已经作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摆在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学者面前。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灵活地处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张力。事实上,通读该书,我们不难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正是作者解读列宁思想及其发展过程的重要视角,也是“思想构境论”的核心基点。③本文将以此为中心视角,探求“思想构境论”的现实根基,同时指认出该方法在具体的分析过程所存在着的隐性的逻辑裂隙。
一、“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
很显然,作者在本书伊始所袒露的研究心迹是该书方法的一个缩影:“在这些年思考和写作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历史进程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始终就是这一幕幕滚涌着战火硝烟和高昂革命激情的历史画面……”④。纵览全书,作者对列宁思想进阶过程的思想构境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实的大地。如同作者前一本影响显著的《回到马克思》的“回到”一样,《回到列宁》的“回到”也并非一种简单的从现实回到书本式的“知性判断”⑤,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原初语境,“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去真实地探讨经典作家的文本。”⑥在笔者看来,此处作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正是理解“思想构境论”的逻辑支点,具体到对列宁思想发展的解读过程中,至少包含如下两大质点:
首先,研究对象的历史生成性。在本书作者看来,列宁的思想(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领悟)原本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作者极力拒斥前苏东解读模式中的列宁思想前后同质性的假设,因为后者所导引的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伪饰。并且,这种具有明显的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及其显性结论,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的光照之下立刻就显现出了其非科学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文饰性。正如作者所言,倘若我们只是简单地、非历史地依据哲学原理对列宁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哲学文献进行专题性的裁剪,那么,我们对列宁思想发展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非科学的同质性的逻辑强暴”⑦阶段。显而易见,就承认列宁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非同质性而言,作者只是重申了一个大多数人都容易接受并认可的事实。然而,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及其衍生出来的陈旧的思想史解读模式下,那种坚持列宁思想前后同质性假设的种种理论表述依旧只是一个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装”。
其次,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辩证关系是理解列宁思想发展的主导线索。诚如作者在本书中的多次指认,列宁思想发展的动因并非仅是理论研究的精进而导致其思想的“逻辑异轨”,而是深深根源于列宁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所致力于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⑧正是基于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辩证认识,我们不难注意到,作者在应用“思想构境论”对各个时期的列宁思想进行构境时,列宁所处时代的革命实践活动始终是该方法的主导视角。作者曾将自己的这项研究工作戏称为一次“田野工作”,在研究纷繁冗杂的文献之外,作者“还认真厘定了列宁哲学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的内在关联”⑨。而在介绍“思想构境论”时,作者也明确指出,“意识与思想构境实现的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性依托”⑩。具体到本书的研究细节中,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内在关联无疑是贯穿本书的隐性线索,而这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作者在本书中首倡并灵活运用的“思想构境论”的核心基点。
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的分析案例。首先,在本书上篇中,作者紧紧抓住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存在于列宁思想中的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过程。(11)对这个线索的把捉,一方面见证了普列汉诺夫等人对列宁的思想牵制,即作者所说的“他性镜像阶段”;另一方面,这也为列宁后来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理解并达至“实践辩证法”的深刻认识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动因。此外,在探讨列宁的理论起点时,作者通过考察同期列宁写下的其他文本后发现,青年列宁此时的思想旨趣和现实努力,主要都聚焦在与俄国的民粹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上,而后者“显然是一个由现实斗争的重要理论需求而产生的特定理论构境”(12);在分析列宁哲学研究的现实旨趣时,作者强调,在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列宁身上强烈的“实践旨趣”并不是一种“显性的理论直白”,而是一种“体现在其具体思想构境中的看不见的逻辑射线”(13);而具体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缘何成为列宁研究焦点这一问题的分析时,作者指出,一方面是因为列宁通过1913年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阅读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现实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14)。作者的分析显示,正是这条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的“逻辑射线”,导引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意识的高度重视、对“经济派”观点的坚决抵制以及与普列汉诺夫政治立场的分道扬镳,更进一步隐匿于列宁突破哲学唯物主义的他性理论镜像,实现认识的“格式塔转变”并达至实践辩证法的认识飞跃中。在总结列宁的思想在“伯尔尼笔记”中实现格式塔转换的原因时,作者强调,“列宁哲学思想场境在‘伯尔尼笔记’中发生的这场格式塔转换,并不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促发。……这种思想转变中最关键的驱动力其实是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下时刻中困扰着列宁的现实革命实践和斗争。”(15)诚如作者所析,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改造,经历了从前期的概念颠倒到以实践辩证法为基点的逻辑颠倒,其中最为关键的“逻辑异轨”正是导源于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的“实践创造和改变存在的命题”的发现(16),在其现实层面上却深深植根于列宁对其时代革命活动的关注和思考。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的哲学文本只是其理论进展的酵母,一个借以发挥实践精神的“题”而已。如此,我们更有理由认同作者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最终指向的,并不是一本有定论、有体系的唯物辩证法专著的写作,而是俄国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和革命事件。”(17)
毫无疑问,该书中能让这一隐性的现实“逻辑射线”得以彰显的分析实例实在不胜枚举。作者对列宁阅读批注细节的细心捕捉和精到分析,在揭示出列宁哲学研究中无处不在的现实旨趣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其“思想构境论”无处不在的现实逻辑射线。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本书中,作者的这一从现实实践出发的立场并没能贯彻到底。如果说,在对迈向哲学圣殿途中的列宁进行思想构境时,作者对列宁理论研究的实践立场表示出了更多的重视,而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从分立趋向融合的过程则是贯穿上篇的一条红线;那么,在下篇中,作者的研究和显性表述似乎对于理论逻辑的内在变迁表示出更为明显的偏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这种隐性的内在逻辑偏向事实上构成了“思想构境论”的逻辑裂隙。
二、隐性的逻辑裂隙
在笔者看来,“思想构境论”的这一逻辑裂隙的端倪最早出现在作者对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分析中。在该文中,作者注意到,在阐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被列宁忽略了。对此,作者只是深表“遗憾”,没有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而只是倾向于认为在列宁此时的思想回路中并没有与拜物教相适合的内容。(18)细细想来,这其实也构成了本书中的一处遗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曾熟读《资本论》并深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列宁不可能不曾碰触过马克思拜物教的理论,然而绝大多数的资料与分析显示,这并没有成为列宁的理论关注点。倘若坚持“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即列宁理论研究中强烈的现实指向性,那么,对该现象的剖析无疑将导向对当时俄国的现实思考。作者也意识到,在当时的俄国,工人的数量相对于农民而言仍只是非常可怜的“少数派”,作为拜物教赖以生长的现实温床的商品经济浪潮在俄国并未成为显性的主流,相比而言,革命与战争才是那个时代当仁不让的主题。如此看来,拜物教理论在当时的俄国而言仍然是过于“前卫”的学说,而关注俄国现实并积极寻求革命道路的列宁对它的选择性漠视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回到本书中作者对该现象指而未析的细节,我们不难联想起作者此前在解读费尔巴哈拜物教理论遭遇列宁的冷遇时给出的解释——在列宁此期“他性镜像式的理论回路中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东西”(19)。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作者在运用“思想构境论”解读列宁思想进程中潜在的逻辑裂隙的症状。因为,作者在本书中曾多次强调,对列宁进行思想构境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立足于列宁的时代背景及其现实活动。然而,在关于列宁对拜物教理论反映冷淡的现象的分析上,作者却表现出对“理论回路”的极大青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便令人遗憾地消隐于作者精心捕捉的“理论回路”中了,这一现象无疑构成了本书分析逻辑的一个隐性的断裂。然而,这道令人遗憾的逻辑裂隙并不仅限于有关拜物教的分析,而是悄悄地延展至作者对“伯尔尼笔记”时期列宁哲学思想大飞跃的构境中。
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的例子。首先是作者对列宁阅读过程中的失语现象的分析。在本书中,细心的作者注意到了列宁前后两次比较集中的失语现象。具体来说,作者的分析显示,在面对《逻辑学》第一部分《客观逻辑》的第一编“存在论”时,列宁对于其中的许多精辟而重要的论断并“没有特别的感想”、“很少发表评论”,只留下了一些“不带评价的摘录”(20)。作者对这一现象原因的分析结论是,“在此时列宁的阅读空间里,能够与黑格尔思辨逻辑构境匹配的相近认知结构是缺失的”,换言之,即“他的现有理论回路中没有相近的链接思考点”(21)。就列宁初读黑格尔《逻辑学》的“失语”现象而言,在笔者看来,我们可能会遭遇两种思考路径,一种是偏重理解构架和“他性镜像”钳制下的分析路径,即本书作者所主张的那样,这是一种偏重思想逻辑线索的可能性分析;另一种是偏重理论研究的现实动机的思考路径,即充分考虑到列宁研读黑格尔哲学是出于理论斗争(回到列宁所处的特殊时代及其特殊身份,理论斗争无疑是直指向现实革命道路的探索问题)和探索现实革命出路的需要,那么,黑格尔思想中与此无关的东西自然被无视了。事实上,正如作者之前所成功演示的那样,这两种分析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当结合起来。拿列宁研读黑格尔哲学初期的失语现象来说,笔者虽然更倾向于认同作者的结论,即列宁还不能进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思想空间,但我们不应掩盖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即此时读到的黑格尔哲学并无太多能与列宁的现实思考相链接的东西,因而自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同样,在分析列宁“伯尔尼笔记”中近百页的空白问题时,作者表现出类似的研究倾向。本书第十章中,作者注意到了一个过去的研究者都未曾注意过的文本细节,即从《黑格尔全集》第5卷的第35页之后,列宁的笔记中出现了篇幅近百页的巨大空白。在列宁没有留下任何阅读摘录的这部分内容中,黑格尔主要讨论的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别;“判断”的实有、否定、无限、反思、必然和概念形式,以及“推论”第一节。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相当异常的无语状态”?笔者注意到,作者通过“对照其后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猜测该时段的“失语”是“列宁边阅读边深陷在逻辑矛盾中痛苦思索和挣扎的过程”。(22)我们不妨暂时悬置对这一猜测的分析,看看作者此处所说的“其后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指的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作者发现,列宁在长段的空白后不仅恢复了摘录,而且把黑格尔关于推理的分析部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章进行了链接:“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第1章中模仿黑格尔”。(23)作者指出,正是这一重要的“思想火花”预示了列宁的“逻辑转向”:“列宁整个读书思路中的第一个巨大思想逻辑异轨就出现了: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极其重要的转变。”(24)如此看来,作者所指认出的这段空白期正是列宁阅读进程中黎明前的最后一道黑暗。
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作者对于列宁阅读进程的思想转变过程的剖析是极具说服力的,并且,如果仅从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前后转变来看,这大段的空白确实是列宁对黑格尔认识过程中的分水岭。(25)然而,如果考虑到列宁的现实处境和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向性,此处颇具说服力的逻辑分析依旧难免引起如下质疑:如同列宁阅读黑格尔之初的失语现象一样,列宁此处的失语或许未尝不是因为,黑格尔在这部分的抽象论述中并没有为列宁提供与其对现实的思考相链接的东西。因为,诚如作者所指认的那样,列宁阅读黑格尔目的是“为我所用”,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列宁此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和俄国国内理论斗争与革命策略斗争的紧迫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显然是不可排除的,即并不想成为黑格尔研究专家的列宁对这一部分几乎激不起列宁的现实思考的抽象论述采取了快速跳阅的策略。或许,这只是笔者的吹毛求疵。然而,在笔者看来,是否将现实层面的考虑列入理论研究的判断依据,也许在最终结论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事实上,对于这前后两处失语现象的分析,笔者仍是倾向于认同作者的分析逻辑和结论),但对于以现实实践为逻辑射线的“思想构境论”来说,来源于现实层面的思考无疑是不可缺席的主导视域。
此外,在拟现列宁研读过程中实现逻辑飞跃的每个细节时,作者的分析模式对于理论逻辑的偏好也是相当明显的。比如,对于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的认识(尤其是列宁对“逻辑的范畴和人的实践”的关系(26)、经过“亿万次的重复”的人的实践与公理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27))、对于“规律”和“本质”都是阶段性的认识的指认(28)以及实践图绘“客观世界图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29))等思想,在作者的“思想构境”中更多的体现为逻辑异轨的关节点,或者是对旧有理解构架的突破,用作者的术语来说,即列宁对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他性镜像”的超越。然而,这种认识飞跃的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列宁所处的革命斗争环境和他个人的现实活动历程这一视角无疑被压抑掉了,成为不在场的幽灵。必须承认,这样的阐述难免给人这样的感觉:似乎作者之前所坚持的“思想构境论”的现实之基已经被抽离了。
三、从后向前看:遗漏的构境视角
在笔者看来,如果坚持“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那么,列宁在哲学研读中实现的认识飞跃在同期以及之后的各种著述中的应用和体现也理应成为“思想构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到列宁》一书中作为主要批判靶子的凯德诺夫,倒是为这一由后向前看的视角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在其《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一书中,凯德诺夫在强调列宁研习黑格尔哲学后所达到的对辩证法的深入理解和阐发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为了展开对这种特殊的阐发形式的分析,凯德诺夫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列宁1915-1924年间的各种政论,从中识别出了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独到运用。(30)在笔者看来,在分析列宁“伯尔尼笔记”时期的认识飞跃和研究心得时,列宁同期以及之后的现实活动(含理论斗争)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在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本书中的两个例子。
在本书第八章中,作者注意到列宁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时,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拉萨尔《所获得的权利的体系》一书的评论表现出强烈的关注。(31)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常常把辩证法变成一种实例的总和,而“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成为辩证法”。(32)列宁对这一观点做出了明显的标识和摘录。列宁重视这一观点的原因在本书作者看来有两点:“一是马克思在讨论辩证法,二是马克思在把黑格尔的东西当作正面的观点来引述。”(33)很明显,该分析的主导视角依然是理论逻辑层面的辨识,而列宁对这一观点的重视是否导源于现实的理论斗争这一视角很遗憾地被压抑了。
同样,当读到黑格尔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的论述时,作者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是列宁的关注点。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机智而且聪明”的辩证法思想,并写下这样的评论:“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34)在此,作者认为这是列宁对自己的“提醒”,并且作者认为,这个自我“提醒”正是列宁初期阅读黑格尔时背负的那种简单的概念颠倒式他性镜像的症状,即“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观念之间辩证法的东西,在列宁这里则成了物质世界的客观辩证法。”(35)
与上述的文本细节相似,作者此处的分析固然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遮蔽了另一重来自现实之维的可能性思考,即列宁与其同时代的俄国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辩证法之争。鉴此,我们不妨暂时绕开这个时段,与列宁后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动的理论斗争进行链接,来透视列宁此期理论关注焦点的现实导因。笔者注意到,凯德诺夫倒是十分重视列宁对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并指出折中主义和诡辩论是列宁理解与运用辩证法的主要批驳对象。(36)具体而言,凯德诺夫注意到,列宁在《五一节和战争》(1915年4月)这一提纲中表述过“辩证法反对折中主义”的观点;(37)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6月)一文中,列宁痛斥了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将辩证法变成“最下贱的诡辩术”的做法,强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考茨基等人的诡辩术之间的根本区别;(38)在《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初)一文中,列宁对辩证法并不是对大量事例总和的归纳这一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发挥;(39)同年,在《国家与革命》(1917)一书中,列宁将折中主义视为辩证法最凶恶也最具欺骗性的敌人;(40)在《再谈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一文中,列宁对辩证法与折中主义的区别展开了具体的阐发,(41)等等。通过对这些政论性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折中主义”(把辩证法等同实例的总和的做法也是折中主义的体现)的理论斗争一直是列宁的工作重点之一。如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列宁此期对辩证法研究的心得与其现实斗争活动的紧密勾连。也因如此,在分析上述两个文本细节时,除了指认出他性理论镜像对列宁的隐性牵制,我们不应忘记其理论研究的现实之“境”。
上述可见,如果坚持“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对列宁伯尔尼时期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发展动态的拟现就不应该淡化了现实之维,尤其考虑到列宁思想研究与其政治活动的密切相关性,这种由后向前看的视角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资料完善,更是“思想构境论”的现实之基的填充。很遗憾的是,这一点在本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体现。或许,这是受制于篇幅;又或者,作者潜在的理论斗争对象(那些无视列宁思想发展和逻辑异轨的动态过程并将其同质化和神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促使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逻辑的深度解剖上?无论如何,这种局限无疑构成了“思想构境论”的一个逻辑裂隙,因为这样的分析理路传导给读者的隐性信号在一定层面上难免被解码为理论逻辑对现实实践的遮蔽。
总体而言,在细致勾勒出列宁哲学思想的步步进展的同时,《回到列宁》的学术努力再次凸显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列宁,现实的实践活动无疑是他的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列宁不是一个在理论王国中欢欣跳跃的纯粹的思想精灵,也不是一个超越了阶级立场的神灵般存在;他在哲学理论领域所取得的突破不仅导源于他所生存的时代境遇以及他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而且他的哲学进展也是以对现实革命策略的思考和制定为服务旨归的。我们拒绝把列宁神化,因为神化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虚化;我们也反对把列宁局限在思想理论的空间中,因为如果将他与其思想赖以生根发芽和突变的现实大地和劳苦大众隔绝,最终只会使他蜕化为杜娜叶夫斯卡娅所指认的那种“游荡在天地之间的无阶级的生灵”(42)。正是出于上述的诸多考虑,笔者认为,揭示列宁思想的步步进展只是展示列宁的思想与其时代的实践活动的辩证互动这一工程的第一步,而彰显列宁思想突进背后的现实思考也正是对列宁“思想构境”应有的题中之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列宁》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探索空间,开拓了一片亟待继续深度耕犁的思想沃土。
注释:
①“伯尔尼笔记”是本书作者对列宁在1914-1915年间写于伯尔尼的哲学笔记文本群的命名,以区别于“哲学笔记”这一传统研究模式中未加区分的各时段文本群的杂合体。“伯尔尼笔记”的核心部分是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读书批注和研究心得。参见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的话”,第3页注释1。
②笔者不久前就《回到列宁》一书的方法论特质写有专文,参见拙文《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远与近》,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③笔者认为,仅就理解列宁思想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张力而言,杜娜叶夫斯卡娅和凯德诺夫代表的是两个极端。前者处处将列宁的哲学研究还原到现实语境中并将列宁塑造成一个被现实运动推动着向前走的不自觉的或被动的思考者,从而淡化了理论研究对现实理解视角的牵引作用;而后者则以理论研究来替代列宁的现实旨趣,将列宁装扮成一个伟大的理论工作者,所有围绕现实策略的斗争及其文论似乎都是列宁辩证法“伟大设想”的阐述方式。参见[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哲学与革命》,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B·M·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周国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⑨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的话”,第16、9页。
⑤⑥⑩(12)(13)(15)(16)(17)(18)(19)(24)(33)(35)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4、78、61、68、68、69、234、208、306、257、281页。
⑦同上,第8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下同。
⑧杜娜叶夫斯卡娅也十分重视列宁的哲学思想与革命活动之间的关联,在她看来,“在列宁的思想中,与俄国民众的密切联系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她的笔下,列宁在思想上的飞跃无一例外都导源于现实中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参见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77页。
(11)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指出,哲学世界观与现实政治立场的分立问题是无意识地存在青年列宁身上的客观事实,这体现在青年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以及波格丹诺夫的矛盾态度上(即肯定前者的哲学立场和后者的政治立场,批判前者的政治立场和后者的哲学倾向)(具体的分析参见本书第103、111、124—125、126-130等页);直到狄慈根有关哲学派别与党性原则问题的论述时,列宁才大受启发,才意识到之前将哲学学理与政治立场分隔开来的错误(具体的分析可参见本书第166-167页);在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之后,列宁的政治立场与哲学立场已不再分立,转而强调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
(14)参见张一兵《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关于后者,黄楠森和曾盛林两位先生合著的《列宁传》展开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参见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418页。此外,杜娜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也对列宁研读黑格尔的现实动因展开了翔实的分析论证,除了上述的两个方面原因之外,杜娜还注意到了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作《论马克思》一文与他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参阅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7页。
(20)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认为列宁“几乎完全忽略存在的一册”,参见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8页。
(21)(22)(31)参见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4、305、257—258页。
(23)《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25)较之于先前零星式的“思想火花”,作者在接下来的分析显示,列宁在空白期后的大段而集中的批注展露出其阅读思路的“重大的逻辑异轨”和新的读书逻辑的凸显。参见本书第306-309页;此外,阿尔都塞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8页;[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26)(27)(28)(29)(34)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86;127、152;182;91页。
(30)凯德诺夫注意到了,列宁研读黑格尔哲学的心得都具体地体现在他的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著作中(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国家与革命》(1917年)开始,直至后期的一些著作)。就此,凯德诺夫倒是不吝笔墨,专门以一章的篇幅加以详细的论述,此即《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第十一章:“列宁的设想体现于生活的特殊性质”。参见B·M·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周国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413页。
(32)转引自《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同时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6页。
(36)凯德诺夫关于列宁反对折中主义和诡辩的思想及其在列宁各时期著作中的体现的具体分析,参见B·M·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周国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398页。
(37)(38)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235—249页。
(39)参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370页。
(40)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41)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98页。
(42)杜娜叶夫斯卡娅曾经不无动情地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精神和实践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他们都“不是游荡在天地之间的无阶级的生灵。他们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当他们失去了与群众的紧密联系时,他们就会开始代表另一个基本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参见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标签: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列宁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