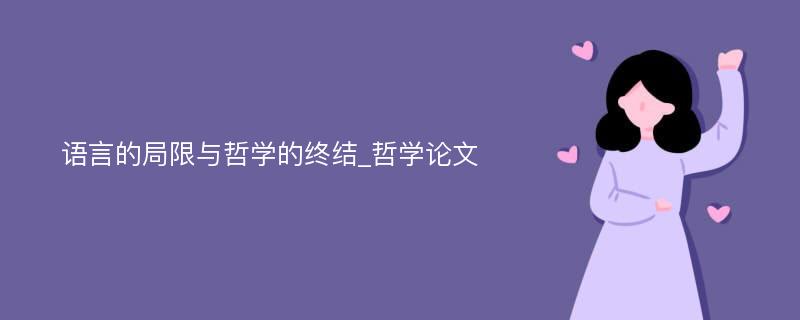
语言的限度与哲学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哲学巨擘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谈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鼓噪,“哲学的终结”已成为20世纪的时代话语。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境遇中,哲学的地位问题在中国更是日见突出,“哲学边缘化”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本文无意剖析哲学的终结问题在中国的某些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根源,而是着力于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维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对这个问题做一学理上的明辩,以期有助于弄明哲学的未来走势。
一
哲学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换其思考的侧重点,与科学相对而言,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向科学割让地盘,每当哲学作出这种变换或割让时,哲学的地位问题便凸显出来,因此哲学的终结问题实际上是哲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经常性问题。从大的跨度来看,当古希腊罗马哲学将目光专注于本体世界,却又最终感到对“始基”、“本原”的追问无法渗透世界、渗透人生之时,以本体论为特征的古代哲学面临终结,以认识论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则代之而起。近代哲学经过笛卡尔等人的开创和努力,到黑格尔建立起绝对理念的逻辑体系,哲学的终结问题再次提出也就具有了必然性,因为黑格尔视自己的体系为大全,黑格尔所建构的终极体系必然导致哲学的终结。而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实质上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宣告了旧哲学的终结。
20世纪哲学的终结问题特别地突出出来则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有人将20世纪定位为“分析的时代”,有人称20世纪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英美分析哲学家或一些偏好语言哲学的人的一厢情愿的意见,但也确实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状况。总体来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是以反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为背景的,特别突出语言的地位的语言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哲学发展中以认识论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即近代哲学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突出的是人作为理性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改造,在这种主客对立二分的认知模式中,主体和客体、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之中,经验论、独断论都源自这种紧张关系。康德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予以克服,但最终在现象与物自体的分界中保留了这种对立。黑格尔试图在其绝对理念体系中建立起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人作为理性主体的极度膨胀为基点的,是建立在绝对抽象的思维基础之上的。因而近代哲学面临着两大突出的问题:一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地位得到高扬却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二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如何弥合。语言哲学认为近代哲学的问题源于其形而上学性质,围绕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进行的不同哲学体系间的无结果的争论应当休止,因为它们是形而上学问题,它们不能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哲学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语言问题,如罗素认为哲学的任务主要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在语言哲学看来,传统哲学问题起源于对语言的误用,研究语言、通过正确的分析恢复语言的本来面目是消除哲学混乱的最有效方法。
语言哲学如此抬升语言的地位,如此看重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必然导致哲学的终结的结论,这一必然性通过语言哲学的突出代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而彰显出来。早期维特根斯坦在指出“哲学的正当方法固应如此:除可说者外,即除自然科学的命题外——亦即除与哲学无关的东西外——不说什么”〔2〕之后宣称:“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最后地解决了。”〔3〕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指出:“哲学只是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由于一切显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4〕进而认为“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5〕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分别表征着语言哲学的两大学派: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早期维特根斯坦在语言与世界间建立起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认为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世界才是可说的世界,而语言和世界的逻辑形式以及传统哲学中的哲学本质、伦理学领域、生命的意义等则是不可说的,以往的哲学问题正是企图超越语言的界限、述说不可说的东西的结果,哲学的任务和意义正是要勾画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这一任务一旦完成,哲学也就可以“登楼拆梯”,寿终正寝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间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是对语言的逻辑的误解,仍然是对语言的一种形而上学用法,因而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要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6〕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治疗哲学的“语言病”, 其处方是对语言只做描述,而不是将日常语言还原为简明的逻辑规则,哲学的作用只表现为我们从事语言游戏的提醒物,当哲学治好了语言病时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因此,无论是逻辑语言学派还是日常语言学派,从其将语言视为哲学的基点出发都将最终导出哲学的终结的结论。
二
在20世纪哲学的终结问题上发生过关键性影响的另一位人物是海德格尔,1966年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追问:“从何种意义上说,哲学在现时代进入其终结了?”“哲学终结之际为思留下了什么任务?”〔7〕明确提出哲学的终结问题, 这是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语言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背景,二者都是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传统的一种反动,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将对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引入了对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的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哲学从一开始就以因果说明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8〕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特性。 海德格尔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特性的揭示实际上表明,一方面哲学遗忘了“存在论差异”,只从存在者出发而遗忘了存在,另一方面哲学以追寻存在者的根据取代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根据对哲学来说具有建基特性。因此,哲学在现时代已经走向终结。但终结不是终止,海德格尔谈哲学的终结是指形而上学的完成,这就是说,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性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形而上学已经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终结问题的看法显然与语言哲学家的看法不同,海德格尔何以做出这种思考呢?哲学的发展进程是与科学从哲学中不断分离、独立的过程相对应的,从哲学不断向科学割让地盘这一事实中,海德格尔观察到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即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海德格尔的思路是:哲学解体、诸科学独立——诸科学为控制论所操纵——技术铸造和操纵着世界和人、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哲学消解于被技术化的诸科学”,“哲学之终结显示为对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哲学之终结就是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的开端。”〔9〕
基于这种认识,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必定持批判态度,语言哲学必定被划入走向终结的哲学之列。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注意到“哲学研究将不得不放弃‘语言哲学’”,〔10〕当海德格尔最终将整个哲学都视为形而上学时,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在他看来是在追求一种元语言,而“元语言学就是要将所有语言彻底技术化为仅仅是星际信息操作工具的那种形而上学”。〔11〕相应地,在形而上学走向完成之际,“控制论把语言转换为一种信息交换”,〔12〕语言也正是在现代技术的本质即框架(Gestell)中被形式化, 语言从而与表象——计算性思维相合拍。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在现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几乎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因素了。语言还对我们隐蔽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的家。语言倒听任自己屈从于我们的愿望和驱策,作为支配存在者的工具供我们使用。”〔13〕当哲学操持着这种语言时,当对语言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逻辑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论争的圈子之中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仍然局限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哲学也因而走向终结,让位于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科学的思。
三
语言问题与哲学的终结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之所以交织在一起,这无论是在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美语言哲学那里,还是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哲学那里,都是与对语言与存在或世界的关系的理解相关的。
从基本倾向上看,语言哲学试图建立起语言与世界间的同构关系,在此前提下,一部分语言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采取根本否定态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排除过程中,语言哲学逐步走向以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澄清语言使用中的混乱为哲学的目的,以对语言形式和语言用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为哲学的方法,哲学实质上被降低到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哲学研究沦为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研究,语言哲学因而走入死胡同。这是语言哲学无视语言的限度、无限抬升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的必然结果。与其他语言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划界,为形而上学保留了地盘,认识到无论是逻辑语言还是日常语言都是有限度的,在此基础上,后期维特根斯坦试图通过对语言游戏的描绘而非解释来显示不可说的东西,并与为语言哲学所忽视的人文世界相关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为语言哲学走出死胡同提供了契机,但从根本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并没有超出语言哲学的范围,其与人文世界的关涉对于克服语言哲学的根本局限的意义也是有限的。
以上分析表明语言哲学阻塞了哲学发展之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使语言哲学远离人文世界,对日常语言的重视也并不意味着语言哲学对日常生活的回归,正如巴雷特所说,“语义哲学对语言的解释不管可能多么有用,却是注定一开始就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没有把握住语言在人类存在中的根。”〔14〕这就提出了哲学中的所谓语言转向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语言哲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却又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形而上学。施太格缪勒在谈到维特根斯坦时指出:“他把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从理性的平面转移到语言的平面。”〔15〕这一看法可以引伸到对整个语言哲学的评价,也就是说,语言哲学实质上继承了认识论传统,只是以语言取代了认识论传统中的理性思维,并在语言基础上重建了形而上学。因此,语言哲学是不能代表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的,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实质上说明当哲学囿于语言之中时必然导致自身的终结。
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的态度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哲学(包括语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走向完成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宣告了哲学的终结,但海德格尔并未否定语言问题的意义,而是对语言作出了非形而上学的思考。关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莫过于海德格尔1946年在《诗人何为》中首次提出,通过《论人本主义的信》而广为流传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对这一提法人们较多地注意到:海德格尔反对把语言认作形声于外的表达,反对把语言定义为交流信息促进理解的工具;语言自己言说,人的语言是对语言言说的聆听和应和;语言是存在的真理的发生,存在只有在语言的言说中才能显现。这些理解是准确的,但由此出发,有人将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归结为一种语言存在论,甚至有人认为海德格尔与语言哲学得出了相同结论,语言问题就是哲学问题本身,这就值得商榷了。实际上,从“语言是存在的家”中并不能推导出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对等关系,应注意到这一提法还包含着对语言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语言是有限度的,“语言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16〕同时,对这一提法应放在整个海德格尔的思想过程中去考察,我认为,与早期对此在的探讨一样,晚期海德格尔对语言的理解仍然是在寻求一条通达存在之途,所不同的是早期海德格尔试图以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为中介,晚期海德格尔则试图以其本身不是存在者的语言为中介,二者都只不过是海德格尔思想之途中的一些探索或路标,其合理程度有多大,依然是有待深究的。当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别》中称“语言曾一度被命名为存在的家”时,〔17〕当海德格尔在《来自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中称自己曾“非常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的家”,并担心欧洲人与亚洲人可能因此住在不同的家里,“两家的对话几乎不可能”时,〔18〕都反映出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复推敲。
海德格尔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中一条不同于语言哲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终结问题以及语言问题的理解对欧陆哲学乃至语言哲学的发展都发生过深刻影响,如伽达默尔在语言引导下所完成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后现代主义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解构及其对哲学的消解等等都是对海德格尔的观点的承袭和夸张。海德格尔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语言应从逻辑和语法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当哲学局限在逻辑语言中并以之为目的和方法时,哲学便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哲学必然走向终结;语言与存在、世界具有亲密的关系,非工具性的、非对象性的、非存在者意义上的语言是通过存在的媒介,存在在语言中显现,但语言并不就是存在本身,语言并不能概括全部存在的性质,语言是有限度的;哲学的终结是指作为形而上学的、操持着形而上学语言的哲学的终结,思仍然是一种哲学之思,只不过作为思的哲学具有了超越形而上学语言的性质;正是在对语言和哲学的这种理解中,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哲学之间出现了对话的可能;中国哲学对语言与哲学有自身独特的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大可不必跟在西方哲学后面亦步亦趋,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并不代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但如何在弘扬自身深厚的人文传统基础上将西方哲学引入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也将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9页。
〔2〕〔3〕维特根斯坦:《名理论(逻辑哲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8页。
〔4〕〔5〕〔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70、71、67页。
〔7〕〔8〕〔9〕〔12〕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见《海德格尔基本著作选》, 纽约1977年英文版,第373、374、377、376页。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 页。
〔11〕〔18〕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纽约1971年英文版,第58、5页。
〔13〕〔16〕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学说。附论人本主义的信》,伯尔尼1947年德文版,第60、70页。
〔14〕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36页。
〔15〕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5页。
〔17〕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别》,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30页。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