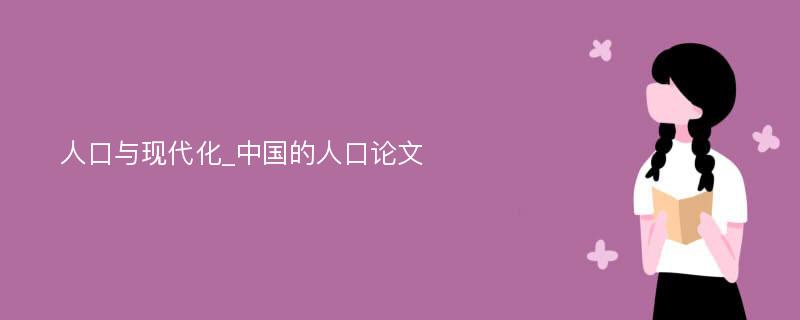
人口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 C
关于当前人类潜在的总灾难,西方学者有人认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由于人口的增殖超过了食物和其他资源增长的极限,导致人类文明的末日,结果可能爆发一场霍布斯式的人对人的战争,或爆发一场善与恶的大决战。这是罗马俱乐部预言的模式。其二是采取核屠杀式的大灾难,这同样导致人类文明的末日。
虽然无法实验,也不应该实验这种预言的准确性,但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虑和警惕。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平衡,虽有一定的弹性幅度,但一过其极点线,危机必然出现。在清初之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就是通过其自我控制的平衡机制来制约人自身的生产的。中国汉代在册的人口约6千万,到经一千多年以后的明代初年,依然是约六千万。 明万历中期(1600年)增殖至1亿5千万,到清初(17世纪40年代)又降至1亿2千万。其自我控制的手段是溺婴、饥荒、传染病和战争。康熙末年(17世纪末),人口恢复至明代万历中期的水平后,出现了空前的人口高峰期。在经济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作出了放弃提高生活质量的选择,使人口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加速繁殖。乾隆18年(1753年),在册人口数1亿8千3百万(实际数当在2亿之谱)。道光13年(1833年)已达约4亿,在80年间增加了一倍。宣统年间(1909—1911 年)调查之人口修正数为3亿6千8百万。1949年,增至5亿4千万。 以广东而言,清初在册人丁1百万(折口约5百万),乾隆末年人口剧增至约1617万,道光19年(1839年)激增至2464万人,宣统年间(1909—1911年)续增至2801万人。1949年增至3000万。在清代的277年历史中, 从500 万增至2801万,增加了四倍多。较之于全国显得更快。人口如此连续激增,是史无前例的。
在欧洲,1750年至1850年(即乾隆15年至道光30年),其人口也得到迅速的增长,人口从约1亿2千万,增至2亿1千万(一说2亿5千万,分见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与刘洪康《人口手册》)。一百年间增加了一倍,也是欧洲的人口高峰期。中国和欧洲几乎同一时期出现了人口高峰,但其原因与结果各异。
欧洲人口高峰的出现,是由于18、19世纪以蒸气机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的高速增长防止了饥饿,以及对环境控制力的增强,有效地防止了传染病的流播。由于死亡率下降,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节制生育的文化观念一时还来不及相应建立,所以人口以超常的速度增长。但是,早在17世纪,已经萌发“欧洲式的婚姻”,即平均结婚年龄提高。16世纪时,平均结婚的年龄是22岁,18—19世纪已提高到25岁。有人称结婚年龄的提高是“古典欧洲真正避孕工具”。再是各个年龄组中婚姻次数的减少。这为人口的控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文化素质的变化,重视人口质量,自觉节制生育。因此,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阶段,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已经出现的人口过剩所作的反映是以和平的方式移民,或利用其先进技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军事力量开拓殖民地。自1846年至1930年间先后有约5000万人移居海外,遍及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尤以北美为主要。由此可见,欧洲工业经济引起的人口高峰,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凭借其先进技术造成的军事优势向外扩张,对世界各地进行殖民主义掠夺。
中国清代人口高峰的出现,其原因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级差,导致人口自我平衡机制的失灵。清代处于“近代前”的经济增长期。边陲地区的开发,高产作物蕃薯、玉米的引进,中国几乎吃用植物粮食的习惯,等等,都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社会安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所谓“康乾盛世”比历代时间都长。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时间达134年(其中康熙61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 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他们又都尽心尽责,精明能干,多有进取。从遗下卷帙浩翰的朱批谕旨,可见其履行职责之认真。政治的相对开明,社会稳定,有利于人口的滋生。对于人口的迅速增殖,康熙已经觉察,并深感忧虑。他严励批评那些只言“垦田积谷”,不顾“食众田寡”、人口猛增的官员,斥之为“不识时务”。他曾下诏要求摸清人口底细,但所报的人口数与实际相去甚远。他认为之所以隐瞒不报,是怕加征钱粮。因此他又下诏规定自康熙51年(1712)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举没有促使摸清人口的底细,反而使老百姓毫无顾忌地多生孩子,既违其初衷,也是他所料不及的。雍正继而实施“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政策,历史上首次取消了人口税。其结果是康、乾二帝实行的人口、赋役改革措施成为人口膨胀的催化剂。又由于“近代前”的经济增长,没有向“近代性”的经济成长过渡,因而没有引起文化观念的变化,也自然没有如同“欧洲式的婚姻”制度出现,更没有注重生育质量,自动节制生育的观念。尽管早在明末,冯梦龙(1574—1646)已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节育的主张(见《太平广记·古元之》),尔后的洪吉亮(1746—1809)、汪士铎(1802—1889)、薛福成(1838—1894)等先哲也都曾指出人口迅速增长的事实,并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些主张,但皆属空谷足音,得不到关注和警惕。相反由于受耕作制度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刺激而引发的“无后为大”的家庭繁衍观念益加强烈。总之,清代人口空间的膨胀,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文化观念的演变,以及当时的政治体制、对生态环境控制的加强等等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中国清代人口膨胀带来的后果是,使本已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趋向高劳力密度化。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桑基鱼塘”生态型农业,更是把这种传统农业推到了极致阶段。为了糊口活命,只要能增加收益,就不惜追加劳动力,哪怕边际效益降到最低限度。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劳动力年均产量,在战国中晚期为3318斤,在唐代4524 斤, 在明代4027斤,在清代2262斤,在1949年1150斤。可见亩产量增加了,一劳力年均产量却下降了。又一结果是使农业和商品性手工业、副业相结合的家庭多种经营型式日益普及。这一家庭多种经营形式,又可使各具技能的劳力和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老、弱、病、残,都可派上用场。看来人无闲手,人人有业可就。但是靠不断追加劳力来取得增加经济效益,掩盖了实际上的失业者。人口膨胀使包容所有剩余劳力的传统农业和多种经营的家庭经济结构益加完善和巩固,而后者又刺激了人口的持续膨胀,形成恶性循环。
人口膨胀的压力下,移民成为人口的“渲泄阀”。类似而又早于近代欧洲的移民热潮因之而出现。在明代还是小批量地移往东南亚,入清之后则是络绎不断,数量益多。自19世纪40年代起,更是流播海外各大洲。单珠江三角洲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出洋的华工便达三、四百万之谱。在国内,康、乾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使因明末战乱而“十室九空”的四川到道光时已“人满为患”;东北、台湾等边陲地区也有大量移民前往谋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流徙城市的人群因无业可就,沉淀形成了一个由流氓、乞丐、小偷、赌徒、娼妓、迷信职业者和杀人越货者等组成的次生社会群。帮会团体也因之兴起。它成为社会动荡不安之源。晚清出现的连绵不断的宗族械斗、土客械斗,究其实质,也同地少人多,为争取生存空间有关。人口膨胀实际上也是酝酿大小农民起义的潜在原因。
欧洲的工业经济引起的人口高峰,导致向外进行殖民主义掠夺;中国因处于“近代前”的经济增长期而诱发的人口膨胀,却使中国积贫积弱终于19世纪40年代以后任各国列强宰割,受尽凌辱。
人口问题作为社会系统演化机制之一,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起着潜在的、长时段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兴衰陵替的命运。对此,多年来当道者却蒙然不察。对于有识之士就人口问题提出的合理建言,不仅不欣然采纳,反而加诸莫须有的罪名大张笔伐。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依然处于“近代前”的增长期。尽管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但包容剩余劳动力的高集约化的耕作制度和农、林、牧、渔、副相结合的多种经营型式不变。如果有所不同的话,是从原来的以家庭为单位改为以生产队或大队为单位进行经营管理,尤其是“学大寨运动”所投入的劳力,其边际效益更是绝对等于零。家庭劳动人手多、挣工分多、领口粮亦多的分配制度,显然对人口的增殖起到刺激作用。在充满革命口号,提倡艰苦奋斗的年代,也不可能萌发少生孩子,提高生活质量的观念。因此,人口膨胀愈演愈烈,乃至于到现在人口膨胀的程度依然高踞不下。
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展示了一幅如梦如幻的前景。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必由之路。但是现代化道路不可割断历史联系和社会传统。前面对人口史的回顾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现代是海市蜃楼,还是梦想成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置人口这一历史积淀的成果。
现代化,不单纯是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包括政治清明、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等在内的全面的社会进步,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其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向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转变。
世界历史显示,人口从高自然生长率到低自然生长率的转变,是进入现代化的前题。欧洲是在工业革命中完成这一转变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完成其人口的转变。中国人口持续膨胀的现状,已经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一人饭三人吃,既缺乏积累扩大再生产,又无法追加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即使完成人口转变之后,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新增的人口绝对数,也远超过其他国家。加之人均占有的资源低,教育水平差,使我们面对的人口现实越发严峻。
人口对本国资源占有偏低的国家如日本,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她是以输出资本和技术去换取别国资源来使自己富裕起来。可见人口众多、资源占有偏低的国家并非就与现代化无缘。日本人的成功靠的是科学技术和商业的智慧,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素质问题。
同时,就目前而论,资源开拓的天地还是宽广的。海上和山区资源距真正的开采和利用还远。但是,开拓新的资源同样需要人的素质的提高。
中国既面临人口的转变,也面临人口素质的提高。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事实上,文化水平比较高、生活比较富裕者基本上能够自觉执行计划生育的。而经济落后的农村,愈是缺乏文化、愈是生活困难者,愈是超计划生育。其人口素质的提高也便越发艰难。目前的人口状况出现潜在的危机:素质高者,人口生育率已经下降;素质相对低者,人口依然超计划生育。就全国人口总体素质而论,难免出现下降之趋势。
出路何在?以增加教育科技的投资,健全教育制度,发展科学技术,和严格执行生育计划相结合,亦即提高人的素质和降低生育率相结合,似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不二法门。这一点也似乎为人们所共识。但实际行动却背道而驰,从对科技教育投资占总收入比例列在世界各国倒数第二即可说明。
更为艰巨的任务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转变。在欧洲,从15世纪起,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历时数百年才孕育出科学、理性、人文主义和民主精神,逐渐建立起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这些精神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并非是西方人的专利。唯有从心理、思想、行为方式等方面,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现代人价值的精神文明,才能实现人口的转变,也才能提高人口的质量。
没有相应人口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势必难以持续,更遑论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了。经济学大师如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Schultz )便主张经济发展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源”的培养,亦即注重教育。社会上“科教兴国”的呼声盈耳,显然源自于这一认识。为一扫“重农轻商”的文化积淀,在一个时期内高扬商品意识,崇尚商业风气是正确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更切中启綮。从物质上、精神上制造一个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是绝对必要的。
人口问题,由于人们的惊觉,西方学者所预言的潜在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正如一句常用话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我们能否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在21世纪充当地球村合格的居民,善处人口问题当是最具深远意义的关键。
(1997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人口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