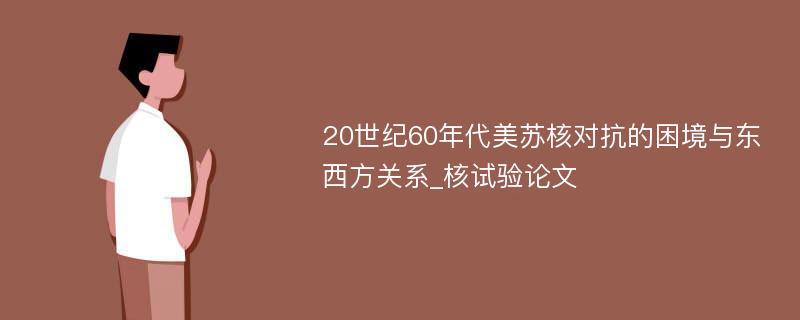
美苏核对抗困境与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困境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5-0043-09
国际关系行为体(特指主权国家)的同时并存,只要不存在具有更高权威的一方把自己的行为规范强加于对方,行为体双方就能维持一种相对的战略平衡。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大部分时间维持着这一战略平衡。但美苏双方都想打破平衡,使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困境模式,它体现两国对外战略的两难选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赫兹(John H.Herz)认为,由于美苏对核威慑的相互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迫使“(双方)竞相增强自己的强权以取得更大的安全”,②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重大危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使代表东西方两大集团利益的美国和苏联处在一种相似“旋转滑梯”(roller coaster)式的关系模式中。③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约翰·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击败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肯尼迪政治上十分精明,入主白宫后,没有立即改变共和党前任总统对共产主义和冷战问题的立场,④但作为在冷战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总统,肯尼迪充分意识到,为了在东西方关系中采取主动,美国对外政策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强调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方面要同前任有所区别。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十分重视战略武器的发展,以消除美苏之间可能存在的“导弹差距”(Missile Gap)⑤另一方面表示要放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两极观念,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对来自苏联的战略攻势采取“灵活反应” (Flexible Response)战略。为核威慑时代美苏对抗与对话关系奠定战略基础。冷战时期美苏核战略对抗的困境始终存在,但双方又都在寻求避免核战争的途径。双方缺少的是对共同努力避免战争的相互理解。随着东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加深、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以及美苏之间日益发展的科技文化交流,促使核对抗时代美苏关系从困境逐渐走向缓和。
一、核对抗困境中的美苏对话
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战略核对抗处于两难的困境时期,美苏两国均拥有大量毁灭性武器,核对抗直接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的“大规模核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遭到美国国内多数人包括新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对,人们普遍质疑这一战略的“可信性”(credibility)。⑥
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要“不惜一切努力,确保(人类)生存与自由愿望的实现。⑦作为试探,赫鲁晓夫以私人名义电贺他当选总统,并借机提出愿意同美国“重新开始和平共处”。⑧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是笃信“个人意志将会影响世界进程”的巨人,维也纳首脑会晤为他们提供了施展个人魅力的平台,但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对峙的冷战环境,使得对话成为两位巨人之间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场所,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防止核扩散问题、柏林问题。
在军控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美苏双方都意识到核武器这个所谓的“万灵药方”是不能为未来提供所需要的战略基础的,但在没有找到一个具有生命力和有希望的战略付诸实施之前,这笔为了维持核姿态而花费巨大、非生产性的开支将无法取消。赫鲁晓夫提出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备忘录,要求对核试验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监督机构应由中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三方代表组成,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主持,坚持禁止核试验应与全面裁军相联系。遭到美国的反对,肯尼迪拒绝把核试验与全面彻底裁军相联系,认为,美苏应先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以防止出现更多的核国家。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维也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相反,美苏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1961年8月23日,苏联进行一次当量达5000万吨的核试验(赫鲁晓夫称有1亿吨),⑨是美国最大当量氢弹实验的5倍。白宫立即谴责苏联在进行核讹诈,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健康,两周后,肯尼迪宣布恢复核试验,使美苏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陷入困境。⑩
核危机伴随德国问题的出现,而德国问题又以柏林问题为突出。关于柏林前途问题,美苏两大集团从1958年开始进行长达四年多的政治较量,这个长时间、时断时续的尖锐危机与美苏两国对于“核危险这一政治的理解与误解的方式密切相关”。(11)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一直视苏联是西德的最大威胁者。肯尼迪强调:柏林“前哨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这一威胁是世界性的”。(12)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态度异常强硬,维也纳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美国在6个月内答复缔结对德和约,以法律形式确立“欧洲战后形成的局面”,让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赫鲁晓夫想单独对德签订和约,迫使美英法三国军队离开西柏林。(13)美国视西柏林为北约安全之关键利益,宣布采取新的防御措施,并且重申“即使面对武力威胁,美国也要保卫其在西柏林的权力和义务”。柏林问题的激烈对抗使美苏核竞赛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大气层和地下进行一系列核试验。(14)但维也纳会谈毕竟使美苏双方能坐到一起讨论问题,承认在许多问题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对于处于核对抗困境中的美苏关系缓和是“有益的”、“值得的”。
二、处于对抗困境中的美国与苏联
柏林危机的出现是冷战环境下美苏战略对抗的产物,也是东西方实力较量的体现。维也纳会谈后,苏联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向西方施加压力。赫鲁晓夫重申“必须在今年”解决问题,否则苏联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缔结和约并解决柏林问题,他警告西方不要以武力威胁,否则将会导致核对抗升级。1960年苏联宣布停止裁减武装部队计划,并增加31亿卢布的国防预算,柏林局势日趋紧张。(15)多年来,西方利用东西柏林间开放的边界对东德实行“放血”政策,包括吸引大批东德居民西逃和西德人进入东柏林抢购东德低价商品,使东德经济上遭受损失。仅1961年7月西逃人数就达3万人。(16)为了采取措施阻止事态发展,华沙条约成员国单独签订对德和约,民主德国部队封锁西柏林四周的全部边界,并沿边界拉起170公里的铁丝网,筑起高3.6米的“柏林墙”。8月13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声明支持这一措施,宣布这是华约国家“建议”民主德国政府采取的,以向对方显示意志和决心。
肯尼迪将华约国家的行动看作是对美国勇气和意志的检验,尤其是“猪湾事件”使美国核大国形象受损之后。美国强硬地提出所谓柏林问题“三要素”:即:西柏林的“自由”及“生存能力”、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进入西柏林的交通畅通不受干涉。坚持要求东德举行“自由选举”,以实现统一。(17)在与盟国协调后,美国与英法一道断然拒绝苏联的要求,严厉警告苏联方针的“巨大危险”,要求苏联不要轻举妄动,强调只有“在和平与自由中,在普遍承认的自决原则基础上”重新统一,才能解决德国问题和实现中欧的安宁。(18)美国国会批准肯尼迪政府32亿美元追加军事拨款议案,增加三军兵员,征后备队入伍,利用拨款大搞国内“民防”建设。(19)同时,美国还要求西欧盟国加强军事准备,增加驻欧军队。美苏对抗达到高峰。双方都发出大量的言辞强硬激烈的讲话、声明、照会、抗议和反抗议、威吓和反威吓、谴责和反谴责,试图在话语上占据上风,以摆脱战略困境。美苏还做出一系列表明坚定态度的姿态,用以平衡各自的心理。美国视柏林为“自由世界的橱窗”,是考验西方国家‘意志’和‘实力’的最重要场所”。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是卡在喉咙里的一个“毒瘤”,决定对其进行“外科手术”,“消除柏林被占领状态”。(20)
与此同时,华约方面举行模拟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演习,第一次召开华约国家国防部长会议;在东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此表示保卫柏林的决心。北约方面重申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不容侵犯;美国海军陆战队1500人奉命乘装甲车沿赫姆施塔特—柏林高速公路支援西柏林以显示美国的决心,并检验苏联是否会干涉西柏林的通道自由,英法等国增加驻欧洲的军队,在中欧和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甚至把演习范围扩大到西柏林大街上,北约部队有意在柏林各区间进出,以示有自由通行之权。美苏双方不时在东西柏林边界过境点上发生阻拦车辆、扣留人员等纠纷,美苏双方的坦克对峙,更加剧了这一紧张气氛。
今天,人们不难看出,当时苏联一心想整合西方力保的西柏林这块政治、军事上的“飞地”。柏林危机的“客观因素”就是西方在铁幕以东拥有西柏林这样一块“飞地”。在这种奇特的环境下,东西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美苏坦克对峙表明“双方不同见解和信念的‘主观因素’”。(21)但西方国家没有采取行动摧毁柏林墙;苏联也没有试图阻止过西方为维持西柏林生存所做的供应工作,没有单独签署对德和约,核威势战略制约着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危机期间美苏双方都在寻求外交途径以缓解紧张关系,双方都采取克制态度。美国不愿为统一德国冒核战争的风险,苏联也无力按自己的愿望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对抗的双方只好承认现实。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美苏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考验对方的忍耐力,形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处理危机的“游戏规则”,即多给对方一点回旋余地。
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代,基本的核威慑,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任何核对抗力量对比的计算。对于处于相对核劣势一方的苏联来说,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是对欧亚大陆边缘的美国实力地位安置一个杠杆。1962年7月26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关于“侵犯古巴任何新的尝试都不会得逞”的演讲,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怀疑。肯尼迪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关注。同年8月底,美国U-2侦察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开始安装防空导弹的照片,照片清晰地展示苏联人建筑导弹发射台的情况,这一情报立即引起肯尼迪政府的强烈反应。面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美国意识到“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虽然扭转不了美苏战略力量对比美国占优势的地位,但苏联利用在古巴的地缘优势,可以“打击他们本来无法打击的更多目标,将会明显减弱美国现有的战略核优势”。(22)美国迅速对这一事件进行战略评估,国务院、国防部作出应对危机的几种选择:政治外交途径(Political-Diplomatic Considerations);实施军事打击 (Military Options Considered);采取封锁“隔离”(The Blockade Decision);对古巴进行封锁“隔离”在肯尼迪与他的高级将领们中达成共识。(23)
肯尼迪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对“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将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军事装备在海上进行严格检查”、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24)危机期间,数百艘美国军舰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巡逻,载有核弹头的B-52轰炸机飞越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海、陆、空三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一切可能爆发的战争危机笼罩美国和全世界。美国紧张地等待苏联的反应,同时积极寻求北约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北约组织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加拿大担心美国的封锁会影响其与古巴的海上贸易,而英国则对美国不同其磋商表示遗憾,称封锁是“法律上有问题”的措施,麦克米伦政府希望“能够进行范围更广泛的谈判”。西方军事集团内部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在取消隔离前苏联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一切进攻性导弹。(25)面对美国强大的压力,苏联终于妥协,尽管赫鲁晓夫宣称:“从古巴撤走导弹,是为了让世界避免一场可能的核灾难”。(26)苏联人首先在核赌注面前退却。苏联从古巴撤走全部导弹,美国则向苏联作出不入侵古巴和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的承诺,美苏核对抗以苏联妥协而收场。(27)
从理论上讲,核对抗困境下的生存是国家利益所在,而核对抗双方的生存都抓在对方手里,因此任何一方也没有把握确保生存,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两国都认识到全面核战争对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两国的根本利益要求避免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的消除就是建立在对核战争认识的基础上的。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避免两国爆发核战争成为美苏心照不宣、严格遵守的原则,这是两个核大国共同的利益资产。实际上,美苏两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28)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双方都面临两难选择,他们所赖以取胜的核威胁,也正是他们自己必须摆脱的安全困境。
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双方都深刻地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绝对的重中之重。它是催生核禁试协议产生的因素之一。美苏双方都清楚认识到,接受敌对政府的存在是明智的。随着危机的解决,美苏之间于1962年12月开始确立在两国首都建热线联系。(29)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不断交换信件,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步伐,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时称:“立即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刻到了”。(30)作为回应,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如果其他国家(指苏联)不恢复核试验,美国将不在大气层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也不会首先恢复核试验”。(31)肯尼迪的演说受到苏联欢迎。不久美、苏、英在莫斯科恢复谈判,1963年8月5日,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即《部分核禁试条约》。这个条约对于减少人类环境的核污染,缓和美、苏对抗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条约存在严重的不足,因为它并没有真正限制美苏核军备竞赛,因为条约不禁止地下核试验。实际上,在条约签订后的五年里,核试验的次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和其它运载工具更是得到大规模发展。
三、促使美苏走出对抗困境的内在动因
古巴导弹危机是检验美苏核对抗关系的重要标志。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认识到避免核战争和任何可能导致核战争的风险和代价;认识到双方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军备竞赛,数量上的多多益善、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最后达成战略均势和僵持的高昂成本,事实上,这样“加强”的威慑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战略或政治收益。
在美国和前苏联档案不断解密的今天,人们对冷战期间苏联对美战略的真正意图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在那种令人“兴奋”的世界革命年代里,赫鲁晓夫的确相信世界正处在“进步”的革命过程中。但是他们并不主张直接向美国及其总统挑战。赫鲁晓夫惯用的手法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多半与其话语内容相反,赫鲁晓夫为肯尼迪不能理解其话语含义深感失望。这个信息就是“必须防止大国卷入战争,不仅要防止核战争,也要防止大国卷入的局部和有限的常规战争。(32)在核威慑问题上,肯尼迪与赫鲁晓夫有着心照不宣的同感,那就是:“防止战争是美苏双方的共同利益”;“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是面临最大毁灭危险的国家”;“是对抗中承受着最沉重负担国家”。肯尼迪甚至提出,美苏可以在不放松警惕的同时寻求减缓紧张的局势。(33)在美苏核竞赛中,美国军方多次强调:“有限的、独立行动的核作战能力是危险的、费钱的、易于变得过时,而且缺乏威慑的可信度”。(34)可见,核竞赛对美苏双方都意味着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政治赌注。认真研究冷战期间美苏领导人话语的隐含内容,不难看出构建冷战期间核大国对话关系的理论基础早已形成。
战后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些国家不甘心完全听命于美国,逐渐成为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西方“盟国之间因各自力量对比的消长而产生离心倾向。盟友们不再表现为小心翼翼和为自身发展寻找理由,而是在证明按照本国模式发展的合法性和价值”。(35)西欧、日本要求摆脱美国经济军事控制、与美国共享战略资源的诉求时有发生。他们还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的石油,金属等场所。以西德、法国为轴心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在经济上向美国挑战,而且政治上也与美国相抗衡。欧共体市场将美国许多货物排斥在外。
戴高乐首先向“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提出挑战。以“缓和、谅解、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法国东方政策,试图向世界表明“欧洲是欧洲人”的政治诉求,目的在于摆脱美苏对欧洲的控制,为推动欧洲和平运动。法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与美国大相径庭,法国试图建立一个由其领导的西欧联盟,反对美国干预欧洲事务,尤其反对美国插手欧洲经济事务,究其原因,除了同法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分不开之外,戴高乐和肯尼迪迥然不同的人格魅力和外交风格是不可否认的因素。(36)
戴高乐还对美苏之间垄断核武器一直不满,反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举行核禁试谈判,有意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同美苏之间拉开距离。法国主张举行多边会谈,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还两次拒绝戴高乐关于建立一个军事战略联合委员会的要求。美国的行为增强了法国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的决心。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艾奇逊飞抵巴黎就美苏对抗一事进行“外交通报”,而不是相互“磋商”,使法国人产生美国有可能将其盟友排除在外之感。美国还向英国悄悄地提供核潜艇和核弹头情报,“法国显然没有得到同样的情报”。(37)出于报复,法国长期以“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是替美国经济和政治力量加入共同市场作掩护”为由,不相信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诚意,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请求,(38)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戴高乐始终强调,如果法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一个统一的欧洲将能对国际外交产生重大影响。(39)1960年法国爆炸第一颗核装置后,立即宣布法国拥有核威慑武器使它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并拒绝美英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谈判”。嗣候,法国一系列的举动,如:中法建交、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要求北约总部从巴黎撤走等,充分表明西方集团内部矛盾的日趋明显。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主张“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发展东欧各国的贸易,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巨大的压力。美国和西欧的矛盾还表现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立场、西欧国家与苏联改善关系等。1963年法国和德国签订《法德合作条约》后,法德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美国对西欧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以发展战核武器、保持核优势、维持东西方力量平衡的美国全球战略收到来自盟国的巨大挑战。
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利益在远东乃至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使日美长期存在的依附关系发生变化。 日本在贸易、投资、货币等问题上与美国摩擦日益严重,政治上日本还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提升自主外交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随着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与苏联集团对抗的意志受到抑制。
东方阵营内部矛盾和分歧也在不断激化。战后,苏联像领头“纤夫”一样,艰难地带着伙伴们径直朝前。由于南斯拉夫主要靠本国力量打败德意法西斯的,所以,苏南关系从一开始就十分紧张。西方人更认同铁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外政策。铁托坚持走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被苏联等国视为社会主义叛徒,将其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使东方阵营内部首先出现严重裂痕,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一系列的争论。
1956年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是波兰的内政,而苏联却断言是“反人民骚动”,“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新阴谋”,苏波关系出现危机。波兰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影响很大,它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前奏曲。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国内政治气氛活跃,成立裴多菲俱乐部,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大谈民主自由,要求被解除总理职务的“纳吉回到中央来”。(40)引起苏联极大的不满,苏军平息这场政治风波,纳吉本人被处死。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暴露,直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使东欧各国民主浪潮发展到新的阶段,严重削弱苏联在东方阵营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维持亲密的伙伴关系。但苏联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某些欺骗因素。在公开场合下,苏联人宣称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合作关系,掩盖不断增加的矛盾。其实,中苏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完全不同观点,其中包括苏联对外政策。(41)尤其是赫鲁晓夫寻求同美国的和解行动遭到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批评。(42)中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直接影响两国正常关系。苏联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公开支持印度反华,直至挑起边境冲突,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加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东方集团与西方对抗力量严重削弱。东西方阵营内部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分歧降低了美苏核对抗的强度,挫伤了美苏维持核优势的信心,为了摆脱压力和被动,美苏之间寻求对话,缓和关系的意识不断增强,客观上推动了两个超级大国走出核对抗困境的决心。
四、促使美苏走出对抗困境的外部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都采取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试图通过援助来扩大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加入到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来。尤其是美国,时刻不忘共产主义在信念和制度上对其的挑战,古巴导弹危机更加给美国一种后院起火的危机感。1961年美国《对外援助法》出台后,肯尼迪政府通过出售、借贷和赠送等方式,向缺乏粮食的国家出售农产品。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43)美国每年对第三世界的粮食援助达15亿美元,既帮助美国农民摆脱粮食过剩,又使印度、埃及、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克服粮食危机。(44)苏联也不断向第三世界渗透,每年平均向这些国家提供6.83亿美元经济援助,3.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45)与美国争夺重要战略范围。美苏核对抗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除了西欧、日本因素外,第三世界力量的聚合使核对抗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不结盟运动的兴起虽然削弱美苏核对抗在亚非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但又给苏联在这些地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关系网提供机会。(46)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非殖民化”运动得到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几乎原来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获得政治上的独立。(47)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约占世界领土63.50%,人口占四分之三以上。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56年7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拥护和平共处原则,坚持民族独立和反对参加对立的军事集团,主张在各国之间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在三国的倡导下,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上提出不结盟运动宗旨:不参加可能导致卷入大国冲突的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等。使不结盟运动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48)此次会议初步涉及反对“旧秩序”问题,要求废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变换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里采取联合行动,为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和奴役奠定基础。根据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原则,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制约东西方关系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49)
发展中国家还组成77国集团,向加强各国经济联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迈开重要步伐。在涉及原料、贸易、能源、货币金融等一系列问题上制约美苏核对抗的深入,既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又促使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同超级大国保持平衡关系。美苏两国在推行扩张战略时,都企图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ideological ally)。一些如印度、埃及等国成功地运用中立和依附的两手策略,在两个集团控制的夹缝地带寻求生存空间。
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对美苏的核对抗行为进行牵制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双方保持缓和与对抗的重要因素。美苏双方都坚信各自所追求的信念能使世界走向统一,都将会给人类带来和平、进步与光明,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政治理念确立行为准则,都不得不在首先挑起战争问题上谨慎行事,意识形态制约美苏核对抗双方行为是研究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余论
美苏两国拥有大量战略武器,是维系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平衡的重要因素。核战争的代价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导致双方大量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模糊了士兵与非战斗人员的界限。由于核战争是交战双方都不能单独获胜的战争,一些西方学者把核力量平衡说成是“防止爆发毁灭性战争的有效机制”。(50)这种提法未免夸张,但美苏双方对核战争的毁灭性却有充分认识,艾森豪威尔曾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总有一天美苏双方“会聚集到谈判桌上”。“人类必须遵循这一规则,否则将会灭亡”。(51)说明“结束核对抗时代”对双方都是生死攸关的。冷战期间,地缘政治竞争和核竞赛持续近半个世纪,美苏双方在每一次重大对抗中,让局势发展到直接引发战争,或使用核武器的地步。这也是双方政治家们对核战争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代价和成本的认知。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攻击能力虽逊色于美国,但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之机,加快发展战略核武器,到1969年底苏联战略核弹头已超过美国。其实,对拥有毁灭人类数次的美苏双方来说,“决定性的核力量现实就是共同承担巨大灾难的风险,与这种灾难相比,核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和劣势最终关系不大。(52)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在一场双方势将同归于尽的核战争中,追求战略力量上的优势,无异追求海市蜃楼”。”有关核武器与“持久和平”、冷战与热战等关系问题,一直在引起学术界的争论,美国学者甚至把核武器对峙下的冷战说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世界战争的‘和平时期’”。(54)这种观点可以被理解成,核威慑是美苏保持对抗与对话关系杠杆。
核对抗时期的美苏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两大阵营内部的分歧与对立、意识形态的差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制约了美苏之间的对抗与对话关系的发展,最终使美苏双方走出核对抗的困境,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制约因素对研究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防范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可能引发的地区冲突、尤其是核战争危机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6-09-04
注释:
①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常被西方学界描绘成“对话与对抗”(rapprochment and confrontat]on)、“不严密的两极体系”(the loose Bipolar systern)、“没有战争的军事对抗”(force without war)关系。
②John H.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③Daniel S.Papp,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Macmillan College
Publishmg Company,1994,p.164.
④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ltzgraft,Jr.,American Foreign Policy:FDR to Reagan,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1986,p.144.
⑤McGeorge Bundy,"The Presidency and the People",Foreign Affairs 42,(April 1964),p.354,根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忆,肯尼迪本人并不相信美苏之间存在什么“导弹差距”,但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宁愿相信这一“事实”,也不愿意失去国会即将批准的追加军费拨款。Ronald E.Powaski,March to Armagedd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1939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4.
⑥Max Frankel ,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Kennedy,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4,p.49; Richard Smoke,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the Cold War,McGraw-Hill,Inc.,1993,pp.83-86.
⑦Max Frankel,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Kennedy,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4,p.50.
⑧Michae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Kennedy and Khrushchev,1960-1963,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p.49-54.
⑨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ltzgraft,Jr.,American Foreign Policy:FDR to Reagan,p.179.
⑩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Kennedy: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1961,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2,pp.580-581,pp.589-590.
(11)[美]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88页。
(12)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Berlin Crisis,July 25,196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Kennedy: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1961,pp.533-540.
(13)Documents on Disarmament,1961,pp.314-315,citing Radio Moscow,Aug.29,1961,Robert M.Slusser,The Berlin Crisis of 1961: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Kremlin,June-November 1961,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159.
(1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p.137.
(1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16)Philip Windsor,City and Leaves:A History of Berlin,1945-1962,Frederick A.Praeger,Inc.1963,p.237.
(17)Norman Gelb,The Berlin Wall:Kennedy,Khrushchev and a Showdown in the Heart of Europe,New York:Times Books,1986,pp.113-114.
(18)Theodore C.Sorensen,Kennedy,New York,Happer & Row,Publishers,1965,p.592.
(19)Hugh Sidey,John F.Kennedy,President:A Report's Inside Story,New York,Atheneum,1963,pp.230- 231; The New York Times,June,1,1961,p.10,Jack M.Schick,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2,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p.151.
(20)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3,p.407.
(21)Raymond L.Garthoff,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A Memoir of Containment and Coexistence,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2001,pp.125-126.
(22)Memorandum(for the Ex.Comm) subject: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the Soviet Missile Bases in Cuba,Oct.27,1962,Raymond L Garthoff,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1987,pp.202-203.
(2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Kennedy: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1962 ,Vol.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3,pp.813-815,see also Lester H.Brune,The Missile Crisis of October 1962:A Review of Issues and References, Regina Books,1985,pp.45-52.根据当事人回忆录记载,肯尼迪十分紧张地等待苏联如何回应美国对古巴采取的封锁“隔离”措施、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将会对美国的行动采取什么样反应。
(24)Herbert S.Dinerstein,The Making of A Missile Crisis:October 1962,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216.
(25)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hzgraft,Jr.,American Foreign Policy:FDR to Reagan,p.176.
(26)Pravda,December 13,1962,p.2;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p.578.
(27)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p.49.
(28)[苏]赫鲁晓夫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65页。
(29)Philip J.Briggs,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p.115.
(30)Public Papers:John F.Kennedy,1962,821; Arthur M.Sehlesinger Jr.,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p.895,see also Herbert S.Parmet,JFK:The Presidency of John F.Kennedy,New York:The DialPress,1983,p.310.
(31)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June 10,196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ohn F.Kennedy: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1963 Vol.3,1964,pp.463-464.
(32)Michae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Kennedy and Khrushchew,1960-1963,Edward Burlingame Books-Harper Collins,1991,pp.60-61.
(33)Toward a Strategy of Peace,Address by President Kennedy,June 10,1963,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49,no.1253,July 1,1963,pp.2-6.
(34)Addres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tract) June 16,1962,Document on Disarmament,1962,Vol.1,1963,pp.625-626.
(35)Gordon C.Schloming,Power an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p.p.97.
(36)肯尼迪任总统期间曾经七次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晤,而同戴高乐仅见过一次面,这仅有的一次还是发生在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的途中。肯尼迪认同戴高乐是二战反法西斯的元老,钦佩他有恢复法兰西民族辉煌历史和自豪的勇气,但肯尼迪对戴高乐的易怒、自负、固执的性格十分反感。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ltzgraft,Jr.,American Foreign Policy:FDR to Reagan,p.181.
(37)[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4页。
(38)Alfred Grosser,The Western Alliance:European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New York:Vintage Books,1982,p.204.
(39)[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第244页。
(40)[英]威廉·肖克罗斯著:《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吴仁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41)Suzanne Ogden,Global Studies:China,McGraw-Hill/Dushkin Company,2006,p.7.
(42)Barry M.Blechman & Stephen S.Kaplan,Force Without War:U.S.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p.351.
(43)L.Carl Brown,ed.,Centerstage: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World War II ,Holmes & Meier,New York,London ,1990,p.517.
(44)James E.Dougherty & Robert L.Pfaltzgraft,Jr.,American Foreign Policy:FDR to Reagan,p.146.
(45)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Communist Activities in Non-Communist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1978:A Research Paper,ER79-10412U,Sept.1979,p.11,see Robert H.Donaldson,ed.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Successes and Failures,p.338.
(46)Thomas W.Robinson,On Soviet Asian Policy:A Commentary,see Robert H.Donaldson,ed.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Successes and Failures,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rado,1981,pp.294-302.
(47)颜声毅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48)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49)陈立成等主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50)Gordon C.Schloming,Power and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p.97.
(51)Jonathan Schell,Nuclear Weapo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War,See Charles W.Kegley,Jr.& Eugene R.Wittkopf,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4) ,p.53.
(52)[美]麦乔治·邦迪著:《美国核战略》,第516页。
(53)[美]布热津斯基著:《美苏关系》,载亨利·欧文主编,齐沛合译,《7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67页。
(54)John Lewis Gaddis,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86.
标签:核试验论文; 核战论文; 约翰·肯尼迪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武器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苏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