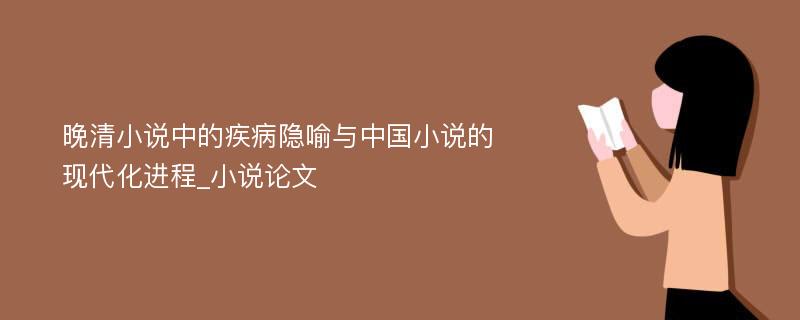
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疾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2-0082-06
当文学家描写疾病的时候,疾病往往不只是作为一个推动情节的道具在使用,而是与其他事物相关,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是任何其它题材所不可比拟的,因为身体与心灵一样,具有最大限度的发散性和开放性。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巨大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当社会文化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会投射到身体上,其表现就是肉体的病态,这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复杂的诸种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1]。当作家意识到这“诸种关系网”的平衡被破坏之后,他便会将其转化为艺术形象加以表达。因此,身体的疾病就成为社会文化的隐喻,它与精神的疾病一道成为社会文化症候的附着物。“作为文学的主题或题材,它们首先传导了人们不寻常的经验。这种患病的经验或通过疾病表现出来的经验丰富了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其次,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了”[2]。
晚清小说中疾病的隐喻对古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各方面都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疾病的社会隐喻功能的加强。在晚清小说中,疾病主要隐喻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古代小说的疾病隐喻是为了否定个体,晚清小说疾病隐喻是为了否定社会和国家以及对个体造成伤害的礼教制度等。然而,从总体上看,晚清小说中又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对病症的不同诊断结果和所开的不同药方上。下面我分别从知识分子在面对疾病时所选取的不同角色定位来论述其思想的差异性。
一、医者之方:以医生的眼光审视病态社会与民德的叙写方式的出现
以医生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始于晚清。新小说发端之始,梁启超就为中国设想了一个健康的未来。为了把这个理想中的中国告诸世人并与当时制度的病态进行对比,梁启超才决定采用小说的方式,这也是《新小说》创刊的原因。梁启超为医治中国之病开出了药方,用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来对中国进行改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高屋建瓴地揭示社会痼疾,寻求救治之方,俨然一个社会医生。
《新中国未来记》里面的那个隐含的医生在《老残游记》中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可见的医生。《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本人精于医道,并于1885年左右挂牌行医[3]。同时,《老残游记》的主人公老残也是一个摇串铃走江湖的医生。整部小说以这个医生的活动为线索,以第三人称的限制视角叙述,用医生的眼光去审视社会。在老残那里,行医救人倒是次要的,在他的整个行医过程中不曾碰到什么他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基本上是药到病除,唯有社会之病难于医治。这部小说的着重点并不在“医人”,而在于医治国家的创伤,这构成了《老残游记》的整个隐喻系统。“作者在老残身上,寄托着医人与医国的双重希望,而老残在游历过程中,对社会现实病痛的关注,远远超出对患者病痛的关注”[4]。所以,刘鹗在《〈老残游记〉自评》中写道: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5]。
在作者看来,国人之病分为两层,一层是“病”,一层是“睡”,要治病需先醒其睡,国病医治之方,首要问题是要唤醒世人,因此,医人之病在其次,医人之睡在其先。“举世皆睡”,那世间还有清醒之人吗?作为摇着串铃的医生,老残既是无病者,又是清醒者;他既是医生,又是启蒙者和侠士。他在替人治病之余,更多是在行侠仗义,在为国家的前途忧虑。因此,《老残游记》既具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又具有启蒙主义精神和侠义精神。医生的眼光使疾病与国家的政治现状结合在一起,对民众精神状态的叙述使《老残游记》具有了一种难得的启蒙精神和人文性,而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救亡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残游记》已经具有一种很强的现代性意义。
梁启超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刘鹗却是文学家。梁启超的观点代表的是政治家的主张,而刘鹗是以一个无所依托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进行思考。所以,同样作为医国的医生,他们的情感态度和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梁启超是乐观的,而刘鹗却是悲观的。刘鹗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出在上,而出在下,在于下层的官僚。所以,在“大船隐喻”中,那些反对者不是来自于船主和掌舵的,而是来自于下等水手和那演说的“革命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驾船的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他们又未预备方针”,当日月星辰被云气遮了的时候,就没有了依傍,这些人隐喻守旧派。那些“革命者”也是反对新思想,反对新法,提倡走老路的人,暗示了革命派的“昌明国粹”,反对西法。
应该说,吴沃尧在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时候,与刘鹗写《老残游记》的时候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是用限制视角来叙述,叙述者对社会态度也是基本一致的。 《老残游记》的视角取道“老残”,意为“补残”,即补社会之“残”,暗示社会的不健全和病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叙述者取名“九死一生”。为何取名“九死一生”?作者写道:“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九死一生”所暗示的,与“老残”所暗示的显然是一个意思,即社会是残缺的、黑暗的。九死一生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小说显然是取了一个社会医生的视角,为社会病症把脉。不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关注的社会病体不是社会制度,而是社会道德,它把恢复传统道德作为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全书所写的188个怪现状,分别“从社会公德和宗法伦理道德沦丧的角度抨击世风堕落”[6]。吴趼人对世风道德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呼应。夏晓虹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是对梁启超维新理想的呼应”[7],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吴趼人的“道德救国论”为中国病体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痛史》第二十一回中,作者借疯道人之口道出了他所认为的世间之病及其治疗方案。在吴趼人看来,世间道德沦丧,其治疗之药应为古代圣贤之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之精髓,这才是使中国富强所必走的第一步。然而这剂药方是否有效?吴趼人自己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他在其他几部小说(例如《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矛盾思想。在《新石头记》中,贾宝玉的理想也被打得粉碎,彻底破灭,依旧浑浑噩噩,迷迷惘惘,最终只好再度回到太虚幻景里去圆他的“自由村之梦”去了。有研究者认为:“趼人知道自己未必就找准了社会危急、国难当头的病根,因而只是对‘症’下药也就当然未必正确、有效,虽然他口中老在叨念‘非恢复旧道德不行’,而脑子里却还是不断地在自我怀疑、自我批评。”[8]是符合实际的。与梁启超的自信不同的是,吴趼人与刘鹗一样也是较为悲观的。
晚清谴责小说基本上都具有这种悲观的调子,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悲观的调子使晚清小说显现出它的现代性萌芽。我们之所以认为王国维的悲剧理论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其主要原因恐怕不仅因为他的悲剧理论体现出了其与西方悲剧理论的接轨,它更暗示了一种处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不仅体现在其语言的白话化和对外国小说的自觉模仿,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
《官场现形记》、《活地狱》和《宦海》都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其对晚清吏治的腐败与黑暗有着深入的揭露与批判。但是,由于晚清知识分子并不能在内心深处完全摆脱士大夫那种治国平天下的宏远理想,他们在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也难于摆脱对传统文化、道德乃至于政治制度的依恋感。体制将他们抛离出来,但是他们与体制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心理上存在着恋旧情绪。所以,晚清知识分子的独立是形式上的独立,批判是表面上的批判,反思是浅层次的反思,个人的抱负与社会文化的结合不是“自觉”的,是受着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牵制的忧患意识。《负曝闲谈》、《冷眼观》、《梼杌萃编》在批判日益沦丧的道德和世风之时,也无法做到价值观的绝对独立,而是用一种既定的道德去剖析与批判病态的社会,用传统道德去批判假道学与伪君子。作为社会疾病的医生,他们是以健康人的姿态,用了根深蒂固的“健康”的思想,去否定批判由于偏离正轨而呈现病态的世风。
二、患者之药:以病人的眼光控诉不良社会制度给人带来的伤害和身心的摧残,从非正常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的症结
对人的发现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功绩之一,然而,在晚清小说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的觉醒意识,对封建专制与婚姻制度的批判、反思也开始出现萌芽。在小说中,限制视角的运用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创造了契机,而以“病人”的眼光对社会病状进行审视则使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程度得到了加强。在《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小说中,作者都使用了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限制叙述视角,然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都是健康的,扮演着医生的角色。在我下面将要讨论的几部作品中,叙述者或作品中的主人公变成了“病人”。
《禽海石》用一个生病的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的语气,记录了自己不幸婚姻的整个过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作品是近代首次自始至终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叙述者自称是一个病入膏肓之人:“看官,不瞒你说,我现在病到这般地步,我是搦定厌世主义,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禽海石》在写作技巧上显得幼稚,语言也显得生硬笨拙,整个故事主体叙述过程也不离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老套。但是小说开头和结尾用病人哀怨凄婉的叙述语气所定下的基调却使整个作品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和批判意义。病人视角的叙述模式本身远远超过故事本身的批判性,这是《禽海石》较同期其他哀情小说高明而独特之处。 《禽海石》不论是在叙述模式的转变方面,在对个人情感的尊重与关注方面,还是对道德与礼教的批判方面,都具有了五四文学中的那种现代性意义。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干脆把笔名就起为“东亚病夫”。作品署名“东亚病夫”且不说,在小说开始却要反复写到做此小说的原由,小说又是怎样通过这个东亚病夫之手写出来的等等,笔名的意义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得到了强化,相当于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就是“东亚病夫”。为何叫“东亚病夫”呢?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人性与制度的不完美,是要引起国人的警觉。在1927年给读者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自己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他说起此名既不是为了做藏身之窟,也不是为了用别号来表示自己对文学的轻蔑。恰恰相反,“我不但信任文学的高尚,我看着文字,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宗教”。既然如此,那么名号应该是曾朴对社会人生的一种独特思考,曾朴酷爱这个名字,一直不改,他是在意识到了国民及国家的病根之后,有感而发。以病人姿态的抒写使《孽海花》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色彩。
成书于1902年的《轰天雷》虽然没有以病人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但是,它所描写的主人公荀北山却是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带有疯子特征的呆瓜。有人认为,荀北山完全是一个反讽性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同《轰天雷》有点相似”[9]。从这个意义上说,《轰天雷》所具有的现代性反讽,以“疯子”的处事原则去对比正常世界中的表面清醒却本质上蒙昧的做法,已经具有了非常深刻的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隐喻技巧,虽然它对人物的病态心理刻画不够,也远远不及《狂人日记》表现的那样深刻。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荀北山这个非“正常”人的行为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他对社会对时政的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用病人的语气,却使我们感觉到了病人的思想和对社会的认识,其深刻之处远非那些直白的政治小说可比。
病人视角的叙述方式在晚清小说中不多,而且对疾病的体验也并没有深入地描写,没有揭示疾病患者与常人不同的感受,无论是从感性的层面还是理性的层面都没有使叙事进入“疾病状态”,但是这种叙事模式的萌芽却改变了小说作者对小说的认识,对晚清小说打破传统叙述模式,从各种不同侧面展示社会状况,批判社会文化的病因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他者之悲:以旁人的眼光,用疾病隐喻社会及文化给人带来的灾难,直接将疾病的隐喻指向社会和文化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早在晚清以前就已经开始,而在晚清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直接而激烈。不过,这种批判并非出自主流知识分子之手,因而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那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也黯淡了其前期思想界和文学界所做的种种努力。当我们拂去“五四”那层耀眼的光环,回到其之前的那段暗无天日的沉闷时代中去的时候,会发现这段时期在充塞着各种冤屈灵魂的同时也洋溢着不屈的呐喊,人性解放的呼声此起彼伏,其对封建专制制度滴血的控诉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伤痛记忆和思想解放的亮光。而这之中,表现得最强烈的,当属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和控诉。
《禽海石》对专制婚姻制度已通过受害人之口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新茶花》中,同样的议论则出自旁观者之口。《新茶花》明显地受到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那种对资产阶级虚伪道德观念的批判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的精神,在《新茶花》中变为了对摧残纯真美好爱情的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批判和对自由爱情婚姻的向往。在《新茶花》中,疾病是弱者的表现,是受摧残被迫害者的象征,而健康和勇气才是最为耀眼的精神火花。武林林自比为茶花女,但却没有玛格丽特那种多病和柔弱,有玛格丽特那种纯洁而高尚的品德,但又比玛格丽特更加勇猛而坚强。相比之下,作为男主角的项庆如却在打击面前一病不起,成为武林林的一个鲜明对照。因此,《新茶花》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对被迫害者的同情,另一个层面是通过对受害者积极的反抗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斗争精神的歌颂。
相对于《新茶花》那种强烈的反抗意识而言,晚清还有一批写情小说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封建婚姻的不幸及导致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描写,而疾病往往成为渲染悲剧气氛、对社会进行控诉的道具。吴趼人的《恨海》叙陈伯和与张棣华、陈仲蔼与王娟娟之间的聚散离合,写人间至情至性,虽然不离对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的回顾与眷恋,然而在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社会隐喻意义。从社会学角度看,作品叙写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颠沛流离的痛苦,虽然表现出了对“拳匪” (义和团)的不理解,但在事实上也反映了统治集团风雨飘摇的政治局面和其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症结。小说中表现出的家国之忧代表了晚清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情感状态:既有对造成社会动乱的义和团之恨,又有对统治者无能之怨;既有对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之悲,又有对国家山河之爱。其情感之丰富和复杂,难于言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吴趼人之所谓写情实际上不外是旧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相,反映的仍旧是一派旧的封建思想。”[10]我认为恰恰相反,透过所谓的“旧派的封建思想”的面纱,在棣华身上显现出来的却是人性的涌动和神性的光彩。类似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他的另一部标为“苦情小说”的《劫余灰》中。小说所写之情并非儿女私情,而且还并非全如作者所说的那忠、孝、节、义,而是洋溢着浓郁的博爱色彩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精神,恰似许地山在《春桃》中所宣扬的那种精神一样。而这种精神才是吴趼人所真正要追寻的精神,是作者所要倾力讴歌、并寄托着强烈的救世希望的精神。所以,他最终让棣华守住这个精神,作为一个火种留存下来。
如果说《恨海》所表现出来的批判色彩、博爱精神与人性的显现和作者所要表现的忠孝节义之大节的初衷相违背,那么《劫余灰》则试图将这种人性关怀再次压抑下来,对忠孝节义极尽夸张歌颂之能事,塑造了朱婉贞这样一个贞妇烈女的典型。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对造成朱婉贞痛苦人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则发现《劫余灰》再次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让人掩卷而难以忘怀的,是列强的压迫和人情的险恶,更让人触目的是朱婉贞对扼杀自己个人幸福而守愚节尽愚孝的自愿。封建礼教导致人的自愿“自杀”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作者对忠孝节义描写得越深,其批判色彩越强。这恐怕是作者甚至于当时诸多评论家也始料不及的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恨海》和《劫余灰》的悲剧性和人文精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它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烈的现代性意义。
在一些宣扬妇女解放的小说中,疾病也被用来隐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种种弊病。《黄绣球》是晚清著名的写妇女解放的小说,其中有大量的疾病描写。而这些疾病描写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暗指社会痼疾、丑陋习俗等问题。如在第十回中,毕太太谈到社会风气开化问题时以痰喻社会痼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痰象征着一个“心结”,心结解开,则不药而愈;心结不解,什么好药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是什么呢?那就是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对妇女的正常欲望和人性的压抑。《黄绣球》从反缠足、兴女学、妇女的社会价值、两性关系等各个不同的侧面触及到了妇女解放问题。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实际上是触及到了人性解放的问题,这与五四时期人性解放把妇女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的做法是一致的,或者说,妇女解放正是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黄绣球》与赵树理的小说非常相似。同时期类似的小说如《女娲石》、《女狱花》、《狮子吼》、《自由结婚》、《女子权》、《中国之女铜像》、《女举人》、《女豪杰》、《女英雄独立传》、《天足引》等小说,单从书名来看,就已经证明这种解放运动和对自由婚姻的渴望已经变成了流行的名词,人性解放通过妇女解放的呼声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呐喊。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萌芽已经通过妇女解放小说得到了最有力的诠释和表现。归根结底,这种妇女解放的呼声是在倡导风俗的改良,也就是改变那种残害人的自由发展的恶风旧俗,认为国魂复活之根恰恰在于风俗。“国魂之于风俗,犹灵魂之于脑筋”,“脑有病者则其魂若失,而风俗的腐败则国魂亦如之”。“(恶)习惯不去,国魂不来”[11]。所以,对风俗的改良和对妇女解放的呼声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晚清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除此而外,疾病隐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疾病隐喻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侵略和文化思想侵略对中国古老文明形成的冲击和给社会带来的病变。这种隐喻形成的根基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华夏古文明的眷恋,其中包含着一种恋旧、复古的保守主义思想,也饱含着对传统文明受到列强欺压的一种深深的忧虑。在形式上,它主要表现为对西方侵略的不满。
《黑籍冤魂》写鸦片侵入中国及泛滥成灾,暗喻西方之药并不能救中国之病。《发财秘诀》更是把变法维新、民主自由的提倡乃至立宪运动都看成了一种闹剧。《黄金世界》则将矛头直接指向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贩卖华工的罪恶。另一方面,更多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制度却基本上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接纳姿态,这与其对中国文化中的传统痼疾的批判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叙事策略更多的是倾向于构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其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康有为《大同书》的构架[12]。这类小说如《痴人说梦记》、《新三国》、 《新水浒》、 《未来世界》等,都持赞成立宪的政治观点。吴趼人则在《月月小说》上发表了若干赞成立宪的短篇小说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等。还有一些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通过小说反对立宪维新,代表作品有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有专对康梁而作的《康梁演义》、《新党发财记》、《上海之维新党》、《一字不识之新党》、《立宪镜》以及各种反维新的《××现形记》之类的小说[13]。因此在晚清小说家中,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为保守派反对维新者,一种为拥护维新立宪者,一种为主张革命而反对维新立宪者。反对维新的革命派在小说中往往将康梁进行丑化,将其塑造成为流氓无赖的形象,康梁及其同党时染沉迷于声色钱财之病,而这多少是一种带有较为低俗的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小说叙述模式了。
晚清小说中的疾病被作为隐喻使用时,其审美化功能已消失,疾病不再赋予人物以林黛玉式的病态美,也不具有拜伦式的浪漫化色彩,它是一个与中国古老的病体相一致的隐喻,疾病象征着羸弱、衰败、阻碍、退化、阴暗、死亡和一切消极负面的东西。疾病也不赋予人物以超强的感受力,而是使晚清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时代把他们推向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之中。
晚清小说家群体在政治观点上虽然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他们之间常常互相攻讦,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却具有更多的共性。这种共性是政治观点的差异性所取代不了的,那就是不再把自己完全交付给统治阶级而成为其使用的喉舌和工具。即使作为思想较为保守的小说家如刘鹗、李伯元等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观点是他们作为一个思想较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自然而然的表达,而不是政治集团对其思想改造的结果。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晚清知识分子的依附人格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失望感而逐渐消失。同时,政府对思想界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弱化使晚清思想界呈现出一种难得而可喜的自由。反立宪的、反维新的、反政府的、批评社会弊病的声音可以同时杂呈于晚清文坛,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较为自由独立的思考方式。不论他们持何政治观点,都始终忠实地扮演着一个医生的角色。
晚清小说家和知识分子医生角色的定位亦不一定必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种种现象表明,恰恰是时代集体无意识把他们塑造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们的行为是自觉的,也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也是知识分子自身所固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结果,这二者在他们身上表面上呈现为矛盾,本质上呈现为统一。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可社会进化论,但小说创作中的医生角色定位又处处暗示着他们是在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之后才做出的选择,小说中的“疾病”正是解开这一疑团的钥匙。疾病隐喻使晚清小说表现出不同于古代小说的鲜明特征。一是证明了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加强;二是表明了小说隐喻性的加强;三是表明了小说人文性的加强;四是体现出了一种启蒙精神;五是体现出了一种救亡精神。而以上这些,都可以被作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构成因素。因此,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表明中国小说已经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晚清论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论文; 读书论文; 老残游记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恨海论文; 黄绣球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