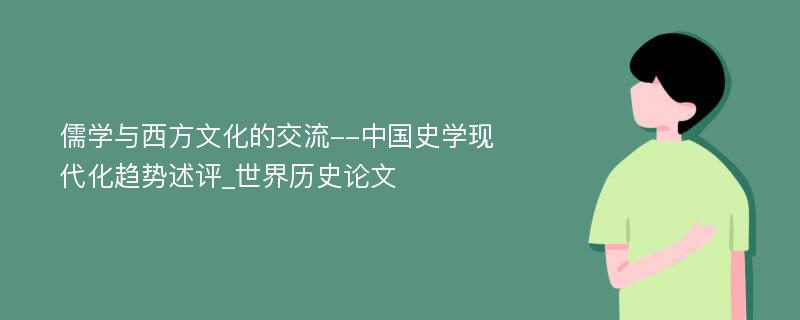
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西方文化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取向与史学近代化
自孔子创儒家学派,至19世纪末,儒学曾经历不同的演变阶段,而它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虽可溯源至十七八世纪,但具有实质意义的输入,并引起中西文化的交流、撞击的阶段,实际上是在鸦片战争至20世纪前期。这一历史阶段儒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是:(一)从总体说,西方近代文化比传统的儒学先进得多,近代进步思想家自魏源起便倡导学习西方。儒学与西方文化由于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文化背景,故形成了猛烈的撞击。但历史进程已经显示,二者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交流。(二)儒学之中蕴藏着许多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当时代的剧变要求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近代因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取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进步文化相揉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三)因此,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移植或取代式的,而是经过吸收、交流,最终形成了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近代文化。
史学这门学科素来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宗,历代有识之士,甚至是跻身高位的人物,都以著史为极其崇高的事业。而且,从孔子著《春秋》、司马迁著《史记》起,我国史学就形成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史家要关心国家的治乱,史书要总结时代的盛衰,作为现实社会的鉴戒。处于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魏源,他们深刻地体察到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呼吁实行变革的急迫性,预见到时代剧变即将到来,因此主张良史必须做到“忧天下”、“惊世变”。(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又生活了十几年,曾到前线参加定海抗战,亲身经历了这场大事变,他所撰写的史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都直接与鸦片战争这场中西冲突有关。在近代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是,他在《海国图志》全书总纲《筹海篇》中最早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由龚、魏倡导的挽救危机、实行变革的主张,以后发展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潮。七八十年代,有王韬著成《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本世纪初,有梁启超著成倡导实行史界革命的《新史学》,有夏曾佑著成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至五四前后和三四十年代,则有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及稍后的陈寅恪、陈垣等,著成出色的史著,近代史学蔚为大观,他们的成果又被随之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吸收。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发扬了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以此为基础,同时大力地吸收了西方进步文化而不断推进的。故审视体现于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的取向,不但对于近代中西文化撞击而交流这一文化进程所亟为必要,而且对展望未来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大有裨益。
二、由批判封建专制通向西方民主学说
由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而通向西方先进的民主学说,这是体现于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儒学优良传统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特征。
西方近代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实行人民共同享有平等权利的学说,比之中国的封建帝制和官文统治思想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启蒙思想风雷激荡的时期,先进人士正以结束帝制、实行民主制度为号召,这是近代文化的时代强音,也是近代史学的思想灵魂。近代先进人物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思想主张,主要是由于学习西方民主学说(当时称为民权学说)而形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民主思想敢于把两千年来视为神圣的封建帝制彻底否定,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何接受得这么顺利?这就是因为中国儒学中本来就有谴责虐待民众、限制君主权力、重视民众意志的优良传统,这些正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沟通,并且成为近代志士仁人顺利地接受过来的思想基础。
从近代思想家、史学家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来说,孔、孟学说的精华是其远源,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君主专制是其近源。孔子继承了西周初年敬天保民的思想,提倡实行仁政,主张惠民、恤民、富民,反对过度使用民力、残酷榨取,主张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不君,就不能责备臣不臣。孟子对孔子学说这一优良部分加以发展,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光辉思想,并且认为民众起而诛杀暴君是正义的行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分别见《孟子》《尽心下》及《离娄上》)汉以下,贾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都有过对封建统治虐民、残民的愤怒谴责。处于宋元之际的邓牧,更尖锐地抨击暴君和酷吏:“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见《伯牙琴》《君道》篇、《吏道》篇)揭露了封建专制帝王和官吏贪婪掠夺、残害民众的实质。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更一再爆发出对封建专制的强烈抗议。清初进步学者由于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大事变,目睹明朝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亡国惨剧,因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专制统治的罪恶。黄宗羲《明夷等访录》便是讨伐封建专制的檄文,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专制君主,揭露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个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还提出“君民共治”和“是非决于学校”的主张。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正是衰老的封建社会终将崩溃的预告,近代社会随之将要来临的先声,启发后来的史学家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两千年的历史。所以尽管乾嘉时期考史盛行,而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却能以大量材料揭露历史皇帝昏庸、专制、嗜杀、淫乐等罪恶。
生活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卓越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魏源,继承了上述儒家重视民众意志、反对专制君主暴虐统治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开启了近代史家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先声。龚自珍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士人“震荡摧残”以肆其淫威(《古代钩沉论一》)。他分析专制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有如将活人放在独木之上,用长绳捆绑起来,“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所以他呼吁废除专制解救社会的灾难,“救今日束缚之病”(《明良论四》)!魏源揭露当时社会危机的各种表现,首先就是“堂陛玩愒”(皇帝耽于逸乐,荒于政事)、“政令丛琐”(专制机构陷于繁文琐事,运转失灵)(《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一》),并且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憧憬,提出“天子是众人人中之一人”,“天下为天下为人之天下”的新论点,希望出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言路开通、重视舆论的局面(同上,《治篇三》)。龚自珍和魏源处在清朝统治在下坡路上急剧滑落、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他们在史著、史论中揭露专制主义的痼疾,是同挽救危机、寻找民族出路相联系的。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发生的第二年即去世,他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现尚未作出评论。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后又生活了14年,他既认识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性,又初步接触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中国自先秦以来重视民心、民意,反对暴君虐民的朴素民主意识,有力地帮助魏源在时代剧变面前,有勇气承认中国的落后,开始注视和探求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此即他发愤撰著《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魏源在这部当时东方最详尽的世界史地巨著中,一再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认为“墨利加北洲之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万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叙》)又称赞华盛顿创立民主政体,“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统领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墨利亚洲总叙》)龚自珍、魏源史学论著中抨击君主专制、向往西方民主政体的言论,使刚刚萌生的近代史学呈现出异彩,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专制主义的堤坝发起了越来越有力的冲击。
七八十年代产生的近代史著,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深入了一步。王韬于70年代著成《法国志略》,内有《志国会》一章,详细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订法律,选举统领、首辅,“一有不当,通国谢之。”并加以评论:“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王,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虽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重订法国志略》卷16《志国会》)强调西方各国实行的民主制度较之封建专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的保证,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便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局面的发生。这些论述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的重大进步意义。稍后,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杰出的诗人黄遵宪著成《日本国志》。他于1877年任驻日本使馆参赞,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本人还阅读了卢骚、孟德斯鸠的民权学说,极受启发。他撰著《日本国志》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确信西方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乃历史之必然,中国也必须效法日本,实行维新,“锐意学习西法”,才能由弱变强。黄遵宪肯定议会民主制的优越是同揭露封建专制的严重弊病对照论述的。他说:“盖自封建之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天门,如天如神,穷极高远,盖积威所劫,上之而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维新以来,悉以西法。……朝廷之下诏,已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日本国志》)卷3《国统志》在这里,他激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在社会地位、经济负担、刑法治理各方面对平民的残酷压制,说明议会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一必然趋势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中国封建专制。此外,黄遵宪在《学术志》、《刑法志》中又对西方各国实行的“君臣上下无甚差别”的政治制度,和“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的法律制度都作了介绍,并且表示衷心的向往。总之,黄遵宪以自己亲到日本、欧美的观察体验和所获新鲜知识,发扬了近代史学救亡图强的优良传统,表达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同当时国内民族资本已经有所发展的状况是互有联系的。
至90年代初,维新思想高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大力抨击专制政治的不合理。维新志士们把自己的事业视为黄宗羲、龚自珍发扬儒学思想精华、大胆抨击专制的言论的继承,梁启超、谭嗣同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钞、印刷,秘密散布,推动变法运动。梁启超还称赞龚自珍批判专制的言论导致了晚清思想解放:“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无不受其激刺者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谭嗣同还以冲决一切网罗的精神喊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真切地喊出广大人民对专制压迫的强烈愤恨。综观戊戌时期的思想界,一方面是西方民权学说迅速输入,一方面是中国先哲反专制思想的发扬,二者交相为功。百日维新失败的惨剧,使人们更加认识清朝专制统治的黑暗反动,加上列强图谋瓜分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于是激起本世纪最初几年革命民主思想的高涨。当时势头很大,影响广泛的是,在史学范围内,出现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倡导“新史学”的热潮。1902年梁启超著成《新史学》,1904-1906年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便成为近代史学正式产生在史学理论上和通史编纂上的标志。《新史学》论述的中心,是激烈批判旧史为专制政治服务,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存在四弊(“知有朝延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梁氏大声疾呼要实行“史界革命”,开创史书“为国民而作”的新局面,使史学成为“益民智”的工具。以此为界标,宣告了以叙述国民为对象的新时代的开始。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完成上古至隋),也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作了激烈的批判,同样反映了本世纪初进步思想界要求结束专制制度的时代潮流。他斥责秦朝的暴政造成“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两千余年,国中社会之情况,犹一日也!社会若此,望其乂安,自不可得。”故“二千年所受之祸,不可胜数。”(《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六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下》)书中对汉光武帝的评价更耐人寻味。夏氏肯定光武帝崇尚气节,为历代专制君主所不及,同时批评其秉政有两大弊端,一是宣布图谶于天下,造成鬼神迷信的盛行,二是使东汉重开女主专政的局面,“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远,利深祸连,终于亡国而后已!”此为前汉败亡覆辙,光武帝却不引以为戒,“其害遂与中国相终始!”(《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光武中兴》)这也正是对那拉氏专制,“定策帷帘”、“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以致行将亡国的有力谴责。中国近代史学经过60余年的酝酿、积累,终于在举国批判专制、宣传民主制度的高潮中,以《新史学》、《中国古代史》的著成而宣告正式产生。史学演进的史实证明:从批判专制、要求民主这一思想境界考察,近代史学的渐进和正式产生,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朴素民主思想的精华与西方进步思想融合的产物。
三、考察历史演进主线与治史方法之中西沟通
近代史学的理论基调和思想灵魂,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已如前述。继之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从形成进化的历史观点和严密考证的治史方法这两个重要方面,在近代史学的演进中又如何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自梁启超起,近代史家解释历史演进主线的观点是进化论,比起中古时期许多史家所持的循环史观以至复古史观来进步得多;而进化论观点是因严复《天演论》传播西方学说而后风行全国。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进化论这一西方学说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在当时具有支配思想界的力量,且迅速在近代史学结出硕果,则是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成戊戌变法时期有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在流传。顾颉刚先生在1919年写有《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一文,讲他本人认识前后的变化,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由旧易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学’──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载《中国哲学》第十一辑)当时他仅27岁,大学尚未毕业,却以亲身体验讲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的成就固然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
“今文学”,主要是指西汉以来的春秋公羊学说,其中包含一套具有独特色彩的朴素进化历史哲学──著名的“三世说”,到了近代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大力推演。“三世说”的雏形,是《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242年的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历史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东汉何休为《公羊传》作注,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据乱──升平──太平”(见《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于是创造出儒家经典中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启示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进程。此后千余年间,今文学说衰落。至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原因是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进步的人物为了变革现实,且在学术上树立新的风气,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公羊学说适逢际遇,它具有既是儒家经典,又长期处于与正统的古文学派不同的“异端”地位这种双重身份,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它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更有耸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拿它跟顽固派的僵死观点作斗争,最重要的人物是龚、魏和康、梁。
换言之,儒学中公羊学派的三世朴素进化观,构成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当时没有更先进的观点,只能以此推演新说。龚、魏批判专制,在史学领域倡导新风气,都跟公羊学说相联系。龚自珍吸收和利用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用来论证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又用“早时──午时──昏时”来隐括封建统治力量由盛到衰的规律,并且预言时代大变动即将到来(见《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尊隐》)龚自珍又以“三世说”探讨上古文明起源、演进的历史,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以《尚书·洪范》中的“八政”为思想资料,解释“食”、“货”相当于据乱世,“祀”、“司徒”、“司寇”、“司空”相当于升平世,“宾”、“师”相当于太平世。他又以“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作概括,表示先有生产经济活动作基础,以后出现各种制度,最后才有教育和思想学说等,上古文明即这样由较低级到较高级阶段推演(见《五经大义终始论》和《五经大义终始答问》)魏源对于将公羊学说变易观点糅合到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也有创造性的发挥,他提出“气运说”来解释历史变局。他以此观察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外关系新变化,意识到: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已显示出东西方由过去的隔绝到互相交往的转变;而中国与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也发生根本变化,需要警醒自强,学习西方长处。因此他呼吁克服闭目塞听状态,大力了解世界。至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于世。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而从学术上说,戊戌前后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都共同经历了由崇仰公羊学到接受进化论的道路。梁启超于1899年撰写《论支那崇教改革》一文,即把公羊学说跟达尔文、斯宾塞“进化之说”贯通起来。在《新史学》中,他更揭起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旗帜,又特别点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谭嗣同则把《公羊传》列为《仁学》思想来源之一。
在近代史学中,将东方的三世说与西方的进化论相沟通,作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主线之集大成著作,是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夏氏精于公羊学,写有“璱人(龚自珍)申受(刘逢禄)出方耕(庄存与),孤绪微茫接董生(董仲舒)”的诗句,概括清代公羊学派的学统颇为精到。1896年底他到达天津,与正在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结识并密切往来,立即倾服于达尔文学说,以此为契机,夏氏实现了由公羊学者向近代进化论学者的飞跃。他在致表弟汪康年信中,对于自己贪婪地学习进化论学说的情景和极其欣喜的心情有生动的记述。他原拟撰写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未能实现,而著成《中国古代史》这部以进化论观点贯穿历史主线的史书。此书虽仍用文言文写成,但从其内容和精神说,已完全跳出旧式经学家的路数,而真正做到用进化论观点考察历史、解释历史。他自觉地抛弃掉以前一些今文学家解释经义牵强附会的成份,而将三世说变易观与说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和阶段演进结合起来。他申明自己尊信今文学,但又与过去的今文学家不同:“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第六十二节)由于夏曾佑做到把东西方进化观点加以贯通融合,所以能够提出崭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书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上古之世”由远古至西周末,其中再划分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由秦至唐,其中再划分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宋以后为“近古之世”,其中再划分五代至明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夏曾佑这样划分中国历史的主线,既不是重复前人的公羊学说法,又不是生硬搬用外来的进化论术语,而是在贯通二者之后加以创造。东西方文化交流而得出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进化观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显示出具有生命力。《中国古代史》不仅撰成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影响深远,至1936年被收入“大学丛书”,50年代又被再版,近年来仍然一再引起学术界研究的兴趣。
顾颉刚先生所讲的“朴学”是指乾嘉时代严密的考证方法,近代史家对此加以发扬,并与西方实证史学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推进了史学的近代化。乾嘉朴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治学的方法以严密考证为特征。在考史范围内,朴学家方法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其论著表述的形式古朴,但他们严密考证的方法实具有科学因素。梁启超把乾嘉宿儒的考史方法归纳为大致遵循这样的路数:(一)做到善于发现问题,“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二)搜集有关的各项材料加以排比分析,“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研究之”,(三)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初步提出见解;(四)有了初步见解,研究决不能就此止步,还须广引多方面证据加以验证,对问题追根穷源,力戒立论失于片面、武断。梁启超称这种方法是“精良”的,“近于科学”的方法,实在并非过誉(参见《清代学术概论》第九、第十七节)。以上诸项原则,可以说是世代学者辛勤治学的有益经验的总结,从事研史的人大凡不能违背这些原则,只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王国维即是在近代条件下加以发扬提高的代表,他总结自己的治史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用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互相印证。所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名文,利用甲骨文的新材料,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山海经》、《世本》、《楚辞·天问》、《汉书·古今人表》等文献材料相印证、分析,取得震动一时的成就。所以郭沫若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近代著名史学还有陈寅恪、陈垣等人,也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将乾嘉考证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写出了有份量的著作,为推进史学近代化作出贡献。
四、从一个实例看儒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景
儒学的优良部分凝聚着我中华民族古代的智慧,又在此后不同时代中得到发扬,这些精华部分必将被东方国家以至全世界各国人士所宝重、所弘扬,这是无疑的。儒学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经过用现代观念加以阐释,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有匡救之效,这也是应该肯定的。然而我们又应看到:儒学是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思想体系,它同大工业生产和形成世界性经济循环的现代和当代,毕竟属于很不相同的历史阶段。先进的人们,只能有远见地运用儒学中(自孔子至康、梁)具有积极意义的命题和思想营养,作为当前面向飞速发展的现实和各国人民大量新鲜创造,思考和建构适合于21世纪发展的新学说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而不受其固有体系的束缚。这样才是现实的、可行的。而今天却仍要拘守儒学的固有体系,则是做不到的。这里,我们即就近代的一个实例作出分析,从中可以引出有益的教训。
近代文化名人、史学名著《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无论就其革新、开放意识,学术上的创造力,和对国外情形的了解说,都堪称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青年时代的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俗儒“昂首道皇古”的泥古、复古习气,主张“识时贵知今”、关注现实社会,提倡诗歌创作中勇于创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革新进取精神。《日本国志》不仅及时地肯定、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而且将他对欧美国家的亲身观察糅合进去,用许多篇幅叙述西方所民主政体和全社会激发竞争的观念、制度和措施。他曾在致梁启超信中批评梁氏一度后退,主张“保存国粹”的保守倾向,相反地明确提出“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902年)。他还一再写诗著文,表达他坚信封建帝制必将被民主制度所代替,这一世界潮流不可阻挡:“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呜呼专制国,今既四千岁,岂谓及余身,竟能见国会。……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以上黄遵宪思想中的革新精神、相信世界大同必至等思想,都是由儒学优良传统培育滋养,并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得到锤炼,加上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而形成的。黄遵宪对当时传入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同样十分倾服,他曾致书严复,说《天演论》一书置案头,时时阅读,至为心折。在黄遵宪身上,一方面主张革新,看到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呼吁并实行吸收西方学说;另一方面,他认为孔子学说至高无上,千秋万世,孔子学说必大行于天下。在其晚年致梁启超另一封信中即有这样的表述:“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大哉孔子,包综万流,……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1902年,《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在这两种思想驱使下,他发愿要著成《演孔篇》,本已感到颇有把握,曾将计划写信告知梁启超,定了19篇的篇数。开列的书目,则包括培根、达尔文等西方著作。但直至1905年黄氏去世,这部本来以为很快能完成的著作却到底也没写出来。“演孔篇”,顾名思义,即要推演孔子的学说,也就是要在保持儒学体系的前提下,把西方社会学说和他本人置身于急剧变动的时代所得到的种种启悟都包插进去。事情必然是,欲求保存儒学之“体”,而又要纳入西方新学术之“用”,定不能成功;而适用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与近代社会要求变革、实行竞争和对外开放,并最后要实现民主政治的现实,也多的互相扞格之处:其中的历史启示值得深思。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龚自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新史学论文; 公羊传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东汉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西汉论文; 东周论文; 中世纪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