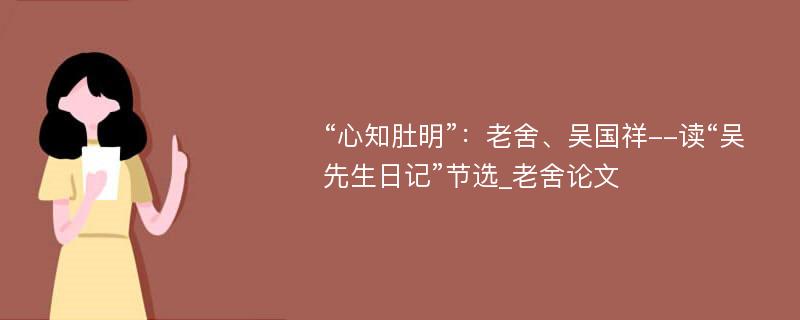
“知心同骨肉”:老舍与吴组缃——读《吴组缃先生日记摘抄》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骨肉论文,知心论文,日记论文,吴组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舍先生于1946年11月写的《三函“良友”·二》一文中,曾经动情地谈及自己对友谊的看法:
你看,我三岁丧父,家里连黄豆都没有过一升。现在,我已经四十六岁了,还活着呢。奇怪吗?一点也不!我有朋友!我有位好母亲,但是除了我的吃穿而外,她并没给我什么更大的帮助。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衣食,而没给我教育。她不识字。我的哥识字也不多。他自顾还不暇,哪有帮助弟弟的能力呢?我的一切差不多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是个没有舵的小舟。可是,这个小舟并没有被社会的恶浪打碎。他到处遇到慈善的手,把他推或拉到妥当的地方去。我有朋友!
“我有朋友!”这是刚刚度过八年艰苦抗战岁月的老舍先生,从心底里发出的激动声音,朋友间真挚的友谊,是老舍先生生命中的支柱。而吾师吴组缃先生就曾说过自己是“老舍很亲密的朋友之中的一个”。近日,读到学友方锡德摘抄的吴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日记,看到了前辈师长们友情交往的事迹,更加体会到吴先生自认是老舍先生“很亲密的朋友”的深刻含义。
老舍先生与吴先生相识于1933年冬北平的燕园郑振铎家中。1938年1月在武汉,得到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他们一起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两人均是文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老舍先生则被一致推举为总务组长,实际等于会长,总管大小会务,一直到抗战胜利。文协迁往重庆后,在陈家桥石板场居住时期,老舍先生与吴先生住处比较靠近,两人来往密切,友情日益加深。老舍先生说:“茅舍距组缃兄宅约七里,循田径行,小溪曲折,翠竹护岸,时呈幽趣,白鹤满林,即近友家矣。星期日,往往相访,日暮始别,以尽谈兴。”②
1942年6月22日老舍先生在《新民报晚刊》上载文幽默地写道: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
吴先生后来曾撰文说:“他有一篇关于我的小文,说他常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③果然如是,现今有日记可以佐证,1942年6月9日吴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老舍、何容两兄来,买来肉三斤,乃由北碚来。舒谈代我通行复旦教课事,陈子展、马宗融诸人均甚欢迎,唯闻现任训导长陈望道下年有任教务长说,须再向陈望道接洽得其同意。……
在当时,要买上三斤肉,真可谓“奢侈”了,朋友的如此盛情,当然足足地让吴先生全家打上了一次牙祭。牙祭是四川土话,意思是,平时总吃素,难得吃上一次荤时,就说是打牙祭了。说起吃肉,不能不提到老舍先生在1942年6月22至25日连续发表于《新民报晚刊》的幽默散文《四位先生》,其中第一篇即是《吴组缃先生的猪》。文章一开始就说: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老舍先生,用吴先生曾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就称许他的“难言的苦趣”,几笔真实朴素的勾勒,就幽默风趣地写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艰难岁月里默契于心的自嘲滋味与内在风采,至今读之令人含泪苦笑。
1942年7月7日吴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老舍先生送来的新作旧诗二首:
端午日大雨组缃邀饮冒雨而行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组缃入城为小江买新鞋节日大雨小江著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小江脚短泥三尺,初试新鞋来去忙。迎客门前叱小犬,学农室内种高粱。偷尝糖果佯观壁,偶发文思乱画墙。可惜阶台着雨滑,朝天卧仰满身浆。
在重庆艰难的岁月中,能有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相处在一起,是最珍贵的事。这两首诗中,老舍先生珍惜友谊之情溢于言表。几年来,吴先生与老舍先生往来频繁,这年的端午节到了,吴先生当然要邀请只身客居异乡的老舍先生来家里过节,不巧偏逢下大雨,老舍先生也不顾“风雨狂”,披着蓑笠,踏着泥泞,冒雨赴约。第二首诗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吴先生的小孩调皮可爱的稚趣,充分表现出老舍先生对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无限喜爱。第一首更表述了老舍先生对与吴先生情深义重的友谊的珍视,“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最为准确地概括出他们之间友谊的分量。这句知心朋友情同骨肉的话,吴先生则记了一辈子,晚年在怀念老舍先生时,仍在文章中举出此诗句。
虽然吴先生是南方人,长于安徽泾县的书香门第;老舍先生是北京旗人,从小生活在贫穷的大杂院里,两人的生活经历全然不同,年龄也相差九岁,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心志,对文学创作的喜好,以及为人耿介不阿的秉性,将他俩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也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1942年7月14日吴先生记:
老舍携一西瓜来,乃起。闲谈小说题材,托尔斯泰、柴霍甫、杜格涅夫等名家作品。我谈我之胸襟不宽大,近来时感生活无保障,精神受压迫,致此心愁烦,不能开舒,情绪长在一种郁结状态之中。故我近来作文,思路甚枯索,下笔甚濡滞,毫无一点从容自如,活泼超脱之趣。似此写的甚苦,活的尤苦。常见友辈熟人中处境苦于我者,而能满不在乎,照样做人豪放洒落,则不胜自愧。
朋友间深厚的情谊,使老舍急切地为吴先生谋求教职奔忙。上述6月9日日记中,吴先生就写到老舍先生已在帮他联系去复旦大学任教。因为此事未果,现在听到吴先生倾诉了内心的愁烦,老舍先生十分在意,回去后,立即又另与中央大学联系吴先生任教之事。不久,1942年7月25日吴先生记:
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署名伍叔傥者快函一通,称“从舒舍予先生得悉尊况,至谢,先生学术甚深,素所钦服,中央大学国文系兹拟聘先生为专任讲师,薪金二百六十元,津贴随时增损,有划一办法。课目自以近代文艺为范围,容再面详。如蒙俯允,无往感荷”。
第二日吴先生复函中书末还提到:“适晤舒舍予先生,届时舒兄亦愿同来一游也。”老舍先生为吴先生找工作,四处托人,倾力襄助,竭尽朋友之谊,实在难得。
吴先生与老舍先生的友谊日益加深,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就能够更多地相互帮助、相互批评。
1942年7月1日吴先生记:
舒来,谈我所作四文,劝以真名投《时事新报》《青光》栏。
1942年7月14日吴先生记:
我又劝舒须暂时放弃剧本写作,而以精力从事小说创作。舒颇表接受,乃谈其一长篇题材,乃其自传性质之题材。
既是知己文友,谈起创作来,才会无所不言,善意相劝。吴先生写的文章,老舍先生给他建议投稿之处;吴先生则恳挚地劝老舍先生,将精力全部用到小说创作上;老舍先生也真诚地说出了自己长期埋在心底的创作愿望:他一直想写一部以家族历史为背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此想法,鉴于民族历史的复杂情况,只有老舍先生的同族至交老友罗常培先生知道。
对于各自的作品,他们相互之间也是有赞美,有批评,无有顾忌。1942年7月20日吴先生记:
阅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满篇世故之谈,甚可读,唯文艺价值不大、不高。
1942年7月29日吴先生记:
再读老舍所作长篇《骆驼祥子》,入后写大杂院情形及贫民之命运,至为深刻动人。
当《骆驼祥子》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受到欢迎,吴先生还曾与冯玉祥将军谈及,1945年7月11日吴先生记:
……良久,我乃谈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在美畅销事,冯笑谓前数日读此书,日以继夜,竟使血压增高。乃谈其书中故事,曹先生逃逋一段……
1942年,吴先生在重庆出版了新著《鸭嘴涝》,老舍先生随即写出书评《读〈鸭嘴涝〉》,在1943年6月18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他说:
组缃先生有七八年没写小说了。《鸭嘴涝》的写成,不但令我个人高兴,就是全文艺界也都感到欣慰吧。
书名起的不好。“鸭嘴”太老实了。“涝”,谁知道是啥东西!
书,可是,写得真好!
全文不长,只有八百三十余字,可评及人物描写、情节安排、口语利用,均能面面俱到,字字准确,将创作的成功与不足一一指出,他说:“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他叫我们看到不少活生生的人,也看到一个活的社会”,“我真希望组缃先生能把鸭嘴涝居民的礼教与生活力量写得更深厚强烈一些,或者到然而一大转的时候——由怕战争到敢抗战,——才显着更自然而有力。”“专从文字上说,已足使我爱不释手!”“书的末尾似乎弱了一些”……朋友之间相互评论作品,好就说好,不作溢美之词;有欠缺处也不讳言,绝不隐瞒敷衍,这才是真正文艺批评的尊严与品格,两位先生为文坛留下了好的范例。
后来,《鸭嘴涝》欲再版,吴先生对此书名不满意,194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说:“思更一名,久久不得。”于是,与朋友们一起商议,1945年10月10日吴先生记:
思将书名更换,以群谓当以两字含示人民潜伏力量初初发动之意。我初想到乡间一种传说,谓地震为鳌鱼睁眼。盖神鳌为张天师降伏于地层之下,每睁眼睛,即地震。故欲以“神鳌睁眼了”为书名。以群说不佳。我乃又思得“惊蛰”二字正副以群之取义,以为甚妥。遂改名。……
……与周(钦岳)同行至文协,与老舍谈甚久,……老舍以为“惊蛰”之名不佳,为另取名曰“山洪”。山字甚佳,洪字则不恰当。然“惊蛰”二字实太泛。
最终,吴先生采纳老舍之意,改书名为“山洪”。1945年10月13日吴先生记:
晨起,作《山洪》新版题记。
这一书名就成了两位文学至交的小小纪念。
记得师从吴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时,曾经听吴先生讲过与老舍先生一起联诗的趣事;后来,吴先生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一文中,专门对两人一起同作人名诗的情景,做了精彩的表述:
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一次,老舍把膝头一拍,对我说:“大雨冼星海!看这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我对下句:“长虹穆木天。”他也说不差。一次我说:“你听这一句:‘梅雨周而复。’”他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这两联,以后凑成两首五律,并加了标题:
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冀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绀弩黄药眠。
《忆昔》
望道郭源新,卢焚苏雪林。烽白朗冀野,山草明霞村。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野望》
这里,吴先生描绘出的防空洞里与老舍先生一起联诗,生动而又传神。他俩几乎是以神来之笔,拿文艺界人的名字,拼凑出意境不同凡俗、对仗极为工整的佳句,进而又形成为相当讲究的律诗,充分显示了他们敏捷的睿智与深厚的文学功底,真令近五十年来看惯了成千上万的人以“解放”、“建国”、“跃进”、“卫东”起名字的我们叹服不已!时代不同了,师长们吟出的是蕴藏着千百年丰富传统的文化古韵,我辈流行的是一色的政治口号。
这种人名诗,“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是的,凡文艺界人士,不分党籍门派,大家的名字统统都可以写进诗里,显现出在一致抗日的目标下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当然,写作起来是颇费心思的,要将现成的人名拿来作近体诗,既要调遣工巧,讲究对仗、叶韵,还要讲究意境,没有一定的文学造诣,是凑不成的。以后,吴先生作得顺手,一共写了十首,题名为《与抗战有关》,在1943年4月4日《新蜀报》副刊《蜀道》398期上发表。其中老舍先生凑的诗句,均有标明。有意思的是王冶秋先生还加了评点:在《梵怨》中“常任侠圣陶”句后批曰:“酷似义山”;在《雨过》一首的“霞村荆有麟”句后批曰:“有晚唐风”;在《城望》中的老舍“胡风陈北鸥”句后批曰:“直追老杜”;在《野兴》中“素园陈瘦竹”句后批曰:“直是长吉句。”而《边解》一诗中的“老向黄庐隐”句后,则是吴先生自批曰:“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相当。”这些诗作、这些评语,真该算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独特的“诗话”了。
1944年4月抗日战争行将达到最后胜利阶段,“文协”成立届满六周年之际,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由邵力子牵头,共廿九人联名发起祝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吴先生作了七律人名诗一首为老舍祝贺:
戴望舒老向文炳,凡海十方杨振声。碧野长虹方玮德,青崖火雪明辉英。高歌曹聚仁薰宇,小默齐同金满城。子展洪深高植地,寿昌滕固蒋山青。
应当说这首七律当是众多人名诗中的佳作,尽管今天的我们已然不全知道其中一个一个的人名,但从字面上可以看出,通过词句的巧妙调遣,真正算得上是一首赞誉朋友的好诗。诗由郭沫若在天官府的祝贺小会上朗诵了出来,连老舍自己也“认为不但工巧,而且有章法,有内容,真象那么回子事,表示欣赏”。
祝贺会是4月17日召开的,十天后,为感谢吴先生对此事的热诚,老舍先生特将一首七律旧作书成条幅,赠吴先生: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深情每祝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村居杂吟之一
甲申初夏,在渝文友相约,为予贺学习文艺写作二十年,组缃兄倡议最力。廿年纸墨成就无多,既感且愧,因录旧作一律,略答勗励之厚意。四月廿七日于东川北碚之鼠肥斋 老舍
吴先生立即和诗一首:
步老舍《村居杂吟》原韵
莫惜年光争战老,好将笔墨寄诗魂。半生踪迹天何阔,一室低徊我自尊。远水遥山无限路,桂宫柏寝有多门。中庭明月间盈仄,露湿苍苔怀旧痕。
两位好友的唱和诗④,记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以文章为命、将笔墨寄诗魂,艰难而又崇高的心路历程。
在八年艰苦抗战中,老舍先生吃着平价米,忍着头昏,拼着命地写作,尽一切力量为文协工作,原本身强体壮的他,已变成为贫病交加的作家代表了。
1945年5月3日吴先生记:
三时许梅林自北碚迎老舍来。老舍头晕贫血,甚显苍老衰弱。
1945年7月2日吴先生记吴师母菽园带回老舍的信函:
菽园带来舒兄函,谓极想我谈天。
是的,老舍先生这时极想与知心好友袒露心声。1945年7月14日吴先生记:
昨日接老舍函,述稿费每月二万,连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万元,故甚窘迫,劝我俟抗战后再作职业作者之计。
1945年9月6日吴先生记:
菽园带来老舍、李紫翔兄及盛光勤函。老舍贫血复发,又患痔病痢,有“深盼死在这里免得再受罪”之语,竟阅,使人万分难过。
老舍先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拼着一条命,用一支笔,忍着贫困、苦难、疾病,完成了自己的气节,他说:“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⑤所以,吴组缃先生见到老舍先生复发旧病,万分难过,立即写信给叶以群,希望文协能为老舍先生筹集治病的款项。同时,又给胡絜青先生写信加以劝慰。1945年9月7日吴先生记:
昨日,书致以群函,请提出文协理事设法为老舍筹一笔款子,俾得从容治病。又致舒大嫂函,谓老舍不当严刻律己如此。力求生存健康,为最道德的行为,否则最不道德,文协款若到,务应收用,幸勿过于狷介。
很快,治病的款项就得到了解决,1945年9月11日吴先生记:
接梅林函,云援华会赠文协款赠老舍十五万元,又赠我三万,将信转舒大嫂。
吴先生与老舍先生这样一来一往,互相关切、互相帮助,在最艰难的年代,真可谓是可以生死相托的过命朋友。1945年12月16日吴先生记:
……又有信一束,老舍说美政府邀请他明年二月动身游美,家眷离川,托我照料。
当时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下江,国民党官员更是纷纷急于去上海、南京当接收大员,发国难财,出川的车票、船票、机票非常难买,拖家带口的难上加难,这种情况下,将家眷托人照料,非至亲好友,是不可能的。
1947年10月吴先生也随冯玉祥将军访美,与老舍先生在纽约相逢,老舍先生书七律一首赠吴先生:
自南自北自西东,大地山河火狱中。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晴雷一瞬青天死,弹雨经宵碧草空。若许桃源今尚在,也应铁马踏秋风。⑥
老舍先生喜欢旧体诗的含蕴丰富,能够通过56个汉字,寄托了极其厚重的内涵。两位老朋友在异国他乡见面,却仍十分惦记大洋彼岸的祖国,诗中含蓄而又分明地表达出“反内战,要和平”这一共同的呼声。
吴先生与老舍先生的友谊是终生的相助相善。1982年,老舍先生离开人世16年后,吴先生无限深切地怀念道:
从八年抗战到解放以后,我是老舍很亲密的朋友之中的一个。尤其在重庆的一段时间,我们同作“涸辙之鲋”,常常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游散,无话不谈。老舍比我大九岁,资历方面也是我的前辈。我本来称呼他“老舍先生”,他多次反对,说:“这不行,多生分!”他要我叫他“舍予兄”。他写给我的诗,有“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之句。老舍于公于私无不肺腑相见,一秉至诚。⑦
这是吴先生回顾当年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老舍先生同生死、共命运,建立的“知心同骨肉”般友谊,写下的心里话。在前辈师长们一生“于公于私无不肺腑相见,一秉至诚”之中,使我们无比感动的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耿介不阿的性格。经历了种种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吴先生虽屡遭批判,仍始终保持直言不讳、独立不倚的人格;老舍先生最后更是以自己的生命,悲壮地保持了人格的尊严。前辈师长们活得太不容易,无论是抗日战争年代的奉献,还是共和国时期的赤诚,作为中国人脊梁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华民族、为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树立了高山仰止、永远铭记于心的榜样。
注释:
①《吴组缃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
②《致××兄——1942年6月29日》,《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8页。
③《〈老舍幽默文集〉序》,《十月》1982年第5期。
④参见吴组缃:《同老舍的一次唱和》,1990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
⑤《致友人——1945年12月23日》,《老舍全集》第15卷,第670页。
⑥《赠吴组缃》,《老舍全集》第13卷,第678页。
⑦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十月》198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