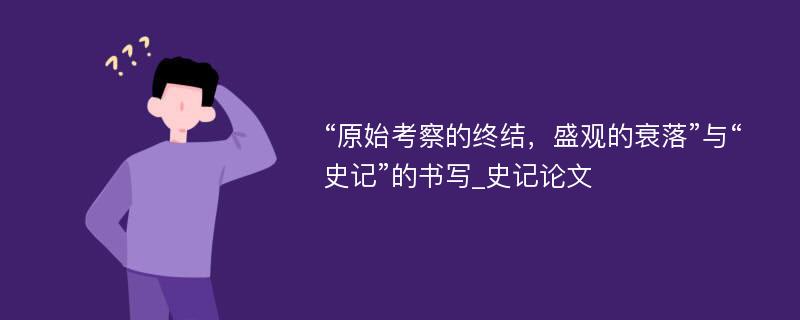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原始论文,见盛观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03X(2000)02-0029-06
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打虎跳,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然而,如何进行史述?如何把自己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寓于其中呢?这是大有讲究的事。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是持审慎的态度的,一方面他以历史文献为史述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为印证这些文献的可靠性,他又亲自深入实地进行考察。文献与实地考察之间的相互印证,使司马迁在信古与疑古之间作出了有机的选择,同时也使他的史述更具有真实可靠性。如他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待中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意向: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性。在史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应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取舍。二是疑古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印证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史述更加真实可信。
那么,是否可以说司马迁就不相信文献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司马迁曾明确地说《史记·殷本纪》系“采于《诗》、《书》”,又如他在《三代世表》中说:“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这就告诉我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十分尊重已有的文化成果的。
依据《史记》所使用的资料情况来看,司马迁最放心使用的资料为六经,进而言之,考信于六艺(六经)是司马迁进行史述撰写《史记》时的基本准则。这种格局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司马迁生活在儒学显于朝廷、定于一尊的年代,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六经”为先王政典的观念已牢固地树立在汉人的心目之中了。六经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早在孔子撰写《春秋》之前,除《春秋》之外,“五经”作为先王留下的政典,就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高的法典。这一意识的出现远远地早于儒家提出“六经”概念的时代,也就是说,“五经”最初并不是儒家的文化专利,儒家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取法于现成,通过认同原有的文化典章制度,在推崇孔子《春秋》的过程中才逐步把“六经”视为自己的文化专利的。
汉初,在人们的意识中,“五经”作为先王政典,与儒家学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新道家陆贾在推明治国之理的时候,就屡屡地在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1]。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的汉文帝,已开始在朝廷立一经博士,即《诗》学博士。这些情况均表明,“五经”显于朝廷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并没有依托于儒家。然而,在诸子中,没有一家像儒家那样重视文化传统和讲究家学,当诸子们出于自身学说和政治观念的原因,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而儒家却通过师传和家传把“六经”捧为了治道的至理。
进入汉代以后,大力提倡“六经”的主要是儒家,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已彻底地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了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当司马迁把“六经”视为先王政典的时候,其思想虽然不是完全地源于儒家,但他接受和认同儒家的观念则又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事实上,“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历史的传承中,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相比,儒家有更加关心“六经”治道之理的倾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其父之口明确地表达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的意愿。从这里出发,司马迁“论考之行事”时把握的原则,是以“六经”为原点为师法对象的。无庸讳言,司马迁认同“六经”不但是因为“六经”是当时最可信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因为“六经”阐述的统治大法早已成了研究治道之理的思想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大体上有三层:一是“六经”皆史,“六经”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郑重地表示他写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二是“继《春秋》”的所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包含着对《春秋》体制与格式的自觉学习。三是司马迁接受儒家的学说,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文化范本,他以孔子激励自己,以孔子第二自居,一直在把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看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史记·天官书》),周公与孔子之间的传递是讲文化传递间的统绪,千年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自视很高,他表示要像孔子写《春秋》那样来建立自己的功业,即写出一部可与《春秋》比肩的《史记》。这就告诉我们,《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专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巨著。
六经是先王政典,其内容是中国历代以来治国治民经验的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思想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的意识中,《史记》更重要的任务是承担着总结历史兴亡之理的责任,这样,“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司马迁提供了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它又给司马迁提供了研究天下兴亡大势的思想武库。可以说,司马迁对夏桀、商纣失国原因的探讨,对成汤、周武得天下事迹的关注,都表现出他对历史兴亡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
这种终极关怀是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相一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因之,司马迁在关注历史的同时,又把他的重点投向了风云谲起的秦汉之际。《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其中直接与秦末汉初事迹相关的有三十篇左右,秦末汉初历史人物的事迹不但在《史记》中所占的篇幅最多,而且也是司马迁刻意描绘的内容之一。仅以十二本纪为例,与秦末历史人物相关的篇幅就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四篇,这四篇本纪不但交待着秦失天下的原因和天下归汉的大势,而且还成功地承担着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
总结历史是为了现实,是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读《史记》则不难发现,秦汉历史人物一直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文以载道,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形式,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呢?它又是如何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的呢?我以为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司马迁热切地关注着秦得天下以后的风云变幻,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除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治理天下的事迹外,他还把重点放在了揭示秦推行暴政的方面,以此引出经验教训,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这一内容不仅仅表现在《秦始皇本纪》的写作中,还反映在《李斯列传》等相关的篇幅中。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为了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借此来充分地揭示秦推行暴政所带来的恶果。贾谊在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统一天下以后,没能及时地用仁义治理天下,是其丧失天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危民易与为非”,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其结果是把全国人民推入火坑;三是“雍蔽之伤国也”,秦二世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暴政,其结果是使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贾谊《过秦论》)。
在《史记》中,“太史公曰”虽然也时常引用别人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但长篇大段地引用却只有《过秦论》一例。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贾谊的观点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贾谊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初一些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贾谊写《过秦论》之前,先后有陆贾通过他的《新语》、贾山通过他的《至言》来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2],他们的观点对贾谊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贾谊写作《过秦论》虽然在传达着他像别人一样关心这一问题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他又对秦亡天下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乃至他的《过秦论》带有集陆贾、贾山观点之大成的意味。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这一点在贾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由于贾谊观点的深刻性,使司马迁在关心秦亡天下的原因时,对此予以了必要的关注。第二,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是为了探究长治久安的问题,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司马迁是史学家,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本着这一原则,司马迁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站在这一原则立场上,司马迁特别地注意观察秦汉间的变化大势,特别地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二,司马迁纵横笔墨描绘着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风貌。面对暴秦残酷的统治,陈涉与吴广商量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寥寥数语,不但深入细致地交待出陈涉扯旗造反的原因,而且透过他的言语还揭示着“天下苦秦久矣”的思想情绪。从陈涉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刘邦建汉再度统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大乱,各类人物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出身不同的人汇聚到反秦起义的潮流中,其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黥布年少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当刑而王”(《史记·黥布列传》)。等到他壮年的时候,果然受了黥刑,因此,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以为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在汇入秦末大起义的各类人物中,既有像陈涉这样出身寒微的贫苦农民,也有像刘邦这样的市井游民、黥布那样的罪犯,还有像项羽那样的旧贵族。总之,群雄乘乱而起,虽然起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反抗暴秦,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实现人生的价值。为此,司马迁满怀激情地描绘着“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为了肯定他们反抗暴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满怀着激情给这些人写下了传记,极有意义的是,司马迁敢于“成一家之言”,不但把项羽的事迹写入了“本纪”,把陈涉写入“世家”,而且还根据他对历史的理解,为那些入汉以后遭到翦除的异姓王作传,甚至掬出了一捧同情的泪水。这一切,都表现出司马迁敢于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纵横笔墨地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独到的看法,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是难以做得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那么,《史记》就不会具有深长的历史哲学的意味。
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则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性给六国人氏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创伤,而六国人氏不满暴秦的统治,则四处散布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谶语。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司马迁特别地关注六国反抗暴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巨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的时候,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精心的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所以宋代的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抄》)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注意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外,还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具体行为进行前后的观照,以此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历史必然性。如在写项羽勇气可嘉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项羽有勇无谋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项羽年轻时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万人敌”(兵书)。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因为这样的原因,使他不但有勇无谋,而且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终于导致失败。尽管如此,司马迁在关注秦末历史风云时,却又把他的笔墨重点放在了关注这些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方面。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同上)而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在寥寥数笔中便勾勒出他们最富有个性的特征。可以说,这些独具匠心的选择与司马迁关注人物的英雄传奇性是分不开的。然而,赞扬英雄的传奇性又是与司马迁以六经为评价人物的标准是相通的。寓论断于史述,司马迁在交待项羽失败的原因时,先写了他坑杀秦军二十万俘虏的事件,后又记载了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史记·项羽本纪》)的事情,这种失人心的做法便成了项羽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宋代的胡寅深得司马迁的心意,他在《诸史管见》中指出:“莫强于人心,而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术诈,不可能法持,不可以力夺也。项籍生于战国,习见白起坑赵卒,效而为之,唯杀是务。二十万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其四,《史记》是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历史著作,进而言之,是一部人学著作。但司马迁又把它视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政要,这样,它给司马迁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深入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把解决“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视为写作《史记》时的重要原则,在解决天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司马迁表现出对现有的宗教神学成果的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对天命的否定,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司马迁以“身死东城,尚不觉寤(悟)而不自责,过矣”之语进行了批判(《史记·项羽本纪》)。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并不是非天命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表现出信奉天命的意绪,尽管如此,他对人道的关心却是主要的。
在处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时,司马迁特别关心人物命运与社会构成的关系,经过他的有意识的选择,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深长的人生哲理意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际遇和奋斗往往与他所处的时势相关,一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和际遇,鉴于此,司马迁特别地注意从大处着眼来关心思考这一问题。如身经百战的李广,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建功封侯的伟业,因时势不同始终难以实现,乃致汉文帝都替他感慨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然而,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夏侯婴等人因赶上了好时光,虽然出身寒微,但自从随刘邦起兵以后,都建功封侯了。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赠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两厢对比,便可得知司马迁对人物进行历史的评价时,是以时势造英雄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这一观念与司马迁在追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是一致的,这样的内容贯穿于《史记》的始终,使《史记》表达出对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思想观念。
其五,《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录入《史记》的各个历史人物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因此,其故事也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质。如何把这些人物统一于“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之下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史记》中,司马迁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本纪编年,突出其纲要的地位,让其它四体围绕着这一编年的线索展开,进而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突出时代的氛围。本纪在《史记》中的编年意义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是《史记》中的纲目,它勾连着《史记》其它四体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发微着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马迁在结构《史记》时显示出来的整体意识。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从发微六经的旨意入手,并赋予十二本纪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经学思想。关于这点,我们从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中就可得知,五帝的事迹很多,但司马迁把他们得天下的事迹定位在以德服天下的方面。这种理想政治经司马迁的推明,进而演化为了“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路线。以君德推及到臣德,有德者昌的思想作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贯穿于世家和列传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无庸讳言的。
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最初的意义与宗教神学相关,上古时期有“同心同德,同姓同德”之说,自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后,德在去其宗教神学意味的时候便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德与仁的外化形式是仁与不仁的对峙,这一内容反映到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便成了司马迁进行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基本观点,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格外地关注秦汉之际的大势,试图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以思想观念的先行性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如对刘邦、项羽等人的评价可以说都在贯穿着这一思想原则。
上述五个方面,是司马迁关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握的一个基本尺度,它的一个总的思想方法是以六经为基本的出发点,由此贯穿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主题思想。考察历史是为了现实,因为这样的原因,《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在写法上却非常地注意略古详今的思想方法,这也是我们读《史记》时必须要注意的方面。
收稿日期:2000-01-09
标签: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历史人物评价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过秦论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项羽论文; 儒家论文; 秦始皇本纪论文; 西汉论文; 离骚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楚汉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