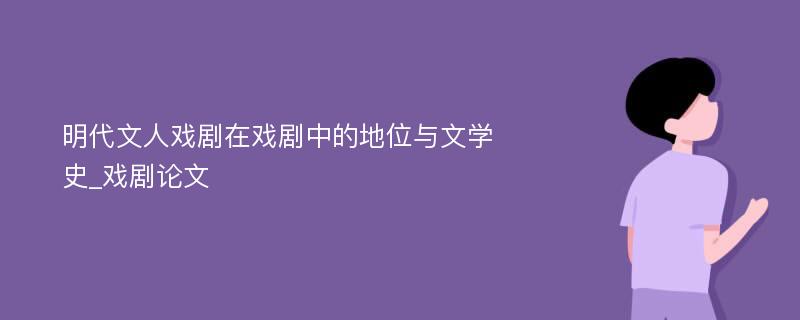
明代文人剧在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明代论文,文人论文,戏剧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名思义,文人剧是指明中叶后由中下层文人创作并反映文人审美趣味之短杂剧,因体制上吸取传奇的因素,呈现南北曲传统交合之趋势,故又称南杂剧,亦称南剧。长期以来,这方面系统研究薄弱。本文拟就现有资料,结合舞台特点,从宏观上对有关问题作一点探索。
一、文人剧的非功利性使其具有某种革新实验的性质
严格说来,远离世俗剧场的实验戏剧是近代戏剧教育发展以后的产物,而处于公元十五、十六世纪的我国明代文人剧具有某种实验性是由于其作家成分、剧场性质等特殊条件作用下形成的。
考察一下明代杂剧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以明英宗正统年间朱有燉、朱权先后去世为契机,明杂剧结束了由御用文人、宫廷艺人和藩王作家独擅的局面,尽管这以后直到明隆庆间尚有辽藩朱宪栉的杂剧创作,但那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看到,从弘治年间的王九思、康海开始,经过杨慎、李开先,直到徐渭、汪道昆以至整个明中后期的文人剧作家,都显示了他们崭新的特色。
从作家成分看,明代中后期文人剧作家和元代及明初都不同,他们大多数是一肚皮牢骚的失意文人。但这种失意又和在元代民族歧视下汉族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之失意不同,而是在科场、官场中不断碰壁后愤世嫉俗的失意。根据现有资料,目前有生平可考的五十多位明代文人剧作家中,就有半数以上没有进入仕途,包括徐谓、梁辰鱼、孟称舜、吕天成、徐复祚这样一些戏曲名家,他们大都以布衣终其一生。而即使侥幸进入官场的那部分人,也大多宦途险恶,如康海、王九思因齐瑾案受牵连;杨慎因忤“圣意”而下狱后充军,陈沂因触犯大学士张璁而终身颠沛流离;李开先则为得罪权相夏言,叶宪祖则因结怨阉党魏忠贤先后遭削籍;王衡则因父亲的缘故大受攻击,如此等等,都不能不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这就是对人生和现实所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明代中后期文人剧作家,一般出生于所谓“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其政治经济地位固然比不上藩府亲王,但也远非元代那些沦为与乞丐、艺伎为伍的落魄儒士可比。就其接触社会面和具有独特个性来说,也和明初宫廷剧作家不同,作为创作主体,借用一下马斯洛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低层次的生存、安全和归属需求已不再是他们创作心理结构中的自然趋向了,决定其创作动机的是强烈地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就是说,在他们那儿,从事戏剧活动已很少带有功利的目的,仕途方面的失意促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戏剧创作,为的是获得情绪上的渲泄和心理上的平衡。如果说政治上他们怀才不遇的话,那么戏剧活动则是他施展这种“才”的适宜场所。从史的角度看,这种非功利性是此前任何时代剧作家所不具备的。
我们知道,杂剧自从金元间形成以来,整个元代都是在市俗社会中度过的。商业性质的民间勾栏、庙会是它大显身手的理想舞台,与之相适应的是深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下层文人、勾栏艺人和广大市民及乡俗观众,他们共同的感情渲泄要求和审美意趣构成了元代杂剧创作演出及整个剧场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剧作家就必须使自己的情绪和市俗剧场息息相关,惟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情感共鸣的艺术氛围中也达到某种商业性的目的。
明初宫廷杂剧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固然,御用文人、宫廷艺人和藩府亲王所活动的宫廷剧场并不带有什么商业色彩,但他们所面临的接受主体,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宫廷皇族、达官贵人。这个剧场所要求剧作家的,不过是承应供消遣而已,也许还包括某些教化作用。在作家本身,不仅御用文人、宫廷艺人的创作纯粹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著书都为稻粱谋”,即在藩王作家那儿,固然已脱离了纯粹以此营生的需求层次,但占优势的也不过是为了消遣或者是出于安全需求,即向最高统治者表明心迹以保全自己不被猜忌。总之,和此时期文人剧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能动范围是很小的。
与文人剧作家创作的非功利性相适应,明代中后期即盛行起文人家庭小剧场,或者可以说,家庭小剧场促成了非功利性文人剧作的最后形成。
从戏曲史角度看,家庭小剧场是元代勾栏、瓦舍等北杂剧舞台衰落后的产物。如果说元代杂剧、散曲和野史笔记以及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文物给我们展示了元杂剧在勾栏、庙会等世俗舞台演出状况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在明初北杂剧已很少出现了。当然,北杂剧进入宫廷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但在世俗下层却不能为私家剧场所取代,并且随着宫廷北杂剧的迅速衰落而使得这种家庭小剧场成为杂剧演出新的寄生地。
家庭小剧场较早表现形式为“家乐”。明人陈龙正在其《几亭全集·政书》中记载:“每见士大夫居家无事,搜买儿童,教习讴歌,称为家乐。”这当是元末杨梓之流“广蓄优伎”的继续。然此时已经普遍,成了杂剧创作和演出新的基地。另外,明初社会变革也造成了许多原属宫廷藩府的乐工流落民间,如明人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记载南教坊顿仁、傅寿等人皆有“暮年流落”之经历。又,隆庆二年辽王朱宪栉以罪废为庶人,钱希言“《辽邸纪闻》即记载辽亡之后,宫廷艺人流落民间,以北曲为生的事。这些乐工、艺人流落民间,客观上促成了私家剧场的发展。
作为北杂剧新寄生地的这种小剧场一度很普遍。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这样记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当然,这种演出尽管很普遍,但规模并不大,一般不出文人士大夫宅院的圈子。有时竟是文人自编自导,如李开先在其院本序中所称:“有时取玩,或命童子扮之,以代百尺扫愁之帚”(《李开先集》第857页),到后来这种小剧场扩展了, 也有在城乡祭神庙会上演出的。如李逢时《酒懂》中的“小青挑灯看《牡丹亭》”杂剧;所演的也不仅限于北杂剧,如陈与郊《袁氏义犬》中的“没奈何”就是个弋阳腔杂剧,此前朱有燉《吕洞宾花月神会》中的“献香添寿”就是个院本。这些演出大多是一场了事。这种规模短小、选择自由的演出场所,既非宋元以来面向市俗大众的勾栏,又非明初皇家藩府的宫廷内苑,也使得气派宏伟的传奇在此大受限制,它们是名符其实的“小剧场”。这些小剧场的出现在戏曲史上很值得重视。正是它们迎合了此时期文人剧作家的非功利性创作倾向,抑或可以说,也只有在这种私家小剧场中,非功利性的文人剧才有着产生与发展之可能。因为这里的创作和组织演出一般都是自己的事,如清人焦循所记:“一词脱稿,即令伶人习之,刻日呈伎”(《剧说》卷五)。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剧作家既非象元杂剧作家那样要照顾到商业性的“票房价值”,亦非如明初宫廷作家那样要考虑迎合贵族观众的喜怒哀乐,就是说,他们几乎用不着考虑能否上演,因而也就有可能摆脱传统戏所特有的过分迎合观众爱好之消极影响而始终保持一种类似革新实验的性质。由于此时期文人剧作家大多数对戏剧对文学既有浓厚兴趣又非外行,因而这里所说的革新与实验也就具有了实在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看得更清楚。
二、文人剧在传统两种体制结构间探索某种结合之可能性
我国古代戏剧体制,自从宋元间成熟以来,即形成了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结构类型,被王国维恰当称为“一代之文学”的元杂剧,以其独创的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化,奠定了我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基础,她在戏曲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元杂剧毕竟是刚从宋金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等多种形式中脱胎而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说唱文学的痕迹。一人主唱的乐曲安排虽有助于主要人物塑造,但千篇一律,则未免单调,也不利于多层次地塑造人物形象;四折一楔子的戏剧体制尽管可以使得结构谨严,而且也确实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剧,但发展到后来,亦感束缚作家的手脚;从文学角度讲,亦难以展开矛盾冲突,“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臧晋叔《元曲选序》),难以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在元代及明初,已有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贾仲名、朱有燉等作家部分地作了突破,可见这种封闭式结构体制的变革已势在必然。
至于宋代南戏以及后来的明代传奇,采用了开放式结构类型,在布局安排、角色分配和乐调选择多方面皆有较大的伸缩性,剧本容量也大,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多层次的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戏剧冲突,表现多样化的生活内容,但也因此带来了剧本冗长、拖沓、头绪纷繁等毛病。吴梅指出:“明代传奇,率以四十出为度,少者亦三十出,拖沓泛滥,颇多疵病,即玉茗之〈还魂〉,且有可议之处”(《中国戏曲概论·清总论》),明代戏曲家兼戏曲理论家李渔即痛感于这种戏剧体制在演出中的弊病,提出要创造一种“短而有尾”的新型戏剧样式。他说:“戏之好者必长,又不宜草草完事,势必阐扬志趣,摹拟审情,非达旦不能告阕,然求其可达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于来朝之有事,即限于此际之欲眠,往往半部即行,使佳话截然而止,予宁短而有尾”(《闲情偶寄》卷四)。他这里主要就戏剧体制的长短而言的,还没有涉及诸如头绪繁杂、内容拖沓以及完全不必要的场次人物等问题,但仅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改革这种长篇巨制的迫切性。于是,南杂剧等也就应运而生了。
从字面上看,南杂剧似乎就是用南曲演唱的杂剧,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今存最早提出南杂剧概念的明人胡文焕所编《群音类选》一书,即于“南之杂剧”栏目下收有程士廉用南北合套填制的《戴王雪访》和徐谓用北曲填制的《玉禅师》。另外,明人吕天成《曲品》也于“不作传奇而作南剧者”题下将徐渭、汪道昆的作品列出并大加赞赏。而我们知道,徐谓《四声猿》中除《女状元》以外皆以北曲填制,汪道昆《大雅堂四种》中《五湖游》一剧也是完全由北曲填制而成。由此可见,当时的南杂剧概念实际上即是包括南曲、北曲和南北合套曲在内的文人剧作,范围比我们理解的要大得多。
徐谓、汪道昆的剧作是此时期文人剧也是南杂剧在创作上臻于成熟的标志。从体制上看,如果说在他们之前王九思、李开先等人还只是从宋金杂剧院本的短小体制启发中寻找变革的参照系,在北剧和南曲之间进行更为大胆的结合。北曲南化、南曲北化的趋已经突破了北杂剧的基本构架,和前期贾仲明、朱有燉偶然采用一点南曲作点缀已是有了质的区别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体制变革是建立在对前人创作参照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显得更成熟,覆盖面也大。
以下是从总体角度对现存文人南杂剧体制作一个概略的统计:
折(出)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用曲
南曲 36
5
5 28
2
7
8 14
2
0
0
北曲 44
1
4 39
5
1
1
1
0
0
0
南北合套 23
3
2 16
5 10
3
5
2
1
1
从表中可以看出,明代的文人剧作,大都突破了传统上四折一楔子的固定格局,采用了开放式结构类型,剧本的长短比较自由,短的可以为一折、两折,长一点的可达到十折、十一折,音乐体制也比较随便,有南曲,有北曲,还有数量可观的南北合套曲。显然传统的规范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其中那不到总数六分之一的北四折剧本,详细考察起来,也是远非旧物了。他们的开场形式、角度和科白称谓等方面皆一如南制,显然是熟悉南曲体制的剧作家对传统北曲体制一种自觉的吸收,它正是此时期文人剧作家突破传统规范而自由选择的结果。
从结构类型上看,此时期文人剧的最大特点是对传统上锁闭和开放两种结构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就是说,虽然它在宏观上属于开放式体制,但在微观上却显然还保持着锁闭式结构的某些特点。
分析具体作品我们发现,此时期文人剧一般只截取最能表现作者创作意图的生活片断,情节比较整一,结构也较紧凑,具有篇幅小而容量大的特点,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家采用了类似物理学中的“蓄势”的方法,注意压缩感情,选择情感处于饱和状态的瞬间加以表现,使它产生爆炸力,从而收到强烈的戏剧效果。剧本出场人物不多,情节简单而感情内涵丰富。
例如陈如郊的《文姬入塞》,仅截取蔡文姬得知汉朝派人来接她回归消息前后的心理变化和语言行动,在实际生活中也多不过几十分钟(剧本时间安排也是如此),但她却经历了也许是一生中最矛盾最痛苦的决择时刻。这就是多年想回家乡的愿望突如其来得以实现的激动和同时又舍不得抛离亲生儿女的痛苦。这样,长期流落他乡迫切向往回归的蔡文姬和面临与亲生子女生离死别的蔡文姬就构成了剧中女主角感情上的尖锐矛盾,这也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作为戏剧冲突主要特征的心理冲突和情感危机的焦点。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情感的凝聚和爆发点。剧作家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能在短短一折的篇幅中展示了最大容量的感情内涵,收到了极强烈的悲剧效果,前人称此剧令人“哽咽不能读竟”(《盛明杂剧》此剧眉批),正是剧本的艺术力量所在。
又如沈自征的《霸亭秋》,仅仅抓住下第落魄而归的穷秀才杜默刚刚到达项羽庙的极短时机,因为此时此地这位抒情主角自然而然地触景生情:见像生怜,继而又怜自己,恰恰断肠人哭“断肠神”,一直郁积着的悲愤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情节不多但却感人至深,而且在时间地点的安排上也是高度紧凑和统一的,真正是“一次动作的戏”(One Act Play)。
类似的剧作,如徐渭的《狂鼓史》、汪道昆的《洛水悲》、《五湖游》、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沈自征的《簪花髻》等,它们或是倾诉悲愤之感,或是寄寓离世之情,都是意态浓重,且都是在精炼的结构形式中完成的,收到了许多宏篇巨制所不能达到的戏剧效果。
其次,此时期文人剧的锁闭式结构特点还表现在它能将复杂的情节压缩、集中,使之高度凝炼,在短小精悍的形式中包含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同样收到良好的戏剧效果。
例如徐渭的《雌木兰》一剧,剧本先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暗中购置刀马器械,改换服色;次写木兰与父母弟妹家人道别;接下又写木兰的军旅生活,身经百战,归授尚书郎;最后又写她返乡与家人团聚,并和王郎成亲。前后时间跨度十多年,地点从家庭到前线,又从前线到宫廷,再到家中,中经千山万壑,变化多端。以此题材,写一部连台大戏亦未尝不可,然而作者将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集中在短短的两出戏中,线索分明,毫不拖泥带水,加上我国古代戏曲特有的虚拟性原则,使得剧情中地点多变丝毫不会使人眼花缭乱,而一位机智勇敢的女英雄形象即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和观众的眼前。前人评此剧“苍凉慷慨”并称其“曲尽老景”(《盛明杂剧》卷七此剧题评),这些看法确有见地。
明中后期文人剧类似这种结构手法的作品还很多,如王衡的《郁轮袍》,徐渭的《女状元》、《翠乡梦》,叶宪祖的《骂座记》、《易水寒》,孟称舜的《死里逃生》、《桃花人面》等等。这些剧作所采用的题材大都比较复杂,容易造成头绪纷繁、结构拖沓的毛病。但文人剧作家运用起来,大多得心应手、干脆利索,很少有多余的场次和不必要的人物,而这些弊病在明清传奇中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手如汤显祖、洪升也难以避免。明文人剧作家在结构安排上的这些特点的确值得我们重视。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文人剧在结构中保存的这些锁闭式特点并没有形成对作家创作的束缚。在他们那里,剧本体制起码在观念上是没有固定框子的,一切安排都随着自己的取材而定。当然,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来看,此时期文人剧在体制上所决定的开放式结构类型也没有妨碍作家尽可能使他们的戏剧结构紧凑化。正如苏联当代戏剧理论家霍洛道夫评论欧洲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时所说,他“虽然不承认任何框子,但总是在当时每一个场合下,始终不逾地遵循戏剧行动的最大限度的凝缩这个原则的。”(《戏剧结构》第40页),这正是剧作家结构艺术成熟的标志。明代文人剧中这种带有锁闭式特点的开放式结构类型,实际上即是作家试图在传统两种结构类型之间探索某种结合之可能性,和他们综合北剧南曲特点相适应,无疑是此时期文人剧作家在创作中大胆革新实验的直接成果。
三、文人剧开了独幕剧、剧体诗的先河
前面我们着重谈了文人剧本体制结构方面实验性的探索,但实际上这种探索远不止此。我们在分析文人剧的结构特点时曾着重提到了作者善于把握人物情感的凝聚和爆发点,因而能收到良好的戏剧效果。实际上文人剧的这些特点有许多是体现在单折戏上面,研究明代文人剧不能不注意到它们中数量可观的单折戏形式。
单折戏,顾名思义,即为只有一折的短剧,与西方近代的独幕剧相似,只是中国古代戏曲舞台都没有设幕,故称之为单折戏。
从戏曲史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单折戏当始于唐参军戏和宋金杂剧院本或者更早一点,但那些大都是滑稽调笑的歌舞杂耍,没有完整的戏剧机制,且无剧本传世。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单折戏本子当为署名王生的《围棋闯局》(注:此剧作者历来有争议,较早的明金台刻《西厢记》和闵遇五刻《西厢记》都把它作为附录,署名“晚进王生”,《录鬼薄续编》则记明初詹时雨有《补西厢奕棋》,从暖红室刊凌刻《西厢凡例》直到今人邵曾祺,皆认詹作即《围棋闯局》)。描写莺莺、红娘正在下棋,张生逾墙偷看的故事。此剧一直作为《西厢记》的附录保存,但在同时代剧作中,这种形式却没有再出现。而明代文人剧中的单折式,从王九思的《中山狼》开始,直至明末都不断有人创作和演出,在清代也有较大的影响。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统计明代这类单折戏约有一百种,现存五十八种,差不多占了此时期文人剧现存剧本的一半。在它们中间,大多数是一折一场,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太和记》、《狂鼓史》、《洛水悲》、《高唐梦》、《五湖游》、《洛冰丝》等;也有一折两场的,如前面提到过的《昭君出塞》、《文姬入塞》、《霸亭秋》等,也有少数一折三场的,如杨之炯《天台奇遇》等。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单折戏中的大多数剧作选题严肃,线索分明,结构紧凑,自始至终为一个完整的行动所贯穿,而且还有一定的广度和长度,自成一整体。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们即可被看作世界上最早的独幕剧。
我们知道,世界戏剧史上,欧洲剧场到十八世纪才出现类似于独幕剧的雏形——“尾戏”( After- Piece )和“开场戏”( Curtain-raiser),而它们“大多数是滑稽剧、闹剧”。“这些歌舞杂耍, 只是为了消磨时间,逗观众笑乐,几乎没有严肃的社会意义”(施蜇存、海岑编《外国独幕剧选序》)。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小剧场运动中,欧洲独幕剧才脱离了尾戏和开场戏的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我国的宋金杂剧院本且不论,即以明代文人剧中的单折戏与之相比,也比西方早了三百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剧作家在戏剧形式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除了独幕剧(单折戏)以外,明代文人剧在体制形式方面值得重视的还有剧诗,它在文学体裁的发展中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
对现存剧本考察表明,相当一部分文人剧作家都把传统诗文的创作手法引入了剧本创作之中,以内心情绪外化的形式表示了对北杂剧传统规范的蔑视,加强了作品的主观抒情效果,客观上表现为某种剧诗风格的美学追求。
汪道昆是文人剧中剧诗创作的代表,他的《大雅堂乐府》四剧大多表现了含蓄蕴藉的神韵境界:
〔高阳台〕泽畔招魂,累臣何外悲咽,江风初动青萍末,断肠处洞庭飞叶。
(《群音类选》卷二十六)
这里融合了楚辞和宋词中的某些意境,也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某些情绪。
又如:
〔五更转〕意未申,神先怆,东流逝水长。晨风愿送,愿送人俱往。落日泣关,掀天风浪,丹凤楼、乌鹊桥,应无望。梦魂为断,不断春闺想。
(同上)
这些是心中美的事物遭到毁灭后主人公的倾诉,也是作者作为封建士子在那个时代的情绪流露。这种情绪的流露在当时失意文人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受汪道昆影响的此时期文人剧作家中有程士廉、许潮、杨之炯、徐野君等人,其中对程士廉的影响为最直接。程的《小雅堂乐府》四剧即有意相对于汪的《大雅堂乐府》而作,系按四季连缀而成,多以历史上文人逸事为题材,与其说是剧,不如说是诗。如:
〔簇玉林〕看天汉,云影移,望长安、人未归,玉绳遥到弘无际,秋高谁鼓南溟翼?漫追谁、厌厌夜饮,四美二难齐。
(《韩陶月宴》)
许潮《太和记》中(注:此系一杂剧集,按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由二十四个短剧构成 ,今存十三,略过半数。关于作者,有传为杨慎所作者,今据吕天成《曲品》改正之)的《兰亭会》、《赤壁游》、《武陵春》 、《午日吟》、《同甲会》诸剧,都是这种剧诗创作的典范:
〔前腔〕青嶂吐蟾光,云汉澄江一练长,那更凄凄荻韵,脉脉蘅香,对皓彩人在,冰壶溯流光,船行天上。
(《赤壁游》)
于闲适中见淡淡思绪,似离世而未离世,其中也有着对世事的寄托。
在此时期这类文人剧中,不仅人物性格、心理刻划已经淡化,即便前期宫廷杂剧所热衷追求的情节完整、场面热闹也已退化,或仅仅成为连缀诗句(曲辞)的一种手段。当然,这里的抒情方式也非徐渭等人剧作强烈的讽刺和热情赞颂,整个情感也都大大平淡,或仅转化为一些若有若无、渺渺茫茫的意念寄托。此类意境,在徐野君的《络冰丝》、杨之炯的《天台奇遇》和车任远的《蕉鹿梦》等剧中都可以见到。
当然,诗意盎然的曲辞在同时期传奇汤显祖的作品和前代元杂剧王实甫等人的剧作中也不乏见,但那是舞台上演剧中的一部分,即整体上的诗剧而非剧诗。如果从广义上的剧诗概念来理解的话,它们是“剧中诗”而非“剧体诗”,而只有后者才构成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剧诗,如歌德的《浮士德》和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等作品就是这样。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曲论界过多地强调戏曲和诗人之间的区别,如清人徐大椿所谓有“全与诗词各别”、“非文人学士自吟自咏之作也”(《乐府传声》),则完全忽视了我国戏曲入明后即以演出和诵读并重的事实,而将戏曲史中这部分具有独立意味的剧诗一概归入案头之曲,进而加以贬斥和冷落,显然是不明智的。今天看来,明代文人剧中的这些剧诗,恰恰是作家对文学史中新形式的一种开创,他们的剧体诗创作手法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即在今天的戏剧和文学界,我们仍然面临着分清诗剧和剧诗,继而摆正它们(特别是狭义的剧诗)在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