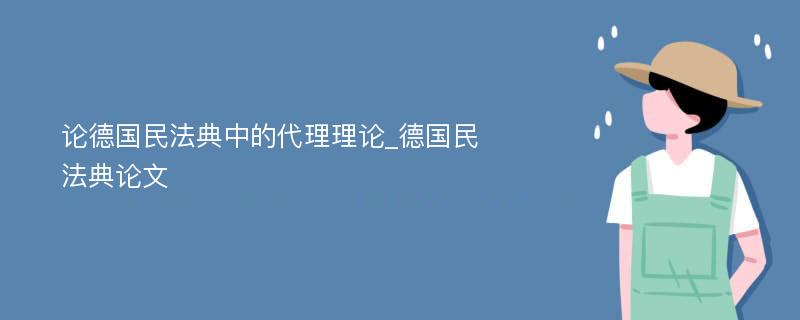
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典论文,德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间接的自我行为还是效力及于他人的行为?
根据《德国民法典》(以下所引法律条文,如无特别注明,都是指《德国民法典》——译者注)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发出的意思表示,效力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然而法典的这一规定并没有澄清相关的法律问题。例如,究竟是谁发出了意思表示?是代理人还是被代理人?谁有权撤回意思表示,谁又有权撤销意思表示?代理人是否必须具备行为能力?在意思表示有瑕疵时,应以谁的意思瑕疵为准?在根据权利表见取得权利的情况下,谁必须是善意的?是被代理人,还是代理人,抑或两者都必须是善意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清晰的代理理论。
1.几种可以考虑的思路
在制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及相继条款以前,学术界对于如何从理论上解释通过代理人从事私法上法律行为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议。以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为着眼点,可以考虑三种可能的方案。
(1)意思表示不是由被代理人,而是由代理人发出的,但是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直接及于被代理人(效力及于他人的意思表示说);
(2)被代理人自己并不发出意思表示,但是法律拟制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是由被代理人自己发出的(意思表示之拟制说);
(3)被代理人自己借助于他的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表示媒介说)。
第二种解释方案和第三种解释方案非常接近,但最终获得胜利的是第一种思路。人们称这种方案为代表说(Repraesentationstheorie),此说主张在代理人自己的法律行为意思与以被代理人名义发出的表示之间作出区分。代表说一般被描述如下:“从事法律行为的人仅仅是代理人,而不是被代理人。在意思表示中,反映了代理人的法律行为意思,只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承受。”(注: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帕兰特/海因利希斯(Palandt/Heinrichs):《德国民法典评注》,1998年第57版,第164条之前的引言,边号2以及第166条边号1。)
今天,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持这种代表说。但是,人们对法律行为学说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方面的分歧又反映在对代理制度的理论解释上。因此,有必要对通行的代表说作出批评。
2.本人说与代表说之间的历史争端
根据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意思说,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表示之所以会对表意人产生效力,是因为表意人自己形成了作为意思表示基础的效果意思。而某人能够为他人从事法律行为的想法,与这一“个人意思说”(Personales Willensdogma)似乎是不相吻合的。不过,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代理就已为一个劳动分工型的经济制度所必需,所以要努力避免出现“意思上的代理”(Stellvertretungim Willen)这种概念上错误的提法。当时两种对立的代理理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维系私法自治的原则。不过两种理论都半途而废,未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本人说(注:此说由萨维尼(Carl Friedrich von Savigny)创立,见其著作《债法作为今日罗马法之部分》,1853年,第二卷,第57章,第59页。)将代理人的意思排除在外,把代理人理解为被代理人私法自治意思的载体,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且以被代理人的计算从事法律行为的,只有被代理人才想在法律上从事代理人行为。
与本人说相反,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代表说(注:此说由布林兹(Brinz)创立,见《潘德克吞教科书》第四卷,1892年第2版,第577章,第333页以及第581章,第360页以下。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潘德克吞法教科书》第一卷,1879年第5版,第73章,第193页)。当然,他们都没有使用今天才通行的“代表”(Repraesentation)这一概念。)则认为,只有代理人才形成其法律行为上的意思。代理人不过是把以他人名义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转移给被代理人而已。无论是法律行为上的代理权,还是法定的代理权,都肇源于被代理人,由此被代理人方面的私法自治原则能够得以维护。
这也即是说,根据本人说,被代理人要想从事法律行为。而根据代表说,代理人要想从事法律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由代理人为被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
在这两种学说(注:媒介说(Vermittlungstheorie)试图走出一条第三条道路。此说认为,“并非代理人单独地,也并非被代理人单独地和排它地在法律上从事行为,而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一起从事行为,他们都是法律行为的生产者”(米特埃斯(Mitteis)言,《代理学说》,1885年,第110页;德恩堡(Demburg)也持此说,见《潘德克吞》第一卷,1892年第3版,第117章)。此说的正确之处是,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在法律上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不过媒介说无法解释法定代理。在法定代理中,被代理人自己没有行为能力。而人们应该把代理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参见下文三3。)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只存在对表示的代理,而不存在对意思的代理。因此,两种学说都试图消除对意思的代理。这种对意思和表示进行区分的做法,依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弗卢姆(Flume)的法律行为学说(注:参见下文三4。)中。
二、意思自由与意思归属
个人意思说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由于意思表示的发出通常都构成一项社会交际行为,因此法典把交易保护这一方面补充了进去。法律应当考虑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利益。这一点反映在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的原则中。一项意思表示,并非在表意人所想赋予的意义上发生效力,而是在受领人所理解的意义上发生效力。此即为客观表示价值说。如果一项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已进入受领人的控制领域,而且受领人在通常情形下可以知悉其内容,则受领人就知道了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到达原则)。
法律行为上的私法自治制度,乃基于对社会利益的平衡。表意人之所欲,以其可能者为限(意思实现);社会之典型期待,以其必要者为限(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
三、代理人行为在法律上被归属为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归属作为共同的事实构成
民法上的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对代理理论起着反作用。如果法律行为上的意思不仅可以自身形成,而且还可以在法律上进行归属,那么对意思上的代理提出的主要异议(即违反了个人意思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各种古老的代理学说是否已经过时了。特别是代表说还有什么用处?此说细加探究,就会发现其异常复杂。它没有回答“代表”的具体所指,也没有指出“代表”概念与“代理”概念之间的区别。此外,代表所指向的对象也是不明确的。究竟是仅指在意思上代表本人(注:参见舒尔茨/封·拉索尔克斯(Schultze/von Lasaulx):《德国民法典》,第一卷,1967年第10版,第164条之前,边号9。)呢,还是也指在表示上代表本人?代理人究竟是仅仅在意思上“代表”本人呢?还是代理人在表示上“代理”本人?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虽然采纳了代表说的思路(注:《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6页:“草案采纳第一种看法,行为是代理人的行为;只是行为的后果指向被代理人。),但是“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进入法典。有人认为:“代表原则”(注:Repraesentationsprinzip。使用这一概念的有帕兰特/海因利希斯(Palandt/Heinrichs):《德国民法典评注》,1998年第57版,第164条之前的引言,边号2;施陶丁格/狄尔希尔(Staudinger/Dilcher):《德国民法典评注》,1979年第12版,第164条之前,边号32。)反映在法律的内容中。不过这一点殊成疑问。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这条代理法方面的重要规定,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注:有关《德国民法典》第166条之规定,参见下文三2。)该句规定“某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发出意思表示”。这说明,代理人从一开始就说明,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才是本人。也正因为这样,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才会在法律交易中“直接为被代理人的利益和对被代理人的不利益产生效力”(第164条第1款第2句)。既然一项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亦即在其所有的要素方面,并非完全由本人决定,它何以能直接对本人产生效力?本人要想成为合同当事人一方,难道不是非得由他最后发出意思表示才行吗?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不是要经过被代理人自始至终的亲自首肯才合法吗?而无论是授予代理人的代理权,还是代理人依法享有的代理权,抑或是其依职权享有的代理权,难道不仅仅是一种旨在将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转移给被代理人的法律技术上的手段而已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不一定非得在坚持二分思想(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被代理人承受法律后果)的代表说的意思上作出解释。毋宁说,从本人说角度来解释164条第1款第1句(在代理行为中,是由本人自己在发出意思表示),也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
从本人说出发来解释,则被代理人就不仅仅是承受代理人意思表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的人。被代理人也不是被视为是他自己发出了意思表示一样。(注:关于此种表示拟制的不必要性,参见下文三2。)毋宁说,被代理人在法律交易中自己借助于他的代理人发出了意思表示。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作为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据此原则,权利主体既可以亲自发出意思表示,也可以让代理人来发出意思表示。
代理人虽然发出了一定内容的东西,但是由于他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的表示行为对他来说并不是意思表示。只有在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针对于自己发出意思表示时,才存在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行为。而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从事的恰恰不是这种行为。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明显地是针对着另一个人从事行为,代理人不过是被代理人的表示辅助人而已。
2.与给付媒介的比较
如上文所叙述的代理法上的表示辅助行为,对于私法制度而言并不陌生。给付媒介可以表明这一点。(注:参见博伊庭(Beuthien)文,载《法学家报》1968年,第323页以下。)接受债务人指示的人,相对于债权人并不履行自己的给付。虽然被指示人转移了给付对象(商品或金钱)上的所有权,但是他只是发出指示的债务人的给付媒介人。从法律上来说,债务人是在借助于被指示人,向债权人为给付。在被指示人方面,他是在向指示人为给付,虽然被指示人实际上并没有向指示人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行为(参见第362条第2款,第185条的规定)。(注:此种给付媒介行为的特点是涉及到整个给付事实构成,亦即扩及至财产流转。这里所称的财产流转,是指被指示人与债权人之间实际完成的价值流动。因为不存在无财产流转的给付,因此发出指示的债务人也是财产给予者。)
3.代理作为表示媒介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代理人可以被理解为被代理人的表示媒介人。作为表示媒介人,代理人并不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因为他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表达他人的(并非仅仅是效力及于他人的)意思表示。法律意义上的表意人是作为本人的被代理人。
依此解释,代理人为被代理人从事行为,而被代理人则是通过代理人从事行为。这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对立,而是从两个方面描述了同样一个过程。这即是说,代理不是代理人之效力及于他人的行为,而是被代理人借助代理人的表示帮助,间接从事的自我行为。
从这个角度观察代理行为,虽然代理人在形成效果意思,代理人在构建意思表示的内容并将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他形成的和表示的不是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一个在法律上属于他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可以作出如下解释:由代理人表达出来的意思表示,由于是由代理人以他人的名义发出的,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自始就是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或者,至少也可以这样解释:由于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和对其不利益产生效力,因此该意思表示依法成为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注:第一种解释在概念上要比第二种解释简单些。第二种解释中,包含了一种类似“逻辑秒”的想法。)
这样,我们不再需要用表示拟制(注:上文一。)之方法来说明问题。因为拟制是一种法律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拟制作为概念上的最后的应急措施,只有在找不到思想上更为简便、更符合法律体系以及实质上更为明白易懂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而表示媒介说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简便的、符合体系的和易懂的解决方案。它要比令人捉摸不透的,把意思、表示和表示效力割裂开来的“代表原则”清晰明了。所以,至少就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法律后果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舍弃代表说来解释。(注:关于代表说对《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的必要性,参见下文五。)
对一种现代的代理理论而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不再在意思上的代理和表示上的代理之间作出区分,而是要把由代理人在法律交易中作出意思表示作为一个统一体,即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上的整体事实构成,归属于被代理人。由于意思表示是由意思和表示组成的,因此第164条第1款第1句所称的意思表示的代理,理应包含了意思上的代理。
除此之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法律行为上的代理(第167条)、法定代理(条1626条第1款)以及依职代理(第1793条,第1909条),归结到代理这一法理上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去。(注:米勒—弗赖恩弗尔斯(Mueller-Freienfels)(《法律行为中的代理》,1955年,第342页以下)对代理法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统一的基本结构表示过怀疑。)正是因为表示媒介说将意思上的代理包含在内,因此此说不问被代理人自己能否有效地形成或表示出由代理人表达出来的意思。
4.与弗卢姆法律行为学说之比较
弗卢姆(注:《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载《德国法律生活一百年——德国法学家大会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960年,第135页以下(第160页以下);《民法总论》,第2卷法律行为,1979年第3版,第43章第3节,第755页。)为了克服源于个人意思说的困难,区分了作为表示行为(Erklaerungsakt)的意思表示以及作为通过该表示行为而形成的规定(Regelung)的法律行为。他把意思上的代理称为“神秘主义”(注:《德国民法总论》第43章第3节,第755页。),认为这种提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想通过这一区分,避免意思上的代理。他认为,由于代理人是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因此只有由代理人达成的法律上的规定(Regelung),才能归属于被代理人。
意思表示的概念,既可被理解为表示行为,也可被理解为表示结果,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法的财产法中,还存在着其他包括多重含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根据概念的文义、规范目的、体系关系以及形成历史,对概念进行解释,得出这个概念在有关规定中的具体意义。最常见的例子是给付的概念。根据法律规范所属的不同体系,给付既可以解释为给付行为,也可以解释为给付结果。
很明显,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并不涉及到意思表示的发出,而是涉及到已经发出的意思表示。因此,此条规定所调整的并非是作为表示行为的意思表示,而是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表示结果的意思表示。第164条第1款第1句正是旨在将这种表示结果转移给被代理人。因此,在“意思上的代理”和“表示上的代理”之间作出区分,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把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上归属于被代理人。(注:《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文意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并未区分意思和表示,而是把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有关第166条的规定,参见下文五。)在代理法上,既必须将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又必须将表示归属于被代理人。这也即是说,我们无法在不同时将他人的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情况下,将他人的表示行为归属于被代理人。
恰恰是由于代理人是从事法律行为的人,亦即是代理人发出了意思表示,(注:这也是弗卢姆的出发点!)并在订立(注:弗卢姆(《民法总论》,第43章,第3节,第755页》所言“在履行法律行为时的代理”(Vertretung beim Vollzug eines Rechtsgeschaefts)易生误解。因为,仅仅为他人订立法律行为者,并非履行该法律行为,特别是该人并不实施该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时候代理了被代理人,因此,由代理人表示出来的意思进入到了法律行为中去,而该法律行为作为规定(Regelung),应该归属于被代理人。所以,认为以上面的方式可以避免“意思上的代理”的提法的人,(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无用的。有关这些尝试的精神上的各种表现形式。参见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潘德克吞教科书》,第73章,注16b(第194页)。特别是在意思与表示之间作出区分的做法,如坎斯坦(Canstein)在其载于《格林胡特(Gruenhuts)杂志》第三卷第684页中所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根据这种看法,代理之“要旨在于:代理人并非代替被代理人欲为,而是代理人代替被代理人表示出被代理人的意思”。但是,如果存在一项意思表示(而要使法律行为成立,必须存在此项意思表示),那么总有某一个人欲为之。被代理人要么无法欲为(如在法定代理情形),要么(根据代理制度之劳动分工意义)授予他人代理权。这即是说。利他的意思形成,只能产生于代理人处(《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7页谓“代理人之意思行为”,这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此种对(应归属的)意思上的代理的畏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畏惧是法律生物学思维方式残留下来的对概念把握的困难。根据法律生物学思维方式,由于从自然科学来看,只有一个自然人才有能力欲为,因此在法律上,由另一个人来代替此本人,为此本人欲为其自身之事,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既然在私法上,不仅自己事实上所为之行为有效,而且归属于自己所为之范围的行为亦有效,那么,上面所说的困难也就不再存在了。这一困难从概念上就消除了。为此,我们不需要一种新的行为学说。(注:弗卢姆(文载《德国法学家大会纪念文集》,第162页)认为代理法在这里“具有范例性”。如本文所示,这一看法并非恰当。此外,在合同订立过程(第145页以下)中,法律行为还包含合同对方当事人发出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毋须在代理法上特别归属于代理人。合同之所以生效,源于拘束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订立行为(第305条)。合同的订立,仅需双方当事人发出意思表示。故此,弗卢姆提出的原则性批评(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不应使用“意思表示”,而应使用“法律行为”的概念),是扑了个空。)
3.撤回权和撤销权的归属
如果把被代理人视为本人,即被代理人不仅是欲为者,而且是表意者,则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被代理人可以根据第130条第1款第2句行使撤回权,根据第119条及相继条款行使撤销权,而不是由代理人来行使此类权利。因为,这些情形中涉及的意思表示是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被代理人有权撤回意思表示,因为他作为本人不愿意受应对他产生效力的意思表示的约束;被代理人有权撤销意思表示,因为他在借助于其表示媒介人从事表示行为的时候搞错了或者对其表示产生了误解。被代理人有权撤销意思表示,因为他在他的代理人方面(也即是间接地在他自身方面)受到了欺诈或胁迫。(注:关于知情归属,详见下文五4。)
依代表说,代理人发出的是自己的意思表示。这样,被代理人就必须撤回或撤销他人的意思表示,才能避免自己承担该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这种解释,不免牵强附会。
6.与授权之界定
代理(第164条第1款)与授权(第185条)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代理人是以他人名义从事行为,而被授权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的(二者都是为他人的计算从事行为)。除此之外,授权仅仅涉及到某项他人的权利客体;而代理权则依据代理的公示性原则(第164条第1款第2句),涉及到被代理人自身。与此相适应,代理与授权情形中的本人是不同的。在授权情形,本人是被授权人,他根据自己的意思处分某项他人的客体。由于他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发出的是自己的意思表示。而在代理情形,由于代理人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只是媒介了他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本人是自身承受法律行为后果的被代理人。
而如果采纳代表说,认为代理人是法律行为上的行为人(虽然其行为是指向另一人的),并且由代理人发出自己的、法律行为上的意思,(注:如帕兰特/海因利希斯(Plandt/Heinrichs)(同注1,第166条,边号1)所认为的那样。)那么代理与授权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7.与传达人的界定
传达人与代理人不同,他仅仅是传达他人的意思表示而已,而并不参与对他人意思表示内容的构建。人们批评本人说模糊了代理人与传达人的界限,因为此说将代理人的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与此相反,代表说则认为代理人具有自己的意思。然而,这一讨论是一种无谓之争,因为代理人与传达人显而易见地承担着不同职能。代理人为被代理人构筑意思表示的内容,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表示辅助人(Erklaerungshelfer)。相反,传达人只是帮助被代理人转达内容已经确定的意思表示,传达人只是被代理人的到达辅助人(Zugangshelfer)而已。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从二者承担的不同的任务角度,对代理和传达作出明确的区分。我们毋需采用代表说。
四、与国家法意义上的代表的区别
在国家法中,“代表”(Repraesentation)是一个与“本体”(Identitaet)相对应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将代表机构的意思作为被代表的群体的意思归属于后者,而是由代表机构的意思来代替被代表的群体的意思。(注:详见施特恩(Stern):《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法》,第一卷,1984年第2版,§22Ⅱ5,第963页;伊森西/基尔希霍夫(Isensee/Kirchhoff),《国家法手册》,第二卷,1987年,§30Ⅱ1,边号第19;齐贝柳斯(Zippelius),《国家学说通论》,1994年第12版,§24Ⅱ1。)所以,议会的意思既不是人民的意思,也不能等同于人民的意思。毋宁说,议会是自负责任地代替人民作出决定。这样的机制是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意思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在个别情况下也很难查明;至于那些放弃选举权的人民的意思则根本无从探知。因此,在国家法上,代表人的意思可以迥异于被代表人的意思(如在制定某些法律的时候)。
在私法交易中,被代理人作为本人(尤其是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他自身在法律上是无时不在的。这即是说,私法上的被代理人异于国家法上的被代表的人民,他在法律上并非缺席,而是在场的(代表其自身)。(注:因此,不能对被代理人作出缺席判决(《民事诉讼法》第330条)。)被代理人作为本人,借助于他的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意思上和表示上的代表)。在此意义上,民法上的任何一种代理学说都必须以“由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的思想作为依据。
私法上的代表(Repraesentation),实际上是代理(Stellvertretung)的另外一个概念。它与国家法意义上的代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私法上的代理与国家法上的代表相比,同个人及个人意思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它总是指向一个特定的个人或若干特定的人。在授权代理情形(第167条),私法上的代理通常涉及某项特定的法律行为或某类特定的法律行为;即使在商法上的经理权(Prokura)或代办权(Generalvollmacht)情形,其范围也是征得了被代理人的概括同意的。(注:与此相反,选民并非事先就对一切表示了同意。只不过选民必须把代表人之包括所有国家权力领域的决定当作议会的意思加以接受,这种接受有时经常是不情愿的。)意定代理的基础,是一项原则上随时可以通过撤回予以剥夺的代理权,而并非像国家法上的代表权那样,基础在于一项在选举期间不可撤回的总括授权。私法上的被授权人必须接受被代理人指示的约束。即使是法定代理人,也必须根据此类代理的照料性质(第1626条第1款,第1793条,第1909条),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顾及被代理人的个人想法、愿望和要求(参见第1626条第2款)。与此相反,国会议员不受任何委托和指示的约束(《基本法》第38条第1款第2句后半段),他仅需听从其良心亦即其自己的呼唤。
私法上的代理,与国家法上的代表之一般性相比,要特别得多。在代理法上持“代表说”(Repraesentationstheorie)学者认为,既然在意思上代理本人(Vertretung des Vertretenenim Willen)在理论上是不可设想的,那么用“在意思上代表本人”(Repraesentation des Vertretenen im Willen)这一看上去影响效力逊于“代理”的概念,可以取代“意思上代理本人”的提法。关际上,这只能说明代表说本身在实质上的不适当性。所以,“代表”(Repraesentation)这一概念,在私法之代理法中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此外,由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将法律行为全面地、无任何限制地归属于被代理人本身,因此“代表”这一概念也是多余无益的。(注:关于“代表”概念在第166条中的必要性,参见下文五。)
五、知情归属与意思瑕疵
1.调整的问题
本人说和代表说争议的焦点,并非仅仅局限于其理论在私法上的合法性、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代理行为以及代理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方式等问题。两种学说之间展开的争论,也还具有其实际的意义,诸如:就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而言,应以被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呢,还是应以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本人说着眼于被代理人的效果意思,因此原则上主张以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而代表说则从代理人的效果意思出发,认为应以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注:参见施陶丁格/狄尔希尔(Staudinger/Dilcher):《德国民法典评注》,第164条之前,边号第11以下。)这里涉及的是现行民法典第166条中调整的法律问题。
通说认为,立法者在第166条第1款(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中采纳了代表说,但在第166条第2款中规定了一项重要的例外。适用第166条第2款之例外规定的条件是,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的指示从事了行为。(注:持此说典型者如:雷曼/休布纳(Lehmann/Huebner):《德国民法典总论》,第一卷,1966年第16版,§36Ⅰ1;埃内克塞鲁斯/倪佩尔代(Enneccerus/Nipperdey):《德国民法典总论》,第一卷,1960年第15版,§182Ⅱ1;拉伦茨(Larenz):《德国民法总论》,1989年第7版,§30Ⅱc,第609页。)
但是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立法者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表示采纳此说或彼说,而是努力找寻一种实际可行的折衷方案。在立法者看来,“法律行为有效和生效的条件”,必须在被代理人那里具备,而就“意思瑕疵”言,则应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注:《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6页以下。)由此,第166条第1款与第166条第2款之间,根本不存在那种规则和例外关系。毋宁说,第166条包含了三条规定:即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以及第166条第2款。它们调整的是各不相同的实体对象。从总体上看,这三条规定也并非代表说的“符合逻辑的结论”(注:在这个意义上表达得特别明显的作者有施陶丁格/席尔肯(Staudinger/Schilken):《德国民法典评注》,1995年第13版,第166条,注1:“符合逻辑的结论”。)。相反,我们不采用代表说,也能在对相关利益(注:米勒—弗赖恩费尔斯(Mueller-Freienfels):《法律行为中的代理》,1955年,第390页,正确地以利益作为评判标准。他写道:“并非逻辑的问题,而是合目的性问题。”)作评价的基础上对这三条规定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
只要我们分析出这些规定不同的保护宗旨,并将第166条第1款和第166条第2款规定的顺序作出一些符合实质的调整,我们就可以对这些规定作出适当的解释。诚然,经调整后的法律规定的顺序,与现行法是有所不同的。
在内容上,第166条第2款与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是联系在一起的。第166条第2款规范的是被代理人的知情和应该知情,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规范的则是代理人的知情或因疏忽而不知情。此两条规定相互之间具有排它性。第166条第2款因以被代理人自己的非善意为判断标准,故该条款与代理人之代表行为毫无关系。因此,规定由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者,唯有第166条第1款。而即便在第166条第1款中,代表说作出之贡献,亦少于表面所示。
这一点在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表现得特别明显。诚然,在法律交易中,知道或应该知道某些情况,会引起特定的法律后果,或者阻碍特定的法律后果的成就。但是,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知情或应该知情才会真正影响代理人的效果意思——而代表说恰恰是以代理人的效果意思作为判断标准的。民法典第460条、第538条、第540条、第634条第4款和第637条是这方面的典型规定,它们的法律后果都是基于补充性的法律规定而产生。在因权利表见取得权利之情形,代表说的弱点就更加明显了。在这里,善意或者恶意并不是处分行为的内容。因此,在这些情况下,知情或因过失而不知情不会影响到代理人的效果意思。
只有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所称之代理人的意思瑕疵,才明确无误地涉及到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属于代表说可以完全适用的范围。
2.被代理人的知情或应该知情(第166条第2款)
由于被代理人作为本人,从代理人从事的法律行为中获得利益,因此必须防止出现下列情形:在因权利表见取得权利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派遣一名善意代理人实施行为,自己虽属恶意却仍可从非权利人那里取得权利。否则,从事劳动分工式经营的主体,会比单独实施行为的主体获得不正当的优待。第166条第2款的规定,旨在防止被代理人以此方式滥用代理权。当然,第166条第2款仅规定了一种极端的情形,即代理人根据恶意的被代理人的指示从事了行为。如果我们拘泥于该条规定的字面意思,那么,只要被代理人未向代理人发布指示,而只是让其在未知中行为,则被代理人的恶意不会给自己产生什么不利影响。司法判例很早就认识到,这种结果是一个不适当的法律保护漏洞。因此,法院着眼于该条规定的保护宗旨,对“依指示行事”作出扩张解释(注:《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61卷,第153页(第161页),固定判例。)。据此,被代理人向代理人授予代理权时,不一定非得再另外发出特定的指示不可。只要被授权人在代理权的范围内从事了某项特定的法律行为,而授权人正是想要被授权人从事此项行为,即可认定被授权人是在依指示行事。(注:《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38卷,第65页(第8章),附有其他说明。)如果被代理人虽然知悉情况并且可以采取措施,但是他却袖手旁观,则视作他向代理人发出了指示。(注:《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50卷,第364页(第368页)。)这种情况,即如被授权人在授权人在场的情况下订立法律行为,而授权人对此不表示任何异议。(注:《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51卷,第145页。)
如果将代理理解为利他的表示媒介行为,那么这种对第166条第2款的扩张适用就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即使是这种扩张适用,也还是不符合法律政策所要求的程度。因为,既然被代理人是本人,那么他自己就不得是恶意的。
罗马法就是正确地以上述原则为出发点的。在罗马法中,知情与否并非仅仅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注:参见弗利茨·舒尔茨(Fritz Schulz):《古典罗马法代理制度中的知情、恶意和错误》(Scienta,Dolus und Error bei der Stellvertretung nach klassischem roemischen Recht),载Sv.-Z Rom.Abt.33(1912),37(40f)。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反对温德沙伊德在《潘德克吞》第一卷,第73章,注18中的观点。)遗憾的是,在制定《德国民法典》过程中,在对法典草案进行审议时,人们在精神上受代表说影响甚深,而完全忽略了罗马法中的上述本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代表说主张原则上应以作为辅助人物的代理人为判断标准,而不是首先着眼于作为主要人物的被代理人。根据德意志帝国法院所提出的正确的看法,第166条第2款“旨在防止通过给不知情的第三人授予代理权,而规避法律行为有瑕疵之法律后果”。(注:帝国法院判例,载《法学周报》1916年,第318页。)但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未加具体说明的情况下,(注:《立法理由书》的评价结论(“因此,被代理人的知悉和应该知悉,必须与代理人的知悉和应该知悉具有相同的效果”)是正确的,但之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将此条规定扩大适用至所有代理情形……殊有疑虑,并且实际上也不存在此种需要(《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7页)。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就错误地认为,这一目的通过下列规定就可以达到了:只有在代理人依被代理人的指示行事时,被代理人的知情或应该知情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立法者的目光显然是过于狭窄了。事实上,第166条第2款所称的发布“指示”,仅仅是被代理人具有恶意的一种特别严重的事例。就此而言,以第166条第2款的规定,是无法实现其更为广泛的保护目的的。立法者的想法和理由,仅当它们具有实质上的说服力时,才能拘束人们的法律适用活动。所以,我们不应把第166条第2款理解为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的例外。第166条第2款是一条独立于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的规定。(注:参见下文五3。)司法判例理所当然地未受第166条第2款所谓的例外性质的影响,超越了该款规定的字面意思,将其准用于法定代理的情形,而且准用的范围也与意定代理的范围一样广泛。(注:《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38卷,第65页(第68页)。)
衡诸第166条第2款之规范宗旨,该款规定不应被理解为是一条封闭性的规定,而应视为是一条具有扩大适用能力的规定。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被代理人发出的指示,而是通过发出指示反映出来的本人的非善意性。因此,即使被代理人没有发出具体的指示,其知悉或应该知悉其些情形仍然可以构成恶意,致对自己产生不利的法律影响。第166条第2款规定应在此上意义上准用,至少也应在此意义上作出法律上的扩大解释(如果法院不敢作出扩大适用)。
综上所述,第166条第2款应该是知情归属方面的基础性规范,因此它应属于第166条规定之首位,亦即应规定在第1款中。
上述分析尤其表明,代表说在有关排除被代理人的恶意方面无能为力。与此相比,本人说的思路要清晰得多。
3.代理人之知情或应该知情(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
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旨在防止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对代理权的滥用。它要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被代理人为了不使自己成为恶意,自身远离法律行为,而派遣其代理人从事行为,但代理人虽然获知了法律交易中可致人恶意的数据,或者因疏忽而不知这些数据,却不向被代理人作报告。显然,如果允许被代理人以此种方式使自己人为地处于不知情状态,他就可以从劳动分工式经营中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如果被代理人自己参与业务交易,他必然会(因知悉有关数据而)使自己本身成为恶意。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即是通过知情归属的方式,防止被代理人做出这种把他人推向前台而自己则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事情来。这样,代理人知悉或应该知悉的事,被代理人也必须作为自己知悉的事或因疏忽而不知悉的事归属于自己。
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作为一种知悉归属规范(Wissenszurechnungsnorm),与第278条第1句规定相类似。代理人的恶意,作为被代理人自己的恶意,归属于被代理人,就如同法定代理人或履行辅助人的过错,作为债务人自己的过错,归属于债务人一样。第178条第1句与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一样,基于同一个归属理由。这就是本人不仅应当从劳动分工式经营中获取利益,而且还应当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如果债务人自己履行了给付或者从事了谈判,那么债务人本身同样也会发生错误的。
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之规定,与第166条第2款规定相比,涉及的情况更远离实际,因此其位置应处在第166条第2款规定之后。在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虽然被代理人作为主要人物并非恶意,但他必须将代理人的恶意当作自己的恶意归属于自己。(注: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的意义,并非在于使代理人的善意产生有利于被代理人的后果。因为只要代理人并非恶意,那么被代理人具有善意就足够了。根据权利表见取得权利,在物权法上毋需一种双重善意,即被代理人和代理人都是善意的。这里只要被代理人是善意的就足够了。第166条第1款只有在代理人的意思瑕疵方面才具有利他宗旨,参见下文七。)被代理人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他在法律交易中,借助于其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或者借助其代理人受领意思表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用源自本人说思路的表示媒介理论,完全可以解释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代表说。
4.代理人的意思瑕疵(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
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是一条在结果上与第166条第2款、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完全不同的规定。第166条第2款以及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旨在防止被代理人滥用代理行为从中获取利益。而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旨在保护被代理人免受代理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与第166条第2款、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一样,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旨在使从事劳动分工式经营的被代理人,处在与他自己亲自从事行为时一样的地位。如果本人是亲自从事法律行为的,那么他就会受到第三人的恶意欺诈或非法胁迫(第123条第1款);他也可能会在实施意思表示行为时搞错(第119条第1款第2种情形)、误解其意思表示的意义(第119条第1款第1种情形)或者对人或物或某项交易中被认为重要的性质发生错误(第119条第2款)。因此,本人不应该因为使用代理人来从事法律行为,而在撤销权方面遭受什么不利后果。这一思想,类似于第166条第2款和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旨在防止被代理人从劳动分工式经营中获得不适当利益的观念。两者都是为了保证:本人自己从事行为与通过劳动分工从事行为,在代理法上具有一样的地位。
在这里,我们同样不需要任何旨在避免“意思表示上的代理”之提法的代表说。毋宁说,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的法律后果源自第164第1款第1句的归属效力本身。既然第164条第1款第1句在法律上将由代理人以他人名义发出的意思表示归属于被代理人,那么被代理人就是以由其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意思表示。这也就是说,被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可能是有意思瑕疵的。代理人的意思瑕疵,不应该产生不利于被代理人的后果。因此,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仅仅具有澄清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功能。(注:如果代理人在被代理人不知情或不该知情的情况下,对谈判对方当事人进行了恶意欺诈或非法胁迫,则毋需考虑适用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因为被欺诈者或被胁迫者可以根据第123条第1款,相对于被代理人行使撤销权。代理人是表示媒介人,他参与了法律行为的订立,因此他并非第123条第2款第1句意义上的“第三人”(《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7页以下;《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20卷,第36页,第39页),被代理人也不是第123条第2款第2句意义上的“其他人”。
如果被代理人自己受到了恶意诈欺,而并非代理人受到了恶意诈欺,则被代理人作为本人,可以根据第123条第1款行使撤销权(《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51卷,第141页,第144页就是这样正确地裁判的)。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与此并不冲突,因为该款规定并非要限制被代理人的撤销权,而是要扩大其撤销权。因此,我们不需要准用第166条第2款的规定或该规定的法律思想(但拉伦茨《总论》§30Ⅱ,第609页以下却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被代理人对将来应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意义发生了误解(第119条第1款第1种情形),或者被代理人对人或物之交易上重要的性质发生了错误(第119条第2款),那么即使代理人方面本身没有发生误解或错误,被代理人也可以撤销意思表示。因为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旨在使被代理人处于有利地位,而并非限制他自己的撤销权。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类推适用第166条第2款的规定(埃尔曼/布鲁克斯(Erman/Brox):《德国民法典评注》,1993年第9版,第166条,边号14,却赞同类推适用)。)
六、代理人的行为能力
即使是无行为能力人也可以充当传达人,而代理人至少必须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第165条、第106条及相继条款)。代表说认为,这是因为代理人是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我们从本人说的思路出发,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代理人仅仅是被代理人的表示媒介人,亦即代理人并非是为了自己而表示什么,那么为什么代理人至少必须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说亦显得不能自圆其说。由于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并非由代理人承受,而是根据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单独由被代理人承受,因此仅仅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的代理人毋需受到保护,他不可能遭受自己的损害。此外,这里也不发生交易保护的问题。因为代理人的谈判对方即第三人,可以通过其自己的行为能力,来保护自己在法律行为上的利益。
因此,实质上的关键一定是在其他地方。之所以要求代理人至少具有限制行为能力,是因为要使被代理人免受损害。因为,至少在被代理人不知道其代理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法律上,保护被代理人的思想源自下列事实:代理人被授予代理权以后,即获得了一项特别的权限,他有权作为表示媒介人构建他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行使此项具有信托性质的权限,要求行为人具备一定程度的理智和判断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代理人必须具有“意思能力”(《立法理由书》(注:《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7页。)用语》。所以,只有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或至少具备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才具有代理能力。这里的关键,并非如代表说不当地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代理人发出自己的效果意思,而是代理人作为表示媒介人行使着一项权限,即发出一项在法律上属于他人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不采用代表说,我们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代理人至少必须具有限制行为能力这个问题。
七、欧洲其他国家的私法
从对某些西欧邻国(如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的法律制度的比较法考察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代理的效果
各国法律都规定,允许进行法律行为上的授权(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1002条、《瑞士债法》第32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387条和第1388条、《法国民法典》第1984条)。
奥地利民法和法国民法对代理与代理所依据的法律行为未加区分。法律行为上的代理被规定在有关委托的法律规定中。如根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002条,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授权合同,委托他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某项事务。《法国民法典》第1984条规定“代理”“为一方授权他方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受托人处理事务的行为”。意大利和瑞士民法则是将代理作为独立于基础行为的行为来规范的。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387条规定,代理权可以根据法律发生,或者由利害关系人所授予。在两国民法中,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且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所授予的代理权的范围内,直接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388条)。(注:《意大利民法典》第1388条规定如下:“由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为其利益、在授权的范围内(参阅第19条、第1392条)缔结的契约,直接对被代理人产生效力。”)根据《瑞士债法》第32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被他人授予代理权,且以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由被代理人而不是由代理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瑞士债法》有关代理的章节中,只有第32条规定涉及到基础关系。据此规定,授权的范围以基础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准。从此可以看出,外国民法对代理制度的理论归属,在某些方面迥异于德国通行的观察方法。
在奥地利学术界,通说强调《奥地利民法典》在理论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注:如格施尼策(Gschnitzer),文载JBL,1957,381(由于在奥国民法典形成之时还没有代理理论)和施坦策尔(Stanzl),载克兰/格施尼策(Klang/Gschnitzer)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四卷,第1分册,第859-1004条,1968年,第770页;施特拉塞(Strasser),载鲁默尔(Rummel)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一卷,第1-1174条,1990年,边号11;维洛帝(Vilotti),载格施尼策(Gschnitzer):《奥地利民法典总论》,1994年第2版,37.C.Ⅱ.2,第775页。)有人既对古老的本人说,也对代表说提出批判。(注:如施特拉塞(Strasser),载鲁默尔(Rummel)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一卷,第1002条,边号11。)有人则赞成弗卢姆对代理的理解,(注:如柯齐奥尔/威尔泽(Koziol/Welser):《民法大纲——总论和债权一》,1995年第10版,第166产。)或者追随米勒—弗赖恩费尔斯的学说,(注:《法律行为中的代理》,第202页以下。)着眼于授权行为和执行行为之“总体过程的统一性”。(注:如施坦尔(Stanzl),载克兰格/格施尼策(Klang/Gschnitzer)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770页,施特拉塞(Straoocr),载鲁尔(Rummel)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1002条边号第11;维洛帝(Vilotti),载格施尼策(Gschnitzer)《奥地利民法典总论》,37.C.1.2.C,第775页。)
德国理论界的争议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法国民法学说普遍认为,合同直接形成于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注:如贝那邦(Benabent)在其《民法债权》,第5版,第31页写道:“合同直接在订约之第三人与被代理人之间订立,代理人只不过是合同订立的一种工具,但他不是当事人。”)代理制度涉及到对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归属(substitution(注:马祖/沙巴(Mazeaud/Chabas):《民法讲义》,1976年以后第4至第10版,第二卷第一册,第155号。))。(注:马帝/雷诺(Marty/Raynaud):《民法论丛》,1976年以后第2至第3版,第二卷,第90号;热斯坦/比育(Ghestin/Billiau):《民法论丛》,1982年以后第3版,第三卷,第788号。)
在意大利,人们持代表说。(注:特拉布奇(Trabucchi):《民法制度》,1992年第33版,第130页以下(第三章68);巴尔加诺(Balgano):《私法》,1990年第6版,15.1-15.3。)
瑞士学术界有关《瑞士债法》第32条的论著也称代表说为通说。(注:如奥泽(Oser):《债法》,1929年,第221页;布赫尔(Bucher):《瑞士债法总则》,1988年第2版,§33Ⅰ,第595页;也请参见高赫/施吕普(Gauch/Schluep):《瑞士债法总则》,1995年第6版,§13,边号1307,1314-1315。)代理被描述为“法律上重要的、为其他人产生效果的行为”。代理之本质,在于为他人从事法律行为,其后果是为他人(即被代理人)产生法律效力,而并非为行为人(代理人)自己产生法律效力。(注:高赫/施吕普(Gauch/Schluep):《瑞士债法总则》,1995年第6版,§13,边号1317。)
2.知情归属与意思瑕疵
在奥地利以及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民法中都没有与《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相类似的规定。
在奥地利,就意思瑕疵以及知悉或因疏忽而不知悉某项事实而言,应根据代理人、被代理人对订立法律行为的影响大小,来决定应以代理人还是应以被代理人,抑或应以两者一起,作为判断的标准。(注:明确持此观点者有施坦策尔(Stanzl),载克兰格/格施尼策(Klang/Gschnitzer)《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1018条注2。维洛帝(Vilotti)(载格施尼策撰《奥地利民法典总论》,1994年第2版,37.C.Ⅱ.2,第776页)也提出了这样一条“一般规则”。)只有在代理人发生了误解,而不仅仅是被代理人发生了误解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撤销权。(注:施特拉塞(Strasser),载鲁默尔(Rummel)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1018条,边号第10;维洛帝Vilotti,载格施尼策(Gschnitzer)《奥地利民法典总论》,37.C.Ⅱ.C。,第77页。)
如果被代理人本人具有恶意,以及/或者代理人具有恶意,则本人会因恶意遭受不利。(注:施特拉塞(Strasser),载鲁默尔(Rummel)撰《奥地利民法典评注》,第1018条,边号第12。)因此,如果被代理人本身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有关法律后果发生或不发生的情形,并且/或者代理人知之或应知之,即可认定存在恶意。(注:热斯坦/比育(Ghestin/Billiau):《民法论丛》,第792号,第805页:“他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志”(qui exprime sa proprevolonte)。)
在法国法中,关于意思瑕疵、善意或恶意,都以代理人(作为表示自己意思的行为人)作为判断标准,而不以被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不过,如果被代理人自己对代理人的意思形成产生了影响,那么就以被代理人的想法为准。(注:上诉法院商事庭1976年3月2日的判决,载《民事公报》(Bull.Civ.)1976年Ⅳ,第78号。马祖/沙巴(Mazeaud/Chabas):《民法讲义》,第二卷第一册,第154号;热斯坦/比育(Ghestin/Billiau),同上揭书,第三卷,第805号;马帝/雷诺(Marty/Raynaud),同前揭书,第一卷,第156号。)这一点,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
在意大利民法中,关于意思瑕疵、善意或恶意以及对某些情况的知悉或不知悉,原则上也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意大利民法典》第1390条和第1391条)。(注:《意大利民法典》第1390条:“如果代理人的意思有瑕疵,则契约是可撤销的(参阅第1427条、第1441条)。但是,当瑕疵涉及被代理人预先确定的要素时,仅在被代理人的意思有瑕疵时契约得被撤销。”第1391条:“在考虑善意或恶意、对特定情况知道或不知道时,要考虑代理人自身的状态,但是涉及被代理人预先确定的要素不在此限。无论如何,恶意的被代理人均不得主张代理人的不知或善意(参阅第1147条)状态的约束。”)只有在涉及到由被代理人事先确定的合同要素时才构成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代理人的意思具有瑕疵,合同也可被宣布无效。
如果有关的合同要素是由被代理人事先确定的,则被代理人的善意或恶意、知情或不知情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391条第2款,恶意的被代理人无论如何均不得主张代理人的不知或善意。这条规定,比《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第2款的规定要更为宽泛。
在瑞士法中,关于意思瑕疵以及知情或不知情,原则上以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因为代理人实施着与第三人的谈判行为。(注:策希(Zaech):《伯尔尼评注》,第六卷/1,第2分卷,第3小分册,1990年,第32条,边号142和144。)然而,瑞士法中明确强调,被代理人本身不得是恶意的。(注:吉尔(Guhl):《瑞士债法》,1991年第8版,第18章Ⅱ3,第147页;高赫/施吕普(Gauch/Schluep):《瑞士债法总论》,边号1444,1448(第277页);策希(Zaech):《伯尔尼评注》,第32条,边号144末尾(援引了联邦最高法院判例43Ⅱ,第491页);布赫尔(Bucher)(《瑞士债法总论——不包括侵权法》,1988年第2版,第33章Ⅶ1,第631页)的理解要窄些,认为仅适用于特别代理权。)
被代理人如知道事实真相,就不得主张代理人的错误。被代理人不得撤销执行行为。如果仅仅是被代理人发生了错误,而代理人并没有发生错误,则亦不得行使撤销权。这样,代理人在意思形成方面的瑕疵,就归属于被代理人承受了。(注:策希(Zaech):《伯尔尼评注》,第32,。边号142(援引了联邦最高法院——瑞士法学杂志1908,09,316第95号)。)
1971年10月在统一私法国际协会(UNIDROIT)研究项目(注:该项目源于由设在罗马的统一私法国际协会(Institut Intermational pour 1' Unification du Droit Prive)于1929年开始举行的有关国际统一买卖立法的谈判。)框架下完成的《国际货物买卖代理统一法律草案》(注:刊印在UNIDROIT,U.D.P.1974,Et.XIX,Doc.55=《统一私法国际协会杂志》(Rev.Dr.unif)1973Ⅱ第200页以下。)(附有报告),并没有对代理人或本人的知情或因疏忽而不知情的归属问题作出规定。
根据关于《欧洲统一合同法》的所谓兰多草案(注:奥勒·兰多/休·比勒(Ole Lando/Hugh Beale):《欧洲合同法原理》,第一部分:履行、不履行和赔偿,1995年。)第1.109条(1),合同一方当事人被视为知道某一事实或应该知道某一事实,如果参与订立合同或参与履行合同的另外一个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该事实,并且该当事人对此另一人应当负责。(注:第1.109(1):一方当事人被视为已知或已预知某项事实,或被视为处于应知或应预知该事实的状态,如果他负责的任何其他人知道或预知该事实,或者应该知道或预知该事实,除非该其他人并未参与订立或履行合同。)这即是说,在通过他人从事行为的领域,辅助人的知情被归属于本人。另外,兰多草案第1.109条(2)制定了一条类似《德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过错归属规定。(注:第1.109(2):一方当事人委托其履行合同的人,或者在征得该当事人同意后从事履行行为的人,如果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或实施了不符合诚实信用及公平交易之行为,则该当事人视作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或实施了不符合诚实信用及公平交易之行为。)不过该草案中缺少一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第2款相适应的规定。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欧洲邻国的法律制度中,还是在国际统一的代理法草案中,有关代理方面的理论问题都尚未最终确定。这说明,外来的法律规定和草案并不能构成从表示媒介意义上解释代理行为的障碍。相反,在这里,《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第2款在法律政策上的狭隘性,倒是被克服了。(注:在英国法中,也不需要被授权人根据授权人的特定指示从事了行为。关键的问题,是要看“在理性的考察下,本人必须给他的代理人提供哪些有关相关行为的重要信息,亦即第三人可以认为哪些信息已经在其合同当事人与实际为他从事谈判行为的代理人之间进行过交流”(陶皮茨(Taupitz):《英国法和德国法中的知情归属》,卡尔斯鲁厄论坛,1994年)。这样,第三人就分担着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所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与劳动分工型经营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本人来说,这种风险原则上是一种企业经营风险,因为本人从劳动分工中获取利益。第三人一般则想处在同他本身与被代理人从事行为时相同的地位。因此,从基本思路上来看,这里涉及的问题与其说是对第三人信赖的保护,还不如说是本人方面对风险的控制。)
八、结论
1.代理并非代理人之效力及于他人的行为,而是被代理人的自我行为,是被代理人借助于代理人的表示辅助行为从事的间接的自我行为。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表示媒介人。作为表示媒介人,代理人发出的并不是其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他人的(不仅仅是效力及于他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表意人是作为本人的被代理人。
2.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即就其全部要素,归属于被代理人。所以,任何一项代理,都包含了对本人意思的代理。
3.一切旨在避免“意思上的代理”之提法的努力,都是多余无益的。这也适用于弗卢姆的法律行为学说。
4.不采用主张在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以及被代理人的法律后果之间作出区分的代表说,也可以解释《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以及第166条的规定。
5.第166条第2款与第166条第1款之间,并非规则与例外关系。毋宁说,第166条包含了三条规定,它们在实体上分属于不同的调整范围。第166条第2款规范的是被代理人的知情或应该知情,而第166条第1款第2种情形规范的是代理人的知情或因疏忽而不知情。这两条规定相互之间具有排它性。两条规定旨在防止被代理人从劳动分工型的经营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相反,第166条第1款第1种情形,则是为了使被代理人免受代理可能产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6.在第166条第2款情形,即使被代理人并没有发出具体的指示,其恶意亦会对他产生不利后果。该款规定也应该在此意义上加以适用。
附:《德国民法典》相关条款
第164条
第1款: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发出的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意思表示系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而为,还是根据情况可以断定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而为,并无区别。
第166条
第1款:意思表示在法律上的效力,因受意思瑕疵或对特定情形的知道或应该知道而受影响时,应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被代理人为判断标准。
第2款:在代理权系通过法律行为授予的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发布的特定指示从事了行为,则授权人不得就自己知道的情形,主张代理人不知情。授权人应该知道的情形,以应知等同于明知为限,亦同。
第362条第2款:
以清偿为目的向第三人履行给付的,适用第185条的规定。
第185条
第1款:非权利人对标的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为有效。
第2款: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且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的,为有效。在后两种情形,对标的已作出数项互相抵触的处分的,则仅有先前的处分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