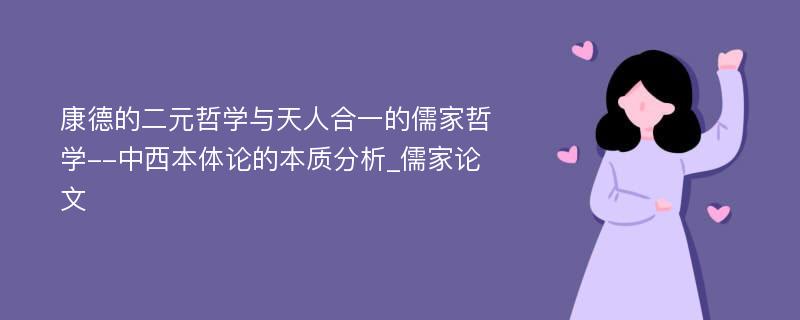
康德二元论哲学与儒家天人合一哲学——中西本体论本质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儒家论文,哲学论文,本体论论文,天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所出现的理性与感性、先验与经验、主体与客体的二者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难对立,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体现在康德的哲学里,成为其哲学的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康德经剥茧抽丝般的分析工作后为我们所还原和昭示出的著名的两个“物自体”的命题,即《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谓作为“先验对象”的“物自体”与作为“先验自我”的“物自体”。前者是感性的来源、基础,是我们从事认识所必须预先地(即“先验地”)设定的认识对象方面的条件;后者是知性的来源、基础,是我们从事认识所必须预先设定的认识主体方面的依据。而“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体现在后者建构、综合、整理、统摄前者的所谓“先验统觉”活动里。
人们看到,尽管康德在其“先验统觉”学说里,一再强调先验的自我作为一纯形式只存在于对象意识之中、而对象意识唯有借助于自我意识才有可能,从而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规定;尽管康德由此出发而竭力鼓吹“统觉”的功能主义的本质属性,反对将自我或对象加以实体化、超验化的传统哲学的种种陋行;但是这种“彻底经验主义”的一元化哲学的努力,实际上仍最终屈服于传统二元论哲学这一欲罢不能的规定。这种规定不仅表现在其哲学始终难以割舍其两个“物自体”的先验设定,而且还体现在当康德从认知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真正的哲学的形上本体的分析时,其对这两个“物自体”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把握,仍然是处于“不可知论”的一筹莫展之中。
康德写道,“人类知识有两个源泉,即感性与知性。它们大概来自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共同的根基”[1],“如果我们想要对感性和知性的来源作判断,那么我只能眼看这种探索完全超出人类理性的界限”[2]。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康德别出心裁地为人们假设出了一种似智而非智、超感而又可感的所谓“智的直观”(an intellectual intuition)的概念。在康德看来,唯有这种“智的直观”才能对(知性的)自我与(感性的)对象的本质关系予以真正的洞观,才是哲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认识之所以可能”问题的最终谜底和答案。但遗憾的是,康德又断言这种极为神秘的“智的直观”“完全超出人类理性的界限”,并非肉眼凡胎的人类所能具有,而是属于上帝的,它不过是具有超凡的睿智的上帝的一种所谓“神知”(divine understanding)。
康德哲学的这种神秘的“智的直观”的提出,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清楚地揭示出其哲学的巨大悲剧性。它说明其建构主体性哲学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不过是一个如泡如影的空诺,而其旨在为科学张目的轰轰烈烈的“批判哲学”最终竟与非批判的宗教不谋而合。因此,康德哲学为人们燃起了哲学新纪元的希望之光,但其身后却依然拖着挥不去的旧哲学的阴影,正如其前辈一样,其哲学始终宿命于西方传统哲学二元规定这一哲学的“原罪”之中。
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康德哲学终止点的这种“智的直观”的提出却为后康德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提供了动机活力。西方现代哲学家们或从康德的“智的直观”的不逞中走向西方哲学基础之重建(这一点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谈到),或对这种“智的直观”予以审美化的诠释而成为康德哲学之继续。例如海德格尔便是走着后一条道路。他在《康德与形上学问题》一书中,称其以一种“冒犯”的态度说出了康德“想说出但又缩回去”的思想,将这种连接沟通自我与对象、知性与感性的具有本体化意义的“智的直观”,径直等同于康德先验统觉学说中的所谓“先验想象”的概念。而这种“先验想象”的本质也即康德所谓作为“先验构架”的内意识的“时间”,于是其从“先验想象”作为“本体论的构成中心”,最终又推出《存在与时间》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所谓时间一元的本体论理论。
无论人们如何激烈地批评海氏此举业已背离了康德哲学的初衷,[3]也无论海德格尔这一新本体论学说是否具有将康德哲学“此在”化即主观主体化的嫌疑,从而最终并未走出西方哲学二元设定的迷局,海德格尔这一向康德哲学的求助都不能不提醒人们再次注意到康德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发展方向的顽强规定,以及西方现代哲学与康德之间的难以割舍的联系。康德哲学是一条纽带,联接着西方思想的过去与未来;康德哲学是一面镜子,记载着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兴灭和荣衰。
二
与这种为康德所深刻揭示的两个难以调合的“物自体”的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学说不同,中国古代儒家的本体论学说却呈露为另一副面孔,它至始至终都是一元论的。而要说明这一点,自然就涉及到人们所熟知的、极具中国哲学特色的“天人合一”理论。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先秦之际已初见端倪。周礼中的“内尽于己”则“外顺于道”的神人相通的思想,周易中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的天人同构的模式,实际上可看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本朴的理论原型。这最终导致了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见《中庸》)观念的提出,以及孟子说中人性与天道为一思潮的喷涌:“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孟子由人心本于性而性乃受于天,推出天人一贯、天不外人。而其著作中诸如“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以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著名的论说,看来了并非无端空发之说,而显然正是循着这一“尽心——知性——知天”的极为明白的理路推衍而生的。
无独有偶的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也遥相应和于儒家另一部经典之作的《中庸》里,而其立论不仅与孟子如出一辙,而且比孟子的论述更为明捷、丰富和深刻。如《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在这里,《中庸》对天人关系的把握已从“明”走向“诚”(成),从“知天”走向“赞天”,从天人之间的受动的合一走向能动的合一。也正是基于这一对天人关系的更为深入的理解,使《中庸》成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作。它所提出的“诚明为一”、“成己成物”、“尊德性而道问学”等等“从容中道”的原则,规定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成为其基本的理论内核。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之所以能够上承先秦下续宋明而源流不竭,无疑是得益于《中庸》这一极富建设性的理论工作的。
然而,考之中国思想的历史,这种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真正被得以充分朗现的,则是到了中国古代稍晚的宋明时期。佛学的大举入侵使当时的中国文化岌岌可危,但其精微细密的本体论的哲学思考,却为儒家自身的本体论思想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创造了新的机遇。在这一对儒家天人合一本体论思想的历史性重建工作中,最具开创性而为人所称道的人物则是宋儒张载。其不仅“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地重新恢复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地位,而且其对这一思想的论述和分析,堪称洞深烛幽、字字珠玑:“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末如之何矣。”[6]这无疑是对《孟》、《庸》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申,但同时其中又深深融入了对佛学的“自蔽”于“我私”的主观唯心论的批判的新的内容。这使得张载对性与命、人与天、明与诚等等关系范畴的理解比起前人更为圆照无遗,也更为立体和厚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向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潮回归的思想在宋明时期并非为张载所独揭,而是关洛并茂地互发在二程的学说里。如程明道言:“天人无间断”,“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仁者以天道万物为一体”[7];程伊川云:“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也”。[8]
不过,在宋明新儒家当中,真正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之大成而使其臻至炉火纯青之境的,应首推明季的巨儒王阳明。王阳明对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积极贡献在于,其既提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答聂文蔚》),体现了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学脉的宗承和继续,同时又在与理学“格物致知”路线中日益凸现的心物二元论思想的短兵相接中,从认识论批判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传统的体认。而其学说中的所谓“意之所在便是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思想的提出都无不是这种深思熟虑哲学思考的结晶。在其哲学中,传统的天人关系已演绎为具有近代哲学意义的心物(理)关系,传统的天人合一已发展为更为逼真的心物(理)合一。这一哲学表达的改变,不仅使其学说更富形而上的思辨的色彩,而且也恰恰是中国哲学思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体现。关于这种心物(理)合一,王阳明写道:“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理岂外于吾心耶?”[9]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命题出发,对王阳明的学说遽下断语将其判定为一种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看法非但失之浮浅,而且以致于完全是戴着西方哲学有色眼镜所导致的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实际上,一方面王阳明反对“外吾心而求物理”,另一方面其又反对“遗物理而求吾心”;一方面其提出“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另一方面其又提出“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因此,王氏的学说既非一种西方式的唯物主义也非一种西方式的唯心主义,而是一种以“意”为中介和中心的别具一格的中国式的“彻底心物一元论”理论。[10]
这种彻底的心物一元论理论的提出,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烂熟形式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真正自觉和完成。同时,它又作为西方传统的心物二元论学说的明确反题形式,为我们直接切入中西本体论的比较提供了立论的坚实可靠的依凭。
三
中西本体论理论之间的根本对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中西文化比较讨论中老生常谈的话题。而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哲学表现为二元本体而中国哲学则表现为一元本体?也即为什么中国哲学能超越主客对立而走向天与人的合一?这一似乎被人们视为“不可诘致”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所不能回避而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
海外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多年从事康德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比较研究,他把这一问题归结为中西哲学对康德所提出的“智的直觉是否可能”问题的不同理解。他在其《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一书中指出:
如依康德的思路说,道德以及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否其关键端在智的直觉是否可能。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智的直觉是没有彰显出来的,所以康德断定人类这种有限的存在是不可能有这种直觉的。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智的直觉却充分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人类从现实上说当然是有限的存在,但却实可有智的直觉这种主体机能,因此,虽有限而实可取得一无限的意义。……我们现在就康德的设拟,顺中国哲学之传统,讲出智的直觉之可能,来充分实现这道德的形上学,我想这是康德思想之自然的发展,亦可以说是“调适上遂”的发展。(第346—348页)
也就是说,在牟宗三先生的学说里,中西本体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智的直觉”的不同解释,而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对康德的“智的直觉”问题的圆满解决、作为“康德思想之自然的发展”,毋宁说已俨然成为一种“后康德主义式的学说”。
这完全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的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是最终根源于其对中西两种根本不同的本体论本质的不作区分和简单混同。
众所周知,西方传统哲学是以所谓认识世界为根本宗旨的,哲学即所谓“爱智”。而认识之为认识,又是以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区分、之对待为前提的。因此,也正是这种认识优先论决定了西方传统哲学一开始就被一种非此即彼的所谓的“主客模式”这一先验前见所规定,决定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学说至始至终都难以摆脱主客之分的阴影。于是,在西方传统本体论学说中,遂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对峙,以及康德哲学中的两个“物自体”之推出,而不管其派别如何林立、花样如何翻新,西方传统本体论学说都万变不离其宗地栖身于这一主客二元的不可逾越的规定之中的。同样地,西方传统的伦理学哲学亦是这一主客二元规定的产物,它从认识论中的主客模式逻辑地推出伦理学中的一种没有“我们”的“我他”模式,其中的“他人”不过是一种异己于我的世界中的“在者”。严格地说,这是一种非伦理、反伦理的伦理学。因此,无论康德的愿望是多么的“科学”,但是从一种康德式的“理性本体”中实际上是推不出真正的“道德本体”的,犹如从物理学定律中推不出真正的爱情法则。
与这种西方传统哲学不同,“人伦,道之大原也”[11],以儒家为其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另辟蹊径地以社会的伦理化为中心,哲学毋宁为“明伦”。而伦理之为伦理,它是以伦理主体之间之认同、之无待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一开始就被非比即彼所谓“主客模式”所制约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始终不越亦此亦彼的所谓“我你模式”之规定;从而,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从认识论走向其二元的本体论学说(再走向伦理学学说)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地从伦理学走向其一元的本体论理论。故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天人合一的结论并非哲人们刻意求之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不解自揭地预示在其伦理学所固有的原逻辑里。
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仁学本体论”为我们所揭示的主要内容。对于儒家来说,“仁”首先是人际关系中我你之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无对待的交互性的体现,也即孔子所谓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程颐所谓的“仁道难名,惟公近之”,戴震所谓的“通天下之欲之欲”。但是“仁”不仅是人际关系的交互性的体现,亦是天人关系的交互性的体现;它不仅要求我们由己推人地走向人我一体,而且要求我们爱乌及屋地从由己推人的人我一体,最终走向把宇宙看作是“准主体”的由己推物的物我一体。这种最终的完成形态的“仁”也即为孟子所强调的“仁民爱物”,为张载所强调的“民胞物与”,为程明道所强调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朱熹所强调的“仁即天心”,以及为谭嗣同所强调的“无之不通”。王阳明曾畅论这一“泛仁论”哲学之旨,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12]
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智的本体论”的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所独具的“爱的本体论”。韩愈谓“博爱之谓仁”,朱子也称“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理”,“仁离爱不得”(《语类》,六)。在这种以仁为其本质规定的儒家的本体化的“爱”的学说里,爱不仅使我们从自我封闭的孤独中走出而克服了与他人、与自然的分离之苦,而且它作为一种与整个世界溶为一体的最为质朴原始的“根于天命之性”的生命要求,也成为一种最深刻最直接的切入对象、体悟事物的方式。在这里,爱已不再是纯粹伦理的价值判断,而是内含事实判断的丰富的认知晓喻;它已不再是囿于一己之私的非理性的生理需要,而是无概念而具有普适性的成为宇宙普遍真理的昭示。故孔子宣称“择不处仁,焉得智”[13],王阳明断言“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14]。我们看到,这种儒家所揭示的中国古老的仁学本体论的仁智统一的思想,与歌德的“爱的越深,认识的越深”这一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命题已不期而遇和深深相契了。
明乎此,我们方能真正明白中国古代儒家的“知行合一”命题的内在所指和深意。在很多人眼里,中国古代“知行合一”中的“行”不过就是所谓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又往往与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改造和征服客体的所谓“实践”简单划等。其实,儒家所谓的“行”既不是主体之于客体的静观的认知,也不是主体之于客体的能动的改造和征服,而是在仁学构架内所自发地、逐步展开的“我”与“你”之间互相深入、互相沟通的一种解释学的交互性过程,一种作为主体间性的“德性”。就此而言,儒家的“行”也即自不容已的德的挚爱,也即伦理应该的“好恶之情”,而其所谓的“知行合一”不过是指仁学本体论中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好恶之情”与“是非之心”、“爱”与“智”之间的原始的统一和互根,不过是指儒家所谓的“仁体事无不在”[15]这一仁的本体的巨大包括性。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时说: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传习录·上》)
在这里,“好好色”与“好色”、“恶恶臭”与“恶臭”这一被人视为不可破斥的主观与客观的相对待的二元,已不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过是人性异化的一种产物。于是,对于儒家来说,主客对立的真正克服不是一个认识的任务,而毋宁说是一个前认识的伦理(“行”)的任务。它不是取决于对康德所谓的神秘主义的“智的真观”的诉诸,也不是取决于对海德格尔所谓的主观主义的“先验想象”的求助,而是最终取决于对德的仁爱的发明,取决于人能否去除“私意隔断”、去除自我中心的封闭而回归仁学的我与你的原始的共体与沟通,一言以蔽之,即取决于他能否“反求诸已”地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的人。所有这些也正是为宋明新儒家们所反复提醒、一再申说的、有别于“见闻之知”的“德性之知”与“致良知”的主要内容。[16]在儒家看来,人只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的人,他才能不仅克服我与他人的相刃相靡而重叙人类的手足之情,而且才能摆脱人与自然对立分裂的悲惨命运而“混然中处”于天地之间,使人“形色天性”地成为自然中的忠实一员,而同时又“天帅吾性、天塞吾体”地使自然成为人性的不言而喻的率真体现。
张载说,“易所谓‘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17]这一断语,也正是儒家对天人合一问题解决的真正答案。因此,在儒家学说中是不存在也不需要康德所谓的“智的直观”的,正如在康德哲学中不存在也不需要儒家的德的仁爱一样。而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文化本位说”代表的牟宗三先生却把儒家学说归结为对“智的直观如何可能”的回答,这正表明其对中国哲学依然未烛幽洞深,而仍像其论敌那样同样未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说”的阴影。
四
这种有别于西方传统哲学“理性”本体的中国古代儒家“仁学”本体的真正揭示,不仅是对中国哲学原貌的忠实阐明,同时也无疑是对中国哲学所内含的现代意义的一种深刻的肯定。
长期以来,受“逻各斯中心”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的影响,哲学一直被视为是西方学人的世袭领地,而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则或如黑格尔那样被人们视为是纯粹的道德说教而逐出哲学领域,或如现代众多中国哲学诠释者那样被人们僵硬地纳入到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范型之中,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东方式的图解的说明。但是,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运动对传统的主客模式哲学的摒弃和将哲学移师于主体间性领域,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对中国儒家哲学予以再认识,使之正日益成为20世纪人类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
作为这种与传统决裂的西方新哲学运动的代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对话哲学的理论。在对人类文化形态的全面梳理之中,布伯为我们揭示出了两种把握世界的哲学模式,即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为其代表的“我它”关系模式,和以对话哲学为代表的“我你”关系模式。在他看来,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客体之依赖于主体的单向服从的关系模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我与你之间的“交互性”的关系模式。他强调“关系是交互性”,“把纯粹关系理解为依赖关系意味着破坏该关系的一个载体并因此破坏关系本身”[[18]]。从而,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借助种种中介的关系模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以“直接性”为其特征的关系模式。他指出:“对你的关系是直接的。我与你之间没有概念、先知、幻象……。我与你之间没有目的、贪欲、期待……。一切手段都是一种妨碍。只有在所有手段都消失的地方相遇才可以发生。”[19]故“成为直接的”(“Be immediate”)已成为其哲学的鲜明的旗号和最高吁请。因此,对话哲学不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之于客体的人为把握的学说,而是一种人际间的不期而然的“相遇”(the meeting)的理论,不是区别与对待,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之间”(the between)成为其哲学的结构中心。同时,对于布伯来说,这种我你的“之间”范畴的提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本体论的原型,它同时又进一步地作为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本真摹本”,乃至于成为人与整个世界关系的本质阐明以及宇宙本体的终极规定。
在这种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消解中,除布伯之外,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的哲学建树亦是不容人们忽视的。如果说布伯哲学试图使哲学从我它领域转向我你领域的话,那么舍勒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贡献则在于,他旨在恢复基督教的爱感优先的思想的地位,抬出伦理的“爱”的本体以对抗传统哲学的认知的“智”的本体。舍勒提出,“一切有理智的行动以及从属于它们的图象内容和意义内容,它们的起源不仅与外部对象和由它们引起的感官刺激的存在有关,而且还与兴趣之行动和受这类行动的引导的注意之行动有关,但最终与爱和恨的行动具有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对某物’感兴趣和‘对某某’的爱才是为一切其他行动奠基的最基本、最为首要的行动,我们的精神在这类行动中才能把握某种‘可能的’对象。”[20]故他断言,“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21],“不是人能认识的事物及其特性决定着并限制着人的价值存在世界,毋宁说恰恰是人的价值本质世界限定并决定着他能认识的存在,将它像一座孤岛一样托出存在之海洋。……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22]这样,在舍勒的重新阐释之中,爱已不再是主观的非理性的经验情感,而是登堂入室地深入为事物本身的普遍的先验规定,而这种对爱的本位论地位的高度肯定,毋宁说已庄严宣布了数千年来一直被视若神明的西方唯智主义本体论的正统性的寿终正寝。
总之,无论是布伯的对话哲学理论还是舍勒的爱的本体的学说,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本体论领域中一种引人注目的“伦理学转向”的激进的呼声,以致于《他人》一书的作者Theunissen在展望当代哲学发展时情不自禁地宣称,伦理哲学的“他人的问题确乎从未像今天那样深入为哲学思想的基础。它不再是一种特定学科的单纯对象而已成为第一哲学的主题”。[23]而所有这一切又与青年马克思当年的这样一种极为杰出的洞观相吻而不悖,即:人类只有首先克服作为“族类异化”的其与他人的分离,从而才能真正克服作为“自然异化”的其与自然分离,并最终终实现向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这一美的终极本体的回归。
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批判性的思想运动。而这一运动在当代的兴起,不正是儒家仁学本体论思想的现代意义的一种旁证和说明,不正预示着中国古代哲学在历史的沉浮中又一次再显其峥嵘吗?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第一版,第15页。
[2]康德:《1978年5月26日给赫尔茨信》。
[3]如著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Ernst Cassirer)称海德格尔对康德思想的解释不是以注释者的身份说话,而是以僭越者的身份说话。
[4]《孟子·尽心上》
[5]《中庸·右第二十一章》
[6][15][17]《张载集·正蒙》(诚明、天道、神化)
[7]程明道:《遗书·二上》
[8]程伊川:《二程语录·十八》
[9]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0]关于“意”在王阳明心物一元论学说中的地位,可参见拙著《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中有关议论。
[11]《张载集·张子语录》
[12]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13]《论语·里仁》
[14]王阳明《传习录·下》
[16]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王阳明也说:“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牟宗三先生把这种为中国哲学家所独揭的“德性之知”解释为一种康德式的“智的直观”,但诚如朱子“仁者固能觉,谓觉为仁不可”一语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以仁为其内核的“德性之知”,与其说是一种智性的觉,不如说是一种德性的爱,它并非是一认识论的范畴,而完全是一伦理学的范畴。
[18][19][23]布伯:《他人》英译版,第275、275、1页。
[20][21][22]舍勒:《爱的秩序》中译版第26—27、47、48页。
标签: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康德论文; 本体论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二元论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王阳明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中庸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