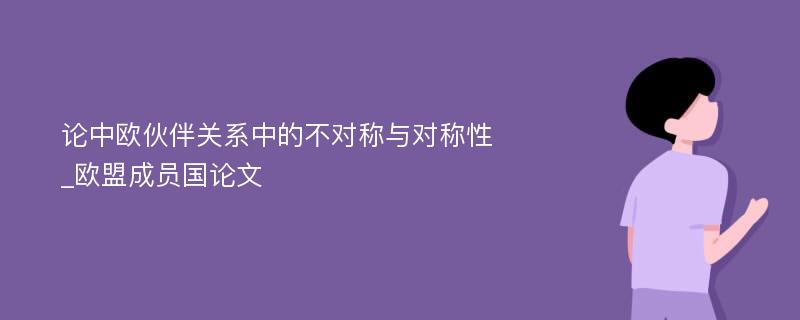
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对称性论文,伙伴关系论文,不对称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是不对称的
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弥漫着战胜东方的喜悦,“永久和平”和“历史终结”成为时尚的预言。但是就在当时已经有人发现,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刻板的简单和舒适的对称”(注: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44)不复存在,“出奇的稳定和可预测的气氛”(注:Lawrence Eagleburger,quoted in Thomas Friedman,"U.S.:Voicing Fears That Gorbachev Will Divide Wes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6,1989,p.1,6.)也成为回忆中的往事。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安全,而是变得更加动荡,更加不可预测。在冷战时期,美苏战略武器的均势和抗衡曾经使两个霸权国家在行为方式、战略思想和军事理论方面产生了惊人的趋同和对称,世界秩序和安全格局也曾经处于它们的掌握之中。但是,在这种表层的对称之下也蕴涵着强大的不对称力量,而这些不对称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国际政治表层对称局面的结束,同时也给各种力量留下了发展和扩张的空间。
1974年,美苏对峙刚刚显出缓和的苗头,毛泽东主席就向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提出了一个令这位学者感到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在政治家的眼中,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基于“动力学”的变化,动力学是惟一重要的因素,而静力学则不然。李政道博士的回答是:“对称这个概念绝不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注:李政道:《对称与不对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这种对称与不对称的关系也完全适用于观察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对称和不对称的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潜藏着挑战,也蕴涵着动力和机遇。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动力都来自于不对称,或意味着打破对称,或意味着创造新的对称。即使在力量相对对称的情况下,希望打破对称的动力也继续存在,使对称难以长期恒定或静止。冷战期间,维持着国际政治简单对称的力量其实是不对称的:前苏联以强大的政治机器动员了次发达的经济实力,维持了和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相对称的军事对抗力量。这种战略对称是以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对称为条件的,一旦政治的动员力急剧下降,不对称的经济力量就难以继续维持军事力量的对称。
类似的不对称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几乎比比皆是。战略核武器的均势并不能取代、更无法掩盖常规武器的不对称与竞争。美国拥有影响整个世界的强大国力,但是决定美国好战特性、可以使美国动用强大国力作用于世界的却往往不是国际因素,而是纯粹的“国内因素”或“国内政治”。(注:Will H.Moore and David J.Lanoue,"Domestic Politics and U.S.Foreign Policy:A Study of Cold War Conflict Behavior",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5,No.2,2003,pp.376-396.)德国和日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能像其他大国那样发展军事力量,但是却能够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经营地区和国际多边组织展现自己的力量。此外,国际力量不同形式的聚集突出地体现了不对称性:美、英等国仰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实施“先发制人”战略,在世界上四处征伐,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基地组织却利用不对称的隐蔽力量和不对称的社会动员力,用人体炸弹使前者防不胜防。
冷战结束了一种相对的平衡和对称,但是新的平衡和新的对称并没有建立起来。各种力量利用不同的比较优势扩展自己的利益,张扬自己的特性。不同的势力占据了不同的范围,拥有不同的支持。(注: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多数人认为布莱尔是英雄,在法国多数人认为施罗德是英雄,在德国多数人认为希拉克是英雄,在中东地区绝大多数人认为本·拉登是英雄。)各种势力都积累了独特的历史经验,都依赖着不同的社会基础,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用不同的语言说话,根据不同的方式行动,从各自不同的观念体系出发去看待世界事务。正是在这种多元的现实中,世界在继续发展和演变。因此,观察各种力量的对称与不对称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必需的方式。
二、当代中欧关系中的三种不对称性
在中欧关系史中有一个经典的不对称故事,就是英国人马嘎尔尼拜谒中国皇帝时不肯按照中国的礼节下跪。在中国人看来是合理的事情,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此后,英国人依靠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在侵略者看来是习以为常的,对于被侵略者来说,当然就是当头国难。
在当代,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三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
“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人民日报》(国际版)2003年10月14日。)认为,欧洲联盟是由一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为核心组成的“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的25%和35%,人均收入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还是只分别占到全球的5.1~5.4%和4.7%,要再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才可能达到世界经济14~18%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02年不到1000美元,与欧盟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0%,与欧盟2%的比例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欧之间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金融服务、市场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使中国和欧盟优先发展和保护的产业有所差别,发展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内部市场发育的程度悬殊,吸引外资的能力相差很大。在中欧经贸关系中,欧洲的很多产业和产品都占据着优势。这些差别既可以提供合作的机会,也能够引起利益的分歧。在最近世界贸易组织的坎昆会议上,这种利益分歧直接导致了南北不合作的局面。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从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看,欧洲的农业政策带有“单边强迫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对称还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摩擦。欧盟国家在亚欧会议机制内和世贸组织规则中极力主张“社会条款”(如最低工资标准、人权问题、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竞争法等),遭到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激烈反对。这些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地位,所剩的优势只有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注:K.S.Jomo,"Winner and Loser of Globalization",http://www.asienhaus.org/publikat/tagung97/jomo.htm.)如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条款”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就等于剥夺了后者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平等机会。
(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对称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都屡次明确表示,中国和欧盟来自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奉行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中欧之间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和不对称,这些差异和不对称还是可能对中欧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欧盟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都不乏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关切”,也不乏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公开指责。在欧盟的“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也就是欧盟第一份对华关系政策文件中,欧盟指责中国“继续拘捕持不同政见者”(注: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COM (1995)279 final.),在后来的文件中甚至批评中国“在民事和政治权利方面”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出现了恶化。”(注: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Brussels,08.09.2000,COM(2000)552 final.)在欧盟看来,尽管中国在开放社会和改革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不属于民主世界。相对而言,中国并没有对欧洲的政治和制度指手画脚,公开加以批评。
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对称以外,中欧关系中还存在着一种政治结构、特别是外交决策结构的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是由欧洲联盟的特性所决定的,它不仅影响着中欧关系,也影响着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洲联盟是一种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通过国际条约建立了超国家机制,使其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让渡了相当部分的主权。它既非传统的民族国家,又非国际组织,以“超级力量而不是超级国家”(布莱尔语)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上个世纪70年代,这支超级力量(或国家联合体)中的各个成员国对它们在联合体中享受的权利和退出的自由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欧洲共同体因而确立了“灵活的一体化模式”和“开放式的合作网络”,使各个成员国能够根据各自在经济、行政和立法等方面的差别,选择适应它们各自发展水平的合作方式和程度。“灵活的一体化”所形成的欧洲共同体是一种结构相当独特的政治体,它在不同领域里有着不同的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制度结构,成员国和超国家的欧洲体制之间也就有了不同的权力关系。例如在经济贸易和货币领域里,超国家的欧盟机构享有最高权力;而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里,尽管政策与机构都在从政府间合作方式向超国家方式发展,尽管在欧盟的层面上已经建立起了力争“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高级代表机制,并将在可见的未来产生真正的欧盟外交部长,但是迄今为止,成员国仍然享有作为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言和行动的充分的外交权力。
欧盟的决策体制复杂得超乎寻常。在核心成员国的国内本来就已经存在着复杂的共同决策机制和社会伙伴关系,而在这种决策机制之上又增加了一套欧盟层面的体制,使得欧盟的决策机制中有着众多起作用的因素和力量:欧盟机构、民族国家政府、协会、企业、地区和研究机构。(注:Ernst-Otto Czempiel,"Governance and Democratization",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 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5-256.)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或政体中都很难找到与此相对称的权力分享和制约机制。
欧盟内部的多重机制还不是欧盟制度复杂的全部原因。欧洲尚处于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一个联合的欧洲不可能一蹴而就”,(注:罗伯特·舒曼语。转引自:Stanley Henig,The Uniting of Europe from Discord to Concord,London:Routledge,1997,p.22.)欧洲联盟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决策工具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例如,撇开经济动因不谈,仅从机制的角度看,欧盟外交就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其一是成员国维护外交主权的努力;其二是共同体寻求联盟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前一种努力使得早期的“欧洲政治合作”无果而终,后一种努力自1987年《欧洲单一法令》颁布以来就不断地取得进展,使成员国保留独立于欧盟的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的同时,建立起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结果就出现了被罗伯特·库柏称为“后现代的国家”的那种既非超国家、又非国际组织的,有着多层外交政策机制的奇怪政体。这种政体造成了大量的观念混乱,它使许多与之交往者都困惑不已:究竟是谁在制订欧洲外交政策?欧洲究竟有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程序?在不同层次上的欧洲外交政策议程中究竟都有哪些议题?欧洲人都使用哪些外交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他们的外交政策成果究竟是些什么?
由于欧盟的对外政策牵涉到联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和行为体,它们在制订政策的程序、优先议题、政策实施工具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差别,所以必须首先确定它们的特性,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动力、共同朋友和敌人。这些并不容易做到,并且大大超出了以“政府外交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欧洲的行为者们有时候组织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有时候又各玩各的游戏。它们交替使用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方式,让外界看上去眼花缭乱,不免产生疑虑和误解。欧盟这个多国的、多层的、变化中的、时分时合的政治行为主体给国际秩序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新的影响。要了解它的外交策略的核心与动力,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挑战。
(三)历史文化的不对称
世界各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产生差异是自然的。但是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不对称性:欧洲文化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一直是以一种自我认定的强势文化态势向世界各地扩张,欧洲人更是将他们对于社会和事务的理解带到世界各地。直至二战之后,这种文化强势地位才部分地随着商业文化的兴起而转移到了美国。不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洲认同感的增强,欧洲文化重新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表现出和美国文化的差别和相对于美国商业文化的优越感。
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自我批判的弱势地位,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为用”,总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多,张扬或扬弃自己的文化少,从而形成了中欧之间历史文化的不对称性。欧洲人在欧洲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用欧洲人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模式来观察、评论中国的事务;中国人也从中国的角度来评论欧洲。但是由于文化力量的不对称,中国人很少会像欧洲人评论台湾、人权、西藏问题那样去评论北爱尔兰问题、极右翼问题和反犹问题。
由于上述的不对称性,中欧关系相对于美欧关系和俄欧关系就有了一种质的差别。库柏曾经断言,外国人不仅是不一样的,而且对外国人产生误解也是不足为奇的。欧美之间尚且如此,中欧之间更其甚焉。从自己的背景出发,去评论甚至评判对方,所谓“以己度人”,假设外国人和自己一样,是产生外交领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那些能够用各种舆论的、话语的、强力的、经济的手段去体现强势地位的国家和政体,它们能否认识到这种不对称性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对于建立并维护国际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在商品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引起“逆向选择”,导致相对优质的商品自动退出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而使市场体系失效。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是否也存在着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呢?如果实力的对比已然不对称,对短期相对优势的错误判断,或对其他多种实力的不切实际的计算,例如,以为靠武力可以取胜,或者靠制裁可以得手,或者靠舆论工具可以达到目的,那么就可能把国际准则和其他正常的外交方式挤出国际关系领域,使整个国际交往的质量下降,安全系数降低,形成怨怨相报的恶劣国际环境。
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怨怨相报的问题,但是不对称所造成的误解或错解仍然存在,这些误解或错解也有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逆向选择”,因此值得我们关注。
三、寻找对称性与互补性
中欧伙伴关系之所以能够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双方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在诸多的不对称中认识并寻找根本利益的对称性和局部利益的互补性,从而推动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
(一)寻求战略共识与扩大合作范围
从“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和欧盟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到,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种突出的对称性,这就是中欧双方都将对方看作是现存世界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欧洲安全战略文件”(草案)将中国确立为欧盟安全战略关系中的重要伙伴之一,中国在首次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则明确指出,“未来欧盟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重视欧盟的作用和影响。基于这种相互之间的共同认识,中欧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前提,以相互尊重为基本原则,采取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促进发展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中欧合作伙伴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寻求高层战略共识。与欧洲一体化之初相似,中欧合作初期,双方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互猜忌、指责和不理解。自从中欧双方最高领导人认定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以后,中欧之间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高层认同出发,开始寻找具体的合作机遇。就像欧盟成员国既有各自的“国家身份”,同时又有“欧盟身份”一样,中国和欧盟既有各自独特的身份,又有类似的“国际身份”和对于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有在一种国际秩序下通过合作维护各自利益的诉求。这是中欧之间根本的共同点。在这种高层认同的前提下,中欧之间的差异就不再是妨碍中欧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绊脚石,而是成为中欧相互借鉴、学习与互惠的机遇。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中欧之间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开展了合作,在加强联合国地位、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敦促早日恢复伊拉克主权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或相似的意见与立场;在军控和裁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做出了共同的努力与贡献;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和人权基本原则方面进行了对话与合作。保障安全与创造繁荣、避免战争和消除贫困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最高的认同。从这种认同出发,中欧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延伸到了各个具体的领域和项目之中。
中欧之间战略合作的基本精神分别来自欧洲和中国的经验。从欧洲的经验看,“规模意识”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在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文献中,“规模”被看作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根据这种判断,欧洲在接受苏美两极格局的同时,一方面认为中国将比日本更有希望在东方取得经济成功,另一方面认定,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注:Stanley Henig,The Uniting of Europe from Discord to Concord,p.8.)当然“规模意识”的动力源首先还在于对欧洲安全的关切。欧洲一体化早期的设计者让·莫内关于“通过扩大范围解决难题”的思路将法德两国的世仇成功地变成了六个利益相关国家共同解决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更高的战略。扩大解决问题的范围还为加深在欧洲伙伴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更多的国家参与同一问题的解决,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比较优势。于是,个别的经验变成了共同的经验,相互学习造成了相互影响、渗透与趋同。
中国的现代外交也体现了“扩大范围”的思路。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并主动通过建立多边机制和组织多边磋商处理国际难题。例如中国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了互利共赢,与东盟共建自由贸易区;为了缓解朝核危机,开创了北京六国会谈机制。在扩大了的多边环境中,以平等、互信、强调共识和共同安全等方式和平解决冲突,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扩大范围的思路一是扩大,二是深化,即通过扩大合作的领域,使合作得到深化。这种思路特别适用于在中欧之间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中欧高层之间富有成果的政治对话机制为加强战略互信,在中欧之间开展多领域、多层面、多渠道的对话拓宽了道路,在很多领域里产生了国家间、非政府或次政府间的合作。这样的交流还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国际领域里,扩展到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亚欧关系的框架中,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平等对话与良好合作。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国家的合作结构可以有效地抵消中欧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不对称性,将合作伙伴关系从宣言变为实践,从体制对体制、政体对政体的关系深化为人民对人民、同行对同行的关系。中欧合作的经验证明,当合作机器开始运转之后,许多由于制度不对称引起的误解、矛盾和分歧便被裹胁进这台合作机器,成为被机器消化的对象,其对中欧合作伙伴关系造成的危害就相应减少。
(二)在经济社会不对称中寻求社会经济互补
在共同追求繁荣和发展的过程中,欧洲拥有资本和技术的优势,中国拥有人力和市场的优势,这些要素根据市场的规律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使中国和欧洲之间有可能相互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所以,公平的市场是中欧之间在经济发展不对称的条件下达到双赢目的的一个重要场所,而公平的市场规则是保障这种双赢的条件。
当然,要使经济社会和市场发育不对称的合作伙伴承认共同的市场规则绝非易事。欧洲的市场机制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不仅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其内部市场也具有一些独特的规则。欧洲仍希望能像历史上那样,继续用自己对于市场规则的理解,影响世界市场的发展,同时在世界竞争面前既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又保护欧洲内部市场的特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迅速、规模宏大的经济体,欧盟既看到了投资的场所、产品的销路、技术转移的可能,也看到了欧洲经验输出的机会。对于欧盟来说,后者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其动力源仍然是欧洲的“安全情结”。这种“安全情结”使得地处欧洲大陆的国家不断地为了自身的安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同化力。在历史上,作为安全机制的“欧洲协调”在形成的过程中就部分地依赖于在欧洲大陆保持各国类似的专制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的机器以和平的方式,不断地扩大核心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力,(注: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4页。)促使其市场规则在欧洲和世界的广泛应用。欧洲人清楚地看到,只有在这种规则下,欧洲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与保护。
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差别很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着自己的规律。由于规模大、人口多,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世界能源和粮食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欧洲的福利地位和维持既定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欧盟的关注超出“直接的贸易与投资联系”。除了扩大贸易量和加强经济联系以外,欧盟更加重视防止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冲击世界市场,减少这种增长给环境造成的影响,避免出现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为此,欧盟强调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帮助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和均衡地增长”,同时力争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市场的开放“符合”欧洲的利益。保持持续和均衡的增长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开放中国市场有可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惠及欧洲,因此,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利益相关,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欧洲。
促进上述双赢局面的最佳方式一是加强对中欧的经济贸易合作,二是加强中国自身的市场能力。中欧领导人早就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优先发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意义,并且在推动投资和贸易合作的同时,建立了双边的工业产品规则的对话机制。通过对话机制,中欧将更加容易理解对方的工业政策和利益诉求,更加了解在产品交换和资本投资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对称而造成的利益纷争和误解,从而为进一步开展企业对企业的合作铺设桥梁。
在加强中国自身的市场能力方面,中欧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对称恰好为合作提供了契机。发展中的中国向发达的欧洲学习发展经济、建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欧洲对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关切来自于欧洲工业化的教训,而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中欧之间这种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大量存在,在此基础上,中欧之间的合作与分工领域还有待拓宽。
2003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 000亿美元的大关,比1975年中国和欧洲共同体建交的时候增长了42倍。由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华出口有“较强的替代性”,而中国对三方的大宗出口则差别较大,市场规则有利于中国“选择合作伙伴”。自1998年起,欧洲对华投资的增速已经超过美、日而居首位。来自欧洲的投资具有平均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且多集中于中国亟待发展的行业(如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及医疗器材制造业、电子、电器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工制品业、食品及饮料制造业和机械工业等)。(注:裘元伦、王鹤等:《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页。)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界人士以他们特有的敏感,不断地发现中欧经济的互补性,并且把这种互补变成现实的商业机会。
当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中欧在众多经济领域里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坎昆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未能取得成功反映了这种不对称的利益。但是,这种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中欧之间,也存在于欧美之间,存在于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但是,这种不对称并不影响中欧发展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由于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中欧在海运领域,在技术合作领域,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在海关合作统一打击商业欺诈领域,在民用航空和空间技术领域,在更加广阔的产业政策、社会信息、宏观经济、公共卫生、就业、教育与培训等领域,双方发展的不对称性都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供了机遇。
(三)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宽容
鉴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都如江泽民主席在中国文联六代会上指出的:“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注:潘嘉来:“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策略——对东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人民网(社会文化版)2003年11月26日。)不同民族参与“明道立法,制礼作乐”是各个民族天经地义的责任和权利,在文化领域里本来就不可能存在雷同,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不仅是必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洲联盟都强调文化多样化,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对称的文化有了一个对称的基础。对此,中国和欧盟都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了解与理解。过去欧盟方面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单方面批评已经发展为中欧双方的人权对话机制,过去欧盟对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状况进行了大量的指责,但是从尊重不同文化的角度出发,这种指责也渐渐地化为积极的合作。欧盟及其成员国援助了中国的法官培训、乡村基层民主的选举试点以及许多类似的项目,在不对称的文化中间铺设理解的桥梁。
解决历史文化不对称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各个民族以世界平等公民的身份相互尊重,而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2003年12月,中国以“文化与文明对话”为主题,主办了亚欧会议部长级会议,这对于增进中欧和亚欧的文化理解与合作,消除文化和文明的不对称造成的不利影响,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文化合作可以避开政治合作的敏感性和经济合作中的利益之争,因此更为便利。而且,无论是政治关系的加强,还是经济合作的发展,都会涉及中欧之间思想、文化、观念的交织、碰撞与相互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欧洲都追求更安全的环境、更高的福利、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自然条件。这种共享的目标“太具有根本性了,任何其他短期的民族国家的考虑都不能以此为代价。”(注:Stanley Henig,The Uniting of Europe from Discord to Concord,p.32.)
实现共享目标的必经之路是建立共享文化。凯特·克劳斯认为,决策者们在界定他们的安全利益的时候使用物质利益概念和文化特性概念,这些都“来自于他们的共同的历史/社会/文化经历,以及他们的领悟力”。(注:Keith Krause,"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Multilateral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Dialogues:An Overviews",in Keith Krause,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p.3.)可以想象,中欧之间交往与合作的经历越丰富,中欧双方决策者共通的想像力和领悟力将越丰富。这种想像力和领悟力建立在欧洲对于“中国方式”的理解和中国对于“欧洲方式”的理解上,文化交流因而可以成为对外关系中一种促进的力量。
(四)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分别寻求共赢
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外交在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地位平等、责任、互不干涉内政、自我约束并信守规则和承诺、不寻求个体力量的最大化,(注:帕特里克·摩根:“多边主义与安全:欧洲的前景”,约翰·鲁杰:《多边主义》,第382-383页。)那么由于这些方式和原则在欧洲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到了20世纪,欧洲的外交格局就早已不仅仅是大国外交,而是包括了“共同体外交”(欧盟外交的经济部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欧盟外交的政治部分)以及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等三个不同的机制。即使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双边外交领域里,欧洲大国之间传统的民族国家决策方式和“合作习惯”也因它们“从共享信息获得的优势”,因它们“对共同威胁的集体回应”,因“越来越多的协作可以节约成本”而明显地改变了。(注:C.Hill and William Wallace,"Introduction:Actors and Actions",in C.Hill ed.,The Actors in Europe's Foreign Policy,London:Roudledge,1996,pp.1-16;Brian White,"The European Challenge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5,No.1,1999,pp.46-47.)
欧洲联盟外交的上述特性也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结构和内容:在中欧关系中既包含了中国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包含了中国和作为国家联合体的欧盟之间的多边政治关系,还包含了中国和欧盟在经济贸易领域里的双边关系,因为欧盟在经贸方面获得了最高权能。这些不对称的关系既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也给中欧伙伴关系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带来新的规则。
从有关中欧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来看,中国和欧盟之间对“中欧伙伴关系”的定义就与中国和法、英等欧盟成员国对“中法伙伴关系”或“中英伙伴关系”的定义有所差别,在表述上既有重合,又有不同的侧重。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涉及了裁军、联合国改革、环境保护、经济贸易、文教科技等许多方面,同时特别强调,两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尊重多样化和民族独立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具有密切合作的共同意愿。中英伙伴关系突出两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磋商,在人权方面的对话,在经济贸易、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造、社保建设、环境保护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合作。由于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职业教育合作伙伴,所以在中德关系的各种表述中,发展更好的贸易合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述差异说明,对欧洲的多层外交既需要整体战略,也需要局部战略。局部不能说明整体,整体也不能替代局部。发展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可以突出欧盟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并借助这种多样化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在中欧关系中,成员国历来而且仍将是欧盟发展友好的对华关系的最主要的动力和根基。不少对中国有利的欧盟政策也来自于成员国。例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希腊1997年在日内瓦撤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控,这一行动导致次年欧盟外长理事会发表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宣言,使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强调“对话”和“合作”成为可能。
在对欧盟作为整体的经济关系中,或对欧盟作为集合体的多边政治关系中,同样存在着共赢的机遇。例如,2002年5月,占世界打火机市场70%的温州打火机就面临欧盟标准化委员会2002年4月通过的一项新的欧盟规则的挑战。温州打火机虽然满足了市场经济的五大标准,但是却受到了新规则的歧视。于是,这样的分歧已经不能在中国对成员国关系的层面,而应在中国对欧盟关系层面上得到解决。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与单一制国家不同,欧盟集合了各种利益,同时又获得了最高权能,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欧盟的特殊规则和标准,对于发展良好的中欧关系至关重要。
同样,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欧盟内部的多边主义有可能平衡单个国家的“私利”。如果一个成员国想采取过激的对台湾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可能因为与其他成员国的对华利益不符而遭到反对,无法通过欧盟的多边程序而成为欧盟的整体政策。因此,理解欧盟这台与中国不对称的决策机器,了解它的政策动力来源,也可以推动欧盟对华政策的发展,使其比某些成员国的对华政策更加理性化,增加更多合作的机会而减少冲突的可能。
当中国和欧盟共同处于多边环境的时候,中欧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其他的结构不对称状况。例如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或在亚欧会议框架中,由于欧洲联盟独特的内部结构,它的多边主义至少比中国多了一个层次。对于其他单一制国家来说,到底谁代表欧盟?这个问题始终令人迷惑。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合作伙伴关系也大有可为。多边主义的假设是尊重国际法,特别是规范国家行为和促进国际合作的规则。(注:Qin Yaqing,"Study of Multilateralism:Theories and Methods",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October 2001,p.10.)当今世界的各种力量极不对称,当代国家的边界正日益被各种交通和交往的工具打破。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在这个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像欧洲联盟这样的行为主体。由于欧洲联盟自身权能有限,它没有硬力量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而是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下,通过在国际规则中运用“软力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中国和欧洲联盟可以共同提倡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均衡发展以及和平的世界秩序,为双方的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在法国创造的传统的双边外交体系中,国际交往的方式和规则是以国家为基础,通过具有官方身份的使节,进行国家对国家的交往。这种外交的惟一尺度就是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发展。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国家仍然将“它们自己国家的福利看得高于一切”,就像摩根索所说,“多数人过于拘泥于他们传统的国家特性,而忘却一种可以理解的目标。”(注:See D.Miller,On Nation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184.)正是出于这种国家利益,英国在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还提出了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成员国和欧盟的对华贸易政策。
不过,双边外交的目的一是国家利益,二是国家特性。如果国家自身的利益和特性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双边外交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欧洲。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中欧关系出现双边和多边共存的局面。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远未将欧洲联盟变成一个“超级国家”,中国对欧洲各国的关系也不可能简单地化为一种中国和“欧罗巴合众国”之间的对称关系。至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欧洲”?(注:See for example,John Agnew,"How many Europes?The European Union,Eastward Enlargement and Uneven Development",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January 2001,p.29.)中国对欧洲关系需要考虑到多少因素?这个问题是欧洲带给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它决定了中国和欧盟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将长期存在。
对于欧洲联盟来说,多层的结构使得欧盟获得了一种单一体制国家所没有的能力:通过这种结构,欧盟将具有多种对外交流的推动力,并且可能达到单一体制国家难以企及的外交深度和广度,可能与合作伙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与一个多层结构的伙伴交往,便要学会更多的交往规则,开放更多的交往层次,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从多层次的交往中获得的机会与利益更加丰富和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