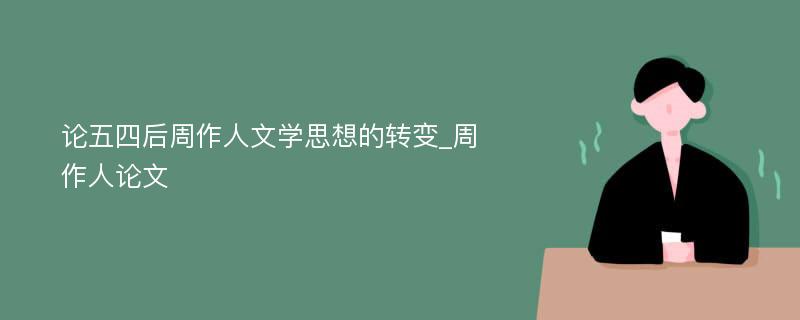
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思想论文,周作人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0]01-0100-03
20年代初,随着黑暗政治加剧,复古思潮泛滥,新文化阵营分化,一度轰轰烈烈的“五四”趋于退潮。这使“新文化”人纷纷陷入迷茫和困惑。一直以“中国新文学运动干部”(注:陶明志《周作人》,P.102,上海书店影印。)的身姿为文坛注目的周作人,同样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瞻前顾后、驻足不前,一度支撑他精神大厦的“流氓鬼”信念摇摇欲坠,他逐渐在“人间的悲哀和惊恐”中流入颓唐,失去了时代先驱者的“热和力”。(注:《过去的生活昼梦》。)他这样自剖:“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托尔斯泰的无我之爱和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注:《雨天的书·山中杂信》。)这是身处“五四”退潮期周作人精神世界极度紊乱的真实写照。这使他最终从文学中“寻求别的慰解”,(注:《雨天的书·山中杂信》。)将文学当成现实的避难所。为此,他要建造文学的“十字街头的塔”,让自己“在喧闹中得安全地”。(注:《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由极度混乱、矛盾走向转变,是周作人“五四”退潮期文艺思想的总特征。
一
放弃“为人生”,转而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主张,是“五四”退潮期周作人文艺思想发生转变的首要表现。
1922年1月,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明确表示了对此前热衷的“为人生的艺术”的异议:“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艺术是独立的,却原来又是人性的,可以既不必使我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艺术好了”。显然,在文学革命口号已提出整整五年之后,周作人已不满于自己当初对于“为人生”派的选择,竭力想“修正”他的理论航向——“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周作人要求新文学以纯粹的个人表现为目的,让接触了作品的读者获得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从而使之成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样,文学成为周作人所谓的“浑然的人生的艺术”——周作人这种充满哲学思辩与经验主义色彩的自圆其说并不能掩盖他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与矛盾:一方面,竭力想逃进艺术的“象牙之塔”以远离现实的浑沌与汹涌;另一方面,此前对于人生的关注又给他一种惯性般的驱动力,使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文学功利性的认同。
从文学革命初期提倡文学“为人生”到此期推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的文学主张,周作人的这一理论选择也深刻地印证出他的思想变迁。“五四”初期,周作人虽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其精神贵族的优越与矜持,但感情上还是表现出一种接近民众、投身社会、关注现实的强烈意愿。这从他早期写下的具有浓厚平民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的诗文可以得到验证。“五四”退潮期,周作人逐渐在情感上疏远了民众,他对于民众的态度,已由前期的关注、期待转为此刻的淡漠、怀疑、失望及至蔑视。他认为对“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进行思想启蒙与道德感化,“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周作人这番思想源出十九世纪英国机械进化论者斯宾塞的“道德教训无用论”。当然,周作人还没有彻底滑入这种社会教育有害论的泥潭,他对于斯宾塞的认同一如他之于庞德、厨川白村、叔本华、尼采等精神导师的亲近,完全出于一种理论上自圆其说、思想上寻求庇护的需要,并无多少理论信仰与继承的成分。尽管周作人从未停止过对域外文艺思想的复述与援引,但与真正的理论信仰与继承相去甚远;在他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的引用中,信手拈来、生吞活剥的理论惶急之态非常明显;这倒不是缘于他的思想浅薄与理论无知,恰恰是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阻止了他向域外文艺思想的真正靠拢。——虽然周作人并没有在斯宾塞面前走出多远,但他疏远民众、远离社会的精神贵族相已昭然若揭:“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得不否认”。(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文学革命伊始,周作人一度成为“人生派”的理论旗手,但“人生派”作家身上几乎不约而同表现出的对时代——社会——民族——人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渐渐不合于周作人过于看重个人的文学思想;20年代以后,“为人生”的文学思想逐渐向“革命文学”过渡,这更难见容于周作人将文学作为精神乐园的个人的趣味。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与其说是为了号召,不如说是出于自慰罢了。显然,对于民众的疏远、对于社会的隔阂、对人生冷漠,伴随着这位孤独的思想者踱入“自己的园地”——走进了一个难以复出的艺术迷宫。
二
对“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取舍态度的转变,是五四退潮期周作人文艺思想发生转变的第二个方面。
周作人曾说自己思想上常有两鬼在搏斗——“流氓鬼”(实为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与“绅士鬼”(实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五四”时期,他基本上疏远“绅士鬼”而靠近“流氓鬼”,这使他在文学上打出了“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的“平民文学”旗帜,随着“五四”退潮,周作人很快离开“流氓鬼”而亲进“绅士鬼”,这表现在他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态度上的折衷做法,这便是“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主张。
在《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周作人全盘否定了自己“五四”时期对“平民文学”的选择(即他所谓“‘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最坏”的说法),他把文学中的平民精神引申为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把文学中的贵族精神引申为尼采的“求胜”意志。
权力意志说是尼采“超人”意识的哲学根据,有着浓烈的贵族主义倾向,这十分投合此期周作人的文学趣味。由此,周作人开始了域外文艺思想的新一轮援引和借鉴。与此前对俄罗斯文学精神的明确信仰相左,他开始要求文学表现“求胜意志”。反对“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中来”,认为文学中的“平民”与“贵族”的区分并非在于阶层、阶级,也不是文学作品的题材、服务对象或创作主体,而是人类共通的“对于人生的两样态度”。周作人批评“平民”文学过于现世,太满足于现状,充满功名利禄观念和大团圆思想,缺少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追求,这种缺陷恰好是“贵族”文学能够加以弥补的,在他看来,“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凭借了自己的特殊权利”,能“引起一种超越的追求”,这种“超越的追求”正是“贵族”文学的主要特点。周作人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他主张“文艺应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据此,他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主张。
不可否认,文艺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不仅需要真实地描绘(再现)生活的真实相,更要透过表象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相,特别是要表达出对于人类未来的理想和憧憬。因此,周作人的这一主张,有其内在合理性。新文学运动走到20年代,总体上确有“过于现世”的倾向,缺乏周作人所要求的那种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追求”的作品,从小说、诗文到话剧,大多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图解与注释——这显然与新文学运动的“左旋”不无关系(注:汪应果《科学与缪斯》,P.139—140,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缺少对于个体精神的探究,诸如对于灵肉冲突的体验、关于死亡的思考、对人类终极的探求、……这些颇具“现代”意味的文学主题,正是周作人同时代的许多欧美作家致力表现的。对此,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至于世界文学的译家”(注:陶明志《周作人》,P.102,上海书店影印。 )的周作人有广泛的了解(在对世界先进文学精神的接触与吸收上,周作人无疑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周作人不满于文坛现状,要求新文学作超乎人生表层的描写,这有益于新文学的发展。
但是,周作人“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主张,从根本上连着他此期思想意识深处中越来越浓烈的贵族化倾向,他是出于一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乃至轻视而将兴趣与希望转移到少数知识者身上的。在《乡村与道教》一文中,周作人露骨地表示了对精神贵族的膜拜:“人类的真的主宰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世界正是由“聪明的少数人”管辖“愚钝的多数”。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平民的贵族化”实际上就是文艺的贵族化。周作人要求文学作品更多地表现“求胜意志”和“超越的追求”,淡化现实生活的描写;同时进一步强化文学的艺术性,这一切充分显明他对于“贵族文学”的倾心与依赖。
三
抛弃文学的社会反映功能(再现),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表现),是“五四”退潮期周作人文艺思想发生转变的第三个方面。
“五四”时期,周作人看重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的紧密联系,把文学当作客观社会生活的再现。他要求新文学表现的情感、情绪——即所谓灵肉一致的人性观、利己利他的人道主义——基本上是立足于“人间本位”的思想。在文学研究会中,是周作人首先“把人的文学”同“为人生”的文学宗旨统一在一起,他强调他之所谓“人的文学”应该“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周作人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是在他明确主张中国文学应该向俄苏文学靠拢的立场上提出的。20年代以后,周作人开始强调文学的个体属性,认为文艺完全是作家的自我表现。他在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这种观点:
“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注:《文艺上的宽容》。)
“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注:《诗的效用》。)
“诗的创造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注:《诗的效用》。)
事实上,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蜕化虽然带有某些对现实“抗争”的色彩,但从根本上仍连着他对“思想革命”的失望。1928年10月,他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中宣称“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五个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了一阵臭打”。周作人感到中国的民众基础还不适宜倡导“思想革命”,因而他干脆要求作家放弃自己曾热衷提倡过的“主义和运动”,转而专注于诚实表现一己情怀,在周作人看来,抓住了“自我表现”,至少还抓住了文艺的“艺术美”。
这一时期,周作人开始更多地到西方表现派文艺理论中寻求安慰与解脱。一度表现出对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的强烈兴趣。厨川白村关于艺术本质的解释十分合乎周作人的文学趣味,他从《苦闷的象征》主要“借用”了两点:其一,便是把文艺作为纯粹一己之“自我表现”;其二,则是认定艺术超乎一切功利之上。但他无视“苦闷说”中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周作人的理论功底和译介能力,这一“无视”实乃出乎有意的忽略,联系周氏援引域外文艺思想的一贯作风,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更不能理解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厨川白村后来文艺观的转变。厨川白村最终意识到作家表现的“苦闷”是在生命底处“两种力”(即生命力和压制力)冲突而生的大苦恼,文艺必须执着于人生,直面惨谈的现实,他拒绝将文艺看作“花鸟风月之事”,认为“文艺决不是俗众的玩弄物,乃是严肃而且沉痛的人间苦的象征”。同时,厨川白村认为艺术家个性的自我表现,并非完全无关乎客观社会生活,他明确指出:“不要误解,所谓呈现于作品上的个性者,决不是作家小我,也不是小主观,——其创作家有了竭力忠实地将客观的事象照样地再现出来的态度,这才从作家的无意识心理的底里,毫不勉强地、浑然地、不失本来地表现出他那自我和个性来。”(注: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创作论》。)——这是“苦闷说”的矛盾之处,也正是它的深刻之处。如果说,厨川白村是出于一种艺术家的良智与敏感找到了“苦闷说”的复归之路;那么,周作人恰恰正是由于思想、理论深处摆脱不了的“贵族”气味,从“苦闷说”彻底陷入了一个理论泥潭:视“严肃而且沉痛的人间苦”不见,偏要在人生的十字街头构筑自己的“象牙之塔”。周作人后半生恍惚迷力的人生悲剧无疑为此作了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五四退潮期的周作人基本偏离了前期思想演进与理论选择,过重的传统文化的负载、对于“思想革命”的失望、向域外文艺思想的片面借用,使他放弃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之所谓“浑然的人生的艺术”、“平民的贵族化”、“自我表现”的文艺主张,其实质是片面强调文学的个人属性,割裂文学表现与再现的功能关系,扼杀文学的社会意义。由此开始,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P.2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激烈得快,颓丧得也快,这也许是对这位新文学倡导者此期文艺思想演变轨迹的最好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