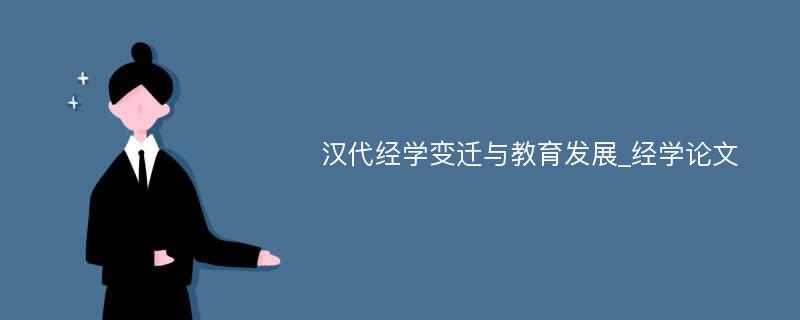
经学变迁与两汉教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两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10)04-0064-05
两汉教育承前启后,其发展变化颇具特殊性。教育发展的背景不是经济发展,而主要和经学谶纬化有关,下面就此作些探讨。
一 经、经书、经学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木牍,因每片容量有限,要用多片才能表达完整一篇文章,为便于阅读,就用丝线等横向把众多片简牍串联起来成“册”。这里的丝线就是“经”,因有把简牍连缀成书的功能,后来就成了书籍的代名词①。伴随着儒学影响扩大,“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纲要,其所指范围缩小,专指儒家典籍——经书,以与一般书籍区分。
经书所指也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春秋时期就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但《乐》未流传下来,实际只有五经。后来,《礼》分为《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左氏春秋》、《榖梁春秋》、《公羊春秋》,这就成了九经。到唐代,《孝经》、《论语》、《尔雅》也成了经,就是十二经,宋代朱熹加上《孟子》,就是十三经。
从内容看,经书既有对先秦风土人情、民歌国颂、典礼制度、占卜筮辞等的记录,又有反映古人对宇宙起源、天文地理、草木虫鱼鸟兽等的认识。大至治国、平大下,小至修身、养性、齐家,都可从中挖掘到相关资料,是名副其实的古代百科全书。其中如《春秋》中有关日食、地震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就为后来谶纬所利用发挥。
那时受书写不便和“文字异形”的影响,书面交流不便,因而口耳相传是主要信息交流形式。这种传播方式虽然非常灵活,但受时空限制也很明显——只能近距离的传递和交流,且保存性极差。所以,作为对儒家经典及其阐释的经学,在长期彼此信息交流不畅、各自流传发展的情况下,就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如阐释《春秋》的,就有《左传》、《谷梁传》、《公羊传》等,《诗经》也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之说。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起初不过是经书传本所用文字不同,加之简牍容易出现断简错简等问题,导致誊抄本不一致,对经书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分歧逐渐增大,最终发展成对立的学术体系。今文经学偏重微言大义,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如《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观念就非常明显,思维显得漫衍恣纵,这些都为谶纬吸收。
二 谶纬和两汉经学结合
谶纬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产生出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以拆字、生肖、五行等中国特有的方式对未来前景进行预测,其特点有敬上天、法圣人、尊儒经。
(一)谶纬的发展
谶的起源很早,据天象以卜吉凶在春秋时期就很普遍。谶作为一种预决吉凶的神的隐语,先秦以降的书中就有不少记载。顾颉刚认为《河图》、《洛书》是最早的谶书[1]92,《史记·赵世家》表明春秋时期就有“秦谶”、“赵谶”。不过还只是一些谶语的零散片段,附杂在经史书中,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
秦汉之交,社会变动剧烈,人生命运难测,祸福无常,于是鬼神符谶大量出现,作为对谶进一步解释和补充的纬也出现了。西汉时期,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有意附会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认为自然灾害是天对人间统治不善的警告:老天先以自然灾害示警,如执迷不悟,又以怪异现象告诫国君,如仍然顽固不改,统治地位就有危险[2]304。于是,相信自己命运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掌控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天子也“畏天命”,承认受命于天,相信只有以诚心诚意感动天,行德政,弃恶从善才能获得保佑,风调雨顺,政通人和,长治久安。
之所以如此崇拜天,是因为自然的天已被当作有意志能支配一切的神秘的天。它高高在上,监视着人间的一举一动,对人的善恶,了解得一清二楚;它主宰赏罚,以祥瑞灾异来表示对人间统治者施政得失的态度,如果统治者治理有方,国泰民安,天就降甘霖雨露等祥瑞表示赞许;如果统治者“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甚至“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就会蓄积怨恶邪气,最终导致“阴阳谬戾而妖孽生”,[2]306灾异就会发生。当然,人间帝王也可以采取措施使天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如天灾不断,帝王若顺应天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下诏减免赋税,体恤百姓,上天就会转而降下福祉,保佑人间帝王。
西汉末年哀帝、平帝时期,伴随着社会政治危机加深,谶纬日渐流行。而到了东汉,谶纬更呈泛滥之势,因为东汉建国和施政都靠的是它,于是整个社会笼罩在谶纬中,盛行将其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不满腐败政治的士大夫利用谶纬向当权者发出警告或抗议,有政治野心的则利用谶纬为篡夺政权制造舆论。
东汉末年,谶纬之学逐渐衰落,原因在于其不利于统治者,它既可以成为阴谋家的借口,也可以成为农民起义的口号。魏晋时期,屡遭禁止。隋炀帝执政后下令大量毁灭谶纬书,但谶纬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天灾人祸、宫廷政变、朝代更替、人民暴动中,仍可见谶纬身影。
(二)谶纬与今文经学
西汉建立后,今文经学首先得到发展,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其中蕴涵微言大义,因而盛行章句之学,有别于训诂之学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这种释经方式被谶纬吸收发展,开启了牵强附会神化儒经的滥觞。
作为今文经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把先秦以来的神学观念、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都纳入以天为本体的解释系统,将“天人感应”理论化、系统化。关于这一点班固说得很清楚:“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3]1082其特点是把儒家的德治仁政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沟通天道(宇宙自然观)与人道(儒家伦理道德),将人伦关系天道化,或者说使天道人伦化,并通过影响皇帝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太学是西汉今文经学传播的主阵地,到西汉末和东汉又是制造谶纬的渊薮。谶纬化后的儒经中的祥瑞灾异说,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首先,用于解释政权的合理性。认为王者将兴,必先有符谶出现,如王莽说自己在未央宫前得到“铜符帛图”,就宣称他承“天命”可为真皇帝[3]3020。其次,用于解释灾异发生的起因和国家施政的合法性。认为君主为政的好坏也有符瑞与灾异以应验之,如发生了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皇帝就下诏自责,认为是朝政有失导致天的惩罚。朝野上下都流行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言天地、释人事,为现实的政治活动寻求理由和根据,而经书中的祥瑞灾异又为谶纬提供了思想养料。
可见,儒学与谶纬是相互需要的,一方面,儒学需要以符谶为内容的迷信思想来为皇权统治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谶”也需依傍经书的权威来扩大其宣传效果,于是二者相互渗透整合,最终成为一神学色彩浓厚、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不仅神化了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把孔子变成了受天命而为汉制法的通天神人,儒家典籍也由不可怀疑的“经”变成神秘的“天书”。经学就这样被谶纬化了。
这些由人制造出来的神话及其预言,今天看来荒诞,但在当时却极具震慑力,从天子到草民,大都信服,差不多成为国家信仰。
当然,即便是在谶纬作为御用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有人对谶纬有清醒的认识,如桓谭就主张远离谶纬,认为谶纬荒诞不经,是虚构出来的,以欺骗迷惑统治者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孔子及弟子都不言说谶纬[4]955。
三 经学谶纬化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
谶纬流行,使汉人崇拜古圣先贤、尊从儒家经典的心理浓郁,固化定型为集体无意识。特别是东汉的光武、明帝、章帝统治时期,由于皇帝重视提倡,谶纬大行其道,国家大政、官员任免等要有谶纬作为依据才正当,兴办学校的动力和教育的内容,也都打上谶纬的印记。
(一)对政治的影响
慑于天的威力,汉人的崇天、畏天心理很浓厚,从《汉书》、《后汉书》来看,两汉皇帝下罪己诏书很多,仅汉成帝一朝,就达13次之多。当地震、洪水等天灾和日月食、彗星出现时,皇帝就诚惶诚恐,因为按照天人感应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才会“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5]92因而就有不少皇帝在自然灾异面前胆战心惊、自我谴责的记载,如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天,发生泥石流,皇帝就下诏自责,认为天灾地孽,是自己为政有缺失[3]172。
东汉时期,随着谶纬风行天下,一有天灾人祸皇帝就自我检讨施政失误,如章帝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因为自己“无德”、“不明”,道德修养不够,用人不当,贪官污吏侵害百姓[4]286。
为求得天的原谅,进而保住江山,他们采取宽囚减刑、减租免税等具体措施,并迫切希望选贤荐良。罪己诏书往往和求贤诏书同步,要求各地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来纠正自己的过失[5]93。皇帝也亲自发掘人才,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人都是通过对策选拔出来的。而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白衣卿相”的示范,就刺激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二)对教育的影响
汉武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都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经书熟,就能致高位,享荣华富贵,如韦贤,“通《礼》、《尚书》,以《诗》教授……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赐黄金百斤。”于是就有“遗子黄金满簋,不如一经。”[3]2152夏侯胜明确对学生说:“经学苟明,富贵如拾地芥尔。”[3]2857桓荣更是以皇帝的赏赐激励弟子苦读经书:“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缓,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4]1523于是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而这背后,有谶纬的影子,下面做一些具体分析。
1.促进私学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人才的渴求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促进了汉初私学的发展。汉承秦制,起初没有建立正式学校教育制度。太学建立前的博士不是专职教师,他们采取“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的方式,应属于私学。对博士弟子“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例”,[6]因而培养出的人才少。
伴随着经学的复苏和谶纬的发展以及二者的结合,谶纬化的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了统治者的施政决策。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而发布的求贤诏书,标准之一就是要通晓经学,这就调动起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凿壁偷光的匡衡和头悬梁勤苦攻读的孙敬就是其中的典型。私人授徒在两汉非常普遍,汉初仅有伏生在齐鲁一带传《尚书》,韩婴于燕赵间授《诗》《易》,申公、辕固生授《诗》,胡毋生授《春秋》的记载。而到西汉中期和东汉,私学大师比比皆是,一个老师带的弟子也很多,如郑玄“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4]618甚至有博士牟长常有学生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4]1026。即便在山泽中,从师学习的人也很多,如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4]1120。
2.促进官学的创建和发展。尽管私学培养出了一些人才,但统治者仍感到“未得人”。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回答汉武帝时指出,皇帝缺少贤才辅佐的原因在不养士,不办教育,因为人才需要教育来培养:“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只有“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2]314才能得人才。汉武帝将此建议提交丞相公孙弘等讨论,后者提出了设立太学具体实施方案,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并要求各地方官推荐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3]2666的青年到太学学习,学成后由朝廷任用。于是中央官学——太学就创建起来了。
董仲舒提出的其他建议对教育也很有影响,如他向汉武帝提出当时选人用人机制上存在问题,官僚子孙靠门荫(任子),富人靠钱买官(纳赀),都不能得人,只有“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2]315,选贤任能才能解决问题,而大、德又须以儒家“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标准,因而太学就成了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儒学也从秦时的萎靡和汉初不受重视成为“独尊”之学,也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接受太学教育彻底改变了命运,如翟方进在太学“受《春秋》”而“举明经,迁议郎”,匡衡也是“从博士受《诗》”而“拜为太子少傅”[3]2490。这种“白衣卿相”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在追求功名利禄心理的支配下,入太学学习的士人急剧膨胀,昭帝时太学学生仅百人,宣帝末增至200人,元帝时达千人,成帝时人数有3 000人,到汉质帝、桓帝时竟达到3万人[3]2668。所以,《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2684
究其原因,和谶纬有关,特别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4]17,发诏班命、施政用人,往往引用谶纬,而学校就是传授谶纬化经学的主要场所。
出于对谶纬人才的需要,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在洛阳兴建了太学。继位的明帝不仅重视太学的发展,还特别注意皇室功臣贵族子弟的教育,于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下令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子弟开设学校,由著名学者张酉甫等任教,从而使这所贵族学校享誉中外,“匈奴亦遣子入学”[4]2546。
在浓厚的谶纬氛围笼罩下,人们对经书上的话深信不疑,如“广教化,育贤才”是儒家经书提倡的,封建统治者也就遵照它兴办学校。汉成帝时,在犍为郡的水边得到古磬16枚,被认为是吉兆,于是有人提议按经书要求,应“兴璧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后果然修建起了明堂、璧雍、灵台等教育场所[4]1587。王莽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大力发展教育:“为学者筑舍万区”,“征天下有才能及小学异艺之士,前后至数千人”[3]2989。东汉从光武帝重建太学,到明帝亲御讲堂执讲,顺帝“更修黉学”,建“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出现“游学日盛,至三万余生”的盛况[4]1682。
地方官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前虽有文翁自发兴学,但并没有形成气候。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令各郡办学,地方就开始广泛设学,郡设学,县道邑侯设校,乡设庠,聚设序。东汉时期,兴学重教成为汉代评价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各级地方官吏更掀起了一股兴办教育的热潮,官吏甚至亲自讲学。以两汉书《循吏传》为例,《汉书》为6人立循吏传,兴办学校的仅文翁一人。《后汉书》为12人立循吏传,明确记载兴办学校者就有卫飒、任延、王景、秦彭、仇览等5人。“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4]29充分显示了官府对教育的重视,地方官学在边郡地区大量涌现更为引人注目。所以班固《两都赋》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4]543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的大发展的状况。
3.对教育内容的影响。汉武帝之前,私学不仅有传授今古文经学的,教授黄老之学的也不少,法家、刑名也各有市场。而随着谶纬的流行,经学内容神学化、宗教化,荒诞怪异的灾异内容增加,如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引谶纬来解释儒经:“天何以有灾变?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行有点缺,气逆于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7]247再如:“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英起,耟鬯出,太平感。德至人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列,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7]183随后出现一大批谶纬书,有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传说,任意比附灾异祥瑞等,“实际就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8]
4.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空间。董仲舒的文教建议,只是定儒学于一尊,对其他学派也没有采取“焚书坑儒”似的灭绝政策;受谶纬影响,两汉统治者对天满怀敬畏之心,宽刑减罚的多,没有出现暴君。特别是到了东汉,统治者对“异端”思想更持相对宽容态度,对直接冒犯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随意施以酷刑。
受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教育也逐渐宽容大度,于是到东汉时期,原先壁垒分明的家学和门户森严的师学传统逐渐被消解打破。汉代官方太学学生,既可在太学接受谶纬化的今文经学,还可在校外从名师受学。如王充“受业太学”的同时,又从师班彪学习史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4]1629郑玄辞别太学老师后,又到处游学,转易多师,最终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师;张衡既入太学“通五经,贯六艺”,又“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4]2483
学术气氛的相对宽松,学术研究的相对自由,使得两汉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蔡侯纸的出现,地动仪的发明,应该和因经学谶纬化而导致的宽松教育环境有关。
[收稿日期]2010-05-29
注释:
① 关于“经”的说法有多种,此处采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