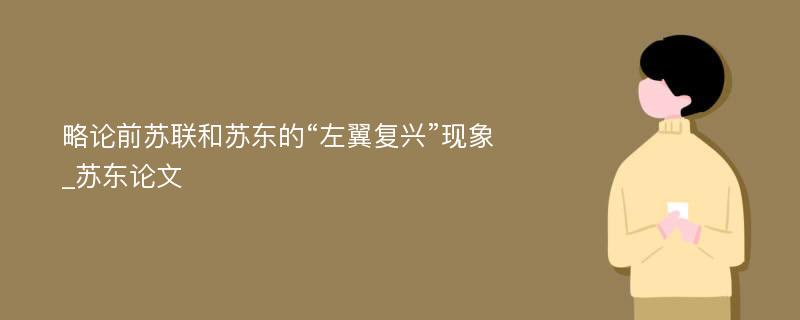
前苏东地区“左派复兴”现象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派论文,现象论文,地区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地图色调的变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诸国社会剧变,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大地骤然易色。仅仅三四年,如今这块大地的政治色调又出现了新变化,造反上台的右翼政党纷纷被拉下马,而以原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左翼政党接连上台:1992年秋,由原罗共转化而成的罗马尼亚民主救国阵线(现改名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在大选中获胜、执政;1993年2月, 基本上由原共产党人组成的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战胜民主派而执政;1993年9月,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右翼组成左翼联合政府,团结工会分崩离析;1994年5月,匈牙利由原共产党脱胎而来的社会党在国会选举中又力挫民主论坛为首的右翼取得执政权。现在,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政权已转到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手中,从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左派复兴”现象。目前,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马其顿、斯洛伐克,而右翼政党掌权的国家只剩下了捷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而在后一类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左右两翼在激烈争夺,而且势均力敌,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则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党,掌握了大多数地方政权,与右翼政党控制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右翼政权比较稳定的只有捷克和克罗地亚两国。
独联体国家的情况与东欧国家有很大差别,除了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少数国家的政权转移是通过共产党下台、民主造反派上台的方式实现外,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共产党人自我演化或分化而实现的。在这类国家,民主造反派的力量比东欧各国弱得多,由他们掌权的国家更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基本上还是原来的共产党人。例如:中亚五国的现任总统仍是原苏共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他们或是把其领导的共产党组织改名仍作为执政党,或是脱离原党而又不参加任何政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任总统也是原来的党政领导人,两国总统易人后继任者也不属于民主造反派,两国的议会和地方政权基本上还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处于战乱中的高加索各国,现政权都属于民族主义性质,其领导人的更迭也不具有左右之争的性质;摩尔多瓦执政者则是属于左翼力量的农业民主党。
在独联体国家,只有俄罗斯的民主造反派曾占据优势,最重要的执政者总统叶利钦虽然也曾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早已公开声明退党,并曾成为民主造反派的旗帜。但是,俄罗斯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政权体系。在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之前,是“两个政权”对峙。十月事件之后,主要由共产党人占据的最高苏维埃虽被撤销,但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左翼力量不仅未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而民主派则四分五裂,其势力和影响不断下降。总之,整个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形势在明显左转,致使某些西方人士惊呼“共产党人又回来了”!
民主造反派何以接连下台
何以出现这种新变化呢?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不同世界观、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会从不同角度观察,从而做出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世界上和这些国家内部右翼人士大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民主派对建立新秩序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过于匆忙地对居民做出了许多一时难以实现的许诺”;“居民对社会经济转轨可能付出的代价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耐心”;“居民对突然到来的生活不稳定和收入不平等现象一时难以适应,产生了心理失衡”;“相对于原共产党人,民主派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也都是促使这些国家右翼势力失势或下台的一些重要原因。但这种解释多属于表面的、现象性的,它们回避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即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方向的合理性以及这些国家右翼政治势力极力鼓吹和推行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模式对于这些国家的适应性。事实上,导致右翼势力纷纷下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不仅远未兑现右翼势力上台之前和之初对居民的种种许诺,相反是普遍地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把大多数居民投入了生活无保障和贫困的深渊。
让我们首先看看被认为是这些国家社会经济转轨最顺利、最成功的捷、波、匈三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在右翼当权的三四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20%左右,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0%以上,失业率高达13—16%,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20%左右,大体有1/3 的居民生活在官方认可的贫困线之下。至于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俄罗斯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在作为民主派核心人物叶利钦总统的治理下,1991—1994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0%以上,包括变相失业或半失业者在内失业率已达12%左右,人民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50%左右,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之下的居民也占1/3左右。此外, 这些国家普遍出现的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以及各种犯罪现象甚至战乱和民族冲突,则不仅使穷人遭难,即使富人也不得安宁,生命财产无保障。
当然,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也并非只有受害者没有受益者。综合各种调查资料,这些国家的居民中大体有15—20%生活水平比社会剧变前总体上没有下降,其中有10—1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5 %左右成了大小有产者和业主,2—3%成了亿万富翁。与此相适应,社会出现了急剧两极分化,75—85%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0%左右的居民不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生活在“生存线”以下。
这种后果不仅超过了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甚至超过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破坏,而这种转轨性破坏在绝大多数国家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人们自然会想、会问:这种破坏难道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吗?除了所选择的道路就无路可走了吗?这恐怕是这些国家的广大选民做出新选择的最重要原因。在现代情况下,在任何国家,一个政党、一种政策若使社会广大居民阶层都受害,其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政权都会是极其困难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对于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家、任何主义都是铁面无情的。如果说这些国家的前共产党主要是由于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而导致下台的话,那么以此为由把共产党赶下台的民主造反派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则更加无能和外行。“民主”、“自由”是可贵的,但它们毕竟不能当饭吃。在这里,埋怨群众“缺乏心理准备”、“缺乏耐心”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公正的。四、五年的时间够长了,民主造反派既然无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生活问题,也该让位了。
说这些国家的民主造反派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是事实,但如今埋怨他们对困难估计不足、说大话、乱许愿已是马后炮。如果民主派造反的时候不说大话、不许愿还能上台吗?如果转轨之初说日子将比从前更难过人民群众还会跟他们走吗?事实上,许多国家民主派的头面人物都是靠造反起家的所谓勇敢分子。在波兰,代头造反的是电工瓦文萨;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剧作家哈维尔;在立陶宛,是音乐家兰茨贝吉斯;在格鲁吉亚,是诗人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阿塞拜疆,是医生贝里沙;等等。这些人在抨击旧政权、旧体制时慷慨激昂,富有煽动性,骤然间成了有魅力的政治明星,但对于如何建设和治理国家则知之甚少,甚至一窍不通。造反时政治魅力是有用的,但建设则更需要知识和理智,经济是煽动不起来,“资本主义乌托邦”政策更是行不通。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带头造反的民主派人士最早被赶下台,或者变成了礼仪、象征性人物。当然,在民主造反派头面人物中也不乏知识里手。例如,波兰的前总理巴尔采罗维奇、俄罗斯的前代总理盖达尔、捷克现任总理克劳斯等。他们都是有造诣的经济学家,但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教育,是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崇拜者,除了克劳斯之外,也大都在第一轮竞争中就被淘汰。他们吃亏就吃在了对本国国情了解的过少,机械地搬用西方模式,成了“休克疗法”的牺牲品。实践证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现实条件,照搬这种模式是这些国家生产大滑坡、社会经济危机加剧,民主造反派下台的关键性原因。
似是而非的“政治时钟”说
在经过一段丢失政权的惊恐之后,现在这些国家的右翼人士及其支持者们又平静下来。人们发现,新上台的共产党人已今非昔比,面貌全非,其政策与其前任并没有原则差别。于是人们又产生了一种新观念、新理论:“钟摆左右摆动是正常的,重要的是政治时钟已经确立”,“问题不在于谁上台或下台,关键是民主制度已在运行”。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还特别以俄罗斯国家杜马取代旧最高苏维埃为例,来证明西方式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的确立。他们说,在现国家杜马中,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反对派力量并不比过去小,“但国家杜马比旧苏维埃更像个议会,这里已经没有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式的人物”,“两个平行政权对峙的局面已经结束,政治游戏规则毕竟已经确立”。
从表象来看,上述“政治时钟”说似乎不无道理。的确,就东欧国家而言,所谓“左派复兴”基本上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崛起,这在西欧国家早已存在。这些政党虽然绝大多数成员是前共产党人,但大都表示要同过去“决裂”、“划清界线”;他们仍主张社会主义,但反对共产主义,并对社会主义做新的解释;他们虽然对右翼政府的某些政策进行抨击,但又坚持现行的社会经济转轨方向。实践表明,新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内外政策的确没有什么原则性变化。为了避免复旧之嫌,怕戴“红帽子”,有的社会党当权者的政策甚至比右翼政府还要右。例如:波兰左翼政府推行的基本上还是前巴尔采罗维奇政府的政策,甚至连右翼人士都曾反对的最激进的“大众私有化”的主张恰恰是社会党提出的;匈牙利社会党人上台后,不仅批评前右翼政府的调子缓和了,而且也在完成其前任未完成的事业,等等。大选获胜后,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为稳固和扩展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往往不是与其他左翼力量合作,而是力图与中间派甚至右翼势力结盟。例如,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已获得单独执政的资格,但却拉比前政府更右的自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又如,波兰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得票第一,但却不愿自己出头,而是把农民党的帕夫拉克推出来组阁。
以上事实说明,东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还相当脆弱,其独立性和个性甚至还比不上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当然,社会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右翼政府还是有区别的。这突出地表现为,大多数社会党人政府力图对其前任的政策进行“纠偏”,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更多地照顾居民对向市场经济过渡引发的各种经济负担和压力的承受能力,放慢私有化的步伐、更多地保留国有经济等,力图缓和社会矛盾。但这种政策调整又遇到国家财政负担加重、通货膨胀更难控制等一系列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右翼人士则冷眼旁观,甚至对社会党人的“新政”进行攻击,宣称“第三条道路”走不通,将来还得由他们收拾残局。
但是,上述现象能否证明,在前苏东国家西方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政治时钟必定永久地在上述两种政党之间左右摆动呢?须知,这种两党轮番执政的旧模式即使在西方国家已经运转不灵。在一系列西欧国家乃至日本,传统性的政党,保守党也好,社会党也好,都在走下坡路,其势力和影响都在削弱,而一些新型的政党和运动正在兴起。这既包括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极右政党,也包括各种平民主义政党和运动乃至绿党等新左翼。一些国家传统的右翼、左翼轮流作庄的旧格局已被打破,一些新右翼、新左翼政党已经得势甚至上台执政。此外,许多国家的居民对竞选和政党政治越来越厌烦,拒绝参加投票或投废票,以致一些西欧国家不得不通过新法律,对拒不参加投票的公民罚款。这说明,西方国家的旧制度、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条件,难以解决不断发展和加深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前苏东国家的某些人士却在不遗余力地效法、移植这种已趋陈腐的旧样板。既然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已经失灵,那么也就很难指望它能在情况更加复杂的前苏东国家奏效。
当然,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大滑坡时期已基本渡过,许多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回升,一些国家(如波、捷)已出现了3—4%的增长率。但也应看到,即使在这些国家这种回升也是脆弱的、恢复性的,是在社会生产已经下降20—40%的极低的起点上实现的,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正常增长率是不同的。同时,这些国家仍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庞大的失业队伍、沉重的内外债负担、巨额预算赤字、相当大一部分居民进一步贫困化等一系列棘手问题,离社会经济健康成长仍有很大距离。还要看到,这些国家的当权者,右翼也好,左翼也好,都把国家发展的希望和前景寄托在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西欧国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融合的基础上,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则恰恰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不景气的地区。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国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制约,这与亚洲“四小龙”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年经济起飞的条件和环境是不同的。事实上,波、捷等国近年来达到的3—4%的增长率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高,而且即使这种低增长在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经济恢复到原起点之后,能否继续保持,也是值得怀疑的。总之,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结合得更为紧密,政治形势的稳定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形势的稳定,这些国家的新执政者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东欧国家右翼政府被赶下台恰恰不是在这些国家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而是在经济大滑坡基本终止之后。这恰恰说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居民政治选择的变化,不仅仅是由于对生活困难失去了耐心,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了信心。作为右翼政府接替者的社会党人能否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能否使广大居民树立起信心,自然尚需进一步观察,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也值得怀疑。经济滑坡基本停止了,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失业率并未明显下降,有的国家还在上升,社会党人上台前的种种许诺也有放空炮的危险。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经济大滑坡已经引起了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座标的转移,那么这些国家的新当权者若仍不能解决面临的社会经济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会不会进一步思考?这些国家的政治钟摆是否仍沿着规定的轨道、按照已有的规则、在限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摆动?看来,即使在形势较好的东欧国家,政局定型说、政治时钟确立说也需要时局的验证。
至于在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上述政治时钟说则更加不适用。在这里,左翼、右翼的性质和内涵与东欧国家有很大差异,其政治钟摆的轨迹也与东欧国家不同。其最突出的差别是: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化程度小得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力强得多,这里的左翼并不是以社会党人为主体,而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因而左翼、右翼不仅政治主张差异更大,而且政治斗争也更具对抗性;在这里,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而且有更为强烈、更有影响的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这里的社会经济转轨破坏性更大,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贫困,因而政治、经济形势更难稳定。总之,在这里形成西方式两大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更为困难。现实是,这类国家不是仍然由一党或个人当政,就是多党、多派混战,与人们追求的那种政治时钟还相差甚远。
当然,在这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也有人力图构建类似西方国家那种政治时钟。最近,俄罗斯由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分别牵头、并得到总统叶利钦赞赏和支持正在组建中的所谓“中右翼联盟”和“中左翼联盟”就是明显的迹象。这两个联盟的政治主张虽有差异,但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企图“排除左、右极端派”,而使政治钟摆沿着“中右”和中左”这种可控轨道摆动。现在看来,这两个联盟在吸收那些分散的、力量单薄的、政治座标尚不太明确的中间派小党可能是有效的,但要想把强大的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以及前民主造反派排除或将它们都吸收进来却是相当困难的。这两个新组织在即将到来的议会和总统大选中将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俄罗斯政局将沿着什么轨迹发展更需深入观察。
综上所述,前苏东地区各国相当普遍出现的“左派复兴”现象,虽然并没有引起这些国家发展方向和政局的原则性变化,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群众思想、情绪、倾向的发展和对现实的不满。它说明,这些国家的社会剧变绝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性过程。各种政治力量仍在激烈较量,人民群众在反思、在选择,其社会经济制度远未定型,何去何从尚难以断定。而且有一点已相当明朗,即西方国家的老路在大多数国家走不通。(1995年7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