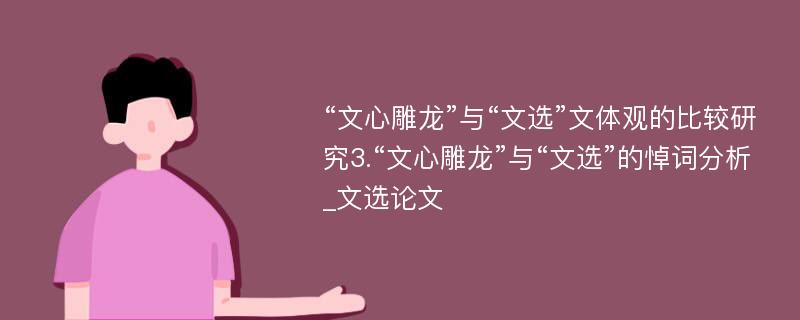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观比较专题研究——3.《文心雕龙》与《文选》诔文观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选论文,文体论文,专题研究论文,诔文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诔在产生之初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体,许慎《说文解字》曰“:诔,谥也。”段玉裁注云“:当云所以为谥也。”[1]是为定谥的实际需要。其内容,《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2]是累列亡者一生的事迹,不外乎功业德行之类。诔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礼制,属于某些官员的特定职责,如《周礼·春官·大祝》所言:“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2]作为国家礼制,诔有许多相关规定。《仪礼》云:“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贾公彦疏曰:“今谓周衰记之时也,古谓殷,殷士生不为爵,死不为谥,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下大夫也,今记之时,死则谥之,非也,谥之由鲁庄公始也。”[2]周以前,诔只适用于国君、诸侯、卿大夫这些地位高贵者,至周衰之时,始下及于士。诔事实上只是官方的特权,并不用于普通百姓,彼时之诔皆官诔。又《礼记·曾子问》言:“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2]诔还要遵循地位高者施与地位低者、年长者施与年幼者的规定。 刘勰与萧统都颇重视诔文一体,《文心雕龙·诔碑》篇详论此体,《文选》选诔8篇,数量居哀祭类文体之首。他们对诔体的认识亦存在一致之处,如都推崇与重视潘岳的诔文创作,都注意到了曹植的诔文等。但二人的不同看法亦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刘勰最重视东汉诔文,萧统选文未及一篇;二是刘勰对曹植诔持批评态度,萧统欣赏曹植诔文。这两点不同,实质反映着刘、萧二人差异较大的诔文观,本文试辨析之。 一、对东汉诔文的不同态度 “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5]是《文心雕龙》论文体的一贯原则和方法,其中“选文以定篇”部分论述各种文体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诔碑》篇论“诔”体,于此部分,除以简短的文字提到扬雄、曹植、潘岳的诔文创作外,其余所论全是东汉作家作品: 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3] 皆是褒赞之词。甚至说“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3],认为潘岳诔文成就的取得,也是学习东汉作家的结果。很明显,刘勰最为重视东汉的诔文创作,以此期为诔体创作成就最高、优秀作家最多的时期。与刘勰不同,萧统并不看重东汉的诔文,《文选》未及一篇东汉之作。 作为一种应用文体,诔产生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并成为检验为政者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毛诗》郑玄注认为“诔”为君子九德之一,“丧纪能诔……可以为大夫”[2]。宋人黄伦注解《尚书·周书·无逸》篇,认为“何谓逸,如鲁文公三不会盟而怠于诔祭……鲁国失自文公始,则逸之过也”,谓鲁文公荒废诔祭之政,是鲁国开始衰弱的一个表征。东汉崇儒重丧,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颇受重视,是当时儒生必备的技能,《后汉书》记载“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髙,帝美之,赐帛免刑”[4]。诸儒被诏作诔,杜笃甚至因为诔文作得好而免牢狱之灾并被赏赐。《后汉书·荀淑传》李贤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载,荀淑之子荀靖卒,“学士惜之,诔靖者二十六人”[4]。亦是诸儒群体作诔之例。又《东观汉记》记载“平原王葬,邓太后悲伤,命史官述其行迹,为作传诔,藏于王府”[3],似乎说明作诔在当时是某些职官的固有职责。东汉甚至还出现了皇帝亲自作诔的情况,如外戚梁商薨,顺帝即为之作诔。 正因为诔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东汉一朝多有士人作诔之例,《后汉书》著录桓谭、冯衍、贾逵、桓麟、班固、马融、蔡邕、延笃、卢植、服虔、杜笃、王隆、傅毅、李胜、李尤、苏顺、曹众、刘珍、葛龚、王逸、崔琦、张升、赵壹、班昭、卫宏、夏恭等近三十人皆作有诔文。可见,诔在当时是创作相当繁盛的一种文体。但是,可惜的是,流传于今的不多。严可均的《全后汉文》仅录有东汉诔文16篇,但相对于其前的漫长时期,这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因为之前仅有鲁哀公的《孔子诔》《柳下惠诔》,扬雄的《元后诔》传世。 可见,刘勰重视东汉诔文本有其事实基础。然而,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东汉诔文相对较好地保存了诔的礼制特征,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稳定的文体模式。 相较于其后,甚至今存其前的诔文,东汉诔文较好地保存了诔的礼制特征。如杜笃的《大司马吴汉诔》,傅毅的《明帝诔》《北海王诔》,崔瑗的《和帝诔》,苏顺的《和帝诔》《陈公诔》《贾逵诔》,汉安帝的《梁商诔》,张衡的《司徒吕公诔》《司空陈公诔》《大司农鲍德诔》等,从篇名即可见出,诔主皆是地位高贵的人物,或皇族,或朝中大臣,而操笔者则多为朝廷文臣,甚至有皇帝为大臣作诔的例子。很明显,东汉诔文基本皆是以官方名义发出的官诔。 东汉诔文的这种对象性决定了其以累列功德为主要内容,虽然同时也抒发哀情,但操笔者既然代表国家立场,又多与诔主并无亲密关系,故所抒哀情往往并非自己的真实感情,更多的是从诔文的实际需要出发,理性地写一种群体之哀。如崔瑗的《和帝诔》云:“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如丧考妣,擗踴号音。”用语颇类扬雄的《元后诔》:“四海伤怀,擗踴拊心。若丧考妣,遏密八音。呜呼哀哉,万方不胜。”它们同源《礼记·问丧》中的“辟踊哭泣,哀以送之”[2]。又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写哀:“于是境内市不交易,途无征旅,农不修亩,室无女工。感伤惨怛,若丧厥亲。俯哭后土,仰诉皇旻。”写北海王之丧引起举国人民的无限哀痛,写的是他人的行为与感觉,并非源于作者真实的体会与经验,这种描写始终隔着一层,难以感人。又如张衡的《大司农鲍德诔》:“命有不永,时不我与。天实为之,孰其能御。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国丧遗爱,如何无思?”张衡本是鲍德门生故吏,二人关系密切,然诔文却从天命和国家的角度写鲍德逝去之可惜可叹。所有这些并不动人的哀情表达,均源于作者的官方立场,以及将诔作为国家礼制活动的出发点。 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将诔文分为两种,卷五“谥诔哀策”类,属于“庙堂之制,奏进之篇”[6],收扬雄的《元后诔》、苏顺的《和帝诔》、潘岳的《世祖武皇帝诔》等作品。卷二十六“诔祭类”,属于“指事述意之作”[6],收曹植的《王仲宣诔》,潘岳的《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作品。可见,李兆洛非常明了前一种诔乃官诔,属朝廷典制之作,后一种诔可称私诔,诔主与作者皆有密切关系,诔文抒发了作者真实的哀悼之情。而刘勰所重恰在前一种保存了相对较强的礼制特征者。 以其礼制特征为基础,东汉诔文形成了稳定的文体模式。刘师培云:“东汉之诔,大抵前半叙亡者功德,后半叙生者之哀思。”[7]据今所存,刘师培所言大抵是事实,东汉诔文基本由两部分构成:述德、叙哀。述德在前,叙哀次之,述德为主,叙哀为辅,且如前言,所序之哀是一种理性的群体之哀,无关作者的真实感情。我们再举苏顺的《和帝诔》为例: 天王徂登,率土奄伤。如何昊穹,夺我圣皇。恩德累代,乃作铭章。其辞曰: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风流万国。立我蒸民,宜此仪则。厥初生民,三五作刚。载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为,钦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载。无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岖,诸夏擅命。爰兹发号,民乐其政。奄有万国,民臣咸秩。大孝备矣,閟宫有恤。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弥留不豫,道扬末命。劳谦有终。实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远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不憖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云,泣涕成雨。昊天不吊,丧我慈父。 文章主要叙述和帝治国之功、孝顺之性、节俭之行,最后简单写及人民对和帝丧亡的无限悲哀。东汉诔文形成了前半述德、后半叙哀的标准文体模式,这种文体模式使诔与其他哀祭类文体如哀辞、哀策、祭文、吊文等明显地区别了开来。刘勰最重视东汉诔文,而对诔体在后来的发展(此点下文将详述)颇有微辞,他看重的正是东汉诔能保存一定的古礼特征,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哀祭类文体的稳定的文体模式。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言:“《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採掇片言,莫非宝也。……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3]正因为认为诔体源于《礼》,所以刘勰要维护诔体原初的一些礼制特征。刘勰的这种观点或许保守,但在魏晋南北朝时却颇有和他认识一致者,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18]认为诔应该尚礼,不能违背儒家的礼教特征,并基于此对曹植的《武帝诔》、陆机的《吴大司马陆抗诔》提出了批评。 东汉诔文保存了一定的礼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文体模式,最受刘勰青睐。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事实是,由于与“礼”相联系,东汉的诔以述德为主要内容,叙哀虽然存在,但却并不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故而难以感人,有失精彩。 二、对于曹植诔文的不同态度 曹植的诔文引起了刘勰和萧统的共同注意,这有其客观原因。一是曹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不必再言;二是曹植确实留意诔文的创作,他今存有《光禄大夫荀侯诔》《王仲宣诔》《武帝诔》《任城王诔》《文帝诔》《大司马曹休诔》《卞太后诔》《平原懿公主诔》等诔文8篇,是先秦至曹魏为止,诔文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 从曹魏至西晋,人们对于诔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曹丕《典论·论文》云:“铭诔尚实。”五臣注此句云:“铭诔述人德行,故不可虚也,丽美也。”[9]言“诔”要“实”,是从诔述德的内容出发的,即要求述诔主之德行功业要遵从事实而不夸张虚造,显然曹丕认为诔主要是用来述德的一种文体。刘桢《处士国文甫碑》云:“咸以为诔所以昭行也,铭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没而令问不忘者,由斯一者也。”强调的仍然是诔的累列死者行迹功业的功能。曹植的《文帝诔》“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亦是对诔的述德功能的认同。但曹植在《上卞太后诔表》中又说:“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冒越谅闇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扬明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则是已经清晰认识到诔文应有叙哀的内容,且明确声明自己作此诔文是重在抒己哀情的。到了西晋,陆机称:“诔缠绵而凄怆。”李善注云:“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五臣注云:“诔叙哀情,故缠绵意密而凄怆悲心也。”[9]文学批评者已经明确诔是用以叙哀的一种文体。事实上,文学批评有相对滞后于文学创作的特性,曹魏时期,诔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叙哀的成分在不断地增加,而且已经由东汉的叙理性化的群体之哀发展到叙感性化的一己之哀。而这种新变正是在曹植手中完成的。 关于曹植诔相对于其前诔文的新变,已多有学者论述,马江涛的《试论曹植诔文的新变》从诔文对象扩大、兼用多种人称、个体情感加强等三方面指出了曹植诔之不同于东汉诔[10]。朱秀敏的《由礼赞到伤悼的衍化——以曹植为例论析建安诔文之新变》则概括了曹植诔文两个方面的新特点:“诔文创作对象的私人化”、“抒情意味的强化”[11]。而不管是诔文对象的私人化,即诔由官诔变为私诔,还是诔文人称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最终只能导致叙哀成分增加,个人化情感增强。时至魏晋,“哀情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因素,叙哀也渐演为个体哀思的抒发,诔文由对生命的礼赞演变为对生命的伤悼”[12]。这种变化实际就是在曹植手中完成的。而显然,刘勰对这种变化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陈思叨名,而体实烦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3]所谓“百言自陈”,正是曹植抒发一己哀情之处。后人对于刘勰的批评,显然有不同意见者,李兆洛即言:“至其旨言自陈,则思王以同气之亲,积讥谗之愤,述情切至,溢于自然,正可以副言哀之本致,破庸冗之常态。诔必四言,羌无前典,固不得援此为例,亦不宜遽目为乖也。”[6]李氏承认诔文的新变,认为曹植多抒哀情使其诔文更加精彩。李兆洛之后,刘师培进一步指出了曹植诔文新变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彦和因篇末自述哀思,遂讥其‘体实烦缓’。然继陈思此作,诔文述及自身哀思者不可胜计,衡诸诔以述哀之旨,何‘烦秽’之有?”[7]又云:“陈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陈哀思,于体未为大违,而刘彦和《文心雕龙》犹讥其乖甚。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体之甚,彦和将谓之何耶?”[7]自曹植之后,以诔抒己哀情已是一种平常做法,刘师培认为诔文自可述哀,刘勰之批评有误,但言语中却也道出了诔文渐渐偏离自身轨道而与其他哀祭类文体相杂的事实。 实则,刘勰批评曹植诔的新变,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他力图维护诔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的固有模式与特征。过多叙哀使诔与哀辞等文体趋于合流,使诔作为一种文体失去生命力。如谢庄作《宋孝武宣贵妃诔》,《南史》却记载为“谢庄作哀策文奏之”[13],这就是诔文“与哀策之体相乱”[6]。江藩的《炳烛室杂文行状》言:“三代时诔而谥,于遣之日读之。后世诔文,伤寒暑之退袭,悲霜露之飘零,巧于序悲,易入新切而已。交游之诔,实同哀辞,后妃之诔,无异哀策,诔之本意尽失,而读诔赐谥之典亦废矣。”[14]明确指出了由于叙哀之辞的增加,诔与哀辞、哀策之体相混。事实亦是如此,如曹植作有《平原懿公主诔》,曹丕作有《曹仓舒诔》,诔主分别是刚生百日而亡的婴儿与年仅十三岁的幼童,哀悼此类无功德可言的幼儿,属“下流之悼”,本应用“不在黄发,必施夭昏”[3]的哀辞之体,曹植却用了“诔”。另外,曹植有《仲雍哀辞》,仲雍名曹喈,乃曹丕之子,三月生而五月亡,曹植作此文哀之,而陆机《挽歌行》李善引为《曹喈诔》,又刘玄《拟古诗》李善注注引为《曹仲雍诔》。可见,至少到唐代,诔与哀辞之体,人们已区分得不大清楚,原因就在于二种文体已经没有明显的可资分别的体制特征。故吴纳《文章辨体序说》亦言:“厥后韩退之之于欧阳詹,柳子厚之于吕温,则或曰诔辞,或曰哀辞,而名不同。迨宋南丰、东坡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15]而如刘勰所指的曹植《文帝诔》的“百言自陈”部分,所用句式还是如“咨远臣之渺渺兮,感凶讳以怛惊”这样的骚体句,骚体本善表情,这更使其与哀体相近,正如刘师培所言:“汉代之诔,皆四言有韵,魏晋以后调类《楚词》,与辞赋哀文为近:盖变体也。”[7]这是从语言形式上得出的结论。很明显,过多地叙哀,并借用善于表达哀情的语言形式,使诔体越来越与哀辞、哀策等主于叙哀的文体相混,这就使诔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至南朝,尤其是齐梁时代,创作者越来越少,诔文一体迅速地走向衰微,这也是它与其他文体相混的必然结果。那么,刘勰强调诔的述德功能,不赞成诔的私人化而致的叙哀成分的增加,也就有他的道理了:他是要维护诔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体制特征,从而固守诔的阵地,使它不致走向消亡。 刘勰非常重视辨体,他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3]他论文体的一个惯常做法,即对各种文体的功用和特征进行细致而明确的描述与规范,避免与其他文体发生交叉混淆,使人们相对清晰地认识每一种文体。如《哀吊》篇论吊文一体,认为此体仅指那些凭吊古人的吊古抒怀类作品,而对向同时人致吊的吊丧类吊文不置一词,因为相对于吊古抒怀类吊文,吊丧类吊文确实极易与其他哀祭类文体混淆。又如《檄移》篇论檄体,刘勰相对单一地只论述了用于军事征伐的檄文,而对晓慰类檄文如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不予提及,原因就在于他要规范檄体的文体功用。诔体亦然,刘勰最重视东汉先述德、后叙哀,以叙哀为辅,且是叙群体之哀的诔文,而反对曹植诔的新变,主要原因实际就在于,他要维护诔的体制特征,使它不与其他哀祭类文体相混而失去生命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诔文在东汉以后渐重叙哀已是不可改变的趋势。而且,在东汉时已显露迹象,刘勰也看到了这一事实。《诔碑》篇有云:“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雾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3]傅毅《北海王诔》开始借助外界自然景物表达一己哀情,并为后世取法。另外,如前所引,刘勰也非常肯定潘岳的诔文创作,看到了潘岳诔文多述哀情的事实,并对他高超而新颖的叙悲技巧予以称赏。可以说,对于诔文的叙哀,刘勰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至齐梁时,诔文创作已名家辈出,诔文多叙哀情也早已成了现实,刘勰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另一方面,刘勰又欲固守诔的阵地,维护它与其他哀祭类文体相区别的个性特征,故对诔以叙哀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不满。 与刘勰不同,萧统重视曹植的诔文,诔体选文即从曹植开始,换言之,其所选皆叙哀成分较多的诔文。事实确实如此,《文选》“诔”体所录曹植的《王仲宣诔》,潘岳的《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颜延之的《阳给事诔》《陶征士诔》,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等8篇诔文,皆善述哀情之作。首先,这8篇诔文中的大部分,作者与所诔对象有密切的关系,曹植与王粲、潘岳与夏侯湛、颜延之与陶渊明是好友,潘岳与杨肇是翁婿,潘岳与杨经是姑丈内侄,这样的关系,是这些诔文能够表达真诚动人的哀悼之情的基础。而潘岳的《马汧督诔》、颜延之的《阳给事诔》两篇,作者与诔主虽关系并不密切,但诔主事迹悲切可感,马敦“功存汧城,身死汧狱”的事迹在潘岳的巧妙叙述之下,颇能激起人们的悲愤怜悯之心,高步灜有评云:“词旨沈郁,声情激越,部司之忌才,烈士之冤愤,俱能曲曲传出。宜曾文正笃好斯篇,并深许其子惠敏称为沈郁似《史记》之言也。”[16]而颜延之的《阳给事诔》是在潘岳的《马汧督诔》的启发下写成的:“专写给事之忠壮,觉慷慨激烈之气直骞云表,可与安仁之诔汧督同起白骨于不死。”[17] 《文选》8篇诔文中较特殊的一篇是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此诔李兆洛《骈体文钞》归入属于“庙堂之制,奏进之篇”的“谥诔哀策”类。与其他7篇诔文不同,首先,此诔乃受命为皇族而作,与东汉诸多官诔颇类;其次,诔主并无义烈可感之事迹。那么,《文选》何以选此诔?原因还在于,与东汉诔文相比,《宋孝武宣贵妃诔》大大增加了叙哀的成分,抒发哀情的手法亦大有进步,确能动人。《宋孝武宣贵妃诔》叙哀情用了骚体句,这是东汉诔文没有的现象,“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露凝兮岁将阑。庭树惊兮中帷响,金釭暧兮玉座寒”,用清秋萧瑟之景烘托渲染悲情,又从深秋之景写出因贵妃离去造成的阒寂不堪之境,加以骚体的语言形式,不免令人悲从中来。作者还细致地写道,贵妃虽亡,然人亡物在,“帷轩夕改,軿辂晨迁。离宫天邃,别殿云悬。灵衣虚袭,组帐空烟。巾见余轴,匣有遗弦”,令人触处成悲,此类描写已颇为细致,感情的触角也较为敏锐,颇类潘岳《悼亡诗》中“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之言,睹物思人,情何以堪!诔文又写及贵妃的薨逝给子女及皇帝带来的哀伤,“纯孝擗其俱毁,共气摧其同栾。仰昊天之莫报,怨凯风之徒攀”“恸皇情于容物,崩列辟于上旻”。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但这些都是人人都能体会得到、又最易动人的人伦亲情。此外,作者还对送葬的场面进行了描绘、渲染:“经建春而右转,循阊阖而迳渡。旌委郁于飞飞,龙逶迟于步步。锵楚挽于槐风,喝边箫于松雾。”缓慢的灵车,飘飞的旌旗,好似都托着载不动的悲哀前行,而酸楚的挽歌、悲伤的箫笛萦绕于林边树下久久不能散去,这是怎样的愁云惨雾啊!可以说,这篇诔文虽无关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作者多样化巧妙的叙哀手法以及多角度的描写,使贵妃薨逝带来的悲痛得到了多角度与深层次的展现,亦善述哀情之作。诔体发展到刘宋,虽仍有如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这样的官诔,但比起东汉官诔已绝然不同,述哀成分大大增加,写哀技巧也颇为成熟。《南齐书·文学传论》有云:“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18]所言不虚。所以,《文选》虽不选东汉诔文,却仍选谢庄此作。因为,作为一部文章选本,萧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出优秀的文学篇章,《宋孝武宣贵妃诔》的文学性比起东汉诔文无疑大大增强了。 综而言之,东汉诔文保存了一定的礼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先述德、后叙哀,以述德为主、叙哀为辅,且叙理性的群体之哀的稳定的文体特征,最为刘勰所重视,而曹植诔文中叙哀成分的增加,一些新变因素的出现,使“诔”体与哀辞、哀策等其他哀祭类文体出现相混之势,刘勰试图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固守“诔”体的阵地。萧统选诔始自曹植,表明他重视善述哀情的诔文,因为这样的诔文才更感人,更富于文学性,这也说明《文选》根据一部选集的性质,萧统是要以自己的标准选录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不论它们是否突出地体现了该类文体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