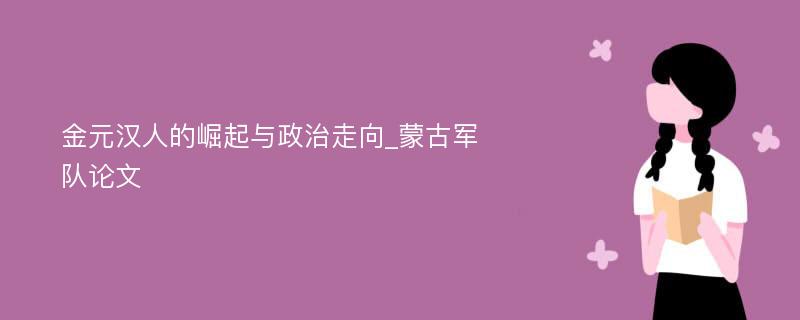
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汉人论文,动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6-0053-08
金元(蒙古)之际战乱频仍,河朔山东豪杰蜂起,聚众自保,以捍卫一方安全;后多为蒙古统治者收编,作为灭金平宋的军事力量,史称(万户)世侯或汉人世侯。以往由于受特定时代学术大背景的影响,对汉人世侯家庭背景的认识显得偏颇,对汉人世侯起家动机和政治动向的论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不加区别地把史籍中的“盗贼”等同于农民起义。本文对上述问题重新探讨,试图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或有不确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汉人世侯兴起的历史背景
金大安三年(辛未,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金。七月,哲别攻拔金乌沙堡及乌月营,成吉思汗连破昌、桓、抚等州。九月,拔金德兴府,哲别入居庸关,直抵金京师中都。十月,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下云内、东胜、武、朔等山后诸州。次年秋,围西京,克奉圣州,连克宣德府、德兴府。癸酉年(1213)七月,拔涿、易二州。其年冬,分兵三路南下,蒙古铁骑踏遍黄河以北地区,连破九十余郡,除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外,“河北郡县尽废”[1](卷一《太祖本纪》)[25],“燕、赵、齐、魏,荡无完城”[2](卷二八《郭瑁墓表》)。甲戌(1214)年五月,金主迁都汴京。
蒙古军的侵掠,对华北地区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惨重的破坏。蒙古在对敌国的侵掠过程中,实行野蛮的屠城政策,“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3](附《耶律楚材神道碑》)[5](卷四《序江汉先生事实》)。在此政策下,蒙古军所到之处,野蛮杀戮,生灵涂炭。甲戌年一月,蒙兵屠灭保州,“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同年,蒙古右路军攻下平阳后,回师漠北,“取道太原,分兵四六州”,“汾、石、岚、管,无不屠灭”[4](卷三五《孟升卿墓碑》)[2](卷二八《郭瑁墓表》)。举此二例,即可见蒙古兵对华北人民杀戮之惨绝。
蒙古军对人口的掳掠是相当惊人的,如1213年木华黎将河北永清一带降人十万余家迁之漠北[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蒙古军攻略河东后,河东百姓被掳掠殆尽,城邑四野为之一空[12](卷一五《刘亨安墓碑》)。蒙古征金战争对人民财产的破坏亦极惨重,如冠氏县民居皆被焚毁[2](卷二九《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赵州为兵冲,其民居官寺被焚毁到“百不存一”[2](卷三二《赵州学记》),庚辰年(1220),平阳诸郡被兵之余,亦至“民物空竭”[1](卷一五一《刘亨安传》)。史称“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廓丘墟。”[21](卷一九《鞑鞑款塞》)人民在逃难的过程中死于饥饿疾病者也很多,如贞祐初年,人民争相南渡而厄于黄河,从河阳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间,积流民数百万,“饥馑荐至,死者十七八”。[4](卷三六《先大父墓铭》)
蒙古军杀掠后北还朔漠,但刀火之余,加之河朔饥馑,以致于饿殍遍野,有“易子食”、“析骸爨□(骨)”者[13](卷二一《綦公元帅先茔之碑》)[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10](卷一八《王义行状》)。这种状况,促使结寨自保的乡兵的兴起和汉人世侯最初的从戎抗蒙。论者往往注意到蒙古军横扫河朔、山东,大掠北还后,金主南渡、金之郡县尽废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下豪杰并起的情况,而忽视了蒙古军侵掠过程对生灵的残酷屠灭是豪杰并起的最主要的原因。
金朝后期已趋向没落,蒙古的侵掠使得金朝的军、政迅速崩溃瓦解。面对蒙古的强劲兵势,金军难于招架,望风披靡。辛未年秋,抚州野狐陵一役,蒙古尽歼金朝三十万大军,“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22]。州县兵更是望风奔溃,不能成军。金朝在华北的统治亦随之残破瓦解,州县官吏望风而遁,逃奔河南,以致“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存者复为土寇所扰”[31](卷一二一《和速嘉安礼传》)[6](卷一六《段直墓志铭》)[31](卷一○九《陈规传》)。金朝军队无力与蒙古军对抗,但在溃败的过程中却“剽掠成俗”,“恐逼小民,恣其求索”,而州县官吏在奔逃的过程中又“多乘乱贪暴不法”[2](卷二七《术虎筠寿神道碑》)[31](卷一○九《陈规传》)[1](卷一五三《王守道传》)。愈使得“百姓耕稼失所”,“平民愈不聊生”[31](卷一二二《从坦传》、卷一○八《侯挚传》)[26]。金军与金朝官吏的祸害实与盗贼无异。面对强敌的入侵,平民百姓自然不会寄希望于金朝军队、官吏的保护,也只有“团结为兵”,聚众自保,抗御入侵的强敌、剽掠的金军及乘乱劫掠的盗贼了。金朝军政的瓦解、金军对百姓的残害,又成为豪杰并起的一个直接原因。
“田畴荒芜”、“民不聊生”是蒙古杀掳、金军剽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又造成了烧杀抢掠的盗贼的蜂起。史载“大安失御、贞祐播迁,田畴污莱,人无所取饱。……乙亥岁,荐饥,人相食,盗贼蜂起”,“互出没劫掠,人不得宁处”[14](卷一五《王善神道碑》)[15](卷二六《靳和神道碑》)。“盗贼蜂起”成为结寨自保的乡兵兴起的又一个原因。
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汉人武装正是在蒙古军的白色恐怖与金军的剽掠骚扰、盗贼的抢掠,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纠集起来的。相对于贫困和饥饿,蒙古兵的杀掠更令人恐怖、惊悸。
二、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
金末元初的汉人世侯,时人称为“诸侯”、“世侯”等,今人或曰“汉军世家”,而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大陆的研究者通常称之为“汉人地主武装”。其实,如果对《元史》、元人文集和金石资料的有关记载作一综合考察,即可发现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具有多种类型[27]。
一类是原金官吏或原金官吏子弟,如:刘伯林,济南人,金末为金威宁防城千户[1](卷四八《刘伯林传》);王玉,赵州宁晋人,原是金季镇守赵州的万户[1](卷一五一《王玉传》);杜丰,汾州西河人,原为金平遥义军谋克[1](卷一五二《杜丰传》);田雄,北京人,金末署军都统[1](卷一五一《田雄传》);张晋亨,冀州南宫人,其兄张颢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他本人也并非原金官吏[1](卷一五二《张晋享传》);焦德裕,雄州人,其父焦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1](卷一五三《焦德裕传》);谭澄,德兴怀来人,其父谭资荣,金末为交城令[1](卷一九一《谭澄传》、卷一六七《谭资荣传》);阎珍,太原上党人,“及长,仕州县”[2](卷二九《阎珍墓表》);何实,其先北京人,其父何道忠仕金,为北京留守[1](卷一五一《何实传》),赵振玉,利州龙山人,“幼仕州县”[2](卷三○《龙山赵氏新茔之碑》);赵仲,其“高祖某、曾祖某、父言皆涉书务农,不乐求仕”,本人在金之季年为本县小吏[15](卷二八《赵仲墓志》);平州王浩于金贞祐初任兴平军节度幕官,摄府事[9](卷五七《王遵神道碑》)。从上述诸人的家庭背景来看,即使是原金官吏,在金朝的职官也并不高,仅是些低级官吏,有的虽出身于金中层统治阶级之家,其本人却不是金朝的官吏。
一类是地主或富农出身者,如:史秉直,燕之长清人,家庭“以财雄乡里”[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济南张荣,历城人,为一富农[16](卷一六《济南公世德碑》);靳和,太原汾州人,“家饶于财”[15](卷二六《靳和道道碑》);张子良,范阳人,大父张臣甫“恤贫乏,乐施予”,当为一富户[2](卷二八《张子良先德碑》);信亨祚,上谷人,后徙须城,其祖、父“以资雄乡里,有万千之目”[2](卷三○《信亨祚神道碑》);杜泉,广平曲梁人,“以财雄乡里”[10](卷一六《杜泉神道碑》);朱楫,泰安州人,其祖父辈“力穑致富,聚而能散”[9](卷五二《朱氏世系碑铭》);高冈,石州人,“世世孝悌力农,以德以勤,遂以土田缗钱雄乡里”[10](卷一六《高冈神道碑》);王汝明,燕人,家庭背景比较复杂,其祖父某,贷圣安寺钱千缗,“遇赦,卒还之”,其父好问明经,三赴殿选试,补御使台椽,“有能名”,昆季五人皆克家厚于资,王汝明本人则“独以远业自期读书,耻无用之学”[8](卷五《王汝明神道碑》);张弼之祖有“善富”之称[17](卷一一《张元帅墓志铭》);隰州曹元亦为一富农[2](卷二九《曹元阡表》)。
一类是出身普通农家者或一般儒士家庭,如:王珍,大名南乐人,“世为农家”[1](卷一五二《王珍传》);杨杰只哥,燕京宝坻人,“家世业农”[1](卷一五二《杨杰只哥传》);乔惟忠,易州定兴人,“世为农家”[2](卷二九《乔惟忠神道碑》);张柔,涿州定兴人,“世力农”[1](卷一四七《张柔传》);董俊,真定藁城人,“少力田”[1](卷一四八《董俊传》);严实,泰安长清人,曾“落魄里社间,不自顾籍”,亦尝“以事被系”,实出身于一普通农家[1](卷一四八《严实传》);李全,潍州北海人,“农家子”[32](卷四七六《李全传》);王义,真定宁晋人,“家世业农”[1](卷一五一《王义传》);邸顺、邸琮,中山曲阳人,“世业农”[8](卷五《邸琮神道碑》);石珪,泰安新泰人,“世以读书力田为业”[1](卷一九三《石珪传》);攸哈剌拔都,渤海人,“世业农”[1](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孙善,真定武强人,祖、父皆“业农穑粟”[6](卷四《孙善墓志铭》);郝亮,新安涞城人,其父郝德昌“起自行武”[8](卷五《郝德昌神道碑》);王得禄,北京兴中府人,“世为农家”[2](卷三○《王得禄墓铭》);张荣祖,真定获鹿人,其父辈以上“三世在野”[2](卷三○《张荣祖之碑》);毕淑贤,大兴府永清人,“大父某,父某,皆以农为业”[2](卷三○《毕淑贤神道碑》);李平,邯郸人,“祖考皆隐于农”[10](卷一六《李平神道碑》);袁湘,太原临泉人,其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高祖亨“隐德农亩”,曾祖迪业儒,祖企京“有父风”,父铎“克世其家学”;史千、谢天吉、周献臣则出身于儒士之家[5](卷一七《袁湘神道碑》)[15](卷三三《史千神道碑》、卷二九《谢天吉神道碑》、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2](卷二二《周鼎墓表》);王善,真定藁城人,其父王增尝监本县酒务,后归田里[14](卷一五《王善神道碑》);张安宁“起天亩间”,跨弓刀以角逐于分崩离析之际,出入行阵[15](卷二四《张安宁墓表》);王兴秀之祖考“皆农蠡之博野宋村”,其本人“生二十年,而劳苦耒耜”[5](卷二一《王兴秀神道碑》)。
还有一部分世侯,主要是中小世侯,史籍对其家庭出身语焉不详,如大宁义州人李守贤、辽东川州人刘亨安、昌平人张拔都、东平齐河人刘通、大名冠氏人岳存、济南历城人刘斌、涿州涞水人赵柔、真定平山人王守道、泽州阳城人郑鼎、汾州平遥人梁瑛、济南人孙庆、易州涞阳人卢德元、泽州晋城人段直、昌平人郝和尚拔都[1](卷一五○《李守贤传》、《刘亨安传》,卷一五一《张拔都传》,卷一五二《刘通传》、《岳存传》、《刘斌传》、《赵柔传》,卷一五三《王守道传》,卷一五四《郑鼎传》)[15](卷三一《梁瑛神道碑》)[2](卷三○《孙庆墓碑》)[8](卷五《卢德元行状》)[6](卷四五《段直神道碑》)[18](卷一○《郝和尚拔都神道碑》)[15](卷二六《吴信碑》)等等,此类人所在多有。史籍虽未记载此类人的家庭背景,我们亦可推知其大概。中国古人尊崇祖先,重视编写家族谱系,如果他们的父祖辈中有为官者或“雄于财”者,他们的碑传中不会不加记载,而且还会加以渲染。因此,此类人当大多出身于普通民众之家。将汉人世侯统称为汉人地主武装,未免失之偏颇。当然,当一些平民出身的武装头目“由鼠而虎”变为世侯,上升为地主阶级后,其政治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蒙古国时期的汉人世侯绝不仅仅上面所述见于史籍记载的六十余人,另有许许多多的中小世侯或因对抗蒙古而湮没无闻(如李璮部属),或因史籍散佚而事迹不彰,或因事功不显而无文人为其作碑志。对他们的家庭出身,我们也就难知其详了。
中国古代有聚族而居的传统,汉人世侯的家庭背景就有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有许多出身于大宗族之家。战乱之时,大宗族之家更容易组织人力自我保护,所谓“平居非强宗,世乱受凌暴”,“当天下草昧,非强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6](卷三《叙节妇贾韩氏事》、卷四《孙善墓志铭》)。富家大族,往往资财雄厚,可以招兵买马,如隰州曹氏以资雄乡里者累数十代,故曹元能于贞祐兵后“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2](卷二九《曹元阡表》)。张柔初起家聚族党千余家,史秉直家百余口[1](卷一四七《张柔传》)[7](卷一○九《史秉直神道碑》),赵天锡家为大族,邸顺初起家时“会宗族”、聚乡人豪壮数百人[2](卷二九《赵天锡神道碑》)[6](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卷五《邸琮神道碑》)等等。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汉人世侯的个人素质,诸如豪爽侠义、多谋略、善骑射。如此则有号召力,“人或赖之”、“乡人倚之以为重”[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卷五《邸琮神道碑》),如杨彦珍质而义,沉而信,修干有力,弛马引强,乡里及旁县豪吏奔走服属之,队伍发展至二万余众;宁晋王义素宽仁,材智足以保众成事,县人遂推举他为万夫长,摄行县事;涞水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各聚众数千,闻赵柔信义,共推赵柔为长;景州群侠少恃贾德之勇,往往依附为用;谢天吉有“宽人之度”,乡人附者数千人[5](卷一八《杨彦珍神道碑》)[10](卷一八《王义行状》)[1](卷一五二《赵柔传》)[9](卷四七《贾德行状》)[15](卷二九《谢天吉碑》)等等,不一而足。
三、汉人世侯起家的初始动机
以往对汉人世侯的研究,既以汉人世侯军队就是地主武装为前提,对汉人世侯起家初始时的动机,自然也就以为是与“盗贼”(指农民起义——笔者按)对抗。事实上,汉人武装之结集,主要是为了避兵和抗蒙。在蒙古兵长驱直入、“所向摧陷”、肆意杀戮焚毁,金朝统治瓦解、“州县残破”、军队南撤、“天兵北来,人无所安息”[15](卷二六《隰州刘氏先茔碑》)的情况下,无论是势家大族还是“元元之民”,都面临着性命不保的危险,出于原始的生命本能,人们最先要做的就是避兵和自保。避兵,首先是避蒙古兵,其次是避金兵和土兵,以及杀人劫货的盗贼。正如虞集在《曹文贞公文集序》中所谓“据要害以御侮,立保障以生聚”。[11](卷三一)
刘祁《史秉直神道碑》:
当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史秉直)与其亲族谋曰:“今兹丧乱,血流成河,吾家百余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数处,或可得生,不然,无遗类矣。”既而知降者得免,乃复议降。[7](卷一○九)
史氏武装是在降蒙后组成的,目标是随蒙古军攻打金军和附金的汉人武装,但从《史秉直神道碑》亦可看出当时金朝民众对蒙古兵的恐惧与避蒙古兵及自保的普遍心态。癸酉年,蒙古东路军至山东,攻下益都、淄、莱、密诸城,“(李)全母及其兄死焉”,李全“与仲兄福聚众数千”[32](卷四七六《李全传》),组织武装。李全初起家时的动机,除了抗蒙自保,别无解释。严实最初从军是在癸酉年蒙军分略山东、河北之后,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因严实为众所服,署为百户[1](卷一四八《严实传》),可见严实初起家时的目的是抗蒙。严实的重要部将如阎珍初隶金上党公张开麾下,毕淑贤起初被金益都宣抚使田琢署为军中都统,孙庆贞祐初挈家往依严实于青崖山,王得禄于贞祐癸酉以骑兵从锦州将王守玉守东平,信亨祚于贞祐兵兴之时,以良家子隶军籍,从金平章政事萧国侯公镇天平[2](卷二九《阎珍墓表》,卷三○《毕淑贤神道碑》、《孙庆墓碑》、《王得禄墓铭》、《信享祚碑》)。其动机无一不是抗蒙。张柔于金贞祐间,河朔扰攘之时,聚族党数千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1](卷一四七《张柔传》)。张柔所避之兵就是蒙兵,当然也有乘时而起的土兵。乔惟忠从张柔聚族属、乡曲,保西山东流埚,别自为一军。1218年,蒙军出紫荆口南下,张柔马跌被执,而乔惟忠不知,“其守东流者如故也”,“大帅以张公(柔)至埚下,谕公(乔惟忠)使降。公盛为御备,日战数十合,力尽乃降”[2](卷二九《乔惟忠神道碑》)。虽然张柔与其他义军有摩擦、斗争,其主要动机、目的,非“御盗”,而是自保兼保金国也。赵天锡之父赵林,贞祐之季中原受兵,以乡豪保冠氏县有功,大名主帅用便宜授县令,所统三州十一县义军,“殁于王事”,即为保金朝而死。赵天锡兄赵显、弟赵颙皆封授金之低级军官。赵天锡本人始弱冠,即“入粟佐军”,此“军”即抗蒙“义军”,后为县城防控属,“大朝兵势浸盛,避于洺水,后以冠氏令避桃源、天平诸山”。“大朝兵”即蒙古兵[2](卷二九《赵天锡神道碑》、卷三○《冠氏赵侯先茔碑》)。张子良,“初大安兵兴,公(张子良)以材选为军中千夫长”,“大安兵兴”,即指蒙古初侵金,则张子良初始之动机亦为抗蒙[2](卷二八《张子良先德碑》)。赵柔,“金末避兵西山,栅险保乡井”[1](卷一五二《赵柔传》),显然是避蒙古兵自保。攸哈剌拔都,金末避地大宁,“国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屡夺大营孽,又射死其追者”[1](卷一九三《攸哈剌拔都传》)。“国兵”即蒙古兵,“大营”则指蒙古兵营。清州张荣于金主迁汴的甲戌年(1214)年“以武勇选守燕都”[10](卷一六《张荣神道碑》)。金贞祐间,边事急迫,藁城令树靶募兵,射中者,拔为将领,“众莫能弓,独公(董俊)能挽强,一发破的,遂将所募迎敌”[33](卷七○《藁城董氏家传》),此“敌”即蒙古军。靳和于“贞祐之乱”时“以富室□(当为子)从军于绛”[15](卷二六《靳和神道碑》),靳和从军的目的当然是抵抗蒙古兵。周献臣于蒙兵攻破雁门关,“游骑骎骎而南”之时,“慨然聚里人戚属避南山之隅”[15](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丁丑(1217)蒙兵围雁门,游骑及县境,金人弃城奔溃。城中遗民共推王兆和刘会同领县事,谋走南山,栅险自保[15](卷三○《王氏世德碑》)。石珪于“金贞祐南渡,兵戈四起”之时,“率少壮,负险自保”[1](卷一九三《石传》)。其它一些世侯的碑传虽没有明确说明他们避兵、抗蒙的意思,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也大多是避兵或抗蒙。也有一部分汉人世侯初起家时的动机是乘时以摄取富贵。
有不少汉人世侯的碑传在记述碑传主起家时,往往说是与“盗贼”作斗争而起家。以往论述这一问题者,见到“盗贼”字眼,便说是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是不确当的。我们认为,所谓“盗贼”,大多应是敌对集团之间的相互指责,如蒙古军与金军之间,附蒙的汉人军事集团与金军、未降蒙的乡兵之间,乡兵与乡兵之间。如《东平王世家》记石天应被杀事,“是岁(1223),群盗陷河中府,杀权行台石天应。未几,贼烧民府舍遁。”(圈点为笔者所加)。又《行录》云:“初,天应闻中条山贼侯七、侯八欲夜攻袭其城,即遣部将吴权府领兵出东门……”[23](卷一《东平鲁国忠武王》),而《元史·石天应传》云:“秋七月,遂移军河中。既而金兵果潜入中条,袭河中。”径称侯七、侯八的军队为“金兵”。附金的所谓“义军”,虽抗蒙,也有“盗贼”的特点,如金末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胥鼎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趣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31](卷一○八《胥鼎传》、《紫山集》)。卷一八《王义行状》:“金卫绍王遇杀,天兵南下,宣宗失燕走汴,河北郡县,虽开设守令,而政治威令解驰沮丧,土寇四起,力不能至,弱肉强食,互相残贼奔窜,莫知所依。”“土寇”正是所谓蜂起的乡兵、“豪杰”中的一部分,他们相互间称对方为“盗贼”。各乡兵之间的残贼、争战,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苦难,对社会生产力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时河朔诸豪并起,各以力相雄长,生民靡灭几尽。”“时诸方州皆事屠并,争地杀人,不恤其民。”“遗民自相吞噬殆尽”[8](卷五《卢德元行状》)[4](卷三六《何伯祥神道碑》)[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自相吞噬的遗民之间相互也是以盗贼相称的,如张柔、靖安民与贾瑀之间,王善降蒙前与武仙之间等。[1](卷一四七《张柔传》、卷一五二《王善传》)。
其次是土豪恶霸以及流氓歹徒之辈,即所谓“草贼”。如《紫山集》卷一六《杜泉神道碑》记载的,“甲申(1224)夏五月,东山草贼奄至城下,所过烧毁室庐,驱掠人畜。”史籍记载的“乘乱剽斥”的“群不逞之徒”,“凶焰可灼,里陌为萧条”的“群盗”,“食人肉”、“析骸骨”的何运副辈[2](卷二九《曹元阡表》)[9](卷四七《贾德行状》)[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其性质决不是农民起义。许多汉人世侯正是在与“盗贼”的对抗中兴起的。因此,史籍中所谓“招抚”,只是已附金或降蒙的武装对归附敌对方和尚未归附任何一方、固守自保的武装(大多数是乡兵)的招抚、收编。当然,反抗民族压迫、封建统治的也有,如一部分红袄军即属起义农民。
四、汉人世侯的政治动向
金主播迁汴京之前,汉人武装降蒙的并不多,主要有刘伯林、史秉直、夹谷常哥等。刘伯林降蒙最早,《元史·刘伯林传》:“壬申岁,太祖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降。”在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迫于重围”而降蒙。刘伯林降蒙后,太祖“以原职授之”。刘伯林即“选士卒为一军”,与契丹人耶律秃花同征讨。《牧庵集》卷一六《夹谷龙古带神道碑》记壬申年十一月,“金主遣使啖以大官,冀其或贰,可复失地,定襄公缚使以闻。”“定襄公”即与刘伯林一起降蒙的女真人夹谷常哥,“定襄公”是其谥号。据此可知,刘伯林降蒙后,金廷曾遣使招附,而刘伯林不为所诱,死心踏地为蒙古攻城略地。
史秉直之降蒙,实为保全宗族性命。木华黎先以史秉直长子史天倪为万户,统诸降卒,以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以史秉直之弟史怀德领其黑军隶帐下,署史怀德之子史天祥都镇抚。史进道则隶木华黎帐下。史氏一门数将领随蒙古征辽东西、中都、河朔。乙亥年,金北京降蒙后,木华黎承制以史秉直为行尚书六部事,史进道先为义州节度使,后留守北京,“管领北京勾当”,史天倪升右副元帅。庚辰年,木华黎又承制以史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史天祥为左副都元帅,并兼利州节度使等[1](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史天祥传》)[19](卷一六六《史进道神道碑》)。窝阔台即位之初,史天泽即为汉军“三万户”之一。史氏一门或为地方长官或为方面将帅,以后一直对蒙廷忠心耿耿,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主迁都汴京前后,降蒙的汉人世侯还有王义、邸顺、董俊、赵迪等[30],这几个人的碑传在叙述他们降蒙时只说木华黎南下时,率众降蒙,不详其细节。其实个中原因也应该和史秉直一样,在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为保全室家和宗族性命不得不降。
汉人世侯之兴起,集中在金宣宗迁汴以后,所谓“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多如牛毛”[8](卷三《重修北岳漏台记》)。由于这一时期蒙古军的大扫荡只是掳掠人口、财物,并不占领所攻下城邑,而旋即北还,更由于许许多多的乡兵长(或称酋长)初始动机是抗蒙自保,所以他们最初的政治动向是朝向金朝的,他们收复失地,接受金朝的收编,金朝也对他们委以大小不等的官职。《圣武亲征录》(乙亥年,贞祐三年):“上遣脱脱、栾斡儿必帅蒙古、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东平,阻水不克,大掠而还。金人复收之。”所谓“金人复收之”的“金人”,主要指这些乡兵长[28]。“在金叔世,宣宗蹙国播汴,河朔豪杰,所在争起,倡纠义兵,完保其乡。金訹以官,冀赖其力,复所失地。”[5](卷二二《荣祐神道碑》)这条史料亦可说明河朔及山东西部地区武装初起家时的政治动向是朝向金朝的。许多后来成为蒙古国和元初典型、比较典型的汉人世侯起初也是归附金朝的,并接受金朝的官封。如前述张柔、严实、何伯祥父子、王义、赵迪、乔惟忠等。
但到蒙古侵金战争的第二阶段,成吉思汗亲率军西征的同时,对金统治地区不仅抢掠财物,掠夺人口,而且攻城夺地,以期实现其长久的统治,因此蒙古更着重利用投降他的汉族军事武装与附金汉族军事武装展开争城夺地的激烈战争。1217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任命木华黎为国王、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都行省承制行事,率蒙古、契丹、汉诸军南征。此前降蒙的汉人将帅刘伯林、史天倪、契丹将帅耶律秃花、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等各率万人以上部队随木华黎征伐[29],王义、邸顺等在河朔一带也与附金的汉人武装展开攻城夺地的斗争[1](卷一五一《王义传》、《邸顺传》)。木华黎率军征金的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汉人世侯背金降蒙。《青崖集》卷五《段直墓碑》说:“及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兵来略地,两河、山东,豪杰并应。”所谓“并应”,当然是隐讳的说法,大批汉人武装纷纷降蒙,却是事实。
前已言及,金朝对河朔、河东一带“义军”实行招附政策,并对他们委以一定的职官。为什么那些接受金封的豪杰、固守自保的乡兵长纷纷降蒙呢?其实与史秉直等一样,那就是对面蒙古大军压境、不降便性命难保之时,出于人的原始本能——对死的恐惧、对人生的贪恋而降蒙。
其次是蒙古的招降政策,降蒙的原金官吏,官复原职;归降“义军”,根据其人口、兵力、地盘封以相应的职官。而且,降蒙的汉人武装头目还可以“随所自欲而盗其名”[24],以名正言顺地招降、收编其他固守堡寨的乡兵。《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金既播汴,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而且“守令”皆可世袭。另外,这一时期,金朝在河朔、山东一带控制的地盘陆续丧失,而蒙古控制的地盘逐渐扩大和巩固,在此形势下,附金的汉人武装背金降蒙,可以说是“识时务”的选择。
蒙古人还有使汉人世侯死心踏地归附他们的方法,即纳质。如张柔降蒙后,“其散卒稍稍来集,主帅恐公(张柔)为变,质二亲于燕,公叹曰:‘吾受国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顾忠孝不两立,姑为二亲屈。’遂委质焉。”[23](卷六《万户张忠武公》)此后,在征金、灭金、征宋、灭宋、与阿里不哥之战以及平定李璮叛乱过程中,张柔一门对蒙古一直忠心耿耿,恐怕与其二亲在蒙廷为质关系甚大。张柔降蒙的同年,其部将何伯祥、乔惟忠、聂福坚等亦率众降蒙。他们此后一直对蒙古忠心无贰,张柔家族“百战立功”,其功劳甚至超过真定史氏[11](卷一四《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
在河北地区,1217年,刘伯林、萧也先攻蠡州,蠡州博野人王兴秀撼三十余村之民,集壮士数百辈出蠡疆迎刘、萧两大帅降。王兴秀降蒙之事,颇能反映大多数降蒙世侯的心态。在蒙古蹂躏山东、河北后,“金不能国,可必亡”,金朝的灭亡大势已定,“民既困征求之繁,馈餫人畜,杂死道路,至不赖生”,金朝政府的征敛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也就失去了民心。所以当“大兵又至”时,人民自然会想到“今已委身饵敌,暴骨草野,且吾君已弃民,民尚谁死哉”[5](卷二一《王兴秀神道碑》),也就不愿为“弃民”的金朝统治者殉命,所以降蒙。王兴秀降蒙后,随征河北、山东地区,由新军千户而升万户。1217年降蒙的另有王玉,领本部军从攻邢洺、磁三州与济南诸部,又从攻河东诸州郡。乙酉年,史天泽击败武仙后,王玉权真定五路万户。[1](卷一五一《王玉传》)
自1218年至1221年,河北地区降蒙的汉军武装头目还有赵柔、耿福、王善、李直、王珍、杜泉、贾德等[30]。这些人降蒙的原因也是为保全性命计,如1221年,蒙古军至景州,欲为屠城之举,贾德行至深州降附木华黎,木华黎许其请,“阖城赖以全活”。[9](卷四七《贾德行状》)
蒙古征金初期,河东一带州县“义军”多“恃险不降”。但1217年起,蒙古军对河东发动强大攻势,此年,蒙兵至坚州繁寺县,乡兵长王兆“度不能支”,与刘会等十数人持牛酒至主帅麾下通姓名归附,且献攻城之策,“繁寺生口一县赖以全济”,王兆继受监国公主教,迁坚州左副元帅[15](卷三○《王氏世德碑》)。同年,蒙兵至忻州定襄县,周献臣知何东必不可保,认为天意不可违,与其殉匹夫之节,不如全万人之命,于是率众迎谒郡王于军门。先受定襄令,继以勋升九原府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行九原府事。后又从征金、伐蜀[15](卷二七《周献臣神道碑》)。也是在此年,汾州乡兵长梁瑛不愿“填死沟壑”,率众诣木华黎军门降[15](卷三一《梁瑛神道碑》)。1218年,汾州县临泉令袁湘在蒙军压境、人心离散的情势下,为保全州人性命,款附于蒙古大将孛罕[5](卷一七《袁湘神道碑》)。1222年,蒙古重兵至蒲州,州郡不支,荣河县乡兵长吴信“私念天命有在,力不可抗”,于是率众诣木华黎军门请降。[15](卷二六《吴信碑》)
“天命”、“天意”云云,皆为史家的临文便辞,不过是保全性命的藉口。由于金朝重点保守山东、陕西地区,对河朔、河东地区的汉军头领招附不力,所以河东南北路的汉军武装头目降蒙后即随蒙古征金,替蒙古招降崖壁堡寨,与金军争城夺地,参加灭金战争。灭金后,或镇守一方,或随蒙古军征宋。山东地区是金、南宋、蒙古三方争夺的地区,金朝重点保守山东地区,南宋又极力招附山东地区的“义军”、“豪杰”(多为红袄军),因此这里的汉军武装初始依附于南宋、金之间,降蒙时间较河朔、河东地区为晚,多在庚寅年以后,且反复无常,在蒙、金、南宋之间摇摆不定的也多。
严实初由金东平行台任命为百户,戊寅年,权长清令。后因谮于东平行台者谓严实与宋有谋,行台以兵围之,严实便归附南宋。南宋以严实为济南知中,分兵四出,但当庚辰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之时,严实数求救于南宋主将张林,而张林逗留不行,致使彰德失守。严实感到宋不足恃,于当年七月挈所部彰德、大名等八州之地、户三十万归降木华黎。木华黎承制以严实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次年,进攻东平,金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去,严实入据之。乙酉年四月,宋将彭义斌围东平,在食尽粮绝的情况下,严实又与彭义斌连合,进攻蒙古占领的河朔一带。不久,严实在真定又临阵倒戈,与蒙古大将合,与彭义斌战,宋兵溃败,彭义斌被擒[1](卷一四八《严实传》)。此后,严实一直随蒙古攻城略地,没有再背叛蒙古。总之,此前每当严实穷急之时,看到蒙古、金、南宋那方强盛,便倒向那一方。严实降蒙后,其部将朱楫、朱泉、赵天锡等也随即降蒙。济南张荣起初并不归附蒙、金、南宋任何一方,并以孤军“独抗王师”(“王师”指蒙军——笔者按)数载。丙戌年,东平、顺天两大汉军集团都已跟定蒙古,人稠地广的山东地区已:“悉为帝(指成吉思汗——笔者按)有”,在无所倚恃的情况下,才款附蒙古的[1](卷一五○《张荣传》)。益都李全起家初期投附南宋,丙戌年九月,蒙古郡王带孙围李全于益都。次年四月,益都城中食尽,李全势穷出降,孛鲁承制授李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32](卷四七六《李全传》)
通观汉人世侯由避兵、抗蒙到投降蒙古并随蒙古征金的过程,其降蒙的主要原因大多是惧于蒙古屠戮生灵的残暴,为保全身家和乡曲的性命才降附的;有的则是鉴于在蒙古铁骑强攻之下一败涂地,毫无胜利希望而降蒙的。由于华北地区的汉人在异族女真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后,民族的界限乃至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淡漠,面对另一个强大的异族蒙古的入侵,为了自己和宗族的性命,自然不会为金国殉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