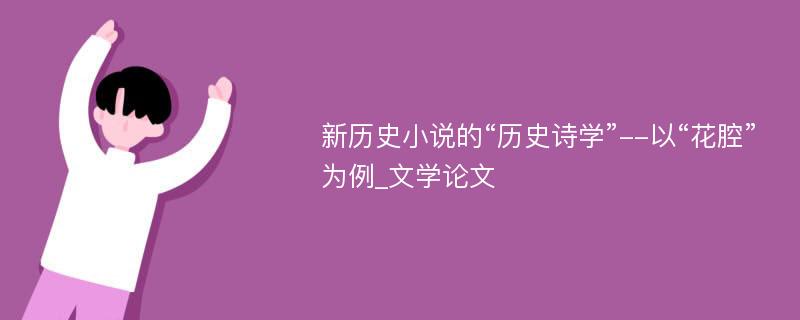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腔论文,诗学论文,为例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洱在他的长篇小说《花腔》[1]中,以小说语言提出并阐释了历史诗学这个概念,其 理论内涵涵盖了我国兴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历史小说,触及到了这个跨世纪的小说创 作思潮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意义已超出了《花腔》本身而成为我 国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花腔》是李洱历史诗学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也是我国新历 史小说的一次小说版的理论总结,标志着这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渐自觉和 成熟。
《花腔》以胡安之死为例阐明了历史诗学的第一要义,便是以个人名义将那些被排除 在历史之外和诗学之外的个人写进历史。胡安在苏区参加了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的 演出,扮演一名白匪军官,因为他演得太像了,被台下观众开枪击毙。可是多少年过去 以后,熟悉胡安革命历史、当年在台下目睹胡安演出并被黑枪打死的范继槐追忆往事时 写了一首诗,却没有提到胡安之死,理由是“胡安”这个字眼“不好押韵”。这说明胡 安作为个人被排除在历史和诗学之外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而写进历史和诗学的理由和 可能却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历史诗学就是要抓住这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将 那些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的个人写进历史,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花腔》对这种 可能性的寻找,是设置了一个“个人”(主人公葛仁的谐音)的后人,也就是关注并思考 个人命运的隐含作者作为三名历史讲述人及相关历史资料的钩沉辨析校正者,同时也是 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思考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以个人身份进入历史书写的隐含作者 ,主人公葛仁及众多知名不知名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才得以穿透历史迷雾进入同为 “个人”后人的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小说以葛仁的生死之谜贯穿全篇,在三个历史讲 述人的分别讲述和隐含作者对史料的编纂校正补遗中,又带出了近代以来百余年间20多 位知名的历史人物和众多小说虚构人物之死,其中尤以邹容之死、李大钊之死、张奚若 之死、胡安之死触目惊心,令人深长思之。作者是以个人的死来浓缩个人的生,以实写 的个人的生和死来映衬、解释虚写的象征性的小说人物葛仁的生和死。死是生命的断灭 ,是最为个人化的历史事件,历史的时间维度对个人而言就是个体生命一次性的永不复 返的时间之流,而个人的历史性就是个人生命的时间性存在。正是个人之死的无以代替 无可挽回最为集中醒目地昭示着个人生命在生存论和价值论上的意义或伪意义。小说把 胡安当年的“造假窝点”安置在一个名叫白陂后沟的山谷中,而当年关押被打成托派的 白圣韬医生的拘留所,也在后沟(枣园)。白陂后沟枣园后沟都是一个隐喻,是鲜为人知 的被尘封的“历史的后院”。众多的难以数计的原本是充满了活力的个体生命就被扼杀 、窒息于这个后院紧闭的门窗后面,沉落在历史的遗忘之谷。历史诗学的使命便是打开 这个历史后院的封闭的门窗,将历史与文学同时提升为人性的、诗性的个人化和语言化 的历史诗学。
历史和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而人是历史 中的人和历史性的存在,这个本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在中外历史理论中却被弄得扑 朔迷离面目全非。对历史是什么的追问永远和对人是什么的追问纠缠在一起,历史观与 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的已然和应然存在、认识论生存论价值论相统一的人的哲学观)不可 分割。这个道理,到了作为实证主义历史学反拨的现代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才明 确地把研究历史与研究人联系起来,把历史与人的关系理论化,认为对历史的解释也就 是对人性的解释,认为人性就是历史。“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能讲清楚”(狄尔 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做过了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柯林伍德 )。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对历史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研究,历史学就成了 一门不折不扣的人学”[2](P380)。历史学是人学,文学更是人学,那么以文学形式进 入历史书写的历史诗学不言而喻更要把自己的目光凝聚在历史与人这个聚焦点上。《花 腔》历史诗学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贡献,是在创作思想上具体地把历史与人的凝聚点 聚焦在“个人”身上,把历史与人的关系具体化为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历史 的也是人的根本。
关于人的个体性以及历史与个人的关系,马克思早有明晰的论述:“人是一个特殊的 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真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 ”历史与人的关系究其本源实历史乃与作为个体生命的个人的关系。“历史不过是追求 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这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历史的合力”, 才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因此,“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可是偏偏就是这个前提性和普泛性事实,却被人类自己弄得暖昧不明,使个人成为 历史的不在场者而长期缺席。
历史观与人的价值观的统一,在我国当代历史小说由传统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嬗 变中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以当代小说书写历史基本单位的变迁为切入 点。在新历史小说之前,书写历史的基本单位是国家、民族、阶级等集团的人,其人的 价值观以集团为本位。这里尽管也活动着有名有姓有男有女的各色人物,可是这些人物 在某一历史活动中不过是某一集团(国家、民族、阶级等)的符号、筹码,一一对应着某 种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所写的历史实乃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的国家史、民族史、阶级 史,其中的人物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不是被扭曲便是被遮蔽。例如歌颂英雄人物的小说 便是以芸芸众生陪衬和服务于英雄史观和人的等级制的生命价值观,而以阶级斗争的胜 败解释历史的历史观,必然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放弃、牺牲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充当阶级斗 争的工具、手段,使个人无声无言地消融于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风云 之中。这是一种以历史的名义吞噬、占有个人价值的历史观。到了新历史小说,书写历 史的基本单位便开始向村落史、家族史(或曰民间史)转移,其中所隐含的历史观价值观 也悄悄发生变化,人的只有一次的生命价值的无谓牺牲开始从历史的重重遮蔽中浮现出 来,历史这个以公正、客观面目出现的庞然大物浸透了血腥味,以历史或群体的名义剥 夺、扼杀、践踏个体生命的历史活动失去了它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而显露出冷漠 、麻木、残酷、荒廖的面目。一些女性家族历史小说虽然是以家族为书写历史的基本单 位,但女作家们书写的是家族中的个人历史,个体生命灵与肉的挣扎,女性主体价值追 求的渴望,以及鲜为人知的女性生命体验。这些挣扎、渴望和生命体验凭借着“家族” “代”这些生存单位和生命范畴从尘封的历史后院中浮现出来,构成了个体边缘史对正 史的对话。到了《花腔》则明确地以个人史为最小的不可通约不可替代的历史单位。它 的众多人物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小说虚构人物,虽然也有着各自的民族、阶级和社团属 性,但作为为个人而生而死这一人的本体属性挣脱了种种类属性的标签,活动在历史的 时间长河中,表现出历史对个人的强制性塑造与个人在历史中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无奈 。葛仁在《谁曾经是我》一诗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他没有找到。他的自传《行走的影子 》,最终也没有完成,而这个自传才是个人成其为独立的个体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其 实正是人对历史中自我的反思,可这样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也就是说人由已然状态到 应然状态的开端还没有出现。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即独立、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 权力的个人的出现,一定要以这个人文反思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腔》标志着 新历史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的时间性以个体生命的时间性进入了历史书写,所 谓宏观叙事“大历史”化解为人性的个人化的日常性生命活动的“小历史”,漠视、无 视人的存在的历史理性由于价值理性的渗透、照亮而放射出人文主义理想的温馨。
作为个人的胡安之死进入历史讲述了吗?《花腔》的隐含作者通过史料的爬梳、补正找 到了四种有关叙述。胡安只有一次生命,今生今世只能死一次,何以出现在历史中的胡 安会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呢?
这里暗含了新历史主义和福柯权力话语的某些理论命题。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 性,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意思是说时间维度的历史转瞬即逝,我们所能够把 握的只是有关历史的讲述,即文本。尽管历史先于文本,但文本之于历史并非如影随形 ,应声而至,而是一个在讲述中有待文本化的过程。逝者如斯的历史只能靠文本为自己 赋形,历史在文本中逝而复返,在一代代人的阅读、理解中获得虽死犹生的生命。如果 说历史文本是人们得以透视已逝历史的一扇窗口的话,这个窗口由于制作者的历史性和 权力话语的运作,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语境和权力话语的制约,而成为受权力集团控制 、挤压的变形的窗口,这样的窗口既不是透明的纯净的也不是惟一的。有关胡安的四种 版本,就说明了历史文本的多样性和非透明性,说明任何一种版本都无法穷尽胡安个人 生死的全部真实。在这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给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以有力的支撑, 使人们得以洞察历史文本制作中那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权力运作的秘密,识破正史、 官史对历史真实解释权的垄断,使历史书写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话语行为。“历史是在街 垒两边制作的,一方的制作与另一方的制作同样有效”(怀特),这种由于识破了权力话 语的隐密而进入历史书写的主动性,启发了我国新历史小说创作的灵感,激发了作家重 新认识历史、认识历史中的人的激情的勇气。正是在这种以个人身份进入历史书写的主 动的话语行为中,个人在历史面前不再是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的,面对权力运作所织成 的语言之网,也并非束手就范和被强制塑造这一条路可走。《花腔》这个标题的立意就 是现代语言学的。三位讲述人一面声称自己不是“耍花腔”,一面却不由自主地“说花 腔”,他们的叙述话语充塞着大量权力话语和流行的广告话语,盛极一时的领袖语录及 商业广告、民间谚语俗语等,表现出一种不约而同的无意识的“语言拜物教”,即对“ 他者”语言的“社会无意识”(弗洛姆)[3]。根据拉康的分析,语言的无意识也就是生 命的无意识,好像是个体生命中的另一个“他者”在说话。这种不由自主的“语言拜物 教”是对权力的恐怖与崇拜,或因恐怖而崇拜而听任无意识的“他者”语言对自己的宰 制。有意味的是,三位历史讲述人平面化的叙述话语,却在整体上达到了对权力话语的 否定,对人之非人的否定,批判了以人为使用工具和人在历史中成为权力斗争牺牲品的 可悲处境。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否定之否定的反讽逻辑,是以后现代的非个人化话语 达到了肯定个人化、肯定人的主体性的现代性历史文本。这自然与隐含作者历史诗学的 价值理性有关。
关于胡安的四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或更真实的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伪问题 。既然历史如逝水忘川一去不返,既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全知全能,更何况还有 权力这只隐形的巨手的操纵,那么任何一种历史文本对历史真实的全部占有便无异于天 方夜谭。这样,传统认识论的主客观统一论、符合论便遭到了质疑和消解。这并不是如 德里达所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而是历史文本之外这个“有”的终极面目究竟如何 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样一来,那些宣称唯我掌握着占有着全部历史真实或历史本质历史 规律者便显露出其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和虚妄。我国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们领悟了这“历 史真实”的奥秘,以个人的眼睛去观察以个人的头脑去思考,写出自己眼中和心中的历 史的真实。这是从个人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历史真实,是个人记忆、经验、智慧和信念 的诗性升华。于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转换为接受者的真实感问题与可理解性。“真实有着 自己的声音,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耳朵都不会听错”(左拉)。这是为什么?尽管并没有一 个真实与否的统一的标准,可每个人对真实与否的判断却大体相同。这是一个深刻的哲 学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人性问题。回到《花腔》胡安之死上来,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 这个“真实的声音”的理解。对胡安个人来说,究竟是何种政治身份的人对他放了黑枪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这四种版本综合起来,便可以看出在他死后还被某种政 治目的所利用,用他的死做文章,死后的胡安又充当了一次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和《花 腔》中《革命军》作者19岁的热血青年邹容生前死后被各派政治力量炒作以宣传自己有 异曲同工之妙。可真实的病死狱中瘦如骷髅的邹容却无人过问。《花腔》对葛仁、胡安 、李大钊、瞿秋白、王实味等历史人物的描写,经受住了它的隐含读者真实感的检验, 一百多年来一大批在历史上留下和没有留下名字的红色知识分子的身影由模糊到清晰。 他们自身那属于一个时代的知识者的革命狂热(当时被称为革命罗漫蒂克)和身陷政治斗 争漩涡无力自拔的沉痛教训,铭刻于“个人”的后人们心中难以忘怀。这便是每个人的 耳朵都不会听错的真实的也是人性的和历史的声音,是“历史诗学”的真实。
第三种版本说观众把舞台上饰演“白匪”的胡安误认为真实的“白匪”,是因为混淆 了艺术和现实的界限。这里的“现实”可等同于“历史”。那么,艺术和历史的界限又 该如何划清又有谁能够划清呢?正是这二者之间难以划清的空隙,为历史诗学留下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文史互通乃至文史不分,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文学史和历史毕竟 又有区别,二者之区别何在,又在哪里互相沟通呢?亚里斯多德《诗学》的有关论述在 此仍具有经典意义:“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之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 受到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描述个别的事”。亚里斯多德允 诺了文学描述带有普遍性的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也就拆除了文学与历史之间原本脆弱的 防线。也许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新历史主义的辩护人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理论 中,认为历史是被历史学家阐释和编织过的有关历史的语言结构,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 像性,它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构和想像的。“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在虚构这 一点上可以类比”。这样,历史和文学在亚里斯多德所奠定的“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哲 学基础上同时获得了在人性的诗学范畴内合理想像与合理虚构的权利,这也正是我国许 多新历史小说家融合历史与文学、纪实与虚构叙述策略理论上的合理性依据。
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将他们的批评理论命名为“文化诗学”“文化政治学”(格林布 拉特)和“历史诗学”(怀特),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新历史观与文学观,与我国新历 史小说家们达成了某种理论上的默契。然而,后现代的消解历史深度和意义、历史碎片 化、时间空间化和理论上的繁杂性说明他们尚未找到历史与人这一历史与文学共同的理 论支点,在经历了80年代后半期的强劲势头之后迅即沉寂,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也曾对我 国部分新历史小说产生过负面影响。《花腔》等出现于世纪之交的新历史小说的“历史 诗学”实践,吸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而避开了它的局限性,是我们自己的中 国版的“历史诗学”,它们在创作理论上的日益自觉,可以证明所谓新历史小说的终结 论未免为时过早。
收稿日期:2002-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