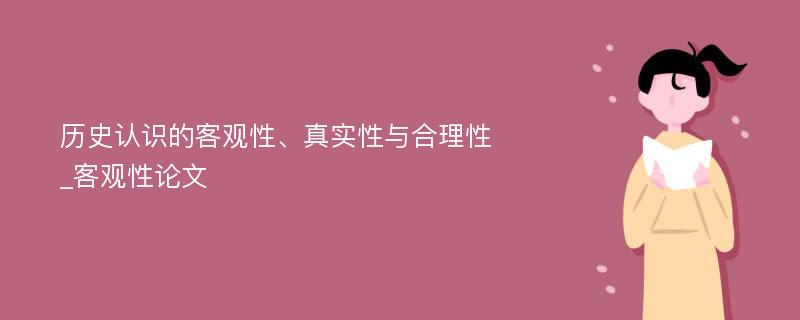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性论文,合理性论文,理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是决定历史学科性质的根本问题。西方学术界一百多年来形成了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两大对立派别,国内关于此也久讼不决。其焦点在于:(1)历史研究少不了历史学家的积极参与和认识主体的介入,能否实现认识过程的客观性;(2)在不可避免认识主体介入的前提下,历史认识结果能否达到客观真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客观真理性。
对于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主体的介入。相对主义者强调主体介入后已无客观性可言,实证主义者则力图消除主体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笔者认为,历史认识不可避免认识主体的介入,认识主体介入同样可以达到认识过程的客观真实性(参阅拙文《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只有遵循历史研究的科学规则,并承认主体的能动作用,才有可能深入地进行历史研究,探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问题。
对于后一问题,以往的历史研究都是用认识了的历史事实与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之间是否一致来衡量其客观与否。而实际上,历史认识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客观真理性。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所有内容都要研究,而是有所选择。综观之,历史研究可划分为历史事实的确定、历史意义的判断、历史本质的抽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层次,亦即在认识层次上可区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此三类认识具有不同层次的客观性要求;在考实性的历史认识层次上实现客观性,在探究具有抽象性、规律性的抽象性认识层次上追求真理性,在历史评价与价值判断的评价性认识上寻求科学合理性。
一、历史事实的确定:考实性认识的客观性
考实性认识是确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存在形态,是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可以归纳为人们时常所说的“历史事实”的确定。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最基础的层面也就是历史事实是否具有客观的性质,以及对它是否能够作出客观的认识。按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论,包括:(1)由一系列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组成,指的是事实的本体;(2)为认识主体所指向的、纳入主体认识活动的成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3)通过史料可以获得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即已经形成认识的历史事实。不论历史事实的定义如何界定,本文所研究的是:已经认识的历史事实能否与客观实在的事件事实具有同一性,或能否真实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
对此,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研究能够“如实地说明历史”。它所依据的逻辑是:(1)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2)经过严格考证的史料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3)如果史料的收集是全面的,主体又不将其个人特征强加给它,那么,对事实的认识就能够与事实本身相符,就可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以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者则持否定态度,强调历史认识不具有客观性。其根据是:(1)历史事实是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选择出来的一部分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在其被确定的时候已经和历史学家的主观发生了联系,外在的“事实其实并不存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2)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史料中介来获得,但史料不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历史事实。(3)史料通过一般的语言概念来表达,必然受到语言的强制性改造。因为历史研究中,不存在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一整套价值中立的技术词汇。(4)在使用语言说明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历时性的影响。语言的内涵是被历史地改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内涵,都有自己的特定情景。后来者由于处在已经变化了的文化背景中,必然会出现理解上的障碍。同时,语言的歧义性、多义性也使得理解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事实永远不能被客观地把握。
如果像相对主义者那样完全否定客观性,则历史研究会失去意义;而要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做不到。在这里是否有第三条出路呢?笔者认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研究需要摒弃下面两种不切合实际的传统观念。
一是那种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从认识与实物之间的关系上来界定真假客观问题的方法,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种看法是将认识与事实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拍摄式的符合关系,是照片与底片的关系。这种看法来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意念、想象,具有拍摄式的符合情景。但是,一旦进入到认识领域,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就无法用照相式的关系来表达了,要求认识达到与事实具有照相式的客观真实性,那只能是一种办不到的理想。因此,我们反对那种照片与底片相符合式的历史认识客观性。
二是过于强调史料记载的全面性。史料记载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是千真万确的。问题在于:其一,史料的不全面的确会影响到认识结果,但历史研究是一个过程,随着认识的深入、史料收集的全面,终将获得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其二,倘若为了获得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为了追求记载的全面性,将现实生活的一切、事无巨细地一概加以录制,后人会愿意看这些杂乱无章的录相吗?为了客观,弄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资料、数据,历史研究还有意义吗?
因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应有其自身的规定性。
首先,事实本身的历史实在是客观的。从一系列曾经发生和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这一概念的第一种涵义出发,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前提是客观的历史实在。比如我们常说,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它,它都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虽然我们无法复活过去的历史,但是,过去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大多数相对主义史学家都承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客观真实性的前提。
其次,并非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的是为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客观历史实在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561页)。如果我们能够对事实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就是一种为我的存在。自在的存在和为我的存在都是客观的存在,但两者的含义不同,不能不加以区别。为我的存在亦即“历史事实”概念的第二种涵义,就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认识客体是一个与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如果说历史事实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的独立存在意义,那么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具有同主体的思维活动相关联的意义。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客观存在,还必须从主体方面、从与主体的关系中去理解和规定。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成为主体的认识客体,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成为为我的存在,不仅表征出认识主体的目的、水平和能力,而且还表明了它与主体之间的有用性或为我关系。这是历史认识的一大特征。
当然,并非一切历史事实都能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只有那些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纳入主体认识活动的历史事实才能称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而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也不会固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和层次上。随着历史认识的发展,许多自在的历史事实不断地进入到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成为现实的认识客体。因此,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又可以分为显在的和潜在的两种。显在的历史事实就是那些已纳入人们的认识活动,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潜在的历史事实是指那些尚未正式进入人们的认识活动,未被人们认识指向的历史事实。我们探讨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只能研究那些显在的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再次,对于为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客观的陈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其客观性。其根据是:
从认识过程看,认识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历史认识的事实是史家由于现实的需要和兴趣而借助于史料建构的关于过去的认识,在认识的特性上是一种观念的认识。其历史认识过程包含着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的就某些历史事实而展开的实际信息交流过程。在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外,西方一批重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历史哲学家们独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提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法国历史批判哲学家马鲁称历史“是经由历史学家的努力,在思想中取得的对于人类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处于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由认识主体的积极、主动的介入而建立起来的关系中、综合中”(转引自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将历史认识过程界定为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强调只有在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之中,历史事件的意义才能被理解。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是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历史认识主体在研究之前的准备不应该消除一切主观因素,而是要更好地装备自己,研究者必须在意识到历史事件的非主观性的同时意识到自身的参与性,研究历史不是“隔岸观火”,而是在历史中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虽然不可能达到认识结果与认识对象的绝对同一,但可以达到观念认识上的客观性。历史研究只能追求观念认识的客观性,而不可能达到照片与底片的绝对同一。
从史料看,虽然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再现的,史料是不全面的,但我们认为,史料的不全面只会影响认识的全面性,而不妨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历史认识只能经由史料、历史遗存物去重构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于史料,史料责无旁贷地成为历史认识的中介。史料能否具有客观性,是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必要前提。以历史文献、历史文物的形式保留下来的人类过去实践活动的遗迹、信息、部分遗存物,是史家重构历史事实的根据,当然也是某一历史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其理由是:其一,历史文物是人类过去实践活动的部分遗物、遗迹,它以物质的形式留存至今,经由文物鉴定、考古发掘可以作为建构相关历史事实的物质依据;其二,以历史文献留存至今的史料,虽然记载者不可避免主体的介入,且不可能面面俱全,但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秉笔直书为传统,客观公正性强。中国传统史学将历史的记载与传述视为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在史料记载上最为讲究客观性方法。中国古代的“实录”与“直书”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在做出很大牺牲的情况下写就的,如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崔杼弑其君,史官据实书写被杀,他的两个弟弟照样书写又先后被杀,第三个仍不改初衷,这是中国古代直书的典型。中国传统史学为实现历史的客观性,要求历史原始记载的客观公正性,历史认识过程则强调对史料分析的客观性,在这方面乾嘉史学之史料分析批判方法往往被人们忽略。
从史料所运用的语言看,的确,语言的使用存在着不当的可能性,但这一点不能作为否认客观性的根据,因为,通过学习能够更大程度地把握和使用语言,尽管语言的历时性、歧义性和多义性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时代断限上,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结论不同,证据同一。他们所使用的史料都是《诗经·周颂·臣工篇》和《诗经·小雅·大田篇》。正因为《诗经》时代久远,出现了语言文字的历时性、歧义性和多义性,造成理解的极大分歧。但对史料理解的分歧只能说明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尚有欠缺,并不能否认史料本身具有客观性。
由上可见,过去的历史不可能复活或再现,过去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史料和其他历史遗存物,历史学家再经由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建构历史事实,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史家主体的介入,相对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否认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他们只看到了主体介入的一面,看到主体不可避免的主体性,却看不见认识主体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必须在遵循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建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实在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那种相互间的交融过程,决定了认识主体并不能脱离史料、历史遗存物去杜撰历史。
因此,历史事实的确定,作为一种考实性认识,只要通过史家的不懈努力,其客观性是可以实现的。亦即历史学有能力对过去的史实做出真实的陈述,在历史认识的初级层次上,确实可以达到沃尔什所说的“对任何一个从同样一组证据出发的观察都可以成立的那种意义上”(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的客观性。
二、历史意义与抽象认识的真理性
在历史认识中,除了历史事实的确定外,还有各类历史事件对尔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意义或历史效应,也还有沉淀于历史背后的历史本质,即我们所知的历史抽象性认识。从层次分析上看,历史可区分为现象与意义两个部分,历史意义中又可抽取出历史本质。
历史现象是浮现在历史表层的一个个历史事实,历史认识不仅要考证历史事实,使之成为历史叙述的对象,还要对具体的个别的事件对尔后历史的影响作出分析,从过去、现在、将来把握历史的意义,从现象认识升华为历史意义的判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某一历史事件作为可观察的现象结束了,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地结束,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浓缩在现实与未来中,对以后的历史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用,即该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一系列由具体时间和空间展现出来的历史事件,其意义即效应取决于它对以后的历史影响,它与现象不同,不属于纯粹的过去,而更多地属于现在和未来。在这现在和未来的进行式之中,对其判断离不开主体的参与,其意义更需要主体的判断和概括,而判断和概括又与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必然渗透着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因此,意义判断不仅仅因认识主体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造成对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历史意义的判断尽管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相对性,但它仍然与过去的历史事实本身紧密相关,不能脱离历史事实而随意杜撰,其客观性、科学性要求以过去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与社会历史本质相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不以已经认识的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为依据,而只看到意义判断的相对性就随心所欲,那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意义的判断都不应当脱离历史实际,脱离社会历史本质和社会历史的普遍性而随心所欲。
透过历史表象看本质,发现历史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这是历史的抽象性认识,它追求认识的真理性。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历史真理问题仍然争论不休(参阅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本文认为,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与真理性,理由是:其一、现实是由历史构成的,在历史运动前后代人之间,前人的主体性活动及其结果是后人实践活动的对象和既定环境,是后人活动的客体。也就是后人面对的是一个既定的不能自由选择的事实,前人的活动结果不可能在后代一下子被全部抹掉,于是,前后代人之间的这种历史联系,使历史的既成性与继承性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从而使历史的运动成为一个客观的过程。简而言之,人们创造历史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并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进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客观的,这一客观过程便具有了历史的规律性。其二、从历史认识中抽象出来的那些揭示了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符合实际的知识体系,便是历史的真理。例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直接把历史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对历史的这一抽象认识就具有历史的真理性,因为,“现实的人”是活生生的、从事活动的人,他为了生存就必然要进行生产,必须与自然、社会发生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必然要在自然规律与社会环境的约束下从事活动,于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便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辩证发展过程。这些认识对于任何历史研究来说,都具有普遍性与客观真理性。
目前关于历史的真理性讨论还纠缠于什么是真理以及真理与非真理的区别。笔者认为,不论任何历史的抽象性认识、任何历史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检验中能够成立的,才能称得上历史真理。其检验过程为:
历史的抽象性认识来之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抽象,其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如下两个步骤的检验:
一是科研实践的检验:(1)历史学家通过各种历史事实的积累与验证来确定其抽象认识是否正确;(2)史学家通过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达到对历史抽象的系统化认识,从史实中来,又反馈到历史中去,通过比较验证其系统认识是否正确;(3)通过历史学家群体间的科研实践来深化和提高历史认识的水平。
二是经由现实社会实践的检验:抽象性认识是从史实中抽象而出,其认识可用现实社会实践作检验。这是因为:(1)现实是由历史构成的,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现实社会实践中渗透着过去的历史实践所遗留下来的信息密码、遗传因子和实践的影子,这些因素存在于现实社会实践中,也就可以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这些因素作为验证历史抽象性认识的证据;(2)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运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过程,有些历史的发展因素不仅存在于过去,还会存在于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的社会实践中,如此历史自身的相同性与相通性,便可用来作为检验历史抽象性认识的证据;(3)历史研究要求从现实出发,历史观念的形成既是来自于过去的社会实践,又反映出史学家的主体思想和对过去历史的抽象性认识,是现在史家与过去史实之间的双向建构,如此历史的抽象性认识,其检验可经由过去与现在的统一来进行,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来验证,脱离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实践就无从谈起。因此,历史认识的真理性,不可能通过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客观中立来获得,而只能由认识主体的积极介入,通过不断的证实和证伪来获得,通过实践来检验。
由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抽象性认识追求的正是其认识的真理性,而真理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三、评价性认识的科学合理性与评价标准的普遍性
历史学不能也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理由至少有三:(1)客观历史是具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摆脱价值观念的影响。任何时代、任何个人,其行为、思想都具有价值倾向,人们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价值判断。(2)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了,要如实地描述这样一个整体的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必然要对研究的内容和事实有所取舍、有所选择。这种研究方法不可能不受价值观念的制约。(3)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它具有借鉴性功能、揭示性功能、教育性功能,等等,几乎所有这些功能的存在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成为历史学的一项本质要素。但是,历史学家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如何保证历史学家价值判断的科学性呢?显然,由价值判断组成的历史评价,要获得客观一致的评价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要求达到评价性认识的科学合理性。
从哲学上看,合理性与客观性是两个相对的范畴。客观性是事物的属性范畴,合理性是行为主体的行为活动范畴。历史科学要获得真理,一方面要有合理性的认识程序,另一方面,合理性根源于客观性,只有在历史实在客观性的制约下,经过合理性的认识过程才能实现认识的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过程的合理性,要求认识主体要达到一定的认识目的,就必须使其认识活动自觉地指向认识对象,合理性地在观念中对来自认识对象的信息进行建构,避免和排除主观臆想和没有根据的猜测,以合理性的认识方式去实现。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评价性认识难于达到科学性的要害有三点:一是评价性认识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而评价者又是当代的,评价者总是从其自身的需要出发,在认识活动过程中必然渗入主体的现代意识,反映的是历史与某一时代的价值关系,即过去的历史与现在评价需要的差异性;二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属性、关系与规定,可以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人们的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多方面的需要必然形成评价的多样性与易变性;三是主体的不同需要与同一历史客体可以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即对于同一历史认识对象,不同认识主体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不同主体赋予同一历史客体的几种不同意义可以都是真的,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况。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在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评价主体之间,必须看到,避免主体价值涉及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面对他的研究课题,浮现在他面前的是多元的价值体系,是一种价值网络。在这张网络里面的价值,有现在的价值,有所指向的那个时代的价值。不论现在抑或过去,价值体系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从历史学家本身所面对的价值看,在主体上,他难免受到如下价值体系的影响:个人价值,即每个历史学家自己的价值标准;集体价值,即诸如民族、种族、阶级、等级、党派、团体等群体的价值;普遍价值,即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在价值的组成方面,则有政治价值、宗教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等等的差异。丰富多彩的价值体系并不是都要用到,这是因为,历史事实是否是本质的、有意义的,取决于研究课题本身所规定的价值,任何历史事件只有当适合于研究课题的价值时才显得有意义,才被定为史实。评价同一事实的价值体系尽管有多种,但所有这些价值体系都必须服从研究课题的内在价值体系。任何一个研究课题都有内在的逻辑原则及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于历史评价的价值标准来说,在历史评价中,除了要有与课题的本质联系的内在价值外,还必须依据课题之外的某种标准来作为终极标准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客观主义者强调历史的价值标准来自于所研究的那个时代,即用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本身所固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过去的时代。而相对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大多主张历史价值判断的标准是现在的价值观,即用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单纯用过去的价值标准容易导致历史主义倾向,容易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再说,历史本身的价值标准也不易确定。完全用现时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历史,容易滑入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历史的评价标准应该强调历史与现时的统一,既遵从所研究的时代的具体价值观念,又遵从跨时代、跨地域的历史价值的统一性,用历史的、发展的价值标准去判断。
在历史评价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上,关键是主体的需要是否合理,亦即主体评价的出发点是否合理。从个别主体的不同需要出发来进行选择评价,其正确与否涉及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的需要是否被正确地意识到,主体能否正确地意识到自身的各种需要,从而形成完整的主体利益体系,以便为主体进行比较和选择评价标准提供基础;二是主体能否对各种利益进行正确的比较,完整的主体利益体系中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等等,取什么样的利益标准进行评价必然形成各异的评价结果;三是主体评价正确与否的关键还在于主体的需要是否合理,主体的利益体系是否符合社会历史的要求,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的合理需要归根到底是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要求。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从社会历史主体出发来进行评价,努力摆正个体的正确评价标准和社会历史主体的正确评价标准之间的关系,以人类更大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来作为历史价值判断的最终尺度。
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同,必然形成对同一客体几种不同意义的评价。例如对哥伦布的评价,西方世界对哥伦布是肯定的,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是否定的,视其为殖民主义强盗。对于同一历史认识客体,不同认识主体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价,不同主体赋予同一历史客体的几种不同意义可以都是真的。这就是真义的多元性和评价结果的多元性。相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对于同一客体的评价确实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如果将历史评价停留在真义的多元性层次上,那么,历史评价确实难有公论,也显得意义不大。问题在于,在现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做到一致性的评价是根本办不到的,主体不可避免的利益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一个必然渗入其中的因素。但在具体的历史评价中,在各利益主体对立的基础上,当然也可以做到求同存异,可以通过历史学家之间不断的交往实践来实现。
除此之外,历史评价中也可运用具有社会历史本质意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标准。如历史评价必须强调该评价所引导的行为是否合乎人类发展性和社会进步性,就是其中之一种。任何评价都将引导一定的行为,都为一定行为提供依据。评价历史的标准正确与否也要以它所引导的行为的结果为标准。当一种评价所引导的行为符合人类追求的进步目标,对人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在评价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意义时,就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哥伦布西航造就了新旧两个文明世界的会合,有利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这是主流。至于新航路开辟以后造成的印第安人灭绝等问题,在严厉抨击殖民强盗行为时,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哥伦布一个人身上。对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分清主次。在历史评价中,除了主体利益体系与价值观外,更须考虑到评价所引导的行为是否合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性与进步性,否则将使历史评价变得十分荒谬。
因此,价值判断与历史评价,更需要强调评价的科学合理性与评价标准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