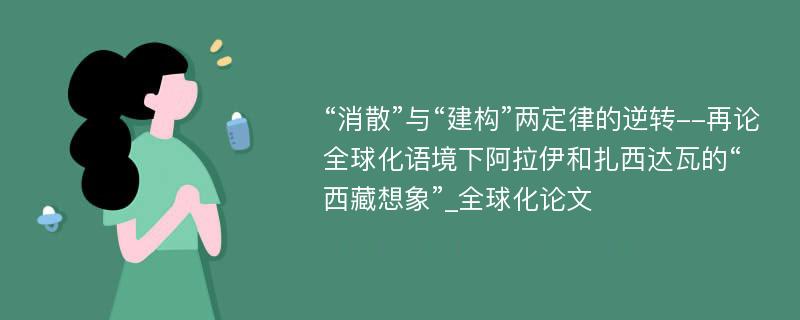
“消解”与“建构”之间的二律背反——重评全球化语境中阿来与扎西达娃的“西藏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语境论文,扎西论文,阿来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他的《圣城拉萨》一书中说:“布达拉宫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①而在藏人的眼中,布达拉宫是火焰,红宫是跳动的火苗,拉萨河是酥油。众所周知,由于封闭严酷的地域环境和同样封闭的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特征,西藏一直存在于多数人的想象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乃至文化全球化开始冲击中国之前,包括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在内的诸多写作者都曾参与了对西藏这种富于神秘感的民族文化的想象性构建,《西藏,隐秘岁月》(以下简称《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下简称《魂》)是扎西达娃上世纪80年代寻觅西藏民族文化之根的代表作品,这种寻觅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对民族性的一种建构。90年代以降,西藏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藏民族文化的神秘性逐步消褪,阿来的《尘埃落定》(以下简称《尘埃》)让人们看到藏族作家开始反观本民族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演变。在他的长篇六卷本新作《空山》中,阿来更是将藏族乡村文化直接引入到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目睹它的变异、裂变和消解过程。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写作似乎代表了藏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且和历史步伐保持了一致。本文所要表述的观点是,阿来的这种“消解”和扎西达娃曾经的“建构”之间呈现的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而是和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紧密相连。在新世纪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此消彼长、盘根错节的背景下,二者日益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历史怪圈之中。
应该说,在西藏进入全球化浪潮后,扎西达娃并没有停止对藏民族这种神秘文化特征的想象性建构。1993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以下简称《香巴拉》),继续了对藏民族心中的圣地、理想之国“香巴拉”的寻找,是对80年代的《岁月》特别是《魂》的主题的呼应和继承。《岁月》以一个小小的廓康村的变迁来隐喻古老西藏在将近一个世纪内的历史轨迹,在故事表面近乎线型的时间之流(1913-1985)里隐含着一个更为隐秘而真实的西藏:一个轮回的时空,一个在神的意志支配下的西藏。无论是故事起初等待达朗归来的廓康村的次仁吉姆,还是故事结局时准备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次仁吉姆,都笼罩在宗教和信仰的永恒力量之中。小说对宗教神秘力量的描写并不仅仅限于展现藏文化所可能包容的某种魔幻色彩,在宗教力量和现代文明的对峙中,小说结局表达了一种对民族宗教精神内核的皈依与舍弃的二难抉择。这一点在扎西达娃当时的写作中得到了自觉的、持续性的强调,《魂》中琼在跟随塔贝寻找理想之国“香巴拉”的过程中,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强烈诱惑,但最终追寻塔贝进入了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地。扎西达娃最后让负载着现代文明意识的叙述者“我”强行进入故事,终止了塔贝的追寻之途,来表达终极信仰不可通达的现代主题。但这样的安排,恰恰显示了终极信仰的诱惑难以摆脱的困惑。此外还有诸如《世纪之邀》等。《香巴拉》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延续了这一主题,萦绕着同样的困惑。小说以贵族之家凯西家族在20世纪后半时期的衰落变迁为主要架构,以达瓦次仁这个凯西家族家奴后代的成长为主线,凸显处于现代文明与民族古老文化、宗教信仰与唯物理性种种矛盾交织时期,在拉萨这片骚动不安的土地上,游荡着的一个个骚动不安的灵魂。没有了或正在失去神灵庇护的他们,生存已经成了受难的历程。琼姬最终变回了千年巨蚊,飞回了属于她的妖魔世界。梅朵也在中秋月夜离开这片佛土,回到自己的神话王国。然而《香巴拉》最后通过对藏历正月十五拉萨盛大宗教节日的描绘,安排了一个肯定性的结尾,将历史、文化、民族的救赎寄托于宗教。这究竟是该视为作者对民族宗教精神资源的坚信,寄托历经苦难的民族最珍贵的信仰拯救,还是遍寻不得通往“香巴拉”之途的不无放弃意味的冥想?其实这并不重要,扎西达娃已经通过他的困惑,构建了一个奠基于民族宗教文化之上,并永存于民族宗教文化之中的西藏。这是他作为一个藏人在困惑中的选择。
宗教是神秘文化的核心。扎西达娃小说的神秘感抑或说魔幻色彩源自于他的宗教情结,而宗教是理解藏民族文化的前提,又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这是否意味着扎西达娃认可藏文化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文化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恰恰取决于作家对藏文化民族属性的认同。从经历与作品看,作为拥有藏汉双重文化背景的扎西达娃,他的民族之根深扎于那片从古海中升起的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地。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当他决定以藏文化作为自己描述和想象的对象时,他写作的尴尬就已经注定了,这是滋润藏文化之源的藏传佛教的来世语言对现世话语的尴尬。藏文学究竟该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对一个藏族作家来说无论如何是大了些。当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花环套在他头上时,扎西达娃写作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寻根”,寻藏文化的信仰之根。《岁月》、《魂》等作品当然不是为了表现宗教在现代文明面前的荒诞和魔幻,而恰恰是表现一种庄严和神圣。琼腰间的皮绳结也并非是用原始的方法在记录毫无意义的日子,它不是电子表所能代替的,尽管后者在记时方面更精确。皮绳结不是科学,它是别的,是扎西达娃不能轻易否定的东西。它属于藏地,属于藏民族,属于宁静的和骚动的“香巴拉”。从宗教的神秘到信仰的神圣,这是扎西达娃在小说中构建的“民族性”之路。他笔下的西藏从不是荒诞和魔幻,而是庄严和肃穆,是“神性”。这才是藏文化的民族性和精神。扎西达娃的小说是在文化上真正属于藏民族的文学(当然还有色波等人),他困惑但坚定地走在这条神性之路上,以至于忽略了对“人性”的表达。
从文学发展的历时生角度看,同样拥有藏汉文化背景的阿来(这里仅就文化身份而言,阿来的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基本上属于后来者。对扎西达娃建立的传统来说,他还是个颠覆者。阿来出身的马尔康四土地区属于嘉绒藏区,嘉绒文化属于正统藏文化的分支,是正统藏文化面向四川盆地时与汉文化碰撞的产物,阿来在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中详尽叙述了这一过程,这里不复赘述。但必须说明的是,嘉绒文化形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夹缝区,以藏传佛教为源但汉化程度颇重。阿来本人的文化身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像扎西达娃那样成年后再入藏文化的中心拉萨从而形成自己的藏文化中心观。阿来长期工作生活在这文化夹缝区,他的文化身份是比较尴尬的。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嘉绒文化的阿来,已经远离藏文化的神性,而专注于“人性”的表达和揭示;远离拉萨与布达拉宫,而专注于这一地区土司政治的兴衰。1985年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老房子》写的就是土司官制,短篇《月光里的银匠》写土司统治下平民的尊严,《尘埃落定》(以下简称《尘埃》)则是土司政治和人性欲望、尊严的集大成者。当然,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完全脱离藏文化的笼罩,但在《尘埃》中,代表苯教的济嘎活佛在麦其土司面前低声下气,来自遥远拉萨的格鲁派的翁波意西最后成了傻子的现代市场化实践的书记官,宗教的角色在世俗的政治权力面前显然边缘化了。而之所以选择一个傻子来作为叙述者,是因为这可以避免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外在精神因素对叙述的干扰,有利于表达阿来一再强调的、那种在神秘的藏文化统治区也普遍存在的人性本能。“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外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②这就是阿来对读者解释的《尘埃》中的“普遍性”。这种选择对阿来来说是很自然的,是他的成长经历和双重文化背景赋予他的。刚出版的长篇六卷本小说《空山》,更是将阿来“自己置身”的藏族乡村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走向解体的过程展示得细致而详尽,将藏文化的宗教神秘感一点点溶解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冷酷、畸形和理性中。之所以要强调“自己置身”这一点,因为笔者认为阿来笔下的藏族乡村仅限于嘉绒藏区,而无法代表整个藏区的全部,而阿来在诸多场合的言论并没有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有意无意误导了读者的阅读和评判。所以有批评者将其笔下的西藏指称为“被劫持的西藏”,笔者以为,更妥当的说法应是“被替换了的西藏”。
阿来用迄今为止包括《空山》在内的小说颠覆了扎西达娃建立起来的对理想之国“香巴拉”的信仰,用世俗的、普遍的“人性”消解了扎西达娃的“神性”。这和现代社会发展步伐保持了一致性,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作家的必然选择之一。阿来在截止到《空山》以前的作品中,显示了他和宗教文化的疏离,这和他自幼接受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又长期在汉文化区工作有直接关系。汉文化在他的文化观念构成中挤压着藏文化,进而影响了他内心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作家的民族身份形成了错位。这种现象在藏族作家中很普遍,当然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对于阿来,则是与处于族际边缘的嘉绒文化的这种夹缝地位、兼容特征分不开的。而扎西达娃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文化全球化甚嚣尘上而本土化顽强据守的今天,能否赋予阿来对扎西达娃的这种“消解”以文艺复兴式的从神到人的积极进步意义呢?问题显然并不是那么简单。
文化身份问题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摆在藏族作家面前的一个特殊课题,它直接源于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与行政籍贯无关,而与文化归属感直接相关。同样作为用汉语写作的兼有藏汉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扎西达娃在文化归属方面属于藏文化,这没有太多的异议;阿来就不太好说了。他在《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一文中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而“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他还说,他与许多西方作家的优秀作品是在汉语中相逢的。③可见,汉语对他的写作影响更大,藏语只存在于他的口语中。从他的写作看,藏文化的民间特质体现的确实不多。《尘埃》中没有多少这些东西,因为一个傻子是不可能有这些概念的。《空山》就更弱化了,藏文化只作为一种传统和背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主体凸出的是现代历史进程。其实,在此之前,他在短篇小说《血脉》中就借“我爷爷”在汉藏两种语言中的进退失据,再现了这种族际边缘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到《尘埃》和《空山》,阿来写作上的文化选择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他在2008年4月央视《面对面》为他录制的节目“边走边写”中说,藏族只是一个“名词”,而许多人认为是“形容词”,是一个象征。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个“形容词”进行“名词化”,就是去神秘化,让它变成真实的存在,从西藏的老百姓的世俗生活层面找到和别的地方的人一样的东西。从这个立场出发,阿来对扎西达娃笔下的西藏的“形容词化”进行了“消解”是顺理成章的,完全符合他的文化选择和西藏作为中国一个行政区域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变化。从背景上说,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作为后来者,阿来的选择是否意味着扎西达娃对藏民族神性文化的持续建构已经失去了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呢?阿来认为西藏没有那么神秘,这是全球化视角下的科学认知,是“事实意义上的存在”。他是在线性发展的时间意识上获得这一认知的,但时间意识只是构成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状态的一维。在某种程度上,阿来忽略了另外一维,那就是空间意识。在萨义德看来,空间意识比事实存在更具有诗学价值:“事实的存在远没有在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后者通常是一种我们能够说得出来、感觉得到的具有想象或具有虚构价值的品质……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④萨义德引述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的观点证实自己的看法,同时列举了文学经典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说明空间总是审视着“看”的空间,“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⑤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具有一定“空间”的文学,失去了这种“空间”,民族文学就失去了题材和形象的可能性。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存储于这种“空间”之中。在空间意识的基础上,来显示“民族性”的时间意义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民族文学最充分的独特性。《尘埃》的成功,也是通过傻子这个特殊审视者的目光,将马尔康四土地区的土司制度和它的近代演变史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独特性。但阿来显然更重视时间意识。扎西达娃则从维护和坚守民族性的角度出发,抓住青藏高原这一孕育藏民族独特神性文化的地域、心理空间,来表现藏民的信仰世界。藏民族的世俗生活也许顺随线性时间之流终将走向现代化、全球化,但和上述特殊地域、心理空间紧密结合的他们的信仰呢?也会走向现代化全球化吗?人们关注藏文化,是关注其独特性,藏区的一切独特人文风貌均源自信仰,源自藏传佛教和本土宗教的世代恩怨。
回到阿来和扎西达娃的文化身份上来,我们发现个人的文化身份其实最终决定于他所处的地域和心理空间,也就是文化空间。空间的开放和封闭的区分其实只是相对的,当一种文化空间取得了某种合理性之后,这种区分便毫无意义。全球化最终也是一个空间概念。扎西达娃对西藏是一种想象,阿来则是另一种想象。能否以一种想象来消解另一种想象呢?或者说能否以一种文化身份来消解另一种文化身份呢?关键看这种文化身份归属的文化空间在当代社会是否取得某种合理性。合理性与否,则又必须引进历史标准,即时间意识。阿来的族际边缘的文化身份,为他赢得时间意识的支持提供了便利条件,历史、文明、人性等具有现代性和普世价值的概念逐渐成为他想象的核心。但不同的声音早就存在,萨缪尔·亨廷顿早就指出,在未来的时间里,所谓普世文明的东西代替不了民族文明,世界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普世文明⑥。笔者以为,民族文化的存在终究是以其独特性为基础的,那种认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初始’,当然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本真’,绝对的民族本质只是一个幻想”⑦之类的过激言论是无益于当代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建设的。民族新生活固然需要关注,但首先应该在该民族的文化空间内进行,很难想象完全脱离藏民族宗教信仰的藏民生活对于藏文学具有什么价值。对民族作家来说,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虽然日益复杂化,但民族文化身份必将长期存在,具有民族特质的文学也将长期存在。值得一提的是,阿来目前已经参加了一个名为“重塑神话”的国际写作计划,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他如何用该计划要求的“现代小说的方式”来想象、描述这位存在于藏民族远古神话中的史诗人物,未尝不是对他处于尴尬境地的族际边缘文化身份的一个检验。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族化的对立矛盾存在是单极化。由于国家、民族的强弱不同,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原则的“全球化”则将导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从而走向严重的单极化。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说:“‘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资本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恰恰是将国际和国内双重的单极化运动融为一体,构成资本全球化的中心。单极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能够更多地从中受益。全球化运动结束了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融合和趋同趋势。”⑧在全球化过程中,在文化冲突方面虽不及经济单极化矛盾表现得那样直接明显,但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地位的确认、文化市场的竞争,如此等等的矛盾,还是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
必须确认,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构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与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样性保证。要想促进文化的全球化,须将世界各个民族的先进的独特的文化,广泛地纳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为世界多元格局中的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问题大讨论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命运令人担忧。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他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从‘世界化’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影响……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交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对于这种文化境遇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依赖于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国家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现。”⑨加利的看法对中国藏文化和藏文学的发展走向很有警示意义:在全球化这个必然走向中忘记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就必然是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单极化。全球化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讨论阿来和扎西达娃的写作是有意义的。扎西达娃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决定了他写作的本土化色彩很强,阿来在截至目前的写作中则有明显的弱化,而且这种弱化显然是有意识的和自觉的,可以说是藏文学开始走向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文化全球化既然是一个既包括一体化又包括本土化的矛盾统一体,那么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存在对藏文学来说都将具有长期的意义。阿来对扎西达娃的“西藏想象”的“消解”代表着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的趋势对民族文化的本土化意识产生的压力和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扎西达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价值守成主义是落后的意识。这里面有文化开放的问题,也有文化安全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民族在接纳外来文化时,不会完全照搬,而是文化利用。局部区域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会是文化同化,而是有可能派生成新的文化。藏传佛教本身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便是一例。总之,阿来与扎西达娃代表的这两种“西藏想象”将会在新世纪藏文学中长期存在,可能相辅相成,最终走向良性循环;也可能激发藏文学的忧患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过度反弹,从而深陷开放和保护之间的二律背反的怪圈,难以自拔。这取决于藏文学在面对全球化时吐故纳新、发荣滋长的能力,更取决于新世纪藏族作家们的集体智慧。
注释:
①[英]斯潘塞·查普曼:《圣城拉萨》,向红笳、凌小菲译,第13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2期。
③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作家通讯》2001年第2期。
④⑤[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68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⑥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⑦黄薇:《当代蒙古族小说概观》“后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第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⑨加利:《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转引自许钧《语言·翻译·文化的多样》,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