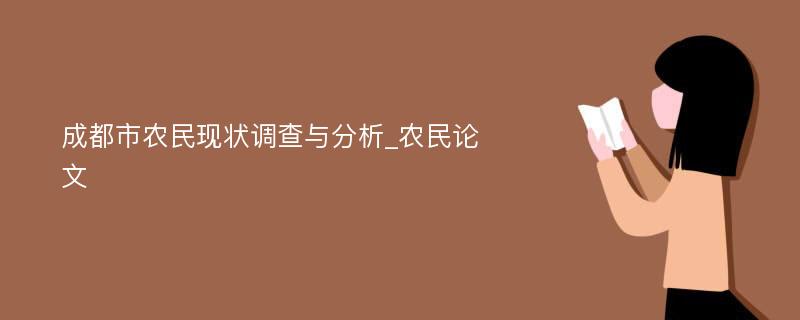
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市论文,农民论文,现状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对在城农民的研究日益深入,更多地关注这一群体对流入地城市体制的冲击(如劳动力就业体制)、群体内部构成与分化、与城市社会的融入与整合等方面。同时,已有的研究多将四川省作为一个劳动力流出大省,而省略了它特别是成都市也是一个进城农民特别是四川省农民的一个重要流入地。正是基于如上分析,我们于2000年7月进行了“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的问卷调查。本文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所获资料,初步描述成都市在城农民这一群体的职业与社会生活现状,并就这一边缘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提出个人观点。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在建筑工地、工厂、餐馆等单位或场所的雇佣就业者(即通常意义的农民工),从事饮食、修理、百货等自营就业者,劳务市场、职业介绍所的求业者,同时三者都必须具有至少半年以上在城市从业的经历,不包括这一群体中已获得相当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因而本分析并不能代表和推及全部在城农民。调查获得有效样本662个。其中:雇佣就业者49.8%,自营就业者23.9%,求业者26.3%;男性75.7%,女性24.3%;18岁以下5.6%,19-45岁80.7%,46岁以上13.8%;小学文化程度25.5%,初中文化程度49.2%,高中文化程度16.4%;流出地为省内的有92.4%。
一、成都市在城农民现状初步分析
(一)在城农民的进城动机、时间、途径与形式
农民进城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历史性转变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在当前也是“三农”问题产生的结果,人多地少、农业经济效益差、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他们在农村从事产业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就个人而言,他们最初进城动机更多的是经济因素如改善住房(64.1%)、子女上学(24.7%)、结婚(16.9%),但已有相当农民关注的是进城所获得的隐形收益如开拓视野(34.0%)、学习技术(29.7%)、寻机跳农门(14.1%)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他们在城时间的延长,这一动机并未因结婚、住房等实际问题的解决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现在最重要的目标仍以经济收入为主:挣钱改善住房和生活(36.9%)、子女读书(20.3%)、结婚(5.2%),而隐形收入如开拓视野(26%)、学习技术(14.3%)、寻机跳农门(3.4%)等变化不是很大。
在我们所调查的在城农民中,1979年前第一次进城的为3.9%,1980-1984年为4.7%,1985-1989年为11.3%,1990-1994年为27.8%,1995年到被调查时为52.3%。农民进城速度有涨无落,由此可见一斑。进城月份最多为9(13.7%)、3(12.3%)和7月(10.7%),其中7-9月(合计32.6%)是高峰,重要原因是年青人多是此时从学校辍学或因升学无望而流入城市的。这与1994年在成都市莲花池的调查相一致[1]。调查对象中,第一次进城之前没有干过农活的有24.4%,干过一两年农活的为20.3%,干过三四年农活的为12.0%,干过五年以上农活的为43.2%,这说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未参加和较少参加农业劳动的身份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farmer)。
进城农民一直被斥之为“盲流”,但我们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进城从业前有56.7%的是先有人帮找到事做或有工作门路才出来的,帮助他们的仍主要是血缘、地缘关系:亲戚38.4%、朋友33.8%、家人7.6%、师傅或师兄弟3.3%,而流出地政府部门(1.1%)和流入地的单位(8.2%)在流动过程中作用并不可夸大。回答未找到工作或门路就出来的有43.3%,但其中有48.7%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如年轻、资金、技术、体力、勤快,18.7%说去的地方有亲戚朋友或本乡本村的熟人,28.0%认为去的地方总会找到事干。因而只有占所有调查对象的12.1%(28.0%×43.3%)才能称得上是盲目的。应该说农民选择是否流动以及流入到何地是经过成本—收益计算的,他们同样是经济理性人。
(二)求业者与劳务市场
被调查的在城农民目前的工作或过去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是通过以下途径找到的:46.9%的通过家人、亲戚朋友、师傅和师兄弟帮助,43.5%的通过劳务市场、职业介绍所等劳动中介组织,35.7%的是自己找到的,4.4%是流入地招工和流出地政府组织的。这一群体的67.4%去劳务市场找过工作,并且到目前为止平均有5.176次工作是通过劳务市场找到的。这反映了劳务市场、职介所等中介组织已成为他们获得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工作的不稳定。
那么,在劳务市场上是否能轻易找到工作?仅有18.8%的回答容易,52.3%的认为不容易,更有14.8%的认为很不容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到劳务市场来找工作?55.6%的是因为自己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10.5%的是因为有亲戚朋友但现在帮不上忙,9.7%的是有亲戚朋友但不想依靠。在找到工作的样本中,仅有0.81次通过市场管理处办理了正式手续,而4.51次是自己在劳务市场外与雇主私下商定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拥有抵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下,求职者就业心切而迁就雇主,签不签合同由雇主决定;并且进入劳务市场内会有各种费用加入场费、登记手续等,而这对他们来说是成本的问题;求职者自身各种证件没有或不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缺少劳务合同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给他们今后的劳务纠纷留下了隐患。
(三)雇佣就业者的职业、劳动时间、收入、合同、与管理人员关系
在被调查群体中,不论他们从事过的所有工作还是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都以建筑工、摊贩为最多,如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为建筑工的有26.4%,摊贩有18.1%。而所有这些工作和农活相比,认为城里的工作轻松或轻松得多的有48.6%,要累一些的或累得多的有26.4%。
被调查的正在被雇佣就业的群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业单位或场所的排列是完全相同的。现在主要分布在:建筑单位39.1%,餐馆和商店18.1%,工厂和小作坊16.4%,学校等文教卫生单位11.7%,旅馆、茶馆、发廊及歌舞厅的3.4%,其他13.8%。有44.4%认为现在单位或雇主所付的劳动报酬和以前差不多,现在要差一些的有20.6%,有27.6%的在流动中收入方面有所提高。这也证实了一点,在城农民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但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而没有地位上升[2]。
这些雇佣就业者每周工作6.65天,每天工作9.76小时,远远超出劳动法所规定的40小时工作制,但他们中一部分认为劳动时间长收入就多,在节假日,当所在单位或场所别的职工都放假时,仍在工作的有67.3%,有时工作的有11.8%;加班但不付工资的占33.9%。除了份内工作外,雇主还经常叫干额外活的有12.8%,有时叫干16.4%;而干额外活的,不给任何报酬的有77%,会给一些的只有2%;一般是每次17.51元,最高为80元。
雇佣就业者所在的单位或场所81.5%的提供住房,37.6%的提供一日三餐,8.5%的提供部分饮食,提供工作服的有33.7%,医疗保险的有11.0%,多少有一点福利的有17.9%,这些福利待遇平均每年折合1584.28元。他们的全部收入,每月200元以下的占3.6%,201-300元的占11.0%,301-400元有15.4%,401-500元的有16.0%,501-600元的有19.0%,601-700元的有10.0%,701-800元的有8.6%,801-900元的有4.6%,901-1000元的有4.8%,1001-1500元的有5.6%,1501元以上的有1.6%。最小值为70元,最大值为6000元,平均值为622.21元,中位数、众数均为600元。在这些被雇佣的在城农民中,有48.1%认为工资报酬与干同样活的城市职工相比“存在差别”,而其中18.3%的认为这种差别还是很大的;认为不存在差别的占37.9%;不知道占14.0%。有56.8%认为报酬差别存在应该,原因是对方是城里人、从学校出来的、有关系后台、工龄技术效率不同;而回答不应该的有43.2%,原因是人人平等、都是干一样的活、自己干得多等。应该看到,在回答“应该”者中相当部分是认识到同工不同酬是户口等不合理的制度性原因造成的。
这些雇佣就业者和单位都签过劳动合同的只占15.6%,都没有签的竟有70.4%。而签过合同的人认为,合同还算公平的有67.3%,不公平的有18.3%,14.4%的认为不一定。所签合同是否有得到遵守是一个关键。79.2%认为对方还是基本都遵守了,有5.8%的认为基本都不遵守,不一定的有13.0%。在回答有对方不遵守的30个样本中,碰到1次的有13人,碰到2次的有8人;当碰到对方违背劳动合同时,39.3%的人会暗地里反抗如怠工,21.4%的据理力争,21.4%的请求政府有关部门帮助,10.7%的请求同伴和朋友帮助,而7.1%的忍气吞声。
正在或曾经被雇佣的在城农民中,有18.1%曾遭遇过管理人员或老板殴打,84.5%的遭遇过辱骂,有13.9%遭遇过不正当处罚,8.7%打骂和不正当处罚都遭遇过。这一群体中的37.2%(219人)有被扣工资经历,被扣工资1次的有94人,2次的有49人,3次的29人,6次的11人;损失100元以下的52人,101-300元51人,301-500元41人,501-700元16人,701-1000元28人,1001-1500元7人,1501-2000元11人,2001-10000元(最多)12人,平均728.32元。这一群体中的8.7%被无理解雇过,有36人经历过1次,2次的有8人,5、6次的各有3人。解雇时,没有任何借口的占52.5%,有借口47.5%。而借口不外乎效益不行雇不起、活不多之类的,也有直接在工作中挑刺的如顾客都丢了、活做得太差等。
这一群体的77.4%认为雇佣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老板平常对他们还友好,6.8%的认为对方瞧不起他们;而他们中的8.3%认为对方很好,34.8%认为较好,40.0%说不好不坏,13.5%说较坏,3.5%说很坏。只有44.3%遇到过能真正帮助他们的管理人员和老板,其中:遇到1个能帮助他们的有30个样本,2个的有68个样本,3个的有17个样本。这样的人在所有遇到的管理人员及老板中,3.4%的人说有很多,14.7%的人说比较多,13.2%的说一般,28.3%的说少,40.4%的说很少。总的来说,17%认为老板和管理人员坏及较坏,而40.4%认为能真正帮助他们的老板很少,这说明他们对管理人员和老板的期望并不高,并不奢望从对方得到帮助。
(四)自营就业者的资金来源、手续、与城市管理人员关系、收入、将来计划
在自营就业者中,他们的本钱平均为1503.46元,中位为500元,众数为200元;它们全是自己积攒的占73.2%,全是借的占14.0%。借钱的主要对象是:亲戚69.0%,朋友52.4%,同乡9.5%,同事2.4%,以前的老板或管理人员2.4%,信用社或银行2.4%。
在自营就业者中,32.1%的办全了规定的各种手续,8.8%的还未办完,而一项也没有办的有59.1%。至于没办的原因,31.8%认为自己没有资格,10.3%的认为有资格但费用太高,9.3%的说想办但不清楚如何办,而48.6%的认为能不办就不办。
在所调查的自营就业者中,仅有1.9%的认为所遇到的城管、市管人员的态度很好,28.2%的认为较好,12.2%认为是冷冰冰的,57.7%认为较凶乃至很凶。11人曾被管理人员打过;43人被骂过;77人曾被罚过款,罚款1次的有11人,2次的有14人,3次的11人,10次的有6人;64人曾被没收过东西,1次的有17人,2次的有15人,3次的13人,5次的5人。就2000年上半年的情况而言,他们被罚款和没收的钱物,平均有343.2元,最多的为5000元。
这些自营就业者的每月营业额平均1844.5元,最低的有150元,最多的有30000元。把摊位费、税收和各种杂费加在一起,每个月要交各种各样的管理费平均203.36元,最多的为4000元。就最近一年的情况来看,除去各种税费外,每月可给他们带来利润平均有692.13元,最少的有12元,多的有7000元。平均而言,自营就业者的收入要高于雇佣就业者,就正是部分雇佣就业者若有机会就要流入到自营就业者中的原因,尽管自营就业会更累、会与城市执法人员及各种城市居民打交道。
(五)在城农民的衣食住行和闲暇生活
这一群体对城市居民穿着打扮看不惯或不顺眼的,由刚进城时的35.1%下降到现在的20.1%。有51.4%的表示他们现在的衣着打扮已经不同于在农村时了。在最近的一年,有78.35%的买过衣服,买过衣服者平均4.72件,众数为2件;平均花费245.85元,最多的为2000元。最贵的衣服平均86.44元,众数为50元,最多的为1000元。77.2%的在城农民在化妆和洗发等用品上花了钱,每月平均15.93元,众数为10元。
这一群体进城后与未进城前在饮食方面相比,22.8%的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65.9%是变得越来越接近城里人的习惯;对不太新鲜或过期但还未完全变坏的食品,还要吃的由27.6%降到18.3%,而不吃的由35.4%升到58.8%。他们一日三餐35.3%基本都是自己做,29.0%基本由雇人单位来解决。9.3%的表示每周进一次餐馆,16.8%的每月两三次,8.4%的每月不到一次,3.6%的两三个月一次,8.2%的半年也难进一次,16.5%的一年也难进一次,更有37.2%的从未去过。去餐馆频率与就业类型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群体中,50.5%的喝酒者的每月酒钱平均为40.26元,众数为20元,中位数为30元;46.6%的抽烟者,烟钱平均每月57.15元,众数为30元,中位数为50元。他们用在饮食方面的费用平均为174.24元,最少为0元,最多为1000元,众数为200元,中位数为180元。
在城农民的住宿与就业类型(雇佣就业和自营就业)有相关关系:82.98%雇佣就业者的住宿是由雇人单位或老板安排的;求业者中32.4%是住在旅店或露宿街头,17.4%的是自己单独租房,13.3%的在亲戚朋友家借宿;而自营就业者的50%是单独租房。他们的住处在市郊的有22.4%,市区与市郊中间地带的有57.7%,市区的有17.8%。住房属于棚户房的有20.3%。22.3%有单独的厨房,30.2%的房内有卫生间。在需要为住房付钱的在城农民中,每月花在住房上的钱平均110.3元。50元以下的20.9%,50-100元的45.2%,101-150元的19.4%,最多的为600元。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近半年来每月在衣食住行娱乐方面平均开支为305.17元,中位数和众数均为300元,最多的为3000元,最少的为30元。除了他和在城里的家人的开支外,最近一年还有以下开支:平均医药129.94元,最多为16000元;平均子女教育、学习费用432.41元,最多为12000元;平均接济亲戚朋友76.97元,最多为6000元。以上最小值、中位数和众数均为0元。
74.3%的每月收入除去各种支出有剩余,平均剩余287.11元,最大值为3000元,最小值为20元,中位数为225元,众数为200元;21.0%的收支平衡;还有4.7%的入不敷出,大约每月差123.74元,最大值为300元,中位数和众数100元。当入不敷出时,61.3%的借钱,20.4%的通过在其他地方打工来弥补,13.6%的动用原来的积蓄。
这一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除家人外,来往最多最密切的是:工作中的伙伴的51.9%,朋友占51.3%,同乡占37.5%,亲戚占26.5%,老板和管理人员5.9%,邻居5.4%。当工作或生活中碰到困难时,除了家人外,常求助的对象:朋友占50.6%,工作中的伙伴28.3%,亲戚26.7%,同乡24.7%,老板和管理人员8.7%,邻居2.1%。这反映出亲缘、地缘关系被带入城市,且在他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流入城市后所建立的业缘关系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六)在城农民对城市居民、管理人员的印象
农民进城后肯定会与周围的普通城市居民打交道。那么,他们眼中城里人如何?33.8%的认为周围的城里人大多数瞧不起他们,47.7%的认为少数人是这样,只有11.3%的认为城里人不会这样。当他们穿着打扮像农民乘车或走进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时,有22.1%常感觉到这些地方的服务人员不够礼貌或瞧不起他们,40.7%的有时有这样的感觉,而没有这样的感觉占36.0%。43.7%的喜欢与常打交道的城里人来往,37.1%的不喜欢,还有19.2%表示要看是哪些城里人。既然他们对城里人褒贬对半,那么他们和周围的城里人交过朋友吗?50.4%的交过,平均交过7.81个,除了因工作结识的(同事、老板和管理人员、顾客、银行职工等)、年龄相仿的、兴趣性格相同的(爱玩的、脾气好的、牌友等)、同一收入阶层的以外,还有街道办事处、法律顾问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中已有人努力融入城市这个社会。
作为城市政府部门直接象征的城市治安及其他管理人员在他们印象中如何,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我们所调查的在城农民中40.4%与管理人员曾经有过直接接触;其中6.2%的认为这些管理人员很好,35.9%的认为较好,30.6%的认为一般,18.1%的认为较坏,更有9.3%认为很坏。有35.2%的曾经遭遇过这些管理人员的不正当处罚和制造的麻烦。
所调查的在城农民,自进城以来,平均被打过0.26次,辱骂过3.76次,受过其他欺侮0.24次。打骂欺侮39.0%来自街上流氓,32.2%是公共场所碰到的陌生人,25.3%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服务人员,21.3%是住地周围的居民。在碰到各种不幸事后,他们忍气吞声的有46.9%,29%的向110报警,14.5%的当即进行反抗,14.0%的约朋友去评理,6.4%的邀朋友去报复,3.8%的向法院和有关部门投诉,2.4%的私下暗地里自己报复,其他2.9%。在向110、法院或有关部门投诉告状的189个样本中,认为有公正的结果占61.4%,没有公正结果的有22.8%,不一定的有15.9%。在所有调查对象中,55.7%的知道用劳动法和其他有关法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而36.0%表示不知道,还有8.3%连劳动法也没有听说过;有29.3%表示完全相信执法人员和机关能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33.7%的有点相信,25.9%的不相信,11.1%的认为说不清楚。
(七)在城农民与农村
被调查的在城农民中,有8.5%已退出所有土地,3.5%已退出部分土地,而83.1%的还承包着土地。而在后两者中,农忙时还回家照料种地的有57.9%,将土地全部或大部分让亲戚照料或代种的为29.0%,用钱雇人种地的为2.4%,将土地全部或部分转包给他人的为9.7%,让土地荒着的有0.9%。至于转包他人或雇人耕种的条件是,只要将土地交给对方就可以的有45.7%,自己还得负担农业税和按亩征收的其他费用的有48.4%。有学者认为,土地既是在城农民的退路即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是他们彻底融入城市的障碍。我们同意前一点,而认为后者有点夸大。因为,当城市工作稳定,61.1%的在城农民愿意退出承包土地,不愿意的有38.9%。
作为出生在农村的农民,有34.5%很留恋农村,48.0%的有些留恋,14.3%的不留恋,3.2%的说不清。但当他们在城里的工作稳定或生意顺利时,33.8%的很愿意一直留在城里并争取转变为城里人,36.7%的愿意,8.4%的拿不定主意,而不愿意只占21.2%。我们在问卷中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现在让您做出选择,您可以自由地留在城市并作为城市居民,也可自由地回到农村,您最愿意做哪种选择”。56.3%的留在城市,34.4%的愿意回到农村,9.3%的拿不定主意。两个不同方式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存在差异,但都可以说明,相当多数有留在城里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
二、初步结论与讨论
在一些城市居民乃至政府官员眼中,农民进城产生了诸如加剧基础设施紧张、挤占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违法经营、破坏城市环境卫生、计划外生育等问题。但通过学术界已有的调查和我们这次成都调查,都可以发现有些指责并不成立,如在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处于不同的就业市场,前者集中于完全竞争的非正式就业部门而后者是在对外(在城农民)垄断对内(城市居民)竞争的正式就业部门,又如我们所调查的只有9.1%的坐公共汽车而谈不上造成城市公共交通的紧张。当然有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从根源上说这是否是在城农民自身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在我国,“农民”指的不仅是一种职业(farmer),更多的是一种由户籍制度及其附着于其上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行政力量所赋予的刚性的外在强制力量的身份(peasant),这一社会身份是会被下一代所继承的且具有先赋性的身份。从职业方面来讲,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从业人员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的过程;从社会身份来讲,它是一个先赋性的向自致性的转移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3]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制度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造成他们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4],使得他们转换社会身份、融入城市从而体验城市文明相当艰难。
一些城市从保护本城市居民的就业和本地稳定出发,限制进城农民进入正式就业部门(如限制准入行业、进城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和不时进行的“清退”工作以“腾笼换鸟”)、提高他们的进入成本(如征收管理费用和其他附加条件)。它不但使进城农民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而且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受损,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这样,在城农民只有正式就业部门中脏苦累差及危险之类的城市居民所不屑的工作和非正式就业部门(主要是自营就业者)可以选择,并且非正式就业部门是城市正式就业部门对他们的封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性劳动就业部门。而就是这非正式就业部门也常常是执法部门在卫生检查、治安管理等借口下所驱赶和取缔的对象,虽然他们也明白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对在城农民的社会歧视不仅来自就业方面,还有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生活待遇方面的歧视、来自城市政府部门的直接象征的执法人员的歧视、来自公共场所管理人员和城市普通市民的歧视,虽然如我们所调查到的这些歧视并不占有绝对比例,但其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往往容易被视为整个城市部门和市民的一般态度。这些社会歧视的根源在于存在地位差别较大、强弱悬殊的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并且这些社会群体缺乏沟通和理解的渠道[5]、[6]。
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顽固存在和城市社会对在城农民的歧视,使得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与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处于边际人的地位,从而与城市社会处于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整合状态: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认同性整合畸形[7],从而发生很多碰撞、摩擦、冲突等。也正是在此环境下,在城农民才利用所谓“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进行产业活动和日常交往,它可能有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人的基本归属的原因,但更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化结构的安排。
随着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下降、乡村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能力的下降,不论是整个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增收,农民走入城市从事产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在也正是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8]困境的时候。从80年代中期实施的“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蓝皮户口”、“开放小城镇户口”等户口政策的改革的确满足了一些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居住城镇的愿望,但已有研究揭示出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大城市,小城镇在解决农民进城中的作用不能过高估计,因而在城市化方向上应走多元城市化道路。“决定农民的去处空间,既不是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参与转移农民的个人愿望,而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所造成的产业布局,离开这一点谈农民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的空间(地域)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9]实际上,“小城镇主义”的现实含义已经从侧重于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变为侧重于阻止农民进入大中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