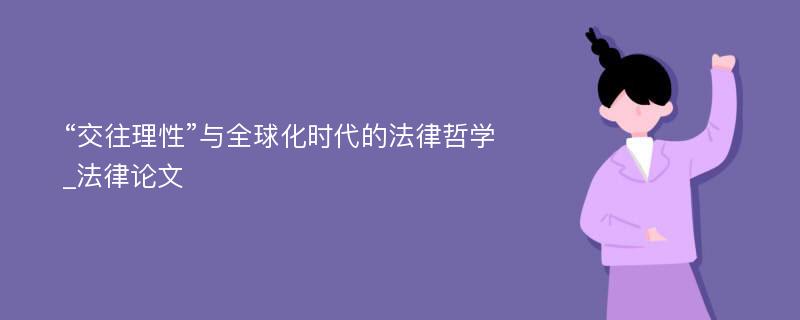
“沟通理性”与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哲学——凡#183;豪埃克《作为沟通的法律》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埃克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6)01—0152—09
“如果法律是理性的,理性又被理解为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那么,法律就是一种沟通,而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不同规范的集合”。[1](P10)
——[比]凡·豪埃克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人们用各种称谓反映这一变迁,诸如风险社会、全球化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主义、对话时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等,不一而足。一系列曾被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构的现代性的理念和制度架构遭到质疑,确定性终结了,似乎“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254) 我们被置于一个似乎没有归依的世界。在这场延续至今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中,哈贝马斯以“沟通理性”为关键词,建构了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重构,成为站在现代性立场上进行论辩的领军人物。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比利时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法理学教授、欧洲法律理论研究院联合主任凡·豪埃克教授(Mark.Van Hoecke,1949—)运用哈氏理论研究了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法律问题,其《作为沟通的法律》(Law as Communication)一书则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该书中,豪埃克教授深刻地洞见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变迁对包括法律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相应的“范式转换”的必要性。豪埃克教授指出:
“法律的创制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单向的,即从‘民选议会的立法——司法适用’的过程。法律和社会复杂性的显著加剧使得这一理论如此的过时。法官作用的加强,特别是宪法法院和超国家法院的出现,相对于政府和行政机关优势地位的议会作用的减弱,绝不仅仅是‘错误的发展’,而必须得以正当化以使现实的发展适合于传统的理论。”[1](P10)
在“价值多元化”和“绝对真理”式微的背景下,为了建构一种阐释现实的理论框架,他主张用“沟通理性”① 代替“实践理性”作为重构法律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该书的导言中,豪埃克教授对其沟通视角的法理学可能面临的批评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理论建构具有主观性,它通常是对现实的一种合理解释。“它们从某一具体的视角建构现实,法律现实进而变成了一种‘规范性体系’、‘社会学互动’、‘正义观’的实践、对‘正确答案’的探求、‘语言’游戏或心理现象等等”。对法学研究而言,“我们不可能同时从所有可能的视角来洞见法律”。[1](P5) 正是出于这一确信,作者试图从沟通的视角理解法律;这一视角仅仅是阅读、描写传统的法理学问题的一种方法。以此看来,如同理论是对现实的一种阐释框架一样,法律也为人类行为、进而为人类沟通提供了一种框架。而且,
“法律在本质上也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契约双方的沟通,审讯时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1](P7)
如果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是哈贝马斯以社会理论家的身份对其“沟通行为理论”在法哲学领域的逻辑展开,从而使得其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成为其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作为沟通的法律》则是豪埃克教授以法律家的身份灵活运用“沟通行为理论”解决法律问题的创造性的成果。毫无疑义,豪埃克教授的沟通法理学最主要的理论渊源即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但正如於兴中教授所指出的,“它受到沟通行为理论、心理学、语言学、法的自创生理论(autopoietic theories of law)② 的启发, 但它不仅仅是哈贝马斯对法理学的理论重构的应用”。[3]
本文将对该书的主要观点进行必要的梳理,并进行一定的归纳和展开。
一、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什么”作为法学的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同时,作为萦绕在法律人脑际中的“形而上情结”也挥之不去。西方主要法学派分别从国家与社会、立法与司法、应然与实然等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各异的回答,[4](P5—6) 豪埃克教授则从沟通的视角给出了一种新的答案。
他敏锐地看到将法律等同于国家法的传统观点在后民族国家时代面临的挑战。在后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乃至国内统治的绝对权威已然受到挑战。“从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将‘法律’与‘国家法’联系起来的观点将很难把国际法或非官方的‘亚国家’法看作(完整的)法律”。故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关于法律的概念,“当每个人都称‘国际法’为法的情况下,法的理论定义应该包括它”。“法的理论定义应该符合我们对法的一般理解,它必须符合实践的发展,并能提供清晰的、连贯的和理性的观点”。[1](P15) 而要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必须结合法律的特征来认识法律。
豪埃克教授主张从人类行为、人类互动与法律、作为一组规范的法律、作为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的法律、法律与国家、法律与强制、法律的自治、法律制度的闭合性与综合性、法律与文化以及法律与正义等九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的几个(可能的)③ 特征。
豪埃克教授认为,法律最突出的特征即是它不是对人们之间的行为的描述,而是对人们之间的行为的一种调整。对个人而言,法律与其说是他能影响的某种东西,而毋宁说是一种他必须考虑的客观现象,之所以如此是源于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对秩序的渴求。法律为我们远离无序提供了可能,法律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种法律提供了社会中人类行为的一种框架”,[1](P18) 为人类的互动和交往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是一种典型的行为规范,它告诉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该如何行为。但是,不同于奥斯丁的“主权者命令说”、凯尔森的“基本规范说”等法律理论,豪埃克教授反对把法律看作规则发出者(norm-sender)或规则接受者(norm-receiver)单向意志的反映。在他看来,法律毋宁是两者意志的互动与沟通。他运用法律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法学关于“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的区分等理论对此进行了阐释。“出自于某人的一个命令或规则,如果其权威性不被人接受并加以运用,该命令或规则只是死的文字而已”。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司法并不总是从属于立法。“如果过去的法律供给者(law-giver)的权威在预先决定(最充分地解释)某一案件背景下规则的具体内容时被否定,行动中的法的具体形态——例如实际有效的法——将取决于国民和(或)官员和(或)法官是否接受该规则,而不是法律供给者的意志”。[1](P20)
在豪埃克教授看来, 法律不仅是一组规范,而且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体系(institutionalized normative system)。这种制度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形式上的制度化(formal institutionalisation)、 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化(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ation)和职业的制度化(profess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形式上的制度化包括结构和程序两个方面,涉及立法和司法两大环节。 法律规范有着不同的类型(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从而使其本身体系化,辅之以法律的职业化和程序化,使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专业机关得以发展。法律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化涉及法律制度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是指法律制度在社会中被一般的接受,并被实施;它是形式上的制度化的进一步发展。职业的制度化不是所有法律体系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但却是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一般而言,一个充分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法律职业包括三个方面:职业化的法律制定者(如国会议员)、职业化的法律适用者(如法官)和职业化的法律学说(如法律院校)等。[1](P21—27)
豪埃克教授主张放弃那种将法律等同于国家法的传统观点。他说:“从理论上看,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关于国际法及其他同类法律的讨论已经使很多法律人确信我们应当对法律的概念采取一种更多元主义的进路。”[1](P27) 接着,他从关于欧盟、国际法、国内和国际体育组织、有组织的少数民族、教会等的规则的发展对传统的主权观和法律观的冲击的角度论证了重构法律观的必要性。豪埃克教授的观点与很多法律家不谋而合。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这两者加在一起,正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力量的单位”。[5](P345)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间国际组织(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间国际组织(non-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正在创造和发展着不同于国家法和传统国际法的新的秩序和规则,从而对国家权威构成强有力的挑战。[6](P36) 那种仅与民族国家时代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正如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指出的:“只有摆脱所有的法律必须来自某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如主权)的观念,才有可能采取一种更宽泛、更开放的法律观。一种新的进路是体系中心的法律观,即强调法律的本质是一种规范体系,而不是某类特定的或排他性的权力关系。”[7](P8) 豪埃克教授认为,国家法和国际法等的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制度化、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化,而毋宁在于职业的制度化。因此, “如果我们把‘共同体’理解为相同的社会关系——穆尔(Moore)和格里菲斯(Griffiths)称之为‘半自治的领域’——,那么,我们可以把‘法律’定义为‘某一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体系’”。[1](P32) 这里的共同体应作广义的理解,它包括文化共同体、休闲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等,但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化规范体系在法律制度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哈特曾指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法律都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它的存在意味着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性。”[8](P7) 韦伯也把强制性作为法律的要素,他通过将强制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即身体的强制、心理的强制、国家强制和非国家的强制建立了他的“非国家的”法律观。[9](P345以下) 豪埃克教授则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当我们定义法律时,强调制裁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制裁对每一种法律制度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公民履行守法的道德义务并非就是出于对制裁的惧怕。现实中,被强迫接受只是和完全接受、有条件的接受相并列的情况之一,而且在很多时候公民守法是不需要强制的。“法律的效力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来源于强制……有效的制裁和现实的强制对法律实施的作用是有限的,大多数规则在大部分案件中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被自发地遵守”。[1](P35—36)
法律的自治性是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10](P6) 昂格尔曾指出,法律的自治包括内容、机构、方法和职业四个方面的自治。[11](P50) 豪埃克教授则以其沟通法理学为视角,运用法的“自创生理论”等对法律的自治性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尽管法律是嵌入社会并受其制约的,但现代法律制度事实上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系统。”[1](P37) 针对法律的自治性与法律的受制性的悖论,[12] 豪埃克教授主张要区分“形式上的自治”和“实质上的自治”与“作为系统”的自治和决定规则内容时的自治等情况。传统的法律自治性理论囿于法律规范的等级体系和立法至上的民主制度强调下位法对上位法、司法对立法的从属性,豪埃克教授以沟通法理学为基点,提出法的“循环”(circularity)理论。④ 在他看来,下位法并不仅仅决定于上位法,它也决定着上位法的运行;司法从属于立法也受到了挑战。现在,“欧洲人权法院、欧洲法院以及大多数国家的行政与宪法法院有权将其法律观点以及对国际条约和国家宪法的解释强加于立法机关”。[1](P38) 这种下位法与上位法、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循环”与沟通使法律制度的运行得以合法化(legitimation)。接着,豪埃克教授运用托依布纳提出的法的自创生理论对“形式上的自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自创生理论认为,法律的自治指那种法律在在其中生产自己的方式的循环性,并非指它对环境的因果独立,并不排除法律、经济和政治相互依靠的可能性;“实际上,它假定它们相互依靠到相当大的程度,其条件是,这被看成一个循环的、因果的过程怎样受外部影响的问题”。法律的自治是运行闭合(operative closure)与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ness)的统一:“在认知开放中,法律以多样性的方法与社会意义相关联,也与社会构成物和社会价值相关联。然而,在一个自我关联地闭合的法律系统中,这些进入当前社会价值的突袭在它的法律形式里呈现出规范化的外观。它们的规范性内容通过反求于这些价值的构成性规范从法律自身中产生。”[13](P47—48) 豪埃克教授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法律制度有其自治的运行逻辑,但为了调整社会关系,从社会中选择和吸纳社会事实、价值和规范对于一个法律制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法律制度对外部世界存在一种认知开放,但它们又保持自治,因为它们是一种运行闭合的系统——外部信息根据法律制度内部的逻辑被选择和采用。“实质上的自治”涉及到自治的内容、种类和程度等。豪埃克教授认为法律制度与外部世界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不断沟通的过程,而非单向的信息流动。这种沟通似乎在法院——在那里,案件的具体事实、具体环境有时也影响社会的观点和其他因素——对法律的解释中占最突出的地位,它影响着案件的判决;这种沟通是如此强烈,这种认知开放是如此普遍,以致于法律制度的“自我生成”(self-production)必然是脆弱的。豪埃克教授还创造性地区分了“作为系统”的自治和决定规则内容时的自治。在他看来,两者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即法律制度作为一个系统越发展,自治性程度越高,则决定规则内容时的自治程度越低。
二、法律规则与法律体系
以拉茨将法律规则看作人类行动的理由的理论(norm as reasons for human action)⑤ 为起点, 豪埃克教授认为厘清规则发出者与规则接受者的关系对于理解法律规则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豪埃克教授认为,在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中,不了解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的沟通过程和形式,信息几乎不可能被正确地理解。对法律规则的理解也是如此。然而,当下法律理论则过于强调规则发出者或规则接受者中的一方,而忽视了两者的互动与沟通。以奥斯丁理论为代表的法律命令说将法律等同于主权者的命令,在解释规则时,过于强调规则发出者的意志,而忽视了规则的字面含义和法律实践中规则接受者的能动性。现实主义运动则将整个法律化约为规则接受者的观点。其中,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把法官作为规则接受的主体,以海格斯多姆(Hagerstrom)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则把国民作为规则接受的主体。在豪埃克教授看来,现实主义的进路抽出了法律规则的规范性的内容,完全否弃了规则发出者的权威,同法律命令说一样,它也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规则。因此,我们还是得仰赖沟通的进路。在这一进路中,规则发出者和规则接受者之间的沟通共同决定着规则的含义。在分析、解释和适用规则时,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
豪埃克教授还就规则发出和规则接受的主体做了富有见地的探讨。关于规则发出者,豪埃克教授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形式上的立法者应被视为‘规则发出者’,准确地说是因为它被法律制度本身如此限定,并且,作为一个规则,立法权的如此安排也被一般的接受。”[1](P83) 但在一些情况下,辨认出规则发出者会遇到难题。比如,国际法和原始法中的习惯法、欧洲大陆过去几十年来作为规则的非典型渊源(atypical origin)的“不成文的一般法律原则”(unwritten general legal principles)等,其规则发出者很难说是立法者或法官,事实上是“传统”或“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我们还是要区分形式上的立法者和实质上的立法者:形式上的立法者完全由法律制度的第二性规则(the secondary rules)⑥ 决定和限定,实质上的立法者则取决于授予这些立法权的第二性规则被共同体一般接受的程度。形式上的立法者和实质上的立法者可能是重合的,如议会在讨论技术性很强的立法时,对该领域很熟悉的议员比对此一无所知的议员在立法中显然占据更大的优势地位,他们是实质上的立法者。此时,我们确定“立法者的意图”(will of the legislator)还不会面临太多的困难。但是,在一些场合,形式上的立法者和实质上的立法者是分离的。比如,在比利时皇室法令(Royal Decrees)的颁布中,国王作为第二性规则确定的形式上的立法者根本没看过法令的内容。此时,我们确定立法者的意图时就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一)承认形式上的立法者根本没有实际的意图,因而法令没有意义;或者(二)考虑实质上的立法者的意图,但实质上的立法者的权力却不能在第二性规则中找到依据;或者(三)断定形式上的立法者的意图只是一个虚构,似乎规则适用者的意图就是立法者的意图。在豪埃克教授看来,解决此难题的一个出路是把实质上的立法者看作是形式上的立法者的隐含的代表。他同时认为,每一条法令的颁布事实上都是政治辩论的结果,是立法者与立法者之外的行政机关、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司法机关、技术专家沟通的结果,乃至是通过这些媒介与整个社会沟通的结果。“只有参照这一预备的过程,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文本。但是,对这一沟通的确切范围的理解也只有结合形式上的立法者颁布的最终文本才正确”。[1](P85) 关于规则接受者,豪埃克教授认为不应把它单独地确认为法官。把法官当作唯一的规则接受者的理论可能更适合刑法,它通常包含着三个预设:国民不知道规则的内容;违法时,只有法官才有权适用制裁;抽象的规则是指向法官的,法官将其具体化并在审判中向一个或多个当事人发布命令。豪埃克教授认为,第一个预设并不成立,因为法官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法律,他们只是拥有更易查找法律的职业优势而已。后两个预设是一种法律命令说的观点,即认为法律是立法者给法官、进而给国民的命令;该观点把所有的规则化约为必须由法官适用的命令性规则,从而可能将实践中公民未经法官裁决而自觉遵守法律的大多数情形理解为没有遵守法律,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豪埃克教授关于从规则发出者与规则接受者的关系理解法律规则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当下日益复杂的立法和司法过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在谈到法律体系(legal system)⑦ 时,豪埃克教授将哈特和凯尔森分别将“承认规则”和“基本规范”视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点的进路称为“封闭规则的进路”(closing rule approach)。这一进路有不同的渊源:(一)对法律体系合法性的实证主义解释;(二)从规范性的观点和科学性的观点识别法律体系的有效性;(三)法律体系的统一;(四)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五)规则与事实的分离。在他看来,上述几个方面都有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哈特还是凯尔森,为了把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有效的体系时都不得不依赖于法律体系的社会效应”,而“如果法律体系最终依赖于对其进行识别的社会效应,那么这些规范性的体系只能建立在社会接受这一事实之上”。“一旦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即法律体系的第二性规则,被大体上接受,法律体系就是可以确认的、就是有效的,这不仅独立于行为的第一性规则的有效性,也独立于任何‘基本规范’和‘承认规则’”。[1](P101—102) 因此,我们对法律体系的正确认识还必须诉诸于沟通进路。
豪埃克教授认为,法律体系只能是弱势意义上的“系统”。强势意义上的“系统”一般是封闭的、完整的、融贯的,通常能以此决定某一实物是否是其要素。弱势意义上的“系统”只要求存在一个结构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法律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豪埃克教授看来,法律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变迁的机理就是哈特所谓的“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一般认为,在发达的法律制度中,法律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等级体系。凯尔森把法律体系看作是纯粹线形的(linear)、等级化的体系,卢曼(luhmann)则认为法律是无序的。柯却夫(Kerchove)和欧斯特(Ost)批判了这两种相对的进路,他们认为凯尔森的进路大体上符合19世纪的公法,卢曼的观点只适合现代国际公法。[14](P68) 豪埃克教授则认为, 如果我们同意任何法律权威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或部分取决于守法者的接受和认可,那么,我们就只能依靠法的循环理论才能解释这一现象。“没有法律制度是完全‘等级的’或‘无序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循环的。……最低限度的循环可以被视为任何法律制度的典型特征,这种循环应被理解为与法律的生成和合法化相关的某一法律制度内个人与组织间的互依和互动”。[1](P113) 柯却夫和欧斯特曾用“游戏”(game)来指称“循环”。豪埃克教授认为,“游戏”的景象正确地指出了法律制度和法律主体之间的互依和互动。但是,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游戏”只涉及一个封闭的规范体系,只提供一个策略行为的框架,游戏者只能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而不能改变它。法律不仅如此,还创造沟通行为的重要空间。因此,法律的这种“循环”只能是“沟通”的。通过沟通行为,不同的人和组织互动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共同的、连续的和多方位的意义循环程序。正是在这种共同的、连续的意义循环中,法律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社会的理想模式而起作用,从而部分地创造了法律系统的结构。关于法律系统的构件(the building blocks), 豪埃克教授给出了一个综合而又不太明确的回答:当我们讨论法律体系的实体结构时,我们可以说是其第一性规则;当我们讨论法律机理的动态结构时,我们可以说是其第二性规则;当我们分析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法律事实的、纯粹的法律的系统机能时,我们可以强调其自创生意义上的“沟通”等等;我们应当把它们综合起来。关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coherence),豪埃克教授认为协调的首要含义是指法律规则的一致(consistency)和不矛盾。协调还涉及法律体系的要素间的结构联系和内部粘合力(cohesion)以及与外部世界即社会的粘合力。豪埃克教授还认为法律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国占基础地位的民主观念。因此,在“法律体系的概念”一章的最后部分,豪埃克教授还专门讨论了民主问题。他分别了讨论了当下流行的两种民主模式,即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模式,并赞同哈贝马斯提出将“商议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作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的理论范式。[15]
综而言之,豪埃克教授认为法律规则以及作为法律规则集合的法律体系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运行闭合与认知开放的统一,这种开放体现在规则发出者与规则接受者、法律体系与社会等之间的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中,正是这种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使得法律规则和法律体系在保持稳定、法律在保持自治的同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作为法律体系的民主基础的政治理念也应是“商议政治”。
三、沟通与合法化
自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以来,“合法性”一词一直是人们考察政治权威实然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韦伯认为,真正的统治是一种“权力——服从”关系,它不是建立在暴力强迫之上的,必须“唤起并维持对统治的合法性的信仰”。[9](P238—239) 在《作为沟通的法律》一书中,豪埃克教授使用了“合法化”(legitimation)一词,将其与法律连用,形成“法律的合法化”(legitimation of law)这一命题。事实上,单从字面上讲, 中文的“合法化”与“合法性”并无太大的区别,其细微区别在于前者可以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即当权者为了追求合法性的一种努力,后者则是静态的。在该书中,法律的合法化是指法律秩序符合人们某种实体或程序的价值准则以及其他非强制的原因而为人们所认可或赞同进而被接受或服从。
豪埃克教授首先指出,法律的合法化对法律制度而言非常重要。人们对教堂和体育规则等不满意时可以随时退出,但是人们对法律制度不满意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国度。然而,人们又不能自由地离开一个国家。因此,法律制度的这种较强的影响及其垄断的地位决定了相对非法律制度而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合法化有着更迫切的要求。法律的合法化有弱势意义和强势意义之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只能是弱势意义上的合法化,即我们接受该法律制度,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需要官方的权威保证契约的履行等等,此种意义上的合法化不要求法律制度在道德上是良善的。强势意义上的合法化涉及法律制度的部分,我们对法律制度的部分进行道德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评价。
在讨论合法化的种类时,豪埃克教授在讨论了常见的形式上的合法化和实质上的合法化后,提出了合法化的第三种类型,即沟通的合法化(communicative legitimation)。他认为形式上的合法化是现代法合法化的最主要的类型。形式上的合法化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进程:16、17世纪时,以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等为代表,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来自于是否服务于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18世纪时,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认为政治权力和法律的合法化来自于其是否经过公民的同意。在现代社会,以卢曼为代表,强调政治权力和法律的合法化来自于正当的程序。卢曼的“通过程序的合法化”理论认为:“至少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种统治才能说是合法的,(一)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二)在规范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这样,合法性信念就退缩成为一种正当性信念,满足于诉诸作出一种决定的正当程序。”[16](P127—128) 在豪埃克教授看来,卢曼的这一学说适应了现代社会复杂化和价值多元化的需要,但是,它只是一种弱势意义上的合法化:同富勒的八个程序性原则一样,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实质合法化的诉求。实质上的合法化就是试图为法律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提供一个评判标准。过去人们主要依据各种各样的自然法学说,现在人们主要依靠人权理论为此提供依据。与实质上的合法化相关的是德沃金提出的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说”。与波斯纳不同,德沃金认为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17](P247以下) 豪埃克教授基本赞同此观点,但是他也认为:“‘找到’唯一正确答案的方式不能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式的超级法官所独具,而只需通过沟通式的论辩即可获得。”[1](P197) 这就为他提出沟通的合法化埋下了伏笔。
在豪埃克教授看来,沟通的合法化是一种社会建构,在这里,所有公民都应该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沟通过程中,这种合法化的获得是以承认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是互为条件的联合体为前提的。具体言之:
第一,要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第二,要在纯粹强调程序和民主系谱的形式主义进路(实证主义)与排他性地强调法律的道德可接受性的实质主义进路(自然法)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在两个极端对立面之间进行平衡,我们必须把这些对立面理解为彼此是互为条件的。
第四,我们关于合法化的进路应是多元主义的,在这里为个人主义提供更多空间的私人领域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公共领域。
第五,这种合法化讨论需要一个沟通的空间,不仅要消极地提供这样一个空间以使讨论得以进行,而且要积极地为讨论创造可能条件,鼓励基于正确和丰富信息的更广泛的参与。
第六,在法律实践中,多数为沟通行为提供空间和方式的公共领域、许多不同的合法化领域的沟通主体仅仅涉及审判中的当事人、不甚重要案件中的法官、法律学说、大众媒体或者在那些与公共利益关系更密切的案件中一定程度上的社会。
第七,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不同的公共领域之间彼此互相作用,为彼此的稳定与合法化创造条件。[1](P198—199)
豪埃克教授还就作为整体的法律制度的合法化与规则和判决的合法化进行了探讨。如前所述,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只是弱势意义上的合法化,规则和判决的合法化则是一种强势意义上的合法化。人们可以从系谱、程序和内容等方面对规则的合法化进行评判。从系谱上看,人们可以考察立法机关是否有权制定这一规则,是否以恰当的方式从适格的上级机关获得了授权。就程序来说,人们可以核实规则的制定是否遵循了既定的程序,是否遵循了基本的程序规则。就内容而言,人们可以追问规则是否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相一致,是否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对判决的合法化而言,人们也可以对法官的能力、程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评判。
事实上,豪埃克教授将法律的合法化与公共领域、沟通理性联系起来的进路与哈贝马斯是一脉相承的。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种政治制度的尊严性……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18](P262) 这种承认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作为前提的,而这种制度机制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上。在他看来,由于公共领域是脱离官方的,它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合法性事物的辨识力,而且是自由沟通进而形成一致认同的价值和规范的场所,所以,它能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论证和价值准则,成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本应作为生活世界的建制化的公共领域被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殖民化”,其政治参与、提供合法性的功能大大萎缩;国家试图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技术性的问题,这样,科技进步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技术和科学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而要拯救晚期资本主义于合法性危机,惟有将公共权力重新置于“持续的同意”的基础上,即经由公众的意志参与和自由辩论来重建公共领域,恢复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以此恢复公众批判的能力和权利,以使文化系统重新具备创造“意义”的功能,为行政系统提供必需的合法性支持。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彰显沟通理性,以沟通理性取代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
收稿日期:2005—08—20
注释:
① 德语“Kommunikation”(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在汉语世界有不同的翻译,常见的有“沟通”、“交往”等等。我们认为,就哈贝马斯的理论旨趣而言,“沟通”和“交往”只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无太多的实质不同。但就豪埃克的法律学说而论,译为“沟通”可能更好一些,特别是就其书的标题而言,若译为“作为交往的法律”总觉别扭。而且,汉语中“交往”只说明人际之间发生来往关系,而“沟通”则不但包含了“交往”,也具有“通过平等商谈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意境,有强调理解、一致、同意、通达等丰富的内容。因此,本文将“Communication”译为“沟通”。而且,为保持一致性,将哈贝马斯的相关学说称为“沟通理性”和“沟通行为理论”。
② 法的自创生理论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贡塔·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在《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Law as An Autopoietic System)一书中提出的。自创生理论在一种沟通网络的自我再生产中看待法律的自治,并且把它与社会的关系看成是与其他自治的沟通网络的干涉。中译本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之所以称“可能的”是因为豪埃克教授旨在强调有些特征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对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必然如此。See Mark. Van Hoecke,Law as Communication,Hart Publishing,2002,p.15.
④ 豪埃克教授的这种学说可能也受到了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理论的影响。自创生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是认为法律是一个“超循环”。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以下。
⑤ 该理论认为法律规则是作为人类行动的理由(norms as reasons for human action)而存在的,并区分第一性的理由(first-order reasons)和排他性的理由(exclusionary reasons)以及相关的命令性规则(mandatory norms)、许可性规则(permissive norms)和授权性规则(power-conferring norms)。See 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2nd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⑥ 在该书中,豪埃克教授直接借用了哈特关于“法律是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结合”的观点。“第一性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授予权力的规则,包括“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等。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以下。
⑦ 豪埃克教授主要是从系统化、体系化的角度来讨论“legal system”,间或也从整体上讨论某种“legal system”。因此,我们将根据情况将其译为“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