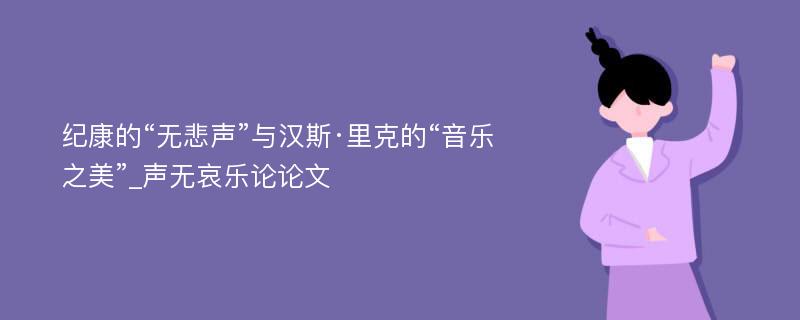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乐论文,汉斯论文,音乐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的重要音乐美学著作。但“声无哀乐”作为命题,并非只有音乐美学的单一部门美学意义,而是同时还涉及一般文艺美学(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世说新语·文学》说:“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又《南齐书·王僧虔传》引录王的《诫子书》也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可见,“声无哀乐”又曾是魏晋玄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热点命题。总而言之,“声无哀乐”作为命题,具有多层次的理论意义。
现当代学术界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或“声无哀乐”命题作了很多研究,但已有的研究往往展开的层面不同,看法也往往不一致,甚至相反。有人认为:“嵇康的以‘和’为核心的乐论的建立,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美学完成”。(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又有人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的命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还有人认为,《声无哀乐论》提出的一些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长久”的意义,但“声无哀乐”说,“使音乐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命题”。(注: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284页。)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从不同层面展示的看法,都各有各的立论依据,但也应该说都还未有切实地解决命题的多层次意义。因此,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既然《声无哀乐论》首先是音乐美学著作,“声无哀乐”首先是音乐美学命题,那么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应该从音乐美学入手,然后过渡、上升到一般文学美学(艺术哲学),乃至玄学哲学并实现多层次意义的统一。在这里,本文就首先关注命题的第一层次意义。若从这一解决问题角度出发,那么我认为钱钟书先生的先在揭示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管锥篇》中说:“西方论师(Hanslick)谓音乐不传心情,而示心运,仿现心之舒疾、猛扬、升降诸动态,嵇《前已道之”。(注:见《钱钟书论学文选》(四),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72页。另钱先生论及嵇、汉二氏关系的,还有重要一段,摘录如下:“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国则嵇中散《声无哀乐论》说此最妙,所谓:‘夫唯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声音以平和为主,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奥国汉斯立克(E.Hanslick)音乐说(Vom musickalischschonen)一书中议论,中散已先发之”。(《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90页。)在这里,钱先生以比较方法,揭示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近、现代西方音乐美学大师奥地利的爱德华·汉斯立克(1825-1904)的《论音乐的美》(注:蒋一民译为《论音乐美》,见蒋氏著《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嵇康先“道之”千载前。但钱先生的揭示,还主要是指点性、结论式的,因此还需要深入追问,作进一步的具体系统分析,问题才能清晰,并同异互见,下文拟从二方面展开探究。
一、音乐的本体与音乐的美
嵇康与汉斯立克虽然分属相距一千多年之遥的不同民族历史文化时空,但在最根本的音乐与本体与音乐特殊之美问题上的确存在着英雄所见的略同之处。当然同中也有异。
先看先“道之”的嵇康的具体看法。我们知道,康的音乐本体观是对儒家音乐传统观念的反拨。在《声无哀乐论》中,儒家的音乐本体观用秦客的话转述就是:“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注: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12页。以下凡引嵇氏语,不另注者,均见该书。)这就是说,一定的音乐与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治亡相“应”,是一定时代人们哀思情感的表现和安乐形象的反映。
嵇康认为,秦客所转述的儒家音乐政治伦理本体本原观,虽然是“先贤不疑”,以至似乎已成为传统定论,但其实却是“令历世滥于名实”的问题。即是说,儒家所谓音乐本体本原定论之“名”,只是滥用,其实并不符合音乐本体本原的实际,也就是说是错误的。那么在嵇康看来,什么才是音乐的真正的本体本原呢?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
嵇康认为,音乐的本体本原不是与特定社会政治制度的亡治相应,也不是特定时代民众安乐或哀思的反映,而是在于天地之气融合产生万事万物,以及四时运行交替,五行因而形成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它与事物的色彩、气味一样,都是天地自然万物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也象色彩、气味等之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它或好听或不好听,其本体只受天地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不会因为特定社会政治制度之治乱而变化。那么,嵇康认为的与儒家音乐政治伦理本体论异趣的自然本体论的内涵是指什么呢?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说了不少描述这个本体内涵的话,如:“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声音有自然之和……克谐之声,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声音以平和为主体,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声音以平和为主体,而感物无常”。“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宫商集比,声音克谐”。“音比成诗,声比成音”等等。从这些地方以及其他有关地方,我认为可以把嵇康的音乐自然本体本原论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与时代政治和人们情感无关的声音自然之和。不过对这里的“自然”与“和”,还要作必要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和”的概念早就存在,《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周礼·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淮南子·汜论训》:“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德莫大于和”,并认为最能体现“和”的是音乐。又《国语·郑语》:“和乐如一”。《荀子·乐论》:“乐也,和之不可变者也”。《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等等。
由上引例可见,我国古代典籍一般认为“和”乃天地人的德性,万物生成和发展的依据。从这一基点出发,在音乐上,儒家也早就用“天地之和”标举音乐的本体。那么,嵇康的“自然之和”与儒家《乐记》等说的“天地之和”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首先是“天地”与“自然”不同。虽然从字面上看,“天地”与“自然”是可以相通的,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不同,首先是哲学基础不同。儒家的哲学基础是孔子提出的“仁”与“礼”,是人为政治伦理。儒家虽然也讲天地、自然、天人合一,但在儒家那里,天地,自然是服务于人为的“仁”与“礼”的,或说“天地”在儒家那里主要是服务于人为政治伦理的天地,而不是客观本原存在的自然天地。因此,儒家音乐本体的“天地之和”,又可以从价值角度表述为“声音之道,与政通”,“乐者,通伦理”、“乐者、德之华也”(《乐记》)。是分明的政治伦理本体。又因此,儒家虽然强调“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但在他们那里,作为音乐创作者的“人”,似乎又主要是指统治者,是“王者功成作乐”。“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音乐只不过是通过规范人的精神心理而为礼治服务的手段。儒家强调音乐的“和”,也就主要是强调音乐在调和等级制度社会矛盾中的重要意义。
而嵇康说的音乐本体是“自然之和”的“自然”则不同,其思想基础已由儒家迁移到了道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认定“老子庄周,吾之师也”。(注:分别见《嵇康集》的《释私论》与《与山巨源绝交书》,载《鲁迅全集》(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87页、47页、45页。)而老庄哲学的“自然”。正是与儒家“人为”相对的范畴,是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客观本原存在,其形而上即“道”。因此,在嵇康那里,“自然之和”的“自然”,也正是排除了人为因素体现“道”的精神的纯粹客观本原存在的“自然”。
这样,嵇康的“和”也与儒家的“天地之和”的“和”不同,这里的“和”,是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体现“道”的纯粹客观存在的自然声音之“和”。“声音之体,限于舒疾”,“声比成音”,“克谐之音”。也就是说,在嵇康那里,构成音乐本体本原的声音自然之和的要素,不是别的,正是体“道”的客观存在的声音的“舒疾”、“猛静”、“善”与“恶”,以及从中提取出来的“宫商”、“五音”。又正是这些体“道”的要素“宫商和比”、“声音克谐”、“声比成音”,即按声音本身美的规律的自然和谐组织排比呈现了音乐的本体。总起来说是,嵇康认为音乐本体的“自然之和”,与人为政治伦理无关,也无关人之利欲情感,它只是作为体道之存在的客观自然声音美的提取,和按美的规律的和谐组织排比,是道之显现的自然声音和谐组织成的形式美。反过来说,正因为音乐的本体本原是道之显现的自然声音和谐组织成的形式美,它联系道,体现道,具有非意识形态性,所以也就与社会政治兴亡无关,与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无关。对这点,如导言所引,钱钟书先生作了非常精要的揭示。
以上大致就是嵇康音乐本体论的基本内涵,由于其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音乐政治伦理本体论相对立等原因,所以在后世中国—直缺乏知音,(注:参见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0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56~257页等处。)但经1000多年后,终于在西方产生了强烈的遥相呼应。这个人就是钱钟书先生指出的汉斯立克。
爱德华·汉斯立克是奥地利近现代著名音乐美学家,与嵇康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儒家音乐思想传统相似,汉斯立克的呼应也基于一冈立面,这就是他说的“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差不多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它不去探索什么是音乐中的美,而是去描述倾听音乐时占领我们心灵的感情”。(注:[奥]爱德华·汉斯立克著、杨业治译《论音乐的美》,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第15页。以下凡引汉氏语,不另注者,均见该书。)这个“通病”由来已久,但较大声势起始于十七、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情感美学或内容美学,而其中舒巴特是典型代表。他说,音乐美是表情,而表情就是“内心的表露”。汉斯立克认为这种“通病”是学术界“把美的哲学也称作感觉的学问”,并且“完全忽视听觉而直接诉诸感受”的结果,是错误的。他大致从如下几方面而具体论述了“音乐表情说”的错误:首先是“情感不是音乐所特有”,而是所有艺术的共性,而且与诗、画等都能引起人的情感的艺术相比,音乐引起人的情感是“最不确定的”。其次,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缺乏概念的明确性”,因此,严格地说音乐“没有能力表现某一明确的情感”,它只能表现情感中的“力度”。再次,所谓音乐中的情感实际上只“是跟旋律相配合的词句所说出的”,并非它本身的能力。总之,音乐美应以音乐所特有的东西为依据,而情感并不是音乐所特有的东西,而是次要的或外加的东西,因此,把情感视为音乐的本体或特殊的美是错误的。汉氏的这一观点的确与嵇康的音乐“无关哀乐”说遥相呼应。汉斯立克把音乐情感论称为他律论。
既然音乐的特殊之美不是“通病”说的情感,那么是什么呢?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他还进一步概括出一个著名的命题:“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汉斯立克这里说的“自由的形式”、“运动形式”,简而言之也就是“形式”。要明确的是,汉氏说的“形式”与流行的一般心理学和音乐理论上说的“形式”不同。这个不同,首要的是哲学基础不同,一般心理学或音乐理论上说的“形式”,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容与形式对立一范畴。而汉氏的“形式”,则是奠基于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并经莱辛——康德——席勒一线而来。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所认为的“形式”,不是一个与“内容”相对立的概念,在那里,“形式”就是“理式”,是总揽万物的“精神”,是生命的本质及其呈现。(注:将一民著《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页。)承此而来,汉氏的“形式”,自然也就有本体论的意义,是音乐的特殊美之所在。他在这里的表述,用的显然是以流行的异己的范畴来表达自己独特思想的方式。因此,汉氏在谈音乐特殊之美时,虽然大讲乐音的组合、协调与对抗等等,但并不把之看作就是音乐的特殊之美,而是看作是音乐的特殊材料。他认为音乐之美离不开音乐的特殊材料,并且就存在于音乐的特殊材料之中,但要由有丰富音乐艺术涵养的人凭幻想力,从对音乐特殊材料的直观即纯粹审美观照中才能于心灵里呈现或感受到。作为音乐本体与特殊之美的“形式”,是总揽所有音乐艺术的。钱钟书在揭示并描述汉氏思想时说:“音乐不传心情,而示心运……”,又说:“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寥寥数语,可谓把握到了汉氏思想的精髓。音乐的本体和特殊的美,作为一种总揽所有音乐艺术的“理式”和“精神”,并不是任何具体的情意。同时也正因为它排除了任何具体情意的纠缠,所以得以实现涵盖、总揽或超越一切情意。
由上分析可见,嵇康与汉斯立克在音乐特殊本体与音乐特殊之美问题上的看法,的确存在着共同性,不过,若加以细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同中也有异。对这个“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两人的立论角度不同,嵇康是从音乐本体论角度立论,由否定儒家音乐政治伦理本体论到确立体现“道”的精神的自然本体论。而汉斯立克则是从音乐特殊之美角度立论。由否定情感美论到确立与“理式”相联系的形式本体论和形式美论。二是两人确立音乐的特殊本体和特殊之美的哲学基础也同中有异。汉斯立克确立音乐特殊之美的哲学基础,如上所述是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其“形式”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理式”相联系。嵇康立论的哲学基础是中国道家哲学。中国道家哲学的“道”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理式”也有相通之处,但也只是有相通之处,并非相同。其深因在于,中国道家哲学的“道”是奠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更确切地说是道家“以人配天”、“以天合天”式的天人合一)基础上。而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理式”则是奠基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天人相分)基础上的。这个哲学基础的差异,导致了本体论的差异,在受制于本体论但较为具体的本源论那里,就更为泾渭分明了。如上所述,嵇康是认为音乐来源于体“道”的客观自然声音,是体“道”的自然声音之和,而否定人为。汉斯立克则刚好相反,认为音乐与自然声音无关,只是一种人为创造,并从两方面作了很有力的分析。首先从音乐本身构成的基本要素角度看,音乐的基本要素是旋律、和声与节奏。汉氏认为,作为可测量的乐音秩序的相继出现的旋律,与作为一定乐音的合响的和声,在自然界中都不存在,自然界中唯一存在音乐的要素是节奏。但音乐中没有孤立存在单纯的节奏,因此,这孤立的节奏与音乐中表现着旋律与和声的节奏仍然不同。总之,自然界中不存在音乐构成的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纯粹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与自然无关。其次,他又从自然声响与音乐艺术比较角度,认定二者是不同领域。汉氏说,自然界没有音乐,只有声响,即一些以不相等的时间片断相继而来的空气的振荡而已。当然,自然界偶尔也会发出个别乐音(即具有一定的、可测量的音高的声响),但只是偶尔的、孤立的,因此,并不是导向人类音乐的阶梯。总之,自然界的声响没有一定可约性,没能给我们一套现成的乐音体系作为艺术素材,自然界的声响与人类的音乐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音乐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汉斯立克认为,与诗歌、绘画等艺术都有自然界提供的自然美的范本不同,自然界没有给音乐创作提供“自然美的范本”、“音乐现象的原型”,只能说至多提供某些诗意的启发。因此,音乐创作只是“一些乐意的排列,作曲家是完全自由地按照音乐的思维规律把这些乐音排列从自己胸中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美无关,也“远离一切对象性的现实”。他甚至认为,连民歌也没有自然界的范本,“追溯不出它的来源”。
汉斯立克的以上分析看到了音乐与自然声响的区别,与嵇康的尚未分别相比,自有其独到之见和高明之处。但因其过于绝对,也孤立了音乐以及作曲家心灵与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内在联系。有使音乐成为无源之水的味道。当然汉斯立克也谈到作曲家的诗意幻想力可以把音乐与自然联系起来,但又强调这种联系是非常松驰与任意性的。其实,这点正是音乐与自然关系的特点。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并非只有诗、绘画与自然关系那样直接的模式,就是诗、绘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一定很直接。在这里,汉氏显然是以诗、绘画与自然关系为唯一模式,去否定音乐与自然的较为曲析,并更富创造性的关系了。
三是在对音乐本体与音乐之美的看法上,嵇康与汉斯立克之间似乎还有一点不同,这就是汉氏的看法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至多带有学派的色彩。而嵇康的看法,则成份较杂,不仅有学术性因素,而且还带有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因素。
嵇康所处时代的魏国,是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斗争的白炽化时期。司马昭阴谋篡夺曹氏政权的野心路人皆知。嵇康虽然并非是曹氏集团的核心成员,但作为这个集团中一个有责任感,又头脑清醒的人才,他的言行是不可能远离现实政治的。正如侯外庐所说:“嵇康的文化论,一句话说完,就是反礼乐,反名教,主观上要修正两汉的博士的意识形态。而他所否定的,却是司马氏偷盗着以欺蒙天下人耳目的法定,因此,客观上也具有政治的意味”。(注: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以此为大前提,我们也就可以说,作为嵇康文化论中占显要位置的音乐理论与活动,客观上也有反司马氏的政治意味或政治针对性。
当然这样认为,并非仅是一种逻辑推演,而是还有两点可以实证:一点是从嵇康的音乐本体论与音乐功能论的矛盾可以看出。嵇康在音乐本体论上是与儒家针锋相对的,但在音乐的社会功能论上却不能超越儒家的铁门限,因而显出了矛盾。他对音乐社会功能作了两种情况的分析。他认为,在“天人交泰”,“万国同风”,人们“怀忠抱义”,“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的古代理想社会里,音乐的“移风易俗”功能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在社会“衰弊”,“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的时代,音乐就不再自然地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了。这确是一种矛盾。对这个矛盾,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理论不彻底而向儒家回归,但也不能说没有反司马氏的政治针对性内涵。因为在嵇康看来,正是司马氏的野心使得国家“上失其道,国丧其纪”,人心充满邪念与贪欲。
另一点是从嵇康的音乐本体论与对音乐的具体爱好的矛盾也可以看出。嵇康的音乐本体论,已如前论,是体现“道”的精神的声音自然之和,是声音克谐集比的形式美。嵇康是酷爱并精通音乐的,他最喜爱的是大型古琴曲《广陵散》,他在这一爱好选择,可能有纯音乐形式美的原因,不过也不能完全忽视内容。关于《广陵散》的内容,学术界各家的说法虽然不尽一致,或“聂政刺韩王”说,或“聂政刺韩相”说等等,但都与战国侠义之士聂政行刺复仇有关。夏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在谈到该曲时分析说:
《广陵散》的旋律显得非常丰富多变,感情起伏也较大。正如北宋《琴苑要录·止息序》所说,它在表达“怨恨凄感”的地方,曲调幽怨悲凉;在表达“怫郁慷慨”的地方,又有雷霆风雨,“戈矛纵横”的气势,例如《正声》部分的《徇物第八》、《冲冠第九》、《长虹第十》,就集中显示了这一特色。《徇物》段以清越徐缓的旋律,反复吟叹,并伴在离调手法,传达出一种沉思而略带激动的情绪,描写聂政决心为父报仇的内心活动,接下去的《冲冠》,由前段的C宫调转入同宫系统的羽调式,曲调保持在高音区,速度较快,情绪悲愤激越,预示出一场搏斗即将来临。自《长虹》而下,速度越来越快,并运用“拨刺锁”的特殊技法,以强烈的节奏进行,造成戈矛杀伐的气势,突出表现了聂政的英勇斗争精神。(注:夏野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据上引夏野先生对《广陵散》的分析,可以推断:嵇康钟爱该曲原因之一,很可能与该曲表现了反抗复仇的主题有关。《广陵散》中聂政刺杀韩国宰相等的内容,也应寓寄有嵇康对现实魏国“宰相”司马昭的仇恨内涵。据史书记载,嵇康临刑从容自若,顾视日影,索琴弹了该曲。弹完后感慨说:“《广陵散》于今绝矣”!(注:《晋书·嵇康传》)对此,有人以临刑“关心的是音乐,已经忘了自己”(注:王晓毅著《嵇康评传》,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来解释,但恐怕也不尽于此,应还有于时局的无可奈何,以及对司马氏的蔑视和深仇大恨。
二、音乐与情感的关系
在音乐与情感关系问题上,嵇康与汉斯立克的看法也有共同之处,用前引钱钟书先生的话概括就是“音乐不传情情”。不过,虽然他们都认为音乐不传心情,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无关,但又都认为音乐能引起情感,与情感有非本体的关系。当然,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既有同也有异。
先看嵇康的看法,如上所论,嵇康认为音乐本体在于体“道”的音声的自然之和。从这个本体论出发,他确认了音乐“无关于哀乐”,“无系于人情”。即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具体情感有关。他大致从两方面作了明确的具体分析:一是“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音声之无常”。他说:“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在这里,嵇康从不同风俗地方的哀乐情感表现不同谈起,进而论定无具体形象的声音与情感不是对应性的确定性关系,而是同一情感可以与万殊之声音相联系。反之,同一声音也可以激发不同的情感。总之,音乐与情感的关系是“无常”的即非确定性的关系,从而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嵇康明确的音乐与情感关系的“无常”,即非确定性关系,道出了音乐与情感关系上的一大特点。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概括的“乐无意,故能涵一切意”。音乐与情感关系的非确定性,也就是音乐能超越任何特定情感,与更多情感发生关系,从而具有无限的涵盖性、广延性。“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能“触类而长,所致非一”。(注:《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92~93页。
二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殊途异轨”。他说:“……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调,然则心之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又说:“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在这里,嵇康通过一系列比喻,进一步从性质上区分了音乐与情感,认为“心”(情感)与“声”(音乐)分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换一个角度说,“声”(音乐)与“心”(情感)走的是不同道路,具有不同的轨迹不可能相互交织。总之,音乐与情感没有性质上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否定了音乐的本体与情感有关。
不过,嵇康虽然确认音乐的本体无关哀乐情感,但又承认音乐与情感有非本体上的联系,能引发人的情感。他大致也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是,因为音乐为人的“情欲”所钟受,可用之调节人的情欲。他说:“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这就是说,由宫商等音声聚集融合而成的和谐的音乐是人们的内心所非常愿意听到的,为人们的“情欲”所钟爱,古人知道情感不能放纵,欲望不能过度,因此,顺应着情欲的需要,常常用音乐来调节,使悲哀的情感不至伤害身心,欢乐的情感不至漫无限度。嵇康在这里是要说明,虽然之调节人的情欲和心理状态,因而又与情感有联系并能引发人的情感。
二是,音乐之所以能引发人的情感,是因为哀乐之情感预先潜藏在人的心里。他说:“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又说:“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醒酒之发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嵇康这里是说,人的哀乐情感是由于人生事件的原因而预先形成并深藏于内心的,只是遇到相应的谐和的音乐引发才明显地表露出来,谐和的音乐本身是没有表现任何特定哀乐情感形象的,人心中或哀或乐的情感是事先形成的。因为人心中先期有了或哀或乐的情感,所以遇到相应的没有表现具体情感的音乐,才会引发表露出或哀或乐的情感。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嵇康还以酒与人性的关系作喻,但应当指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时,无补于问题的进一步明晰,倒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因为作为人的精神作品的音乐,与作为物质产品的酒不同,酒作用于人的浅层生理,音乐则主要作用于人的高层精神心理,两者有明显的质的区别。嵇康关于音乐与情感关系的这方面问题。在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倒是有一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这就是东汉初年哲学家桓谭在《新论·琴道篇》里讲的雍门周与孟尝君故事。桓文说:
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富而今贪,摈压穷巷,不交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谗罹谮,怨结而不能言;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出以野泽为邻,入用掘穴为家,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呜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了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在前,谀谄侍侧,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练色以淫目;水戏则舫龙舟,建羽旗,鼓钓(吹)乎不测三渊;野游则登平原,驰广囿,强弩弋高鸟,勇士格猛兽,置酒娱乐,沈醉忘归。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虽有善鼓琴,未能动足下也”。孟尝君曰:“固然”。雍门周曰“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纵)即衡(横),从(纵)成则楚王,衡(横)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极弱薛,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之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儿牧竖,踯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见之凄怆]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征,叩角羽,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注: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这个故事的确可以说明上述嵇康的观点。但这里也有个问题,就是:雍门周所鼓的引发孟尝君悲哀情感的琴典是一乎怎样的琴曲?是一首有相应的旋律、节奏与和声的琴曲?还是随便一首琴曲?对嵇康上述的理论观点,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即引发人的或哀或乐的多种情感的音乐形式结构,与人的或哀或乐的多种情感的结构,是否应有某种可以相互对应性?没有则罢,若有,又是怎样相应的?对这,在嵇康那里还缺乏必要的说明与分析。当然,嵇康在当时要说明这个问题是难的。即使到现代,也不能不说依然是个难题。有学者以西方完型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来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这不失为一种尝试。
以上是谈嵇康对音乐与情感关系问题的看法,以下谈汉斯立克。
如前所述,汉斯立克也否定情感是音乐的本体和特殊的美。不过,他也承认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在听众中能引起情感,甚至引起比其他艺术更强烈的情感。他还对音乐引起听众的情感作了精到的两种区分:一种是发生在生理层次上的非艺术性情感。他认为这种情感不是音乐的艺术因素——从精神中来到精神中去的因素—引起,而是音乐的材料,或音乐的原始素质—声音和运动—对神经系统的刺激引起的。是生理现象,甚至是病理现象。因此,与真正的音乐美无关。他认为古代音乐缺少和声,旋律局限在宣叙性表现的狭小界限内,而且古代乐音体系不可能发展出真正音乐性的丰富的形象,这样就使绝对意义下的作为音乐性艺术的音乐成为不可能。音乐也许从来不是独立地运用,而总是跟诗歌,舞蹈、表现艺术等结合,作为其他艺术的补充。它的职责只是通过拍节奏和各种不同音乐起活泼生动的作用。此外,还用它来加强宣叙性的朗诵,作为词句和情感的注解。因此,音乐的作用主要是在它的感性和象征性的一面,它的活动限制在这些因素上,它只能高度集中地发展这些因素,使它们产生巨大的甚至很巧妙的效果。他还特别谈到典型的古代音乐调式的特殊效果问题,即古人为了一定的用途严格选择一定的调式。如:多里亚调式是为了庄严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宗教的目的;弗里季亚调式用来激励士气;利第亚调式意味着悼伤和忧思;爱奥利亚调式是变爱或饮酒作乐时弹奏的。这四种主要调式间严格的,有意识的区分,配合着四种心情状态,每种调式总是跟与之相应的诗歌结合。这样一来,耳朵与心灵听到某一种音乐时,就有复制与调式相应的情感的不由自主的强烈趋势。在这种片面的训练的基础上,音乐成了所有艺术的不可缺少的顺从伴侣,为了教育、政治、道德和其他任何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与工具,它什么都是,但就是不是独立的艺术。总之,他认为,以上种种由音乐的原始素质、声音与运用所引起的情感都属生理性甚至病理现象的情感,而不是音乐艺术性的情感。他还认为,没有受过音乐美艺术鉴赏的教育的外行听众,对音乐所陶醉、感受引发的情感,大多是这种非艺术性的情感。
汉斯立克认为,音乐引起的情感,除了上述由音乐中的原始素质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发生在生理层次上的非审美性的情感之外,还有一种是由音乐的艺术因素—从精神中来又到精神中去的因素—引起,“与纯粹观照相配合的情感。”听众“只是在它始终不渝地意识到它自己的审美来源,即某一美物,并且正是这一特定美物给了它愉快时,这种情感才能算是艺术性的。”汉斯立克这里说的“美物”,是指音乐的特殊的美,又称音乐个性,即音乐中客观存在的乐音系列、音乐造形,与“理式”相联系的音乐形式。汉斯立克在这里显然是指现代音乐,因为他已认定现代意义的艺术性和音乐在古代是没有的。同时,自由的有意识的纯粹审美观照,与上述生理甚至病理的激烈状态完全不同,它是静观的倾听音乐的方式,在静观过程中,客观的音乐系列的运动形式,唤起主体精神上的追随,“幻想力的思索”,从而对音乐的艺术造形感到一种静观的愉快,精神上的满足,这是一种清醒的心灵感到的内心的快乐。汉斯立克说,音乐“美的最后价值永远是以情感的直接验证为根据”。这里的“情感”,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内心的满足或快乐,艺术性情感。而不是指音乐中的原始力量刺激神经系统而产生的生理层次上的情感。
由上分析可见,在音乐与情感关系问题上,汉斯立克的理论思路与侧重显然与嵇康有异。他集中于对音乐引起情感性质的区分,以及对区分的两种情感,特别是其中艺术性审美情感的界定上。应该说他的区分与界定都极具新见,在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比较,也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嵇康的对音乐引发的情感尚未见科学区分的浑沌状态。但在汉斯立克那里,主体静观乐音的运动形式如何产生精神性的审美情感,作为中介因素的主体条件,以及主体与乐音运动形式间关系如何?汉氏的分析也尚显得抽象。
以上,本文以钱钟书先生的先在揭示为起点与指导,对嵇康《声无哀乐论》与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集中从音乐的本体与音乐之美,音乐与情感关系等两方面作了一些具体分析与探讨。这个分析和探讨在较充分地展示嵇、汉二氏思想之“同”的同时,也试探了两人思想的同中之异。本人觉得,无论对两人思想之“同”,还是思想之“异”,都还可以作更深刻的研究。
在统治阶级长期局限音乐为政治伦理的工具,或在学术界长期抹煞音乐的特殊性,使人们已逐渐不知什么是音乐的特殊本体与特殊之美的情况下,嵇康与汉斯立克以真正理论家的勇气强调音乐的特殊本体与特殊之美,由异化的他律回归自律,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强调音乐的特殊性时,往往不可避免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倾向。他们或者否定音乐与自然现实有关,或者否定音乐与现实政治伦理的某种联系,否定音乐有社会意识形态性质。这种倾向也无形中孤立了音乐。音乐自然有自己的特殊本体与特殊之美,有自律性,但音乐毕竟也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而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这就是说,音乐作为人的一种特殊意识,它也始终是大网络结构的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与社会经济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因素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他律性。音乐就产生发展于自律与他律的矛盾冲突的动态平衡之中。因此,强调音乐特殊本体与特殊之美是应该肯定的,但若因此走向绝对,也会陷入矛盾。如前所论,嵇康在音乐本体论与功能论上就陷入矛盾。汉斯立克也有过矛盾,据说,他原计划只把《论音乐的美》“作为论争性的开端”,进而写成一本系统性的音乐美学专著。但他后来认识到:“真正有成果的音乐美学只能在深入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于是他改变了方向,不再对问题作孤立的研究,而是“更多地从文化史方面考察音乐形象,而不再回到音乐美学方面来”。(注:《汉斯立克小传》,见《论音乐的美》附录一,第119页。)这个“转问”,说明了他意识到了实际与初衷的矛盾,并且已超越了某种孤立绝对倾向而走向了开放,由单纯的自律走向了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不过,尽管嵇康与汉斯立克立论有一定的偏颇,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对音乐美学来说,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很清楚,尽管对处于网络关系中的音乐可以作面面观,并作出种种规定,但的确只有其中为嵇、汉二氏所张扬的作为音乐的特殊本体与特殊之美的“形式”,才是音乐存在的关键所在。也只有揭示了音乐“形式”的“嵇密”,才算真正掌握了音乐。还应指出的是,嵇康与汉斯立克提出的问题的意义,并不中止于音乐美学本身,而是对其他艺术的美学问题,乃至整个文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也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正因此,嵇、汉二氏论著能不断吸引现当代学术界投注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