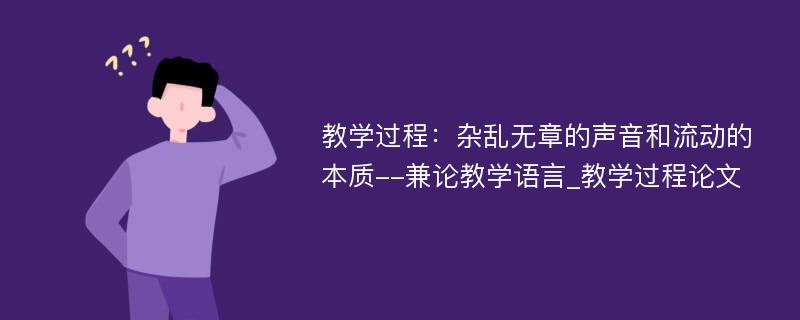
教学过程:飘忽的声音和流动的本质——兼论教学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过程论文,本质论文,声音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教学因其语言性、因其言语声音的一过性而导致意义的瞬间生成或瞬间飘荡的结局,进而导致教学过程的本质特征是其流动性。动的教学才是真正意义的教学。教学的流动性指的是教学中所包含的各种基本信息和意义伴随教学语言有秩序、递进的变化,最终引向教师的目标这样一种教学特征。教学的流动性给师生理解创造了更大空间也带来了更大困惑,既对教师提出了挑战,又给教学论研究以新的启示。
关键词 教学语言 流动性本质 意义 瞬间生成 即兴发挥
“××,请你谈谈刚才我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教授对他的一位得意门生提问道。
“对不起,教授,我不知道。”学生沮丧地回答。他不好意思说,他在教授正讲那段话时恰好心飞窗外,因而压根就不知道教授究竟讲了些什么。
学生的表现令教授失望。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不完全是学生优秀与否认真与否刻苦与否的问题,如果是课本,他们能顺利地再次阅读它并抓住文中的内容从而圆满地回答教授的问题。但这不是课本,这是言语,这不是静止地阅读,而是飘忽的声音及由这飘忽的声音铸就的流动的教学,这关涉的不是凝固的文字,而是稍纵即逝的声波。我们的多数专家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
无论有多少改变,除了介绍性成果外,迄今为止我国的教学研究基本上仍是循着凯洛夫划定的内部教学框架探索过来的,基本特征是把教学当作一个超脱于社会的封闭系统而进行内部结构的静态分析和描述,诸如教学过程、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与技术手段等,很难有跳出这一框架或静态思路的,这是我国教学论研究的主流。
我们认为,一切教学都是非静态的,是流动的,这因为一切教学都是语言的话语的教学,这种语言性的教学其意义远远超出语言本身。语言的获得过程是对贮存于语言系统中的思想、内涵、概念、理性、态度与判断的分析、斟酌过程,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语言之外无教学[①]。教学具有语言性,语言具有多义性,教学中的言语具有一过性。教学的语言性和语言的多义性以及教学中言语的一过性导致教学的本质特征的属性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动的教学才是真正意义的教学,教学中的动才是教学本质特征的真正属性。
一、教学的流动性本质:根植于教学语言
教学(本文指课堂教学及其各种变式)赖以进行的基本联结方式是语言。美国学者史蒂文森(Stevens·R)曾用多年时间研究课堂教学,发现教学谈话平均占用64%的课堂时间[②],福兰德(Flander)的研究获得同样的结果: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上课时间的2/3用于谈话[③],若考虑课堂上读和写这两种书面语言活动时间,那么可以说教学就是、至少几乎是语言性的,教学充斥着语言。
教学的语言活动可分为两类:其一,书面语言的教学,以文字的阅读和写作为特色,其二,口头言语的教学,包括演讲、解释、讨论、提问、答问、复述等形式,以讲解聆听为特色。如前所述,口头言语的教学尤为常见,占主要地位。本文着重研究后一类语言活动构成的教学。
教学的口头言语内在地成为师生课堂学习的主要方式和课堂中人际交流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已被许多专家认识到,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学的口头言语性特征本质上导致理解的倾刻生成性和意义的多歧性,因而它内在地规定了教学的流动性本质,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
所谓教学的流动性,指的是一堂课教学中所包含的各种基本信息和意义伴随教学语言有秩序、递进地变化,最终引向或指向教师的目标这样一种教学特征。其重点落在教学信息与意义随言语的变化而变化上,变化是有秩序的,一般具有某种递进过程,也即后一种变化往往建立在前一种变化的基础上,教学的变化决不是漫无边际的,递进过程必将(至少主观上将)学生引向正确或教师认为正确的轨道,在教学流动过程的末端应该是教师的目标。在这种教学中,学生随着教师的思想言语流向教师所预期的目标。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规范的流动性特征。实际中不排除个别、偶然情况下出现不规范的出乎意料的、跳跃性的意义或信息的流动进程。尤其当教学以口头言语形式展开时更为突出。口头言语使意义与信息更丰富但更有了随意性,更活泼但更缺了反复把握的可能性。因而教学的流动性有可能常常逻辑地导致意义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学生理解的困难性。由此可见,教学的流动性概念不等同教学速度,它比速度更复杂,后者只是教学快慢的问题,而流动性则是一种有内在规律的完整结构模式的进程性特征。有的教学模式一时成绩巨大,一时又一落千丈被人冷落,有的教学模式长期冷落后又突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都是教学在流动中与特定情境相互作用后的结果。
如前所述,教学的流动性乃根植于教学的语言性尤其是口头言语性特征。事实上言语是一过性的,除非被物质化(如录音),否则言语将一飘而逝,言语一经发出,它们便永远地在世界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教学一旦走下书本成为具体的言语活动,就失去了永恒的绝对的东西,每次教学都是特定的、相对的,教学的真理或意义或一般,如果说有,也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此时此地的流动的教学活动之中。由言语性导致的教学的流动性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若细细品味不同的教学,就可能发现教学是如何随声音而流动的,就可能发现那声音流动背后的时间的流动、思维的流动、瞬间心理和即兴情绪的流动。教学的流动性既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很多的创造性,使得教学主体一方面可能超越言语,从流动的内容中发掘出超内容的内容,也即,同样的言语同样的声音,不同的学生将获得不同的内容。如此看来,有时候意义并不存在于言语之中,而是存在于言语外围。也就是说,当学生们在听课时,实际使用的主要不是耳朵而是大脑,从同样的声音中,不同学生听出了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学主体甚至可能仅仅从言语的物质化外表,诸如声波、声调、口形、表情、手势、言语的句法特点和篇章结构等,超越言语内容本身获得某种崭新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言语是一种教育,嗓子(包括与之相随的表情)也成了一种教育,而不仅仅是天赋的生理器官。极端而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已经表明,那些不能理解的所谓“言语不能”的人,仅凭声音和口形及句子结构等语言内容外围的东西,仍然能较好地评判出言语者是在讲真话或在撒谎[④],更不用说正常学生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待研究的新课题。乔姆斯基甚至认为,言语的把握也许有某种遗传的超后天的力量在起作用。
二、教学的意义理解:根植于教学的流动性本质
内在地看,教学的流动性表明教学是一次性完成的特殊活动。这种特殊活动致使师生达成的相互理解以及对教学内容(意义)的把握都将是变动不定的。因为教师的讲解和传授因教学的流动性本质而成为一过性的,不会等待很久让学生去慢慢接受,这决定了教学中的意义随言语的飘出而成为瞬时的流动的,不可能让学生象对待书本那样牢牢把握反复咀嚼,以细细品出其中含义。教学意义将随着教学语言的消失而隐去。当然,这种隐去有两个方向,第一,学生根本没有听或没有认真听教师的讲解,因而其意义只能随飘落的话语而自然消亡,这种单一的声音什么也没有生成,什么也没有结束,什么也解决不了。恰如本文开始时所举的例子。再一个隐去的方向是,意义虽随教师话语的消失而隐去,但已再生于学生的头脑,已隐入学生的心理结构或智能结构。这时已出现潜在的两个声音:教师的与学生的,只有两个声音才是意义的最低条件,因为任何理解都有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双方,任何理解都是理解者在理解对方时渗入了自己主观的东西的结果。前一种单一声音的隐去是教学的失败,后一种两个声音的隐去又不见得是教学的成功,尽管有可能是教学的成功。因为在后一种隐去中,虽然教学意义转化为学生自在的内容,但有可能这内容已不同于那内容(意义),教师的教意图达成X,但学生在被教中则获得了非X。只有学生实际获得了或接近于教师意图的X,我们才可能在传统教学论的立场上说教学是成功的。但站在教学语言学的立场上,有可能学生虽然没有获得或接近X,但仍然是成功的,这一点当另文研究。
然而在流动的教学中,教师的意图并不是衡量教学意义的唯一尺度,言语一旦说出,教学就近乎一种自在事件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教师意图。也就是说,理解一句话和理解说这话的人的心理意图是不同的。教学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教师的原意,真正意义处于同接受者理解者复杂组合而不断生成的言语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可视为教学的意义生成过程,是教师的心理行为与学生的心理行为(通过语言交流)碰撞后的即时闪现,是作为理解者的学生和作为理解对象的教学内容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统一物。在这种关系和统一体中,同时存在着理想中的客观意义和现实中的理解意义。这是否可以说,任何教学意义都是生成意义的教学与参与教学的师生的结合,任何教学内容是内容本身与师生对内容的理解共同生成的。意义不在课本,不在教案,不在教师的内心,而在教师的表达行为和学生对表达的理解行为共构的流动性教学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意义既顷刻生成,又能顷刻隐去。教师上课时所讲的话,天然地具有脱逸心理意图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教学流就是意义流,在流动中意义永远无法穷尽,永远无法达到满足教师要求、教材要求、社会要求的所谓客观标准。这里我们受海德格尔影响,在海氏看来,作品的意义是不断生成,不断流动的过程[⑤]。而教学意义较作品意义流动性瞬时性更强,因为前者稍纵即逝,后者可细细咀嚼。
教学的流动性和意义的瞬时性既为学生的理解带来广阔无垠的心理空间,也为我们的教学带来了种瓜得豆的困惑。不同的学生以及同一学生在教学的不同时间段将捕捉住教学流中的不同片断,产生出不同的意义或意义的不同重点,于是乎,同一节课教学,不同学生将获得不同意义。一方面,不同学生将因其自身的经验个性等心理特点获得不同的教学意义。教师问:雪化了是什么?A答:是水。B答:是春。这一例子笔者虽曾多次引用,但在它面前,我们确实不需要补充什么了。另一方面,同一个学生也可能完全随机地偶然地获得不同侧重的意义,也许这一随机而偶然获得将对他后续的进一步理解造成了相当不同的结局:有可能促进理解顺利进行,有可能给理解带来困难。犹如一节课中,一贯学习认真的A生在某一时间片断偶然(多种因素)心飞窗外,没有捕捉住这一瞬间扑面而来的意义流X(尽管他较好地捕捉住了这堂课教学的其他大部分意义),而平时学习不认真的B生却在这一时间段偶然地(多种原因造成)专心听教师讲解,较好地捕捉住了片断的意义流X(尽管整个意义流的其他部分B生并未捕捉住),而不久后的评价恰好突出了X的重要份量,这样,B生有可能偶发性地获得较好成绩,A生则同理有可能偶发性地失利。本文开头所举现象是存在的。当然,长远地看,A生对完整的意义流掌握较准确,就必然在整体上会优越于B生。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教学标准的无法完整性以及教学中因其意义的瞬时性而影响学生对意义的把握与内化,从而受到片面评价的问题。
教学的流动性和意义的倾刻生成性也为理解的差异性造成了条件。在流动的教学中,一成不变的原意是不存在的,教者也好,学者也好,都是当下的、此刻的教学者,都会有当下的此刻的理解。这种差异性理解是正常的,必然的,不要一味去克服差异,而要正视它,肯定差异的绝对性与合理性,一定程度上,有差异才能有创新。差异为学生的创造性理解提供了可能,学生超越教师,高出教师的理解的基础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也对学生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学中听一节课的分心显然较之读一本书时的分心危害性要大得多,前者是一闪而过的,无法弥补追回,后者则可以静下心来再读一遍乃至数遍。
三、教学的流动性对教师的挑战
首先,这种挑战表现在对学生的准确认识上。教师如欲使学生达到预期的X,在教学前就得对学生的理解背景进行预设,备课就是受潜在的学生的影响,努力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与学生保持大体一致,预设学生的回答,以自己特有的对策去与学生的原有妨碍理解的图式抗衡,并力图改变学生的原有图式。除了备课中的预设外,还得充分认识到,教学中的学生与图书馆读书的学生完全不一样,即便完全是同一批学生,也即完全预设或充分备课是不可能的。书是由个人慢慢读完的,教学却是由集中在一起的一群学生和一个教师来完成的。任何教学于学生面前,未知的和心理上无法预料的可变量实在太多。同样的内容,印在书上可能令学生打呵欠,课上讲解则可能令学生捧腹,印在书上毫无理解困难,在课上讲出则可能产生疑虑。文字的和言语的,当教师的须有考究。教学的流动性限定了教学自身的成功因素:这些因素有充分备课、有高超的讲课水平、语言清晰等等,但最活跃而又最无法预测的因素是面对不同语言形式的学生。
其次,这种挑战表现在教师对教学意义(内容)的恰当把握上。教学的流动性与教学内容密切关联,内容组织处理得好,流动的教学就易引起学生注意,教学的意义就易被学生瞬间生成。相反,若内容处理不好,流动的教学就更显得捉摸不定,教学的意义将飘浮教室空间迅即隐去。但教学只有在学生接受或理解中才真正存在,才谈得上是“教学”。
第三,这种挑战表现在教师话语表达意义的恰当性上。如果教师对意义把握不恰当,意义的瞬间生成就更易对学生误导,如果教师掌握了意义但其话语表现得不恰当,同样会把学生引上意义的歧途。有个笑话:某大学班主任正在讲话,突然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打瞌睡,他脱口而出:“你俩昨晚没睡觉吗?”顿时一片哄堂大笑。是笑话,但寓意深,意义的把握与话语的表达是两件不同的事。教师说出的话的意义是自足的,自己运动的,它一旦被说出就不再受讲话者所控制,意义就自然生成了,即使这意义不是教师的原意。据观察,由话语造成的误导远大于对意义把握不当的误解。在这个层面,教师的重要任务是把握内容并表达思想上所把握的内容。
教学的流动性和意义的瞬时性为教师自我实现和教学实现提供了极大的即兴可能,或者说使教师的教带来了强烈的即兴特征。这种可能或特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也许会使教师的教随心所欲,质量缺乏保证,另一方面那些高水平教师的教能恰当地达到有机天性结合的即兴创作的佳境,这是任何固定的范本教学所望尘莫及的水准。即兴教学、教学的瞬时性是典型的当场意图对原来意图的突破[⑥],是一种既具破坏性又具建设性的突破。为减少破坏性,即兴教学不能远离课本,应将课本看作坐标系中以零为标志的横轴,看作心电图的显示仪,教师的即兴发挥则是个体心脏的搏动,总围绕这个横轴上下浮动,画出或上或下的标记。
教学的流动性除了给听方造成意义的差异性、理解的不一致性外,说方本人也容易出现意义差和理解偏离,从而进一步加剧对方理解的偏差。教学中的“说”多是准备和超准备状态下展开的,是既有所准备又无所准备状态下展开的。所谓“准备”,指教师教学前曾多方考虑、利用过学生的理解基础,所谓“超准备”,指教学过程毕竟是流动性的个性化过程,受个人影响太大,个人的好恶、当时的心境都会超越原来的准备而发挥作用,这时的超准备已经使教学无所准备了。教学就是这样在准备、超准备、无准备的特定背景下交叉展开。任何教或讲都建立在充分备课的准备基础之上,但课堂上教师用哪一句话来表达已准备好的内容或意义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教师当时的心情、学生的诱发、教室周围的状况、天气情况等等因素相联系。就是说,言语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可准备性远不如备课时的书写,它不易精心设计,语境变化大。用临场即兴发挥的或多或少脱口而出的言语表达充分准备的有备而来的意义,有时甚至会使教师自己在一过性言语飘逝后,在课后学生的进一步追问中对自己表述的意义发生认同偏差,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出现教师自己不承认自己在课堂上作了如此这般的理解与讲述,而学生或听课的其他人则坚持认为该教师确实作了如此这般的理解与讲述的现象。
一过性的教学将这种自我意义的背离推到极致,于是,可以说,教学意义的独立存在本身是不独立不存在的,教学中存在的只是流动的意义流动的关系。教学的客观内容永远不能真正客观,表面上教师是在讲教材编者的话、讲科学的话,讲课本的话,其实质这里面夹杂有教师自己的声音,而且这声音还时时相互冲突,形成不和谐音。
四、教学的流动性对教学论研究的启示
教学的流动性特征启示我们:我们只有在教学意义生成的流动过程中而非其稳定的静止状态中,才能把握教学的内在本质。传统教学论是截留了教学的一刹那横断面来进行研究的,在这静止的稳定的横断面探讨教学的本质特征。教学的稳定状态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实在的教学只能是流动的,教学一稳定一静止就不是教学了,那只是静止的师生相处的画面。一旦成为教学,教学就是流动的动态的,甚至可以说,教学一旦形成,即为过去的东西。任何一次教学,都只能是此刻的教学,教学是唯一的[⑦]。意图用静态的规范来约束流动的教学,是值得怀疑的。
教学的流动性特征启示我们:对教学内容的传授与接受永远不可能客观化。教学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使教学成为即兴发挥的结果,使意义有异、理解有偏,尽管教学语言的言辞属于社会,教学负载的内容属于社会,但教学语言后面隐现的“潜在意义”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教师个体。就是说教学再现的不仅仅是他人(教材)的内容,而是在一定范围作为教师个性经验起伏的即时呈现物。教师隐藏在他人后面传授自己的东西。即时性导出意义的瞬间生成,前一段教学导出后一段教学、个性的差异性和理解的个人性替代了传统教学论所认定的对内容的准确传授与接受。教学的流动性本身是一种创造性,能修正和充实教学内容,它留下了充分的意义空间余地,供学生去创造性构建或填充。已经很明显了,难道我们不应把主要精力从对教学内容的准确传授与接受的结果研究上,转移到对传授与接受的过程本身的研究上?在教学论上,成为问题的主要不是我们所教的内容和应教的内容,而是超出教师意愿和教的行为的,在教学的流动过程中实际生成的那些意义,它们不是已经生成已被规定而是不断生成不断规定的意义。
教学的流动性特征启示我们:教学永远不可能重复,实际上也就是永远不可能自然科学化。前人的东西,后人不可能教学得像原作一样,他人的东西,自己不可能接受得像他人一样,自己昨日的东西,今日不可能重复得像昨日一样。犹如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节相同的课。因为教师(还有学生)不可能在此刻存在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背景中又同时超越这一存在进入另一个已逝去的状态和背景之中。昨日的东西显现给今日的师生收到的将是结合后的新意义。在教学的流动过程中,学他人思想的终究是当下的我,不可能以静代动,本人化他。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在80岁时第500次指挥“英雄交响曲”,他依旧像刚开始指挥生涯一样,埋头细读总谱,琢磨如何更好地表现贝多芬,每一次指挥他都能找到新的色调。难道我们的教学艺术不应这样不是这样吗?
可见,教学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实际上教学的每一片刻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一旦形成,就被它后面的世界所替代,甚至立即消失。因此,我们要求教师力求做到使每一堂课都成为一次精彩的即兴、一次出色的创新,哪怕是教同一内容的课。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教学论理论工作者如何在这转瞬即逝的世界中抓住教学的实质,抓住教学内容、教学思想乃至于教师和学生存在之本质呢?教学中人们既然逃不出流动意义的笼罩,那么我们的教学论该将如何认识这一切,探究这一切?也许,教学的流动性特质逻辑地意味着:教学科学永远不能成为有些人所企盼的完全量化、公式化、操作化的自然科学。
一言以蔽之,所谓教学,可以说是学生借助言语从心理上重新体会并创造性构造教师精神状态的活动。在教学中,教师要借用言语表达、寄托他的所思所知所接受,学生则通过把握教师的言语追溯出教师的所思所知所接受,这颇似江河奔腾而下之势,将教的过程喻为发源于教师意图的江河,借言语一泻而出,学生的接受则将思维分为两路,一路溯江而上,逆言语奔泻的轨道,索出教师意图之源头。一路则沿江而下,站在言语奔泻的潮头,从中窥探教师意图的彼岸,这种上溯下随的过程,一方面由语言规则导引着,一方面又循着它所载负的意义及教学流动的轨迹,更重要的是循着学生自身的思绪。教师由内容(的接受)到言语(的表达),学生由言语(的接受)到内容(的内化),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流动方向既相同又相反,而语言这一舟楫却始终同一。
注释:
①石鸥:《教学中充斥着什么?——试论教学语言》,《现代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
②转引自台湾《教育研究资讯》1995年第3期,第123页。
③Roland Meighan 《A Sociology of Educating》,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7,P.131。
④感兴趣者可参阅 Oliver sacks《The Man Who mistake his wife for a hat》,Harper and Row,1985,P.80-84。
⑤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⑥石鸥:《试论教师传授教学内容时的失真现象》,《上海教育科研》1995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5年第10期。
⑦石鸥:《教学话语与师生理解》,《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6年第2期。
标签:教学过程论文;
